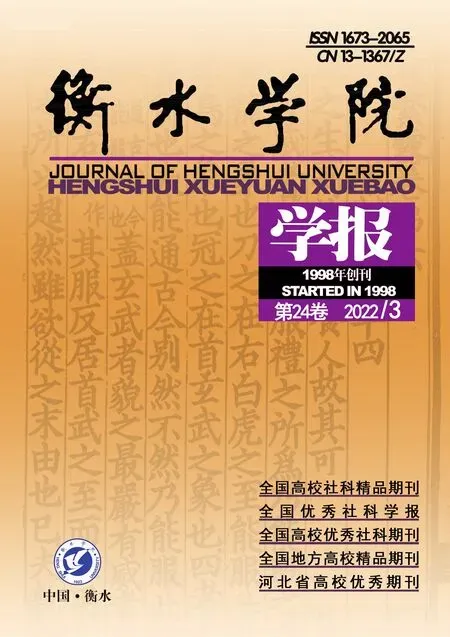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
刘振英
韩非子对荀子礼学思想的通变
刘振英
(邯郸学院 文史学院,河北 邯郸 056005)
战国是中国文化学术史的轴心时代,《荀子》与《韩非子》皆是历经百代淘洗的经典。韩、荀学术虽各具独特品格,但又相互融生。韩非子与李斯俱事荀卿的历史事实,使得韩非子的法术范畴与荀子的礼学思想存在天然的通变关系。韩非子对荀子礼学的“通”体现在三个方面:“得君行道”,学术成为公器与国君的结合;礼学与法术之学都以政治为中心;学术品格独特而鲜明。而其“变”则体现在三个转向上:从王与礼的统一转向人主与法的统一;从纷繁复杂的礼学体系转向简明扼要的法术之学;学术品格从自由、独立转向功利化、依附性。
荀子;韩非子;法术范畴;礼学思想;致用途径;学术品格;通变
先秦诸子是中国古代思想文明史中的辈出精英,共同经历了中国学术史的轴心时代。诸子为什么会“辈出”?除了旧的社会秩序崩溃(礼崩乐坏)、新的社会秩序(大一统)尚处萌芽之中这一社会现状迫切需要学术这一公器来指引之外,以它嚣、魏牟、陈仲、史鰌、墨翟、宋鈃、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为代表的诸家学术思想之间既排斥斗争又相生相融的学术关系也促进了先达辈出、精英共时局面的形成。韩非子与荀子即是其中的一对。韩非子与荀子有着一种天然的思想学术之联系,所谓天然的联系首先取决于二人的关系,司马迁称:“韩非者……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1]2146司马迁所述这一史实,界定了荀子、韩非子与李斯三人存在于相同的时空,且关系密切。不难推断韩非子与李斯在学术思想上以荀子为尊,他们是具有相同学术理想与生活志趣而从不同地域走到一起的同一阶层的人。其次,除了这种相同时空交往关系之外,韩非子与荀子在传世文献上也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宋代理学家朱熹说:“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2]荀子《成相》篇的内容与韩非子学术思想存在着一致性,而且阐述了申不害、韩非子刑名法术之要义:明法制,执赏罚。其三,申不害刑名法术之学是经过韩国政治实践验证了的成功之学。申不害用“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1]2146。这一学术用于政治的成功个案,不仅影响着贵为韩国公子的韩非子,同样也天然影响着荀子。
如何认识韩非子与荀子的关系?韩非子法术范畴怎样对荀子礼学内容进行通变?储昭华曾经从心性范畴探讨过荀子对法家的扬弃①储昭华认为:“与法家的单面之‘人’截然不同,荀子的‘人性’概念其实具有情欲之性与‘心—性’双重维度;法家旨在通过扣押和绑架人的肉身而驱迫、役使臣民,为君主所用,而荀子思想的主流则是主张以礼义来保障和促进人的自然本性的合理实现,进而实现人性的升华。”(参见储昭华《从身心关系视角看荀子对法家的扬弃及其对儒家文化的意义》,《邯郸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第61-67页。),本文则侧重以荀子礼学思想中的“王”与韩非子思想中的“法术”两个范畴为中心,探讨韩非子对荀子礼学的通变。
一、学术公器致用于政治的途径:王、人主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从荀子到韩非子,都把自己学术理想的实现寄托在帝王身上,把王或人主作为践行学术治国的终极途径。故荀子把礼学与王统一起来,韩非子把法与人主统一起来。荀子礼学体系的起点在于《性恶篇》,即人本身天然存在的“好利”“疾恶”之性与“耳目声色”之欲。韩非子法术之学的起点在于《八奸篇》,即群臣玩弄权术的邪恶行为。他们理论起点的不同必然导致学术的灵魂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荀子礼学着眼于全社会各领域与各阶层群体的全面治理,即“王天下”。韩非子着眼于“富国强兵”“存亡绝续”。但其实现学术思想与政治的结合点都落在了国君身上,得君行道是他们思想理论的唯一途径。
荀子以性恶论为其礼学的理论基点,并尝试实现两种改造,即对个体进行修身以化育心性、对社会进行群治以趋向文理。如何将礼学致用于政治,这是由礼的政治属性决定的。何谓礼的政治属性?即礼尊王,王修礼。国君至高无上和唯一的政治权力地位得到认同和尊重,同时,王权和以礼治国又是统一的,修礼是国君的义务和责任。因此,荀子在礼学体系中提出了一个“王”的范畴,他推尊古代圣王,在其理论中“圣王”“先王”“王制”“王霸”成了高频词,其推尊尧舜禹三王多达164处。此外,还谈到了“齐桓”“晋文”“楚庄王”“勾践”“阖闾”等前代杰出帝王。同时国君实现王天下,要“隆礼”“修礼”。荀子指出了王者三个基本素质:“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3]180其中“隆礼敬士”是帝王最重要的素质。隆礼是指国君对待礼的态度,还不足以王天下,“隆礼”的目的是为了“修礼”。只有修礼的国君才能实现王天下。荀子界定“成侯、嗣公”是“聚敛计数之君”,子产是“取民者”,管仲是“为政者”,同时判断聚敛者不及取民者,取民者不及为政者,为政者不及修礼者,最后得出“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3]181的结论。因此“王”是能够在地域、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方面实现统一的国君,在荀子看来“王”是把其礼学思想致用于政治的唯一途径,“礼”与“王”是统一的。
赏功罚罪是以礼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功不赏、无罪不罚”成为荀子提倡的“王者之论”的重要内容。但是以赏罚治天下仅仅实现了“霸”的政治境界。荀子说:“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是知霸道者也。”[3]184-185很显然“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是国君实现霸道的重要手段。那么,荀子的王道如何实现?第一,王者能够做到“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3]186。第二,辅佐王的人能够做到“饰动以礼义,听断以类,明振毫末,举措应变而不穷”[3]187。第三,治理天下的“王者制度”必须符合“道不过三代,法不二后王”[3]187。具体表现为:“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3]187-188荀子的王道即复古之道,也就是以“仁”“义”“礼”为中心的夏殷周三代君臣治理天下之道。
与荀子礼学思想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点相类,韩非子“法术”范畴以“八奸”[4]53-56“十过”[4]59-77为立论之基。“八奸”主要揭示为人臣者八种危害政治的奸术,这些奸术必然使“世主所以壅劫,失其所有”:权臣结好“夫人”“孺子”,“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谓之“在同床”;利用“优笑侏儒,左右近习”,“内事之以金玉玩好,外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谓之“在旁”;利用“侧室公子”“大臣廷吏”与国君的关系,“处约言事,事成则进爵益禄,以劝其心,犯其主”,谓之“父兄”;“尽民力以美宫室台池,重赋敛以饰子女狗马,以娱其主而乱其心,从其所欲,而树私利其间”,谓之“养殃”;“为人臣者散公财以说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劝权誉己,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谓之“民萌”;“求诸侯之辩士,养国中之能说者,使之以语其私。为巧文之言,流行之辞,示之以利势,惧之以患害,施属虚辞以坏其主”,谓之“流行”;“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焉己者必利,不为己者必死,以恐其群臣百姓而行其私”,谓之“威强”;“重赋敛,尽府库,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谓之“四方”。
“十过”主要揭示为人君者十种不良德行,必然带来杀身亡国之祸:1)以司马子反鄢陵之战中的嗜酒不能忠于楚共王的行为为例论述“行小忠,则大忠之贼也”;2)以晋献公假道于虞事论虞公“顾小利,则大利之残也”;3)以楚灵王为申之会事论灵王“行僻自用,无礼诸侯,则亡身之至也”;4)以卫灵公濮水听琴事论“不务听治而好五音,则穷身之事也”;5)以智伯瑶晋阳之战为例论“贪愎喜利,则灭国杀身之本也”;6)以戎王使由余聘于秦事为例论戎王“耽于女乐,不顾国政,则亡国之祸也”;7)以田成子游于海事为例论“离内远游而忽于谏士,则危身之道也”;8)以齐桓公问政于管仲事为例论桓公“过而不听于忠臣,而独行其意,则灭高名为人笑之始也”;9)以秦攻韩之宜阳事论韩君“内不量力,外恃诸侯,则削国之患也”;10)以晋公子重耳出亡过曹事论曹君“国小无礼,不用谏臣,则绝世之势也”。
“八奸”“十过”不只是对前代大臣与国君历史教训的总结,其终极用意是针对母国“弱韩危极”之时,奸猾贼民恣为暴乱,纵横之徒颠倒人主以窃利的社会现实而大声疾呼,更是为其刑名法术之学而张本。
为了矫正“八奸”“十过”,韩非子提出了“法”“二柄”的范畴。国家无常弱无常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奉法者。韩非子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4]31如果国君能够做到“去私曲就公法”“去私行行公法”,那么就能够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4]32。韩非子强调人主与法的统一。人主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尊严也有赖于“法度”,国君能够“审得失”,用“法度之制”管理群臣,那么就“不可欺以诈伪”,能够以“审得失”“有权衡之称”的原则来“听远事”,那么人主“不可欺以天下之轻重”[4]32-33。人主审察百官,为了避免臣下的“饰观”“饰声”“繁辞”带来的蒙蔽,不用目观,不用耳听,不用虑思,而尊奉法度,即“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人主做到了严奉法度,就能够“任势使然”“独制四海”,并且让聪智者“不得用其诈”、险躁者“不得关其佞”、奸邪者“无所依存”,实现“远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辞;势在郎中,不敢蔽善饰非;朝廷群下,直凑单微,不敢相逾越”的政治效果[4]37。所谓“二柄”,是明主导制群臣的代名词,韩非子解释为刑和德。即“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进一步解释:“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4]39在韩非子看来,刑和德是人主管理群臣的最重要的手段,人主无刑德,则必然丧失最高的政治权力和地位,国家也将随之分崩离析,相反只有人主很好地利用刑德“二柄”,做到人主与刑德的统一,整个国家机器才会高效地运转起来。
二、礼、法两个学术范畴的属性
荀子礼的属性内涵极为复杂和丰富,拙作《荀子礼学范畴的理论基点与渊源》梳理了荀子礼学与前代儒家典籍之间的联系,归纳出礼的六种属性:即社会群体中的道德属性;宗族群体中的伦理属性;政治群体中的政治属性;分配体系中的经济属性;人与自然关系中的生物属性;心性改造中的教育属性[5]。前三种属性由来已久,它们适用于尊贤、亲亲、君臣等范围,在荀子之前的儒家传统中已成体系,并有效地管理着尧、舜、禹时期的社会,形成被后世,尤其为宋代知识分子极力推崇的“三代之治”的局面,并成为夏、商、周治理国家的经典政治文献。
后三种属性是荀子在《礼论篇》中详细阐述的观点,礼的经济属性起源于物质资料的分配,无“度量分界”的分配,必然导致人的欲求处于“争则乱,乱则穷”的局面。因此,“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3]409。礼的经济属性在此刻就成为荀子的另一个学术范畴“分”,荀子的“分”即按等级分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意思。荀子认为“分”是“百王之所同”“礼法之枢要”,是礼学的中心原则和灵魂。荀子说:“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止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所同,而礼法之大分也。”[3]253-254社会的各行各业,都要根据对本行业的土地、货物、管理事件进行分配,然后进行本行业的生产劳动。诸侯、三公甚至天子都被纳入这一“分”的大原则之中,享有利益并严守责任和义务。荀子在《礼论篇》中强调“礼之三本”,即“天地”“先祖”“君师”。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3]413“天地”是指人生存于其中的生物界、自然界,是人的衣食住行不竭的源泉。“先祖”是人的群类和种属的族根,没有人种,则无从谈到人类文明,这是礼的生物属性。“三本”之中,荀子君、师并提,与中国古代社会君师合一、政教合一的历史特征相适应。中国上古的国君与王公大臣负责管理国家和教育子民的双重责任,既要以仁义来教育百姓、提高国民素质,又要引导、组织群体团结合作,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因此,在中国的上古社会礼的教育属性与政治属性是统一的。
韩非子法的属性则较为单一,其论述法的范畴始终围绕“存韩”“人主”“爱臣”“扬权”“八奸”“二柄”“南面”“安危”“用人”“内储”“外储”等国家政治的主体和主题来阐述的,国家政治的主体即人主和群臣,国家政治的主题即用人、用法与存亡、安危。因此,韩非子所力倡的法,只具有政治属性,这是他与荀子礼学的根本区别,是韩非子刑名法术之学的精髓。
韩非子《八奸篇》把群臣的奸术分为八类:“一曰在同床……二曰在旁……三曰父兄……四曰养殃……五曰民萌……六曰流行……七曰威强……八曰四方。”[4]53-54韩非子之法对“人主”做了相应的约束和提醒。针对“同床”,他强调“人主”管理后宫要“不行其谒,不使私请”;针对“在旁”,他约束“人主”对左右身边的人要“使其身必责其言,不使益辞”;对于“父兄大臣”,他提醒“人主”要“听其言也必使以罚任于后,不令妄举”;对于“观乐玩好”之“养殃”,他教育“人主”要“必令之有所出,不使擅进擅退,不使群臣虞其意”;对于“民萌”,即“德施”,他强调“人主”要“纵禁财,发坟仓,利于民者,必出于君,不使人臣私其德”;对于“流行”,即“说议”,他主张“人主”对“称誉者,毁疵者”,“必实其能,察其过,不使群臣相为语”;对于“威强”,即“养士”,韩非子明确“人主”要“军旅之功无逾赏,邑斗之勇无赦罪,不使群臣行私财”;对于“四方”,即“诸侯之求索”,他主张“人主”要“法则听之,不法则距之”。以上韩非子关于“八奸”的论述,主要是引导“人主”实现对群臣的治理,根据不同的执政现实来推行自己政治管理的具体措施。与荀子不同,韩非子“法”的范畴主要针对的是大臣。通过管理大臣实现对国家与社会的有效管理。韩非子《八奸篇》所论述的内容即是对以群臣奸行为中心的官吏治理。
同样其《内储》《外储》两篇文章也在谈国君对群臣治理的问题。唐司马贞在《史记索隐》按语中说:“《内储》言明君执术以制臣下,制之在己,故曰‘内’也;《外储》言明君观听臣下之言行,以断其赏罚,赏罚在彼,故曰‘外’也。”[1]2148司马贞指出了韩非子《内储》《外储》的核心在于明君的制臣之术与赏罚之术。韩非子在《内储》篇确切提出开明国君对大臣的管理和考察应注重“七术”与“六微”。所谓“七术”,即“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信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4]210。明君对臣下的治理要兼听广闻,才能听到真实诚恳的建议;明君要树立绝对的威信,不能“爱多寡威”;赏罚分明,薄厚得当,才能树立国君威信,褒扬杰出之士;治理事物要有恒定专一的标准,绝不能让臣下滥竽充数;明君要做到挟智而问,智者千虑,才能做到“众隐皆变”;明君应该“倒错其言,反为其事”,来观察考证他所怀疑的臣下。所谓“六微”,即“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托于似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4]238。国君的权势不能假借给臣下,否则人主就会受到壅蔽;君臣的利益应该一致,否则人臣就会成其私利,失去忠诚;国君应该对“似类事件”明察秋毫,不能水溺不分,错杀大臣;因国害则省其利者,臣害则察其反者;国君应该明断,不要让事情形成“参疑”之势,否则就会危害国家;明君应该明确敌人的目标,否则就会轻易地废置自己的人才。
从对韩非子《八奸》《内储》的内容梳理来看,其法术之学主要围绕明君权谋、制驭官吏之术来展开,政治属性是其唯一的本质属性。
三、《说难》——韩非子对荀子学术品格与信仰的巨变
荀子礼学与韩非子法术之学虽然有大量的相通相融之处,但其两种思想体系具有迥异的学术品格和精神灵魂。在荀子礼学中,荀子之于国君、礼学体系之于国家政体都具有普遍的哲学意味,荀子及其礼学具有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格和人格。其关于王、圣有着明确的界定。
荀子在《解蔽》篇中说:“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恶乎止之?曰:止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法其法以求其统类,以务象效其人。向是而务,士也;类是而几,君子也;知之,圣人也。”[3]481所谓“王也者,尽制者也”,意即国君的职责,在于完善法令制度;所谓“圣也者,尽伦者也”,意即学者的职责,在于完善自我,以成君子。在这段论述中,荀子指出了学者学习的明确目标和由于天分与后天努力而达到的效果和层次。王圣之学是学者读书、思考、立说的根本目标,“王圣之学”是显学、绝学。因此,达到了这个目标,即“学止”,即到了“至足”之境。“士”“君子”“圣人”是荀子对学者不同学习效果和学者层次的描述,学者“以圣王为师”,以“圣王之制”为法度,法其所以为法,向圣王看齐,孜孜以求,努力去做就到了学者研究“圣王之学”的第一层次,即士的层面。按照以上学习的程序和方法坚持不懈地学习就会与圣王相差无几,这个层次是圣王之学的第二层次,即君子的层面。“知之,圣人也”,王先谦解释:知圣王之道者,即掌握了成为圣王之道,并且可能成为圣王的人。因此,荀子所说的圣人是指具有学者属性,并致力于“王圣之学”,且达到了学术至足之境的学者中的精英分子。荀子当之无愧为圣人。
荀子在《劝学》篇中对达到学术“至足”之境的学者的信仰和品格也做了明确的勾勒:“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故诵数以贯之,思索以通之,为其人以处之,除其害者以持养之。使目非是无欲见也,使口非是无欲言也,使心非是无欲虑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是故权利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3]21-23学者追求的显学是圣王之学,至全、至足、至粹是最基本的学术标准,熟读成诵、深刻思考、设身体验、去伪存真是对学者学习的基本要求,其所欲见、欲言、欲虑都归于是,天下之好色、好声、好味集于一身,并且利惠天下万姓。因此,学者就成了君子,其具备了生死以之的学术追求和学术操守:权势和利益不能使之倾倒身躯,众人之力不能使之变移心志,天下之利不能动摇其信仰,然后能坚定所有以应对世界之变。荀子之学仍然坚持了学为君子、学为自己的为学理想。成为“成人”“君子”“圣人”是荀子的为学目标和学术品格。得君行道则为帝王之师,士不遇则或为布衣、或为岩穴之士。这种学术品格和学术理想是自由的、独立的。
与荀子礼学相比,在韩非子法术之学的体系中,韩非之于国君、法术之学之于国家政治都具有了一种功利色彩,其学术理想与学术品格不再独立和自由,而转向功利化、依附性。这在《说难》篇体现得最为真切。以此文字考察,韩非游说国君是不设退路的,这与孔孟荀有着本质的区别。孔孟荀的周游列国都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为原则,君臣各从其志。而韩非子《说难》篇则可以游说任何国君。因此,他提出:“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4]86
游说万乘之君的学者,首先要对帝王性格、心事、执政理想了如指掌,是谓“知所说之心”。然后对症下药,把自己的学术思想或删繁就简或踵事增华,以最适当的形式呈现于帝王面前,并且使之欣然接受。是谓“以吾说当之”。具体来讲,国君“为名高”,游说者“说之以厚利”,国君就会认为游说者品节低下、身份卑贱,游说者必然会被疏远,其学术也会被置之脑后。相反,国君“出于厚利”,而游说者“说之以名高”,国君就会对游说者失去兴趣,也一定不会采纳游说者的建议。还有更复杂的情况,国君口是心非“阴为厚利而显为名高”,游说者“说之以名高”,国君则表面上接受游说者而内心却疏远他;游说者“说之以厚利”,那么国君就会内心接受游说者的言论而拒绝光明正大地接纳他。
因此,韩非子指出,在上述场景下,“谏说谈论之士”尤其要“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他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谏说谈论之士游说国君的“逆顺之机”,他说:“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4]94向国君进谏,顺逆之机,危在其中,顺以招福,逆以制祸。众所周知,韩愈一封《谏迎佛骨表》,批了唐宪宗的“逆鳞”,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一文中用“忠犯人主之怒”[6]一语称赞韩愈的大义、胆略和勇猛。很显然,这与韩非子“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的原则相违背。换句话说,士大夫进谏可以丢掉气节。那么韩非子及其法术之学的独立自由的学术品格,已荡然无存了。
怎样才能游说成功呢?韩非子在《说难》篇中道破了天机:“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4]89什么是“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其意思是指要谏说国君,就要知道国君引以为傲并想要自夸的东西,那么,游说者就要美化它、褒扬它。还要知道国君引以为耻并不愿提及的心事,那么,游说者就要回避它、湮灭它。韩非子非常自信地说:“今以吾言为宰虏,而可以听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夫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以此相持,此说之成也。”[4]92韩非子之意,即以违心巧饰之言先结帝王之欢,以为缓兵之计。然后等待时机“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所谓“旷日离久,而周泽既渥”,是指游说者与国君的关系日益信任、日渐牢固。因此,韩非子的进谏之术抛掉了儒家学术的是非观、荣辱观,也丢掉了游说者的独立自主的人格,而沦为人主的附庸,从而处于次要地位。
结论:韩非子法术之学对荀子礼学的“通变”分别表现在三个方面,其“通”为:“得君行道”,学术成为公器与国君的结合;礼学与法术之学都以政治为中心;学术品格独特而鲜明。其“变”则体现在三个转向上:第一,从王与礼的统一转向人主与法的统一。荀子对国君素质有要求,不仅以君为王,而且引导国君用王的标准改善自己,强调王与礼的统一。韩非子对“人主”则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对“游说人主”的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法与人主的统一。第二,从纷繁复杂的礼学系统转向简明扼要的法术之学。荀子礼学涵盖了政治、经济分配、生物种群、宗族伦理、社会道德、教育等多个领域,而韩非子的法术之学则集中于政治领域,尤其以明君制臣之术为中心。第三,学术品格从自由、独立转向功利化、依附性。荀子与国君的关系是独立的、自由的,而韩非子与国君的关系是从属的、是有主次的。
[1] 司马迁.史记[M].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3255.
[3]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3.
[5] 刘振英.《荀子》礼学范畴的理论基点与渊源[J].河北学刊,2017(4):189-194.
[6] 苏轼.苏东坡全集[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6:372.
The Adaptability of Han Feizi to Xunzi’s Thought on Rites
LIU Zheny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andan University, Handan, Hebei 056005, China)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as the pivotal era of Chinese cultural and academic history. Bothandwere thought to be classics going through hundreds of generations. Although Xun Zi’s and Han Feizi’s academics have their own unique characters relatively, they are integrated into each other. The historical fact that Han Feizi and Lisi both served Xunzi made the category of “fa” and “shu” (generally, referring to the means of calling wind and rain, expelling ghosts and eliminating diseases carried out by immortals, warlocks and witches) of Han Feizi and the thought of ritualism of Xunzi have a natural relationship of accommodation. Han Feizi’s understanding of Xunzi’s theory of rites is embodied in three aspects: “ de jun xing dao ” (It means talented people were trusted by enlightened monarchs to carry out their own political ideas and plans) , indicating academics becom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public tool and the monarch;both the studies of rites and “fa” and “shu” are centered on politics; the academic character is unique and distinct. While its “change” is reflected in three changes:from the unity of kings and rituals to that of human masters and law; from the complicated system of rituals to the concise study of “fa” and “shu”; from free and independent academic character to utilitarian and dependent academic character.
Xunzi; Han Feizi; scope of “fa” and “shu”; ritual thought; application approach; academic character; adaptability
10.3969/j.issn.1673-2065.2022.03.010
刘振英(1971-),男,河北成安人,副教授,文学博士。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项目(20210601040)阶段性成果
B222.6
A
1673-2065(2022)03-0079-06
2021-08-14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