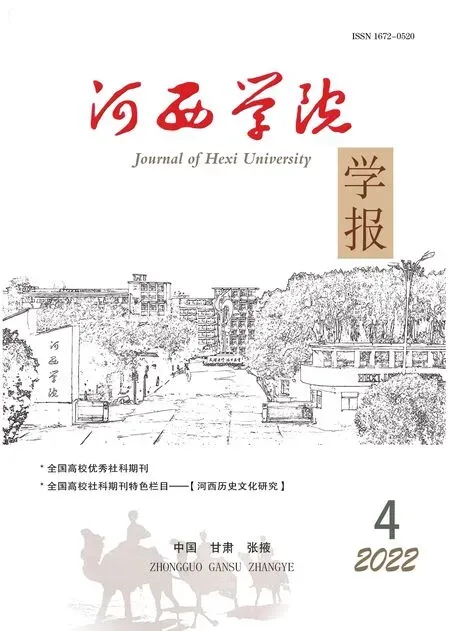贴地书写与诗意追寻
——甘肃“小说八骏”王新军作品论
张 惠 林
(河西学院文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王新军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被评论界誉为“第三代西北小说家”[1]群体当中的代表人物。王新军扎根于农耕与游牧文化交汇之地的河西走廊,熟悉这片土地黄沙漫漫、鹰击长空的别致景色,也用心灵去感知这个别样的世界。他的大部分作品将河西走廊的村庄、草原作为叙述的源泉,一方面对其进行了现实批判,另一方面又进行着诗意叙述。基于此,他的作品也呈现出二重建构:在对人性的关照和关怀中,既有对现实的批判与思考,又有对理想精神世界的诗意追寻。
一
评论家曾说:“八十年代的文化乡土小说虽然拓宽了乡土世界的表现领域,但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乡土与现实乡土的关系割裂,并曾一度导致人们对寻根派创作脱离现实生活的理论责难。”[2]这种状态的产生与作家生存境遇的变化有关:八十年代涌现出的大批乡土小说作家现大都已进城,他们熟悉的是八十年代的农村生活,而对九十年代之后的农村已疏远和隔膜了,面对变幻莫测的农村现实,他们难以把握,因此所描绘的乡村就依然是停留在记忆中。而王新军是个例外,他出生于甘肃玉门,并且一直生活于此,他的乡村经验和基层工作经历使他对现实的乡村具有更真实的感受,也更容易走进乡村及其中人们的内心深处。作为一位“在场”的作家,他始终关注农村、农民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存状况,真实描绘了正在行进中的西部乡村的现实生活。学者赵园曾言:“作为艺术创造条件的内省体验、自我人生省察,无疑构成了作家乡土审视的内在视野。他们写的‘乡土’,更是一种‘内在现实’,属于他们个人的一份‘现实’,乡土既内在于‘我’的生命,写乡土作为一种自我生命体验的方式,所能达到的深度是难以预测的”。[3]王新军就是用近乎透明的文字和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讲述着西部乡村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将西部的自然景观与民俗风情统一于作品中,将自己的乡村体验熔铸其中,展现着西部文化与现实生活的意蕴和价值。
王新军的作品首先写出了西部乡村及乡村里人的内外生存处境。如《甘草滩》《麻黄滩》中的沙尘暴、泥石流,带走了农人们的生命,也带走了他们对生活的希望和念想。而沙洼洼村是王新军作品的主要叙述对象,如在《闲话沙洼洼》中,这个位于中国西北内陆的小村庄,四面是灰黄的野滩、沙梁,尤其是刮个不停的白毛风和沙尘,春天里会将刚刚发芽的幼苗吹死或湮没,冬天里会将人吹得灰头土脸,猝不及防。作者表面上呈现的是自然环境之恶,但在中国现代乡土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下,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对现实和农民精神的批判。作品通过“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数十年来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巨大的变化”这样的描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本身:正是农民急功近利、贪欲金钱,才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生存的困顿。即使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等依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作者带着复杂的情绪既为他们的生存境遇深深的担忧,也批判他们的封闭、保守、落后。比如作者这样来叙述一场关于风的故事:当带着沙粒的风从冬天吹到春天,这里的人们并不因此而感到稀奇,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吹风的日子,而从电视上看见沙尘暴居然吹到北京时,他们把肚子都笑疼了。这样的叙述中有着一种深沉而无奈的忧伤——沙洼洼村人对酷烈生存环境习惯的背后,固然是一种坚韧,但也是一种对现实屈服的无奈,更不乏阿Q 式的妄自菲薄和他们精神世界的沉滞、荒芜。
对人性的透视是文学永远的任务,王新军的作品也正是通过对人精神和灵魂的关注表达着对脆弱、复杂人性的透视。《树皮面具》中的丁方,因为自家的树被别人剥掉了皮而愤愤不平,为寻求心里平衡,便半夜里将全村人各家门前同数的树剥了树皮,如此一来,他走在村街上的时候,感觉“心里的伤口已经完全愈合了,仿佛就是他昨天晚上割下的那一块块树皮,填补了他心里骤然生出的那个空洞”。这是作者对人性卑污与脆弱的鞭挞。在《两条狗》中,老方家的花狗和老吕家的“四眼”在一个春天的自由之夜因“爱情”酿造了新的生命,却促使两家的主人将原有的芥蒂升华成仇恨:当花狗产下八只“四眼”的翻版后,原本还兴奋着的老方又迅速将它们倒在了严冬的河坝里冻死,最后甚至将花狗也吊死在树上,人的嫌隙和仇恨就这样牵扯到了无辜的动物身上。小说表面是在写狗,而内里将人性当中的狭隘、自私等阴暗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两个男人和两头毛驴》中,娄大明和史红旗并没有什么利益冲突,只因为一个女人便心生怨恨,致使无辜的毛驴成为他们内心较量的牺牲品。《两窝鸡》《两窝狗》中,主人公都将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无奈和无助转化成了愚昧和狡黠。《八墩湖》中,孙福在目睹举贵和寡妇李月兰亲密后,四处宣扬,又向村长及月兰公公告密。作品将光棍孙福内心极度的孤独和他的自私、变态、精神世界的贫乏都揭示的淋漓尽致。在这样的作品中,王新军倾注众多笔墨去叙述西部的环境、村庄和农民的内外生存状态,不仅将西部的现实生活跃然纸上,更是深入到地方与人的深层文化心理,对西部乡村的人情冷暖、人性的复杂等进行了展示与深入的思考。
王新军小说在描绘处于沙漠戈壁边缘的这片土地时,也通过呈现生存在这里的乡民们凡俗生活中的沉重和他们的精神痼疾,冷峻地审视和挖掘了其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八墩湖》中,为了延续子嗣,三爷不顾伦理纲常,要与守寡的儿媳过。《艾草》中,尕奶奶前三胎都是丫头,分别起名换换、招娣、迎弟,直到儿子金贵出生,才觉得自己的日月囫囵了。这种子嗣观念和重男轻女的思想虽多受人诟病,但作者将其放置到自然环境恶劣、不得不依靠孔武有力的男性支撑才能更好生存的西部乡村,使得它的存留就成了必然。因此,在西北乡村,它也就成了现代化无论如何也化不了的痼疾,因为它关涉生存。王新军用他貌似温情的笔锋,犀利地写出了这种悲情,也揭示了其深厚的历史与现实生长土壤。尤其是长篇作品《厚街》,作者将其放在乡土文学的“向城求生”这个向度上,以近乎荒诞的故事展示了淳朴的西北乡村女孩王春麦在东莞的陷落。而她的陷落不仅仅源于富足的欧阳家族用钱和荣誉一步步的推动,更主要的是源于这个乡村女孩欲望的驱使。作者表面上把这种陷落叙述得温情优雅,但通过将王春麦在偏远西部乡村“厚街”与现代都市“厚街”不同生活的对比和展现,表达了他对都市文化、西部现代化对人性改变等的思考,也传达出了他对西部乡村和乡村里人未来的担忧。
二
河西走廊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相融之地,其偏远的地理位置使之有着相对迟缓古朴的文化氛围,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曾经生活过如匈奴、月氏、乌孙等许多游牧色彩相当浓厚的少数民族,留下了浓郁的游牧文化色彩。直到今天,这里依然有裕固、藏、蒙古等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当然,随着时代变迁,在一系列相关政策日渐稳定与成熟之后,“逐水草而居”的范围已固定在相对稳定的区域之内,曾经的举族迁徙、流动不居等特色已大大减弱,他们已开始了半定居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其“游”的特色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倒是在现代化的进逼之下,其内蕴已转化为和农耕者相类似的家园故土情结。自认为有着游牧因子的王新军就有着这样的体验,他在《八个家》的题记中写到:“我无法控制我柔弱的忧伤,草原在消失,我的八个家已将在这场不知不觉的灾难中一去不返,伟大的神啊,你怅然的看着这片土地,你不知道你广大的子民将去向何方。”[4]他创作的以“八个家”为主要关照对象的“草原群山系列”小说,就是在对现代化弊端的审视中对草原生活场景进行的诗意叙述,通过对这种带有前现代文明特质的游牧文明的怀恋,表达了对游牧精神的诗意追寻。
“八个家”是祁连山麓河西走廊上一片草原的名字,也是王新军的精神家园,它是一个伴随着神秘宗教、和谐自然的理想世界:海子湖旁的俄博,微风中飘动的经幡和哈达,俄博周围与祭祀有关的羊头、牛头、羊尾、牛尾,牧民嘴里念着的经文和手里闪闪发亮的金色转经筒,老人吟唱的神秘的“劝奶调”等,既有着宗教的神秘,更体现了游牧民族心灵深处对自然的依恋、对生命的敬畏等。在他笔下,草原上的人不仅仅以他们的主体地位管治着草原,同时也将这种管治转化成爱的力量来爱护草原上的一切生灵。在《八个家》中,草原上的撵狼事件就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包容等。牧民用快马撵狼这种古老的方式来遏制草原上渐渐增多的狼祸,而不是赶尽杀绝。在撵狼活动结束之后,他们又会围着篝火用歌声超度狼嘴下毙命的生灵。无比辽阔的草原同时也孕育了人宽阔的胸怀,启迪着他们对人生和生命的认识。当巴图鲁因为马肚带被割而摔瘫痪时,阿吉娜没有放弃爱情,而是无怨无悔地照顾他;阿吉娜的父亲为了给巴图鲁治病准备卖掉所有的牛羊;当小旦旦格怀着无比内疚的心情向巴图鲁说出是她割断马肚带时,摔瘫痪的巴图鲁原谅了她;巴图鲁不愿拖累阿吉娜一家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受他托付的好友乌克鲁勇敢承担起了照顾阿吉娜的责任……在这里,每个人都如这承载万物的广阔草原,不计个人得失,始终以最美、最广的胸怀与他人相处。王新军用诗意的笔触写出了草原游牧文化滋养之下草原人的爱情、友情、亲情,在这里,忠诚、信义、责任远胜于利益、仇恨。八个家是一个自足、和谐而诗意的世界。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在静与动、点与面、放任与管理等的有机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更大程度上带着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特点。因此,游牧高地不是思想的荒原和沙漠,其思想和文化深处渗透着对自由精神的向往与追寻,王新军小说便展现了这样的追寻。例如在《海子湖》中作者写道:“至于什么时候搬家,那还是要思量一番的。思量归思量,该搬走的时候,大家也是五六只驮牛驮起家当来纷纷搬走,从冬窝子到夏牧场,翻过一个山,再翻过一个山。”这种逐水草而居的动态生产、生活方式,使得牧民们不被约束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他们的生存空间相对自由,因此,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里也就有对自由的不羁追求。在《醉汉包布克》中,王新军用大量笔墨将西部草原人追求自由的精神特征进行了细致的描绘:在祁连山深处,当夏天来临时,男人们骑着自己的骏马,在蓝天与白云、青草与湖水、牛羊与歌声等的陪伴下,跟随着长风、落日,穿越过一片片草原,来宣泄他们胸中天长日久积蓄的豪情。伴着疲惫和憔悴,他们一路向西,一路高歌,把忧伤散落在风中,有时也会把爱情播撒在某个敞开的帐篷中。在这样的人和景的描绘中,是作者对西部游牧精神真谛的深刻理解和诗意表达。对生命原本应有的自由、自在状态的追求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主题之一,庄子、李白、吴承恩等笔下,都曾表达过对生命自由境界的向往。随着现代社会的来临,人类的自由自在状态日渐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作家们再次通过对自由意识追寻的书写,来表现着现代文明的异化与反异化的思考。王新军笔下对牧人们这种自由状态的诗意构建,是当下作家们反抗异化的表现,也是他对中国文学中古老主题的延续和遥远的回应,更是在当代社会里对家园体验与思考的延伸和深入。
除了这些草原系列作品,王新军在对传统乡土社会的描绘中也渗透着一种诗意,就如雷达所说:“王新军在独特的生存环境中却蕴含出了别一种具有西部风韵的抒情性,你在他的小说中可同样体味到天地人融为一体的那种和谐境界,但不同的是,王新军给农耕诗意中滴进了一滴游牧文明的,含着沙尘味儿的粗犷颜料。”[5]就如王新军在《闲话沙洼洼》里写道的:“每到瓜熟的季节,沙洼娃总是要让人家把最好的瓜拉走,尽管那样,他们还要一再自责说,自己没把瓜种好。其实,沙洼娃的西瓜,上电视也不下四五回了。他们说这些冬天就送定金的人,都是实在人,不给他们好瓜,我们就不实在了,不实在了,还怎么活人。”作者写出了西部农民让人感动的朴实与善良。海德格尔曾提出人类“诗意地栖居”的话题,认为“诗意地栖居”意味着返回到本源的近旁[6]。返回本源不仅意味着回归自然,同时也意味着天然、质朴人性的回归。
在偏远地域里靠土而生的西部农民,他们生存在让自己心灵踏实和自在的大地上,远离了欲望,而多了一份对生活的自足和对他人的友善。《乡村爱情》《夜深人静》等作品里的桂桂、二宝、红梅等普通农人,在并不是太富足的生活中,没有争吵,也没有贪欲,有的是对自己淳朴生活和婚姻的自足,和永远浓浓的夫妻情分。在《白露过后是秋分》中,作者用诗意又忧伤的笔写出了五成子对花儿终其一生的痴情。在《农民》中,李玉山看着场上的粮食,想着自己勤劳质朴的女人和天真可爱的儿子,内心涌出的是实实在在的自在和自足。他们这种心灵的惬意状态,不是启蒙意识下所认为的不思进取或目光短浅,而是千百年来静态的乡村农业文明哺育下的自然、质朴人性与心灵的体现。王新军在这样的构筑和表达中,有意略去了现代社会勾起的人的欲望和焦灼,也不刻意去构筑生活的戏剧性矛盾,而是将乡村包含在一个圆圈内,写出了其内核里的一种静态和常态,给人家园般的温暖和对它深深的依恋。就如评论家李建军所说:“王新军的小说有乔治桑的温暖的爱意,有汪曾祺小说的浓厚的人情味,朴实中富含着诗意,平静中包蕴着热烈,将爱情及其他形式的伦理亲情,表现得感人至深,别有一种打动人心的伦理内容和道德力量。”[7]当然,他这样的构筑和表达无形中也就与圈外的世界形成一种对照,从而有了作者对现代化对人性异化的审视和思考。
结语
农民、土地、村庄、家园等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永恒的母题,在它们的内涵被不断延续、扩展的过程中,对乡土中国的叙事已日益发展成为一棵根深叶茂的文学大树,但随着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人认为乡土这块最强大的精神资源渐趋萎缩了。而在王新军笔下,他对乡村的关注一方面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对更加丰繁复杂的乡村现实进行着实在的呈现,也对其做着批判。另一方面,他也将乡愁根植其中,在西部这片融游牧与乡土气息的特殊土地上,以积极的心态,用“诗意”去书写和诠释这片土地,进而表达他对理想的追寻。通过他的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乡土这块文学资源并没有萎缩,作家们其实已经从多侧面将其呈现出来,不仅扩大了它原有的范畴,而且也丰富了它的表现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