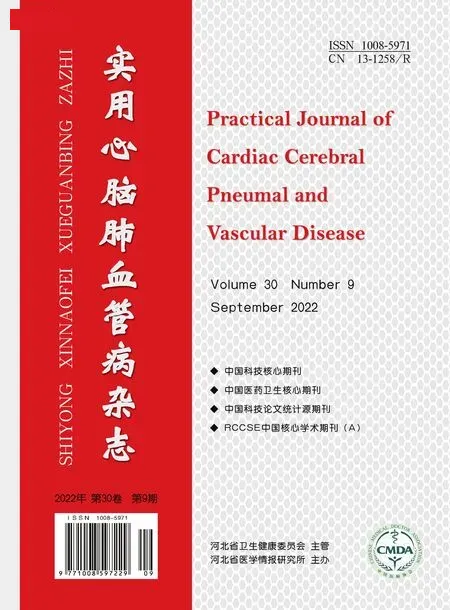肺表面活性蛋白D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何响,孙泽蕊,石雪峰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是一种常见的以气流受限持续存在和相应的呼吸系统症状为特征的疾病[1],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重大经济、社会负担。据统计,我国40岁以上人群COPD患病率达13.7%[2]。目前,COPD的发病机制尚不完全清楚,研究认为可能是由于吸烟等多种环境因素与免疫、基因等自身因素长期相互作用所致[1]。目前COPD的诊断及病情严重程度评估主要依靠肺功能检查,但其具有一定局限性,如轻度COPD患者肺功能检查结果经常发生变化,而重度COPD及急性加重期患者无法完成肺功能检查。此外,现有的治疗方法无法降低患者死亡率,也不能实质性地改变患者肺功能的下降速度。因此,迫切需要生物学标志物来指导COPD患者的诊治,并提高药物开发成功的可能性。肺表面活性蛋白D(pulmonary surfactant protein D,SP-D)是一种主要由肺泡Ⅱ型细胞合成和分泌的亲水性蛋白,属于胶原C型凝集素家族的一员,在肺稳态和肺免疫功能维持中具有关键作用[3-5]。SP-D参与了包括COPD在内的多种呼吸系统疾病的病理生理过程[6],且其在COPD病情评估、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可能为COPD的潜在生物学标志物,其在COPD发病中的重要作用可能为新药的研发提供重要依据[7-9]。本文旨在分析SP-D与COPD的关系,以期为COPD的诊治提供参考依据。
1 SP-D的分布及生物学结构
SP-D首先在呼吸道被检测出来,其在肺泡中表达水平较高,在肺外组织中也有表达,包括胃肠黏膜、角膜、泌尿生殖道表面、大脑、心脏、肾脏、脾脏、唾液腺、汗腺等,但表达水平较低[10]。SP-D单体包含355个氨基酸(43 kDa),由4个区域〔分别是C-末端碳水化合物识别域(carbohydrate recognition domain,CRD)、α-螺旋结构、胶原结构域和N-末端结构域)〕构成1个三聚体,4个三聚体通过氨基末端结构域的相互作用,齐聚成十字形的十二聚体结构,从而形成SP-D的四级结构[11]。SP-D可通过CRD以钙依赖性方式识别并结合细菌、病毒以及真菌等多种微生物或病原体表面的碳水化合物结构,从而起清除作用[12]。
2 SP-D的功能
2.1 调节炎症反应 SP-D通过与不同受体结合,可以发挥双重调节作用,即抑制或促进炎症递质的产生。SP-D由球状头部区域和胶原尾部区域构成,在生理状态下,球状头部区域通过CRD与细胞受体抑制性信号调节蛋白α(signal regulatory protein-α,SIRP-α)结合,抑制p38信号转导,阻止单核吞噬细胞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κB,NF-κB)的激活和炎性因子的分泌,进而抑制炎症反应[13]。相反,当机体受到某些氧化应激时,如细菌、真菌、病毒等的感染,SP-D通过CRD识别微生物表面的碳水化合物结构,破坏自身十二聚体结构,变为三聚体或单体,暴露胶原尾部区域,而后尾部胶原结构域通过与钙网蛋白/CD91结合,磷酸化p38,活化NF-κB,从而促进炎症反应,消除病原体[13]。GUO等[14]认为,SP-D可能通过其生化修饰作用与钙网蛋白/CD91相互作用的;S-亚硝硫醇SP-D(S-nitrosothiol pulmonary surfactant protein D,SNO-SP-D)是由SP-D中的N-末端半胱氨酸亚硝化形成的,而不是天然的SP-D,其对巨噬细胞具有趋化作用,可诱导下游的p38磷酸化,因此推测在病理状态下,SP-D通过钙网蛋白/CD91介导的信号启动炎症反应,而在生理状态下其通过SIRP-α信号开启抗炎通路。
2.2 调节免疫反应 SP-D被认为是先天免疫的重要调节剂,其通过调节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介素1α(interleukin-1α,IL-1α)、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及干扰素γ(interferon-γ,IFN-γ)等细胞因子的分泌,同时通过与巨噬细胞、单核细胞、中性粒细胞等多种免疫细胞相互作用而调节免疫反应[15]。免疫球蛋白(immune globulin,Ig)有两个功能区,即抗原结合片段(fragment of antigen binding,Fab)和可结晶片段(fragment crystallizable,Fc),其中Fab可识别细菌和病毒等抗原,Fc可识别集合素和补体等免疫细胞。而先天性免疫凝集素SP-D可以直接结合Ig,将天然免疫途径和获得性免疫途径联系起来,已知SP-D可以结合不同类型的Ig,包括IgG、IgM、IgE和分泌型IgA,但不与血清IgA结合,如SP-D以钙依赖的方式识别IgG的Fc和Fab,进而聚集免疫复合物,并增强其吞噬作用[16-17]。
2.3 清除凋亡细胞 快速清除凋亡细胞,被认为是维持免疫稳态和炎症消退的重要机制[18]。随着细胞凋亡的进展,质膜完整性丧失,导致潜在毒性细胞内容物泄漏,并在邻近细胞中引发炎症反应[19]。研究发现,敲除SP-D基因后小鼠凋亡和坏死的肺泡巨噬细胞数量增加了5~10倍,而使用重组人SP-D片段(recombinant fragments of human SP-D,rfhSP-D)治疗可以减少小鼠巨噬细胞活化及凋亡、坏死的巨噬细胞数量[20],PILECKI等[21]研究亦得出相似结果,提示凋亡细胞的清除需要SP-D的参与。CLARK等[20]还在体外研究中发现,SP-D重组片段优先与凋亡、坏死的细胞结合。这些研究揭示了SP-D在通过控制凋亡细胞数量来调节肺部炎症中的关键作用。
还有研究显示,SP-D可以结合并促进烟曲霉、屋尘螨和各种类型的花粉变应原的摄取和清除[22]。总之,SP-D可以调节炎症反应及免疫反应,还可以清除凋亡细胞、过敏原和其他有害颗粒,对维持肺内环境的稳定有着重要的作用。
3 SP-D在COPD患者中的表达水平及意义
研究发现,与对照组相比,COPD稳定期患者血清SP-D水平升高[23]。有研究者通过测定COPD急性加重期及稳定期患者血清SP-D水平发现,COPD急性加重期患者血清SP-D水平升高较COPD稳定期患者更为明显,且与肺功能呈负相关,提示血清SP-D水平可以反映COPD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8,24-29]。一项大样本量的研究证明了COPD患者血清高水平SP-D与病情加重的风险增加相关,且患者经皮质类固醇治疗后血清SP-D水平降低,提示血清SP-D水平可以作为COPD急性加重风险的评估指标[30]。研究显示,血清SP-D水平可以预测COPD患者急诊入院频率与自身健康状况[31]。STOCKLEY等[32]发现,血清SP-D水平升高与COPD病情恶化、肺气肿进展和死亡率相关,提出SP-D是一种重要的COPD候选生物标志物。但也有研究认为血清SP-D水平与肺功能无相关性[33-34]。造成以上结果的差异可能与研究样本量、检测试剂、纳入标准、COPD患者严重程度及异质性等有关。
有研究发现,COPD患者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较对照组明显下降[35]。WINKLER等[36]研究显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COPD患者血清SP-D水平明显升高,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明显降低。李小波等[37]进一步研究发现,支气管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与吸烟状态以及患者气流受限程度有关。TKACOVA等[38]研究提示,COPD患者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和血清中SP-D水平的比值与气流受限程度呈负相关,提示血清及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对COPD病情监测有重要意义。目前研究认为,COPD患者肺泡灌洗液中SP-D水平降低,血清SP-D水平升高可能与SP-D由肺泡转移到血清中有关,具体为:COPD患者肺泡上皮细胞有不同程度的损伤,肺泡间隔被破坏,肺部炎症使血管通透性增加;另外,吸烟可破坏SP-D四级结构,使其降解为小分子物质,从肺部更容易进入血液循环,导致SP-D从肺部向血液中转运增加[36,39]。
此外,高莹等[40]研究表明,COPD患者呼气冷凝物中SP-D水平与气流受限程度具有相关性,认为呼气冷凝物检测可以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方法来评估COPD患者气流受限程度,这与LIN等[41]研究结果一致,提示SP-D水平可作为判断COPD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一项敏感指标。
综上,SP-D可以在血液、肺泡灌洗液、呼气冷凝物中被检出,其水平在COPD严重程度评估、治疗及预后评估等方面具有一定指导意义。
4 SP-D基因多态性与COPD的关联性
人类SP-D基因定位在10q22.2~q23.1染色体上,其染色体内存在着多个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位点,并且某些位点的多态性与多种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有关[6]。研究表明,在不同人群中,SP-D基因的SNP与COPD存在关联性[42],其中研究较多的是rs2243639、rs721917、rs3088308位点。
2001年GUO等[43]首次在墨西哥人群中进行了SP-D基因多态性与COPD遗传关联性的研究,结果发现,SP-D基因rs721917位点和rs2243639位点的基因型与COPD易感性无关。有研究显示,巴基斯坦[44]、我国[45]人群的rs2243639位点与COPD易感性无关,而有研究者在埃及人群[46]中发现rs2243639位点与COPD明显相关。FAKIH等[47]研究发现,rs721917位点与黎巴嫩人群COPD发生风险无明显相关性。FOREMAN等[48]在欧洲多中心进行的预测替代终点的COPD纵向队列研究(the Evaluation of COPD Longitudinally to Identify Predictive Surrogate Endpoints,ECLIPSE)和挪威卑尔根队列研究证明,rs721917位点多态性与COPD发病风险无关,而在美国国家肺气肿治疗试验-标准老龄化研究的样本中发现rs721917位点与COPD明显相关。ISHII等[49]证实了rs721917位点等位基因C与日本人群COPD的发病风险有关。SHAKOORI等[44]对巴基斯坦人群进行研究发现,rs721917位点等位基因C与血清SP-D水平降低有关,rs721917位点T/T基因型与COPD的发病风险升高有关。我国研究亦显示,rs721917位点与COPD易感性相关[50-51],但有学者认为等位基因T突变可能是COPD的危险基因[50],而有学者认为等位基因C突变可能是COPD的危险因素[51]。还有研究通过Meta分析发现,在亚洲人群中,rs721917位点等位基因T与COPD发病风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52]。另外,有研究者首次在巴基斯坦人群中发现,rs3088308位点等位基因A与COPD患者SP-D表达水平降低有关[44]。还有研究发现,rs3088308位点等位基因T与吸烟导致的肺功能损伤呈负相关,并且可能是吸烟者发展为COPD的一个危险因素[53]。而JOHANSSON等[54]在丹麦双胞胎人群中并未发现rs3088308位点多态性与吸烟导致的肺功能损伤有明显相关性。
综上,SP-D基因多态性与COPD易感性相关,这些关联有助于预测COPD发病风险,进行早期干预,还可以为COPD更精确的靶向治疗提供证据。但目前国内外研究结果仍存在差异,其原因可能与环境因素、遗传背景、纳入标准、其他基因的干扰、样本量及研究方法等有关。
5 外源性重组SP-D治疗COPD的相关研究
有研究发现,SP-D可能在COPD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靶向敲除SP-D基因后小鼠肺泡巨噬细胞大量被激活,表面活性物质结构发生改变,过氧化氢和基质金属蛋白酶等氧化物质增加,发生自发性肺气肿,而这种情况可以使用rfhSP-D来逆转[20]。rfhSP-D是人肺中天然存在的SP-D的重组形式,其在结构上与天然的SP-D有一定差异,其缺少大部分的胶原样结构域,只有CRD和α-螺旋结构、胶原结构域的一个短区域(8个三联体)[55]。虽然研究显示rfhSP-D能形成功能性三聚体单位,具有糖结合活性和SP-D的一些抗炎特性,但只有十二聚体才能介导SP-D的一些功能,如聚集病原体和调节肺表面活性物质的动态平衡,而三聚体无法执行这些功能[56]。由于SP-D结构的复杂性、功能上的特性,大规模生产出全长重组SP-D仍有困难。此外,在生产、储存和给药过程中保持蛋白质结构、寡聚形式的分布、稳定性和生物活性也极为重要。
目前采用外源性重组SP-D治疗COPD的研究只局限于动物模型,尚无相关临床研究,应进一步明确外源性重组SP-D治疗COPD的具体机制,为临床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此外,如何把基础研究的发现转化为临床研究仍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6 小结及展望
综上所述,SP-D作为一种肺特异性蛋白,具有消灭病原体、增强免疫功能、清除凋亡细胞、减轻肺损伤等功能,在呼吸道疾病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SP-D表达水平与COPD的严重程度和病情恶化情况具有密切关联,这可以用来辅助指导COPD的诊疗。SP-D基因多态性与COPD易感性相关,但国内外研究结果存在差异,未来仍需要大样本量、多中心的研究进一步验证。此外,关于外源性重组SP-D治疗COPD,尽管基础研究发现其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但目前尚缺乏相关临床数据支持。未来应进一步探讨SP-D在COPD发病过程中的具体作用机制,以期为COPD的诊治提供更精确的方向。
作者贡献:何响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撰写论文,进行论文的修订;石雪峰进行文章的可行性分析,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孙泽蕊进行文献/资料收集、整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