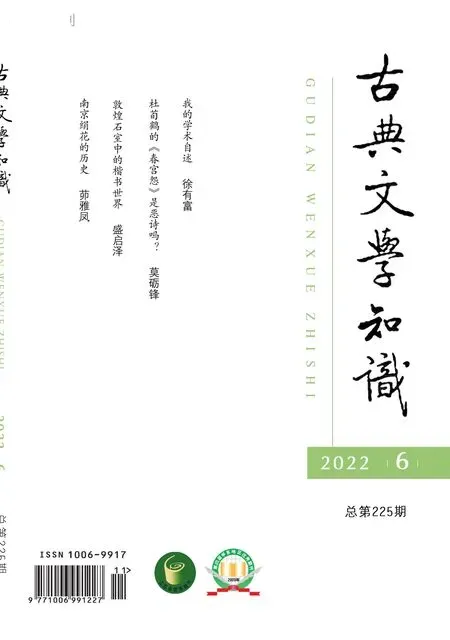唐代的鬼诗(下)
陈尚君
五、 幕客抒愤借鬼言
唐代中期以后,士人进入仕途,很长一段经历都在幕府中度过,个人前途与府主之前途大有关系。如果府主出将入相,功存鼎铭,幕客今后自然也机会多多。如果相反呢?那就可能永无出头之日。幕客心积怨愤,也无处表达,那就借鬼泄愤吧。

唐代门客为故主鸣冤而托以鬼言者,还有《桂苑笔谈》所载甘露寺鬼事,说天复二年(902)夏夜,润州甘露寺有四人饮酒谈诗。其中朱衣者唏嘘低头,感叹“时世命也,知复何为”,另三人一边赏赞其诗,一边指陈他的失政。最后有人建议,可否“各征曩日临危一言,以代丝竹,自吟自送”,众人同意,其中三人所吟,皆南朝叛乱被杀者临终之诗,朱衣者吟:“握里龙蛇纸上鸾,逡巡千幅不将难。顾云已往罗隐耄,更有何人逞笔端?”则为唐末事。所叙较晦涩,所幸明末胡震亨在《唐音统签》卷九九七分析此节,认为作者“常游骈幕府,不得志,与同幕顾云、罗隐不叶,故曲致讪口”,朱衣者即指高骈,诸鬼赏其诗而斥责他之失政,亦门人寄意之作也。
六、 人鬼殊途情未了
男女情爱,夫妻相守,青梅竹马,白首相对,自是历来诗人歌咏不尽之主题。然而爱河曲折,生命短暂,无端灾病,意外变故,都会阻隔彼此之情感。文人写来,则坚信爱情永恒,生死无隔,即分阴阳,也难阻情愫。
韦璜,《太平广记》卷三三七引《广异记》载她为潞城县令周混妻,“容色妍丽,性多黠惠”,美丽而有心机。常与其嫂、其姊相约:“若有先死,幽冥之事,期以相报。”生二女后,肃宗乾元中卒,月余后托梦,述到阴间后,因妆梳之能,太山府君嫁女时让她为其女梳妆,因此有特殊优渥。赠其嫂、其姊诗各一首外,还赠夫诗二首,其一云:“不得长相守,青春夭蕣华。旧游今永已,泉路却为家。”是遗憾年轻先逝,不能长久相守,回顾夫妻以往曾游之处,再也无法实现了,现在只能以黄泉为家。其二云:“早知离别切人心,悔作从来恩爱深。黄泉冥寞虽长逝,白日屏帷还重寻。”以往平常而恩爱,生离死别后才真正体会到彼此情深恩重。死后生活清冷寂寞,魂魄重回夫妻共同生活之所在,仍然充满眷恋之情。作者自称“泉台客人韦璜”,当然是执笔写此故事者戴孚之笔墨,传达的正是虽分阴阳,难阻恩爱的情感。
《太平广记》卷三三二《通幽记》:晋昌人唐晅,娶张氏小女为妻,留之卫南庄。开元十八年(730),晅因故入洛,累月不得归,梦其妻隔花泣,俄而窥井笑,解者认为“隔花泣者,颜随风谢;窥井笑者,喜于泉路”,即其妻已亡。过了数日,果然得到其妻凶信,乃悲恸倍常。几年后方回卫南,追怀陈迹,感而赋诗:“寝室悲长簟,妆楼泣镜台。独悲桃李节,不共夜泉开。魂兮若有感,仿佛梦中来。”“常时华堂静,笑语度更筹。恍惚人事改,冥寞委荒丘。阳原歌《薤露》,阴壑悼藏舟。清夜妆台月,空想画眉愁。”前一首写回到夫妻旧栖之地,看到妻子梳妆的镜台,想起往事,不胜悲伤,期盼亡妻魂灵有感,能够托梦寄情。第二首想到往日华堂,欢笑度时,如今一切都变了,我老了,你也久在荒丘,寂寞凄凉。夜深人静,夫妻画眉恩爱的旧事,仍然如在眼前。唐晅如此深情表达,据说感动得张氏从阴间现身,初有泣声渐近,唐晅虽怀惧怕,祈祷娘子之灵若能相见一叙,“勿以幽冥隔碍宿昔之爱”,即彼此之爱绝不以阴阳两界的阻隔而相分。其妻答以:“闻君悲吟相念,虽处阴冥,实所恻怆。愧君诚心,不以沉魂可弃,每所记念,是以此夕与君相闻。”你对我的真心诚意,我虽身在阴间,也被感动到了。你没有忘记我这已经死亡多年的人,因此今夜特来与你相见。小说其后彼此还有大量私密情话的交谈,临别,唐晅赠妻诗:“峄阳桐半死,延津剑已沉。如何宿昔内,空负百年心。”夫妻本是一体,现在阴阳相隔,如峄阳桐树一半已死,延津双剑其一已沉。桐可做琴,喻夫妻之琴瑟好合,延津剑合,喻夫妻之终为一体。百年好合,是夫妻共同的愿望,可是现在则无限伤心。其妻也答诗二首:“不分殊幽显,那堪异古今。阴阳途自隔,聚散两难心。”“兰阶兔月斜,银烛半含花。自怜长夜客,泉路以为家。”不分是唐人俗语,没料到之意。幽是阴间,显是人世。第一首诗说死生成古今,阴阳隔人世,相距遥远,聚散都为难,即眷恋人世,难忘真情,虽隔幽明,此心不变。第二首说深夜与夫相见,眼前之景虽然落寞,仍然值得牵挂。冥间漫漫长夜,我只能一个人独自面对。言下之意,虽然独居泉路,也会珍惜你的真情。其间还有一细节,唐晅并不知妻能诗,妻答:“文词素慕,虑君嫌猜而不为,言志之事,今夕何妨!”一直喜欢文词,怕达不到夫君的要求而不为,现在直诉心声,也就不计较了。据说这一故事来自唐晅本人的手记,即他记录与亡妻的幽明交流,确实是唐人版的人鬼情未了的记录。
还有苏检的故事。《太平广记》卷二七一引《闻奇录》载,苏检登第后,归吴省家。行至同州澄城县,醉后,梦其妻取笔砚,书红笺为诗:“楚水平如镜,周回白鸟飞。金陵几多地,一去不知归。”检亦裁蜀笺赋诗:“还吴东去下澄城,楼上清风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树已凋零。”归方知在他梦妻之时,恰是其妻卒时,时为春暮,妻墓四面多是海棠花。其妻诗前两句写临终之景,平淡而凄凉,稍存幽怨之情。后两句中的金陵指京城,抱怨夫君为求功名,眷恋京城,久而不归,深得哀而不伤之旨。苏检的诗写于澄城,其地还在今陕西境内,因为取得功名,小有欢庆,因而清风醉酒,流连光景。后两句写回家情景,到春末,海棠花也该凋零了。在他当时是无意,却预言了无可挽回的家庭悲剧。此组诗在梦诗与鬼诗之间,写出科举生存中的家庭悲剧,具有相当的普适意义。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将其改写为江南钟辐梦中答妻诗,细节也有很大不同。
七、 艳梦不免到鬼域
人之大欲,曰食、眠、色。君子之人,其实内心都萌动着魔鬼,有些可以说,饿了求食,渴了思水,困极躺平,倦甚小憩,谁都不会指责。唯色欲无边,情急难耐,即便如唐人之不讳谈色,毕竟也有许多见不得人的野望。如《游仙窟》所述,其实就是作者自述之一夜风流。更过分一些,就是极古今之美色,拥缤纷之佳丽,色欲难禁,有时不免驰骋两界,犯及尊贵。

唐人思与前代嫔妃交合的小说还有裴铏《传奇》(《太平广记》卷六九)所叙薛昭与颜浚故事。薛昭于元和末为平陆尉,以气义自负。让他看守犯人,他钦慕其人为母复仇而杀人,赠金而纵其逃逸之,因是得罪,坐谪为民。其间遇异人田山叟,赠其药一粒,能去病绝粒,并指示他往兰昌宫方向而逃。薛昭夜遇三美女,姓字分别为张云容、萧凤台、刘兰翘,张自云是开元中杨贵妃之侍儿,杨曾在绣岭宫赠张诗:“罗袖动香香不已,红蕖袅袅秋烟里。轻云岭上乍摇风,嫩柳池边初拂水。”诗当然为裴铏所附会。另二女亦当时宫人有容者,遭忌毒而死之。三女与薛昭诗酒唱和,一夜风流。虽涉及贵妃,但仅及其侍儿,也算是小说家思及宫闱而抱持分寸的范例。颜浚则于会昌中下第游建业,遇青衣赵幼芳邀游瓦官阁,居然遇到了陈后主时张贵妃、孔贵嫔,赵则自承是江总家的受宠者。人鬼四人,诗酒唱和,接着还来了江修容、何婕妤、袁昭仪,也是一度风流。
传为牛僧孺所作,其实可能出于李德裕门下士之手的小说《周秦行记》,可以说把唐人占有古今最著名美女的欲望发挥到极致。《周秦行记》以牛僧孺第一人称来叙述,说他贞元中举进士落第将归,在伊阙南道鸣皋山下迷路,至灯火明处见一豪宅,进入后见到老妇,自称是“汉文帝母薄太后”,这里是她的庙,既说牛不应至此,又说各处汉、唐两朝,不相君臣,因此不须拘礼。进一步引见,则见到汉高祖戚夫人、汉元帝时王嫱(即王昭君)、唐玄宗贵妃杨太真、南齐东昏侯潘淑妃,以及西晋石崇妾绿珠,可说最有名的美女都聚齐了。其中且有一段“沈婆儿作天子”,直言代宗即位前在乱中走失的沈氏,即德宗生母,因此而引起对本朝大不敬的诉讼。其间当然有各女与牛分别吟诗的风流应对,更过分的是牛留宿一夜,薄太后问诸女谁可作陪,最后以王昭君先已失身于呼韩单于父子,且胡人也管不到汉地,逼她就范,可谓意淫到了极点。牛僧孺喜欢做小说,君臣大义必不会忽忘,只有伪造者才会这样地肆无忌惮。
唐代是士族社会的末期,士人几乎无不纵情声色,在小说中喜欢夸耀一夜艳遇,甚至思及前朝与本朝之宫掖,时亦加宽容,亦风气使然。
八、 文人借鬼存褒贬
时政得失,不在于当局或局外人是否能有所见,更在于以各自的处境、地位是否合适言传。若有不便,托鬼传言,亦一法也。
《太平广记》卷三二八引《灵怪集》:“唐太宗征辽,行至定州,路侧有一鬼,衣黄衣,立高冢上,神彩特异。太宗遣使问之,答曰:‘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荣华各异代,何用苦追寻?’言讫不见。问之,乃慕容垂墓。”慕容垂为十六国后燕开国之主,在乱世中曾割据北中国东半部,也算英雄豪杰。当唐太宗征辽时,亡殁已经二百多年。贞观十九年(645)太宗东征,确实曾驻跸定州。这首诗是什么意思?似乎在告诉太宗,不要自我感觉太好,以前我也曾称雄一时,而今衰微荒冢,各有各的时代,不要盛气凌人。几乎同样的诗,还有另一个版本。《鉴戒录》卷二《鬼传书》载高骈懿宗间任剑南节度使,开筑成都罗城,在城西南角掘到赵畚相公坟,赵遣使致书及诗,其诗云:“我昔胜君昔,君今胜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与慕容垂所吟十分相似。赵畚不知为那一时代之人,甚或全出虚构,但意思非常清楚,你急切要拓地建城,但也务必照顾亡者的权益。此事也很可能是高骈修城受到侵害的民众,借鬼书以为抗议。
元载在肃、代间长期为相,专权颇甚,旁观者则能知其势危,殆君臣之际,有难以尽言者。据说大历九年(774),也就是代宗杀元载前三年,载上朝,有书生投献并诵其诗一首:“城东城西旧居处,城里飞花乱如絮。海燕衔泥欲下来,屋里无人却飞去。”据说诵毕即不见人,因知为鬼。诗以海燕设喻,寄托华屋,高处筑巢而不知危险已甚,诗要传达的则是旧居飞花乱絮,极见凄凉,有盛极必衰的警示。这是《太平广记》卷三三七引牛僧孺《玄怪录》的记载。同书卷一四三引《通幽录》,诗则作“城南路长无宿处,荻花纷纷如柳絮。海燕衔泥欲作窠,空屋无人却飞去”,语异而意思相近。元载门下多有机警之文士,或有观察敏锐者,知其危而难以直言,亦未可知。
九、 释家借鬼言报应
释家讲生死轮回,五道周转,今生辛苦为了修来生欢乐,今生苦难缘于前世未积善行。谓予不信,自有起死回生或死后受难者为之传达。在多数情况下,佛家慈悲为怀,恩及动植,不太恶意相向,偶然也会有过激行为。这里说一位名僧的遭际。
明解是唐初名僧,俗姓姚,字昭义,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人。自幼出家于长安普光寺,有文彩,擅琴,工书,能画,时称三绝,《续高僧传》二七有他的传。太宗贞观十三年(639)书《智该法师碑》,早年出土,《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刊出,可以见到他的书迹。到高宗显庆五年(660),据隋相杨素旧宅建成西明寺,几乎是长安最大最豪华的寺院,有高官荐他住持,为弘福寺僧灵闰所阻,明解因此有些牢骚。到龙朔元年(661),诏征四科,他居然还俗,自举射策登第。与友人治酒欢会时,作诗述志云:“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归?幸得金门诏,行背玉毫晖。未能齐物我,犹怀识是非。赖尔同心契,知余志不违。幕齐云叶卷,酒度榴花飞。寄语绳床执,辞君匡坐威。”居然对佛教一乘三空的原则提出怀疑,对朝廷有自己的知己心怀感激,轻慢佛法,动了凡心。还因醉题壁曰:“老母在堂,袈裟去体,前途暗漆,浪称明解。”其实他年纪也不轻了,努力佛事居然不为同道所解,心间一片凄凉。又说“舍驴子皮而复人身”,对往日经历居然如此怀恨。但不久即因病辞世。据说卒后托梦于相知僧慧整,请他设食祭奠。第二年又托梦于画工,请他为自己写经超度,并赋诗为别,诗云:“握手不能别,抚膺还自伤。痛矣时阴短,悲哉泉路长。松林惊野吹,荒隧落寒霜。离言何以赠,留心内典章。”据说画工不识字,但凭梦中记忆写出,以示明解故旧,惊叹正是他的诗体。其实这首诗正是初唐还不太讲究粘对时期的五律,很可能即为明解临终之作,后传为鬼诗。这位名僧的选择,确实有些过分了,释家中人愿意借此而贬斥他的错误,更据以阐明佛说之不可怀疑,一切也都可以理解吧。
本节所据以《释门自镜录》卷上为主,各书叙述稍有出入。
十、 小说家借鬼逞才
唐人喜作小说,据说写小说可见作者叙事、议论与文彩,即可见文学综合能力。小说的另一好处是凭空说来,无所依据,驰骋想象,娓娓动人。鬼的世界怎样,反正谁都没有见过,正是施展才学的好场域。
牛僧孺《玄怪录》中,有两篇很特别。其一说梁天监元年(502),县吏顾总数遭鞭捶,郁郁愤怀,因逃于墟墓之间,彷徨惆怅。遇二黄衣人,自称是王粲、徐幹,认定顾总就是刘桢。顾总死活不认,二人解释:“足下生前是刘桢,为坤明侍中,以纳赂金谪为小吏,公今当不知矣。然公言辞历历,犹有记室音旨。”建安文学的三位代表诗人,就这样意外聚首了,二人拿出刘桢诗集,顾总一下明白了,诗思也如泉涌喷薄,还记得刘桢死后的诗篇,题目是《从驾游幽丽宫却忆平生西园文会因寄修文府正郎蔡伯喈》,诗曰:“在汉绝纲纪,溟渎多腾湍。煌煌魏英主,拯溺静波澜。天纪已垂定,邦人亦保完。大开相公府,掇拾尽幽兰。始从众君子,日侍真贤欢。文皇在春宫,烝孝逾问安。监抚多余闲,园囿恣游观。末臣戴簪笔,翊圣从和鸾。月出行殿凉,珍木清露漙。天文信辉丽,铿锵振琅玕。被命仰为和,顾己诚所难。弱质不自持,危脆朽萎残。岂意十余年,陵寝梧楸寒。今朝坤明国,再顾簪蝉冠。侍游于离宫,高蹑浮云端。却忆西园时,生死暂悲酸。君昔汉公卿,未央冠群贤。倘若念平生,览此同怆然。”这首诗是仿刘桢体,写回忆旧游往事寄赠前辈蔡邕,且说明是刘桢死后作。作者写此的目的,当然不是要表彰刘桢,要表达的是自己模写建安体诗歌的能力。
另一篇则讲元和初,丹阳进士陆乔好为歌诗。某日有一男子自称沈约,来与他谈诗,还约来了梁初著名诗人范云,其间议论颇多,所吟诗则仅有早逝的沈约之子沈青箱所作一首:“六代旧江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卵色天。伤时与怀古,垂泪国门前。”已经是成熟的近体五律,且梁时哪来六代之说,显然是唐人附会。《全唐诗》卷八六五收此诗题作《过台城感旧》,还算妥当,近人辑六朝诗,仍将此诗辑出,就属误认了。
十一、 托名鬼诗多佳什
世上有无鬼魂,坚信无神论者当然可以坚守无鬼,进而批驳一切有关神鬼的故事都是胡说八道。不过就唐人的生存环境与人生信条来说,似乎多数愿意信其有,且不断提醒自己,多行善事,畏惧天谴,广积阴德,福庇七代先亡及来世子孙。他们对鬼之认识,以及对死后世界的描述,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受当时世俗观念的影响,阴森恐怖,由冥司主掌,世间的恶行在那边也有。如果在唐诗中一定要挑两句来描述冥间景色,大约一定是曹唐《大游仙诗》中“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原诗写刘阮天台遇仙,二句似乎更契合鬼域。以唐人之执意体会与超强感悟,其揣摩人鬼及冥间精神世界,也多刻意用心之作,颇多好诗。如无名鬼之“芫花半落,松风晚清”二句,即曾得苏东坡之极赏。这里也举两首好诗,稍作分析。
襄阳旅殡举人诗:“流水涓涓芹努牙,织乌双飞客还家。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诗见《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三,说贞元末于頔镇襄阳时,有选人刘某入京,逢一举人,年二十许,言语明晤,意甚相得。举人指着小路说:“我的住处离此不远,能惠顾否?”刘似乎有所感悟,推辞程限所迫,要赶路,举人于是赋此诗为别。刘某次年归襄阳,再寻此举人,则仅有殡宫尚存。此诗写他的住处流水潺潺,春来草芽萌生,生机盎然。鸟则双飞营巢,客人也各自回家。荒村里的孤坟,到了寒食祭祀先人的节日,也没有人来祭祀,只有棠梨花开,自生自灭,陪伴孤坟,寂寞凄凉。颇觉得此诗本为诗人吊祭孤坟之作,流传中就成了旅殡荒郊的孤鬼之作。诗的意境寂寞而明亮,写春日之生机勃勃与孤坟之寂静相对,表诉同情与感慨。
再如高侍郎《凭张立本女吟》一首:“危冠广袖楚宫妆,独步闲庭逐夜凉。自把玉簪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此诗有两种异传。一是很早就传为诗人高适诗,《高常侍集》卷八和《全唐诗》卷二一四都曾收归高适,其实肯定属于传误。二是署白行简撰《三梦记》,说诗为淮安西市帛肆张氏女梦并州帅王公口授吟诗,文字稍有不同。此记自署会昌二年(842),时行简卒已十五六年,断然伪托,这里也不谈。此诗最早记载见《太平广记》卷四五四引《会昌解颐录》,说“丞相牛僧孺在中书”日,“草场官张立本有一女,为妖物所魅。其妖来时,女即浓妆盛服,于闺中如与人语笑,其去即狂呼号泣不已。久每自称高侍郎”。忽吟此诗。其女后服药得愈,说宅后有高锴侍郎墓,其中有野狐窟穴,因为其所魅。这里错误很多,即牛僧孺两度在中书,均早于高锴卒前十多年,因高锴而称高侍郎,再误为高适,传误线索也很清楚。排除这些讹误,不能不承认此诗艺术造诣非常之高。首句写女子装束,次句写闲庭避暑逐凉的清夜,女子以所载玉簪敲打庭砌前的青竹,在泻满月光的庭前清歌一曲,多少层的渲染,将此少女的清唱,渲染到极致。实在无法解释如此好的一首诗,为何附会到如此荒唐不经的故事上去。也许前人有鉴于此,好诗总要归属名家,于是高适出现了。
夏日炎炎,忽一阵凉风袭来,依稀似乎还有人语,有鬼!
- 古典文学知识的其它文章
- 公子彻夜不眠:曹丕诗歌中的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