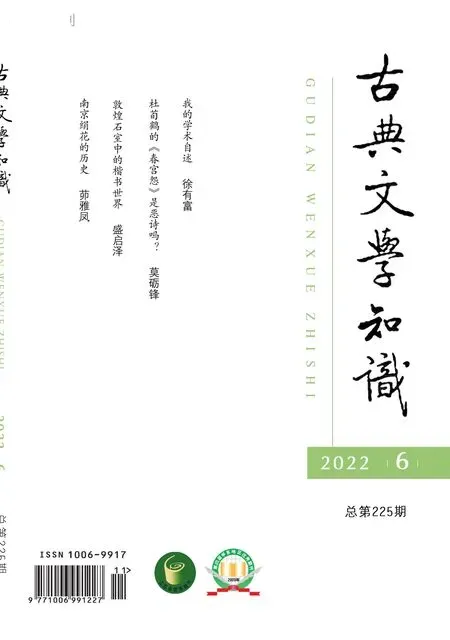公子彻夜不眠:曹丕诗歌中的夜宴
梁 爽
在《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曹丕这样记叙他往昔和朋友们快乐的“南皮之游”:
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骋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沈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魏宏灿校注《曹丕集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曹丕的盛大宴会似乎和后世在一个固定的室内举行的文人宴会有所不同,他们不断转换着地点和宴会的内容,既有文章学术的讨论,又有弹棋六博这样的游戏,伴以音乐、美食。白天结束之后,一行人在夜晚车马队列出行,游赏园林,这样夜以继日的游乐记载也同样出现在曹丕和其他参与者的诗中: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曹丕《善哉行》)
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曹丕《芙蓉池作》)
永日行游戏,欢乐尤未央。遗思在玄夜,相与复翱翔。(刘祯《公宴诗》,俞绍初辑校《建安七子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
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大康。(刘祯《赠五官中郎将》)
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曹植《公宴》,赵友文校注《曹植集校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
作为魏公子的曹丕是这些宴会的组织者,也是整个邺下文人集团的核心。在曹丕之前,很少有文学作品大量铺陈的夜宴,却成为建安诗歌产生的重要场合,也成为曹丕恋恋不舍的回忆场景。这一场合究竟有何特殊性呢?
一、 夜宴的奢侈
从刘祯诗中的“辇车飞素盖,从者盈路旁”可见,宴会的规模宏大,而对于夜游和夜宴而言,照明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烛火和灯光,就成了邺下诗人公宴诗中的常见意象:
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曹丕《孟津诗》)
众宾会广坐,明灯熺炎光。(刘祯《赠五官中郎将》)
清夜宴贵客,明烛发高光。(曹丕《于谯作》)
“烛”在古代是极为珍贵的物品。上古时代的“烛”大多指火把,又称火把为“庭燎”,郑玄说“在地曰燎,执之曰烛”,又云“树之门外曰大烛,与内曰庭燎,皆是照众为明”。在经典的记载中,需要夜间集会“共坟烛庭燎”的时候是“邦之大事”(孙诒让《周礼正义》,中华书局2013年版),是一种极为庄严的场合。
蜡烛在东汉时代已经开始使用,葛洪《西京杂记》中有“蜜烛二百枝”(葛洪《西京杂记》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王符《潜夫论》亦有“知脂蜡之可明灯也,而不知其甚多则冥之”。汉画像石中有大量蜡烛的造型,也有许多烛台实物出土(苏晓薇《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陶瓷烛台的类型学分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6年第5期),因此,东汉末年的曹丕所使用的烛火,完全有可能是蜡烛。但是直到六朝,蜡烛依旧是贵族才能使用的奢侈品(田晓菲《烽火与流星》,中华书局2010年版),《世说新语》中石崇以蜡烛作炊,被视为极奢侈的行为。无论是油脂制成的火把还是“新发明”的蜡烛,如果大量使用无疑都是昂贵的。东汉至魏晋的油灯有植物油和动物油,以动物油为主,称之为“脂膏”。时谚有所谓“深处脂膏,不能以自润”(《后汉书·孔奋传》),就是称人清廉,以“脂膏”代指财富。
由于“脂膏”与“蜡烛”的昂贵,夜宴成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场合。也或许正因此,建安之前的诗歌中鲜见“夜宴”的描写。夜以继日的宴会被视为一种“非常”的、奢侈的行为。《晋书·石虎载记》记载“宴饮终日”,令人制作巨大奢华的庭燎:

石虎的“庭燎”是一个巨大的、装饰复杂的大灯,最终因为“油灌下盘”的事故毁坏,被史书作为奢侈无度的事例记载下来。
曹丕和他的文学之友们的作品所描写的“灯烛”重点不在于复杂的装置,而是明亮、炫丽的光。建安公宴诗中,常见到对宴饮中的珍馐、宝物、嘉木的铺陈,如“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于谯作》)、“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芙蓉池作》)、“华馆寄流波,豁达来风凉”(刘祯《公宴诗》),以此来渲染作为宴会的豪华和主人曹丕的慷慨。而在建安时代的物质文化背景中,这些灯光与烛火实则与宝物相互映照,构成了一幅极为奢华侈丽的图景。
北宋晏殊在讨论如何写出“富贵”的作品时曾说:“‘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以为富贵,此特穷相者尔,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欧阳修《归田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对于建安公宴诗同样适用。夜以继日的游宴耗费巨大,建安文学集团的“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不但是风雅的,畅快的,也是奢侈的。学者多关注前两者,其实公宴的物质性同样值得注意,这一场合也决定了诗歌中的欢欣和感恩之情。放纵性情是建安文学的特色之一(葛晓音《八代诗史》,中华书局2007年版),曹丕夜宴中的一掷千金亦是这种“慷慨任气”的体现。
二、 欢乐与哀情的两面
“任气”与“悲风”往往在形容建安文学时与“慷慨”连缀使用,而长夜不眠的宴饮不但构成了建安奢华的一面,也始终与忧生之叹相关。这一点在曹丕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确,哀叹流年易逝、人生苦短是他作品中最重要的主题,也在本应该是“欢乐极”的公宴诗中同样反复出现。
“夜宴”和“夜游”的这种书写方式并不是曹丕的独创,在《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一首就提到了“秉烛夜游”: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55年版)
《古诗十九首》对于建安作家的影响显而易见,曹丕在《与吴质书》的最后,曾经感慨道:“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李善认为这里用的就是《生年不满百》的典故(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秉烛夜游的触发点是“人生苦短”的观念。诗人不但意识到生命的短暂和苦难,同时也对以往汉代人所坚信的神仙世界失去了信念和兴趣,直言“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因此何必爱惜资财,如同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面对时光必然的流逝这一事实,《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作出的反映并不是“积极”的努力和惜时,而是抒发一种对人生的绝望感和幻灭感,转向享乐主义(吉川幸次郎著,郑茂倩译《推移的悲哀——古诗十九首的主题》,《中外文学》1977年第6卷4期)。应当注意到的是,诗歌中的“何不秉烛游”正是“愚者爱惜费”的反面,也就是说,“秉烛夜游”本身就是散尽千金、及时行乐的实践。
如果通读曹丕描写“夜游”和“夜宴”的作品,会发现他最终所抒发的情感与《生年不满百》极其类似。《与吴质书》中他写道:“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余顾而言,斯乐难常。”结局是与朋友们的生离死别:“今果分别,各在一方。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在第二封信中他又说:“谓百年已分,可常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芙蓉池作》中,他同样抒发了对人生的无可奈何:“寿命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既然时间终将易逝,不如享受当下的快乐。而在白日逝去之后所举行的夜间宴会,正是曹丕对“生年不满百”的焦虑所做出的对抗之一,及时行乐是曹丕面对时光必然流逝的方法。奢侈不但是“公子敬爱客”的体现,也同时构成了曹丕作品中的悲伤底色。
三、 曹丕的奢与俭
同时作为一流的文学家和大权在握的政治家,曹丕的行事为人与他作品表现出的复杂的悲欢和哀乐高度契合。诗歌中那种奢华、任情的宴会,同样可以在正史记载中得到印证。
游猎、宴饮和大兴土木是史书批评为政者奢侈的几种典型,也正是曹丕的爱好。《文帝纪》中有“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三国志·文帝纪》)。依照《三国志》体例,《魏书》本纪中对曹魏皇帝多有回护,此处直书,意味深长。另一位大臣鲍勋因为数次指出曹丕游猎过度、大批建造“台榭苑囿”而被处死:
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
“内行既修,廉而能施”原本是东汉以来,深受儒家规训的士大夫恪守的道德,或许正因此鲍勋获得了钟繇、华歆等人的支持。可是曹丕显然不愿意被这样的准则所约束。而对于历史上评价极高的汉文帝,曹丕也曾经说:“我亦有所不取于汉文帝者三,杀薄昭,幸邓通,慎夫人衣不曳地,集上书囊为帐帷。以为汉文俭而无法。”汉文帝的节俭是整个汉代引以为典范的美德,曹丕显然并不认同这样的价值。
可是另一方面,与“及时行乐”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丕的薄葬思想。《三国志·文帝纪》正文引曹丕《终制》:
封树之制,非上古也,吾无取焉。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
曹丕指出他拒绝大封大树的首要原因是“礼法”,接下来又阐述了墓葬受盗扰的诸多事例,“祸由乎厚葬封树”。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这种悲剧的必然性:“自古至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作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一份严肃的、公开的官方文件中坦白生命终结和王朝终结的必然性,这是曹丕对生死存亡最直白的态度。
生时的奢与死后的俭形成的对照,恰恰与“何妨秉烛游”的观念类似,及时行乐的背后是意识到死亡的必然和死后世界的不可信。曹丕一向相信人的肉体“必朽”,他在给王朗的书信中有著名的论说:“生有七尺之形,死为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雕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这种面对生与死观念都与过去的传统不同。与他的父亲曹操相对比,史书称曹操“雅性节俭,不好华丽,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遗令则是“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着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下施穗帐,朝脯设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文选》卷二十)。曹操既然相信死后也可以享受饮食乐舞,他的陵墓陪葬也不像曹丕一样要求薄葬,这一点,可以从高陵的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印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曹操高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而与曹丕作风相似的是西晋玄学名士夏侯湛,“湛为盛门,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及将殁,遗命小棺薄敛,不修封树。论者谓湛虽生不砥砺名节,死则简约令终,是深达存亡之理”(《晋书》卷五十五)。
“生不砥砺名节”“深达存亡之理”的评价用在曹丕身上同样恰当。魏晋时代的傅玄曾说“魏文慕通达,天下贱守节”,曹丕的诸多行为与东汉士大夫要求的“名节”相违背,走向“通达”的一面。其实,“通达”与“守节”的对立实际上是汉魏之际世风转变的反映。就以奢侈与节俭为例,王伊同总结说:“盖魏末风俗,渐臻奢汰”(王伊同《五朝门第》,中华书局2006年版),东汉时代,节俭曾是名士之间标榜的美德,至魏晋时代,“奢侈”则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同样燃起蜡烛、爱好园林和宴饮的石崇曾对着颜渊和原宪的塑像说:“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牗哉!”(《晋书·石崇传》),这则故事同样被记载进《世说新语·侈汰篇》,正如罗宗强指出的,石崇的理论指向魏晋士人更加名正言顺地追求个人享乐的生活(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奢侈的石崇与奢侈的曹丕一样,都是一个文学集团的核心,石崇金谷园的集会也和邺下集会一样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诗歌作品。“奢侈”作为一种新的世风,或许也对魏晋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