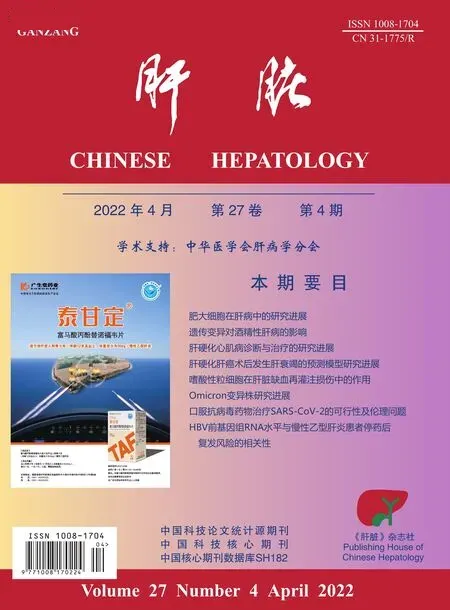遗传变异对酒精性肝病的影响
柳涛 刘雅丽 肖鹏 高沿航
酒精性肝病(ALD)是全球范围内常见的慢性肝病之一, 其疾病谱包括酒精性脂肪肝、酒精性脂肪性肝炎、酒精性肝纤维化和酒精性肝硬化。根据2018年WHO的全球酒精消费报告显示[1],2016年全球近23亿人饮酒,2005—2016年人均饮酒量由5.5 L增长到6.4 L;2016年,饮酒导致全球约300万人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5.3%)和1.326亿个体伤残。然而,ALD疾病的进展并不完全与酒精消耗量成比例,长期酗酒者中超过95%会发展为脂肪肝,但只有35%的个体进展至较为严重的疾病阶段[2],提示饮酒和其他因素协同作用促进ALD的发生、发展。近年来,遗传因素对ALD所发挥的作用被逐步揭示,本文就此领域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一、遗传变异与饮酒的相互作用
(一)遗传变异对饮酒的影响 饮酒是ALD发生和发展的前提条件,饮酒相关遗传因素并不会对肝脏产生直接损伤,却可通过影响饮酒者对酒精的摄入来影响ALD发生、发展。女性饮酒者在同等饮酒量情况下更容易发生ALD,可能与女性胃内乙醇脱氢酶(ADH)水平较低、体脂比例较高以及雌激素的存在有关[3]。酗酒被认为是一种家族性行为,有家族性酗酒史的人更容易发生酒精依赖[4]。同时,在亚洲人群中,ADH1B/1C、乙醛脱氢酶2(ALDH2)的携带与酒精依赖显著相关。2012年,Stickel 等[5]基于双胞胎人群所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同卵双胞胎和异卵双胞胎之间的疾病一致性可相差3倍,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生的双胞胎更易患ALD,说明ALD的发生与发展存在个体间的遗传差异。2015年,Verhulst等[6]进行了一项关于双胞胎过度饮酒的荟萃分析,结果发现过度饮酒(AUD)约50%可遗传,证明了遗传因素在AUD中的作用。
(二)饮酒对遗传变异的影响 2022年,Kim等[7]使用韩国基因组和流行病学研究(KoGES)健康检查队列数据,从国家健康检查登记者中招募来自韩国城市地区58 701名40~79岁的韩国人,基因型数据由韩国生物银行阵列生成[8]。最终符合入组标准的共 36 782人,基于饮酒问卷调查结果,将入组患者分为三组:无明显饮酒史(NDs)、每周饮酒量少于140 g(女性)和210 g(男性)(LDs)、每周饮酒量超过140 g(女性)或210 g(男性)(HDs)。在上述三组人群中,出现γ-谷氨酰转移酶(GGT)/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2.5或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ALT>3.0(ALD的生物学指标) 共3 346人,其中NDs组为782人(4.1%),LDs组为1379人(9.5%),HDs组为1185人(34.5%)。
在全部饮酒组中,编码GGT的GGT1 rs2006227次要等位基因与肝功能恶化的相关性最强,无论饮酒与否,携带GGT1 rs2006227次要等位基因的人群更容易发生肝脏疾病。此外,锌指蛋白827(zinc finger protein 827,ZNF827)的一个内含子变异与NDs、LDs人群ALD发生风险增加(+30%)相关。同时,肝细胞核因子1A(HNF1A)与ALD的发生风险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位点rs1183910的次要等位基因在LDs人群中显示为 ALD 的保护性关联,但在HDs人群中则无此关联。将前述结果在第二个KoGES队列中进行验证,得到了相似结果。
2015年,Buch等[4]一项荟萃分析结果显示,饮酒会放大patatin样磷脂酶包含区域3(PNPLA3)驱动的遗传风险。Kim等[7]的研究强调了ALD的遗传易感性是多因素的,并受饮酒量的影响,上述研究均提示饮酒量可以影响遗传因素。kim等的研究结果所提示的相关差异也可能与种族和研究队列的其他特定特征如体检人群、自我报告的饮酒量、排除数据缺失的人等因素有关。未来,进一步明确饮酒量对遗传因素的影响需要通过更多的大样本、多中心、多种族的研究进行验证。
二、遗传变异与酒精代谢酶
酒精进入人体后90%以上会经过肝脏代谢。乙醇被吸收后, 首先在肝细胞胞质内的ADH和微粒体中细胞色素P450 2E1(CYP2E1) 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醛, 并进一步在 ALDH的作用下转化为乙酸,最终转变为二氧化碳和水排出体外。三者都存在基因多态性,这种多态性与他们降解各自底物能力及宿主饮酒行为密切相关。
人体与乙醇代谢密切相关的ADH中,ADH1B对乙醇代谢影响最大,在该基因三种亚型中,ADH1B2、ADH1B3对ALD的影响最大。ALDH1B2在中国及日本人群中基因频率较高,对该地区男性饮酒者有较强的保护作用;ALDH1B3几乎只存在于非裔个体中,该基因能明显降低非裔个体发生酗酒的风险[9]。70%以上的中国汉族人口中存在ADH22,能编码活性较高的ADH,快速代谢乙醇,从而起到保护性作用[10],这些保护作用的产生可能与乙醇快速代谢成为乙醛,导致乙醛在体内积聚从而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使得宿主产生厌恶感,进而减少酒精摄入有关。
人体中ALDH共19种,其中ALDH2与人体乙醛代谢最为密切,该基因在ALD的发病中起了关键作用,它拥有2个等位基因,即野生型ALDH21和突变型ALDH22。ALDH22编码的酶活性明显降低甚至完全丧失,不能快速将乙醛代谢成乙酸, 使乙醛在体内大量蓄积,易出现面色潮红、心动过速及恶心、呕吐等醉酒症状。这种效果类似于双硫仑,而这些反应会减小ALDH22携带者继续饮酒的欲望,从而降低其发生ALD的风险[9]。但若携带ALDH22等位基因的人群长期坚持饮酒或酗酒,即使总饮酒量较小也可发生ALD,并使发生肝癌的风险显著增加[4]。
CYP2E1属于可诱导酶,约占体内乙醇代谢的20%~25%,其活性可在持续饮酒下增加约20倍,通过激活微粒体乙醇氧化系统和ADH一起将乙醇分解为乙醛。有研究发现,CYP2E1限制性酶切位点多态性与ALD易感性相关[4]。Psa I/Pst I酶切位点的位置上的遗传多态性形成三种基因型:A型 (纯合子c1/c1) 、B型 (杂合子c1/c2) 和C型 (纯合子c2/c2) ,2003年Piao等[11]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C2基因可能在脂肪肝的发病机制中起关键作用。
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及相关基因检测技术发现,除了ADH1B和ALDH2家族成员酶变异与酒精代谢之间的密切关联外,在欧洲、非洲和亚洲人群中,还发现多个额外的基因可能对AUD产生调节作用[4]。
三、PNPLA3对ALD的影响
2015年,一项基于欧洲人群ALD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显示,PNPLA3变异体p.I148M是肝硬化的重要风险基因[4],该突变基因在不同种族之间的基因型频率不同,在全球人群中突变基因频率接近50%[4]。PNPLA3 属于patatin磷脂酶家族,其编码基因位于人22号染色体上,该基因突变最常见位点为 rs738409,此位点野生型为 C,突变位点为 G。PNPLA3 的错义突变I148M(rs738409: C>G)与肝脏脂肪沉积增加显著相关,基因型为 GG 型的人群肝脏中脂肪含量显著升高,主要由于突变的PNPLA3阻碍甘油三酯脂肪酶与其辅助激活因子,比较基因鉴定58(CGI-58)的结合,使得脂肪分解减少,导致甘油三酯的沉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脂肪肝疾病,从单纯性脂肪肝到脂肪性肝炎、进行性纤维化、肝硬化和肝癌[4],作用范围广泛引人关注。
四、遗传变异与免疫
人体肠道分布存在数以亿万记的细菌、真菌等微生物,正常情况下,肠道微生物组成及数量处于一种平衡。长期过量饮酒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调,同时酒精代谢物通过影响肠道黏液层及连接蛋白表达,导致肠道屏障功能减弱,肠道通透性增加,进而使得肠道细菌产物脂多糖(LPS)等进入循环中。进入肝脏中的LPS会与肝脏库普弗细胞表面CD14受体结合,刺激库普弗细胞分泌TNF- α,导致肝脏细胞损伤、凋亡,进而引发肝脏炎症反应。有研究结果显示,CD14内毒素受体基因存在多态性位点-159 C>T[12], T等位基因可使发生酒精性肝硬化的风险明显增加。2016年,Zhao等[13]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TNFα-238 A等位基因与ALD发生风险显著相关。
五、其他
跨膜6超家族成员2(TM6SF2)基因的变异会引起肝脏VLDL分泌紊乱,导致肝脏甘油三酯和脂质含量增加,可导致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同时,TMS6SF2基因多态性为酒精性肝硬化的风险因素[4]。编码膜结合的含O-酰基转移酶结构域蛋白7 (MBOAT7)基因的变异(rs641738)也被证明影响ALD的疾病进展[14]。17-β羟基类固醇脱氢酶-13(HSD17B13)蛋白具有视黄醇脱氢酶(RDH)活性,编码基因变异导致酶活性丧失,HSD17B13 rs72613567变异可以显著降低ALD的发生风险(杂合子42%,纯合子53%)[4],同时在亚洲多种族NAFLD患者中降低了肝脏不良结局的发生率。2020年一项GWAS结果显示,线粒体酰胺基减少组分1基因(MARC1)rs2642438中的次要A等位基因降低了酒精性肝硬化相关风险。α1-抗胰蛋白酶(α1- AAT)缺乏的PiMZ杂合表型是促进ALD发生肝纤维化的独立风险因素[14]。
六、未来与展望
ALD病因尚待完全阐明且发病机制复杂。除遗传变异外,合并症和社会经济因素对ALD个体的疾病进展和治疗也会产生重要影响[15]。未来,尚需要关注ALD的社会差异并加入到肝病管理的决策中。治疗ALD需要将生物学研究(如遗传风险因素)和社会经济学研究相结合,同时解决两个系统存在的问题,才能更好地帮助这一疾病群体[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