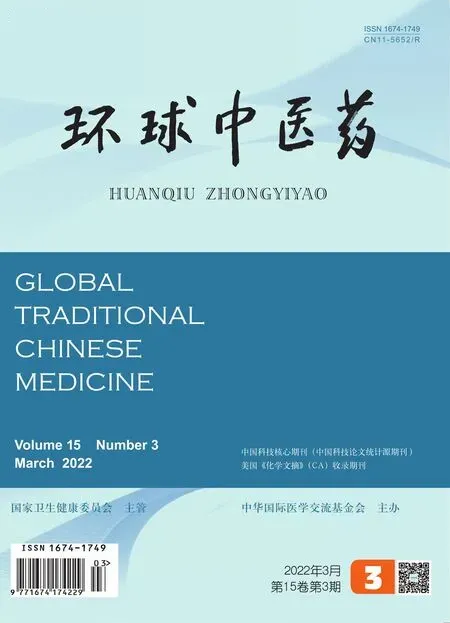基于脾虚为本辨治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
张祥毓 何晓瑾 徐婷婷 袁芳 钱斐 薛博瑜 金实
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rimary biliary cholangitis,PBC)是一种慢性胆汁淤积性的自身免疫性肝病,其病理特点为进行性、非化脓性以及破坏性肝内小胆管炎[1],首发症状常以乏力为主,随着病情进展可陆续出现皮肤瘙痒、黄疸、肝区压痛、腹水等症状。现代医学治疗药物主要有熊去氧胆酸、奥贝胆酸、贝特类药物、免疫抑制剂及生物制剂,但存在应答不完全[2]、耐受性差[3]、价格高昂等问题。近年来,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运用中医药治疗PBC的优势不断显现。对该病的治疗,众家学说各有侧重,有从肝治之者,如张玮教授[4]等;有从胆络治之者,如金实教授[5]等;亦有从“湿”治之者,如王彦刚教授[6]等。笔者在诊疗过程中常从脾入手[7],遣方用药常以调理脾胃、培补正气为主,佐以疏利胆络之剂,往往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不仅能有效降低患者的异常胆酶指标,还可明显改善患者的诸多症状。本文结合中医五行理论及现代生物学理论,论述基于脾虚为本辨治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的相关经验。
1 脾虚为发病之本,贯穿PBC发生发展始末
1.1 从五行生克制化关系论PBC以脾虚为本
中医古籍中并无PBC病名,从其临床表现来看,可归属“虚劳”“黄疸”“胁痛”“积聚”等范畴。中医学认为PBC直接病位虽在肝胆,然发病与否却取决于脾。郝娟等[8]对329例PBC患者的中医证候分析发现,且证候分型以脾气亏虚证最多,其次为肝肾阴虚证,这与PBC独特的发病特点有关。
PBC呈现家族聚集现象[9],患者之父母祖辈亦常患有此疾。PBC患者大多存在先天脾胃虚弱的情况,劳逸失度、饮食失节均可加重脾胃功能失调,引起运化失司,气血生化乏源,正气不足而百病皆生。且本病好发于中年女性,更多见于更年期女性[10]。女子以肝为先天,肝的疏泄之性在女子调气运血、开通郁结、通调胆络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肝脾同处中焦,经络血脉均紧密相连;而基于五行理论,肝木和脾土之间的制化推动者两个脏腑动态平衡。若脾土偏弱不足,木克土太过,就会形成“土虚木乘”之证。正如《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言:“肝木肆横,胃土必伤;胃土久伤,肝木愈横。”《灵枢·水胀》云:“鼓胀何如?岐伯曰: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也,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苍为肝气旺,黄为脾土衰,腹筋起指腹壁络脉怒张,青筋暴露,肝主筋,乃肝郁气滞的表现。
脾虽有补天之功,却易被内外诸因所伤,饮食失宜、情志失调、劳逸失度、外感病邪均可损及脾胃。脾胃受损,健运失职,津液输布代谢障碍则水湿内停,壅遏中焦。湿邪郁久而化热,横逆壅塞肝胆,因而肝疏泄不利,胆汁运行不畅,阻塞胆络,气滞血瘀,发为此病。《医宗金鉴》云:“盖肝为木气,全赖土以滋培,若中土虚,则木不升而郁”,说的便是此“土虚木郁”之证。不论是“土虚木乘”或是“土虚木郁”,皆直指土虚。故知PBC属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但以脾虚为病机关键,脾虚贯穿疾病始终。
1.2 脾虚可致免疫调节紊乱,引发PBC
PBC属于免疫介导的慢性肝内胆汁淤积性疾病。中医学认为脾为后天之本,是布散体内精微物质的重要脏器,是组成机体卫气的重要来源,具有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的免疫功能。正如《灵枢·本脏》中所说:“脾坚则脏安难伤。”《太素·脏腑第一》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脾胃健旺,五脏安和;脾胃受损,则五脏不安。”这些都指出脾的功能失常会影响到其余四脏的功能,导致机体防御病邪的能力下降。而《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中也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的理论,李东垣《脾胃论》有“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之说,这些论述都强调脾胃功能强盛则正气充足不受邪,脾胃功能虚弱则正气虚弱易发病。
中医学所说脾脏的卫护功能与现代医学中的免疫功能十分相似。大量实验及临床研究也显示,脾虚证与机体免疫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自身抗体角度来看,线粒体抗体是PBC的特异性抗体,线粒体抗体靶抗原是线粒体内膜成分,大量研究也显示脾虚证患者存在线粒体能量代谢障碍[11-12];从免疫细胞上来看,各类免疫细胞在PBC疾病过程中都起着重要作用[13-15],而脾虚证患者的细胞免疫、体液免疫及相关免疫功能均呈现较正常人明显异常的表现[16-17];从免疫器官上来看,脾虚证会导致动物的脾脏和胸腺发育受到抑制,其超微结构也有明显破坏[18-19]。临床上PBC患者常伴随一些基础疾病如自身免疫性肝炎、类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综合征、过敏性鼻炎、哮喘等,这些疾病大多属免疫性疾病,故而正是因脾虚导致一系列免疫调节的紊乱,进而更易诱发PBC。
1.3 脾虚可致肠道菌群失调,引发PBC
中医学所说“脾”不单指一脏,更是其运化水谷、化生气血的功能概括。从现代医学来看,脾与消化吸收及肠道菌群均有关联。《卫生宝鉴》曰:“治中焦,生育荣卫,通行津液,一有不调,则荣卫失所育,津液失所行。”脾主运化,脾气化水谷为精微,化水饮为津液,并转输水谷之精于全身各脏腑形体官窍。如若脾气亏虚,水谷精微堆积不能转化,肠道菌群失于濡养,平衡被打破,便形成肠道菌群失调,从而引起一系列症状如腹胀、大便稀溏或不调、消化不良等。
随着高通量测序技术的发展,肠道菌群在PBC发生发展中的重要角色被逐渐揭示[20-24]。肝脏具有来自肝动脉及门静脉的双重血液供应,其中肝门静脉系统主要接收肠道血液并汇至肝脏,从而使得肠道与肝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形成肠—肝轴,并构成肠道黏膜屏障,抵御肠道内的有害物质和病原体进入机体。大量研究表明,肠道菌群的失调会损害肠道黏膜屏障,进而导致门脉内毒素血症、继发性肝损害和肝内免疫系统紊乱。而肝功能受损后,胆汁分泌异常,肝脏的解毒功能减弱,又进一步加重肠道菌群的失调,由此形成恶性循环。
基于中医五行学说、免疫调节及肠道菌群等多个方面,笔者认为脾虚作为PBC发生的起始因素,顾护脾胃是防治PBC的重中之重。
2 脾虚致多种病理产物生成,使PBC呈早、中、晚三期表现
PBC的临床症状虽与病毒性肝炎较为相似,但两者的发病特点却大相径庭,病毒性肝炎以外感湿热毒邪为主因,而PBC却以“脾虚”贯穿始末。
脾属中土,主运化,将饮食水谷转化为精微物质而奉养全身;肝属风木,主疏泄,人体津液气血皆赖其升发之性而流转周身,运行无阻。生理状态下,脾胃纳化正常,气血生化有源,可充养肝气,濡养肝体,顺其冲和之势,更利其疏泄功能的发挥;同时肝性条达,疏利胆汁,亦使脾胃气机升降有度,促进脾胃对水谷精微的消化吸收和输布功能。肝脾二脏相互为用,配合密切,共为人体疏运协调之总轴。反之,若脾胃受损虚弱,也会影响肝脏疏泄,以致肝脾失调,气血津液疏运失司,胆络阻滞而为病。
2.1 PBC早期以脾虚肝郁、气滞络阻为主
PBC早期,患者由于先天禀赋不足或饮食劳逸失调而损伤脾胃,致脾胃气虚,加之忧思伤脾、恼怒伤肝,肝失疏泄,横逆犯脾,脾虚失运而病。脾主运化,脾虚则水谷精微难以布散,而食欲不振,饮食难消;脾在体合肉,主四肢,脾虚则气血生化乏源,无力濡养肌肉四肢,因而四末羸弱,身体乏力;脾虚又致精血化生不足,肝体失养,阴阳失衡,不能顺其条达之性,故疏泄失职,气机阻滞,而见两胁胀满不适。此期病机特点总属“脾虚肝郁、气滞络阻”,患者肝功能检查尚可,无明显不适,或仅出现乏力以及轻微的消化不良症状。
2.2 PBC中期以脾虚湿滞络阻为主
疾病发展至中期,脾胃虚损益重,无力输布水谷精微,反而内生湿邪,如《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所言:“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湿邪困遏脾阳,健运失权,中焦受阻,故见脘腹胀满,恶心呕吐,大便溏薄或黏滞不爽,舌苔厚腻;湿邪壅塞肝胆,阻塞胆络,胆汁不得循常道而行,上行眼目为目黄,流溢肌肤为身黄及皮肤瘙痒,下注膀胱为小便黄。此期病机属脾虚湿滞络阻,实验室检查可见明显的肝酶、胆酶或胆红素异常,患者乏力、消化不良的症状进一步加重,且出现腹泻及便溏等一系列湿滞证候。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这是长期肝内胆汁淤积致使机体消化吸收障碍而出现的脂肪泻。
2.3 PBC末期以脾虚血瘀络阻为主
疾病末期,脾虚生湿,湿性黏滞,最易敛邪,病情迁延,缠绵难愈。气虚、气滞、湿阻日久,必然导致血液运行不畅,而致瘀血阻络之证,出现面色黧黑,或见赤丝血缕,面颈部出现蜘蛛痣,舌质暗有瘀斑瘀点,正如《景岳全书》中所言:“凡人之气血,犹源泉也,盛则流畅,少则壅滞,故气血不虚则不滞,虚则无有不滞者。”瘀血结于胁下发为癥积,表现为胁肋部刺痛,或胁下有结块。脾虚统血无权,上逆则见吐衄,下泻则见便血尿血;中焦虚损,津液代谢障碍,聚于腹中而使腹大如鼓,可见单腹胀大而四肢干瘦,皮色苍黄;若水饮犯溢四肢,则成水肿。此期证属脾虚血瘀络阻,为PBC失代偿期,患者出现肝脾肿大、血象减少、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等门脉高压表现,若失治误治,更会出现血证、臌胀等严重并发症。
3 健脾乃治PBC之要
3.1 以健脾通络为大法治疗PBC
PBC以虚为本,患者大多先天不足,其长辈宗族多有患相关疾病者,又适逢人到中年,肝肾阴亏,胆络失养,本可依靠后天调摄补其不足,却又因内伤外感损伤中土,土虚木郁,肝脾失调,胆络淤积而发病。因此,PBC的临床治疗当以健脾通络为基础贯穿全程,随各阶段气滞、湿阻、血瘀、水停偏重不同随症加减。笔者临床以自拟健脾利胆通络方[25]为基础,药物组成为太子参、白芍、茯苓、生麦芽、柴胡、黄芩、半夏、路路通、泽兰、土茯苓等。方中太子参健脾益气,白芍柔肝养阴,二者合用,肝脾气阴并补,共为君药;茯苓健脾兼能利湿,生麦芽疏肝又可行气,半夏燥湿化痰,和胃降逆,三者为臣药,辅佐君药健脾疏肝;土茯苓、黄芩清热解毒除湿,柴胡疏利肝胆行气,泽兰活血化瘀,此四者为佐药,以制湿阻、气滞、血瘀标实之证。路路通活络通经,携诸药直达病所,为使药。全方诸药各司其职,共奏健脾调肝、利胆通络之功。
3.2 分期论治,随证加减,健脾通络
具体加减时应注意辨明虚实偏倚以及疾病所处阶段。PBC早期肝郁气滞明显者,可加用枳壳、郁金、木香、香附等疏肝行气以运脾;中期湿邪为患,壅塞中焦者可加用厚朴、砂仁、白蔻仁、苍术等化湿和胃,湿热横犯肝胆者则加用垂盆草、茵陈、泽泻、车前草、大黄等清利湿热;后期瘀血阻滞胆络,宜加用赤芍、片姜黄、参三七等活血化瘀,通利胆络。因PBC以脾虚为本,脾虚贯穿疾病三期,故对于脾虚甚者可加用黄芪、白术、山药、芡实等以增强健脾益气功效。
3.3 用药轻灵,补而不滞,顾护脾胃
应当注意的是,脾虚为PBC致病之本,而祛邪药大多性味苦寒,易于败胃,用之宜慎,过量则会加重上腹不适、大便不调等症状。同时,扶正时又忌一味蛮补,以防滋腻碍胃,正虚邪恋,选药宜轻灵平和,补而不滞。
4 典型验案
患者,男,24岁,2020年5月14日初诊。患者诉3年前体检时发现肝功能异常,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anine aminotransferase,ALT)100+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lutamyltransferase, γ-GT)300+U/L, 因无明显不适, 未予重视。 近1年半患者乏力较重,时时欲寐,食欲不佳,大便不成形,严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于当地医院查肝功能:ALT 83.1 U/L,γ-GT 239.4 U/L,故前来就诊。舌质暗,边有齿印,苔白腻,脉弦。西医诊断:肝功能异常;中医诊断:虚劳(肝脾不调证)。治法:调和肝脾,疏肝解郁,养血健脾,兼以降酶。方用逍遥散加减,具体用药:醋柴胡10 g、炒白术10 g、炒白芍10 g、酒当归10 g、茯苓15 g、法半夏10 g、土茯苓30 g、太子参15 g、酒黄芩10 g、垂盆草30 g、防风10 g、黄连3 g、生山药20 g、沉香曲3 g、炙甘草3 g,21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
2020年6月5日二诊:患者诉服药后乏力感减轻,食欲改善,大便转调,但汗出严重,复查ALT已恢复正常,γ-GT仍高(295 U/L),抗肝抗原谱提示线粒体抗体M2(±)。舌质偏红,边有齿印,苔白稍腻,脉弦滑。修正西医诊断为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修正中医证型为虚劳(脾虚胆络瘀积证);治法:健脾利胆通络;方用健脾利胆通络方加减,具体用药:太子参15 g、炒白芍10 g、茯苓15 g、麦芽10 g、法半夏10 g、土茯苓30 g、酒黄芩10 g、醋柴胡10 g、泽兰10 g、路路通10 g、炒白术10 g、酒当归10 g、防风10 g、垂盆草30 g、黄连3 g、沉香曲3 g、生山药20 g、麦冬10 g、炒赤芍10 g、茵陈20 g、炙甘草3 g,28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另予熊去氧胆酸(优思弗)口服,每日1次,每次0.25 g。
2020年7月3日三诊:患者诉服药后乏力明显改善,纳食可,二便调,汗出减轻,γ-GT下降至203.3 U/L,舌脉同前。上方加浮小麦30 g、糯稻根30 g,14剂,每日1剂,水煎早晚分服。口服西药同前。其后以此方为基础加减治疗3月余,诸症均得缓解,乏力感消失,汗出明显减轻,食欲佳,二便调,γ-GT逐步下降至128 U/L,ALT、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碱性磷酸酶均正常。
按 本案患者初诊时以乏力为主症,伴见食欲不佳、大便不成形,γ-GT升高,结合舌脉,当属肝脾不调之证,故以逍遥散为基础方调和肝脾,加土茯苓、垂盆草、黄芩等药以降肝酶。二诊时查抗肝抗原谱确诊为PBC,此时患者乏力、大便稀溏已有缓解,然出汗严重,此为卫外不固所致,且ALT虽恢复正常,γ-GT却较前升高,这说明患者症状虽有改善,但PBC进展尚未得到控制,γ-GT久高不下为胆络瘀阻之象。仔细询问病史得知,患者双亲素来体弱,其外祖母亦有肝功能异常病史,因受限于当地医疗条件未能明确诊断。可见患者先天禀赋实为不足,加之后天喜好烟酒,长期熬夜,损伤脾土,继而湿邪内生,横逆肝胆,胆络受阻;卫气本为水谷之悍气,脾胃受损,水谷不化,卫气不充,不能固摄津液而见自汗。因此辨证为脾虚胆络瘀积证,方用健脾利胆通络方加减,在初诊药物的基础上,加用具有利胆通络功效的赤芍、泽兰、路路通等药。予患者本方联合小剂量熊去氧胆酸治疗,肝功能明显改善,全身症状均得到缓解,这提示从中医思维出发,从脾论治,以健脾利胆通络为原则辨治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不仅能改善患者症状,而且能有效降低肝酶、胆酶指标,从而控制病情。这种中西药联合治疗PBC的方法值得继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