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角度思考碳中和
——《碳中和经济分析》书评
我国已作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将带来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我们应以怎样的理论范式来分析研判这个问题,以怎样的机制设计构建相应的政策框架?
十多年前,周小川就敏锐地认识到气候变化和低碳经济的重要性,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开始思考这些问题,逐步探索了一套碳中和经济的分析模型和政策框架,奠定了绿色金融的发展框架,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快速起步。
本书结集了周小川在2008—2021 年间关于碳中和、绿色金融和绿色治理领域的多篇学术成果,以其独特的国际视野、创新思维和超前洞见,打通了严整的学术思考和复杂的政策制定,不仅呈现了严谨的“有配额的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也提供了从供需两端如何推进减排工作的实操路径。本书还体现了周小川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上思索而成的“碳全球观”,既高屋建瓴,又近接地气,实现了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极具可读性。无论是专业人士还是初入门者,都能从本书中学到知识、得到启发,进而为实现“双碳”目标集聚更多智慧和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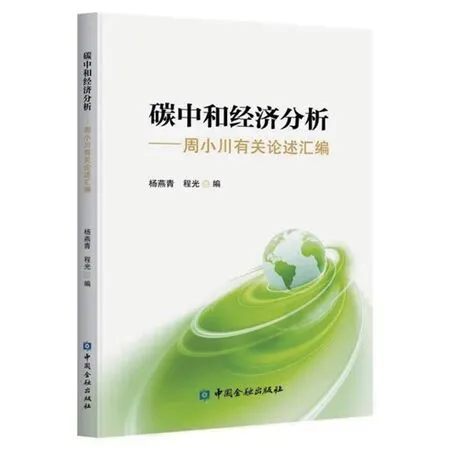
本书作者基于规范的经济分析得出:低碳转型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而且中国有一些优势;在减排机制的选择上,基于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框架得出碳市场是最优的机制安排;在国际碳市场连通与碳关税问题上,也基于国际治理的分析框架给出了机制设计思路。
低碳发展首先是认识上的问题,中国社会在认识上的扭转实际上经历了很长的时间。2005 年,习近平在浙江时就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在国内最早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但是,早期中国社会对低碳发展问题的主流看法是不一样的。比如,2009 年中国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当时大部分人认为,低碳发展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由于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没有兑现,难免会有阴谋论的想法,因此主张中国不能承诺绝对量的硬指标。直到2020 年底,习总书记向全世界两次公开承诺“30·60”目标,才一举扭转了社会上的主流认识。
减排机制是低碳发展的核心问题,在机制安排上社会上也有不同观点,周小川最早提出了对此问题的经济学分析框架,论证了碳市场是最优的机制。低碳减排在机制上至少有两种思路,包括行政化的任务分解,将任务摊派给各地方、各行业、各企业,以及依靠财税和金融调控来实现碳资源的配置,主要是碳税和碳市场。在早期的时候,有些人支持行政化的任务分解,这种方法简单、可控,现在还有不少人支持碳税。脱离经济学分析框架来谈论机制选择,是很难有结论的。
周小川早年有纺织品配额的研究经历,当时就有很好的分析框架,碳减排与纺织品配额在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周小川就将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框架应用于碳减排分析。使用这个分析框架从理论上证明了,让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配额价格并实现市场分配,仍会实现有配额的一般均衡,碳市场是比行政任务摊派、碳税等更优的机制。周小川还将这个分析框架应用于土地制度改革等其他类似问题研究,比如,基于配额交易的思想提出,建立可交易的全国土地当量市场,既能保持18 亿亩的耕地红线,又让土地市场供给更加市场化。
如何在一般均衡框架中纳入碳排放,既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也有深刻的政策含义。经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不考虑因外部性造成的市场失灵,认为自由竞争市场通过价格的充分调整,能实现一般均衡状态和最优资源配置。但碳排放造成的全球变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大负外部性,碳减排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市场干预活动,将对经济增长、价格、投融资、消费和国际贸易等产生深远影响。
周小川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配额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基于简化的一般均衡模型(s-GE)与简化的递推优化模型(s-RP)之间的等价关系,先在s-RP中加入碳排放约束,再通过库恩-塔克定理转换在s-GE中找到等价的附加表达。这样就将碳排放纳入一般均衡框架,体现在“收入函数与收入分配”部门中。碳排放约束的拉格朗日乘数(或影子价格)就对应碳排放配额价格,等于碳配额对净附加产值的边际贡献(通常为负)。因此,碳排放约束机制实际上使碳成为一种作负贡献的资源约束。
按照有配额的一般均衡框架的分析结论,基于碳市场的价格信号引导全社会的碳减排是最优的机制设计,但形成有效的价格信号又以总量目标的顶层设计为前提,这也是周小川近年来持续呼吁的关于减排机制设计的两个重点。碳价格应能够产生足够激励,而且碳价格相对稳定才能对长期投资、科技创新起引导作用。
周小川很早就意识到,低碳转型中各个国家的利益是不同的,要纳入国际治理的框架予以分析,特别是要有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机制。气候变化在经济学上是个公共产品负外部性的问题(也是“公地悲剧”问题)。发达国家历史上排放得多,发展中国家如果因为碳减排而影响到自身发展是不公平的,所以,国际上强调“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如果从国际治理的角度,国际碳市场连通和碳边境调节税的一些机制安排就能看得比较清晰。很多发达国家已经碳达峰了,发展中国家碳排放还在往上走,所处阶段不同,碳价应是不同的。直接打通各国碳市场,会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碳价抬升,后果难以承受。所以需要把握好碳减排的进度,把握好创造GDP 流量需求与成本控制之间的平衡点。
周小川提出,为了让各国碳市场连通的速度、范围可控,以及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补偿机制,可参照类似沪港通、深港通等连通机制,建立连通的小管,类似之前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可以购买发展中国家低碳减排的成果,用于抵减自身的碳排放。基于同样的原理,如果发达国家一定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相关收入也必须全部返还用于支持出口国、资源国等的低碳发展,体现对发展中国家的补偿属性。
此外,周小川认为,绿色金融是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并推动国内绿色金融快速起步发展。人民银行等金融管理部门很早就及时跟踪国际上绿色金融的发展,考虑到中国绿色金融与国外情况有所不同,ESG(环境、社会与治理)投资人基础尚不牢靠,提出采用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底层探索紧密结合的发展思路。此后逐步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2016 年多部门联合发布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绿色金融的定义、激励机制及绿色金融产品发展规划和风险监控措施。同时,2017 年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陆续设立。此外,人民银行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合作,2016 年首次将绿色金融引入G20 议题,并发起G20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2017年与8 家金融监管机构共同成立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
在适合的发展思路与发展框架下,中国绿色金融实现了快速起步。截至2020 年末,绿色信贷全球第一;绿色债券全球第二。这些成绩的取得既缘于周小川很早就意识到绿色金融是低碳转型的重要支撑,同步提出了发展思路并奠定发展框架,推动国内绿色金融起步,也与之后人民银行一直坚持推动绿色金融分不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