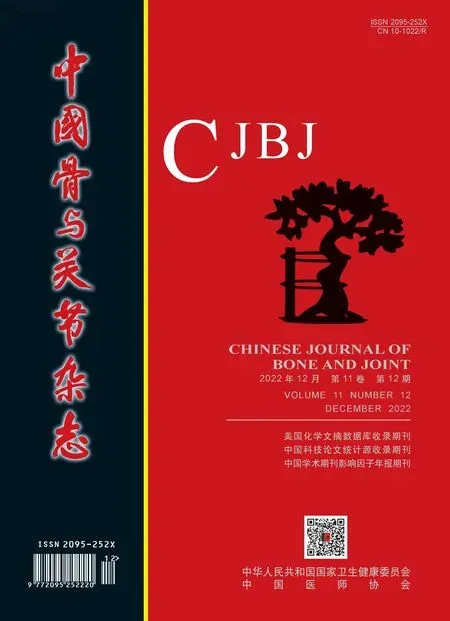先天性多发关节挛缩及其综合征的遗传研究进展
陈丹 田文 王树峰
先天性多发关节挛缩 ( arthrogryposis multiple congenital contractures,AMC ) 等 )[1-3]一般用来描述先天性、可累及身体两个或更多部位的关节异常屈曲的疾病[3]。目前对于 AMC 的认识有限,甚至在众多研究和文献中使用的名称也较为混乱[1]。一般认为,AMC 是一个基于形态学特征的临床诊断[3],包含了一组临床表现、病因各异的疾病[1]。有学者认为,与 AMC 相关的综合征可超过 400 种[4-6],这一类疾病的表现复杂多样,关节挛缩可以出现在全身各个大、小关节,包括上肢、下肢、脊柱及颞下颌关节,挛缩表现的程度轻重不一,此外有的还可以合并中枢神经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生殖系统的症状[1]。
AMC 为先天性疾病,有文献报道这一疾病在美国新生儿的发病率约 1 / 5000~1 / 3000[2]。由于此类疾病可造成胎儿娩出困难,且病变程度严重的患儿出生后存活困难[6],AMC 很早便有关注报道,但目前的研究对 AMC 的认识仍十分局限。随着近些年分子遗传学的发展,基因检测等技术成为了进一步了解此类疾病的有力手段[7]。现对 AMC 现有的遗传学领域的研究进行综述,以期进一步加深对 AMC 的认识。
一、AMC 的病因研究
AMC 的确切病因仍未知,但目前认为 AMC 的发病与胎儿在宫内生长发育过程的活动减少 ( fetal akinesia ) 关系密切[3,6]。造成胎儿活动减少的原因复杂多样,基因异常、母体或外界因素都可能引起胎儿活动减少[1-3];上述各因素引起 AMC 的具体比例尚不得而知,但有学者认为基因异常是 AMC 发生的主要原因[3]。
目前,直接造成胎儿活动减少的原因未知,但已经发现有不少情况可以造成胎儿活动减少,具体包括以下方面:肌肉相关发育异常;中枢或外周神经疾病或神经肌肉终板相关发育异常;结缔组织形成异常;能够引起宫内空间有限的情况 ( 如多胎妊娠、子宫畸形、羊水减少、羊膜带等 ) ;母体疾病 ( 如:多发性硬化症,妊娠期糖尿病,寨卡病毒、风疹病毒、麻疹病毒等感染等 );母体孕期暴露 ( 如:药物、过量酒精及毒品等 );胎儿或胎盘的血供减少;代谢异常 ( 如:母体酸中毒等 );表观遗传疾病等[2-3]。
在致病基因的研究方面,至今已经发现了 400 余个基因与 AMC 有关[8]。某些基因的点突变,染色体异常如染色体三体 ( 特别是 21,13,18 三体 )、染色体微缺失或重复,这些均可能造成 AMC 的发生[1]。Kiefer 等[8]对目前发现的相关基因运用基因本体论 ( gene ontology,GO ) 进行分析,402 个致病基因根据其功能分为 29 组,这一方法可展现不同致病基因功能上的关联;而目前只有其中的 19 组包括了 1 个以上的基因,这也为之后发现新的致病基因提供了方向。
AMC 中最常见的类型为肌发育不良 ( amyoplasia ),其次为远端关节挛缩 ( distal arthrogryposis,DA )[9],这两类占到了所有诊断的 AMC 中约 50%~65%[10]。肌发育不良与远端关节挛缩为 AMC 两种不同类型,两者具有相似的临床特征,但有不同特点可将二者区别。肌发育不良的诊断较特异,常表现为肌肉量减少,出生时患儿四肢固定,指 ( 趾 ) 屈曲挛缩,上肢的肩、肘、腕关节及下肢的髋、膝、踝关节也多有异常屈曲,且四肢关节挛缩多为对称累及[11];这一疾病可能为非遗传的综合征,多为散发病例,确诊患者的家族很少出现新发患者,病因方面目前研究尚未发现与这一类型相关的染色体或基因[10];对于同卵双胞胎患者的研究中发现,至少约 6.6% 的双胞胎表现为一个患病而另一个不患病[12]。DA 是表现为肢体远端多发关节挛缩的综合征,DA 表现形式多样,各类型 DA 均存在手足等肢体远端关节异常屈曲,而较少累及肢体近端关节,伴或不伴肌肉及神经异常;此外 DA 通常有着确切的遗传学异常,多表现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10]。
二、部分综合征的遗传学机制
当前发现的 400 多种 AMC 相关综合征中,有部分综合征的发病机制已经得到一定认识。遗憾的是这种认识仍十分有限,具体某一综合征的发病率亦缺少相关研究支持,需后续开展更多的研究。下面将着重介绍笔者所在科室临床工作中接触较多的几种 AMC 相关综合征[13-14]。
1. Beals 综合征:Beals 综合征或 Beals-Hecht 综合征,又称为先天性挛缩性蜘蛛指样畸形 ( congenital contractural arachnodactyly,CCA ) ( OMIM 121050 ),为远端关节挛缩的第 9 型 ( DA9 )[15-16]。
Beals 综合征可有十分复杂广泛的临床表现。典型的 Beals 综合征具备以下特征:蜘蛛指 ( 趾 ),累及肘、膝、髋、踝、手指等的多发关节挛缩,脊柱后凸 ( 通常为进行性 ),耳廓卷曲畸形以及类似于马方综合征的表现 ( 身材瘦高,肢体、手指细长,胸廓畸形,肌肉发育不良,拱状腭 )。严重者同时还可有心血管系统异常 ( 主动脉弓离断,房间隔或室间隔缺损,主动脉根部扩张 ) 及胃肠道异常 ( 食管或十二指肠闭锁,肠旋转不良 )[15]。
Beals 综合征为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目前该疾病的发病率仍不清楚。基因 FBN2 ( OMIM 612570 ) 与该综合征关系密切,是目前发现的惟一与该综合征相关的 基因[17]。
FBN2 位于染色体 5q23.3,具有 65 个外显子,长度为 279.57 kb,编码一个 10 166 bp 的转录物,生成一个由 2912 个氨基酸组成的蛋白产物原纤维蛋白 2 ( fibrillin-2 )[16]。 原纤维蛋白 2 是结缔组织微纤维的组成成分,可参与形成弹性纤维[18]。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ClinVar 中记录的 FBN2 突变达 1833 种;与 Beals 综合征相关的突变有 1088 种,有 47 种为致病或可疑致病突变。大多数与 Beals 综合征相关的 FBN2 突变位点在外显子 23~35[19]。
具备 Beals 综合征典型症状的患者中,约 25%~75% 存在 FBN2 的突变[15,17,20]。Meerschaut 等[17]提出了一种根据临床表现进行评分的诊断方法,发现 FBN2 存在致病突变的患者在这一评分体系下获得了更高的得分 ( P < 0.001 )。目前尚未发现这一疾病基因型与表型的相关性。Lavillaureix 等[21]发现染色体缺失可能导致出现更加严重的临床表现。Kloth 等[22]发现 1 例存在严重临床症状的 Beals 综合征患者,其 FBN2 基因具有一个错义突变和一个无义突变,分别遗传自健康的父母,呈现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马方综合征 ( Marfan Syndrome,OMIM 154 700 ) 致病基因为 FBN1 ( OMIM 134 797 ),位于染色体 15q21.1,马方综合征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FBN1 与 FBN2 结构类似,FBN1 基因的蛋白质产物原纤维蛋白 1 同样为细胞外基质的组成成分[18]。马方综合征与 Beals 综合征在前文提到的部分症状上表现类似,但马方综合征患者中仅部分存在多发关节挛缩的症状[23]。
2.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Freeman-Sheldon 综合征 ( Freeman-Sheldon syndrome,FSS;OMIM 193 700 ),也称作 Freeman-Burian 综合征,吹笛手面容综合征 ( Whistling face syndrome ),颅、腕、跗骨发育不良 ( craniocarpotarsal dysplasia or dystrophy ) 等[24],为远端关节挛缩的第 2A 型 ( DA2A ),是 DA 中症状较重的一型[25]。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具有特征性颌颜面畸形:小口畸形,噘唇,眼深陷、眼距增宽或眦角异位,小鼻、长人中及鼻翼发育不全,下巴处存在 V 型或 H 型瘢痕样结构,鼻唇沟深;手指屈曲挛缩,尺侧偏斜,可有马蹄内翻足伴趾挛缩,也有少数患者不存在肢体受累;患者的生长发育迟缓,身材矮小,但智力正常[25-26]。有时还可有代谢、胃肠、视听觉的异常[27]。不同患者的疾病严重程度不一。此外,Freeman-Sheldon 综合征与远端关节挛缩第 1 型 ( DA1 ) 在肢体症状上表现十分相似,通常需要通过特有的面部症状来鉴别这两种类型[28]。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遗传方式主要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但也有部分情况为常染色体隐性遗传[29],目前该疾病的发病率未知[25]。基因 MYH3 ( OMIM 612 570 ) 与该综合征关系密切。
MYH3 位于染色体 17p13.1,具有 43 个外显子,编码的蛋白质为肌球蛋白 3 ( myosin-3 ),由 1940 个氨基酸组成。肌球蛋白是肌肉的主要组成,在细胞运动以及细胞内物质传输中发挥功能;肌球蛋白 3 在胎儿时期的肌肉形成发育具有重要作用[30]。
截至 2021 年 11 月 14 日,ClinVar 中记录的 MYH3 突变达 439 种。与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相关的突变有 175 种,有 8 种为致病或可疑致病突变;有的突变可造成肌球蛋白 3 的 ATP 结合位点结构发生变化,从而改变肌球蛋白的催化活性[31],影响早期肌肉发育[32]。
但部分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患者未发现 MYH3 基因的突变[33],Zampino 等[34]发现至少约 7% 的患者不存在 MYH3 基因的突变。
MYH3 突变还与 Sheldon-Hall 综合征 ( DA2B,OMIM 618 436 )、多发翼状胬肉综合征 ( multiple pterygium syndrome,DA8 ) 的 1A 型 ( OMIM 178 110 ) 及 1B 型 ( OMIM 618 469 ) 有关[3,35]。Sheldon-Hall 综合征与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在名称上相似,临床表现亦相近。Sheldon-Hall 综合征除远端肢体的多发关节挛缩外,同样存在特殊面容:鼻唇沟深,小口,蹼颈,下巴小而突出;但 Sheldon-Hall 综合征的张口程度较 Freeman-Sheldon 综合征更大,且 Sheldon-Hall 综合征患者下巴上不存在 V 型或 H 型瘢痕结构;在这两个疾病中,虽然同样存在 MYH3 的突变,但突变影响的肌球蛋白残基位置不同[31]。
三、总结
AMC 作为罕见病,学界对其认识仍在不断探索过程中,遗传学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这一疾病的病因及疾病发生过程。在治疗领域,现有的 AMC 治疗缺乏统一的标准,临床医师多根据患者的形态学及影像学特征,予以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这类患者的手部畸形,多采用支具固定及手术干预,以期改善畸形关节的功能,但目前对于这类患者的手术干预也多缺乏大宗病例报道及长期的随 访[13,26]。国内的临床医师对于这类疾病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有时可能无法在临床上及时做出准确的诊断,予以恰当的治疗。希望通过对于 AMC 现有遗传学研究的简述,临床中常见的几种综合征的介绍,能够加深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进一步推进 AMC 在中国的诊疗完善及研究开展[36]。
而目前对于 AMC 的遗传学研究仍在不断深入,在未来会有更多的致病基因被发现,相关致病机制也将进一步阐明。一方面,对于 AMC 以及胎儿活动减少的研究能够帮助临床医师更好地认识新生儿早期发育与运动的相关机制。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有助于更加全面认识这一疾病的发生、发展,在未来也许可以实现通过基因检测的方式明确 AMC 及相关综合征的诊断,并针对其致病位点或通路,通过使用特定药物,激发替代通路、对致病基因的靶向治疗、进行表观遗传修饰等[8],实现这一疾病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