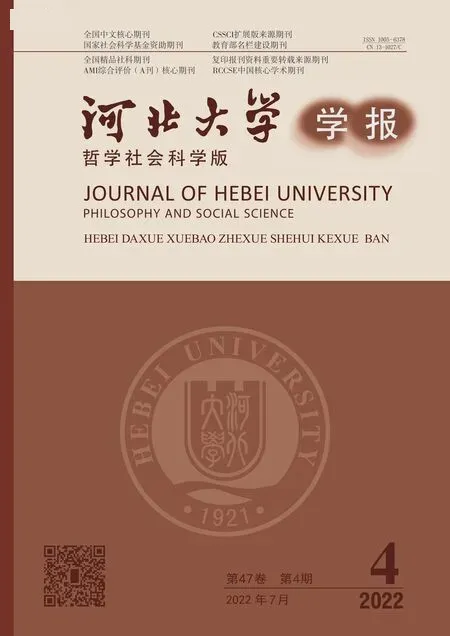古代宵禁制度的文化意蕴及明清小说中的宵禁书写
史小军,王献峰
(暨南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0)
“宵禁”作为古代夜晚出行的重要管理制度,主要是指通过按时关闭城门、坊门和禁止居民夜间出行,以限制夜间人员流动,确保社会治安平稳有序。它的形成与发展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并因此衍生出顺应传统伦理的宵禁文化。在此种文化意蕴的影响下,宵禁进入了文学家尤其小说家的视野,成为其反映世态人情的重要工具,以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关于宵禁,很多学者多是从历史的角度对制度本身进行还原与重构①关于宵禁制度历史学方面的主要论文:陈熙远《中国夜未眠——明清时期的元宵、夜禁与狂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006第4期;冯之余《古代中国的黑夜秩序》,《东南学术》,2009年第3期;贾文龙《宋代社会时间管理制度与昼夜秩序的变迁》,《郑州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王茂华、张金花《元朝城市夜禁考论》,《兰州学刊》,2016年第3期;刘浩《唐长安城夜禁制度施行的时空背景及内容研究》,《人文杂志》,2017年第4期;王茂华、张金花《宋朝城市公共空间夜晚秩序》,《城市史研究》,2018年第2期。,而较少关注其蕴含的深层文化内涵,本文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宵禁的文化意蕴进行阐述,并关注宵禁在文学尤其明清小说中的书写。
一、宵禁制度的沿革
宵禁制度最早由周朝创制,周朝曾专门设置“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1]550。汉代承袭并加强了宵禁制度的管理,由执金吾负责。之后,为加强统治、禁除犯罪,南北朝在两汉的基础上更强化了宵禁管理,甚至身为皇帝的萧赜都曾担心臣下夜行会遭到尉司的呵责:“同辇夜归,至宫门,嶷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2]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第414页可见南朝宵禁的严厉。
唐代,是宵禁制度系统化和完善化的重要时期。首先,唐统治者采纳马周的奏议在城市街道设置街鼓,以鼓声提醒宵禁的终始。街鼓的设置结束了专人传呼的落后状况,给予时人极大的便利,所谓“旧制,京城内金吾晓暝传呼,以戒行者。马周献封章,始置街鼓,俗号‘冬冬’,公私便焉”[3]卷十《厘革第二十二》,第149页。其次,唐代实行坊市分区,并在每坊设置坊门,由坊正负责开关坊门。坊正配合宵禁的街鼓声,夜晚按时关闭坊门,严禁居民随意出入。最后,唐代更是首次以律法形式对宵禁诸方面做了明文规定,弥补了之前宵禁制度的不足,并为后世宵禁律法的制定做出了表率,如《唐律疏议》规定“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搥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4]卷二十六,第489-490页,从而保证宵禁更为制度化、合理化。
尽管唐代在各方面都不断推动宵禁制度的完善,但终唐一代并未完全贯彻落实,而是呈现出一种前严后宽、渐变松弛的趋势,甚至在严格执行宵禁制度的唐前中期都存在元宵弛禁的情况:“西都京城街衢,有金吾晓暝传呼,以禁夜行,惟正月十五日夜敕许金吾驰禁前后各一日。”[5]1780这说明,宵禁作为一种制度,它并非僵化不变之物,而是会根据社会经济的需求做出相应变革和调整。
宋代的宵禁基本是延续唐代而来,但在实际执行中,宋代宵禁制度较之唐代严重松懈,甚至一度被废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宋代城市建构由唐代的坊市分离逐渐走向坊市合一,这种坊市制度的变更大大刺激了商贸经济的发展,使得贸易时间不断延伸,甚至出现以供夜间交易的夜市经济,如《东京梦华录》记载,潘楼街“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6]卷二《潘楼东街巷》,第15页。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耍闹去处,通晓不绝。”[6]卷三《马行街铺席》,第21页夜市的交易、商贸的往来都使得宵禁一再张弛无度,甚至在北宋初期一度被取消。二是宋代废止了唐代确立的街鼓制,所谓“二纪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7]卷上,第9页。这就使得以往严格限时的夜晚活动被不断延迟,如遇到上元、中秋等重要节日,宋朝都市甚至会出现彻夜狂欢、通宵达旦的景象。
元朝的宵禁则一改宋代的宽松之态,变得尤为严格。“夜禁政策执行时间长和夜禁时间长,夜禁规定对犯夜者的惩处力度较前代重。与一般朝代初期严厉、中后期宽缓相较,元朝是古代少有的统治期间持续执行夜禁的特例政权。”[8]元朝之所以在宵禁制度上出现如此变化,这是和唐宋两朝的“松弛变化”紧密相关的。尽管元朝经济仍进一步发展,但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不断加强夜晚秩序的管理,从而使得宵禁重回唐制,这种改变在宋朝松弛状态的衬托下尤显严格。
明清时期则延续了元朝对夜晚严密管控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对宵禁制度不断深化完善,进一步严格化和系统化。
首先,明清律文详细规定了宵禁律令的处罚。明清律令虽仍将宵禁时段规定在“一更三点钟声已静;五更三点钟声未动”[9]1170的范围,却在犯夜惩罚上出现了次第等级的不同,如明律规定“二更、三更、四更,尤为夜深,此时有犯者,在京城则笞五十,在外郡城镇则减一等,笞四十”[9]1171。但行人若在“不系禁人行之时”被诬执为犯夜,巡夜人则需抵罪,并根据情节轻重对巡夜人给予责罚:“诬执京城者,笞三十;诬执外郡城镇者,笞二十。”[9]1172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行人的权利,使得巡夜之人不敢借此肆意妄为。
其次,针对暴力抗法行径,律法也有明确惩处措施。《大明律》云:“若犯夜拒捕及打夺者,杖一百。因而殴人至折伤以上者,绞;死者,斩。”[9]1170大清律例与之相同。律法分明,惩处严厉,这对犯夜尤其抗法之人颇具震慑力。
此外,明清两朝对人们夜晚出行不仅在律法条例上做了严格限制,并且为了保障律法的妥善实施也采取了多种举措,如栅栏的设置、更夫夜巡等,这些都体现出对宵禁的重视和管控。
从宵禁制度的历代沿革来看,其在执行中大体呈现出总体严格、中间略有反复的状态:从周到唐,宵禁管理逐渐深入,盛唐虽更自由开放,但在宵禁上反而更制度化、系统化;晚唐五代及至两宋之时,宵禁管理出现松弛,甚至一度被取消,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宽松状态;到了元朝则又重回唐制,并更显严格;明清两朝承续前代,将宵禁管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无论如何变更,历朝历代对宵禁政策的执行是一以贯之的,尤其自唐代确立法典以后,各朝法律都设有专章对宵禁进行明文规定,这也与古代宵禁制度的文化意蕴密切关联。
二、宵禁制度的文化阐释
宵禁作为一种管理制度,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现,同时,它的形成与发展又植根于深厚的作息观念、社会功用与经济基础,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并进一步形成专门的宵禁文化。历朝关于宵禁的实行与变革代有不同,严密与松弛交替,遵奉与背离并有,由此可见传统社会中宵禁文化与守夜意识的高扬与消解。
历朝之所以实施如此严峻的宵禁制度,根源在于顺应天道所产生的作息观念。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中,白昼光亮作用下人们适合劳作,到了夜晚,目不见光,万物俱籁,农牧等相应室外活动被迫搁置,《诗经·王风·君子于役》就有记载:“鸡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10]卷四,第67页对此,朱熹认为:“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11]卷六十二《中庸一》,第1496-1497页曹庭栋更是将这种作息观念与阴阳天理联系:“况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昼动夜静,乃阴阳一定之理。”[12]卷一《晨兴》,第11页此外,昼出夜伏的作息习惯也是人类自身健康的需要。人类虽然不像绿色植物那样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完成生命的循环,但同样离不开日光,日照对人类的健康和自身的发展都大有裨益。这一点早已经被古人所认识,《黄帝内经》就曾根据四季太阳升落的不同对人类的起居做出了要求:“春三月……夜卧早起,广步于庭。……夏三月……夜卧早起,无厌于日。……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冬三月,早卧晚起,必待日光。”[13]卷一《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第7-9页中医更是主张应常晒太阳,尤其冬季要多进行日光浴。中医学从“阴阳调和”角度出发,认为常晒太阳能够助发人体的阳气,起到调和阴阳,温经通脉的作用,清代曹庭栋在《老老恒言》里说:“背日光而坐,列子谓‘负日之暄’也,脊梁得有微暖,能使遍体和畅。日为太阳之精,其光壮人阳气,极为补益。”[12]卷一《晨兴》,第13页以此可见,昼出夜伏既是自然界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是古人根据自身需求做出的主动选择,是顺应天道、有利人事的必然结果。
从自然规律来看,昼出夜伏是顺从“阴之冷的和黑暗的特性与阳之暖的和明亮的特性之间处于某种平衡或交替”[14]的必然选择,而当这种阴阳平衡的天地现象作用到人欲伦常上,则是大宇宙与小宇宙之间的道德匹配,所谓“在天只是阴阳五行,在人得之只是刚柔五常之德”[11]卷六《性理三》,第104页。在儒家伦理作用下的社会规范必定与之密切相关,而“儒家规范的合理性根据在于太极、天道、天理、本然之性,而这些道、理、性既是宇宙的理法,也是人的本性,同时还是社会规范的根本原理”[15]。是故,不按规律办事,昼伏夜出的行为往往不为古代的道德规范所允许,是与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念背道而驰的,需要进行有为节制。
首先,夜晚主静,可以放松心绪,进行自我内部的调节,是人的一种道德自觉。《孟子·告子上》就提出“夜气”一词:“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是岂人之情也哉? 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16]卷十一《告子章句》,第337页在孟子看来,夜晚是善心萌发之际,暂时屏蔽白日纷扰的世俗欲望,可养浩然之气,这种观念在传统社会中历有延续,夜晚常被允许的多是静坐、读书等一系列闭门之事。从个体延伸到家庭内部,除节日宴饮外,家庭管理者常严格要求各房闭门落户,不可在庭院之间随意穿错。而有志于仕的学子儒生更要熬灯点烛、孤身闭读,晚清名臣曾国藩修身十二条之末就以“夜不出门”约束自己:“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17]11
其次,黑夜向来是被视作罪恶的代名词,成为匪盗出没、作奸犯科等非礼无法者的自由舞台。“在古代人的想象世界中,在风高月黑之际出来的,非抢即盗,非嫖即娼,更不消说还好多人聚在一处。夜幕下不仅是黑暗,而且是阴谋、混乱、肮脏和反叛。这一连串的联想是传统生活习惯的产物,也是传统秩序中建构的观念。”[18]因此,在人们的潜意识中,黑夜往往为不法之徒提供了一种天然有效的安全庇护,是他们掩藏“妖淫谋逆”行径的有力屏障。故民间广泛流传着“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等熟语,代表着上层官方意识的史书也常不自觉地流露出昼伏夜游、非奸即盗的叙事意识,这都使得“夜在文化系统里不光是一个自然的时空概念,同时还是政治的、军事的、伦理的和道德的时空范畴”[19]。
在这样的思想认识下,宵禁制度就不仅仅是对人身体的规训与惩罚,更是对人性、欲望的有为节制。《国朝汉学师承记》就记载了顾炎武拒绝夜饮一事:“东海两学士延之夜饮,怒曰:‘古人饮酒卜昼不卜夜,世间惟淫奔纳贿二者皆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20]卷八,第132页在顾炎武看来,夜晚进行的都是不道德之事,所以才借夜掩饰、趁夜交易,故而他坚决反对夜出聚会。可见,“实行夜禁就既有社会稳定、政权治防的意义,同时也有道德的、世风人性的规约目的”[19],它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承载着深刻的文化意蕴与价值导向。
这种文化意蕴又是深刻复杂的,它固然是上述修身养性、道德约束的一种外化规范,但也同时受到政治文化与经济文化等多重影响。在战乱四起、灾难横行之时,统治者常下达突发命令与硬性要求,其中就包括“宵禁令”,尤以军事宵禁为代表。两国交战期间,城池之间查守细苛、防备森严,城池内部实行军事宵禁,这种暂时性禁制除了维护治安、稳定秩序与方便管理之外,更是谨防间谍进行战争机密的输送,保证信息安全,这在当代社会仍有延续,由此可见它存在的必要性。
正因为宵禁的历史特殊性与其中所蕴含的道德意识,故我们可将昼夜交替视作社会治乱之反映。这不仅是前文所述的隐于黑暗的抢盗嫖娼、兴于战乱的阴谋企图,更是朝代交替、世事兴亡的一面镜子: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世界。[21]354
在王阳明看来,“夜气”象征着一个国家与朝代的气象,治世道德严明,属清明之夜;乱世道德败坏,故而“神气渐昏”;等到道德沦亡,则是昏夜笼罩,家国皆暗沉于夜色之中,不可挽救。到了这个层面,“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16]卷七《离娄章句上》,第282页,小宇宙联系上大宇宙。
当然,除宵禁自身具有文化意蕴外,宵禁的历代沿革同样彰显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如前所述,唐朝尤其是前中期是宵禁实施最严格的时期,宋朝则是宵禁实施最为宽松的朝代,这种“松弛之变”恰恰是宵禁作为一种管理制度受政治、经济影响的鲜明体现。史上常以“盛唐”“弱宋”相称二朝,但这主要是指二者的国威国势,实际上宋朝的太平富足、经济繁茂远超唐朝,尤其是宋统治者“与民同乐”的政治心态使其不断放松对夜晚活动的限制,甚至一度废除宵禁禁令。而元明清三朝统治者为巩固皇权、强化统治,将本已顺应经济发展而日益宽松的宵禁又进行了严格收缩。政治上加强对居民夜晚活动的管控,经济上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都使得原本活跃的商品经济一度低迷。但他们更甚于前的宵禁管控不仅未能挽救政治颓势,反而更加速了封建统治的没落。从这个角度看,宵禁实施严宽程度的变化也反映出封建统治的盛衰演变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势。
三、明清小说中的宵禁书写
宵禁作为古代由来已久的管理制度,本身就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进入到人们的文化记忆当中,“不能否认,文学的夜禁书写其实正是一种‘历史的叙事’”[19],因此,从文学的角度去考察宵禁文化正是历史和文学双向互动的一种必然要求,而在众多有关宵禁书写的文学中尤以明清小说的记述最为详瞻。明清通俗小说尤其是世情小说往往脱离了明君贤臣、英雄豪杰的传奇书写,而致力于普通人生活琐事的描述,所以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宵禁更是成为小说中稀松常见的情节。这些宵禁描写既丰富了宵禁的文化内涵,又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小说的艺术性和现实讽刺感,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与价值。
(一)只许州官放火——宵禁下的舞弊专权
明清小说关于宵禁下的舞弊专权情状的生动刻画,正是对现实生活里宵禁实施现状的戏剧呈现,这在《金瓶梅》中就有形象鲜活的描写。《金瓶梅》往往将西门庆贪赃枉法的行为放置于夜色朦胧、掌灯时分的特殊时刻,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任一角落。第六十九回西门庆为通奸林太太,即“约掌灯上来,就逃席走出来了。……那时才上灯以后,街上人初静之侯”[22]1121,而等他志得意满地骑马回家时,“街上已喝号提铃,更深夜静,但见一天霜气,万籁无声”[22]1126。西门庆的奸情之所以干得如此神不知鬼不觉,很大程度上就是借了更深人静、行人稀少的东风,而宵禁则为其趁夜行事提供了安全保障。因为普通民众限于禁令,入夜后常闭门居家、足不外出,这就为拥有官身护符的西门庆行此掩人耳目的事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此种行径恰恰违背了朝廷设置宵禁令的初衷。宵禁令的设置本就是为了防止黑暗掩盖不法勾当、夜色遮蔽奸恶行径,正如《大明律》在制定夜禁律条时所言“凡盗贼率起于夜禁之不严,夜禁不严,则盗贼多矣”[9]卷十四《夜禁》,第1171页。而西门庆作为当地理刑千户——专门缉拿、问捕等诸多刑事的官员却背道而行。可见,在晚明这个吏治腐败、监察不周的时代,本应公正的朝廷禁令已成为一些特权阶级掩人耳目的弄权之法。
此外,宵禁令有时不仅不能禁除犯罪,反而会成为执法不公、滋生罪恶甚至钻营弥缝的有利便当。应伯爵为了小杀韩玉钏的锐气,故意扬言以犯夜之名让巡捕拿去拶她一顿好拶子。这里固然带有戏谑调笑之意,但以应伯爵久历世间的乖觉圆滑,对其中伎俩想必深得三昧。而韩玉钏“十分晚了,俺们不去,在爹这房子里睡。再不,叫爹这里差人送俺们”[22]624的答语自是与西门庆故作亲昵的得宠之语,却也道出了西门庆无忌宵禁的特权行径。
宵禁制度下非法不公的情况在《醒世姻缘传》中同样存在。监狱作为关押囚犯、保证治安的国家机构,夜巡制度尤其严格,“每更,监中用禁子一人,鸣锣走狱监外,外一人鸣梆,内一人提铃,相约各十步一声。先一声锣,次一声铃,次一声梆,周而复始,不许断续,亦不许铃梆乱响,致令狱中动作不闻”[23]581。监狱夜巡除需狱卒值班外,也会安排相关狱吏随机下监巡查,以防监内出现不法之行。《醒世姻缘传》就有一节写到柘典史“一日间,掌灯以后,三不知讨了监钥,自己走下监去,一直先到女监中”,他发现监狱果然别有洞天后故作公正无私:“原来是个囚妇,我只道是甚么别样的人!这也不成了监禁,真是天堂了!若有这样受用所在,我老爷也情愿不做那典史,只来这里做囚犯罢了!这些奴才!我且不多打你,打狼狈了,不好呈堂。每人十五板!”[24]180但他依法巡监的目的并不是兴利除弊,而只是“闻得珍哥一块肥肉,合衙门的人没有一个不啃嚼他的,也要寻思大吃他一顿”[24]180。于是他接着“出了监,随即骑上马,出了大门,要往四城查夜”[24]181。“查夜”是指州县官夜巡视察更夫、巡夜人的工作情况,防止其出现玩忽职守、懈怠公务的行为,它是宵禁制度的重要环节,许多典籍对其多有记载,《牧令书》中“至官出巡夜亦自有法,如或预行吩咐衙役,则必早为声张,彼皆预备,巡亦无益,必须小灯快马,多带家人随役,出其不意,则怠玩者无从措其手足,因而责警一二,人人畏法矣”[25]卷二十《戢暴·弭盗要法》,第478页即指出了官差查夜的要诀所在。但柘典史查夜显然只是为了做做样子,实际是希望通过查夜为晁大舍打点留下时间,因此他不仅不怕声张,反而有意大张旗鼓以便晁大舍得到声讯。不出所料,当晁大舍听闻典史外出查夜后,立刻以慰问典史查夜为名备酒御寒,水到渠成地拉拢典史,打通关节。此处,作者显然是有意将这些不堪入目的不法勾当设置进有法可依的宵禁时段,使得本应是正当执法的查夜为其提供打通关节、贿赂通行的可乘之机,以此讽刺了人性的贪婪、丑陋和社会的腐朽、黑暗。换言之,由宵禁令而起的查夜成为了作者管窥、洞察世情的聚焦点和契合点。
(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宵禁下的钻营取巧
古代宵禁在实施过程中有时不仅会被特权阶级利用,出现执法不公、滋生罪恶的现象,且法禁律令中颇可伸缩的规定也为市井细民提供了诸多变通或钻营的可能。明清小说就描写了很多避令或钻营的事例,刻画鲜活生动,讽刺入木三分,尤以《金瓶梅》《歧路灯》可堪代表。
以《金瓶梅》中应伯爵和韩玉钏为例,当应伯爵扬言要以犯夜之名使巡捕夹打她时,韩玉钏的第一反应就是“十分晚了,俺们不去,在爹这房子里睡”[22]624,这说明留宿他处即可以避免犯夜。而这种办法似乎也是最通用、最实效之策,且由来已久,早在唐人传奇中就留有这方面的文学印迹。如《任氏传》中郑六从任氏宅回家“及里门,门扃未发”,他选择“坐以候鼓”[26]34。《李娃传》中,遭李娃欺骗的荥阳生想从平康坊重返宣阳坊,向李娃诘问原因,但终因宵禁之前难以抵到而不得已选择“质馔而食,赁榻而寝”[26]101。
如果说留宿不归以避禁令是迫不得已的话,那么夜晚出行则是典型的明知故犯,尤其鲜明地显现出宵禁的难以周全和世风的浇漓,这在《歧路灯》中有具体形象的刻画,其中“夜出遇巡”一段就颇为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清代宵禁政策的执行情状。
第二十六回,谭邵闻受夏蓬若哄骗不顾夜禁而出外聚赌,不巧,刚至街道就遇到巡夜官员,邵闻是“吓了一惊”,颇有退缩躲闪之意,而随身的夏蓬若却镇定自若地安慰谭绍闻道“怕啥哩,一直往前撞去”[27]89,原来这位混迹市井的“捣鬼”早积累了颇多的应对之策,他以为母亲外出抓药为名轻松应付了巡夜人的严查盘问,事后并不无得意地传授绍闻道“晚上街头走动,说是取药就不犯夜了。这一包子金银花,我已使过三遭了”[27]189,甚至在绍闻追问“那无药呢”时更是自鸣得意“那就没法子么?就说是接稳婆。难说做老爷的,去人家家里验女人不成?”[27]189可见,严厉而周密的宵禁制度仍不免会被这些无耻小人钻了“疾病、生产、死丧不再禁限”[9]1170的法律空子,且他们不以为耻,反而颇以此躲避律法的惩罚而自鸣得意,这副小人嘴脸被作者以寥寥数语勾勒得一览无遗,强烈的反讽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作者对那个道德沦丧、聚赌诲淫的浇漓世风的失望和愤慨。
这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明清小说中关于宵禁的描写真实再现了宵禁在实施过程中的不同样态,是宵禁制度生活化、形象化的直观呈现,其文学意义在于叙事者通过小说文本展现出宵禁制度背后更多的生态文化内涵,并借助宵禁这一特殊视角管窥世情、描摹世态,向读者展现出一幅真实的明清社会图景。
综上所述,宵禁作为顺应古代生产、生活方式而产生的制度文化,其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古代阴阳和合的哲学思想和农耕文明下的时空观念及伦理意识的体现,因此一经确立便得到历代统治者的认可和接受。尽管历朝统治者在执行上张弛不同,但毫不例外都将其作为重要的制度载入法典。宵禁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人们的生活秩序,影响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当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病。这些都作为一种文化记忆进入文学作品尤其是明清小说的书写当中,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现象,并生发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当然,宵禁制度作为古代的一种管理制度,在当代社会已不多见,但是它所昭示的文化意蕴及在文学书写上的意义仍值得我们去不断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