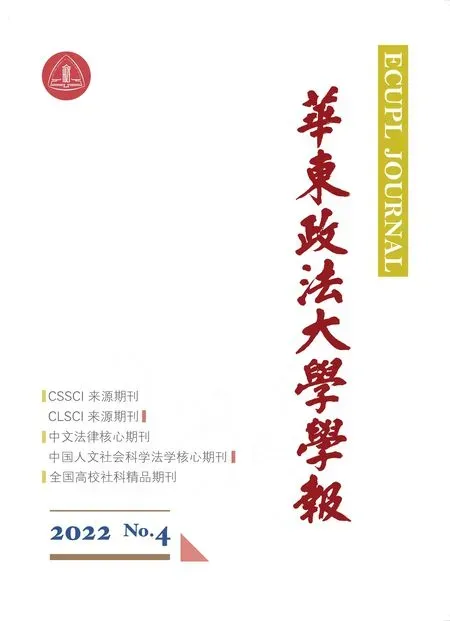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新解
——基于公开权路径的批判与超越
彭诚信 史晓宇
目 次
一、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的研究空白
二、传统公开权路径的起始与发展脉络
三、公开权理论的法理基础演变
四、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之公开权路径的批判
五、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对公开权理论的超越
六、结语
一、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的研究空白
(一)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在数字经济中的体现
在当前的技术背景下,数字经济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人类高质量经济形态,其核心是通过信息的海量收集、加工和整合,形成大容量、高速度、多样化的数据集,借助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指导企业制定富有洞察力的商业决策,从而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数字经济的两大核心是数据和算法,其中数据的主要来源是个人信息的收集,而收集后的信息经过深度处理后可转化为具有财产价值的重要资产,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1〕参见[荷]玛农•奥斯特芬:《数据的边界:隐私与个人数据保护》,彭诚信主编,曹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主编序“算法、数据、规则与法治”,第7页。市场上广泛存在的以个人信息为核心的商业运营模式是个人信息具有潜在财产价值的直观体现,这些商业运营模式的核心就是个人信息的交换和转移。
首先,公司交易中个人信息集合形成的数据是重要的公司资产。例如,面向网络用户的科技型公司的合并与收购,其中汇聚了个人信息的数据集合也被纳入公司合并或收购的范围。在医疗领域中,同样也涉及很多关于患者生理健康信息的数据整合和转移。除此之外,在公司破产中,也不乏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表现。比如,国外部分电子通讯公司在破产中试图向债权人转移用户的个人数据,以达到规避其隐私保护政策中对个人信息加以保护的合同义务。〔2〕参见余佳楠:《企业破产中的数据取回》,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1年第5期,第79-80页。这些都表明个人信息集合形成的数据是企业十分看重的资产。其次,以数据经纪商为核心的数据交易市场已经由理论设想变成现实。美国学者劳登曾设想设立专门的信息受托机构来代理个人信息的数据交易,〔3〕See Kenneth C. Laudon, “Markets and Privacy”, 39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92, 99-101 (1996).目前,美国也已经形成了庞大的数据交易市场,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数据经纪商(data broker)。〔4〕Se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Data Brokers: A Call fo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May 2014.最后,消费者交易合同中随时可能发生个人数据的交换。数字时代带给人们生活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关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基本上都可以通过线上支付的方式完成。比如,每当我们进入一个餐厅通过扫码的方式点单时,微信app内的账户信息也会同步,形成个人的用餐情况等交易信息;通过大众点评app进行搜索、购票及点评出行体验时,这些信息内容也会与个人的身份信息建立联系;通过支付宝app使用城市共享单车,也会同步出行信息等实时数据,这些线上交易都伴随着个人数据的共享。随着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阂被打破,人们越来越习惯于通过数字身份开展各类活动,而人们在虚拟世界中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被忠实地记录和留存于海量的信息数据中,从而塑造了“数字人格”,〔5〕参见马长山:《智慧社会背景下的“第四代人权”及其保障》,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5期,第20页。并通过网络型构了联系消费者、商品或服务及实时监控或评价消费者数据的物联网。〔6〕See Stacy-Ann Elvy, “Contracting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rticle 2 of the UCC and Beyond”, 44 Hofstra Law Review 839, 845 (2016).
(二)既有研究对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的缺漏
个人信息保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被置于“人格权编”,个人信息权益作为一种人格权益为立法所接受,国内学者对此也予以支持。〔7〕参见程啸:《论我国民法典中个人信息权益的性质》,载《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8期,第2-14页。不过,现实中围绕个人信息开展的众多商业运营模式表明,个人信息在数字经济中具有广阔的商业利用前景,因此个人信息权益相对于传统的人格权又有所不同,系内含财产价值的人格权益。〔8〕参见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第85页;彭诚信:《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第119页。个人信息天然的财产性特征决定了个人信息保护需关注其商业利用的路径,即其内含的财产价值如何与主体分离,并外化为可以积极利用的财产,从而为个人信息主体获取数字经济发展的红利提供法律路径。对此,有学者提出所谓个人信息权说或新型权利说,其本质是径行创设一种新的权利,〔9〕参见李伟民:《“个人信息权”性质之辨与立法模式研究——以互联网新型权利为视角》,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3期,第67-71页;钱继磊:《个人信息权作为新兴权利之法理反思与证成》,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4期,第112-118页。但其打破了人格和财产不可通约的民法本旨。有学者指明个人信息权益具有“本权权益”和“外部约束力”的多重构造,提出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首先要注重人格尊严的保护,其次是促进信息的流通利用,挖掘其潜在的财产价值,不过对财产价值的具体实现方式没有论证。〔10〕参见张新宝:《论个人信息权益的构造》,载《中外法学》2021年第5期,第1148-1149页。因此,在现有的理论研究中,对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外化路径的研究尚存空白,而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现状却要求必须对个人信息商业利用中的财产价值保护有所回应。
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需要遵循人格权益向财产权益转化的一般理论,对此,美国法上的公开权历经多年的判例法和制定法的协力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对传统公开权理论的批判展开考察,以期论证传统公开权理论在解决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问题上力所不逮,进而寻求可能的新解。
二、传统公开权路径的起始与发展脉络
美国法下的公开权(The right of Publicity)并非所有州都一致确认的权利,且在承认公开权的各州中,有些州是基于判例法予以承认,有些则是以制定法加以认可,也有二者兼而有之。〔11〕See Rothman’s Roadmap to the Right of Publicity, https://rightofpublicityroadmap.com, accessed January 6, 2022.因此,对传统公开权路径起始和发展脉络的历史性考察需对各州的经典案例进行梳理,同时关注以加州为代表的各州针对公开权制定的法案。
(一)公开权的起始渊源
一般认为,公开权在判例法上被正式确立是1953年弗兰克法官主审的海兰诉托普斯案(Haelan Labs. v. Topps Chewing Gum.),海兰案虽然是公开权在判例法中被承认的标志性案例,但关于其起始,需要追溯至更早的时期,方能对其产生的原因及权利的性质等问题有更清晰、准确的判断。
1.隐私权概念下的“公开”与规范意义上的“公开权”的区分
便携式摄像机的出现促使隐私权不仅限于私密空间和私人生活不受他人干扰的保护,在公共空间中也需要防范对隐私的侵害,尤其是对肖像等身份标识基于商业目的的非法占有。因此,隐私权概念下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对个人身份是否可以用于商业广告宣传的“公开”控制。〔12〕See Jennifer E. Rothma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Privacy Reimagined for a Public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1.这一附属于隐私权概念下的“公开”,早在当下人们所理解的由判例法确立的规范意义上的“公开权”产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其核心内容是一个人控制其姓名或肖像在公共场合被他人使用的方式和时间。〔13〕See Samantha Barbas, “From Privacy to Publicity: The Tort of Appropriation in the Age of Mass Consumption”, 61 Buffalo Law Review 1119, 1120 (2013).隐私权概念下的“公开”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判例中有很多例证。最初的判例是帕维希奇诉新英格兰保险公司案(Pavesich v. New Eng. Life Ins. Co.)。在该案中,原告认为被告未经其许可在人寿保险广告中使用了自己的照片,构成对其个人声誉的诽谤,并造成精神损害,因此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被告的行为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14〕Pavesich v. New England Life Ins. Co., 122 Ga. 190 (1905).在此之后,类似的案件还有很多,均涉及个人肖像照片未经许可被用于商业广告领域。〔15〕Loftus v. Greenwich Lithographing Co., 182 N. Y. S. 428 (N.Y. App. Div. 1920); O’Brien v. Pabst Sales Co., 124 F.2d 167 (5th Cir. 1942).在上述案件中,原告都是基于个人隐私遭受侵犯,造成人格尊严或情感损害而提起诉讼,不涉及侵害财产权益的主张。在规范意义上的“公开权”产生之前,隐私权概念下的“公开”都只关注个人精神损害救济,以个人姓名或肖像的非法公开使用构成对权利人的侮辱、诽谤,引发精神痛苦为前提,而未涉及对当事人财产权益的保护。
2.法律保护的漏洞导致公开权呼之欲出
判例法上创设权利源于既有的权利保护存在法律漏洞。对此,可以从法院对系列案例裁判的变化中得以印证。
首先,在克里斯诉沃克案(Corliss v. E. W. Walker)中,一名已过世的发明家曾与一摄影师签订合同约定由对方为其拍摄个人照片,且不得将其肖像照片向任何第三人转让。原告是该发明家的遗孀,她认为作为被告的某出版商及其职员未经许可将发明家的照片用于出版物,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被告的该项行为。对此,法院认为被告并不是肖像照片许可合同的一方法律关系主体,因此不受合同限制,从而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16〕Corliss v. E. W. Walker Co., 64 F. 280 (1894).该案表明,法院认为,一方面个人肖像标识的控制权不是一项财产权,不可以继承,如果涉诉行为未造成精神损害,其配偶无法基于隐私权获得保护;另一方面,如果被告不是合同关系中的一方,就无法基于合同获得保护。
之后,部分判决除了坚持精神层面的救济外,开始出现关注点向财产层面转移的苗头。在罗伯森诉罗切斯特公司案(Roberson v. Rochester Folding Box Co.)中,被告未经原告同意便将原告照片用于宣传其面粉厂的日历上,原告基于精神损害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认为原告并没有因其肖像照片的使用而面临诽谤等否定性的评价,且其肖像的公开并不会造成个人情感或精神层面的损害,因此没有必要创设一种隐私权之外的新权利。但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判决的依据在于原告主张的是精神损害而非财产损害,并因此导致其败诉。少数意见则明确指出,在被告未经权利人许可而使用其肖像用于产品营销时,应当创设一种不同于隐私权的财产权,以防止企业等主体为了商业利益而侵占他人的肖像。〔17〕Roberson v. Rochester Folding Box Co., 171 N. Y. 538, 556-557, 564 (1902).在蒙登诉哈里斯案(Munden v. Harris)中,原告是一名五岁的幼儿,被告未经原告的许可将其照片用于珠宝产品的广告宣传,原告以被告侵犯其隐私权并造成精神损害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裁判认为幼儿对其照片享有专属权利,而这项权利是具有价值的财产权。〔18〕Munden v. Harris, 134 S. W. 1076, 1078 (1911).对此,上诉法院予以认可,不过上诉法院认为涉诉行为不会对被告造成侮辱等严重的精神损害,因此推翻原审判决。〔19〕Munden v. Harris, 153 Mo. App. 652, 665-666 (1911).从以上两项判例可以发现,虽然非知名人物以其肖像等未经许可为他人使用而主张隐私权保护时,仍须以造成侮辱、诽谤并产生精神损害结果才能获得保护。但已有法院判决承认尽管是非知名人物的肖像未经其许可而用于产品营销时,其财产权利仍然值得保护,只是由于原告仅提起基于隐私权的诉讼而败诉,所以法院才没有进一步试图超越先例而创设隐私权之外的一项新型财产权。
由于大多数普通人的肖像等人格标识不具有显著的商业价值,对其滥用主要是造成精神损害,因此在普通人物的肖像等人格标识被非法用于广告营销的案件中,隐私权保护模式不存在什么困难。不过,一旦出现涉及公众人物或更广泛的人格标识商业应用场景的案件时,这种传统的裁判模式将面临严峻挑战。〔20〕See Harold R. Gordon, “Right of Property in Name, Likeness, Personality and History”, 55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553, 555 (1960).比如,在爱迪生诉爱迪生公司案(Edison v. Edison Polyform Mfg. Co.)中,原告作为知名的发明家,将其发明的药剂制作工艺授权转让给一家公司,后该公司为被告吸收合并。原告认为被告未经许可便将其姓名和肖像用作企业名称和产品营销,于是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被告继续使用其姓名和肖像。在本案中,原告没有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其与被告也不存在同行业竞争的关系,因此无论是基于隐私权还是反不正当竞争保护,都无法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然而法院最终认为公众人物的隐私较之于普通人必须受到限制,并基于衡平法判定原告的财产权益遭受损害,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过,对公众人物是否可就其人格标识被非法商业利用而主张单独的财产权利,该案法官则明确表示不发表任何意见。〔21〕Edison v. Edison Polyform & Mfg. Co., 73 N. J. Eq. 136, 144-145 (1907).
通过以上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法院逐渐注意到在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的场景下,隐私权、合同法或反不正当竞争保护模式存在保护漏洞,特别是当涉诉的原告是知名人物时,因其身份标识具有显著的财产价值,这一法律保护漏洞更加明显。这种观点经历了从最初的不被接受,到罗伯森诉罗切斯特公司案中成为少数意见,直至上升为爱迪生诉爱迪生公司案中的多数意见这一曲折过程。但由于该类案件中原告均是基于精神侵害而非财产权侵害提起诉讼,法院尚未找到合适的契机在裁判中明确阐述这一不同于隐私权的财产权利的存在,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法律保护的漏洞使公开权呼之欲出。
(二)公开权在判例法上的正式确认
1953年海兰诉托普斯案在判例法中正式确立了规范意义上的“公开权”。在该案中,原告公司与一名知名的棒球运动员签订合同,约定其可以在口香糖产品的销售广告中独家使用运动员的肖像,而被告公司诱使运动员签订了同样的授权合同,允许被告在产品宣传中使用其肖像,原告因此向法院起诉。在判决中,弗兰克法官明确指出,除了基于纽约州制定法内的隐私权外,运动员还有权享有其肖像照片的形象宣传价值,即有权授予第三人使用其肖像,且这一权利可以直接转让,法院也可以对侵犯该权利的行为要求财产损害赔偿。这实际上是直接创设了一种新的财产权利来控制名人姓名或肖像等人格标识通过商业利用产生经济价值。本案另一法官斯旺(Swan)虽然同意主审法官的结论,但认为没有必要在判决中专门设立一项新的权利来追究被告责任,完全可依据被告诱使运动员违反与原告的合同而构成第三人侵害合同权利(The Interference of Contract),在既有的合同法和侵权法中得到相同的裁判结论。〔22〕Haelan Labs. v. Topps Chewing Gum., 202 F.2d 866, 868-869 (2d Cir. 1953).
通过对海兰案的阐述可以发现,美国法确实不必通过创设新的财产权的方式解决这一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弗兰克法官创造新的不同于隐私权的公开权就没有价值。正如尼莫所言,公开权确实填补了之前关于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未经许可而被使用的案件中存在的法律保护漏洞。〔23〕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3, 204-215 (1954).在该案后,很多判例都援引并参照了海兰案,从而促使公开权进一步独立为一项不同于隐私权的财产权。比如,在埃托雷诉菲尔科电视广播公司案(Ettore v. Philco TV Broad. Corp.)中,原告以被告未经其许可转播其参加的一场拳击比赛,构成对原告财产权的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法院判决支持原告诉讼请求。〔24〕Ettore v. Philco TV Broad. Corp., 229 F.2d 481 (3d Cir. 1956).在因素公司诉创意卡公司案(Factors Etc., Inc. v. Creative Card Co.)中,原告认为知名歌星“猫王”普雷斯利生前的个人形象商业利用由其进行专业管理,这项公开权是可以继承和转让的财产权,不因普雷斯利的去世而灭失,因此向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被告通过制造、销售印有“猫王”姓名或肖像的纪念品获利,对此,一审和二审法院均予以认可。〔25〕Factors Etc., Inc. v. Creative Card Co., 444 F. Supp. 279 (S. D. N. Y. 1977), aff’d, Factors Etc., Inc. v. Pro Arts, Inc., 579 F.2d 215 (2d Cir. 1978).
通过以上案例可以明确,海兰案为之后的许多判例提供了先例指引,公开权在判例法上被明确为保护名人姓名、肖像、表演等形象标识的经济价值的财产权,可以转让、继承。一项公开权主张在个案中被支持需要满足以下要件:第一,客体必须是名人的姓名、肖像或其表演作品,即因权利人自身的特殊社会地位和名望而使其身份标识具有显著的商业价值,可以在市场上形成产品销售的优势;第二,涉诉行为必须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使用名人的身份标识;第三,未经权利人的许可。
(三)公开权的发展变迁
1. 权利主体的扩张
公开权最初是为了保护名人对其姓名或肖像等身份标识的潜在经济价值而确立的财产权,因此并不扩及非名人。这主要有两方面的考虑:其一,在美国的传统社会文化背景下,公众人物没有隐私,特别是演艺明星,其职业生活需要曝光,并向社会公开,以接受公众的评头论足,维持足够的社会关注度。传统的隐私权只能保护名人的私密生活领域,无法保护其面向公众的形象等身份标识的使用。其二,普遍认为非名人的身份标识本身并不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依据传统隐私权类型中的第四分支“对身份标识的商业性滥用”来防范侮辱、诽谤等精神损害足矣。〔26〕美国学者普罗瑟将隐私权的保护类型基于侵权行为的具体形式进行了四种类型化的区分,其中前三分支均指向私密空间内不为外人打扰的独处的权利,第四分支则是面向公共空间的、对个人身份标识的控制。See William L. Prosser, “Privacy”, 48 California Law Review 383, 389 (1961).易言之,非名人姓名、肖像等身份标识的保护对应的是传统隐私权概念下的“公开”概念,而非规范意义上的“公开权”概念。
不过,之后的公开权判例出现了权利主体从名人向非名人扩张的趋势。在克里斯托弗诉美国雀巢咖啡公司案(Christoff v. Nestle USA, Inc.)中,原告是一名曾做过职业模特的幼儿园老师,因被告未经本人同意在生产的速溶咖啡包装标签上使用了其肖像照片,便基于加州制定法中的公开权起诉,法院最终判决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27〕Christoff v. Nestle USA, Inc., 62 Cal. Rptr. 3d 122 (Ct. App. 2007).如果说该案中原告曾经从事的是面向公众的演艺行业,还不足以完全证实权利主体扩张的趋势,那么21世纪以来出现的典型判例则完全证明了公开权已经不再是由演艺明星等社会名流独享的财产权。在弗雷利等诉脸书公司案(Fraley v. Facebook, Inc.)中,原告等人是脸书网站的注册用户,其主张被告在网络页面的付费广告中使用了原告的姓名和肖像,并注明原告喜欢这些广告所推广的品牌或产品,被告将这些广告向原告的朋友推送和播放。原告基于加州制定法中的公开权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法院判决支持其诉讼请求。〔28〕Fraley v. Facebook, Inc., 830 F. Supp. 2d 785 (N. D. Cal. 2011).再如,在帕金斯诉领英公司案(Perkins v. LinkedIn Corp.)中,原告等人是领英网站的用户,其主张被告从原告的电子邮件的联系人列表中获取了其他联系人的地址,不仅向其发出加入领英的邮件邀请,还在邮件中使用了原告的姓名和肖像。原告基于加州制定法中的公开权向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法院判决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29〕Perkins v. LinkedIn Corp., 53 F. Supp. 3d 1222 (N. D. Cal. 2014).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并非基于加州制定法中的公开权,而依据的是判例法中的公开权。在法院看来,若按照制定法,原告必须同时证明其遭受精神损害,否则其诉讼请求不成立。
通过以上判例可以发现,公开权权利主体的扩张主要是传播媒介的变迁引发的结果。20世纪是电视、广播媒体时代,因此演艺明星、体育明星等名人姓名或肖像的商业价值要远高于普通人。而21世纪是网络媒体时代,特别是自媒体、视频、交友、直播等网上互动交流软件的兴起,使人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社区中的“名人”,其个人在网络社区中的人脉影响力可以转化为产品营销的经济价值。普通个人的姓名、肖像等身份标识的财产价值也逐渐受到公开权的保护,只不过名人与普通个人之间的主体差异在公开权领域仍然存在。一方面,加州制定法中的法定公开权要求普通个人必须证明被诉行为造成其精神损害的后果,且损害赔偿并非源于财产损失,而是法定的最低损害赔偿。〔30〕Cal. Cir. Code § 3344(a) (West 2019).另一方面,与名人的声望具有显著财产价值相比,普通个人的人格标识是在被企业统一收集后才具有整体的财产价值,一般只能通过集体诉讼的方式主张公开权。
2. 权利客体的扩张
公开权最初仅限于个人的姓名、肖像,随着判例的扩展,其客体范围也迅速扩张,可以涵盖姓名、肖像、声音、表演、行为等,甚至除了现实身份标识之外,还可以包括扮演形象中的虚拟身份标识,即一切足以使受众唤起与主体身份联系的人格标识。〔31〕See Sheldon W. Halper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Maturation of an Independent Right Protecting the Associative Value of Personality”, 46 Hastings Law Journal 853, 856 (1995).如米德勒诉福特汽车公司案支持了对声音的公开权保护,〔32〕Midler v. Ford Motor Company, 849 F.2d 460 (9th Cir. 1988).卡森诉约翰尼便携式厕所公司案支持了对特定语言表达的公开权保护,〔33〕Carson v. Here’ s Johnny Portable Toilets, 698 F.2d 831(6th Cir.1983).怀特诉三星电子公司案支持了对特定形象和动作的公开权保护,〔34〕White v. Samsung Electronics America, Inc., 971 F.2d 1395 (9th Cir. 1992).卢戈西诉环球影业公司案支持了对特定扮演角色形象的保护等。〔35〕Lugosi v. Universal Pictures, 603 P.2d 425 (Cal. 1979).此外,在制定法中,同样存在权利客体的扩张趋势,如印第安纳州的法案规定姓名、肖像、声音、签名、独特外观、特定手势、行为习惯等都可纳入公开权的客体范围。〔36〕Ind. Code § 32-36-1-6 (2019).
三、公开权理论的法理基础演变
海兰案的主审法官弗兰克将心理学层面的精神分析应用到司法审判实践中。要想证成公开权的独立性,首先需要找到公开权与隐私权相分离的理论基础,从深层次讲,需要考虑人格之上何以能分离出具有财产性质的权利,如果这点无法证成,就必然会面临学者们对人格商业化正当性的质疑。〔37〕马多指出,弗兰克法官只是基于名人无法控制其姓名、肖像的潜在商业价值而创设一项财产权,这一论据并不充分,完全没有考虑到人格被商业化后与财产毫无差异造成的道德层面的巨大不良后果。See Michael Madow,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Image: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ity Rights”, 81 California Law Review 125, 173 (1993).对此,弗兰克法官基于弗洛伊德将人格区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精神分析理论,得出人格并非不可分的结论,继而从荣格对人格的二元划分理论中找到公开权可以独立于隐私权存在的基础。荣格将人格区分为内在自我与外在人格,其认为后者只是为了获得社会认可或经济利益而在公众场合呈现的“虚假面具”〔38〕C. G. Jung, “The Persona and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 in Herbert Read, et al. ed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 G. Jung:Two Essays Analytical Psychology, translated by R. F. C. Hu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92.。因此,公众人物展示在媒体面前用于实现经济和商业价值的不是人格,只是用于公共交流的社会角色,而真实的自我始终隐藏在角色曝光的阴影里,因此也就不存在出卖人格的道德难题。基于以上分析,公开权虽然出自人格层面的隐私权,但其实质却为财产权。
(一)经济产权理论
弗兰克法官基于精神分析理论对公开权作为一项新权利的证成,必然导致公开权具有财产权利属性这一结论,其后的学者也由此讨论公开权的正当性基础,大体包括劳动产权理论、不当得利、经济激励和消费者权益保护四个角度,其论证理由均是经济产权层面为公开权提供的法理基础。
第一,一般认为公开权的法理基础建立在约翰•洛克提出的劳动产权理论基础之上。尼莫最初就是从劳动产权理论的角度来证成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正当性,他指出:“个人都应当有权享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只有在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技能甚至金钱之后,才能获得相当可观的金钱价值。”〔39〕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19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203, 216 (1954).按照这一逻辑,公开权行使的正当性基础是相关的名人通过努力工作为自身身份带来的经济效益。
第二,赋予名人控制其身份名望所带来的经济价值有利于纠正不公平的财产价值分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求。即使名人为保持其社会名望和声誉所付出的必要努力无法构成劳动,也可以通过纠正不公平的价值分配的方式为名人控制其身份的商业利用提供合法基础。公开权可以防止社会上出现不当的搭便车行为,即防止他人在没有播种的情况下收获。〔40〕See Thomas McCarthy & Roger E. Schechter, The Rights of Publicity and Privacy, West Group, 2019, §2, p. 6.其设立缘由可以归结为防止不当得利,保证其他人必须通过付出相应代价才能利用公众人物的名望获取经济利益。不过,不当得利的前提是公众人物的身份标识是个人独有,而现实情况是公众人物的形象和个性并不完全由个人独立塑造,相反需要汲取社会和文化才能形成,因此其正当性存疑。
第三,创设公开权有助于为创造社会财富提供经济激励。美国最高法院至今唯一裁判过的公开权案例是扎齐尼诉斯克里普斯霍华德广播公司案,其中体现了创设权利用于经济激励的说理思路,论证了表演者对其角色的商业利用享有控制权的正当性。该案确定的公开权与著作权的价值相当,是为了通过赋权的方式促使人们愿意花费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创造有益于社会的作品,从而实现经济激励。〔41〕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 Co., 433 U.S. 562, 576 (1977).赋予名人对其表演角色的控制权可以弥补聚光灯下的负面影响,从而鼓励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愿意冒险登上舞台并向社会公众展示作品的人就会减少。〔42〕See Michael Madow, “Private Ownership of Public Image: Popular Culture and Publicity Rights”, 81 California Law Review 127, 206 (1993).不过,对此种理论观点也不乏批评的声音。首先,在特定公共领域取得成功的激励和发展社会公共角色的激励虽然时有重叠,但通常并不相同。并非所有取得巨大成功的明星都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并在公众中间形成广泛影响力,换言之,也并非所有具有公众号召力的名人在其职业领域内都可获得专业性的成功。〔43〕See Mark P. McKenna, “The Right of Publicity and Autonomous Sell-Definition”, 67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Law Review 225,259 (2005). 比较典型的情况就是在演艺圈存在所谓流量明星和实力派演员的区分。其次,公开权的经济激励价值并不总是呈现对社会的正向作用,有可能导致对名人活动的过度投资,有学者将其称为只是“产生了一些为出名而出名的人”。〔44〕See Jennifer E. Rothma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Privacy Reimagined for a Public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01.最后,着重保护创作动机这一焦点的偏离会导致公开权侧重于保护权利人的“作品”,而非其本身作为“人”的存在,由此也导致公开权的保护范围仅限于具有商业价值的名人形象,而不能惠及公共领域中的普通个人,使公开权成为仅服务于少数上流名人的特权。〔45〕See Joshua L. Simmons & Miranda D. Means, Split Personality: Constructing a Coherent Right of Publicity Statute, https://ssrn.com/abstract=3187810, accessed February 20, 2022.
第四,创设公开权有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在美国法上,有些学者主张公开权应当是一种商标权,其价值在于防止消费者混淆名人商品代言,难以区分产品的来源。〔46〕See Stacey L. Dogan & Mark A. Lemley, “What the Right of Publicity can Learn from Trademark Law”, 58 Stanford Law Review 1161, 1190 (2006).根据这一理由,当消费者面对由某一名人形象代言的产品广告时,会自然地将名人的声望与对该产品或品牌的赞助和支持联系在一起,此时创设公开权可以为名人提供诉讼的途径,防止他人未经许可将其身份形象用于对产品的背书,从而保护消费者权益。根据这一导向,公开权被限定在造成公众混淆的案件中,避免该权利概念过于宽泛。不过,基于该种理由的公开权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其最致命的缺陷在于,鉴于公开权和商标法关注的焦点并不一致,如果将二者完全融合,将会导致人格标识商业利用活动的规制重点由保护自然人对其身份经济价值的利益转向保护公众对免于欺骗的利益,偏离了未经授权盗用自然人人格标识所涉及的真正利益。〔47〕See Sheldon W. Halpern, “Right of Publicity: The Commercial Exploitation of the Associative Value of Personality”, 39 Vanderbilt Law Review 1199, 1242 (1986).也就是说,虽然创设公开权有助于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但其核心仍然是保护名人对其身份形象的控制,因此避免消费者对产品的混淆只是其附带价值。其次,在美国制定法已经存在《兰厄姆法案》〔48〕15 U.S.C. § 1125(a) (2018).(《联邦商标法》)的情况下,将公开权再理解为商标权便显得功能重复且多余。申言之,如果公开权的真正关注点是保护消费者,那么就应通过修订《兰厄姆法案》以纳入该意图,而不是让公开权构成单独的诉讼理由。
(二)个人自治理论
经济产权理论下,公开权是一项财产权,可以自由转让和继承。〔49〕11 U.S.C. §541(a)(1).按照这一逻辑,公开权控制下的经济利益可以用于清偿债务,甚至作为破产财产或婚姻共同财产。但司法实践并没有坚持该观点,在高盛诉辛普森案(Goldman v. Simpson)中,法院直接指出公开权不能转让给债权人。〔50〕Goldman v. Simpson, 72 Cal. Rptr. 3d 729 (Ct. App. 2008).类似的,制定法层面也有明确禁止向债权人转让公开权的立法例。〔51〕例如,伊利诺伊州法中虽然认可公开权是一项可以转让的财产权,但是明确禁止将其作为破产财产用于清偿债务。在离婚案件中,将个人声望价值所产生的经济收入向配偶分享的前提是配偶对其职业的成功或发展有所贡献,言外之意就是当公开权所体现的声望价值纯粹属于夫妻中的一方时,不能用于财产分割。〔52〕Elkus v. Elkus, 572 N. Y. S. 2d 901 (App. Div. 1991), Piscopo v. Piscopo, 557 A. 2d 1040, (N. J. Super. Ct. App. Div. 1989).以上例证都表明现实中公开权的转让和继承受到限制,与财产权的一般理论出现逻辑矛盾,这是公开权可转让定性必然产生的消极后果。公开权以权利人对其身份形象的控制为核心,不过这种控制在现实中可能因财产权的可转让性而无法实现,并导致对权利人的保护不足。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合同谈判能力的差距造成权利人的控制力量薄弱。演员、歌手、模特、运动员等不一定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在其职业生涯早期尚未成为公众人物前谈判能力有限。公开权表面上看似是保护角色形象的有力途径,实际上很容易转化为经纪公司或品牌开发商买断其身份形象的法律工具。其二,当权利人与相对方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时,相对弱势的一方会面临身份剥夺的法律风险。比如未成年子女的身份形象公开权如果允许由其父母代为转让,那么会导致其在成年后丧失对其身份形象的控制。〔53〕Shields v. Gross, 448 N. E. 2d 108 (N. Y. 1983).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以及雇主与雇员之间,如果双方存在债权债务纠纷,处于弱势的一方可能随时面临身份形象财产价值被剥夺的危险。
上述消极后果都源于公开权的经济产权理论对个人身份形象的理解出现偏差,个人身份形象从本质上讲立基于人格,关乎个人的尊严和自治,因此并不完全植根于获取经济价值的功利性理由。〔54〕See Jennifer E. Rothman, The Right of Publicity: Privacy Reimagined for a Public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55.由精神分析理论对内部自我与外部自我的区分而发展出的经济产权理论看似可以保护外部自我,实际上会对内部自我人格的造成侵害。因此,关于公开权的法理基础讨论,出现了以海默里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他们主张立基于个人尊严与自治的法理基础,反对仅从功利性的角度出发将公开权作为一项完全的、可转让、可继承的财产权。
与以洛克劳动财产理论为基础的经济产权理论不同,主张个人自治理论的学者首先试图明确公开权的正当性基础并非经济上的理由,而是关乎个人的尊严和自由。对一个人的姓名或肖像的商业利用行为,即使在客观经济层面为个人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也仍然侵犯了公开权,这是由于未经本人许可的商业利用行为损害了个人的尊严,削弱了个人的自由。〔55〕See Roberta R. Kwall, “A Perspective on Human Dignity, the First Amendment, and the Right of Publicity”, 50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1345, 1346-1353 (2009). Edward J. Bloustein, “Privacy as an Aspect of Human Dignity: An Answer to Dean Prosser”, 39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962, 971 (1964).由此,公开权的重点从严格的经济权利转移到同样注重道德和人格的权利。海默里从康德哲学中寻找公开权的正当性理由。在康德看来,自由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是因人性而属于每个人的唯一和原始的权利。康德哲学中自主性的核心概念,为公开权提供了哲学上的理由,即自主意味着个人有权控制对自己人格身份的使用,具体表现为免受他人强迫的自由。〔56〕See Alice Haemmerli, “Whose Who-the Case for a Kantian Right of Publicity”, 49 Duke Law Journal 383, 416 (1999).海默里试图将个人自治的概念与康德的财产理论联系起来,财产源于自由,而自由对形成主体的自我人格必不可少,因此作为人格天然来源的个人最应当有权利主张就其身份标识开展商业利用的财产权益。
(三)网络社区兴起后出现的第三种理论
经济产权理论与个人自治理论都采纳了弗兰克法官对个人自我人格两分的精神分析观点,不过近年来美国学者马尔兰提出了公开权法理基础的新理论,即不再以内外界分作为限定人格的方式,而是将人格理解为人与人之间表达性的交际行为。个人自我人格在现代网络社交媒介更新的背景下很难固守内外严格区分的传统,个人的自我人格不再是传统精神分析领域提出的所谓“孤立个体心灵的神话”,而是“正在进行的动态交互主体系统”,〔57〕Robert D. Stolorow & George E. Atwood, Contexts of Being: The Intersubjectiv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ical Life, Analytic Press, 1992, pp. 7, 30.个人自我人格的形成来源于其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领域中交往的经验,与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人们在日益频繁的交流互动中形成基于情境的身份,这种基于交流互动形成的对个人自我人格的界定可以归纳为“主体间性”〔58〕国内有学者将哲学上的“intersubjectivity”翻译为“主体间性”,本文遵循该译法。参见童世骏:《没有“主体间性”就没有“规则”——论哈贝马斯的规则观》,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第24页。(intersubjectivity)。〔59〕See Dustin Marlan, “Unmasking the Right of Publicity”, 71 Hastings Law Journal 419, 459-460 (2020).类似的,科恩将网络空间中个人身份的概念描述为“化身人类社会实践的纽带”。〔60〕Julie E. Cohen, “Cyberspace as/and Space”, 107 Columbia Law Review 210, 236 (2007).马尔兰等人吸收借鉴哲学界提出的“主体间性”的观点,将其应用于个人身份标识商业利用领域,可以理解为在网络媒介产生的背景下对传统公开权理论的改造和发展,其目的是将传统现实世界中的公开权理论适用于网络虚拟空间,以防范虚拟空间中可能出现的对个人身份形象的滥用,其主要功能在于为个人在网络社交中过滤过度的信息收集和由此出现的个性化广告推荐。
四、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之公开权路径的批判
(一)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与公开权路径形似神异
公开权在保护客体上的扩张趋势意味着所有足以识别到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内容都可能被作为个人人格标识予以保护,具体来说,公开权的客体范围标准采用的是“关联结合”标准(Associative value)。所谓“关联结合”是指当姓名、肖像、声音等这些特定人物的身份标识被应用于产品或服务营销活动中,促使消费者产生联想,将产品或服务与该人物关联结合在一起,从而起到商品促销的作用。按照这一标准,公开权的客体范围与个人信息存在相似性。一方面,二者的客体范围都涵盖了自然人的身份、行为标识;另一方面,在客体范围的判断标准上都采纳了识别说,即对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行为的识别。因此,个人信息的多样性不再是其财产价值通过公开权进行保护的障碍。不过,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外化路径与公开权路径仍然是形似神异,即二者存在诸多“质”的差异。
第一,公开权中的人格标识和主体之间的关联方式与个人信息不同。姓名、肖像等人格标识与主体之间的联系主要是以产品或服务营销活动的受众消费者认知作为识别依据,而个人信息对自然人的识别包括数字化技术手段的识别。因此,对于某一条个人信息,数字化技术手段应用具有一般性,不会因主体的不同而在识别方式和手段上有差别,而在公开权中,社会公众识别和区分主体标识的前提就是主体本身的声誉、名望等个性,只有在公众领域形成一定影响力的主体标识才能构成公开权的保护客体,体现了其权利主体较之于一般群体的区分性。
第二,个人信息财产价值不是因为其中某一条个人信息有多高的价值,而是来自众多信息内容整合后的分析和挖掘价值。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外化可以反映在数据生产领域,数据生产涵盖了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后续的其他处理行为,从个人信息主体获取的原始个人信息通过汇集、推演、分析,会形成高质量的衍生数据和数据产品,从而凸显财产价值。〔61〕参见高富平:《数据生产理论——数据资源权利配置的基础理论》,载《交大法学》2019年第4期,第9页。在数据生产环节中,无论是汇集性的数据处理还是分析性的数据处理,主要的贡献者和参与者都是以数据企业为代表的数据生产者,个人信息主体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与之相反,公开权保护模式下,某一姓名或肖像等人格标识的价值恰是基于主体个性或身份的与众不同才唤起社会的关注,并带来经济效益。公开权保护的人格标识的财产价值是从一开始就立基于个人对其人格标识的积极处分和利用,而不同于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主要通过后续数据生产者的参与而被实现。上述财产价值来源的差异反映了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是数据加工形成的附加价值,而公开权模式下所保护的个人人格标识的财产价值是主体的声望价值,源于人们对权利主体的公众形象的身份认同,而理解并寻求相应认同的公众为权利人提供了财产权益实现的路径。〔62〕See Bi-Rite Enters., Inc. v. Button Master, 555 F. Supp. 1188, 1199 (S. D. N. Y. 1983). Ali v. Playgirl, Inc., 447 F. Supp. 723, 728(S. D. N. Y. 1978)
第三,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与公开权模式所依据的法理基础存在差异。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不能套用公开权模式所依赖的任何一项法理基础。
首先,经济产权理论下,个人对其姓名或肖像等人格标识可以主张财产权利的正当性基础是劳动,由于权利人为其公众形象在社会范围内的声望提升付出了个人努力,故而在道德上使其享有对公众形象利用产生的财产权益。如果将该理论适用于个人信息商业利用领域,会出现诸多疑问。因为,劳动赋权仅是在最低限度证明个人信息经商业利用产生的财产价值被凝聚在生产的数据中,难以回应究竟是谁在生产以及在不同的数据生产者之间如何分配财产价值的问题。〔63〕参见韩旭至:《数据确权的困境及破解之道》,载《东方法学》2020年第1期,第102页。还有,劳动赋权仅意味着创造信息财产价值的数据生产者会独享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而信息流动链条中的其他参与者将无法获取个人信息的任何财产价值。以上荒谬结果的产生源于经济产权理论本身与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并不契合。经济产权理论认为当某一权益之上存在相反的主张时,劳动使其中一方获得排他性的所有权是可接受的结果,故而在上述理论下,权利人对人格标识享有绝对的控制和支配权,这在个人信息商业利用领域显然行不通。一方面,个人信息的信息本质决定了其无时无刻不在流动、复制,因此其可以不断再生,同时为多个主体所使用。〔64〕参见梅夏英:《在分享和控制之间 数据保护的私法局限和公共秩序构建》,载《中外法学》2019年第4期,第853、856页。另一方面,赋予某一主体对个人信息绝对的控制、支配权与个人信息的社会公共价值不符,甚至会造成信息垄断。个人信息主要是在社会交往环境中产生的,具有刺激信息流通、鼓励科技创新、保障言论自由的公共价值。个人信息作为集合的整体资源性价值不容忽视,上述资源价值的开发显然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加入。
其次,个人自治理论虽然可以克服个人信息商业利用中可能存在的对个人人格尊严侵害的问题,但其价值立基点仍在于控制和支配,与信息的流通共享本质存在冲突。而且,事实上因信息处理技术的复杂性和不可预知性,个人对其信息的全面支配也不可能完全实现,个人对其信息内容的控制无法覆盖个人信息流向的整个生命周期。〔65〕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载《法学研究》2018年第3期,第99页。因此,这种基于控制和支配的主体自由很难实现。
最后,马尔兰提出的以“主体间性”作为公开权的法理基础,在现实样态上也无法涵盖个人信息商业利用的交易结构。个人信息中的财产价值交易链条具有时空上的无限延展性,远非传统的有形资产所遵循的线性交易结构所能涵盖。〔66〕参见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第92页。按照马尔兰的理论,普通线上用户与信息收集者达成的交易主要是一对多的格式合同,在发生争议纠纷时为线上个人信息主体提供集体诉讼的救济途径。然而,上述交易形态只限于用户创制和生成内容的网络交流社区,最典型的情形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和大众点评、豆瓣等生活内容评价、推荐和共享平台,无法涵盖所有的个人信息商业利用场景。申言之,基于“主体间性”所产生的公开权保护的交易形态是线下熟人社会的线上虚拟形式(如微信、QQ)或线下陌生人社会的线上虚拟形式(如微博、大众点评、豆瓣等),其共同点是个人直接参与信息内容和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其财产价值的来源仍然是人们在线下社会关系中所建立的交流信任。以上交易形态只是大规模信息处理活动的冰山一角,后续的数据生产者对信息数据的加工和分享则完全无力涵盖。
(二)适用传统公开权路径导致信息不平等关系加剧
在个人信息商业利用中存在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不平等的权利对比关系,国内有学者将其称为“持续的信息不平等关系”。〔67〕参见丁晓东:《个人信息权利的反思与重塑 论个人信息保护的适用前提与法益基础》,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341-345页。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自然人较之于大型数据企业等信息处理者在思维认知能力、信息掌握和获取能力等方面存在天然的差距,因此自然人面对在线服务供应商披露的信息隐私政策时,不足以评估被收集的信息潜在的使用方式,从而对其个人信息权益的风险难以作出有效的预判。〔68〕See Daniel J. Solove, “Privacy Self-Management and the Consent Dilemma”, 126 Harvard Law Review 1880, 1889 (2013).其次,以机器算法为代表的自动化处理的广泛应用导致个人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鸿沟被进一步放大。海量的信息数据汇集后通过自动化处理生成相应的决策,由此信息处理活动规则被各种技术代码和算法黑箱占据,容易诱发算法歧视和偏见。〔69〕参见李成:《人工智能歧视的法律治理》,载《中国法学》2021年第2期,第136页。最后,自然人交易磋商能力相对低下,难以在信息处理活动中获得真正的选择自由,人们很容易陷入算法主导的商业决策中,造成集体性的盲从而丧失个体的意志自由。〔70〕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7页。
上述信息主体与信息处理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导致个人信息主体无法通过有效行使控制权的方式实现个人的意志自由。传统公开权所遵循的控制、支配原则会出现失灵的问题,即导致赋权的同时又失权的矛盾现象,加剧个人信息商业利用领域主体关系的不平等,造成个人信息权益受侵害。〔71〕参见马长山:《数字时代的人权保护境遇及其应对》,载《求是学刊》2020年第4期,第107页。具体来说,传统公开权模式下所要求的财产可转让性会加剧现有市场中个人信息交易的弱点,引发颇为吊诡的矛盾:在传统的财产自由转让模式下,个人对其财产有足够的控制力,而在网络数据交易领域,个人在磋商协议能力上与数据处理企业的实质不对等,导致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力实际削弱,数据企业获取的个人信息在进行二次数据交易时可能会违背个人的意愿,或者超出个人授权的数据使用目的和范围,因此财产自由转让规则在个人信息市场上并不能适用。〔72〕See Pamela Samuelson, “Privacy as Intellectual Property”, 52 Stanford Law Review 1125, 1138 (2000).寄希望于通过披露信息隐私政策、获取用户对每一次信息收集或后续处理行为的同意方式,强化个人对其信息的控制对减少网络新媒体和平台用户之间的不平等权利分布状态,几乎没有任何作用。一方面,对普通的个人用户而言,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活动难以被真正理解,即使披露和公开也毫无意义,相反会成为平台规避和摆脱侵权责任的工具。另一方面,用户对信息隐私政策的同意不能等同于传统公开权模式下对其身份可用于商业营销活动的许可,大多数人都不会仔细阅读长篇累牍的信息隐私政策声明,这种同意不是医疗活动或姓名、肖像标识商业化利用中的肯定性许可,而只是一种被动的知晓和选择。〔73〕See Robert H. Sloan & Richard Warner, “Beyond Notice and Choice: Privacy, Norms, and Consent”, 14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Law 370 (2013).综合以上,将公开权保护模式适用于个人信息商业利用领域,会造成个人信息及其财产权益被转移,个人将丧失对抗个人信息被无限制收集、储存、加工、处理和传输的权利,并对个人生活及其人格的自我发展产生持久的消极影响。
五、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对公开权理论的超越
个人信息与姓名、肖像等人格身份标识一样都体现着主体的人格尊严价值。其在财产价值上的最大差异在于个人信息的财产价值并非一开始就可以显现,而是需要通过数据生产者的参与,才能创造附加的财产价值。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路径一方面需要解决与人格相关的信息内容如何可以与主体分离,成为可以普遍实现自由转让的商品,另一方面也要尊重数据生产者对信息财产价值有所贡献的事实,保障数据生产进程中的参与者获取财产价值的主体权益。
(一)个人信息与主体分离成为商品的路径证成
1. 个人信息财产价值外化的一般判断基准
当客观存在与人或人的身体生命相关时会面临商品化上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这些客观存在与人格紧密相关,如果允许其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进行交易会面临道德伦理上的非议,违背法律上人格与财产不可通约的理论前提,造成人格被降为物格,贬损个人的主体尊严。对此,拉丁将这些与人或人的身体生命相关的内容称为“有争议的商品”(contested commodity)。〔74〕Margaret Radin, Contested Commodi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xi.根据拉丁的理论,某一与人格相关的客观存在能否与主体分离从而成为法律上允许转让的商品,需要经过筛选和评价,在满足相应的条件后,才可以商品化并实现其财产价值。具体来说,与人格相关的内容的商品化需要保证不侵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要符合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的要求。拉丁认为,如果商品化导致放弃或出卖个人的自由,这种对个体自由的践踏最终会造成广泛的社会损失,只有尊重并保护人们共同的意志自由,才能使得社会整体从商品化中获益。〔75〕See Margaret Jane Radin, “Market-Inalienability”, 100 Harvard Law Review 1849, 1854 (1987).
2. 个人信息与主体分离的可能性
个人信息关乎的个人在传统线下社会的自然评价和在数字社会的算法评价,是构成个人人格完整性的重要内容。〔76〕参见彭诚信:《论个人信息的双重法律属性》,载《清华法学》2021年第6期,第81页。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决定了其不可以完全不受限制地进行商品化,个人信息商品化在本质上是个人信息之中财产价值的外化。然而,个人信息之上人格利益与财产价值在物理上的不可分性,使得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商品化也需要受到限制,〔77〕参见彭诚信:《数字社会的思维转型与法治根基——以个人信息保护为中心》,载《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5期,第121页。否则破坏人格完整性便会损害个人人格的尊严价值。个人信息内含的财产价值经线上自动化处理后便可外化出来,如果能够确保个人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个人信息主体便有权按照自己的意志自主决定何时、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人传达有关自身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不能确定其个人信息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第三方获取,个人信息主体即被剥夺善意行为的自由。〔78〕See Charles Fried, “Privacy”, 77 Yale Law Journal 475, 483 (1968).这种关于意志自由的价值预设在线上个人信息处理中很容易被打破而丧失意志自由。具体来说,当企业通过关于个人需求和偏好的信息来开展商品和服务投放时,人们会在潜移默化中失去对自主行为的控制。个人的思想、信仰和行动本来就容易被周围环境影响和塑造,自主性也因此不可避免地陷入所处的场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动态构造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们的习惯、偏好和信念。〔79〕See Julie E. Cohen, “Privacy, Ideology, and Technology: A Response to Jeffrey Rosen”, 89 Georgetown Law Journal 2029,2034-2035 (2001).具体到企业的商品和服务营销实践中,企业可以利用人们过去的行为特征信息塑造其关于未来的偏好和选择,从而达成从预测到控制的目的,削弱个人信息主体的意志自由。
基于以上分析,个人信息财产价值从其人格属性中抽离出来本身不成问题,只是需要在保障个人意志自由与鼓励创造信息财产价值的数据生产者之间确定实现利益平衡的具体方式,而这是基于个人身份控制而形成的传统公开权路径所不能解决的。
(二)告知选择作为个人实现其信息财产价值的方式
1. 告知选择与公开权模式下合意的区别
现实中个人信息财产价值是以数据生产者开展的数据处理活动实现的,个人信息主体是通过网络参与到信息流动的链条中。既然传统公开权所采用的赋予控制权的方式会加剧对个人信息权益的损害,那么就应当重新理解个人在网络空间中做出的同意在法律上的效果,避免将其直接作为授权的许可。在传统的公开权模式下,个人主要是通过签署许可合同的方式将其身份标识授予他人使用,在法律效果上体现为双方当事人就财产权益的划分达成了真正的合意(real consent)。〔80〕按照拉丁对“真正的合意”的理解,需要双方就合同中的核心条款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磋商后达成深入的共识,通常需要有专业的背景知识作为支撑。See Margaret Jane Radin, Boilerplate, the Fine Print, Vanishing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89.而在网络环境下的信息收集和数据生产活动中,无论个人主观上是否积极地做出同意,在客观上都是被动地参与,体现为告知选择(notice and choice)。告知选择在性质上不同于一般的合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印证。
第一,告知选择规则与合意规则设立的出发点有所差异。“选择”意味着根据对方提供的内容和事项进行被动的接受或不接受,其默认的思维方式是“常人”的启发式选择机制。〔81〕See Margaret Jane Radin, “Taking Notice Seriously: Information Delivery and Consumer Contract Formation”, 17 Theoretical Inquiries in Law 515, 517-518 (2016).“合意”意味着双方通过磋商等积极的互动达成一致,其默认的思维方式是“理性人”的风险评估自负机制。选择意味着自然人在面对个人信息处理时,除了选择接受或不接受没有任何其他更有意义的方式。相应地,很难说自然人在选择接受时与个人信息处理者达成了合同法意义上的有效合意。〔82〕See Ari Ezra Waldman, “Privacy, Notice, and Design”, 21 Stanford Technology Law Review 74, 78 (2018).
第二,选择的对象与一般合意的对象存在差异。在个人信息处理领域,个人信息选择接受或不接受的是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的隐私或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声明,其内容并非双方基于平等关系经磋商达成的一对一的合同关系,而是在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由相对强势的个人信息处理者一方提供的一对多的格式条款,相应地在合意成立与生效规则上有所差异。
第三,选择的客体与一般合意的客体存在差异。个人信息主体选择的客体是个人信息权益,而一般合意则包括个人经济和生活事项中需要保护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个人基于一般的理解和预判对其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所做的选择不见得比对其身体健康与完整性利益、常规生活与经济事项选择更容易。
2. 告知选择的法律效果
告知选择具有不同于一般合意的法律效果。以美国和欧盟为例,美国法上对告知选择的法律效果,出现了两种不同观点。其中一方以拉丁为代表,提出选择并非接受合同的承诺,双方并不存在真正的合意,此时合同没有成立。〔83〕See Margaret Jane Radin, Boilerplate: The Fine Print, Vanishing Rights, and the Rule of La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pp.30-33, p.177.另一方以沙哈尔为代表,提出选择虽然不同于传统合同法上的合意,但是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场景下,除了采用隐私保护政策声明的格式条款来框定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外,没有更好选择。因此,应当认为个人信息主体与个人信息处理者之间成立合同关系,不过是否具有法律强制履行的效果(enforceability),则端赖格式条款内容的具体规定是否有对个人信息主体权利的不当剥夺,如果存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的情况,个人信息主体可以随时主张合同撤销。〔84〕See Omri Ben-Shahar, “Regulation through Boilerplate: An Apologia”, 112 Michigan Law Review 883, 886 (2014).统观美国法上对选择的法律效果的两种观点,可以明确双方其实殊途同归,均实现了将告知选择规则与合同法上一般合意规则相区分的目的,只是合同成立说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与保护上借鉴了合同法的有关规则,通过合同是否在法律上有强制履行的效果,实现了对个人信息主体的权益保护。
而在欧盟法律语境下,根据GDPR立法理由书第32条的规定,沉默、预先勾选的对话框或不作为,均不构成同意。不过,该条同时指出数据主体的同意可以包括“在访问网站时勾选对话框,选择信息社会服务的技术设定”。〔85〕Article 32 of GDPR Recitals.这意味着GDPR将“选择”纳入个人同意的方式中,不过将预先选择行为排除在同意范围之外。结合GDPR规范指南中规定“只有向数据主体提供了控制权,并且在接受或拒绝所提供的条款或在不损害其利益的情况下拒绝这些条款方面提供了真正的选择,同意才能成为适当的法律依据”。〔86〕Se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Guidelines 05/2020 on consent under Regulation 2016/679, Version 1.1, adopted on 4 May 2020, p.5.根据GDPR规范指南,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获取个人同意的过程存在瑕疵,同意会沦为无效的法律基础,这表明GDPR其实已经将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个人被动的选择与同意做了区分,被动的选择并不能产生同意的法律效果,相应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具有违法性。进一步说,欧盟GDPR所要求的同意与合同法上一般的合意也有实质区别。GDPR规范指南中指出“即使个人信息的处理是以当事人的同意为基础的,这也不会使收集个人信息的行为合法化,因为就特定的处理目的而言,收集个人信息是不必要的,从根本上讲是不公平的”。〔87〕See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Board, Guidelines 05/2020 on consent under Regulation 2016/679, Version 1.1, adopted on 4 May 2020, p.5.因此,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同意如果无法基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关系,也不应视为双方达成有效的合意。
综合美国与欧盟法律对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存在的“选择”的处理方式,其体现了殊途同归的特点。首先在价值层面上,二者都反对将“选择”与一般的合意相混淆,认为个人基于信息不对称而对信息处理活动做出的接受“选择”并不是有效的合意。其次在路径选择上,GDPR试图通过弱化同意的效果,即仅将其作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之一,而将基于知情的主动“选择”也纳入经改造的知情同意规则体系中。美国法上则将“告知选择”与一般的合意相区分,直接将其择出合同法的调整范围。
在实践中,告知选择之行权模式具有显著的优势。首先,由于告知选择的法律效果弱于一般合意,因此不会发生公开权模式下的权利转让,相应的,个人信息主体一直保有对信息流动进程中防止个人信息权益侵害的追及力,个人信息主体不需要承担无法预知的信息处理对人格尊严造成的风险。其次,告知选择并不要求个人信息主体对信息内容的绝对控制,可以与线上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网状型交易结构相契合,便于信息处理者随时随地开展信息的收集、使用和加工,而不必付出较大的交易成本来开展合同的磋商议价,有助于信息的流通和共享。特别是告知选择可以与第三方数据信托制度相衔接。具体而言,信息处理者不是与个人信息主体直接形成合同关系,而是从个人信息主体集体授权的第三方受托人获取许可。由此,个人不必承担与其自身能力不匹配的磋商议价和风险评估活动,个人信息处理者也只需要向个人履行基本的告知义务,个人则通过自主选择的方式加入或随时退出集体数据信托计划。数据受托人基于汇集起来的多个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代表个人信息主体来对抗信息处理者。〔88〕关于国外数据信托模式的详细论述,可参见翟志勇:《论数据信托:一种数据治理的新方案》,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4期,第70-75页。
六、结语
个人信息来源于个人,与个人身份或行为紧密关联,具有人格属性。数字经济背景下,个人信息被交易、处理的现象频繁发生,个人信息的资源性和财产性特征被前所未有地挖掘。个人信息流通体现了个人的意志自由,也满足了社会整体福利的要求,个人信息的人格属性不妨碍其内含的财产价值可以与主体分离,外化为财产并可为商业利用。不过,与传统基于控制的公开权保护模式不同,个人信息财产价值的外化路径不再通过许可使用合同实现,而是借由告知选择之行权方式达到弱化权利移转效果的目的,一方面可以保护处于弱势的个人信息主体,继而保有防范个人信息权益侵害的防御权能;另一方面也降低了信息交易磋商的难度,促进数据流通共享,由此实现数字经济发展带给人们的经济福利,继续保护与提升人的自由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