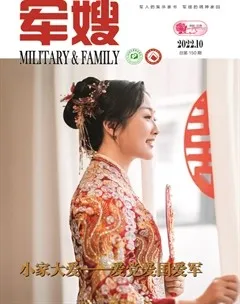追寻父母的精神坐标
2011年金秋时节,我随同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组织的“纪念新四军军部重建暨一师成立70周年——鲁南苏北行”寻访团,走进苏北那片热土。
在这里,我追寻父亲刘毓标、母亲赵倩留下的战斗、生活足迹。盐城—停翅港—千棵柳—黄花塘—徐州,都是书写下他们深刻记忆的地方啊!
盐城——爱情“信物”
盐城,东方湿地之都,仙鹤神鹿世界。这里也曾是新四军军部重建时的驻地。
1940年底,在盐城,我的父亲、母亲因抗日战争而相遇了。我父亲于1939年6月,离开战斗了12年的皖浙赣边区,到隶属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的教导大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工作。1940年9月,学校的两个大队由教育长谢祥军叔叔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父亲率领,随同刘少奇同志从淮南北上到达盐城。11月,与苏北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等部合编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即新四军抗大总校),父亲任政治部副主任。
1940年11月,我的母亲经地下党安排,和吴秀丽、汤翠弟、吴映、王珏、钱玲弟、顾梅芳等工友姐妹,毅然离开繁华的大上海,到盐城参加了新四军,成为抗大五分校女生队的第一期学员。
就这样,一个江西农民出身的老红军和一个上海工人出身的新战士,在抗大五分校这座革命熔炉中相逢了。

1941年6月11日,父亲调新四军后方政治部工作。这是他们相识后第一次离别。父亲向母亲赠送了一份爱情的“信物”——日记簿,并在扉页上题写道:“共产主义者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来确定与坚强自己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决心,同时要在不断的革命斗争中锻炼自己。为此,必须从理论上去努力学习,从工作中去追求经验,从思想上去检讨自己。”
对于这一天的情景,母亲在日记中作了记述——
6月11日星期三雨
今天,我正在上课的时候,秀丽说刘主任送你一本日记簿。我连忙回来看,原来是一本精美的小本子,上面还留着勉励我的字句。我看了真感谢他这样的鼓励我。同时我知道我拿到小本子时,他已离开抗大了,去担负更重要的工作任务。起先时我总有些想念他,但后来我克服这一点,便不时常想起他,我只希望时常通信好了。
停翅港——生死重逢
停翅港,位于苏北阜宁县县城西南约十几公里处的一个小村庄。村中有一个方圆120多亩的大水塘,水塘西北侧有个长满青草、垂柳和芦苇的小岛,相传凤凰在这个岛上停过翅,因而这岛子被称为凤凰墩,村名也便成了停翅港。
1941年7月,日寇对盐阜抗日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主动撤离盐城,转移至阜宁境内,8月初迁驻陈集镇停翅港村,直至1942年12月25日迁往黄花塘。
从盐城到停翅港,刚刚离开抗大的母亲经历了一场生死考验。她在日记中写道——
7月21日星期一晴
今天情况很不好,所以我们队伍整个离盐城。早上二时便动身了,在静静的操场上,黑黢黢的坐着一堆堆的人,都是我们抗大的同学。抗大,你给了伟大的教育,今天我要离开你了,不知何时再到母校!到六时半,我带了介绍信与两个同学,因她们有事,所以也到军部,由我负责。她们因为怀孕,路又不能走,东西又是那么多,只好叫了一个老百姓挑了行李送到西门外再说。但到了西门也不知怎样走法能到军部,只好准备一路走一路问。结果总算还好,出西门不多远,终于看见了几只我们队伍的船,我们就拼命叫他们停下来,后来他们停下来了,原来是“联抗”的队伍。我们乘着这船走了。
后来得知,母亲她们乘坐的船刚离开,日寇的汽艇就进了盐城。脱险后,母亲随新四军三师二十团的部队行动了一个多月。当时,父亲从传闻中听说母亲在反“扫荡”中牺牲,非常痛苦,到处打听母亲的消息。直到9月,母亲才辗转来到驻在停翅港的军部,见到了父亲。生死重逢,真是悲喜交集。在日记中,母亲记载了重逢的情景——
9月15日星期一晴
到军部来后,已有五天了。毓标也来了,当时我看见了他,心里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总是有感情的,因为我们俩分开了很久,同时,在这次反“扫荡”中,他们猜想我已经死了,所以觉得更不同些。他对我的确很关心,我也感谢他。他今天到周门去,晚上很晚还没有回来,我觉得他不会来了,正要准备睡的时候他到来了,我就谈了些工作的问题。因为老百姓要睡了,就送他出门。可是到了外面又不想分开了,谈了很多的话。夜已很深了,但我俩还不想分开。最后,我的理智克服了情感,催他回去,因晚上天气很凉,他身上衣服又穿得很单薄。
不久,经组织批准,父亲、母亲在停翅港幸福地结合了。
结婚后,父亲任新四军直属政治处主任,母亲在军部三科协理处当政治干事,每周见面一次。他们在停翅港军部工作了一年多时间,共同渡过了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
1942年12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军部机关实行精兵简政,充实作战部队。父亲调任十八旅五十二团政委。当时,母亲已怀有6个月的身孕,根据组织决定,通过地方组织护送回上海“打埋伏”。
在去上海的途中,母亲又一次遇到了险情。当时,她和同行的3个女同志分乘两只小木船溯河南下。在经过一个日伪据点时,前面船上的两个女同志被汉奸识破而被捕。护送母亲的地下交通员十分机警,母亲也很沉着冷静,巧为周旋,从容应对,方才脱离虎口。
千棵柳、黄花塘——再历艰险
千棵柳村,位于江苏省盱眙县县城东南约50公里处,是由卢家圩和吕家圩两个小村子组成的(今名长江村,属盱眙县旧辅镇),曾属安徽省天长县汊涧镇。新四军军部在这里约7个月,指挥新四军顺利进行了战略反攻及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1943年4月,父亲调任由留在汊涧的原江北军政干部学校一个大队和部分机关人员扩编而成的抗大八分校(隶属新四军二师)政委。
同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大哥,取名“华申”(上海也称为申城)。夏季的一天,一位女同志突然来到母亲住处,说她已被捕一月余,由家里保释放出。她在敌人那里,看到有母亲的名字,因敌人不知地址而没有抓到母亲,她要母亲立刻离开上海。母亲当即转移,数天后,在舅舅赵帛(地下党员)的帮助下离沪脱险。
母亲独自抱着大哥华申,历经千难万险,找回解放区,来到千棵柳,与父亲会合。多年后,母亲向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我带着4个月大的孩子,到了千棵柳八分校校部。毓标正在开会,有人告诉他,我带着孩子回来了,他没有分心,直到会议结束才回来。看到我们母子平安回来,他高兴得抱着孩子亲呀吻呀。看到这个情景,我把对他刚才冷落我们的意见全消除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对工作一点不懈怠,我们母子费尽周折,从上海回到解放区,他因开会却不能先出来看一看。”
团聚后,父亲、母亲同在抗大八分校工作,直到1945年。
今日千棵柳,已与附近村庄并无二致。据当地老乡介绍,新四军军部1945年10月北迁后,旧址即被丧心病狂的敌人烧毁,连柳树也未能幸免,“千棵柳”已无柳。
从千棵柳向北约20公里,即是黄花塘。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抵达黄花塘,代号为“黄河大队”,在这里约两年零两个月。
1945年4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之际,在黄花塘军部医院,母亲生下了她和父亲的第二个儿子,取名“华明”,意为迎接中华民族光明的未来!
徐州——红色传承
1946年9月23日,以3个地方团组成的七纵三十一旅在苏中东台县成立,父亲由新四军二师六旅副政委调任三十一旅政委。次年5月15日,十一纵三十二旅在苏中台北县洋岸灶成立,父亲调任该旅政委。1948年初冬,父亲率部来到了徐州,参加了淮海战役。
徐州,古称彭城,历史文化名城,汉文化的发源地,汉高祖刘邦的故里。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东军区的坦克部队有了飞跃的发展。1950年秋,在徐州成立了华东军区摩托装甲兵司令部。父亲任副政委(后任政委),他克服文化水平低、缺乏技术知识的困难,认真地虚心学习,和首任司令员兼政委何克希伯伯、继任司令员刘涌叔叔一起,为建设华东军区装甲兵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1951年初,母亲手牵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怀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我的姐姐东东),离别福建厦门,到了江苏徐州。在华东军区装甲兵,母亲担任了司令部副政治协理员。
正当母亲投入紧张的工作之时,一个小东西来“捣乱”了。母亲在日记中数次写道:“整天的无精神,总觉得浑身不舒服”“精神一点都提不起来,总觉得头昏脑胀”“反应时间已不短了,还没有好,真要命”,等等。
这一年11月8日,在徐州西关医院,母亲经历了惊险的难产,终于生下了我。因我生在苏联“十月革命节”的第二天,故取名“华苏”。又过了一年零四个月,在徐州华东军区陆军医院,父亲、母亲的第四个儿子出生了,取名“华建”,因为他生在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
1953年7月,父亲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父亲作为新技术兵种的组建者和领导者,为装甲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1954年,随着父亲进入文化速成中学学习,我们一家到了江苏南京。一年后降生的刘家老六、我的妹妹,取名“晓宁”。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名字都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地域特征;刘家的命运,始终与党和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息息相关!
在离开徐州18年后,1972年底,父亲、母亲把两个儿子又送回了徐州,到坦克某师当兵。此后,我和弟弟华建依靠父母给予的思想品德基础和身体素质,在党组织的培养和同志们的帮助下顺利发展,直至相继走上军职领导岗位。
巧合的是——我们父子三人被授予共和国少将军衔时,工作单位(华东军区装甲兵、工程兵指挥学院、某集团军)都在徐州!我和华建出生在徐州,入伍在徐州,授将在徐州,这方热土怎能让我们忘怀?

父亲、母亲周转各地,聚少离多,感情却更为深厚。1997年4月25日,父亲辞世后,母亲念念不忘:“毓标是我的革命伴侣,也是我的领导。我们之间有三种关系:一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二是同志关系,三是夫妇关系。在抗大时听过他上的党课和作的报告,他是我到革命部队后的启蒙老师。我们共同生活56年,我始终尊重他,永远不忘他是我的首长。”
父亲生前也曾多次对我们说:“你们的母亲,把你们兄弟姐妹抚养教育成人,是她对这个家、对革命的重要贡献。”在难忘的岁月中,母亲以战士、贤妻、慈母的三重身份,与父亲有两地相隔的挂念、有胜利重逢的喜悦、有儿女降生的幸福,更有并肩战斗、相互支撑的坚强。
2008年5月2日,母亲也永远离开了我们。经历了战争环境的大哥华申经常向我们回忆:“战火中的母爱,更加弥足珍贵。我记得,在一次渡河时,国民党的飞机上下俯冲、投弹扫射,机头涂着红色的飞机尖厉地呼啸着……母亲把我和弟弟华明紧紧地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躯保护着我们。”大哥还说,在那个特殊年代的母爱,凝聚着母亲多少的心血和付出。尤其是,她还是一个战士,还要履行她对组织、对人民的承诺——身为战士的母亲群体格外伟大。
革命家风永流传!父亲、母亲用一种特别的爱,向我们诠释、潜移默化地传递着“千车载不尽、万船装不完”的珍贵家风:信念坚定、意志坚强,严于律己、清廉俭朴,真诚相对、善待他人!
(本文参阅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的《新四军战史》、1996年7月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战史》等资料。作者曾为工程兵指挥学院政委,少将军衔)
编辑/牛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