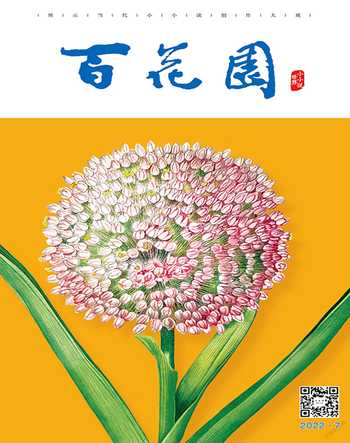扁 担
王春迪
拾来猛地推开家门,像突然起了阵狂风。
媳妇正抓着小米喂鸡,被吓了一跳,窝在墙根角的鸡,吓得扑腾到了墙头上。
拾来径直走到水缸边,放下手里的布口袋,舀了一瓢水,仰着脖子咕咚了一气儿,剩下的,浇在了头上。
“干吗你?打火焰山下来的?”拾来媳妇嗔道。
拾来嘿嘿一笑,抖了一下布口袋,扔给了媳妇。
媳妇打开袋子往里瞧,一股香味直往鼻子里冲。袋子里有几张芝麻烧饼、两三根香油馃子,用草绳系着,还有半只烧鸡,用草纸裹着,纸上浸透了油。
“你疯啦?不过了你?你咋不割点儿龙肉回来?”媳妇急了。
“我今儿个干了个巧活儿,没大出力就弄了半吊钱。”拾来边说边从袖子里掏出一把铜板,在掌心里当啷当啷地颠了几下,喜滋滋地放在了媳妇手里,顺手还抓了媳妇一把。
拾来没啥手艺,过了三十岁,也当不了铺子里的学徒,只能在老街上给人当“扁担”,干苦力,卸煤、装货、搬家……拾来倒是有一身蛮劲儿,人精瘦,手脚却大如蒲扇,干活儿实在,不留气力。拾来天亮进城,揣一块大锅饼、一个豁了口的黑碗。等卖馄饨、卖豆腐脑儿的出摊,拾来凑过去,跟人喊哥叫姐的,求口热汤水就饼。吃完饼,拾来就蹲在城门楼前,抱着扁担,等活儿。等活儿的人不少,每每遇到雇主,大伙儿小炕鸡似的围上去,一边撸着袖子,一边吆喝自己。拾来却不,拾来只是在一旁干咳,并唰唰地搓他那大如蒲扇的手。雇主一看那手,就知道是个气力人,伸个袖筒,要跟他问价。老街上,价钱都是在袖筒里,用手“谈”的。拾来不懂这里的规矩,也不计较,只是嘿嘿地笑:“您看着给,看着给好了。”
拾来说的“巧活儿”,其实就是跑了趟腿。一早,他扛着扁担经过老街西头一家赌档时,看到一个胖圆脸的少爷站在门口,一边左右张望,一边喊人。不知道喊谁,半天也没人答应。胖圆脸骂了几句,便对拾来招手。胖圆脸一看就是个富贵子弟,辫子梳得整齐油亮,上身青缎薄棉褂,下着白棉袜、纺纱套裤、凉里皂靴。胖圆脸少爷丢给他半吊子铜钱,让他到路对面买三五斤香瓜,送到海昌楼王妈妈那里。胖圆脸嘱咐拾来:“一定得说是孙大少送来的。”
那个海昌楼,也叫海娼楼,是一卖春的青楼妓院。

拾来接过钱,道声谢,赶紧到路对面,在一个拉瓜的独輪车上称了五斤香瓜,急吼吼地往海昌楼跑。海昌楼里的脂粉气,十步远都能闻到;此起彼伏的浪笑,钻进拾来的耳朵里,像一根狗尾巴草,这儿挠挠,那儿撩撩。拾来把瓜送给王妈妈,木木地说清来由。王妈妈并不接,只是示意让拾来放下。王妈妈拿着耳挖子剔牙,眼睛却瞅着外面出神,像是在想什么。拾来把瓜从他的布口袋里一个一个往外掏时,发现里头有几个香瓜的瓜蒂霉黑了,有点儿烂菜味,捏一下还发软,铁定是坏的,想来称瓜的时候,那卖瓜的趁他着急不注意,手上使了个巧,弄了几个坏瓜进去。拾来暗想,哪天遇到那卖瓜的,非得跟他论论理。
但一连两天,拾来也没见到那卖瓜的,每每经过赌档的时候,倒总忍不住停下脚步,往赌档里张望。拾来巴望着,什么时候还能遇到这样的巧活儿干干。
这天,拾来恰巧遇到那个卖给他坏瓜的人,上去跟他讲理。卖瓜的人像是对拾来有印象,也不回嘴,只是笑。等拾来抱怨完,卖瓜的人笑笑:“兄弟别急,我问你,你那瓜是不是送到海昌楼的?”
拾来脸一红,道:“你卖你的瓜,管我送哪儿!”
卖瓜的笑嘻嘻地说道:“好瓜歹瓜,也就是个信儿罢了。”
拾来一愣。
卖瓜的说:“瞧你,真跟个扁担似的,啥也不懂。这条街上,随手捡个石子,里头都有故事。”
拾来瞪了他一眼:“你少跟我卖关子!这瓜你赔不赔?赔不赔?”
“这样吧,教你个学问,就当我赔你瓜了。那帮阔少,在赌档里手气差了,会到妓院里找个没开苞的姑娘过夜。他们说这样能转运。你送那瓜,就是给青楼里的老鸨子送个信儿,给他预备个雏儿。他们管这叫‘破瓜转运。这事儿,我遇到不止一回了。”
话未了,拾来头顶好像劈了个响雷,脑袋里像有几百只绿头苍蝇在飞。
拾来拖着自己的身子回去,扁担也忘了拿。此后几天,拾来像是生了一场病,一直脸朝着墙,猫儿似的窝在床上。
再去老街寻活儿时,只要经过海昌楼,拾来都把脸扭向另一边。偶尔遇到那卖瓜的,拾来也装作不认识他。
[责任编辑 王彦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