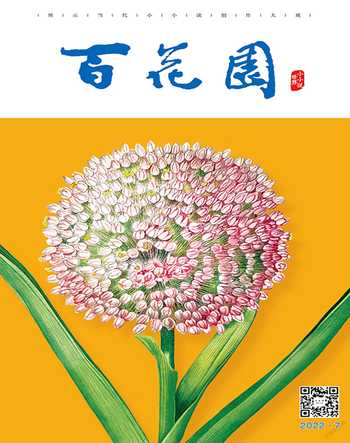将军道
王东梅

我爹惦记上了田二爷的菜园子。他贴着菜园子垒了猪圈,搭了茅房,还密密实实地栽了一排紫穗槐。田二爷气得脑门子疼,却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只能把篱笆墙加高再加高。
我爹的土坯房只有三间,半米高的矮墙隔在河岸与土坯房之间。我爹想着矮墙应该能够挡得住雨季里汹涌的河水,但是河水比想象的更猛,竟然几次越过矮墙,向土坯房逼近。我爹意识到失策了,想着得赶紧把土坯房向外挪一挪。
哪有那么容易?再向外,就是田二爷的菜园子了。田二爷是村里的“五保户”,却固执地守着这块地,要自己栽瓜种菜养老。穿过菜园子,再向外就是村里那条著名的斜街了。
我爹的房子被困在菜园子和河道之间,动弹不得。
大雨又来了。河水翻涌,水面几乎与矮墙等高,我爹急得直搓手。突然,西房山上一声闷响——菜园子里的大柳树倒了,不偏不倚,砸在了西房山上。
田二爷一下子蔫了——一园子的菜也不够赔的呀!
让田二爺没想到的是,我爹没难为他。
田二爷的侄子出面协商,房子由我爹自己修,只是房基向外移了整整一间房的距离。
我爹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子, 新房子成功盖到了大路边——五间房的大院子啊。房子盖好了,可我爹又有了新的心事——路,是斜的。斗门河从北面浩浩荡荡而来,到了村口突然改了主意,一扭身,向东奔去;走了不远,又觉着不对劲儿,拐向南逶迤而去。村民们依着河岸建房子,因为河道中途拐了弯儿,村里的路也就跟着斜了。看着剑一样刺过来的大街,我爹心里别提多堵得慌。
那一年,田二爷的侄子也整天坐在我家门墩上唉声叹气——孩子们小的时候,院子宽得能跑马;孩子们大了,七间房的大院子却无论如何也安置不下三个儿子。大儿子、二儿子两家各分三间房,老儿子就只能剩一间了。
后来,田二爷的侄子就把心思动在了斜街上。
田二爷没了,菜地荒了,地边的小路越踩越宽——向南,连上了村里的大路;到了我家房角,一转身向北,奔向村口去了。
田二爷的侄子把他的想法和我爹说了,我爹一拍大腿:“好主意。”田二爷的侄子占上斜街的路面盖了两间房子,三儿子的家就有了着落。前院的田四,猪圈也能从院子里搬出来搭在斜街上。而我爹,也可以把西门改成东南门,出门就能上大路,一步将军道,纳福迎祥,好彩头啊!这样一来,不但各家院子都宽敞规矩了,改了道的大街也规整了。
想法成了建议,建议上了村委会的办公桌,报给了乡里的领导。顺民情,合民意,一条斜了几十年的街没了,一条崭新笔直的大路闪亮登场。
那些日子我爹做梦都能笑出声,只操心怎么变着法儿把日子过得更顺溜了。
别看我爹种了半辈子地,可一点儿也不缺乏经商的头脑。生产队刚解散,我爹就拎起他的木匠家什,各家各户地揽活儿。后来他发现牛仔裤的市场巨大,愣是背着一包包牛仔裤敲开了北京大商场的门。我爹成了我们县第一个万元户。我爹到处去做报告,介绍发家致富的经验。县长说:“你一个人富了不叫富,要带着大家一起富。”于是,我爹就带着村子里的人“一起富”。
村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可是一遇到下雨天,我爹又有了新的愁心事,啥呢?出村的路实在是没法走。
村北一条出村的大路,一面是粮地一面是河道。不下雨的时候,路有两三米宽;一下雨,挨着河道的一面常被冲出一丈多深的沟,走个人都战战兢兢,更别提装满货的货车。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县长也说过,我爹觉着这句话说的就是这条路。
说干就干,我爹招呼全村老少齐上阵,拓宽了路面,垫了渣土,用碌碡压平压实。再走上去,确实比以前平整了许多。可高兴了没几天,下雨了,雨水冲毁了路面,渣土被冲进沟里,路被冲出一个大口子。修修补补解决不了大问题,得从根上解决。村里出面,村民集资凑了十万块钱,挖开路面,夯实地基,铺上二十多厘米厚的混凝土。一个月后,村里的大小车辆就奔跑在新修好的水泥路上了。
路宽了,人的心也宽了,村里人过好日子的门路也越来越广了。我爹开上了新轿车,喜气洋洋。
村主任说:“村子对面划成了高开区。”我爹抻着脖子望了望,工厂都修到村边上了。新工厂的楼房高大气派,比村口的大杨树还高,机器彻天彻夜轰隆隆地响。我爹说:“还缺一条路啊,缺一条配得起城市建设的大路。”
仿佛领导们又听到了我爹的呼声,一条双向六车道的大路修到了村边上。从村里出来,一步就能迈上大路。我爹说:“这将军道,真是豪气。”
如今呀,我爹74岁了,没有一天闲着。我爹每天从自家出来,走上大街,一路向北,经过街两边的饭店、旅社、商店、居民委员会、健身广场、街心公园,来到河边的休闲码头,顺着河岸边的长廊,顺着斗门河奔来的方向,一路向前走。
[责任编辑 吴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