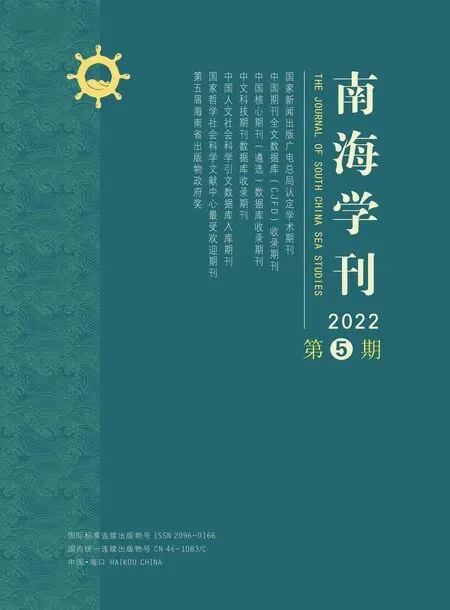博通包容 艺为人生
——苏轼的艺术批评理论
毛宣国
(北京大学 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苏轼一生没有留下系统阐释自己艺术思想的理论著作,他的艺术批评散见于他的诗、文、书信、游记、笔记、题跋、铭文、赋颂等文体之中,不少还是兴到之言,甚至自相矛盾。但是,苏轼的艺术批评,无论诗文还是书画,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重要原因在于他的艺术批评不仅承继前人,有自己独到的理论建树,而且与他独特的人生感悟和情怀相关。苏轼一生坎坷曲折,处于政治漩涡之中,所经历的苦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却从不消极遁世,而是心系天下,为国为民,人格独立、文心旷达,不做阿谀奉承之徒,对百姓民众充满同情与关爱。他少年时立志做范滂,青年应试杜撰圣贤典故使得考官汗颜,中年时屡遭打击从不妥协,即使被贬谪到蛮荒之地的惠州、儋州,其官职几近乎一介平民,也依然顾念苍生,痛斥朝廷苛政,写下《荔枝叹》之类的作品——“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1)苏轼:《荔枝叹》,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21年,第706页。;面对无医无药的窘境,也不消极气馁,而是调侃地告诉朋友:“每念京师无数人丧生于医师之手,予颇自庆幸。”他曾经对弟弟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2)陶宗仪:《说郛》卷12,贾似道《悦生随抄》引《漫浪野录》,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3-4页。。这种人格独立与人间大爱,使他可以超越人世的险恶与是非而生活得光鲜磊落、多姿多彩。他的艺术批评即是他人格精神和人格境界的真实写照,充满人生智慧、人生感悟和创造精神,所以能超越一般的艺术创作技巧和经验的探讨,在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批评史上独树一帜, 产生深远的影响。李泽厚认为,在苏轼那里, “‘文’不只是文艺,而更是人生的艺术”(3)李泽厚:《李泽厚十年集》(第一卷),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82页。,对于苏轼的艺术批评理论也应该这样理解。
苏轼艺术批评理论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于诗文,他提出“以诗为词”和词“自是一家”之说,提出“辞达”“行云流水”“随物赋形”之说,推重平淡的诗风和审美趣味,追求自然天成的文章表达境界,是宋代诗坛文坛开辟风气的人物。相比诗文理论,苏轼的书画理论,由于“文人画”(士人画)、“形神”、“尚意”、“无法之法”、“诗画一律”、“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一系列主张和命题的提出,在艺术批评史上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以苏轼的书画论为例,选择“文人画”论以及“形神”“无法之法”“诗画一律”几个命题来展开。需要说明的是,以书画理论为谈论对象,并不意味着忽视诗论文论。徐复观说:“(苏轼)以知画自许。而他对画的基本观点,乃是来自对诗的基本观点。”(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4页。这种观点不一定准确,却也说明在苏轼那里,诗文书画理论是相互贯通的。苏轼是一个对人生有着大觉解的艺术家,在诗文书画各个领域都有很高造诣,所以他能将诗文书画贯通起来,提出深刻独到的见解,引领和改变时代的艺术风气,并影响到宋代乃至整个中国艺术批评史的进程。
一
谈到苏轼的书画和艺术批评理论,首先进入人们视野的当属他的“文人画”论。“文人画”论是中国书画史上影响深远、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它的萌生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时期顾恺之的“传神”论和宗炳、王微的山水画论。但文人画的兴起或者说作为一种独立意识的绘画形态的正式确立,却是在北宋时代,与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的理论建构和艺术实践密切相关。
苏轼并没有明确提出“文人画”概念,他所提出的“士人画”概念,学术界一般认为就是“文人画”。苏轼说:
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许便卷。汉杰真士人画也。(5)苏轼:《又跋汉杰画山》,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503页。
苏轼是在比较画工画不同的基础上提出“士人画”(文人画)概念的,认为“士人画”重视“意气”,而画工画则“只取鞭策皮毛”等,也就是重视外表的相似(形)而非“意气”(意)。苏轼提出“士人画”(文人画)这一全新概念,将“写意”和“神似”放在重要地位,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对此学术界普遍是认同的。但是,如何理解苏轼所提出的“文人画”观的理论内涵,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自从明代大画家董其昌提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并划分南宗、北宗画派开始,人们就习惯于将苏轼的“文人画”论与庄学趣味和南宗画风联系起来,认为“平淡”“萧散简远”“神韵”一类诗学标准构成了文人画的理想与极致。比如,钱锺书就以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中某些话为依据,认为南宗画派开山之组的王维在“画品”上高于“画工画”代表的吴道子,认为苏轼论诗倾向神韵派,论画倾向南宗,将“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有远韵”“得之于象外”作为绘画(文人画)艺术的最高境界(6)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2-23页。。徐复观讨论苏轼文人画主张,亦认为他“所以知画,实因其深于庄学,庄学的精神,必归于淡泊”“他论画的极谊,也必会归结到这一点上来”(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322页。。陈传席也认为苏轼文人画在境界上的要求是“萧散简远”“简古”“淡泊”“清新”,而这一切“都是受庄学审美观影响的结果”(8)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88年,第256页。。
有一些学者则不这样认为,他们更看重的是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人画家的儒学思想背景。高居翰认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所持的绘画理论反映了他们的儒家背景,在儒家著作中,诗、书、画早就被认为是寄情寓兴的工具,是用来传达性情的”(9)高居翰:《图说中国绘画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99页。。阮璞则不同意钱锺书等人对文人画观念的理解,认为苏轼思想相当复杂和充满矛盾,但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而非老庄和佛家,论画并没有表现出尊王(王维)贬吴(吴道子)的倾向,也不是像钱锺书所认为的那样是“论画倾向南宗”,其审美趣味归于“平淡”“萧散简远”一极,而是诗崇李杜,画重吴生,将“才力富键”“气势雄直”“大雅”“正声”作为评论诗文书画的重要标准(10)阮璞:《苏轼的文人画观论辩》,《中国画史论辩》,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119页。。
笔者认为,将苏轼的“文人画”观念简单归结为庄学或儒学的背景都是不妥当的。苏轼论诗、论书、论画,的确表现出“平淡”“超逸”“萧散简远”一类庄学趣味,这从他比较吴道子和王维的画,更赞许王维画能“得之于象外”(11)苏轼:《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卷),第114页。,提出“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萧散简远,妙在笔墨之外”的主张(12)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24页。,推崇陶渊明、柳宗元的诗和钟繇、王羲之的书法等就不难看出。但仅仅以此为标准看待苏轼“文人画”论则是将问题简单化了。苏轼是一个集儒、释、道于一身的大艺术家,博通包容、不囿于一家之言是苏轼思想的显著特点,对此,苏轼自己有着明确的认识,他说自己为学是“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13)苏轼:《祭龙井辨才文》,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3281页。。每一种思想,每一个宗派,在苏轼那里,都可以很好地融通起来,就像溪流江河可以汇合起来流入大海。正是这种开放包容性决定了苏轼在艺术和审美方面不拘常见,博采兼收,勇于创造。他的“文人画”主张也可以这样加以理解。
苏轼提出“文人画”(士人画),强调写意和绘画的人文特征,是针对院体画和画工画的精工写实特色和画工身份而言的,但并不意味着对院体画和画工画的否定,他对院体画和画工画的精工技法和形似写实的趣味是包容的,对于院体画大画家吴道子予以高度赞赏,认为他的创作是“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花生客慧”(14)苏轼:《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卷),第674页。,是“画人物,如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15)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8页。。苏轼现存的书画作品很少,被称得上文人画代表作的作品可能一幅都没有留下来,不过,这并不能否定苏轼对于“文人画”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从同时代画家评价看,苏轼的画作擅长墨竹、枯木和松石,如现存的可能被看作是苏轼作品的《枯木怪石图》和《潇湘竹石图》,画中的枯木竹石扭曲怪异,不在于外形的相似和逼真,而在于表现一种主观的意趣、胸襟和矛盾苦闷的心情。如米芾评价苏轼作品:“子瞻作枯木,枝于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16)米芾:《画史》,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2页。清人卞永誉亦认为苏轼所作偃松图,怪怪奇奇,其目的在于表现“胸中磊落不平之气”(17)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十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28册,第788页。。苏轼的人生历经坎坷,受尽磨难,但他却从不因此退却和气馁,反而勇于进取、达观旷达,他的画作表现的即是这种人格和精神,这亦是他提倡“文人画”的目的所在。
对于“文人画”理论,学术界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文人画”是为人生而非为艺术的,如陈师曾所言,“即画中带有文人之性质,含有文人之趣味,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必须于画外看出许多文人之感想,此之所谓‘文人画’”(18)陈师曾:《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5页。。苏轼的文人画创作和理论即是如此,它“不在画中考究艺术上之工夫”,而是抒发内心之感受,追求人生之境界。所以他称赞朱象先的画“能文而不求举,善画而不求售”,只为“达心”“适意”(19)苏轼:《书朱象先画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8-2499页。,“无求于世,虽王公贵人,其何道使之”(20)同④:第2499页。;称赞蒲永昇作画“性与画会”,“不择贵贱,顷刻即成”(21)苏轼:《画水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905页。,即不是为了牟利来作画,也不是刻意于形式技巧,而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性情和人格精神。何楚雄说,苏轼提出文人画(士人画)概念,体现了“一种雄伟奔腾、浩荡于胸中的气势意象”和“不可荣辱”的艺术精神(22)何楚雄:《中国画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76-178页。,这的确构成了苏轼文人画的重要特点。另外,苏轼的“文人画”论又是得庄学之神韵,追求超迈高逸、平淡简远的艺术趣味,体现士大夫文人高尚的情趣和性情修养。更重要的是,多种思想、多种情趣有机地交融在一起,服务于苏轼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体现苏轼的人格和精神境界,这是苏轼“文人画”论的意义所在,也是为后人赞许和称道的缘故所在。
陈传席说:“宋以后,没有任何一种绘画理论超过苏轼画论的影响,没有任何一种画论能像苏轼画论一样深为文人所知晓,没有任何一种画论具有苏轼画论那样的统治力。”(23)陈传席:《中国山水画史》,第256页。这里所说的“画论”就是“文人画”论。文人画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时代社会方面的原因。宋代是中国封建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其思想、艺术和文化观念的开放与包容锻造了文学艺术(诗、词、话本小说)、书法绘画、园林戏曲的辉煌,也锻造了理学这样以儒为宗,同时兼容佛道的成熟思想形态。文人画潮流的兴起与出现反映的正是宋代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成熟与包容。“文人画”意识兴起还与北宋时期题画诗的创作,重视书画创作中诗书画交游酬唱的风气相关。唐五代时期,由于山水画论的发展,水墨山水画语言形式的形成,山水画由宫观山水、金碧山水向水墨山水转换,这也是文人画兴起的原因之一。但唯有苏轼才真正将文人画与文人精神联系起来,将绘画看成是抒写人生,表现人格人品和精神境界的工具,这对于以院体画和画工画为主导的中国绘画传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也奠定了文人画创作的理论基础。正是在苏轼“文人画”理论的引导下,后世文人画强调写“士夫”气,写“胸中逸气”,以绘画的形式来表现文人的性情修养和人格精神,将绘画引向为人生、抒写人的性情和心灵的轨道。
二
“形神”论是中国艺术批评的重要命题。“形神”原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形”与“神”对举,“神”比“形”重要的思想,早在《庄子》中就显现出来了。《庄子》提出“抱神以静,形将自主”(《在宥》)、“津人操舟若神”(《达生》)、“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德充符》)的观点,均将“神”放在重要地位。《淮南子》继承庄子思想,明确提出“神贵于形”(《淮南子·诠言训》)的观点。但在艺术领域中谈“形神”问题,却是从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人物画论开始的。顾恺之提出“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世说新语·巧艺》)的观点,认为画像传神的关键在于点化眼睛。苏轼对“神”的讨论正是从顾恺之的观点出发,但是他将顾恺之所说的“传神”与“意”联系起来。“传神”即“得其意思所在”。“得其意思”也就是“凡人,意思各有所在,或在眉目,或在鼻口”(24)苏轼:《书陈怀立传神》,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502页。,即不仅“眼睛”,而且“颧颊”“眉或鼻口”都可以传神,关键是“得其意思所在”。“得其意思”重在“意”而不是“形貌”,与顾恺之“传神”说的精神是一致的,但比“传神”论更加突出了作品内在“意气”和精神个性的重要性。苏轼所言的“传神”不仅针对人物画,山水花鸟画同样需要传神。如他赞叹陈直躬画雁画出野雁见人如若无人的状态(25)苏轼:《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二首》,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卷),第431页。,评燕公山水画“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26)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9页。,均是以“传神”为标准。
对于苏轼的“形神”论,从宋元时期开始,就有一些人抓住苏轼的“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表述,并将其与文人画观念联系起来,认为其只重视“神似”而不求“形似”。如元代汤垕评价苏轼即是“大抵写意,不求形似”(《画鉴》),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苏轼“文人画”论并没有将画工画与文人画根本对立起来,他的“形神”理论也是一样,并没有因为主张“神似”就否定“形似”。比如,他赞赏苏辙“所贵于画者,为其似(形似)也”的主张,认为“此言真有理”(27)苏轼:《石氏画苑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875页。,赞扬吴道子的人物画好比“以灯取影,逆来顺往,旁见侧出,横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28)苏轼:《书吴道子画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8页。,就是以“形似”为基础。苏轼还提出“余尝论画,人禽宫室器用皆有常形”(29)苏轼:《净因院画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876页。“形理两全,然后可言晓画”(30)李日华:《六砚斋笔记三笔》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663页。的观点,亦说明了“形”的重要性 。但相比“形”,苏轼无疑更强调“神”的重要性。苏轼提出“于形既不可失,而理更当知”“善画者画意不画形”“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31)苏轼:《书朱象先画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8-2499页。诸多观点,其实都是在讲“传神”。在苏轼那里,言“神”与言“理”言“意”是一致的,均是强调艺术不能停留在对象之形的层面上,而是应该超越“形似”走向传神写意,表现艺术作品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气韵。
苏轼强调“传神写意”,与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密切相关。因为只有传神写意,才能具有精神的高度,表现艺术家的人生情怀和胸襟气度。这与他大力倡导文人画主张是一致的。在《净因院画记》中,苏轼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世之工人,或能曲尽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办”(32)苏轼:《净因院画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876页。,将形神意理的表现与艺术家的人格胸襟、怀抱气度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赞赏文同画竹石枯木:“真可谓得其理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挛拳瘠蹙,如是而条达畅茂,根茎节叶,牙角脉缕,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欤。”(33)同①。文同的画之所以“得其理”,传神写意,就在于它寄寓了艺术家的怀抱理想,表现出艺术家的人格气象。徐复观谈到苏轼的“常理”说时说:“苏氏提出常理一词,乃是要在自然之中,画出它所以能成为此种自然的生命、性情,而非如一般人所画的,只是块然无情之物。”(34)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第316页。这道出了苏轼“形神”理论的一个根本,那就是艺术家所追求的“神似”“意似”并非一个简单超越对于事物外在特征的描绘而走向“神似”“意似”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将表现对象变成有情之物,变成艺术家的内在生命和精神。正因为此,苏轼赞扬文同画竹——“独能得君(竹)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贤,雍容谈笑,挥洒奋迅而尽君之德,稚壮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势,风雪凌厉以观其操,崖石荦确以致其节”(35)苏轼:《墨君堂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867页。,即文同画竹,充满对竹的爱,将“竹”变成自己性情的产物,充分体现了“竹”的品行与节操,使“竹”成为自己人格生命的写照。也因为此,苏轼赞同文同在“未得为已”和“意有所不适”的情况下不做画(36)苏轼:《跋文与可墨竹》,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7页。,因为这样的画违反了人的真性情,自然也无法达到传神写意的艺术境界。苏轼这些思想,可以说是丰富了中国美学和艺术史的“形神”理论,使“形神”论不再局限于简单的“形似”与“神似”、“写实”与“写意”之争,而成为艺术家人格、生命、精神世界的写照,成为艺术家的心灵和性情的体现。
三
“无法之法”是苏轼评价王安石书法时提出的一个命题。相比“文人画”观和“形神”论,苏轼的“无法之法”之论在中国艺术批评史上的影响要小得多,但它对于理解苏轼的艺术批评观却十分重要。苏轼在《跋王荆公书》中说道:
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稍得意,似杨风子;更放,似言法华。(37)苏轼:《跋王荆公书》,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70页。
苏轼认为,王安石的书法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掌握了“无法之法”的精髓,这种境界是不可学的。在《跋山谷草书》中,苏轼进一步阐释了自己对“无法之法”的理解。他借南朝草书大家张融的话评论黄庭坚的草书,“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38)苏轼:《跋山谷草书》,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1页。。也就是说,从古到今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法”,每一个人对于“法”都有自己的理解,只有突破“定法”走向“无法之法”,才能创造优秀的艺术作品,黄庭坚的草书正体现了这种精神。在苏轼的书画理论中,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比如,“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39)苏轼:《石苍舒醉墨堂》,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卷),第136页。“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手”(40)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5页。“燕公之笔,浑然天成,粲然日新,已离画工之度数而得诗人之清丽”(41)苏轼:《跋蒲传正燕公山水》,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9页。,都是从艺术实践总结出来的经验,均是强调艺术创作要得“无法之法”,突破成法成规,充分体现艺术家创作的自由。
“无法之法”命题的提出并不意味着苏轼不重视不遵守法度。苏轼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重“法”的时代,特别是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将“法”作为创作的根本,宋代书画特别是院体画也非常重视法度与规则。对于“法”和“规则”,苏轼也不否定。苏轼大概是在熙宁十年(1077)以后开始作画,早期以为画画靠的是天赋,不必刻意师法前人,后来改变了这一看法,开始向文同学习画竹,对竹的技法予以钻研。他推崇文人画,但是对于画工画的技巧与规则也不否定,这从他对于吴道子画的赞许就可以见出,称它为“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而将那些不出于法度创作的作品贬之为“狂花生客慧”(42)苏轼:《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卷),第674页。的主观臆造。对于其他画家的艺术创作和批评,他也表现出对“法”的认可和尊重。比如,他看了苏辙写给文同的《墨竹赋》,认为他只懂得文同画的“意”而未能掌握其“法”,而他自己却是“岂独得其意,并得其法”。他还提出“书初无意于佳乃佳”“乃是平生亦有意于学”的观点,“无意于佳”即是“无法”“无心”的境界,但要达到这种境界,“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43)苏轼:《评草书》,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74页。,即对“法”的学习和掌握,若缺少了这一环节,理想的艺术境界将难以达到。
苏轼曾这样评价自己的创作:“吾书虽不甚佳,然出自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44)同④。不践古人,对新意的追求,是苏轼创作最显著的特点。这一特点建立在对“法度”的掌握和超越的基础上。清人戴熙曾记载苏轼画朱竹的故事:“东坡在试院用朱笔画竹,见之者曰:‘世岂有朱竹耶?’坡曰:‘世岂有墨竹耶?’善鉴者固当赏诸骊黄之外。”(45)戴熙:《习苦斋画絮》卷八,台北:汉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2年,第427页。用朱笔画竹,这看似违反常识和规则,因为画家笔下的竹是以墨色为基础,这已成为艺术的常识,大家都应该遵守。但是在生活中,竹子是绿色的,谁又见过墨色的竹子?所以苏轼用朱笔画竹并不违反常识和规则,关键在于“赏诸骊黄之外”,即不再局限于物象之真和眼见的色彩,大胆地突破常规和常识,进行新的艺术创造。黄庭坚评价苏轼创作言:“士大夫多讥东坡用笔不合古法。彼盖不知古法从何而出尔。”(46)黄庭坚:《山谷题跋》卷五,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22页。“不知古法从而出”可以说是道出了苏轼创作的一个根本,即“法”不能成为创作的障碍,关键是要法出胸臆,自由地表现艺术家的情感和思想。朱熹评价苏轼散文说:“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4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3322页。朱熹是懂苏轼的,知道苏轼的创作看起来随心所欲,其实是藏有法,不违反法度的。艺术是有“法”的,是讲规则的,如果这种“法”和规则束缚了艺术创作,不利于表现艺术家的情感思想,那么就应该大胆摒弃它,突破它,这便是苏轼所说的“无法之法”。它是对常规陋习的突破,是对艺术家常识和守旧思维的突破,也是对艺术家大胆革新和自由创造精神的肯定。
苏轼提出的诸多观点和命题都体现了“无法之法”的精神,比如说“随物赋形”。“随物赋形”是苏轼评论唐代画家孙位画水时所提出的一个命题,认为孙位画水做到了“始出新意,画奔湍巨浪,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画水之变,号称神逸”(48)苏轼:《画水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905页。。这里面就有一个“法”与“无法”的辩证关系问题。画家画水,有法度在,即“与山石曲折”,不能脱离“山石”之形来表现。但更重要的却是要突破山石之形也就是“法度”的限制,“画水之变”,即将艺术家的情感寄于“形”之中,使艺术家的情感得到自由的表现,这样才能表现出水(奔湍巨浪)的神逸风采。“随物赋形”之论,也是苏轼论诗文的根本主张。他将行文过程比喻成“如万斛泉源”的水的流经形态,“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49)苏轼:《自评文》,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385页。,这与画山水所提出的“随物赋形”的精神是一致的。“随物赋形”追求的是自然天成之美,是“无法”,没有固定的模式和规则可循,所以它是“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但是“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又说明这种追求不是主观随意的,而是无法之中也有定法,即“无法之法”。艺术家的创作正是建立在“有法”与“无法”辩证统一的基础上。
“无法之法”亦可以看成是苏轼“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50)苏轼:《宝绘堂记》,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6卷),第2867页。的艺术人生观和人生态度的体现。在《宝绘堂记》中,苏轼提出了“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命题,他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51)同③。“寓意于物”是既寄情于物又不受物的奴役,所以是“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在“寓意于物”的人生世界中,物与人各安其所,人与物都是自由的,人不试图去占有物,物也不会奴役人。“留意于物”则不同,它过于看重物自身,以功利的态度对待人生,所以是“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即人被物奴役和侵占,失去了本心和应有的快乐。苏轼的“无法之法”之说,便寄寓着这样的人生理想与态度。只有“法”(有法),便是“留意于物”,便是人被“法”被物所奴役和占有,艺术家便失去了创作的本心和自由。“无法之法”则是“寓意于物”。唯有“寓意于物”,才能做到“无法之法”乃为至法,才能不失本心,从物我对立的状态中超越出来,破除情感表达与艺术技法之间的对立,创造出具有无穷魅力和生命力的艺术作品。
四
“诗画一律”是苏轼艺术批评理论中最重要的命题之一,语出苏轼《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其一:
论画似形似,见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52)苏轼:《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二首》,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卷),第489页。
此命题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常常是苏轼是否主张不要形似的问题。其实,苏轼提出这一命题的中心并不是讨论画要不要“形似”问题,而是讨论如何以诗入画,将诗与画融为一体,做到诗画一体、诗画相通的问题。它包含两层基本意思:一是以“诗”的眼光看待画,重视画的言外之意和诗意表达,所以他赞赏王主薄的画“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即富有诗意和言外之意,而这是只懂得写生传神的边鸾、赵昌的画所不具备的。二是将“诗画一律”与“天工清新”意境营造联系起来,认为诗理与画理一样,都要求追求天工清新的艺术境界。这也是苏轼一直追求的艺术旨趣所在。比如,他提出“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的主张,称赞文同的画“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53)苏轼:《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竹三首》,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1卷),第487页。,称赞燕公的山水画“浑然天成”,评论张旭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54)苏轼:《书唐氏六家书后》,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4页。,评论欧阳修书法“纵手而成,皆有自然绝人之姿”(55)苏轼:《跋刘景文欧公贴》,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86页。,皆以“天工清新”为标准。“天工清新”的艺术趣味和境界的形成,并不是每一个画家都可以做到的,它源于一种清朗高洁的胸怀,是艺术家精神意趣和人格修养的体现。“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主张与苏轼的“文人画”“传神”“无法之法”理论的精神是一致的,都重视艺术家的精神气象和文化修养,将诗画的本质归结为抒情写意而非模拟形似,归结为“天工清新”的艺术创造而非对规矩法度的恪守。
与“诗画一律”理论相关,在《书摩诘〈蓝天烟雨图〉》,苏轼还提出著名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命题:
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56)苏轼:《书摩诘〈蓝天烟雨图〉》,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5卷),第2496页。
这一观点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和争论,争论主要是围绕着诗与画的功能和界限来展开,焦点是诗与画能否做到相融与相通。其实,苏轼提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命题,并不是简单谈诗画相通,诗能不能通过画来表现,画是否等同于诗的问题。它是针对王维诗所表现的艺术境界而言的。所以,学者们对苏轼的批评,如“若以有诗句之作画,画不能佳,以有画意之诗为诗,诗不必妙”(张岱《与包严介》);诗画的差异不仅在动静、时间与空间,更在于“虚实”,诗常常表现的是“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含蓄空灵的境界,而画则不能做到(57)钱锺书:《读〈拉奥孔〉》,《七缀集》,第33-36页。;等等,皆是不得要领的。苏轼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不是简单地说诗有画境、能描绘形象鲜明的画境,也不是简单地说画可以用自己的笔墨语言创造出诗的意境,而是从王维“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的诗句中体会到一种独特的精神意趣,感受到诗人所表现出的清旷超逸、潇洒自适的心境,这与苏轼提倡文人画,追求清新脱俗、传情写意的文人画风是一致的,这里面便有一个诗境与画境相通的问题。这样的意思也体现在其对于其他诗人的评论中,如对吴传正《枯木歌》的评论,“天公水墨自奇绝,瘦竹枯松写残月。梦回疏影在东窗,精怪霜枝连夜发。生成变坏一弹指,乃知造物初无物。古来画师非俗士,妙想实与诗同出”(58)苏轼:《次韵吴传正枯木歌》,曾枣庄、舒大刚主编:《苏东坡全集》(第2卷),第659页。,就认为其诗是得“天地造化”的产物,随兴挥洒,浑然天成。同时认为画家也应该如此,有诗人之妙想,有诗人之心胸气度,才能摆脱画工的趣味,创造出清新自然的艺术作品。
“诗画一律”虽是苏轼提出的著名观点,但它不始于苏轼。在宋代,人们对于诗画同一性问题有着普遍关注。钱锺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中,引用宋人孔武仲“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东坡居士画怪石赋》)、张舜民“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跋百之诗画》)等观点,即说明了这一点(59)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第4页。。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说“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盘车图》),亦认识到了诗与画相通的问题,但苏轼的命题则进了一步,它不仅看到诗与画的相通,画可以有诗意,诗可以通过画来表现,更是看到了画与诗一样,都是天地造化的产物,是艺术家情感胸臆的体现,是自然天成而非人力所为的,所以它不能局限在形似模拟、再现写实的功能表现上,而是应该做到画与人心相通,画与诗心相通,用画来表现抒写性情心灵,创造出美的意境。“诗画一律”命题不仅体现了苏轼博通包容的艺术趣味,更是其追求“艺为人生”的高远的人生理想和人生境界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