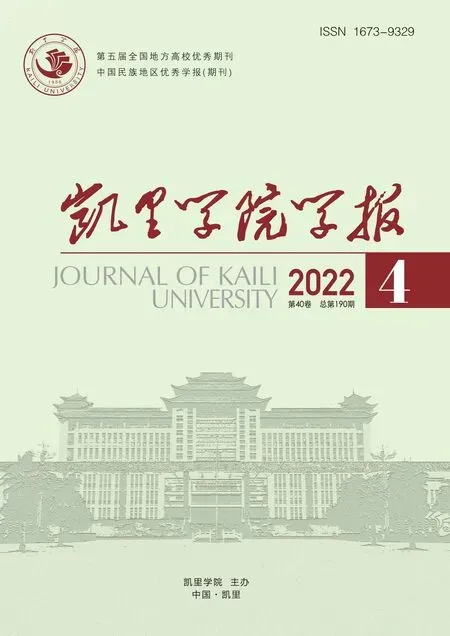明清黔东南苗汉文化交融及其对现代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李储林
(贵州师范学院历史与档案学院,贵州贵阳 550018)
一、明清时期黔东南民族社会发展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区,苗、侗、汉等多个民族在这里大杂居小聚居,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较高,民族关系的发展和民族文化的交融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的苗汉文化交融和相互影响为我们今天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探讨苗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苗族源于上古时期以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集团,居住在黄河流域以及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涿鹿之战后,一部分苗族先民逐渐南迁。最迟在唐宋时期,苗族已经形成单一的民族;同时,最迟在宋代,黔东南境内大部分主要苗族支系已经迁徙到该境内,成为黔东南地区的主体民族。明以前贵州的夷汉民族关系和民族交融呈现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汉族“夷化”;二是汉文化对夷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从秦汉至元迁徙入黔的汉人,在给当地带来了经济生活和文化方式影响的同时,在“夷多汉少”的情况下,大都“变服易俗”被“夷化”,被视为“蛮夷”的一部分。
黔东南处于贵州东南部,历来是西进的南蛮族群和北进的百越族群交融和集中聚居的主要区域,加之山高林密,地理环境复杂,较之于贵州其他地区,汉人入境的时间要晚,数量要少,在民族间的交流互动上,少数民族文化受汉文化的影响更小。在这一区域内,夷影响汉比汉影响夷更显著,夷影响汉的程度也比贵州其他地区更深。
明清时期,苗族文化和汉文化“交流碰撞”的全面深入来自政治关系的变更,即自明至清,中央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将黔东南地区从“化外”统一到“制内”的过程。首先,土司制度肇始,试探性地延续“羁縻之治”控制外围的熟苗区;然后,大量派驻屯军管控驿道和交通沿线,同时旨在防苗;在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伴随着熟苗区的改土归流,在生苗区“开辟新疆”。至此,黔东南地区纳入国家统一建制,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交流双方的另一主体——汉人移民伴随着政治导向进入黔东南,汉人移民的种类主要有军籍移民、民间移民和仕宦移民等。汉人移民大量进入黔东南境内后,苗汉两大族群不可避免地被放在了同一个交流接触面上,黔东南境内的族际关系开启了新篇章。汉人进入黔东南境内之后,苗汉形成杂居的态势。明代,苗汉杂居仅限于驿道沿线和水路交通沿线,清“开辟新疆”以后,汉人深入生苗区,使清水江流域、雷公山腹地和月亮山麓等生苗区也出现了苗汉杂居的情况。苗汉之间的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界也随着王权和汉人的递进而递进。然而总的来说,明清时期黔东南境内依然是“苗多汉少”。
“开辟新疆”后,黔东南已完全纳入中央王朝的统治之下,清政府的经略从“征服”黔东南生苗区改为“防控”和治理黔东南生苗区。从这时直至清末,清王朝为彻底实现对黔东南生苗区的长治久安采取了不少措施,主要体现在上层建筑和苗族群众之间的政治互动,对苗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明清王化进程的逐步推进,黔东南境内各熟苗生苗区都逐步纳入国家的实际管控之下,汉族人口逐渐增多并日益土著化,聚居于场市集镇或散布于各山地,长时间与苗人错落杂处,在生产生活中密切关联,交往日益加深,族际间在经济、文化、生活、教育等方方面面的互动频繁。随着汉族人口的增多,汉民族的生活习俗对苗族的影响日益深刻,苗族的传统习俗在发生变化,一些具有民族特征的习俗逐渐消失,同时,一些新的民族特征又在不断产生。冲突和斗争,是明清时期苗汉族际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生激烈碰撞而又不能及时调适所产生的特殊形式的互动,其结果也必将产生新形式的苗汉族际之间的交流和交融。
二、明清时期黔东南苗汉文化交融
黔东南各族人民,在居住上相互错杂,在经济上相互促进,在文化上互相交流,在生活中互相往来,在语言上互相沟通,共同开发黔东南,缔造黔东南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形成历史上各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有交流交融也有民族矛盾和斗争,然而就人民之间的族际关系而言,友好合作无疑是主要的[1]。
明清时期,在文化交融的基础上,黔东南苗汉两族还出现了民族融合。融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事物化合为一体,失去了事物的本性。在民族学上,习惯上把民族融合用来指两个以上的民族融为一体。明清时期黔东南境内苗汉民族频繁的交流互动,或友好往来,或矛盾纠纷甚至发生民族斗争,从而导致了民族间最终极的关系形式和结果,即产生了民族融合。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汉间的民族融合表现为三种形式:汉人苗化、苗人汉化以及苗汉融合为“他族群”。在实际的田野调查中,苗汉融合为“他族群”又有两种形式,其一,苗汉融合为家[2],出现了有别于苗汉的另一个族群;其二,苗汉融合为“酸汤苗”[3]或“三撬人”[4],出现了“非汉非苗”“亦汉亦苗”的“他族群”。在田野调查中,我们发现汉人苗化的情况比较多见,黔东南境内许多地方的老人能清晰描述自己家族或者相关家族有汉人苗化的历史经过,在苗人家谱中也常发现其追溯汉人先祖的记载,可以说汉人变苗的个案在黔东南境内较为常见。
现代部分学者认为,明清时期黔东南出现了大规模的苗人汉化现象,考其论证过程和论据,再参考大量黔东南地区的明清史志,其实未必,史志多载:苗族聚居地区社会风貌“渐趋中州”,但只能证明苗汉杂居,交流频繁,苗人风俗习惯受汉人影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迁而“渐趋中州”。当然,考察历史,我们不能否认明清时期苗人汉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但难以在史志和口述史里面寻其踪迹,这是因为苗人汉化具有隐而不显的特征。总的说来,明清时期的黔东南地区,汉人苗化多,苗人汉化少;汉人苗化显,苗人汉化隐;汉人呈现个体苗化,苗人呈现整体文化变迁。在汉苗的融合过程中,族际之间的婚姻关系呈现出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汉人苗化和苗人汉化通常是通过缔结婚姻关系来实现的。通过缔结婚姻出现的民族融合,其融合的走向取决于融合家庭所在村寨和社区是以苗文化为主体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其融合的后代也相应地成为文化主体一方族属的成员,成为这一主体文化的传承者。
苗族是黔东南境内的主体民族之一,境内苗族人口比例最高,苗族文化占主导地位,苗族对自己的身份有强烈的认同感,苗族和这片土地相依相生,融于一体,浑然天成,这是黔东南地区历史以来的自然生境。清代开辟黔东南生苗区后,汉族移民相对以前较多地涌入黔东南境内,他们被称为“客民”。汉族移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处于领导和优势地位,但是在文化上,少数民族文化特别是苗族文化特征依然处于主体地位。自明清至近代,黔东南苗汉民族间的融合关系,以汉人移民“苗化”为主,苗人“汉化”仅存在于集贸市镇,个别读书取仕的仕子及嫁于汉家的苗女等等,其数量小于汉人苗化的数量。苗人汉化具有偶然性,汉人苗化具有普遍性。
现代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黔东南地区苗人汉化严重,其根据是史志里面屡见不鲜的诸如“渐趋中州”“服同于汉人”等记载。笔者认为,“趋”并非“同”,“服同”多指男性,而史志里面有这样的记载,恰恰证明苗人和汉人还有实质的区别,只是“趋同”。这些记载,证明开辟黔东南生苗区以来,生苗变为熟苗的普遍性。生苗虽变为熟苗,生产生活习俗等方面发生了一些呈汉化趋势的改变,然而其苗族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并没有改变,其苗族的身份并没有改变。生苗变为熟苗,这是苗族文化在吸纳汉族文化的基础上,对自身苗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这样的文化发展使得其更具生命力和包容性,也更加丰富和具有多样性。
明清以来,苗族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主要动因来自汉族移民的出现和汉文化的浸润,这使得苗族文化的变迁看似一个被动的结果,其实不然。我们发现,明清中央王朝想要控制和“内化”黔东南生苗区的一系列强制性的政令往往并不能产生实质性效果,这些政令包括改装、赶苗拓业、禁止苗汉往来、设置关卡、禁止苗汉通婚等等,这些政令无论是促使苗族内化还是阻止苗族发展,由于其违背了苗汉人民的意愿,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往往实行不久,并不能奏效。真正使得苗文化发展变化的是来自苗族人民内部的意愿和主动性的民族间交往交流。比如为发展而改良农作物,改进生产方式,为交流而学习汉语,为进步而学习汉字、接受汉姓,为方便而改进着装,为文明而接受儒学、中医,等等。
三、现代苗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启示
可以说,自苗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开发黔东南这片土地后,这片土地就打上了苗族文化的烙印,成为苗族人民的大地母亲,是苗家的根,是苗族文化创新发展的沃土。然而改革开放以后,苗族文化传统的生境和存在模式逐渐被打破,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席卷而来,苗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外因并非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内因才是主导动力,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根据对明清时期黔东南民族关系和苗族文化发展经验的总结,外来文化的冲击并不足以使苗族文化发生根本的改变,按照历史的经验,这些外因苗族文化可以吸收和利用。只要苗文化的根未变,可以调整她强大的创新性和包容性来融合外来文化。
然而,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和开放的时代,所有的传统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苗族文化也概莫能外,苗文化的因子在许多方面发生着一定程度的嬗变。在打工潮、学生潮、族际通婚普遍化的今天,苗族同胞自我认同感不强甚至抵制苗族身份这样的心理在部分地区还有所体现,现代文明对传统苗族文化的冲击日益加大。一旦失去了“根”则无法传承、发展和创新。很多苗族年轻人不再会古歌、刺绣、织布等民族技艺,甚至在部分苗族地区,苗族语言也在逐渐消失,这种情况下,苗族文化的发展和创新将会失去根本和依托。因此,在当今社会,保护、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根本是提高苗族文化的内生动力,活跃苗族文化因子,提高苗族文化的创新性和调适能力,提升苗族同胞民族身份认同和增强苗族居民的自信心。
自元在今黔东南施行土司制度始,明初置卫所建屯田,汉移民开始迁入苗岭山区,熟苗区形成苗汉杂居之势,这是苗、汉文化接触之始。雍正年间“开辟新疆”,在黔东南生苗区设立了“新疆六厅”,乾隆年间在黔东南苗族地区屯军设堡,苗汉形成完全的大杂居、小聚居之势,苗寨和屯堡交错,既有汉人杂居苗族村寨,也有少数苗族杂居在汉人村落,同时还有苗汉参半的寨子。苗汉族群接触互动,进行各种经济文化交流,即使明清王朝间或的征伐和隔离也挡不住苗汉族群间的联系交往。苗民接受了客民带来的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汉人也接受了一些适应于山区生存的苗人生活方式。经过几百年的文化接触,苗文化受到了汉文化巨大的冲击和影响,苗文化由此呈现出的巨变是显著的,然而对于大多数黔东南境内的苗区来说,这种变化也只是量而非质的变化,苗文化虽受汉文化影响显著但从未消失,在黔东南的很多地方依然是主体文化。到新中国成立前,黔东南地区总体来说还较为完整地保存着鲜明的苗文化特色,程度上略有不同,城镇地区汉苗文化参半共存,“新疆六厅”等原明代生苗区依然长期处于比较封闭的高山深菁,民族特征保留更加完整。
20 世纪中叶响应国家政策进行三线建设,一批汉族技术工人和干部群众随之迁徙落居到黔东南地区。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族和其他民族迁入黔东南地区的同时,苗族同胞也开始走出苗寨,到外地务工、就业、上学。苗汉民族关系出现了新变化,苗族文化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以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苗族社区金井村为例,改革开放后,经过各族人民40 多年的建设,凯里成为新兴的小城市。坐落在凯里城区边缘的金井村,不断受到来自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击。金井村苗民从20 世纪60 年代起逐渐成为菜农,为凯里市供应蔬菜,使其商品经济的意识日益增强,同时与外来文化的接触也日益增多。村里除少数老年妇女只会苗语外,一般的青壮年都既会苗语又会汉话。平时穿苗衣的也比较少,中老年妇女虽保留苗族发式但却着汉装,男子的装束则与汉人完全相同,青年无论男女则多追求现代流行的服饰和发式。村里原先保留有少数吊脚楼,近年新建的砖瓦房则几乎找不到苗族建筑元素。苗、汉通婚相当普遍,葬俗和婚俗与汉人基本相同。节日上,不再过传统的鼓社节和苗年而过汉人的节日,只是在正月举行的芦笙会上,跳芦笙、对歌、斗牛等活动还保存着鲜明的民族特色[5]。在广大的乡村苗族村寨中,情况要稍好,但同样也存在汉文化影响巨大,部分苗文化特征消失的现象。除了民族间自然交往交流交融的影响所产生的民族文化变迁外,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造成对民族文化的过度开发也引起了社会大众和苗族同胞对苗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担忧。
纵观黔东南以及其他地区苗族的发展现状,苗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危机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婚模式和家庭结构多元化。传统的苗族青年婚配,往往有着相对比较固定的婚姻圈。改革开放前,黔东南许多苗族地区对苗族与他族通婚往往存在芥蒂,改革开放后,阻止族际通婚的传统观念逐渐放开,苗族与外族特别是与汉族通婚的情况日益增多。通婚模式的变化造成家庭结构的多元化,在文化上也呈现出家庭内的多元文化并存。虽然苗汉间通婚的后代子女在填报民族身份的时候多会选择苗族族别,然而他们在传承苗族文化的时候会出现新的挑战,容易出现苗文化的断代和传承危机。
第二,居住较为分散。在传统苗族社会,苗族往往聚族而居,以“鼓社制”“议榔制”“理老寨老制”等内部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和固定的婚姻服饰圈为稳定和传承苗族文化的中轴。然而现代,苗族同胞广泛走出村寨,外出打工、就业、学习,定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传统的聚居模式发生了改变,离开了苗族文化世世代代所植根的土壤,到别的地方分散居住,周围没有或者很少有家乡父老,生活和生产习俗势必发生一定的改变,传统苗族文化的传承受到挑战。
第三,文化表征弱化。现代社会的开放性和全球化趋势,使得苗族的传统文化,如语言、服饰和习俗等受到严重的挑战。年轻人为了生产、学习和生活等方面的便利很少穿民族服装,很多城镇苗族青年不会说苗话,传统的生产模式、生活习惯和节日习俗等也因为经济发展、旅游开发、生活便利或者环境变迁等诸多因素而出现减省或者变化,如此等等,都是苗族文化表征弱化的表现,换句话,苗族文化的特征越来越不明显,这也是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巨大挑战。
第四,传承机制变化。在传统苗族社会,家庭教育和村寨社会教育让苗族文化得以传承,口传心授的民族文化传承方式让苗族传统文化一代一代地延续。在近代以前,苗族儿童特别是苗族女童以接受家庭教育为主,她们在家庭口授心传的教育中继承和发展了蜡染、刺绣、飞歌、舞蹈等民族技艺和民族文化。如今学校教育取代了传统家庭教育和村寨社会教育,传统文化的传承机制发生了变化。无疑,学校教育是新时期最有效、最直接和最科学的文化传承发展方式,但是如何在学校教育中科学系统地进行苗族文化和苗族技艺的传承教育,如何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也需要在不断地实践创新中进行研究探讨和健全完善。
第五,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的脚步不断加快,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相比较而言,苗族地区因为历史和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较慢。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部分苗族地区由于经济状况欠佳而导致传统民族文化出现失传危机,如,因为汉族服饰比苗族服饰更加便捷、便宜而改为着汉装,砖房比传统木房造价更低而建砖房。可见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苗族文化和苗族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危机和挑战。
四、保护、传承和发展苗族文化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全球化、现代化和外来文化对苗族文化的巨大冲击,在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但也并非无可参照,考察历史上苗汉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文化变迁,我们依然可以得到启示和借鉴。明屯军入黔东南和清“开辟新疆”后汉文化对苗文化的浸染,都为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参照。明清时期苗文化对汉文化的“趋同”而不“等同”,彰显了苗族文化的巨大生命力和调适能力。要使苗族文化得到良好的保护、传承和可持续性发展,笔者尝试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第一,保持苗族文化的创新性。任何民族的文化都绝非是一成不变的,苗文化亦然。明清时期在汉文化的巨大影响下,苗族文化实现了创新性的调适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无论是农业生产方式、经济运作模式还是文化本身,苗文化都作出了极大的创新,创新后的苗文化依然是苗文化,得到了苗民自身的广泛接受和他族的认可,内化于自身文化当中,成为新的民族特征因子。现代社会,人们常将民族文化看成是传统的不变的因子,因此一旦稍有改变就质疑或忧心其发展前景和未来。其实,苗族文化恰恰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社会的变化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冲击,真正实现可持续性。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当下,真正的孤岛文化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化的多元发展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导趋势。苗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苗族社会内部,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广大的苗族群众。增强苗族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提升苗族文化的创新性和兼容力,消解苗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冲突,创造既具有现代色彩,又兼备本土民族特色的苗族新文化,是实现苗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第二,提高苗族群众的经济收入。传统观点常常认为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封闭和相对贫困使得苗族文化得以保存,这在当时较少受到外来文化浸染和影响而言固然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显然已不再适用于完全开放的现代社会。恰恰相反,经济落后已经成为制约苗族文化传承发展的瓶颈。提高苗族群众收入,实现经济上的振兴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环节,而最有益的方法莫过于实现开发苗族文化和提高苗族居民收入之间的良性循环。积极发展苗族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加强苗族传统手工艺保护与传承,打造苗族文化创意产品和旅游商品品牌。在提高苗族群众收入,增强苗族同胞获得感的同时,促使苗族同胞自觉参与到民族文化传承当中。
第三,增强苗族同胞的自我认同感。现代社会,苗族同胞常常远离其原生居住村寨,分散到外地和城市工作、就业、生活,这更需要苗族同胞增强自我认同。即使着汉服、说汉话、习汉字、习汉俗也依然保持着强烈的苗族意识和苗族记忆。在苗族聚居的乡村,接续加强经济发展,深入实施乡村振兴的同时,大力推动民族村寨、传统村落和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保护和发展,创建一批苗族地区的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乡镇、示范村,让苗族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从而增强苗族同胞的自我认同感。
第四,完善苗族文化的传承机制。传统苗族文化丰富多彩,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缺失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大多数传承已久的少数民族文化一样,苗族也是只有语言,没有记录民族文化的文字,苗族五彩斑斓的民族文化是通过苗族同胞一代代口口相传而不断地传承下来的。现阶段,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机制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对于传统的口授心传的教育方式,如今的学校教育机制显得更加系统化和科学化。开展苗族文化教育的学校,课程体系设置要结合当地文化实际情况,取材尽量贴近苗族地区文化实际,选择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题材进行教学、传承和拓展;开发适合当地苗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教学教材;设计实施适合当地苗族艺术和苗族手工技艺传承和发展的课程体系。在苗族社区和苗族村寨,开展苗语、苗文和苗歌等的传承活动和培训,系统地开展苗族各种艺术和各种手工技艺的传授和培训,通过节日活动、旅游开发、对外交流合作等多种形式促进和完善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和传承机制。同时,整个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不断树立、培养和提高人们的苗族文化价值观念,引导正确的苗族文化价值取向,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