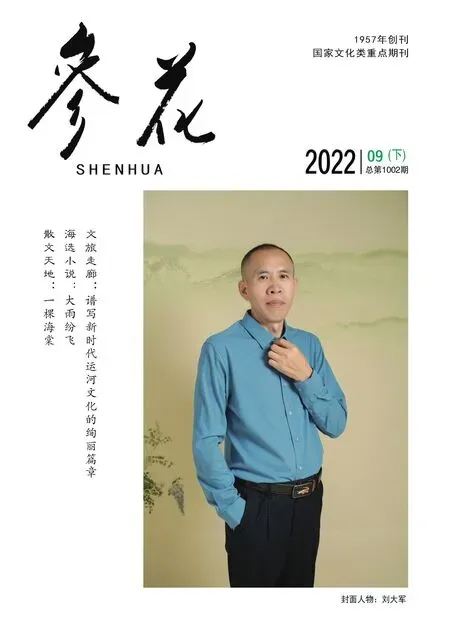风车的流年
◎周书华
一
乡下老屋的储物间里,有一架木制风车,在时光的碎影里,由于平时无人打扫已落满了厚厚的灰尘,风鼓里布满了蛛丝,静谧如初,却给人以久违的亲切感。自父亲去县城居住后,老屋里的一切都闲置了下来。每次和父亲回乡下老屋,父亲看到这台风车,他的眼神总会明亮有神起来,因为这是他和母亲当年劳作使用过的风车,为我们度过那段艰辛的岁月,做出了突出贡献,也算是我们家的有功之臣。
这台风车,储满了太多的记忆。自我离家时便把它装进了背囊,伴随自己奔走在异乡,从青丝缕缕到白发丛生。风车里装满了我们熟悉的粮食,装满我们欢乐的童年和少年,装满我们熟悉的风景和炊烟的味道。
风车,是我国传统的农村木制农具,在老家乡下,又叫风谷车。听村里年长的老一辈说,是“木工祖师”鲁班发明的。主要用来去除谷子、小麦、苞谷中的杂质,也可以用来去除掺杂在黄豆、豌豆、胡豆里的一些细碎屑末等。
小时候,风车在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的眼里是个稀罕物。任何东西都是有生命、有灵性、有感觉的,山有山神看着,河有河神护着,花里面住着花仙子,石头里藏着精灵,何况风车,其形如马,它有眼有鼻有荡气回肠的胸膛,早已融入了乡亲们的生活。在悠悠岁月里,它就是一个庄重的生命,一个爷爷辈分的长者。
家住四队的本族刚爸所做的家具做工精细,样式美观,榫卯结合严密,漆面干净,受到十里八村乡人的青睐。记忆里,刚爸不是在陈家赶制陪嫁的嫁妆,就是在丁家制作结婚用的大木床,一年四季休息的时间很少。
一到粮食收获时,家家户户都要用风车。为了在收割谷子、黄豆、麦子时不到处去借别人家的风车,母亲和父亲决定请木匠做一台风车。第二天,父亲去村里的小商店买了两瓶酒送到刚爸家,请他给我们家做一台风车。刚爸说,先找树形粗大且直的杉木料,放倒后将其放置在阴凉处自然风干,然后他再来打制风车。他说,新鲜木料没晾干做出来的风车会出现裂缝,也会影响风车扇叶的出风,如果风力过小,夹杂在稻谷中的细碎干禾叶、谷糠、秕谷等就不能正常分离。
在一个晴好的日子,父亲到舅舅家屋后的山上选了一棵杉木,伐倒去枝,扛回家裁成两米左右的木料平放在堂屋里,待其阴干备用。
一切准备妥当后,父亲择好日子,刚爸便带着他的工具到家里来打制风车了。刚爸做事一丝不苟,前腿弓,后腿蹬,刮拉凿砍锛,用工具将木料齐整地刨平,看得我羡慕不已。
风车形如“木马”,其制作考量着木匠师傅对我国建筑榫卯结构的熟稔程度,抱肩榫、夹头榫、楔钉榫、暗榫、长短榫、托角榫、挂榫……变化多端的榫卯结构集中在这“木马”上。每一个榫卯结构,都必须先画出榫卯线,再凿出榫槽、锯出榫头,最后检验榫卯能否咬合牢靠。
其中,最考验手艺的是风车的“大圆肚”,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制作的部位,全部用杉木板围成,每一块木板都需要精心测算后并形成一定的弧度,两块衔接的木板之间用竹钉铆住,最后围拢成一个圆桶状,要严紧密实才算成功。
风车的扇叶要选用一根坚硬的杂木料做芯,围绕木料的面凿孔,再插入风叶固定好,使风叶分布均匀,牢靠,这样才不会在摇动手柄时剐到“风车肚皮”。刚爸做出来的风车“大圆肚”,扇叶转动轻盈,风力均匀,手摇起来不费力。
刚爸的木工手艺,让我真正见识了什么叫高超,主要体现在严丝合缝和材尽其用两个方面。严丝合缝事关木质家具做成后是否坚固美观,尤其是全榫卯结构的,比如风车、八仙桌、板凳之类的家具,更是追求严丝合缝。用刚爸的话说就是,榫卯严实了,做出来的家具可不用一颗铁钉而稳固异常。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材尽其用的技巧,在我们看来几乎没有用处的一段木头,有的甚至是短小的木棍,在他的手里就可能魔术般地变成一根椅子扶手或者是橱柜上的装饰。就连榫头上截下来的小木片,他都能用锛子砍成一个个小木楔,再用来加固榫卯,真正做到了物尽其用。
二
村里晒粮的地坝空旷,每到丰收后的夜晚,老老少少聚在这个最热闹的地方。孩子们在这里嬉闹玩耍,摆在地坝边上的风车就成了我们的玩具。对于风车,孩子们的眼里满是好奇,这里摸摸,那里瞅瞅,摇动几下风车的手柄,听它发出嗡嗡的回声。我们最喜欢的是,在盛夏的傍晚,一个孩子摇着风车摇把,一群孩子站在出风口,感受缕缕小风。大家轮流着来,乐此不疲。借助风车降温,这大概也是山里农家风扇的祖师爷了。别的大动作不敢乱做,大人说,风车的构造比较复杂,整坏了得拆开来修,这让懵懂的孩子眼里满是新奇和小心翼翼,因此,这类游戏,我们都是背着大人才敢做的。
风车一般摆放在地坝边缘,便于将分离出来的杂物吹到一边去。母亲会吩咐我和哥哥将地坝里的谷子收拢在一起,然后装在箩筐里。等待父亲将箩筐里的谷子送到风车最顶部的入料仓里。
摇风车由母亲掌控,她说这个动作看似简单,谁都可以操作,其实还是有一定技巧的,既要掌握摇手摇动的快慢,又要控制漏粮斗下搁条的位置。倘若摇手摇得太快太猛,风力过猛,会把饱满的谷粒扇出去,那就浪费了粮食;如若摇得太慢,风力微弱,秕谷和杂屑等就分离不干净。因此,摇动摇手要适度均匀。
距离扇叶最近的地方,有一个漏斗形的出口,出来的是最饱满的粮食;另一侧稍远还有一个出口是出秕子的,一般用于喂养家畜家禽;最尾部的出风口出来的是草屑和灰尘。
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我们在旁边或帮忙拿盛粮食的口袋,或帮忙把谷子和苞谷朝风车顶端的梯形入料仓传送。累了,就躺在地坝边那些背回来的麦草垛上面,伸展四肢,看着深邃的夜空,让人真实地感受劳作后休憩的放松。
月亮挂在苍穹,浮在树梢,淡淡的清晖洒在村庄的每个角落。大人们不停地忙碌着,夜色在山野间弥漫开去,如水的月华融入了红土地。山村的夜晚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卷,凝神望去,无尽的墨色布满眼际,田间的绿色掩映于无边的黑暗之中,和夜色重叠交融,给浓浓的夜色增添了一层浅墨……
乡村的夜晚,是一种难得的悠闲和安逸。当凉风徐徐吹来的时候,会闻到庄稼地里飘来的味道,里面含着各种不同的香甜。蝉儿、蛐蛐的叫声,会随着微风一起飘到耳边,顷刻间,周围便弥漫着温馨与幸福。
三
七十年代末,农村实行分田到户,承包到人。这下,农民高兴得跳起来。耕种时间缩短了,效率提高了,产量增加了。渐渐的,乡人家里的粮仓满了,喜悦的笑容挂上了脸庞。
老屋里的风车,留下了我童年许多美好的记忆。孩提的我,常看着母亲手摇着风车慢悠悠地转动,倾听着风车奏出吱吱呀呀的旋律,看饱满的粮食从出仓口出来装满了箩筐。那是回响在红土地古老而质朴的乡音。
粮食是上苍和红土地馈赠给父母最贵重的礼物。粮食凝聚着父母从白天到黑夜从冬天到春天付出的汗水与心血。多少个日子,起早贪黑,在月色下还佝偻在田地里劳作。油菜籽、黄豆、苞谷堆成小丘小山的季节,父母在汗流浃背的焦灼中,在风车不停地运转中,完成对喜悦的一次次储存与装载。
那些在土地上劳作的日子,仿若昨天。
粮食丰收是一件喜悦的事情。有时候头天收的谷子没晒干,第二天还得接着晒,晚上得有人照看,这一般都是我们小孩子的事情。于是,哥哥早早地在地坝里紧挨着风车的地方放上凉板,上面再搁一床棉被。等待着夜晚的来临,这对我来说是件迫不及待的事情。
我们家的地坝在公路边上,晒粮食的时候被修整得又光又平,四周空旷,视线极好,躺在凉板上总会想到很多虚浮的东西来。
小时候,在奶奶家听里得最多的就是几位叔叔“讲古”,里面总有一个人物“红毛嘎嘎”,披着长长的红头发,长得面目狰狞,平日藏在大山里,到了晚上会把那些不好好睡觉的小孩抓走,有点类似狼外婆的样子,把我们吓得睡觉总喜欢蜷成一团。
于是,哥哥和我晚上在地坝里照看粮食时,会把晚上照看粮食睡觉的地方选在靠近风车的地方。风车就如一堵墙,给人安全感,就像是奶奶家的大黄一样给自己精心弄一个狗窝,觉得天天睡在这样精致的窝里就心满意足了——这是我年少唯一憧憬过的地方。
躺在凉板上,身上只盖一床薄薄的棉被。哥哥胆大,让我靠着风车,他身子挨着我,不一会儿就发出了细微的呼呼的打鼾声。
看着远处高大巍峨的九台山,挂在夜空中的月亮,如精灵般在云雾中游走,月光洒落在池塘里,如闪闪晃动的鳞片,一波一浪,随波而散,把一种美好的意境从自己的内心逐渐扩散开去,像月光下田埂上的一对倩影,让人充满无限想象与希望。
白天,那一棵棵生长在地坝边的洋槐树投下浓浓的树荫,我们坐在树下歇凉,看着人们从地坝边经过,再慢慢远去。
但是到了夜晚就全然不同了,那些高大浓密的树完全没有那么高大粗壮了,仿佛在天黑之前就老了,显得老态龙钟,快要支撑不住了。
山野间昆虫的叫声不绝于耳,从远处,近处,草丛里,墙头边,黑黢黢的树叶子里不时传来。叫声无处不在,无处不响。然而,这叫声又不是有节奏的,一声声低,一声声高,一声声呐喊,一声声窃窃私语,所有的声音都无法揣测。于是,内心有些莫名的恐怖在黑夜中没有尽头地弥漫而去。
地里的蛐蛐所展示的声调是唯一有节奏的。当一只独唱的时候,其他的就参与和声,此起彼伏地唱起来了,它们有的就在牵牛花的架子上,有的就在我枕头边不远的红苕地里,有的好像就睡在我的耳朵里,每一声都那么清脆震耳。
满天的繁星闪烁,密密麻麻地洒落在天地之间。只有栖息在山野林中的鸟儿和蛐蛐熟悉这样的黑夜,我能想象到它们的声音或许就适合这样的黑暗和浑浊,在悄无声息当中放开歌喉,让高唱的声响在红土地中间萦绕,回荡不息。
山村的夜晚是清静的,静得出奇,静得舒适,静得让人通透,就连对面三爷爷关闭房门的声音也是清晰的。夜晚越来越深,所有的声响也更加清晰。风很小,奶奶家地坝边上的树还是那么静,远处盘山公路上却有灯光亮了起来,那是一辆汽车,顺着盘山公路而行,出现在能照着我睡的地坝时灯光就直射过来了。那时恐惧感就退去了些,也许觉得并非如见到的这样恐怖。暗想,或许在某一天,我也会坐上县城的班车去大山外繁华热闹的地方吧。我还没有离开过村庄,我所乘坐的车会不会是去另外的一个村子呢?
就这样,天马行空地想着,迷迷糊糊地入睡了。在梦中,紧挨着我的风车变成了可以飞的大白马,带着我飞过高高的九台山,翱翔在红土地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丁点儿恐惧和害怕。
清晨,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只见几只鸟雀正歇息在风车上,亮开了嗓子,叽叽喳喳地叫嚷着。金灿灿的阳光从屋后的山顶冒了出来,踩着静静矗立在红土地里的葵花秸秆,攀爬过山墙边柏树的树尖尖儿,将金色的光芒洒向大地,瞬间便让人们睁不开眼来。田地里的蚱蜢飞虫东蹿西跳,开始活跃起来。洋槐树林里枝丫间蜘蛛们拉扯的细丝儿,在阳光的照射下亮晶晶的。
我们在风车的转动中,一天天地长大。
四
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木制风车现在已很少有人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更现代化的机械化脱粒去壳机器,风车的流年戛然而止。那些存放在老屋里的风车,开始慢慢退出农耕生活的舞台,只是作为一种曾经的农具,向世人展示着特定时代的存在以及那些纯真、艰苦、朴素的年代记忆。
此刻,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一隅,想起老屋里的风车,看着在云层中时隐时现的月光,我们由异乡到故乡,由故乡到异乡,生活的旅途就是这样不断地切换和变换,思绪也随着故乡异乡的改变而改变,有淡淡的乡愁,有浓浓的乡情。但这所有的一切,都随着至亲的远去,而被渐渐淡忘,感伤开始结茧,随之,将会麻木。在异乡的日子里,在某一个时刻,怀念往事,感慨时事的变迁,很少再能够回去了,即使回去了,也找不到心里所期盼的人和物,我的心也只是落在了母亲在红土地上青青麦田边上那方矮矮的坟墓,母亲在里头,我在外头,她们在故乡,我在异乡。
风车也在日复一日的旋转中,伴随着岁月,一点点地远去了,远到只有在泛黄的记忆里,才能找到它们越来越模糊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