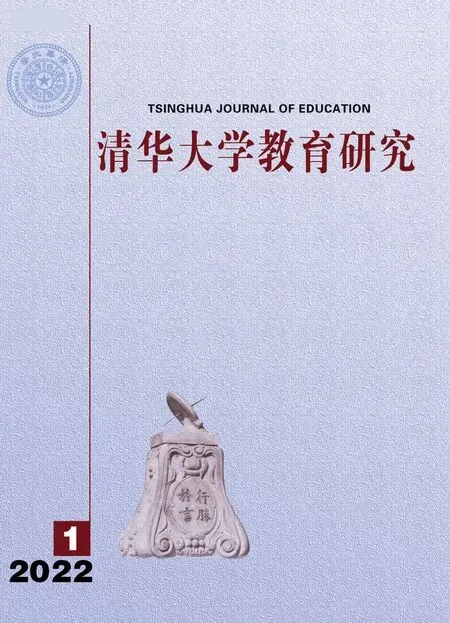论艺术教育的意义与价值*
凯瑟琳·埃尔金
(哈佛大学 教育学院,美国)
洪瑞祥 译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北京 102617)
当预算削减迫在眉睫,校委会首先会砍掉的就是艺术课程。因为在他们看来,艺术教育是多余的——资金充裕的时候可以有,如果资金紧张则没必要。不过,财务问题并不是艺术教育面临的唯一威胁。当下的课程是围绕国家规定的考试而设计的,如果将时间投入到艺术课程上,那么对学校而言就是减少了投入到那些更重要课程上的时间,比如像准备那些国家会组织考试的相关课程。很明显,在时间和资金的严格限制下,艺术教育成了学校的奢侈品。
认为艺术教育是多余的这种想法并不新鲜。布克·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曾认为,只有在非裔美国人社区实现繁荣之后才可以将艺术纳入教育计划。(1)Booker T Washington,“Industrial Education for the Negro,” in The Negro Problem: A Series of Articles by Representative Negroes of Today,ed.Booker T Washington et al.(New York: AMS Press, 1970).然而,这种认为艺术对于人类福祉而言并不重要的观念却忽略了艺术的普遍性。与科学不同,艺术显然是一种文化普遍现象。已知最早的油画和素描已有14,000多年的历史,已知最古老的乐器也已有7,000至9,000年的历史,繁荣不是艺术的前提。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回忆说,“(奴隶们)让他们狂野的歌声回荡在周围几英里远的茂密老树林里,以展露出最大的欢乐和最深沉的悲伤。他们且行且歌,忘却时间,忽略音调。一出现灵感就要让它流淌出来,哪怕没有词,没有调。”(2)Fredrick Douglass,“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in the Douglass Autobiographies(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但是,艺术的普遍性并不支持艺术教育的合意性(desirability),反而是其不合意的论证。如果人们无论用何种方法都能创作艺术,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投入本来就不够丰富的教育资源来教授艺术呢?道格拉斯描述中的奴隶没有受过正规的音乐训练,却创作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动人音乐。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就这样直接地让艺术发生呢?
如果这个论据对艺术不可教来说是成立的,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语言不可教。孩子们可以通过在讲母语的人身边成长来学习母语,却没人会认为我们就不再需要语言课程而只是这样顺其自然地让孩子们自学语言。我们感谢教育提高、强化、发展和完善我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但如果校委会不用同样的态度看待艺术教育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教育的误解以及对艺术的误解。一旦这些误解被修正,艺术对教育的贡献和教育对艺术的价值就会显现出来。
一、艺术可教吗?
对艺术教育可行性的怀疑来自于对艺术可教的怀疑。社会的刻板印象对此影响很大。艺术源于灵感,拥有灵感的天才也只是少数,可是人们如何获得这些灵感却没有答案。另外,艺术鉴赏纯粹是主观的,它和人们对艺术产生的感觉相关,因而口味这种东西是没有办法解释的。如果以上这些老旧的观点都是正确的,那么似乎艺术教育对艺术家或欣赏者都没有什么用;与其教艺术,倒不如去花钱教孩子们一些更实际的东西,比如尼罗河的起源。
对教育的误解则和一种假设有关,即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信息传递。学生就像是一个空瓶子,老师把正当的、真实的信念倒入其中,学生因此获得了知识储备,这就像弗瑞尔(Friere)所说的教育银行模式(3)Paolo Friere, The Pedagogy of the Oppresse(New York: Continuum, 2000).。但是因为许多艺术都不是命题性(nonpropositional)的,所以它不包含真理;同时大多数艺术也是没有论据的,因此也无法传达理由。尽管艺术以深刻的方式推动着我们发展,却很少带来新的信念(belief)。艺术作品几乎无法传达那些可靠的信息。马瑟西尔(Mothersill)认为 “从知识来源的角度分析,艺术表现不佳;作为获取世界或精神的新真理的一种手段,它在和科学与哲学竞争。”(4)Mary Mothersill, Beauty Restored(Oxford: Clarenton, 1984).在这场竞争中,艺术并不出彩。但是教育并不完全是信息传递。学生不仅要知道2+2=4,还要学会如何进行加法。学生不仅要知道“lid”在德语中是指“与格的”,还要学会如何使用和识别德语的与格结构。学生不仅要知道人们很讨厌被高高在上的态度所对待,还要了解那些被高高在上态度所对待的人是怎么想的,并且设身处地体会他们的感受。因此,尽管艺术一般不能成为可靠知识信息的来源,但也不应武断得将其从教育领域中剔除。也许,它是学习其他有价值知识的宝库和桥梁。
如何对艺术和教育不相干这种看法进行反驳呢?我们应该从艺术家和欣赏者两个角度来思考。如果灵感是艺术的本质并且灵感是无法教的,那么就意味着艺术的关键方面不能被教。毫无疑问,灵感有时会在艺术创作中发挥作用;但艺术完全是灵感的产物这一假设是没有根据的。管弦乐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乐团成员需要了解如何调乐器、如何识谱、如何演奏乐器以及如何在指挥下一起演奏;他们需要识别调式、主题、小节,同时具有对强弱、节奏和音调以及其他演奏者行为的敏感性。作曲家需要充分了解各种乐器的功能和局限性,了解声音和音调的特性及其相互作用,了解旋律、和声和节奏的模式及其可能性。这些东西是可以学习的,并且其中一些内容也是可以被教的。当然,我们无法保证了解这些知识的作曲者或表演者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但对这些事情毫不关注、一无所知的作曲家或表演者却会很容易成为糟糕的艺术家。
视觉艺术也是如此。美术专业的学生学习各种媒体的功用和局限,学习离散因素的相互作用,学习颜色、光线、阴影、形状和形式的效果及其各类组合并置所带来的影响。各个领域的艺术家也都会从了解其艺术领域的历史中受益——已经做了什么、如何被做的、哪里成功了以及哪里失败了。即使艺术天赋是天生的,教育也可以培养和发展各种艺术技能,而且技能会影响天赋的发挥。
这可能是艺术类院校拥有教育价值的一个理由,不过大多数学生并不会成为艺术家,那么艺术是否应该成为普通课程的一部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欣赏者的角度考虑。尽管我们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成为专业艺术家,甚至也不会成为严肃的业余艺术家,但我们都会成为观众。观众这个群体不完全由文化精英组成,无论你是看电视的、看电影的还是使用智能手机听音乐的,都包含在其中。
二、艺术欣赏可教吗?
观众不能被教这种观点来自于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用兰格(Langer)的话说就是艺术不是话语性的(discursive),而是呈现性的(presentational)(5)Suzanne Langer,Philosophy in a New Key(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她认为,在审美交流中,我们回应的是物体呈现出的可感知的品质,像色彩、形状和色调。我们的回应可能纯粹是感觉上的或是情感上的,但不是认知上的。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艺术就没什么可学的了;再加上欣赏者的品味完全是主观的(与个体感受有关),就更没有必要学习艺术了。
这种观点存在几方面的问题。首先,感觉回应(sensory responses)和情绪反应(emotional responses)可以被教。例如,在品酒或品茶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学会感知最初品尝时无法分辨的细微差别;通过视唱练习可以训练耳朵,让人们能够捕捉以前听不出的音调。而当我们关注自己和他人的情绪反应时,可以学会分辨本来无法分辨的差别。例如,我们能够学会分辨曾经认为没有什么区别的爱和迷恋。因此,即使艺术品纯粹是呈现性的,也存在一些东西需要学习。虽然简单地告诉学生应该敏锐辨别那些他们现在还无法区分的各种深度的蓝色是一种没有前景的教学策略;但是,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练习,学生是能够辨别颜色上的细微差异的。
也许有人会问,如果对艺术的回应纯粹是主观的,我们为什么要干预?如果没有理论说明天然的反应会比训练后的反应更差,那么学生在绘画时分辨不出各类蓝色也不会比能分辨得出更差。这里可以向康德求助(6)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他指出我们采取判断的形式对艺术进行回应。在谈论艺术时,并不像表达“我不喜欢奶油糖果”那样简单地表达我们的个人感受;我们是在向他人表达一种观点。如果有人说“这件作品是模仿的”或“那件作品太棒了”,那么他其实在暗示别人也应该这样想。为了使观点更有说服力,我们会给出为什么这样评价的理由,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依据都是可以被质疑的。在艺术的讨论中,我们总是假定存在某种错误。尽管对《哈姆雷特》有许多可以接受的解释,但将其解释为关于一个男孩和他的狗的故事,或者认为它是一部闹剧却是不对的。我们不认为对一件艺术品的任何感觉回应或情感反应都可以被接受。一个认为《蝴蝶夫人》的境遇挺好笑的人是无法理解这出歌剧的。忽略了《火鸟》组曲(7)火鸟组曲,美籍俄罗斯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根据其芭蕾舞剧作品《火鸟》的总谱改编的三部组曲,其中以第二部组曲最为著名。中有调性和无调性并置的人也不能理解这部作品。对艺术的讨论说明了我们认为审美反应并非是纯粹主观的。可问题是,它们怎么能不那么主观呢?
三、艺术是符号性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摒弃一种观点,这种想法隐藏在“艺术不是话语性的”这种表述背后。兰格这样表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不应假定如果艺术不是话语性的,就没有象征意义(8)Nelson Goodman, Languages of Art(Indianapolis: Hackett, 1968).。
古德曼(Goodman)认为艺术品是具有确定的句法(syntactic)和语义(semantic)结构的象征符号。句法确定符号的特性;语义决定了它所指的是什么。如果我们将艺术作品视为象征符号而不是仅仅作为有吸引力的(或缺乏吸引力的)艺术品,那么与艺术和教育有关的许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因为解释符号与认知有关,教育是可以影响到它的;甚至艺术中使用的各种符号也可以被直接用于教育领域中。
在艺术和其他领域,我们构造和使用具有不同句法和语义属性的符号。地图、图片、图表和乐谱是我们熟悉的非语言符号。在句法层面上,关键区别存在于那些属于由离散的、急剧分化的字符组成的系统符号与那些属于缺乏这种分化的字符组成的系统符号之间。书面语言中每个有语言意义的符号都由字母、空格和标点符号组成。这些原始元素的数量是限定的,也可以说是非常有限的。音乐乐谱同样是由相对较少的离散和确定的原始元素组成。此外,诸如图片和地图之类的再现性(representational)符号在句法上是很密集的。在某些方面最小的差异会对表像性符号的身份造成影响。如果地图或绘图上的线长短不一,它们则是不同的符号。但是,如果字母k以不同的字体或不同的大小打印,它则仍然是k。
库尔维奇(Kulvicki)通过融入信息论(information theory)(9)John Kulvicki, “Beholder's Share and the Language of Art” in the Meditations on a Heritage, ed. P.Taylor(London: Paul Holberton, 2014), 127-138.对古德曼的观点进行了拓展。他的信息论超越了弗瑞尔的教育银行模型,因为符号可以通过多样的渠道传达不同种类的信息、见解和启示。它们并不是被倒入空的容器中,而是会受到接收者能够理解以及可能理解的能力的影响;同样,接收者们接收到的信息也不限于传达者想传达的内容。密集和丰富的符号简洁地传达了丰富且复杂的信息。一首传统的布鲁斯歌曲可能在通过歌词传达快乐的同时也通过曲调传达忧郁。试图以话语的方式表达混杂的情感将是漫长的、模糊的、甚至是无效的。
一种超越文字消息的信息符号传递方式是通过暗示或暗示未明确说明的事物来进行的。如果有人说“公共汽车迟到了”,他其实是在暗示公共汽车应该要在特定位置、特定时间停靠的。同样,如果一幅画向我们展示了仓库的外在,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仓库也是具有内部空间的。库尔维奇认为,通过这种方式,艺术品可以在吸引和扩展观众的认知资源的过程中自我体现并且与人交流。
在语义层面,古德曼认识到两种基本的指称模式:指谓(denotation)和例示(exemplification)。指谓是一种语义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名称指代其客体,谓语指代其外延成分,图片指代其主体。因此,描述和再现依赖于指谓。虚构的符号,如独角兽图片或虚构人物的名字,都是指缺乏指谓的符号。古德曼认为,它们的可理解性来自于指谓它们的符号。因为有关“亚哈”的描述(Ahab-description)指谓了一个由特殊名称(names)和描述组成的集合的内容(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来自于《白鲸》(10)《白鲸》是19世纪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于1851年发表的海洋题材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亚哈船长为了追逐并杀死白鲸莫比·迪克,最终与白鲸同归于尽的故事。),因此这些名称和描述形成了亚哈的虚构身份。通过阅读小说,我们可以了解亚哈船长是谁,就像我们通过阅读传记来了解库克船长(11)库克船长,是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航海家、探险家和制图师,他曾经三度奉命出海前往太平洋,带领船员成为首批登陆澳洲东岸和夏威夷群岛的欧洲人,也创下首次有欧洲船只环绕新西兰航行的纪录。是谁一样,但是不管传记是怎么说的,库克船长还是他自己;但小说中这个角色却是由有关亚哈的描述所构成的。
有些符号,包括抽象的艺术作品、大部分的器乐和舞蹈在内,并没有意图来指谓些什么。他们通过其他方式传递象征意义。其中最突出的是例示,即样本或示例和其特征之间的关系。古德曼认为,要举例说明一种特征,象征符号必须与之有关并对其进行实例化(instantiate)(12)Vermuelen, Brun和 Baumberger (2009) 认为例证越多越好,示例必须通过其参照物的实例化来指代其参照物;Inga Vermeulen, Georg Brun and Christoph Bamburger. “Five Ways of (not) Defining Exemplification” in the Goodman: From Language to Art, eds. Jakob Steinbrenner, Oliver Scholz (Frankfurt am M.: Ontos Verlag, 2009), 219-50.。根据这种标准解释,织物样本可以例示其图案、颜色、质感和编织方式。该样本使这些特征得以体现,并提供了对它们的认知途径。同时,该样本还具有大量未例示的属性,例如特定的质量、年龄和距离。
由于商业样品(commercial sample)属于规制化的例示系统,所以既定的惯例和公认的先例规定了作为标准示例的样本特征;但是在艺术领域之外并非所有示例都如此规制。老师可能会将某同学的论文向全班展示以作为优秀或不优秀的例子。当他这样做时,该论文就是他希望学生们关注的论文示例。根据老师当前的教学目标,这篇论文可以示例说明其内容、形式、论据策略,甚至是作者整洁的笔迹。示例是精心选择的。它们通过边缘化、遮盖或淡化其他特征来表现、强调、展示和传达某些特征(13)Catherine Elgin, True Enough.(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
例示在艺术中起着重要作用。艺术作品彰显了自己的某些属性。例如,蒙德里安(Mondrian)(14)皮特·科内利斯·蒙德里安(Piet Cornelies Mondrian),荷兰画家,风格派运动幕后艺术家和非具象绘画的创始者之一,对后代的建筑、设计等影响很大。自称“新造型主义”,又称“几何形体派”。的方形画不仅由正方形组成,而且还指出了自身的这个特征。《火鸟》体现了有调性和无调性之间的张力,它关注并强化了我们对这种张力的敏感性。再现性作品(representional works)也可以作为例证。提香(Titian)(15)蒂齐亚诺·韦切利奥(Tiziano Vecelli或Tiziano Vecellio),英语国家常称呼为提香(Titian),他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的代表画家,他是意大利最有才能的画家之一,兼工肖像画、风景画及神话、宗教主题的历史画。他对色彩的运用不仅影响了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画家,更对西方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画的教皇保罗·伊尔(Paul Ill)的肖像指谓了教皇,并例示着衰败。托尔斯泰(Tolstoy)对博罗金诺(Borodino)战役的描述既指谓了战斗,又例示了一种对战争的态度。道格拉斯的歌曲既指谓了奴隶生活的各个方面,又例示了欢乐与痛苦的交融。在艺术中,一个简单的符号可以同时体现出不同种类的指称功能。与商业样本不同,艺术的例示完全不属于规制系统,它们反倒更像是学生论文那种类型,不是自动的,而是需要确定它们到底要例示什么。
例示在科学中同样重要。实验可以例示其结果——它使得结果变得显而易见。我们假设实验要揭示的现象是自然发生的。比如某种物质具有致癌性或分子键是弱的,但是该实验对其例示的特征却总会被混杂因素所掩盖。通过对样品进行提纯处理,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环境中,实验就可以突出其特征。这个过程就像是在小说作品中构想了一个可以体现情爱的场景。这个实验和虚构的小说一样,将自己与现实拉开了距离,以便揭示那些已有的特征,不过这在自然环境下是很难辨别的。
指谓和例示不一定是字面意义的。隐喻符号实际上可以指代它们的隐喻主体。像“斗牛犬”虽然是隐喻性的,但实际上可以指丘吉尔,那么“丘吉尔是斗牛犬”在隐喻性的解释下就是成立的。许多人认为隐喻纯粹是装饰性的,它们只是可以用字面意思表达的艺术性方式;但是,众所周知,隐喻通常会和其释义不同。尽管“丘吉尔固执”是正确的,但它的精确度不如“丘吉尔是斗牛犬”。隐喻显然不仅是文字事实的花哨释义。他们表现出了在语义上没有标记的延伸意义(16)Glucksburg Sam and Boas Keyser,“Understanding Metaphorical Comparisons: Beyond Similarity,”Psychological Review 97,(1990): 3-18.。在“斗牛犬”的延伸意义中,标准英语不包含针对此类人群的字面判断。因此,隐喻扩展了我们的语义和认知范围。它们使我们能够说出严格意义上无法用字面意义表达的事情。这种功能和再现领域(representational realms)也很类似。有关丘吉尔的漫画将丘吉尔画成斗牛犬,以这种方式来刻画字面上无法完全表现出的丘吉尔的特征。隐喻对科学也至关重要。在最前沿的研究领域,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那些字面意义贴切、能够直接表达的词汇,隐喻在这个时候就承担了助力交流和思考的责任。
隐喻不限于指谓。在隐喻涉及象征符号所具有的特征时,象征符号也就隐喻地例示了该特性。古德曼认为,表达(expression)是一种隐喻例示(metaphoric exemplification)的形式,具有这种功能的艺术作品可以表现出其隐喻示例的特性。由于没有生命,《圣母怜子》(Pietà)(17)《圣母怜子》是1497年米开朗琪罗应法国红衣主教之邀创作的一部雕塑作品。故事题材来自《圣经》,描绘了圣母玛利亚怀抱着被钉死的基督时悲痛万分的情形。不能真正地表达悲伤,但是它可以并且确实在隐喻上例示其属性,并以此表达悲伤。
因此,例示符合了兰格认为艺术是呈现性的属性。作品可以从表面上体现感觉特性(sensory properties),而在隐喻方面则体现情感特性(emotional properties)。由于例示是展示特性的一种手段,我们可以说作品展示了所讨论的特性。但是,根据古德曼的观点,艺术作品表面上的例示不仅限于感觉特性,表达也不限于情感特性。一幅画虽然不动,但可以表达运动;画中的号角虽然实际上是看不见的,但可以表达亮度和色彩。
上文已经详细讨论了古德曼的理论,建构性的以符号为代表的艺术作品可以帮助解释什么是艺术教育,为什么教育可以促进艺术的创造和欣赏,以及对艺术的理解如何与其他类型的理解相交融。例如,科学和哲学都经常使用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这些是简短的,关注虚构的,旨在例示某种现象或现象理论的特征。伽利略(Galileo)著名的思想实验例证了物体重量与下落速度之间的独立性。麦克斯韦尔(Maxwel)虚构的小恶魔破坏了热力学的第二定律,从而证明了该定律是统计意义上的,而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伽利略的实验可以进行,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做,因为它需要前提条件的还原。我们从实际的实验中学不到什么,我们也不知道实际实验可以从思想实验中学到什么。麦克斯韦的思想实验依赖于一个不可还原的虚构实体,它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认真对待小说来学习有关热力学的重要知识(18)Catherine Elgin, True Enough(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由于艺术中使用的符号同样也可以用于其他学科,如果要否认这些手段在认知上起作用,就是剥夺了我们在自然和社会科学等认知领域中使用的资源。但是一旦我们承认它们在这些领域具有认知功能,就很难否认它们在艺术领域同样发挥了认知作用。
四、艺术教育何以可能?
如果艺术品是一种符号,那么创作艺术品就是设计一种符号。创作能够传达特定意义的艺术品,就是设计一个适当有效的符号;而理解一件艺术品就是正确地解释符号,这需要掌握其句法和语义。这和语言也有相似之处。学生需要知道如何阅读非语言艺术以及语言艺术中的作品。这样看,艺术教育就类似于扫盲教育。学习如何有效地进行读写需要掌握自然语言的语法和语义。学生需要学习字母,词汇和语法。他们必须发展一种可以使用和识别字面的以及以其他各种形式起作用的语言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如何识别和解释隐喻、典故和其他比喻,并具备有效构建和使用它们的能力;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分辨话语表面之下是否还存在一些没说的东西,并掌握使用暗喻来传达比实际所说的更多的内容;他们甚至还需要掌握明晰特定段落中未说内容、特定段落所例示或表达内容的能力,以及学习如何撰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根据沃尔顿(Walton)(19)Kendall Walton, Mimesis as Make-Believe(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的观点,理解小说就是将其看作假扮游戏中的一种道具,让小说来构建和引导想象力。
所有这些能力在文学学习中大家都很熟悉,但他们其实在其他领域也很关键。比如说政治话语充斥着隐喻、典故、暗示和表达。如果要搞明白政治家的言论,那么了解一个对族裔表达蔑视的用语比了解该贬义用语所指谓的族群的确切界限要重要得多。比如某个政治家没有提及与对手正在进行谈判,那么这个行为可能暗示他已准备参战。要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氛围,需要拥有一系列复杂的语言能力。因此,阅读并理解历史上那些重要的原始文档需要依靠各种类型的象征符号。
理解文学作品所需的技能与理解语言的其他用途所需的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有着连续的关系,因此,和任何与艺术相关的研究相比,文学学习都更深入地融入标准学校课程。但是,语言符号(linguistic symbols)和再现符号(representational symbols)之间的句法差异似乎在说掌握表征符号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两个标记之间的差异会构成特征之间的差异(比如说线条的长度或形状的差异会使之成为另一个不同的符号),那我们就永远无法准确知道自己看的到底是哪个符号。如果我们连符号是什么都不能确定,又怎么能期望去解释这个符号呢?
幸运的是,这种观点并没有根据。学生习惯性地掌握语法密集的再现性系统。即使我们暂时不关注他们解释图片的能力,至少也能明显地看到他们学会了阅读和制作地图、图片。地图代表着诸如河流的路线,山的高度,城市的位置,州的边界之类的东西。标记之间的每个差异在某些方面都会影响地图上符号的性质。举例来说,如果代表尼罗河的线段更短或更细,那将是一个不同的符号。这种差异可能(但不一定)有着语义上的重要性。在一张试图准确展示尼罗河源头的地图上,如果代表这条河的线变短,那就表明这条河从更北的地方发源。代表河流的线的粗细一般来说和河流的体积相关,那么用较细的线来表示就表明它是一条较小的河流。不过,如果只是在地图上大概地指出其源头,并且代表河流的线的粗细没有什么意义,那么这些语法差异就不会产生语义上的后果。
这是地图上很常见的内容,学生学起来也很容易。地形的重要特征往往会在地图上标出,类似的重要特征也会以相同的方式表示。例如,在一张导航图上,相同大小的城市会用相同大小或相同颜色的点表示;在一张政治地图上,具有相同投票模式的区域会以相同的颜色表示。因此,那些在一张地图上以相同方式表示的城市可能在另一张地图上有不一样的表示。在学习制作和阅读地图时,学生需要学习如何构建和解释非语言符号。这不仅涉及识别像蓝线代表河流、点代表城市这样的知识,还涉及那些地图上没有呈现出来的内容。比如地图上没有体现罗切斯特(Rochester)和锡拉丘兹(Syracus)之间有城市,这是否可以推断出两者之间就真的没有城市呢,抑或是两者之间没有重要城市,再或者两者之间没有人口众多的大城市?这其实都可以。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学生需要知道地图旨在传达什么样的信息。他们需要学习从什么样的地图中得出什么样的推断是合适的(20)Elizabeth Camp,“Thinking with Maps,”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20,no.1(2007): 145-182;John Kulvicki,“Maps, Pictures, and Predication,”Ergo 2,no.7(2015):149-174.。这里的关键点在于地图阅读和地图制作是容易学习的技能。尽管每个特定方面的差异都会带来特征的变化,但我们也可以学习如何在特定情况下识别那些真正有用的特征。
因此,句法密度原则上不会妨碍对符号的掌握。学生可以轻松学习阅读地图和图表。但是,也许有人会说,所有这些符号都是经过严格规制的。地图上会有一些关键性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告诉读者标志代表着什么,如何代表的及其缩放比例。图表已经被这种形式标准化了,但绘画、雕塑这些艺术作品却无法提供这样的关键信息(21)Frigg Roman and James Nguyen,“Mirrors without Warnings,”Synthese 198,(2021):2427-2447.。其实艺术并非如此。为了理解政治海报,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图片和文字一样具有批评意味。要理解政治家的竞选演说,人们需要认识到他的某些手势什么时候表示蔑视,什么时候表示钦佩。正确解释他的言语、图像和手势对于理解他正在做什么很关键。因此,学生在其他学科(例如历史和公民)中掌握符号所需的能力与他们掌握艺术符号所需的能力是相同或相关的。
不过与其他学科相比,艺术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历史、地理或物理学中,因为语境会受到很大限制,所以会提供一些与符号有关的线索,即其在哪些方面很重要以及它们可能表示什么。但是绘画或四重奏(尤其是当代绘画或四重奏)原则上可以通过任何特征来象征任何事物。这是程度的差异,不是种类的差异。这只不过表明学习解释美学符号要比学习解释其他学科的符号更困难。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让步太多。尽管这样的艺术允许在任何维度,以任何精确度进行符号化,但并非每件艺术作品都是如此。学习解释艺术作品就像在学习解释其他符号,学生从相对简单的符号开始,然后逐步增加难度。例如,在颜色明亮、色调简单、人物清晰、情绪凸显的幼儿绘本中,一张画有巫婆家附近树林的图片在表示恐惧感,对一个三岁的孩子而言,我们不能奢望他精确地表达出这种恐惧感究竟是胆怯、骇人还是不祥。如果小朋友意识到图片描绘了树林并且表达了恐惧的感觉,那么她就足以正确阐释这张图片。尽管恐惧还可以进一步细分成不祥、胆怯和骇人,但这个符号本身也不需要反映这种更进一步的区别。正如我们可以不用特意精细地去表达某事是恐怖的,一张图片也无需特意精细地去表达恐惧。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生会遇到更复杂的图象,这些图象有着更多的象征维度,并且属于那种有着更精细区分的符号系统。学生可能会被要求判断像丢勒(Dürer)(22)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 )生于纽伦堡,德国画家、版画家及木版画设计家。丢勒的作品包括木刻版画及其他版画、油画、素描草图以及素描作品。《骑士、死神与恶魔》是丢勒的铜版画,形象深含着对时代认识的哲学内容。的《骑士、死神和恶魔》(Knight, Death and the Devil)是仅仅表现恐惧还是表现那些更精细的情感。尽管这个问题很困难并且不管怎么回答都会存在争议,但要是与确定里尔的疯狂场面表现出的究竟是神经、暴怒还是狂怒相比,这个问题显然没有那么困难,也不存在那么大的争议。学生进步的一种方式是学习不断构建对艺术品的敏感解释,随着学习的深入,这种敏感解释的正确性也在不断提高。
很显然,艺术教育是可能的。艺术中使用的各种符号也会被用在历史、语言、地理这些毫无争议的“主科”上。创作和解释艺术品所需的技能也同样被其他学科需要。并不仅仅是艺术,所有学科都需要创造力、才能和天赋,而且艺术也没有比历史、科学等其他学科对它们更为需要。所以认为艺术在教育范围之外的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不过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并非所有可以教的东西都应该被教,那有什么理由可以证明艺术应该成为普通课程的一部分呢?
五、作为普通课程的艺术
针对上面的问题,一种答案关涉艺术的内在价值。创作和欣赏艺术品本身就是目的,这一点不需要通过任何艺术产品来证明其合理性。体现艺术内在价值的证据来自艺术的普遍性。每种文化都在创造并重视艺术。与商业和技术不同,艺术似乎没有什么进一步的目的(further end)。那么认为艺术本身就具有价值至少是合理的。如果是这样,提高有关创作和欣赏艺术的能力的教育就很有价值,因为从本质上讲,它能够使学生实现价值目标。
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却面临着挑战。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论点来说明某物具有内在价值是极其困难的。挑战者总是会问:“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它?”由于本身的目并不需要服务于进一步的目的,因此对于内在价值的好处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受到挑战需要来证明其确实有意义时,我们似乎没有办法为其辩护。因此,可以考虑将艺术教育作为一种不错的手段(means)。
以众所周知的所谓的莫扎特效应(Mozart Effect)为例。正如一个口号所表达的,“音乐让你更聪明”,它认为聆听古典音乐可以增强智力。这种观点使得父母让幼儿(甚至在子宫内的胎儿)去听古典音乐,并让他们从小就开始上音乐课,理由是这将使孩子的SAT(23)SAT是由美国大学委员会主办的考试,其成绩是世界各国高中生申请美国大学入学资格及奖学金的重要参考,它和ACT(American College Test)都被称为美国高考。分数更高。但是并没有研究表明这种相关性(24)Rauscher, F.H.,G.L.Shaw, and K.N.Ky,“Music and Spacial Task Performance,”Nature 365(1993): 611.。一个有趣的神经学研究发现古典音乐的聆听与特定空间能力的短期改善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但是这种改善仅持续了15分钟左右,并且这种技能(折叠纸工作)也没有特别的价值。那种听古典音乐可以提高数学、工程技能或一般推理能力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从铃木小提琴(Suzuki violin)到提高智商仅一步之遥的观点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
与其像莫扎特效应的倡导者那样认为艺术教育有利于促进其他类型教育的进步,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通过艺术教育可以获得和发展那些掌握其他教育所需要的技术和能力。一个学生能意识到莫里哀(Moliere)的《厌世者》(Misanthrope)(25)《厌世者》又译作《愤世嫉俗》,是莫里哀于1666年创作的的一部喜剧作品。它以整个贵族社会作为讽刺对象,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腐朽堕落以及贵族社会内部自私虚伪、勾心斗角的情景。是具有讽刺意味的,也就能很容易地察觉柏拉图(Plato)的《申辩篇》(Apology)或孟肯(Mencken)(26)亨利·路易斯·孟肯(Henry Louis Mencken),美国记者、讽刺作家、文化评论家.有关猴子审判(Scopes Trial)(27)1925年3月23日,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便寻求一位自愿在法庭上验证这条法律的田纳西教师,于是制造了轰动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性事件:“猴子审判”(Monkey trial)。又因涉案的教师名叫斯科普斯(John Thomas Scopes),所以也叫“斯科普斯案”(Scopes Case)。的报道出现的讽刺意味,反之亦然。
尽管如此,却仍然存在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学生理解政治评论员的讽刺意味,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们学习政治评论呢,何必要绕道艺术呢?
虽然相同的符号功能是由艺术品和其他种类的符号共同表现出来的,但制约因素却有所不同。地图、图表是标准化的,由这些符号想要体现的功能所规定的外部限制条件决定了这些符号如何被解释——象征着哪些方面以及象征相关特征的程度。由于艺术作品设定了自己的限制条件,因此它们可以用作思维的实验室(laboratories of the mind)(28)Catherine Elgin,“The Laboratory of the Mind,”in A Sense of the World: Essays on Fiction, Narrative, and Knowledge, eds. Wolfgang Huemer, John Gibson, Lucca Pocci(London: Routledge, 2007), 43-54.。艺术作品可以隔离某一具体特征,并以更纯净或更清晰的形式呈现它们,或者以比我们日常生活更生动的角度来呈现它们。这和科学实验有相似之处。
由于限制较少,所以要确定艺术品的某个特定方面是否具有象征意义,以及它所象征的意义是什么,就需要对作品进行整体解读,并弄清楚艺术品本身会有哪些限制。由于这些符号一般是密集的,因此对此类问题的答案可能就不确定。通常来说作品会接受多种正确的解释,例如,给定的并置(juxtaposition)是否重要,取决于它如何帮助作品整体进行解释。可能对于一种解释,它是重要的;但对于另一个解释可能就不重要。比如说,批评家不同意塞尚(Cézanne)的《勒孔波蒂埃》(Le Compotier)中果盘唇形的重要性(29)Catherine Elgin, True Enough(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7).;那么为了使作品有意义,释义者就需要弄清楚各种可能的解释,并明确赞成或驳斥每种解释的理由是什么。它要求在认知的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达到微妙的平衡。
这种可以在认知上达到平衡的能力对各类学科的学习都很有价值,尤其在研究前沿领域的时候特别有用,它们并没有像我们之前所想的那样被限制。如何表示资料、如何区分有用和无用以及如何处理资料可能尚不清楚,具体的做法也可能会引起争议,但人们在解释艺术作品时获得的技能和在此过程中培养出的性情却可能有助于解释科学前沿成果。
提斯曼(Tishman)强调了“慢看”(slow looking)的价值(30)Shari Tishman, Slow Looking(New York: Routledge, 2018).,“慢看”即花时间并集中精力仔细观察,这在许多领域都很有价值。它能够使观众领悟并欣赏无法一眼就领会的特征的重要性。涉及缓慢学习的观察技能通常是很有价值的,而视觉艺术却为获得这些技能提供了特别的支持环境。因为从原则上讲,美术作品表面的任何特征都可能很重要,所以观看者不应过分迅速地将其略过;而且辨别出作品细微的、非显而易见的特征并且对作品进行玩味通常是有回报的,这种过程可以建构一种反馈循环(feedback loops),以促进观赏者更仔细地观察、更积极地认知。她认为,这种回报不仅是对艺术更丰富的欣赏,还是使我们能够认真研究自然和社会特征的技能。当然,这种技能是需要时间来领悟的。
认识论研究者经常关注那些证据少而无法证明结论的东西。但我们也经常会遇到很多拥有大量资料、却没有明显的方法将它们搞明白的问题。我们不知道如何将有用的与无用的分开,或者将有关的和无关的区分开。虚构(fiction)可以帮助我们。虚构的作品可以设计出一种情境,它能带来那些特定的模式、特征或可能性,并使读者意识到它们。具有虚构主题的绘画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虚构符号可以例示资料中存在的一种模式,但是它也会被其他重要因素所覆盖,因此很容易被遗漏。一旦学会辨别这种模式,我们就可以在普通生活中认出它。例如,俄狄浦斯·雷克斯(Oedipus Rex)体现了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观点,即人只有在死后才会觉得幸福。看过这部戏后,我们就能很容易在日常生活中识别一些看似不太稳定的好运时刻。(31)Catherine Elgin, “Imaginative Investigations: Thought Experiments in Science,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in the Literature as Thought Experiment, eds. Faulk Bornmüller, Johannes Frazen, Mathis Lessau(Paderborn: Wilhelm Fink Verlag, 2019), 1-16.。
发挥这种作用的也不只是虚构的作品。一件艺术作品,无论是否具有呈现性,都可以例示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存在却无法辨别的特征或模式。一旦我们学会了识别,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它们。道格拉斯对奴隶之歌的讨论体现了这一点:“他们讲了一个悲惨的故事,那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他们的声音响亮,悠长而深刻;他们低声的祈祷,抱怨着灵魂被极端的痛苦煎熬。每一个音调都是反对奴隶制的见证,也是希望能摆脱奴役命运的虔诚祈祷。”(32)Fredrick Douglass,“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Douglass Autobiographies(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94).
通过表达奴隶制带来的苦痛,这些歌曲体现一些蕴含在表象之下的东西。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并没有强调这些歌曲的歌词。嘹亮绵长而深沉的音调传达了奴隶的痛苦。他说:“我常认为,仅仅听这些歌,比阅读整卷哲学书更能让一些人记住奴隶制的可怕特征。”(33)Ibid.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艺术的力量远远超出了审美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和解释诸如奴隶歌曲符号的能力就显得至关重要。
这个例子似乎使事情变得太简单了。因为我们坚信奴隶制是邪恶的,所以好像这种能够让人们分享共同观点的方法可以增进理解。但是,无论歌曲如何动人,都无法向我们传达任何实际的证明论据。看起来,歌曲最多能让人们改变对奴隶制的看法,但并没有传达任何事实依据。这就存在一种危险,像这首曲子一样动人的作品可能会使人们认可不合理的结论。如果歌曲或其他艺术作品成为结论的全部理由,那么这种担忧就很容易解决。艺术作品只不过是强调特征、指出模式、表达或引人思考事物那些还未被发现的方面,从而使我们能够构建假设。除了在罕见的、自指的情况下,歌曲、故事或绘画本身并不能证明事物本身和它们是相一致的(34)米科宁(Mikkonen)特别针对文学提出了这种担忧。文学作品可能会误导他人,无法保证其不阻碍理解。的确,这是没有保证。但是,自称是事实的作品——科学论文、新闻报道、随意交谈也可能会误导他人。在对其中任何一个进行肯定之前,我们需要对其进行测试。。不过,构建那些值得研究的假说本身在认知上就很有价值。因为我们不太可能检验我们从未构建过的假设。即使艺术只能让人们构建这样的假设,它在认知上还是有价值的,不过有时它不仅仅是如此。通过例示特定的模式或特征,艺术作品可以促使我们提出假设,这些假设我们有充分的证据;但没有这些作品,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构建这种假设(35)David Lewis, “Truth in Fiction, Postscript,” in Philosophical Paper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使我们将熟悉的事实汇集在一起,以便感受和了解更多。
坚持认为艺术作品可以提高理解力,好像是低估了艺术作品在主观和情感方面的价值。它似乎使凝视《蒙娜丽莎》(Mona Lisa)就像凝视有问题的X射线一样。线条或阴影重要吗?它代表什么?它预示着什么?别人在看时和我看到的一样吗?如果没有,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们?但是,有人却认为,看蒙娜丽莎并不像看有问题的X射线。对于X射线,每个放射线医师都应尽可能客观,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在尝试得出结论,并据此得出本领域其他专家能认可的理由。这种情况强烈要求解释上的共识。但是欣赏者在观看《蒙娜丽莎》时,却不应抛弃其主观性。共识不是必要的,体验所带来的共鸣才是重要的。
将艺术作品视为符号的理论能平衡这种不同吗?我认为可以。我之前否认艺术纯粹是主观的,因为这可能会导致对艺术作品的误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主体性在艺术解释中不重要。与艺术相遇是充满反思的。我们走进艺术作品,也就在对它做出回应。我们会认为自己的主观反应可能是艺术作品某些方面的表现。如果《蒙娜丽莎》让我们感到神秘,我们会思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 在面对古罗马两面神雅努斯(Janus)(36)雅努斯(拉丁语:Ianus或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双面神,被描绘为具有前后两个面孔或四方四个面孔,象征开始。时,我们也会有同样的感受,它们不仅反映了艺术作品,也反映了我们自己,并且两者相互影响。我们越理解自己的这种感受,就拥有越多的资源来理解艺术作品;同样我们越了解艺术作品,我们的感受就越敏感和精妙。这就像提斯曼描述的那种反馈回路,主观感受并不是与艺术之美相遇的目的,而是促进艺术理解并与艺术相遇的手段。我们的感觉就像我们的感受一样,是解释的资源,它们表明了作品象征什么以及如何象征的。像其他的指示一样,它们也可能会产生误导。因此,需要对敏感力(sensibilities)进行教育。我们需要学习什么时候会产生误导、这些误导是怎么产生的,以及如何识别这些误导。我们还需要学习如何从误导性的表象中推断出实际情况。在可感知的情况下,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情。假如有一枚倾斜着的硬币,我们就会知道自己所看到的形状并不是其真实的形状,同时我们也学会了如何从我们所看到的表面形状中找到其真实的形状。关键点在于,对敏感力的教育并不是摆脱主观反应;而是在完善它们,以便在保持主观性的同时,使之成为越来越有价值的认知资源。
我们已经看到,符号理论下的艺术很容易说明艺术教育的可行性及其价值。杜威的手段——目的连续体(means-ends continuum)概念在这里很有用(37)John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16).。我们不应该像“莫扎特效应”的倡导者那样,将艺术仅仅视为手段来达到某一些具体的目的,而应该将它们既看作目的,又视为手段。理解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有价值的,这也为进一步了解艺术和其他事物提供了平台。我们要发展那些能够帮助甚至影响我们问出问题并找出答案的资源、观点和动机。无论是在艺术领域还是在其他领域,目的都是制定和追求进一步目的的一种手段。艺术教育促进了这一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