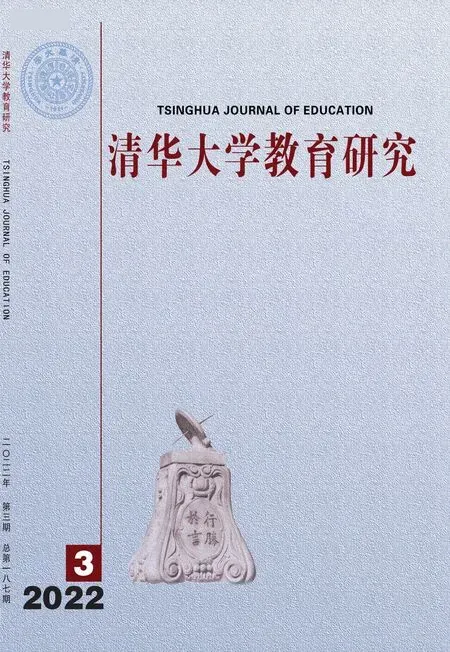西方大学和学术的祛魅
杨 锐
(香港大学 教育学院,香港)
为了进一步理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近年来,我特别关注东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这些社会与我们在文化传统上高度相似,但自近代以来在与西方的接触方面采取了不同的途径,也取得了不同的效果。这种相似和相异使得我们与其他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比较有其独特的意义。就我的体会和观察,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关于当代欧美大学发展模式。这一发展模式始于西方,几乎完全建立在欧美高等教育发展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欧洲向世界的征服和扩张,成为了西方向世界出口的第一产品。它与西方向世界出口的另一主要出口产品英语相结合,形成一幅沉重的十字架,严重束缚了几乎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学术和文化的健康发展,影响深远。今天,以西方经验为基本模式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在全世界普遍建立起来了。
目前不同国家的高等教育均日益难以摆脱外部影响,使得建立起与欧美模式根本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任务,至少是成本过高。西方大学由此形成对知识的控制。因此,国际知识体系在文化上充满偏见,在政治上极不公平。这是历史造成的。你可以不喜欢,但却不能不接受。认识到这一现实并对之加以妥善处理很重要,简单的抱怨、回避和抵触均不可取,必须主动而积极地对待之。
第二,关于当下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的判断。首先,从国际上看,西方社会及高等教育整体呈现颓废萎靡之状。相反,东亚尤其是华人社会的高等教育则表现出生机,活力和希望。华人社会的许多优秀学者具有在东西方社会工作生活的丰富经历,对于其所在社会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表现出高度乐观和自信。对于这种自信,按我个人的理解,它是缘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不少长期在东亚工作生活的来自西方文化背景的学者精英也越来越表现出类似的态度和认识。
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欧美是世界学术的中心。今天,东亚正在成为新的学术中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化更为突出。其中,我国高等教育日益增强的作用和影响尤为明显。我们的高等教育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期,重点已不再是规模扩张,下一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应该从数量转向质量,强调效能和品质。从“三千年未见之变局”到“百年未见之变局”,外部形势变了,我们的实力和处境不同了,但作为我们终极目标的民族复兴没有变,他人对我们实现目标的阻扰也没有变,而我们的策略则需要加以调整。
作为后发国家,发展对于我们而言,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强大的(甚至是霸凌的)西方做出正确的反应。一直以来,我们的发展总受到外部环境的高度制约。今天,学习西方仍然至关重要,但战略上应有转移,从以追赶为主转向更强调创新。这里有两点需要予以关注:首先是眼下情势的新变化,应高度警惕我们所熟知的全球化的破裂现象对于我们可能造成的影响;另一点则对我们更为有利,即下一阶段世界性的知识转移现象,从“西学东渐”到“东学西渐”,将为我国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提供知识支撑。
然而,我们的高教发展表现出了不少矛盾现象。比如,我们在对于本民族文化和社会表现出充分自信的同时,却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阐明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真实而系统地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理论、实践和决策。由于西方知识体系在我国建制已达百年以上,我们常常在做人时更加传统,做事时则更加西化;在动情时是中国人,动脑时就变成外国人了。这种不协调现象充斥于我们日常的工作生活之中,无时无刻不施以影响。这种矛盾的状况既表现于学术界不同的群体之间,甚至也表现于同一群体或个体之内。
第三,我们的高等教育理论研究问题。当前,在我们亟需建立文化自信的同时,我们中的不少人却对西方理论及其背后的价值存在着有意无意的顶礼膜拜。究其缘由,则是对于西和中均缺乏充分的认识,也因此未能扎根于我们自己真正的现实。我们常常不能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何支撑高等教育发展,而不知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理论思维的工具和方法常常是食洋不化的,存在消化不良的现象。有不少学者和大量的研究常常是悬在空中的,既没有落实落地,也不能走向世界。
我们需要祛魅西方大学,这不是去贬低它,而是客观深刻地认识之。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用西方作为参照和标准去发展、规划和看待自己,所以很有必要认识真正的欧美大学。西方大学在殖民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却并非总是光彩的角色,甚至有不少学者认为,它们仍然在扮演这种角色。在长期的追赶过程中,我们需要对之加以模仿,这是必要的,但仍然有必要了解其真实面目。这一要求在下一阶段的创新发展中则更为重要,因为它还同时影响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规划未来。
比如,学术自由常常被用来界定大学。其实,世界上没有哪个社会的大学具有绝对意义的学术自由,它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之下,总是有限制的。当前,国际上普遍强调大学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就更可能受到影响。苏格拉底和哥白尼的遭遇都发生在西方,当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我们的稷下学宫和百家争鸣却进展得很好。生硬地套用西方理论会导致严重的误解,西方学界长期将我们的历史描绘成他们进步的衬托者,僵化而专制。我们的学者则跟随之,不但不了解我们自己,甚至不乏曲解。
再举一例。对于西方大学中学术自由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进一步认识。其学术自由中的自由是自由于皇权和教廷,不少地方与我们的历史有很大的差异。而且,西方学术自由是典型的被动的自由,与我们儒家文化所强调的主动而肯定的自由,如家国意识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等,有着极大的区别。可是,我们常常一方面广泛使用我们理解得不够透彻的西式学术自由去框定我们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对于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特点却缺乏深入了解。这方面的例证很多。比如,创造我国两弹一星事迹的学术行为是那些强调个体权利得失的学者所难以企及,甚至无法理解的。试想,对于像范仲淹这样的儒者来讲,西式学术自由的意义如何?当我们将东方的专制和西方的自由对立时,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思维也都是西方式的,常常于不经意间毫无疑意地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和范式。再比如,长期以来我们都严重误解了罢黜百家和独尊儒术,关于焚书坑儒的解释更与历史极不相符。总体上,我们极大地夸大了西方的自由和我们的专制。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应该将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看成是自晚清引进西方文化以来社会变革的一部分。这点听起来很平常,但实际上非常重要。自那时起,我们一直在试图厘清中与西、古与今的关系。新文化运动已过去百余年,在许多人眼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旧是“世界的中国”,即以西方的标准衡量中国,而非“中国的世界“,即以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正如涂又光先生所说,我们的大学办成“在”中国的大学,而不是中国“底”大学。
自从西方文化在近代强势进入我国以来,我们一直纠结于如何妥善处理好古今中外之间的关系。尽管我们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处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探索仍在继续。今天,寻找适合我国国情的高等教育发展道路,仍是近代以来民族复兴的组成部分,目的在于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建立起一套精神价值。为此,高等教育研究者必须融中西、通古今,站稳自己的脚跟,探索出中国一流大学发展的独特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