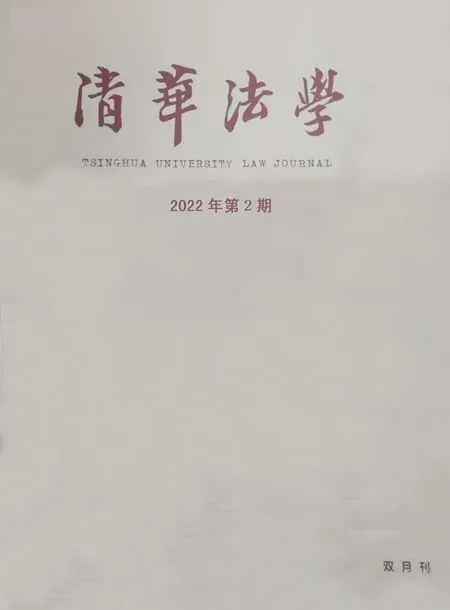“旧法律”还是“新权利”?
——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再研究
于 明
1689年的英国《权利法案》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宪法性文件之一。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权利法案》都作为世界历史上划时代的法律文件占据重要的位置,(1)参见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第一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与《人权宣言》《美国宪法》等宪法性文件一起共同构成西方法律文明的象征,也成为了普通中国人熟悉程度最高的外国法律文献之一。
但也仅仅是名称的“熟悉”。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权利法案》的深入研究却很少;在已有的中文著作中,对《权利法案》的介绍总是寥寥数笔。仅有的一两篇中文论文,也只是简单的介绍,缺少对法案本身及其意义的深入讨论。(2)参见张新宇:《从〈权利法案〉看英国革命》,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第96-97页;高全喜:《英国宪制中的妥协原则——以英国宪制史中的“光荣革命”为例》,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59-62页。以至于当我们思考《权利法案》时,会发现很多基本问题依然模糊不清:究竟为什么制定《权利法案》?它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权利条款的意义究竟为何?对于这些最基础的问题,中文学界至今未有专门的讨论。
本文试图回应这些问题,基本的论述结构如下:首先是重返历史现场,回溯从《请愿条款》到《权利宣言》的制定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主要争论与妥协。之后是对于《权利法案》主要权利条款的分析。这些讨论将表明,《法案》中规定的多数权利都并非“古代权利”的恢复,而是革命过程中确立的“新权利”;同时,即便在所谓“旧权利”中,也存在诸多观念与制度的更新。最后,我将检讨《权利法案》之所以被包装成“古代宪法”的历史成因,重新理解资本主义与新有产阶级的兴起对于英国宪制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并由此进一步呈现《权利法案》作为现代主权国家宪法开端的革命意义。
一、两种叙事:革命vs.复古
1689年《权利法案》的诞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传统的中文研究中,《权利法案》的意义,被简单概括为“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但这种“基础”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存在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权利法案》确立的原则是“新”的,剥夺了国王曾经拥有的特权,扩大了议会的权力,因此构成了一份推翻旧制度、创立新世界的革命性文件。但也有很多研究者倾向于否认《权利法案》的革命性,认为其中的内容“基本上是在重申英国人自古就有的权利”,(3)钱乘旦、陈晓律:《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5页。几乎毫无新意。就革命性而言,《权利法案》的创新在于形式,而非内容。
回到西方学界,这种认为《权利法案》只是恢复“古老权利”的观点并不新鲜。早在《法案》起草时,制定者就一再强调,《权利宣言》只是“为了确认和伸张古老的权利与自由”。(4)Lois G.Schwoerer,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1689,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295-298.这一论调在19世纪后更是发展成为“辉格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正如辉格史家麦考莱(T.B.Macaulay)反复强调的,《权利宣言》并未改变任何已经存在的法律:“王冠上的花朵未动分毫。没有一项新权利被赋予人民。最伟大的法律人霍尔特、泰比、梅纳德和萨默斯都断定:整个英国法在革命前后都没有改变。”(5)[英]托马斯·麦考莱:《麦考莱英国史》(第二卷),刘仲敬译,吉林出版集团2014年版,第387页。屈威廉(G.M.Trevelyan)已坚持“《权利宣言》在形式上是彻底保守的,没有引进任何新的法律原则”。(6)[英]G.M.屈威廉:《英国革命1688-1689》,宋晓东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89页。汤姆逊(G.Thomson)也写到,《权利法案》“并没有提出比既有法律更多的东西,它只是保护了英国历史上已拥有的权利”。(7)Mark A.Thomson, A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1642 to 1801, Methuen, 1938, p.175.
由此可见,中文学界否定《权利法案》革命性的观点,本质上仍是此类辉格观点的延续。对于“辉格史学”的观念,中国史学界已有较多的批判,(8)参见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118页、第168-172页。作为整体叙事模式的“辉格史学”已被摒弃,但不可否认的是,“辉格史学”的一些思维模式或具体观点在中国学界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比如,在英国法律史的叙事中,很多研究都强调英国自《大宪章》以来的悠久传统,将17世纪的英国革命解释为议会为恢复“古代宪制”而展开的伟大斗争,(9)对此类观点的批评和反思,参见于明:《议会主权的“国家理由”英国现代宪制生成史的再解读(1642—1696)》,载《中外法学》2017年第4期,第891-910页。而《权利法案》的意义也更多是对古老传统的恢复,而非创新。
但真的只是“复古”么?本文质疑这一看法。事实上,在西方学界的已有研究中,有关《权利法案》的“新旧”问题始终存在争论,传统的辉格观点亦不乏批评者。比如,韦斯顿(J.R.Western)和施沃霍尔(L.G.Schwoerer)的研究都指出,《权利法案》中多数条款都是新创造的权利与法律。(10)See J.R.Western, Monarchy and Revolution: The English State in the 1680' s, Rowman and Littlefield, 1972, pp.330-333; J.Carter, The Revolu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Geoffrey S.Holmes ed., Britain After the Glorious Revolution: 1689-1714, Palgrave Macmillan, 1969, p.43;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284页。本文即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检讨争议的焦点,重新回到《权利法案》的制定背景与文本,追问“新旧之争”背后的隐藏的宪制意涵,进而丰富中文学界对于《法案》的理解与研究。
二、“缩水”的权利——从《请愿条款》到《权利宣言》
首先有必要重返历史现场,重新理解《权利法案》为什么制定?又是如何被制定出来的?只有澄清这些基本问题,才能理解《权利法案》的来龙去脉,及其“新旧之争”的来源。
(一)曾经的宏伟蓝图:《请愿条款》的诞生
1689年2月13日,非常议会(convention parliament)的上下两院在白厅集会,参加威廉与玛丽的加冕仪式。上议院议长哈利法克斯侯爵向亲王与公主致敬,然后亲手呈上由议会两院通过的《权利宣言》。随后,议会礼仪官朗读了《权利宣言》,并将王冠授予威廉和玛丽。在接受王冠后,威廉国王发表了承认《权利宣言》的致辞,赢得现场热烈的欢呼。在许多史家看来,这无疑是英国历史上的“高光时刻”——在这一刻,“国王与人民自由地达成了一个彼此都同意的契约”。(11)同前注〔6〕,G.M.屈威廉书,第84页。尤其是加冕仪式上宣布《权利宣言》的事实,无疑意味着威廉与玛丽是以《权利宣言》“作为新国王登基的条件”。(12)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5页。
但历史真的如此么?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英语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传统的辉格解释强调,《权利宣言》构成威廉被授予王位的“条件”,强调在国王与议会之间的“契约关系”。但也有学者认为,将这一文件作为授予王位的“前提”,只是最初的企图;但事实上,威廉凭借自身的强势地位,很快迫使非常议会放弃了这种想法,并大幅削减了最初的《请愿条款》。(13)参见Robert Frankle, The Formulation of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17 The Historical Journal 265, 265-279 (1974); Howard Nenner, Constitutional Uncertainty and the Declaration of Rights, in Barbara C.Malament ed., After the Reformation: Essays in Honor of J.H.Hexter,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0, pp.304-305。因此,当《权利宣言》在加冕仪式上被宣读时,其意义仅仅是礼仪性的,并不构成威廉获得王冠的条件。《权利宣言》只是“威廉与玛丽发表的即位公告的一个序言”。(14)Andrew Browning ed., Memoirs of Sir John Reresby, Jackson and Co., 1936, p.547;同上注,Robert Frankle文,第270页。
从现存会议记录来看,非常议会对《权利宣言》的定位的确经历了较大转变。最初,非常议会召开的目的是解决国王的人选问题。但与此同时,非常议会的一些议员也开始思考如何“控制国王”的问题。福克兰(A.Falkland)主张首先要考虑“哪些权利是要给国王的,哪些是不要给的”。(15)Honble Anchitell Grey,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rom the Year 1667-1694, Vol.9, T.Beckett and P.A.De Hondt, 1769, p.30.坦普尔(R.Temple)还提出了全面的宪制改革建议,(16)参见同上注,第30-32页。但这种全面改革也遭到部分议员的反对。这些议员批评改革方案过于庞大,“必将占用过多时间”。(17)同前注〔15〕,Honble Anchitell Grey书,第32-36页。而一旦空位的时间太长,就会给詹姆士党人以喘息机会,并有成功反击的可能。用梅纳德(John Maynard)的话说,尽管改革是必要的,但“最紧迫的事还是要有一个国王”。(18)同前注〔13〕,Robert Frankle文,第267页。
基于时间的考虑,全面改革方案被抛弃,但议会依然决定制定一份文件来确保臣民自由。1月29日,下议院成立由39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由辉格法律人乔治·泰比(George Treby)担任主席,着手起草被称为《请愿条款》(Heads of Grievances)的权利清单。《请愿条款》共28条,虽然放弃了全面改革的计划,但较之后来的《权利宣言》,还是勾勒了一幅颇具激进辉格党色彩的路线图。其中很多内容在《权利宣言》中被删除,这些内容包括:①议会所议事项未能议决,议会不得被宣布解散;②法官非经审判不得被解职,法官薪金不得减少;③大法官与其他法庭的改革;④叛逆罪审判程序改革;⑤禁止买卖官职。(19)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23页。总之,《请愿条款》的内容远比《权利宣言》要广泛,改革的激烈程度也更大。
(二)“阉割”新权利:《权利宣言》的妥协
面对《请愿条款》,非常议会产生了激烈争论,并最终放弃《条款》,转而制定新的《权利宣言》。对于这一转变发生的原因,学界亦有不同看法。
一种解释来自辉格史学家,认为下议院删改《请愿条款》是为了避免威廉与玛丽继位的延迟。比如,麦考莱就认为,议会对被删除的条款并不反对,只是认为王位继承更重要,因此推迟了改革。(20)参见同前注〔5〕,托马斯·麦考莱书,第381-382页。另一种解释认为,由于议会内部存在严重分歧,下议院担心《请愿条款》提交上议院会被否决;因此,为减小阻力,下议院选择自行“阉割”《请愿条款》。(21)See David Lindsay Keir,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485-1937, Adam and Charles Black, 1956, p,269; Christopher Hill, 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 1603-1714, Thomas Nelson, 1961, p.253.
对于这两种解释,弗兰克等研究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在弗兰克看来,将《请愿条款》被抛弃的原因归于“时间压力”是不成立的。因为当时《请愿条款》已经完成,只要议会及时通过,就不会造成王位继承的迟延;相反,制定一部新的《权利宣言》将花费更多时间。(22)参见同前注〔13〕,Robert Frankle文,第272-273页。至于担心上议院的反对,弗兰克认为同样难以成立。从事后看,《权利法案》通过后,《条款》中被删除的一些内容又被重新制定为法律,但在这些法律通过时,上议院并未表现出明显敌意。甚至在一些法案(比如《三年法案》)的通过上,上议院比下议院更积极。
更重要的原因,或许来自威廉亲王的反对。威廉对《请愿条款》的反对态度在当时并非秘密。很多与其有直接交流的人都曾指出,威廉拒绝对其王权施加任何限制;在威廉看来,既然他是来恢复英国人的法律和自由,那么他也不会容许对国王传统权利的削减。(23)比如曾与威廉私下交流的苏格兰议会领袖蒙哥马利(James Montgomery)即持这一观点。参见同前注〔13〕,Robert Frankle文,第276页。从当时的情势来看,威廉的强势地位也足以迫使议会放弃激进立场。威廉即位后多次否决与《请愿条款》被删除内容相关的立法,也同样表明了他本人的立场。(24)比如,威廉即位后曾否决有关法官独立的法案(1691年)和《三年法案》(1693年)。总之,以上因素表明,从《请愿条款》到《权利宣言》的转变,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威廉对激进改革的反对。
这种转变从2月4日就开始了。在之前的讨论中,已有议员指出,《请愿条款》实际上包含了两种性质的条款,“其中一些条款是必须制定新法律才可能救济的权利,还有一些是无需制定新法的古老权利”。(25)同前注〔15〕,Honble Anchitell Grey书,第51页。因此,面对威廉的压力,下议院在2月4日作出决定,将《请愿条款》重新退回泰比担任主席的委员会,并要求他们“将条款区分为两类,一类是需要制定新法律的权利,一类是无需新法的古老权利”。(26)同上注,第51页。三天后,委员会完成了新的《请愿条款》,内容分为两部分;其中,11个条款(第1—4条、第6—9条、第19条、第21条、第26条)被视作“古老的、确定无疑的权利”,其余条款则被归于“需要新法律”的内容。(27)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23页。
在此基础上,下议院于2月7日组建了新的委员会,由辉格党法律人萨默斯(John Somers)担任主席,起草关于授予王位的决议。为推动《请愿条款》的通过,萨默斯趁机提议将修订中的《请愿条款》与授予王位的决议写进同一份文件中。(28)参见同上注,第24页。在得到议会授权后,萨默斯的委员会在《请愿条款》的基础上制定了一份《权利宣言》,与授予威廉和玛丽王位的决定捆绑在一起交付议会表决。2月12日,《权利宣言》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
三、古老自由的重申——“旧权利”中的新原则
1689年12月16日,新成立的英国议会正式将《宣言》通过为法律,称为《权利法案》。接下来,我们进入有关《权利法案》的“新旧之争”的讨论。
在《权利法案》的13个权利条款中,究竟哪些是“旧权利”,哪些是“新权利”?对于这个问题,不同学者一直有不同看法。有如前述,辉格史学家们往往倾向于宣布这些权利只是对英国人的“古代权利和自由”的重申。(29)参见同前注〔5〕,托马斯·麦考莱书,第387页。但也有的学者,如韦斯顿和卡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权利法案》在事实上改变了国王的权力。(30)参见同前注〔10〕,J.R.Western书,第330-333页;J.Carter文,第43页。还有的学者,如施沃霍尔,具体考察了13个权利条款,认为其中征税权、请愿权、持有武器权、议员选举自由、正当程序等6项权利确系中世纪以来的“古老权利”。但除此之外,如法律的中止、常备军的维持、议员的言论自由等7项权利均属议会在革命后才获得的“新权利”。(31)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284页。
当然,施沃霍尔的看法也并非定论,争论仍然存在。因此,在接下来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我将以最具争议的一些条款为例,深入考察这些权利的“新旧之争”。在第三部分,首先以“议会征税权”和“武器持有权”为例,考察所谓真正的“古老自由与权利”。之所以选择这两者,是因为在施沃霍尔列举的六种“旧权利”中,请愿权、选举自由、禁止酷刑、正当程序这四种权利几乎不存在异议。但对于“议会征税权”与“持有武器权”,依然存在不同看法。事实上,本文的分析将表明,即便是这些所谓的“旧权利”,也同样包含了新原则。
(一)议会征税权
在《权利法案》中,议会征税权无疑是一项“古老”的权利。依据《法案》权利条款的第4条,“未经议会授权,以国王特权的名义,为国王或其用度而征收赋税,超出议会授权的时限或方式者,皆属非法之行为”。从《法案》之前指控詹姆斯二世的内容来看,这一条款并非反对国王征税的特权,而是针对詹姆斯超越议会授权征收赋税的行为。
从表面上看,征税权从来都属于议会。在中世纪封建法中,“国王依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国王征税须经贵族大会议同意的习惯,并在1215年被写进《大宪章》。(32)参见[英]威廉·夏普·麦克奇尼:《大宪章的历史导读》,李红海编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13世纪后,随着封建制衰落,英王的封建收入锐减,难以维持政府开支;(33)See John L.Bolton, The Medieval English Economy, 1150-1500, Rowman & Littlefield, 1980, pp.325-326.同时,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动产税、关税等新税种成为王室财政的主要来源。这些基于商品经济的税收,不仅需要与贵族协商,还需要得到由骑士与市民代表组成的下议院的支持。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对征税的控制权逐渐向下议院转移。
爱德华三世时期(1327—1377),由于百年战争的巨额军费,国王被迫做出妥协,同意下议院成立专门委员会管理国王的税收。同时,1340年法案规定,“非经议会中伯爵、男爵和平民的普遍同意,国王不得征收任何赋税”,从而第一次在制定法中确立了议会的征税权。(34)See Bryce Lyon, A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History of Medieval England, W.W.Norton & Company, 1980, p.550.此后,经过一系列斗争,大约到14世纪中期,议会已基本控制征税权。随着骑士与平民力量的增长,下议院的征税权也开始超过上议院;在15世纪90年代的议会立法中,已不再使用“经上下两院批准”的提法,改为“征得上议院同意,由下议院批准”。(35)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到16世纪亨利七世时期,基本确立了财政税收议案只能先由下议院提出和决定的惯例。(36)参见刘新成:《英国议会研究:1485—1603》,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9页。
因此,《权利法案》对于征税权的规定,的确可被视作对传统的重申。但这并不意味着《法案》在这一问题上毫无创新。事实上,在17世纪前,议会从未控制全部的税收,国王对税收依然拥有实际的控制权。这种控制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国王基于特权,仍然享有征收“附加税”“船税”等特权税的权力,并拥有调整关税税率的权力;其次,从15世纪开始,依据惯例,议会是在国王即位之初授予国王终身征收关税的权力,从而导致关税的征收在事实上不受制于议会。(37)参见于民:《论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国财政体制性质的演变——财政收入构成角度的分析》,载《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第10-19页。而这两种情况的改变,都有赖于17世纪的宪法斗争。
首先,在17世纪的财税斗争中,国王的特权税始终是议会与国王斗争的焦点。1606年有关“附加税”冲突的贝特案、1627年关于“强制借款”的“五爵士事件”,以及内战前夕的“反船税”斗争,都共同指向反对国王特权税的目标。(38)相关讨论,参见[英]亚当·汤姆金斯:《我们的共和宪法》,翟小波、翟涛译,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99-106页。但直到1640年长期国会召开,这些国王特权税才被取消,国王对关税税率的控制权也转移至国会。(39)See L.B.Smith, This Realm of England, 1399 to 1688, D.C.Heath and Company, 1996, p.317.其次,对于国王的终身征收权,则直至1688年才获得解决。在17世纪后半期,由于海外贸易扩大,关税收入剧增,从原来每年30万镑增至60万镑,国王对议会税收的依赖也随之大大减弱。詹姆斯二世时,关税增至100万镑,以至于詹姆斯根本无需召集议会。因此,在《权利法案》中,明确强调,国王征税“不得超出议会批准的时限”,而议会对于威廉国王的征税权时限也严格限制为4年,(40)See Michael J.Braddick, The Nerves of State: Teaxation and the Financing of the English State, 1558—1714,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4.从而最终结束了国王对于税收的实际控制权。
由此可见,即便是《权利法案》对议会征税权的规定,也并非单纯的古老权利的恢复。从历史上看,非经议会批准不得征税,只是一种抽象的原则。事实上,国王在议会之外长期享有特权,并经常绕开议会征收税收。而由议会授予国王终身征收权的做法,更是直至1688年革命后才获得解决,从而确保了议会对全部税收的实际控制。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法案》对议会征税权的规定,同样是在宣告一项“事实上”的新原则。
(二)臣民持有武器的权利
较之议会的征税权,争议更大的是武器持有权。
在传统观念中,《权利法案》第七条关于武器持有权的规定,无疑是“古代权利”的一种。依据这一条款,“具新教信仰之臣民,在法律许可之范围内,根据其自身情况,可以拥有以防卫为目的之武装”。而从历史上看,臣民持有武器的权利,来自于民兵这一古老的军事制度。亨利二世时期,曾颁布著名的《军备法令》(1181年),要求所有自由民必须置备武装,并对不同财产的武装配备做了规定。(41)参见同前注〔34〕,Bryce Lyon书,第161页。
到爱德华一世时,由于骑士制的衰落,民兵地位进一步提高。1285年的《温切斯特军事法令》进一步明确了不同财产等级的装备配置,并开始由国王支付薪酬征召民兵作战。(42)参见施诚:《中世纪英国财政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6-87页。玫瑰战争后,都铎贵族逐渐向资产阶级化的新贵族转化,军事职能不断弱化,民兵完全取代骑士成为军队主力。(43)参见王萍:《从传统回归现实——英国都铎时期世俗贵族传统军事职能弱化现象简析》,载《世界历史》2009年第5期,第76页。总之,在传统观点中,正是由于民兵制的长期存在,臣民持有武器的权利,被视作当然的古老权利与自由。甚至是施沃霍尔这样主张《权利法案》包含大量新权利的学者,也依然将武器持有权归入到“古老权利”之中。
但即便如此,对于这一权利的“古老”,依然存在质疑。其中最主要的反对声音来自美国学者马尔科姆(J.Malcolm)。他强调,在1689年之前,英国人实际上并无持有武器的“权利”,而只有持有武器的“义务”。换言之,尽管在中世纪存在诸多武器持有的法律,但这只是为了满足公共防卫目的而强加的义务,而并非不可剥夺的“权利”,更非一种自由。相反,在任何时候,臣民的武器持有都随时可能受到国王法令的限制,甚至被完全禁止。(44)See Joyce Lee Malcolm, The Creation of a "True Antient and Indubitable" Right: The English Bill of Rights and the Right to Be Armed, 32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26, 226-249 (1993).
这种限制在中世纪与近代早期随处可见。比如,1389年的《狩猎法》(Game Acts),对于持有武器者的财产等级做了明确规定,其目的即在于解除社会最底层的武装,以防止1381年农民起义的重演。(45)See William Blackstone,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 Vol.2,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p.412. 转引自同上注,Joyce Lee Malcolm文,第232页。此后,许多国王都曾制定《狩猎法》,对臣民持有武器做出严格限制,其真实目的都是为了削弱民众反抗的力量。1661年,查理二世以伦敦骚乱为借口组织了国王的长期卫队,并通过法令宣布在伦敦禁止任何的武器持有。1685年后,詹姆斯二世亦借口蒙茅斯叛乱,通过《狩猎法》大量裁军,命令各郡长官解除当地民兵武装。(46)See John Miller, The Militia and the Army in the Reigh of James II, 16 The Historical Journal 659, 659-679 (1973).
在这个意义上,直至1689年之前,持有武器都并不构成真正的权利。这种从“义务”到“权利”的转变,正始于《权利法案》的制定。值得注意的是,《权利宣言》最初的表述仍然是“义务性”的,即“作为新教徒的臣民应提供和持有武器,以满足共同防卫的需要”。但在修订过程中,“应当提供和持有武器”被改为“可持有武器”。正是这一改变,将原本“应当”的义务转变为可选择的权利。同时,“公共防卫的目的”,也被改为“以防卫为目的”——而这也意味着持有武器的目的开始从公共安全转向个人防御。
由此可见,即便是武器持有权,《权利法案》中的规定也并非是“完全”古老的权利。在《权利法案》对武器持有的规定中,实际上包含着从“义务”到“权利”的视角转移,从而构成了对传统原则的重构。
四、重塑权力的边界——“新权利”条款解读
在检讨了“旧权利”的争议条款之后,第四部分集中讨论所谓“新权利”条款。
有如前述,“新权利”条款主要包括第1条(法律的中止)、第2条(法律的豁免)、第3条(教会事务法庭)、第4条(召集常备军)、第9条(议员言论自由)、第11条(陪审员资格)和第13条(议会经常召集)。从数量上看,这些“新权利”至少涉及7个条文,无疑在13个权利条款中占多数。以下,我们就选取其中最重要的五项权利——即“法律的中止”“法律的赦免”“征募常备军”“议员言论自由”与“议会召集”——展开具体的分析。
(一)法律的中止权与赦免权
《权利法案》第1条、第2条的内容均为对议会立法权的规定。具体而言,规定了两种停止法律的方式——中止权与赦免权。所谓中止权,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停止法律效力及其执行的权力,但并不完全废止(repeal)法律;而所谓赦免权,则是赋予某个体或团体以不受某项法律约束的权力。依据《法案》第1条和第2条的规定,国王如中止法律及其执行,或赦免特定人免受法律约束,须经议会的批准。
之所以将这两种权利置于首位,是因为在《法案》指控的詹姆斯二世的诸多暴行中,首先就是谴责“国王僭越并滥用权力,未经议会批准,中止法律的执行”。为争取天主教的合法化,查理二世在1672年颁布《信仰自由宣言》,宣布对一切非国教徒实行宗教自由,同时赦免“刑事法”(处罚不出席国教仪式的人)的适用。(47)See J.P.Kenyon ed., The Stuart Constitution, 1603—1688: Document and Commenta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p.407-408.相关背景,参见姜守明等:《英国通史》(第三卷),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37-138页。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不久后就宣布,他试图中止《宣誓法》,使天主教徒可在军队中任职。对此,反对派议员认为,“除非通过新的制定法,《宣誓法》不能被中止”。(48)Honble Anchitell Grey,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rom the Year 1667-1694, Vol.8, T. Beckett and P.A. De Hondt, 1769, p.362.1687年,詹姆斯再次颁布《信仰自由宣言》,宣布对天主教徒免于适用“刑事法”,并最终导致了“七主教案”和光荣革命的发生。
从历史上看,中止权与赦免权,的确属于国王的特权。有史料表明,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王就已拥有这两项特权。(49)See Carolyn A.Edie, Revolution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End of the Dispensing Power, 1689, 10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434, 434-450 (1977).就其本质而言,这两项特权源于处理紧急状态的必要性——当危机发生时,有必要存在某种权力去改变法律,而无需等待缓慢的程序。而在中世纪社会,这种紧急权力从来就属于国王,属于国王特权的范畴。(50)参见孟广林:《英国“宪政王权”论稿——从〈大宪章〉到“玫瑰战争”》,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28-329页。但问题是,这种特权是否应当受到限制?在中世纪,由于王权弱小,国王很少行使此类特权;但在都铎和斯图亚特时期,随着王权加强,此类权力的行使日益增多,相关争论也开始增长。尤其是在斯图亚特后期,随着反天主教运动的兴起,有关中止权与赦免权的争论日益成为宪法斗争的中心。
在这一时期的判决中,多数法官依然选择支持国王的特权。比如,在1675年的托马斯案(Thomasv.Sorrel)(51)See William Reynell Anson, The Law and Custom of the Constitution, Vol.1, Clarendon Press, p.349.和1686年的古登案(Goodenv.Hale)(52)该案中,被告人黑尔是天主教徒,经詹姆斯二世的赦免担任了军职;他的马车夫古登向法院起诉黑尔违反《宣誓法》。See Howard Nenner, By Colour of Law: Legal Culture and Constitutional Politics in England, 1660—1689,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7, pp.100-101.中,绝大多数法官都支持国王拥有赦免法律的权力。同时,布拉迪(R.Brady)等托利派学者也不断为这些特权辩护,宣称“如果国王不能行使赦免权,则无法统治”。(53)See Corinne Comstock Weston, Legal Sovereignty in the Brady Controversy, 15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09, 409-431 (1972).但与此同时,这些观点也遭到了辉格党的激烈反对。比如,阿特金斯(R.Atkyns)强调,英国君主制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同构成,因此对法律的中止和赦免,也应由三个机构共同通过,而不能由国王单方面行使。(54)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63页。
当然,随着詹姆斯复辟天主教的步伐不断加快,托利党人也开始放弃对詹姆斯的支持,并意识到国王滥用赦免权的危害。因此,在1688年的“七主教案”中,詹姆斯国王原以为法官们会继续支持他的赦免权,但结果却遭到多数法官的反对。(55)参见同前注〔47〕,姜守明等书,第141-142页。而这一案件的判决亦表明,英国议会已在此问题上达成共识——赦免权不应由国王独自行使。综上所述,议会对于中止权与赦免权的“攫取”,绝非源自古老的传统;恰恰相反,这一特权自古以来属于国王,直至在1688年的宪制革命中才被交到议会的手中。
(二)议会征募常备军的权利
有关常备军的条款,无疑也是《权利法案》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被视作议会主权得以确立的关键。依据《法案》第6条,“除经议会同意,于和平时期,在本王国境内,征募并维持常备军,皆属非法”。但回到英国历史上看,军队的召集与维持,从来都属于国王的特权。
在诺曼征服后的英国,最初的制度是有国王的总封臣提供的封建骑士军役的。14世纪后,由于总封臣数量下降,封建骑士军役逐渐衰落。(56)参见施诚:《中世纪英国的军役制度》,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11-18页。都铎时期后,贵族的军事功能进一步减弱,国王指挥下的临时征募的民兵,逐渐成为英国军队的主力军。(57)参见同前注〔43〕,王萍文,第76页。但不可否认的是,在17世纪之前,传统军队的征募和指挥,都当然地属于国王的特权,无需经过议会的批准。
但需注意的是,在中世纪的英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常备军。英国历史上的第一支常备军来自于1642年内战中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从这一时期开始,有关常备军的设立是否需要经过议会批准的问题,也成为了宪法斗争的焦点之一。(58)See Lois G.Schwoerer, The Fittest Subject for a King' s Quarrel: An Essay on the Militia Controversy 1641-1642, 11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45-76 (1971).1647年,查理一世在内战战败后与议会谈判,议会提出的恢复王权的条件是《纽卡斯尔建议》(Newcastle Propositions),其中就包括“由议会掌握军事力量,包括海军、陆军和民兵”。(59)Allan I.Macinnes, The British Revolution, 1629—1660, Palgrave Macmillian, 2004, pp.171-173.在此后的空位期,克伦威尔的批评者——包括长老派和平等派——也都主张将军队的最终控制权交给立法机关。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在内战前后,这种将军队交给议会的主张从未实现过。内战爆发后,常备军始终控制在克伦威尔与其他军阀手中,议会对军队毫无掌控。1660年复辟后,军队控制权又重回国王手中。1661年《民兵法案》规定,军队控制权属于国王,并强调“议会无权控制军队”。(60)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73页。同时,查理二世以伦敦骚乱为借口,组织起一支听命于国王的长期卫队。(61)See John Miller, Catholic Officer in the Later Stuart Army, 88 The historical Review 35, 45-46 (1973).在复辟时期,国王不经议会即可征募军队,不仅是客观事实,也得到制定法的确认。即便是常备军的批评者也承认,只要国王能够承担军费,国王就有权在和平时期征募军队。(62)See Lois G.Schwoerer, "No Standing Armies!" The Antiarmy Ideology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02.
舆论的转变开始于1678年。由于天主教阴谋的恐慌,人们对常备军的恐惧也急剧增长。议会反对派开始主张由议会来任命军队的官员。还有议员提出,国王唯一能够合法征募军队的理由,只能是战争的威胁;在和平时期,国王则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募军队。用威廉姆斯(Williams)的话来说,“国王征募军队,只能是为了对外战争的原因”。(63)Honble Anchitell Grey ed., Debate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from 1667-1694, Vol.6, T.Beckett and P.A.De Hondt, 1769, pp.42-44.此后,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接连任命大量天主教徒为军官,更激起议会的强烈反对。因此,至1688年革命前夕,英国议会已经普遍形成共识,应当对国王的常备军予以限制。(64)参见同前注〔62〕,Lois G.Schwoerer书,第146-147页。
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法案》的常备军条款,恰恰意味着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征募军队的权利从国王手中转移到议会。这一条款绝非对古老权利与自由的重申,而是对全新原则的宣告——自古以来属于国王的特权,被正式赋予作为新的主权者的议会。
(三)议会的言论自由与召集
对议会权利的保护,也是《权利法案》的重要内容。比如,《法案》第9条规定:“议会中之言论自由、辩论及其议程,不受议会之外任何法庭或者场合之指摘与质询”;第13条规定:“为纠正一切诉冤,也为修正、加强和维护法律,议会应当经常召集”。依据传统的观点,这些言论自由和频繁召集的权利也往往被视作“古老的权利与自由”。
但事实亦并非如此。从表面上看,在17世纪的斗争中,反对派议员经常主张“古老”的言论自由不受侵犯。(65)参见刘淑青:《英国革命前的政治文化——17世纪初英国议会斗争的别样解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75-176页。但事实上,在中世纪,议员从来不享有言论自由权,并可能因为言论侵犯国王特权而遭到指控。比如,1397年,汉克西(T.Haxey)就曾因在议会中批评理查二世而被上议院判处死刑。(66)参见同前注〔35〕,阎照祥书,第89页。直到近代,议会的言论自由权才开始受到法律保护。1512年,亨利八世时期的议员斯特罗德因提议限制采矿特权而被指控,此举遭到议会反抗,并且议会通过制定法禁止针对议员言论的指控。这也是第一部保护议员言论权的法案。(67)参见[英]F.W.梅特兰:《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5页。
但即便如此,在这一时期,议员的言论自由仍并未得到普遍认同,亦未得到真正的保护。在伊丽莎白时代,议员因冒犯国王而被惩罚的情况仍时有发生。(68)See Harold Hulme, The Winning of Freedom of Speech by the House of Commons, 61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25, 825-826 (1956).在詹姆斯一世时期,艾略特等议员也因批评国王征收吨税和磅税而被捕,王座法院裁决艾略特的言论构成煽动性言论,应被处以监禁。(69)See John Reeve, The Arguments in King' s Bench in 1629 concerning the Imprisonment of John Selde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25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264, 264-287 (1986).直到1660年斯图亚特复辟后,议会言论自由权才真正得到重视,并被写入1661年《叛逆罪法案》,艾略特案的判决亦得以纠正。(70)参见同前注〔47〕,J.P.Kenyon编书,第32页。光荣革命后,议员言论自由被作为一项重要权利被正式写入《权利法案》。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法案》或许构成一种对传统的恢复,只不过这一传统并不“古老”,而是来自于近代英国宪制的“新传统”。
除言论自由外,《权利法案》中所谓“议会应经常召集”同样并非“古老”。从历史上看,议会的召集与解散,从来都是国王的特权。在中世纪,议会的召集并无明确规定,何时召集完全取决于国王。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希望国王能够“经常召集”议会的呼声,并在制定法中有所体现。比如,爱德华二世时的议会曾通过《1311年法令》,规定“国王每年应召开两届议会”。(71)参见同前注〔67〕,F.W.梅特兰书,第116页。但这一法令在爱德华二世摆脱贵族束缚后很快被废除。在15世纪后,议会平均每三年才召开一次;尤其是在都铎时期,议会召开的频率更低,平均间隔在四年以上。(72)参见同前注〔36〕,刘新成书,第100页。
进入17世纪后,由于国王与议会的冲突,议会召开的频率更低,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都曾长期不召集议会。1640年长期国会后,曾制定《三年法案》,规定至少三年召开一届议会。但由于法案未限制议会的存续时间,长期国会存在了13年之久。1660年复辟后,《三年法案》因侵犯了国王的特权而被废除。(73)关于17世纪有关议会召开频率的讨论,参见同前注〔67〕,F.W.梅特兰书,第189-191页。复辟后召集的骑士议会也长期存在,一直延续到1679年。此后,詹姆斯二世继位后,更是彻底抛开议会,除第一年短暂召集外,再未召集新的议会。可见,直到1688年之前,议会的召集实际上都取决于国王的喜好,并被普遍视作国王的特权。
总之,以上历史回顾表明,无论是言论自由,还是议会召集,都并非议会的古老权利。直到近代以后,议员言论自由才开始受到保护,并时常处于威胁之中;议会的召集,更是直至1688年革命之前,都被普遍视作国王的特权。只有从《权利法案》开始,言论自由和议会召集才被真正确立为议会的权利,并在实践中开始得到切实的保护与执行。(74)1694年议会制定新的《三年法案》,明确规定了议会的定期召集和存续时间,英国历史上的“无议会”和“长期议会”等现象一去不复返。参见同前注〔35〕,阎照祥书,第202页。
五、新与旧的背后——重新思考宪制转型的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不难得出初步结论——《法案》中所列举的权利,并非都是“古老”的;相反,在13个条文中,至少一半以上都包含了“新权利”。同时,也正是这些新权利(包括法律中止与赦免、征募常备军、议会言论自由等)构成了议会主权新宪制得以确立的基础。同时,即便在所谓“旧权利”中,也存在诸多观念与制度的更新(有如之前对“征税权”和“武器持有权”的分析)。因此,回到本文最初的问题,答案是肯定的——《权利法案》并非古老宪法的“复辟”,而是“新权利”的创制。
但问题是,《权利法案》为什么会被披上“复古”的外衣,被视作对古老权利的重申?更进一步追问,这种“复古”的说辞,为什么会为西方学界普遍接受,甚至对中国学界的认知产生广泛影响?在表面的“辉格”解释之下,还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历史变迁与视角转换?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我将更深入地考察这些“话语”得以生成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本文的分析将表明,《权利法案》的制定,本质上依然从属于新兴的有产者阶层谋求财产安全与自由的政治行动,从属于现代主权国家诞生的宏大历史进程。
(一)古代宪法的“包装”
有如前述,《权利法案》的“古老外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在17世纪英国盛行的“古代宪法”思想。依据波考克(J.G.A.Pocock)的概括,在17世纪,柯克首先最典型地展现了“普通法心智”的历史观,并成为这个时代“弥漫于全体智识阶层”的观念。(75)参见[英]J.G.A.波考克:《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英国17世纪历史思想研究》,翟小波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1页。在这一观念中,英国人的古老自由与权利都来自于不可追忆的时代,并一直留存至今。因此,在英国的历史上,无论是1215年的《大宪章》、1628年的《权利请愿法》,还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都并非对于新权利的创造,而是对于遭到侵犯的古老权利的重申。
在波考克看来,“古代宪法”主要来自普通法法律人的意识形态。正是在律师会馆中,诞生了以“技艺理性”为核心的“普通法心智”,以及对于古代习俗的尊崇。因此,这一时代的法律人,普遍用“古老习惯”的眼光来理解英国法,将《大宪章》视作对传统自由的重申。同时,“古代宪法”的思想还强调议会的古老,主张议会来自“不可追忆”的时代,在国王之前就已存在。因此,议会的自由与特权也绝不来自于国王的授予。(76)参见同上注,第117页。
在一些学者看来,《权利法案》的“古代宪法”色彩,正来自于制定者中的辉格派与法律人背景。起草《权利法案》的两个委员会共43人,其中辉格派29人,占据明显优势。(77)第一委员会中,辉格与托利是28∶12;而在第二委员会中,这个比例更高达16∶6。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32页。两个委员会主席泰比(G.Treby)和萨默斯(J.Somers)也都来自激进辉格派的阵营。(78)See Michael Landon, The Triumph of the Lawyers: Their Role in English Politics 1678-1689,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0, pp.53-54.同时,普通法法律人也在委员会中占据重要位置。在第一委员会(39人)和第二委员会(21人)中,法律人分别达到19和13人。(79)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35页。其中,多数人曾担任过重要法律职务。比如,芬奇(Finch)曾任总检察长;威廉姆斯(Williams)和索耶(Sawyer)曾任副总检察长;泰比、萨默斯、霍尔特(Holt)等都曾任伦敦等自治市的法官。(80)参见同前注〔78〕,Michael Landon书,第47-59页。在起草过程中,法律人也经常援引布拉克顿、福特斯库、柯克等法律人的论述,将这些正在讨论中的权利诉诸“不可追忆”的历史。(81)参见同前注〔4〕,Lois G.Schwoerer书,第37页。总之,从制定者的构成来看,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正是由于辉格党与法律人的关键作用,《权利法案》被打上了“古代宪法”的深刻烙印。
(二)在“古老神圣服饰”之下
但问题并没有结束。有如前述,更细致的分析表明,《权利法案》中的权利多数并非古老的,而是在革命之后才确立起来的新权利。因此,应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辉格党人和法律人为什么要借用“古老权利”的话语来包装这些“新权利”?仅仅是因为法律人的出身或天然的意识形态,他们就必然选择以所谓“古老权利”来建构《权利法案》的理论基础么?或者说,只要是法律人主导制定的《法案》,就天然被赋予“古代宪法”的属性么?
本文怀疑这种解释。事实上,已有研究指出,“古代宪法”在17世纪宪制话语中的地位是复杂的——它既非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也并非法律人唯一的智识资源。(82)See J.P.Sommerville, Royalists and Patriots: 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England, 1603—1640, 2th Edition, Routledge, 1999, pp.63-65. 对于“古代宪法”话语优势地位及其生成背景的反思,参见于明:《“不可追忆时代”的用途与滥用——英国“古代宪法”理论的再检讨》,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5期,第88-101页。法律人也并不总是守旧的;相反,在这一时期,对于法典编纂的热衷,同样是培根、黑尔等许多法律人的共同观念。法律人同样相信,法律是可以被创新的,可以通过制定法来创造新法来回应新环境。(83)See Barbara Shapiro, Codification of the Law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1974 Wisconsin Law Review 428, 428-465 (1974).因此,仅仅是法律人的主导地位,并非《权利法案》诉诸“古代宪法”的全部理由,更非根本的原因。
那么,《法案》诉诸古代话语伪装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要回到16—17世纪以来的经济基础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结构的改变。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17世纪英国革命的发生,就经济基础而言,根本原因仍来自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的有产者阶层的兴起。(84)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1892年英文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1-762页。随着土地所有权逐渐从贵族转移到乡绅,(85)参见[英]J.G.A.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4页。乡绅成为这一时期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和“新生豪富力量”。(86)[加]C.B.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从霍布斯到洛克》,张传玺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乡绅还普遍担任地方的治安法官,大举“入侵”下议院,成为了下议院中占绝对优势的群体。
因此,英国的内战与革命,根源于新兴有产者阶层的夺权行动。正如休谟最早指出的,正是在从封建社会向贸易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英王政府赖以生存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征税体制日渐衰弱,英王不得不更多依赖于国王特权,大肆征收无须议会批准的特权税,从而与捍卫乡绅财产权的下议院之间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并最终导致了英国革命的发生。(87)See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Vol.5, Liberty Fund, 1983, pp.134-136.也正因为这一革命的目标本身旨在维护有产者的财产安全,因此也必然是“有限”的革命。事实上,光荣革命后的辉格党人也并未接受洛克的人民主权理论,而是将英国的主权置于乡绅们牢牢掌控的议会之中,(88)See Edmund S.Morgan, Inventing the People: The Rise of Popular Sovereignty in England and America, W.W.Norton & Company, 1989, pp.119-121.以最大程度建立稳定的秩序,以建立能够更好满足有产者安全的世界。(89)See H.T.Dickinson, Liberty and Property: Political Ideology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Methuen, 1979, p.83.而在辉格派看来,较之一个不受约束的国王,一个由有产者自己构成的议会显然更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围绕《权利法案》的“复古”话语。之所以将《权利法案》中的“新权利”伪装成“古老的权利和自由”,根本的原因还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掩盖革命的本质,以维护革命时代的政治稳定与秩序。正是这种被人为“制造”的历史连续性,掩盖了革命的断裂,才可能避免更激进的社会革命的发生。用梅特兰的话来说,“主导这场革命的人力图使这场革命看起来尽可能波澜不惊,使之看起来像是进行了一道法律程序”。(90)同前注〔67〕,F.W.梅特兰书,第183页。而在有产者的革命世界观中,英国革命也自然构成了所谓成功革命的典范——它们既完成了政治秩序的重建,又避免了类似法国大革命的剧烈暴力与动荡。(91)参见李猛:《革命政治——洛克的政治哲学与现代自然法的危机》,载吴飞主编:《洛克与自由社会》,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19页。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理解了《权利法案》的辉格解释长盛不衰的原因。如果说这种诉诸“古代宪法”的话语,在制定时期是为了减小阻力和避免更激进的革命,那么在《法案》颁布后,这一话语的延续和不断被重述,无疑来自于有产者阶层对既有统治秩序的维护。通过诉诸“不可追忆的时代”,英国统治者不断以历史传统来掩饰持续进行中的变革,以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避免英国内战或法国大革命式的政治动荡的发生。英国宪法史也由此呈现出“阿尔戈之船”式的变革,在“古老的神圣服装”之下“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92)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载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9页,译文略有调整。
(三)被掩盖的真实革命
本文之所以关注这层话语的伪装,并不只是为了“去伪”,同时也为了“求真”。就《权利法案》而言,这种诉诸古老宪法的传统解释,可能误导现代的研究者,使其忽视《法案》本身的革命性意义。因此,在接下来的部分,我将回到英国革命的深层逻辑之中,重新讨论《权利法案》的革命性本质。更深入的分析将表明,《权利法案》不仅界定了诸多在英国历史上从不存在的新权利,并且借助全新的话语完成了议会主权的理论证成。
有如前述,《权利法案》对英国宪制的革命性改造,集中表现为对国王特权(Prerogative)的重塑。在《权利法案》的权利条款中,最重要的内容即是对国王特权——法律中止与赦免、税收、征召军队、召集议会——的系统性限制。这些国王特权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治理中应对战争与危机等紧急情况的需要。(93)布莱克斯通强调,授予国王特权是为了使国家更强大、更高效。当出现紧急情况时,经不起拖延和耽搁。参见[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一卷),游云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7页。从中世纪以来,国王就拥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一是“依法律的统治”(jurisdiction),一是“个人决断的统治”(government)。所谓“依法律的统治”即国王的权力在法律范围内行动;而所谓“个人决断的统治”,则是国王不受法律约束、依据个人意志决策的权力,即国王的“特权”。(94)参见[美]C.H.麦基文:《宪政古今》,翟小波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关于中世纪国王的两种权力,参见陈思贤:《西洋政治思想史:近代英国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8页。或者说,国王权力中包含“日常”与“绝对”的“双重权力”。(95)See Joseph Robson Tanner, Constitutional Documents of the Reign of James I, 1603—162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pp.340-342.
回到《权利法案》,其中涉及的国王特权,也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例外”的应对有关。比如,国王有权中止法律,或赦免法律的适用,就是为了应对超常规的例外状况的发生。又如,在中世纪的国王财政中,常规税收非常有限,一旦面对战争危机,就不得不依靠补助金、吨税与磅税等国王特权税。同样,历史上的英国也不存在常备军,军队的召集都来自国王应对战争的临时举措。总之,《权利法案》关注的焦点,即在于如何系统性地限制国王的特权——这些特权在传统宪制中被赋予国王,但在《权利法案》中开始被转移到议会的控制之下。
从历史上看,这种国王特权,的确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以至于引发激烈的宪法冲突。但在总体上,由于传统社会的相对稳定,以及基本政治共识的存在,这种“超越法律”的特权,只构成对常规权力的补充,其风险亦在有限范围内。(96)参见同前注〔94〕,陈思贤书,第7-8页。同时,贵族力量的强大,也使得“之前的君主只能间歇地使用这些特权”。(97)David Hume, Essays: Moral, Political and Literary, Liberty Fund, 1987, p.209.然而,进入现代社会后,传统的国王特权却遭遇重大挑战。较之传统社会,16世纪以来的现代社会被视作一个“普遍危机”的时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阶层与新观念不断涌现,也导致不同阶层、观念与信仰之间的持续冲突。因此,在17世纪英国,原本应对“例外”状态的国王特权,也随着危机的持续频发,不断成为统治权的日常形态。无论是税收、征兵,还是法律废止,都已无法继续依靠“间歇”的特权,而不得不转向一种更具权威也更能系统应对危机的常规性权力。
这种具备强大变革能力的最高权威,正是现代主权的诞生。有如亨廷顿指出的,现代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变动社会;而主权的本质,正是为了应对变动社会挑战而产生的超越法律之上的权力。(98)参见[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4页。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法案》对于税收、军事、立法等权力的重塑,同样服务于在变动社会中寻求稳定秩序的总目标。议会主权的诞生,首先意味着主权的诞生,是一种全新的“至上权力”对于“根本法至上”的传统宪制的取代。(99)关于这一宪制转型的讨论,参见同前注〔9〕,于明文,第891-910页。有如前述,在传统宪制中,国王权力主要表现为“依法律统治”的日常权力;只有在“例外”状态下,国王才行使“依个人决断”的特权。但议会主权的诞生,却意味着这种传统二元权力结构被打破;传统旨在应对危机的国王特权,逐渐为常规性的、具备持续变革能力的现代主权所取代。(100)See Charles Howard Mcllwain, The High Court of Parliament and Its Supremacy: An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Boundaries Between Legislation and Adjudication in Engla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0, pp.93-96.
同时,这种新宪制的革命性,还体现在主权的归属上。与欧陆流行的君主主权不同,《权利法案》在创设新主权的同时,将其置于议会,而非国王。在17世纪的英国,君主主权也曾作为可能的方案出现过,并一度成为重要的宪制话语。(101)See John Neville Figg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Hardpress Publishing, 1922, p.237.但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新时代,在新兴“市场社会”中形成的新中产阶级,较之传统的土地贵族,更依赖议会来保护自身的财产和自由。(102)参见魏佳:《贸易与政治——解读大卫·休谟的〈英国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1页。正如麦克弗森指出的,这些新兴有产阶级具有强大的阶级凝聚力,其共同利益意识足以支持一个稳定的主权政府,同时保留选举主权机构的权利。而较之世袭的君主,一个能够被“周期性选择”的议会,显然更有利于有产阶级控制主权政府,也更有利于维护其财产安全与自由。(103)参见同前注〔86〕,C.B.麦克弗森书,第95-96页;另参见同前注〔89〕,H.T.Dickison书,第43页。
综上,本文的分析表明,1689年《权利法案》的制定,绝非“古代权利与自由”的重申;相反,这是一场具有“双重革命”意义的制宪行动。一方面,《权利法案》对议会权力的塑造,宣告了主权政治这一现代宪制的诞生,也宣告了以根本法至上为特征的古代宪制的终结。另一方面,《权利法案》也重新塑造了国王特权与议会权力的边界,在限制国王传统的“非常权力”的同时,第一次明确将主权权力置于较之君主更可靠、也更具稳定性的议会之上,从而开创了议会主权的新宪制。在这个意义上,《权利法案》构成了对“古代宪法”与“君权神授”两种宪制传统的“双重否定”,是一部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新作品。不同于作为封建协议的《大宪章》,《权利法案》首次构建了足以应对总体危机的主体性权力,并将“议会视作统一政治题的代表”,从而完成了对“政治统一体的存在类型的总体决断”。(104)[德]卡尔·施米特:《宪法学说》,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8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689年的《权利法案》才有理由被视作英国“现代宪法”的开端,乃至世界宪法史上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