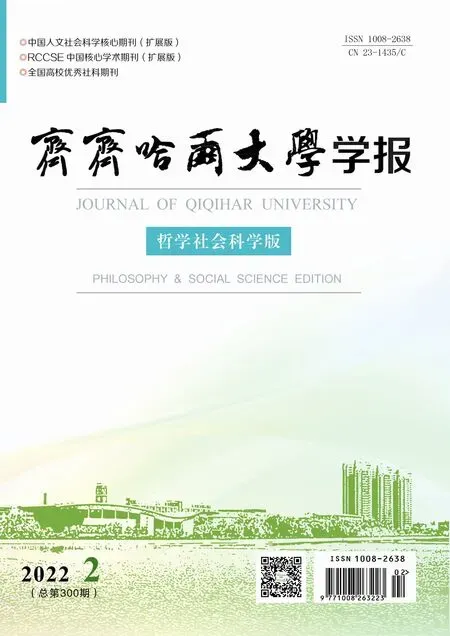《山海情》:扶贫剧“中国梦”叙事及其审美意蕴
许心宏,李智敏
(1.安徽财经大学 艺术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2.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山海情》(2020)是“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剧展播”剧作。剧情以“东西协作”扶贫为背景,以涌泉村的吊庄移民为线索,讲述了西海固“闽宁村”在国家政策帮扶下筑梦家园的故事。作为“中国梦”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剧集的故事起点是因贫思变,过程是家园创建,目标是冀以小康。在文艺“二为”方向上,扶贫攻坚“脱贫梦”汇入“中国梦”,“中国梦”引领“小康梦”。基于扶贫攻坚“点-线-面”叙事,点为西海固地区的贫瘠村落,线是东西协作,面是减贫脱贫的中国实践。选好点,连成线,织成面,这是扶贫剧立足中国大地的生命点、情感线与意义面。
一、梦想诗学的精神成长史叙事
文化原型的母题叙事上,“母题”、“原型”都是“梦想诗学”叙事的直接推动力。《山海情》中的“迁徙”、“逐梦”、“家园”、“探索”、“报效”等“母题”作为“母式动作”,建构的是扶贫剧“向梦而生”与“逐梦而行”的故事情节与场景画面。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剧集建构与传递的是扶贫攻坚梦想花开的精神生成史叙事的中国诗篇。
1.少年逐梦的主题引入
剧情开篇,马德宝带领山里娃娃向外跑既是触发事件也是激励事件。作为触发事件的逃离之因,如其言“早上煮洋芋,中午蒸洋芋,晚上烤洋芋,我已经吃够洋芋了”,由其引出的是少年逐梦山外世界的生存梦想。作为激励事件,少年“出山记”梦想虽然夭折,但因之引出了易地搬迁的故事线索,架构了逐梦未来的故事脊椎。从弟弟“出山记”到哥哥“吊庄移民记”,作为贯穿剧情始终的功能性人物角色,马得福亲历与见证了易地搬迁的整个过程。在逐梦主题的空间切入上,故事发生于我国“胡焕庸线”以西的西海固大山深处的涌泉村。基于印象式人文地理感知,“胡焕庸线”既是我国的一条地理和人口分界线,也是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分隔线。长期以来,西海固地区因干旱缺水而“苦瘠甲天下”。在深度贫困的故事讲述上,“村里女子为一头驴就能嫁人”、“兄弟仨只有一条裤子”、“珍珠鸡吃得只剩下最后一只”便是遥远画面的情景再现。在“说”与“听”叙事交流上,叙事本是“某人在某个场合处于某种目的对某人讲一个故事。”[1]作为现代“说书人”,大众传媒的电视不仅是讲故事,而且是召唤某一行动的实践。如此,剧集通过问题代入,驱动了故事情节发展,建构了逐梦主题生成,搭建了脱贫奔小康的叙事交流机制。
2.逐梦家园的精神自觉
“所有故事都表现为一个求索的形式”,[2]《山海情》亦不例外,这正如片头的花儿所唱“干沙滩上花不开,想喊云彩落下来,喊了一年又一年,喊了一年又一年”。花儿的吟唱不过是梦想求索的变体表达,隐喻的是扶贫攻坚的甘霖普降。从穷则思变的内生动力到扶贫攻坚的外力牵引,在国家吊庄移民政策号召下,剧集据实再现了易地搬迁的全景过程。从故土别离到逐梦新家,部分吊庄移民户逃回了故地,因为当时的金沙滩只是概念化的梦想空间。在向外走与原地守拉锯战中,涌泉村老支书说“再穷,也不能把骨头穷没了。有奔头那就不算苦,没有奔头那才叫真的苦”。耆老寥寥数语,呼应了少年的外出梦想,点开了故事主题,点醒了待时而动的寻梦者,点出了逐梦的行进方向。两点一线寻梦之旅,一端连着迁出地涌泉村,一端连着迁入地金滩村。聚焦移民路上的风沙肆虐场景,吊庄户抱成一团抵御沙尘暴侵袭。天大人小的远景与全景画面,凸显了逐梦之旅的主体意识自觉与精神崇高。基于女性视角“一片戈壁、一条土路、一辆驾车、一家人”全景特写,水花拉着驾车,拖着男人带着娃,拉着全部家当,七天七夜方才抵达金沙滩。相距七天七夜的路途之远反衬了逐梦之艰,但逐梦之志坚如磐石。从干沙滩到塞上江南,在筑梦新家的黑白画面闪回中,当年吊庄移民户冒着漫天风沙一寸一寸筛出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命根。戈壁滩上开荒、整地、种地“开荒记”的远景与近特两极镜头的交叉剪辑,间隔了过去与当下的时距,建构了筑梦新家的沉浸式故事语境。基于“土地-家园-梦想”原型叙事,涌泉村人寻梦之旅再现了西海固人脱贫攻坚生存史、梦想史与奋斗史生根发芽的历史过往。
3.梦想成长的甘甜
吊庄移民至干沙滩,建新居、建学校、建邮局、建医院、建银行是希望;通水、通电、通路、通网、通航是希望;有地种、有活干、有钱赚是希望;孩子的希望,年轻人的希望,老人的希望,无尽的希望奏响了希望之歌。问题是,未来何时来怎么来?据记载,从1991年到2016年,“闽宁镇”战贫之路关关难过,关关都要过。正是在“希望-困境-奋斗-实现”一个个圆圆相切故事讲述中,从概念化的金滩村到现代化的闵宁镇,剧集建构了梦想诗学的生长性与人物角色的成长性。当然,正是在逐梦家园之旅中,剧中人物角色观之可亲近之可爱,使得不同地区、年龄、阶层的观众从中找到一种角色代入感。再就人物角色台词的无意识表白而言,反复出现的“未来”“明天”“日后”等,都不过是逐梦未来的同一表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脱贫梦贯穿着中国人梦想的始终。如此,剧中无论是扶贫干部、科教扶贫工作者,还是吊庄移民户,每个人都有梦,而每个梦又都汇入“中国梦”。穷荒绝漠里生长,风沙烟尘中筑家。放眼于一无所有的干沙滩,在白描式一群人开创家园的奋斗史、成长史叙事中,观众化身为剧中的精神村民与其一同成长。基于共生、共感、共情的情境通约,观众在角色代入的逐梦未来、角色成长中分享了梦想花开的甘甜。
二、逐梦家园的沉浸式叙事策略
《山海情》逐梦家园叙事引发的共情是果,而架构共情的叙事策略是因。基于梦想起始的因果逻辑、故事讲述的生态逻辑与角色演绎的情感逻辑,剧集建构了沉浸式的故事语境。
1.真人真事的原型叙事
《山海情》以真实故事、真实人物为原型,在史料纪录基础上,以“史”述“事”,以“人”叙“史”,通过艺术的构思与想象,建构了艺术真实的叙事逻辑,使得非虚构的影像叙事具有了地方影像志的历史价值与审美价值,成为中国西海固地区移民脱贫故事的影像志。基于“原型”叙事的历史意义而言,“原型故事挖掘出一种普遍性的人生体验,然后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具有文化特性的表现手法对它进行装饰。”[2]4故而,基于空间地理、人物角色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型叙事,“原型故事能创造出世所罕见的场景和人物,令我们目不暇接地去欣赏每一个细节;而其讲述手法又能揭示属于人性真谛的冲突,使之得以从一个文化到另一个文化不胫而走。”[3]从故事发生到故事讲述,三十年的时间间隔,以马得福为兄弟、翠花代表的年轻人的成长与历史发展的同时、同向、同构叙事,《山海情》既是青春题材的怀旧,又是怀旧的青春题材。故而,以“涌泉村”为代表的“村落里的中国”到戈壁滩上的“闽宁镇”,再现的现代化进程的文化怀旧主题叙事。
2.召唤结构的情境代入
基于受众视角的情境代入,以“涌泉村”为基点的空间吐纳中,西海固、沙尘暴、戈壁滩、干旱、缺水等地理画面,建构的是一方村落的地理邮票,定格了“村落-中国”视觉空间记忆。基于微缩化、典型化的村落缺水场景再现,一是故地虽曰“涌泉村”,但苦咸水寓意生存繁衍危机;二是村里人名大多与水有关,内寓深切的盼水情结;三是除了最后一只“扶贫珍珠鸡”与几只羊,村里再无其他动物甚至一只鸟飞过。在村落地方经验讲述中,裸露经络的荒山秃岭,土房、土院、土路的村落,弯曲的盘山土路等,主色调的土黄色虽有几分暖意,但难以掩饰空间诗学的荒凉、落寞与忧郁之意。挣扎于世纪干旱的土地上,极限的环境制约成了逐梦新家的内生动力。故地无出路,新家太荒凉,但剧集并未因之而编设煽情、矫情、苦情桥段,而是在逐梦戈壁滩的空间、角色与情感带入的移境、移情、移志叙事中,剧集建构了“移民记”→“开荒记”→“筑梦记”沉浸式故事语境。据此,共情的蘖芽并非难事,要义在于如何构建情境通约的召唤结构。就是说,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因为笃定梦想的无畏险阻,故而在勇于探索的实践中收获未来。正是在开创家园成长型叙事中,人物角色从“三记”中走出来,演员从中活起来,观众从中沉浸下来。
3.故事讲述的时空生成
电视剧《山海情》拍摄前,纪录片《闽宁镇的故事》(2018)、长篇纪实文学《闽宁镇记事》(2019)与广播剧《闽宁镇》(2019)均以纪实性手法讲述了闽宁镇从戈壁滩成长为现代城镇的故事。[3]故而,“真实指的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如何发生,为何发生。”[4]如此,作为时代报告剧,《山海情》“既美且信”的故事讲述得益于生态化的要素合成。体现在年代感上,从戈壁滩到闽宁镇,剧中“地窝子→土坯房→砖包房→砖房→现代城镇”居住空间形变再现了筑梦新家的时光荏苒。自外而内,室内的贴画、报纸墙、楹联、家具、生活用品等,器物层面与精神层面的物象在场,承载的是故事演进的岁月印痕。由物到人,因为时代、年龄与性别差异,人物角色的衣袜鞋帽的细节处理,凝聚的是贴时、贴地、贴人的生活肌理,物语无声更是流淌出时光怀旧的味道。以脸识人,但因长年风沙吹打,演员脸上或深或浅的“红二团”便是当地百姓日常生活本相的空间证明,“地方脸”因之成了文化地理独特性与人物群体典型性的美学再现。因地而语,作为扎根特定文化土壤的根须,《山海情》原声版中的泥滋味土气息的方言土语,唤起的是耳畔回响的空间记忆,建构了人物角色扎根一方土地的故事立体感与真实感。如此,“天-地-人-物-景-情”要素的生态合成营造了故事讲述的审美意境与文化底蕴。
4.方言土语的听觉唤醒
作品“接地气”体现在人物角色的方言土语之中,“泥滋味、土气息”方言土语与剧情的主题、人物角色“不隔”,凸显了与流行时尚大众文化的相异性,体现了地域文化的原汁原味,彰显了显著的地域特征。《山海情》中,一是地名的称谓,如“苦水村”、“涌泉村”“戈壁滩”等,内寓的大西北对“水”的渴望;二是人名称谓,村里人的名字大多与水有关,如马喊水、李水花、水娃、水旺,水水等,寓意世代对生存之水的渴望;三是当地方言土语的言说,如“胡日贵”“碎怂”“没麻达”“日塌了”等,演员在举手投足之间,建构了地方性记忆,拉近了剧中人物角色与观众的心理距离。有别于书面语、普通话,方言土语的节奏、音调、语气词等,具有地域的扎根感与生活还原的原汁原味感,人物角色具有生活的立体感、真实感、亲近感。故而,正如康·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我们拥有一个主要的、永不枯竭的语言源泉-人民本身:农民、渡船的船夫、猎人、渔夫、老工人、护林巡查员、手工业者以及一切饱经世故的人,他们不开口则已,一开口无不字字如金。”[5]如此,《山海情》人物土、故事土、情感土、方言土,演员土,土得原汁原味,使得故事是从土里长出来,人物从土里走出来,唤醒的是观众的听觉记忆与历史回响。
5.人物角色的本色表演
人物角色演绎上,演员不仅要再现人物角色的外在生活,更是要给人物角色注入灵魂,变“演生活”为“就是生活”。故而,进入角色的表演追求的则是没有表演的表演,呈现与还原的是生活本然或应然的样子。“演员要跟角色感同身受,要融入到角色中。演员的工作不单是展现角色的外在生活。他还必须要把角色的品性演得恰到好处,要给角色注入灵魂。”[6]人物角色演绎“既视感”上,剧中可圈可点之处俯拾皆是。以水花为代表,她坦然面对命运,接受命运,但又不屈服于命运,她微笑着哭,哭着微笑,情境各异中的矜持、微笑、眼神动作应景入心,形塑的是其清澈阳光、积极向上的人物性格,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言“我们觉得是美的人,只是因为他有一双美丽的、富于表情的眼睛。”[7]为发展庭院经济,当马得宝养菇赚得人生第一桶金后,他从身上四处往外掏钱数钱场景,由其脸上荡开的是未来可期的欣喜与欣慰之情。解民之困,凌教授骑着二八式单车忙得灰头土脸,一盆水洗头,头没洗好水已浓稠,“外来者”赤子之情不言而喻。盼水之切,村民李大有一口咬下黏连着沙土味的干枯麦苗,炙热的土地深情再现了乡土中国“农民父亲”质感画面。李大有虽精致自利,但不乏硬汉的寸心柔肠。被他鞋底子打长大的水旺外出打工后,他曾托同村的麦苗给儿子带去家乡味道的“定心蛋”。间接的“父之过”自责场景中,他说话时的语速、眼神、体态语等细节,再现了“怨-恨-爱-念”心理过程转变。“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以情动人”之“情”是演员对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思想情感的触摸、体验与萃取之后的情感演绎。正是因为演员吃透了人物角色内涵,演员才能在无痕有味的本色表演中功力尽显,也才使得饰演的人物角色惟妙惟肖情真动人。
三、文化寻根的审美意蕴
电视剧就是讲故事,而讲故事不仅要以情动人,同时还要情深树人。在生态移民逐梦新家的故事讲述中,《山海情》后三集有三段特别对话场景。一是兄弟对话,揭开了长兄自责与救赎的故事;二是荒山祖坟前的父子对话,引出了村里“百家宴”故事;三是昔日恋人对话,赓续了马李两姓“涌泉相报”故事。根据艺术审美统一性原理,“每一个故事成分之所以出现于故事之中,是因为它们能够与其他每一个成分发生某种联系。”[2]237依据三段对话时序对应的语义层次,家庭层面的“兄弟怡怡”开掘了文化寻根诗学的乡土中国伦理叙事。
1.家庭层面的兄弟情深
穷人的“穷办法”就是“抓阄定命”,其结果,就是哥哥上学弟弟弃学。举全家之力供养马得福上学无非是培养出一个光宗耀祖的“公家人”。因为利己损弟,马得福埋怨父亲心太硬,但其父不以为然。他说穷人家只有把钱花在一个人身上,有出息的那个人才能带领全家人都好。相反,钱平均着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还是一窝穷。如此,穷人家只有集中力量才能办成一件事。因而,兄弟俩抓阄定命之后的人生轨迹看似各异,但实为互为表里的异体同构。出于愧疚的补偿心理,哥哥帮助弟弟的建筑公司中标,后经调查并无徇私舞弊的贪腐行为。如此,看似偏离主控思想的剧情延宕,内中却大有深意:一是情与法之间凸显了血浓于水的兄弟情;二是引出了家国天下的从政伦理道德问题。体现在“为政以德”仪式感上,身为镇长的马得福坐小汽车回村必须村口下车,这是其父为他立下的规矩。如果说“世界的各个角落,生活都包裹在仪式之中”,[2]188那么“村口下车”则是中国古代“下马石”异形同构的现代转换。如此,“学而优者仕”并非为了小家的光宗耀祖,虽然当初的出发点带有这种真切的成分,相反只有对得起父老乡亲才算是真正的光宗耀祖。故而,“村口下车”仪式感,使得故事主题从小家的光宗耀祖过渡到社会层面的为官为公。
2.社会层面的乡土伦理
剧情开篇,村口土墙上写着“涌泉村”,但为何叫“涌泉村”却未做背景说明,当然也无须说明,因为那不过是村落的标识而已。待至结尾,通过黄山祖坟前的父子对话,马喊水口述了“涌泉村”李马二姓兄弟情深的往事。二百年前,马家先人逃难至涌泉村,因为李家先人收留而有了落脚之地,他们帮着马家先人挖窑、开荒、种庄稼,马姓因之开枝散叶。再就是夏收以后村里都要举办“百家宴”,马家先人自认是外人而不敢赴席,但李家人还是拽着马家先人吃了“百家宴”。自那以后,马家先人立下逢年过节要跪拜两个祖宗的规矩:一是骨血亲宗的马家,一是恩重如山的李家。从施恩在先到报恩于后,正如水花所言“当初,我们李家先人把你们李家先人收留到这儿,现在你们马家后人带着我们李家去更好的地方,这也算是报答了!”慎终追远,方可民德归厚。故而,整村易地搬迁当天,一是村里赓续了“百家宴”传统。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百家宴”唤起的是国人对儒家仁义文化传统的心理认同;二是村里年轻人将村口土墙上褪色的“涌泉村”深描了一遍,寓意“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世代相传。故此,开场的“涌泉村”是熟悉的陌生,结尾的“涌泉村”则是陌生的熟悉。在“村落-中国”缩影中,兄友弟恭的李马两姓实为同根异枝的兄弟,两者相扶相依再现了乡土中国最深厚持久的同患难共命运的社会伦理主题。
3.国家层面“东西协作”
《山海情》原名为《闽宁镇》。“闽宁镇”指扶贫攻坚的一个点,“山海情”指向国家扶贫攻坚的社会面。从“闽宁镇”到“山海情”,点是面的缩影,面是点的升华。就“山海情”空间跨度与精神高度而言,“山”指宁夏,“海”指福建,“情”指相距2000公里历时20余年对口帮扶之情。然而,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进程中,因为我国人多地少,基础差底子薄,地区发展不均,东西差距较大,这意味着共同富裕并不是同时富裕、同步富裕、同等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然后通过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如此,剧集在自点而面、自小家而大家的阶梯性伦理生成上,从兄弟抓阄定命的无怨无悔到李马两姓的涌泉相报,使得故事主题演绎为“家庭-社会-国家”阶梯上升的相顾、相扶、相依的乡土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图景叙事。在多层次、多形式、宽领域、全方位“东西协作”对口帮扶下,东部沿海发达省份对口帮扶西部落后地区发展,再现的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先富带动后富的生动历史画卷,正如结尾字幕所示“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24年来,闽宁镇的发展成就了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援的典范,也体现了中国式脱贫致富的成果。”故而,“东西协作”寓意兄弟省份携手共赴“中国梦”的世纪梦想与伟大实践。除此,减贫脱贫的中国奇迹更是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的强大生命力,同时召唤了不同圈层不忘初心砥砺奋进“中国梦”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总之,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全国832个贫困县“摘帽”,1亿左右人口“脱贫”。作为“中国贫困之冠”地区,《山海情》播出档期具有时间节点的象征意义。一是经过30多年河山再造,西海固地区现已山川凝翠,“绿水青山”正在变成“金山银山”;二是在决胜脱贫攻坚战中,乡土中国的“仁爱互助”“和衷共济”“家国天下”优秀文化传统历久弥新;三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那么在处理疾病、灾荒、贫困、生态治理等全球性问题时,“中国策”“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则愈来愈有吸引力。故此,在平民视角、国家叙事、国际表达中,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以《山海情》为代表的扶贫剧正当其时,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闽宁对口扶贫协作援宁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