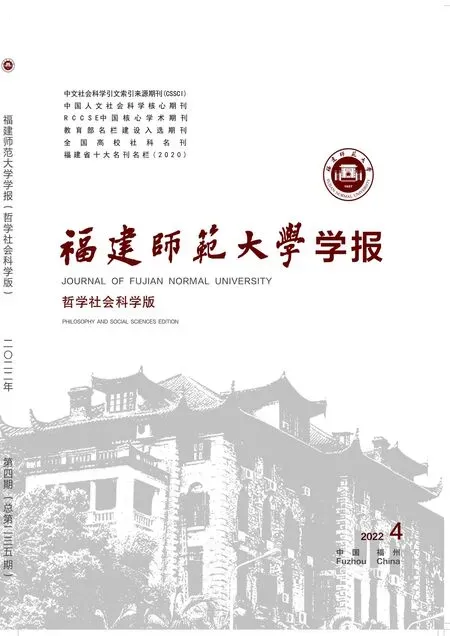艺术意义中的三维配置:符形、符义、符用
赵毅衡,罗贝贝
(四川大学 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四川 成都 610207)
一、符号学三分维
“意义”可能是全世界语言中最难说清其意义的术语。语言学家莱纳德·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sfield)曾经提出,意义问题不是语言学能处理的,应当排除在语言学之外。(1)Leonard Bloomsfield,Language,New York:Allen & Urwin,1933,p.7.C.K.奥格登(C.K.Ogden)与I.A.瑞恰慈(I.A.Richards)早在1923年的《意义的意义》(TheMeaningofMeaning)一书中梳理出意义的十六种“都可以成立”的定义,并提出“符号研究科学”(science of symbolism)……这启发了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W.Morris)从不同方面考察符号意义,使其“廓清了一般符号理论轮廓”。(2)Charles W.Morris,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Mouton & Co.N.V.,Publishers,1971,p.7.此后,这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而是越讨论越复杂,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感慨:“在整个语言中,你要找出意义这个词的意义,恐怕是最难的了。”(3)Claude Levi-Strauss,Myth and Meaning,Toronto:Toronto University Press,1988,p.2.可惜不讨论意义问题的语言学尚未发明,而符号学就是意义学,不讨论意义,符号学就是在自我取消。
仔细考究一下,不仅每一种文本体裁的表意过程侧重点不同,实际上每一次单独的表意过程中,主导位置也不同。符号意义的表达与接受过程极为复杂,从符号文本的发出、传播到解释,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意义的变异。这就迫使符号学的研究不得不有所侧重,对符号学研究本身进行分维,才不至于把很多问题做笼而统之的回复,讨论越说越乱。
莫里斯出版于1938年的专著《符号理论基础》(FoundationsoftheTheoryofSigns),对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符号学体系的进一步展开贡献极大,此书在介绍皮尔斯符号学原理的同时,把符号意义过程的研究做了三分维。当时符号学远未成为显学,莫里斯的努力,为符号学发展成为一个学科作出了重要贡献。莫里斯认为人类活动涉及三个基本方面,即符号(Signs)、使用者(Users)、世界(World)。这三者的组合,出现了三门学科:R(S,S) = 符形学(syntactics)、R(S,W) = 符义学(semantics)、R(S,U) = 符用学(pragmatics)。莫里斯此处对意义研究全域的三门分维说得非常清楚:所有人的意义活动,都与符号有关,只是关联方式不同。符号之间的搭配(S,S)组成具有合一意义的文本;符号文本与世界的关联(S,W)即是符号文本的指称意义;符号被接收者在某种场合的使用与解释(S,U),构成了符号的使用意义。这三者的关系划分分明、简洁而通透,但真正讨论起来却很为纠缠,不易分清。
这三个分维名称,原是语言学术语,莫里斯借来命名符号学三领域,西文原术语至少没有“语”字,用于符号学,解释并无太多难处。中国符号学界却沿用语言学翻译法,分别称为“句法学”(或“语形学”syntactics)、“语义学”(semantics)、“语用学”(pragmatics)。译名点明是在讨论语言,而用于符号学经常说不通。杨成凯指出,“(20世纪)60年代我国学者周礼全先生在翻译(莫里斯)此书时把它们分别译为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4)杨成凯:《句法、语义、语用三平面说的方法论分析》,《语文研究》1993年1期,第39页。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一书中译云,“符号学的发展分成三个科目,第一,‘句法学(syntactics)’:研究‘符号’与‘符号’的结合;第二,‘语用学(pragmatics)’:研究‘符号’与指示物的关系;第三,‘语义学(semantics)’:研究‘符号’与使用者的关系。”(5)[日]池上嘉彦:《符号学入门》,张晓云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第30页。可见这些术语译法沿自日语。
莫里斯解释说:“符形学问题(syntactical problems)包括感知符号、艺术符号、符号的实际使用,以及一般语言学。”(6)Charles W.Morris,Foundations of the Theory of Signs,Chicago:Univ. of Chicago Press,1938,p.16.以上引文把syntactics翻译成“句法学”,与莫里斯描述的问题范围相差很远。不同符号文本的组成方式千差万别,一幅图画,一曲音乐,一首诗,它们之间没有如语言的“词法-句法”那样清晰的形态学共同规律,它们的文本构成中,符号元素的配合有独特规律可循,符形学研究比语言的“句法”研究,或许困难得多。因此笔者不用语言学的学科名,以避免误会。
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科,充分汲取了当时学界讨论意义问题的各种研究成果,囊括的视域更广,分析的内容更具体,表述更加清晰。自其提出以后,符号学及其学科分野被确定下来,并一直沿用至今;符号学也逐步从哲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剥离出来,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皮尔斯是符号学的奠基人,莫里斯是符号学科的体系化者。自此之后,要谈论符号意义问题,就不可能绕过莫里斯对意义过程三维度与符号学三分科的划分。
二、符形学的再理解
符号不可能单独表意,我们觉得某个符号在单独表意,仔细一看,意义的出发点必然是一个符号组合而成的文本。符形学讨论的是文本的构成方式,文本化是表意的必定方式。同一批符号元素,组成的文本不同:一个交通警察、一个抢银行的强盗、一个看风景的行人,在同一个街景中看出不同的文本,因为他们找到不同的意义。符号起源于对现象的片面零散的感知,绝不可能,也不必要,对物整体的掌握。因此文本化就是这些片面感知的集合:接收者不仅在符号的可感知方面进行挑拣,而且把挑拣出来的感知组成一个有“合一的意义”的文本。一个足球运动员,“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看到己方与对方每个队员的相互位置与球的方向速度,迅速判断这个“文本”的意义以决定自己的跑位。体育界行话称此人善于“读”比赛,此语很符合符号学。显然,一个后卫与一个前锋,必须读出很不同的“文本”。
奥格登与瑞恰慈早就发现符号文本的这个基本特性,他们称符号文本意义的“单一性”(Canon of Singularity)为“单一原则”,认为这是“符号科学第一准则”。但事实上我们经常看到多意的符号文本,难道不是瑞恰慈指导他的弟子燕卜荪(William Empson)写出了著名的《复义七型》(SevenTypesofAmbiguity)?奥格登与瑞恰慈认为,“当一个符号看来在替代两个指称物,我们必须把它们视为可以区分开的两个符号”(7)② C.K.Ogden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New York:Harcourt,Grace & World,1946,p.91、88.。也就是看成两个同形的符号。例如词典上的多义词,给我们指向不同指称:没有“多义的符号”这回事,只有分享同一形式的多个符号。一些符号组合成一个文本,经常似乎“多义”,原因是这个文本落在“一组外在的、或心理的语境之中”(8)② C.K.Ogden ,I.A.Richards,The Meaning of Meaning: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New York:Harcourt,Grace & World,1946,p.91、88.。可以作此解,亦可作彼解,就是同形的两个不同文本。如果一个符号双意并存,不好拆散,这二者就可以而且必须联合解读,以形成一个复合意义。(9)参见赵毅衡:《双义合解的四种方式:取舍,协同,反讽,漩涡》,见赵毅衡:《哲学符号学:意义世界的形成》,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06-207页。
钱锺书《管锥编》对文本合一问题理解得深刻,书中认为老子“数舆乃无舆”之说“即庄之‘指马不得马’”,或《那先比丘经》“不合聚是诸材木不为车”。钱锺书指出,“不持分散眢论,可以得一”,而“正持分散眢论,可以破‘聚’”。(10)钱锺书:《老子王弼注》,见钱锺书:《管锥编》(第1卷),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第685页。“分散眢论”,是钱先生对拉丁文Fallacia Divisionada(分解谬见)的译文:一个个数车辐,看不出车轮的存在;一条条指出马腿,指出的并不是马——整体并非部分的累加,而是单一意义的合体。
在数字时代,单元与文本的距离更加远:电子文本分解后的符号单元(数字、像素)几乎没有文本的影子,而文本组合起来后(例如一个软件)也看不到单元的构成。所有电脑创造或者模仿的事物——包括声音、音乐、线条、表面、实体等等——都是一堆数字根据不同方式组合的结果。世界包含的信息可以被分解,然后再被组装:数字信息就是“组合已有的信息”而成,(11)转引自:Erkki Pekkila,David Neumeyer,Richard Littlefield(eds.) Music,Meaning and Media,University of Helsinki,2006,pp.137-138.看起来像个 “七宝楼台,碎拆不成片段”。(12)(宋)张炎、沈义父等:《词源注·乐府指迷笺释》:“吴梦窗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 碎拆下来,不成片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第16页。数字时代的文本几乎是个“黑盒子”,文本的构成元素,与我们面对的功能文本相差实在过大:一幅绘画拆成元素,可以看到色块线条;一副游戏的电脑图景,拆开只是数字。数字文本是一种“纯文本”,一种无法从构成方式的角度进行理解的文本。
那么,有没有不与其他符号组合、而以一个独立的符号单独构成文本来表达意义?没有。有些符号看上去似乎没有明显的组合因素,一个红灯,一个微笑,一个手势。我们仔细考查,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符号。要表达意义,符号必然形成文本组合:一个交通灯必然与其他信号(例如路口的位置、信号灯的架子)组合成交通信号;一个微笑的嘴唇必然与脸容的其他部分组合成“满脸堆笑”或“皮笑肉不笑”;一个手势必然与脸部表情、身姿相结合为一个决绝的命令或一个临终请求;“佛祖拈花,迦叶微笑”,似乎只是解读“一朵花”这个单独的符号,其实迦叶解读的是个相当大的文本:“尔时如来坐此宝座,受此莲花,无说无言,但拈莲花,入大会中八万四千人天,时大众皆止默然。于时长老摩诃迦叶见佛拈花,示众佛事,即今廓然,破颜微笑。”(13)《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拈花品》,《万续藏》第八十七册。因此,符形学研究的重点,是符号的“文本性”。
在莫里斯时代,符形学据说是符号学三个分支中“发展得最充分的一支”(14)③⑤ Charlew W.Morris,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Mouton & Co.N.V.,Publishers,1971,p.28、30、35.。许多不同领域,如语言学、逻辑学等在符形学上的成绩,都加速了符形学的形成。在莫里斯看来,符形学考量的不是符号载体的个别特征,或是符号与符号过程中其他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是遵守符形法则的“符号和符号组合”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莫里斯的符形学研究,如他所说,在其“广泛意义上”必须“包括所有符号组合”。(15)③⑤ Charlew W.Morris,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Mouton & Co.N.V.,Publishers,1971,p.28、30、35.符号文本的体裁规定,很难总结出一套通用的法则,要深入到每个符号体裁本身的规律,例如各种诗体的格律,或是各种球赛的规则,再从中总结出一套共同的原则,的确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莫里斯认为,与符义学和符用学相比,符形学的发展相对容易一些,他可能是指语言学与逻辑学关于符形的研究成果可以扩大应用于符号学。实际上,符号组合成文本的方式比语言的句法与语法困难得多,任务复杂得多。要探索符形学的全部领域,需要综合各种体裁中符号组合和转换的研究,比如研究符号文本的渠道与媒介,它们的伴随文本,它们的组合-聚合双轴关系等等。单独讨论某个体裁形态规律的研究很多,总体探索符形学规律的研究至今远远不够。连瑞恰慈最早提出的“单一原则”至今也很少见到学界讨论,我们还不知其中的符号现象学的根本机制。整体看起来,符形学几乎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16)参看赵毅衡以下作品:《艺术与冗余》,《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第11-19页;《论聚合系列文本——一个普遍的文化符号学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第110-115;《主体部件出租:论作品中艺术家主体性的表现方式》,《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第156-163页;《论“自小说”》,《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第211-218页;《艺术与动势》,《文艺争鸣》2020年第9期,第68-74页;《艺术的拓扑像似性》,《文艺研究》2021年第2期,第5-15页;《当代文化的“双轴共现”文本增生趋势》,《文艺争鸣》2021年第5期,第46-51页。
三、符义学及其对象
长期以来,符号学家一直认为符义学是符号学的核心,semantics(符义学)一词,与semiotics(符号学)同根,都来自希腊词sema(符号、神迹)。莫里斯认为符义学研究符号表意中“固有的”意义维度,关注的是“符号和符号指谓(designata)之间的关系”,即“符号和符号可能指称或实际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17)③⑤ Charlew W.Morris,Writing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Signs.The Hague:Mouton & Co.N.V.,Publishers,1971,p.28、30、35.所谓“指谓意义”,是指符号文本与其意义对象是如何连接的。这个连接关系,目前符号学界用的词是“指称”(reference)。在皮尔斯笔下,符号所指称的是符号的“对象”(object),很多人把此词译为“客体”。客体是针对“主体”而言的,在符号学这种形式分析理论中,最好慎用“主体-客体”这对容易陷入哲学史上无穷争议的词语。
皮尔斯认为符号表意过程是再现,符号就是再现。皮尔斯自己的行文不太用“指称”,而常作“符号,或再现”(a sign,or representation),把符号称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18)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Univ.of Harvard Press,1931-1958,Vol.1,p.339.“再现”就是对某种被“呈现”(presentation)于人的心灵之物进行可以感知的显示,对象是否实在不是符号意义的一个前提。若说符号的意义是再现对象,符义学就是研究符号与对象如何发生此种联系的,这就是皮尔斯说的“像似-指示-规约”的理据性,与弗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说的能指/所指之间的“任意武断”关联。这是任何符号学书籍中最基本的论述。
那么就出现一个根本问题:符号是再现已有的对象,还是创造一个对象?一幅荔枝的画,一个“荔枝”,或“荔枝”这个词,或“lichee”这个英文单词,指向的一个事物,是在符号之前预先存在的、一个经验中的概念。这个概念并不一定是“现实”。“无人知是荔枝来”,除了杨贵妃、唐明皇,当时大部分中原人没见到过这种岭南名果。推而广之,有什么根据认为对象是现实的呢?“对象”完全可以是心灵的构造物,是白居易告诉我们的一段奇闻。对象是否“现实”,实际上不是符号学意义活动的出发点。(19)参见赵毅衡:《论意义顺序:对象先于符号,还是符号先于对象?》,《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第145-150页。这个旧问题中有一个更基本的疑问始终没有得到透彻的讨论:符号表意的“对象”,经常不是实在物,而是心灵的构造。按照皮尔斯的看法,符号意义对象可以是想象的(imaginary)、虚构的(fictional)、“神话的”(mythological)、甚至是臆造的。此时它们并非“客体”,却无疑是符号创造的意义对象。“荔枝”这幅画或这个词换成“凤凰”,问题就更加明显了,因为“凤凰”明显是我们文化的集体幻想,有人信其有,有人信其无,无论是有抑或无,“凤凰”一词在表意机制上并无差别。
皮尔斯提出,符号再现的“对象”有层次问题,一种是“即刻对象”(immediate object),也就是任何一次符号再现的意义所指向;(20)Charles Sanders Peirce,Collected Papers,Cambridge MA:Univ.of Harvard Press,1931-1958,Vol.2,p.293.另一种是“动力对象”(dynamic object),可以认为是“真实”(real)的对象。这个真实不是预先存在的实物,而是符号意义的累积构筑。同样意义的复合行为,最后会累积成一个“真实”。符号表意的累积永远不会结束,所以这个所谓真实的对象,实际上永远不会完全存在,只是在符号活动中意义趋近于“真实”,或者说是“共识”。符号活动每次都有“即刻对象”,只是这种对象很可能是模糊的,甚至是偏见的产物,但是它们会逐渐趋近真实的“动力对象”,虽然理论上永远不可能抵达之。因此,符号再现“对象”的过程,不一定不会误导,这与皮尔斯的符号真知观相当一致,(21)参见赵毅衡:《真知与符号现象学》,《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78-83页。也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一致。(22)[德]恩格斯《反杜林论》:“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符义学与符形学之间也就存在着一种依存关系,符形学的发展必然会促进符义学的进步,符义学的进步反过来又会给符形学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养料。符号,具体来说是符号的符义维度,因为符义法则而存在,又受到表现为某种习惯的再现方式(即所谓“理据性”)的限定,此处,已经卷入了符用学的范畴。符义学处理符号与其对象的关系,必然关涉符号的使用法则,要将符义学从符用学中抽离确实相当困难。毕竟,符号的意义总是与符号的使用相关。
四、符用学的再界定
按照莫里斯的定义,符用学研究的是符号与接收者之间的关系,研究接收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接受,何种意义才会发生。只有落实在具体解释中的意义,才是符号实现了的意义,即“实例化”(instantiated)了的意义。凡是必须考虑到使用者的问题,都落在符用学的领域。符用学推进到了传统符号学的边界上,因为符号意义必定涉及使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或心理条件,这就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形式分析的范畴。符号学家杰弗里·N.利奇(Geoffrey N.Leech)指出,凡是应对了以下四条中的任何一条,符号的解释都进入了符用学的范围:(1)是否考虑发送者与接收者?(2)是否考虑发送者的意图,与接收者的解释?(3)是否考虑符号使用的语境?(4)是否考虑接收者使用符号想达到的目的?(23)Geoffrey N.Leech,Semantics:The Study of Meaning,Penguin Publishing Group,1974,p.2.
不但意义完全靠使用而产生,而且使用的具体语境不同,符号的意义也会变得无穷复杂。人类活动的各个领域,包括社会、文化、个人生活,都影响符号的确切意义。要理解一部电影,几乎会卷入整个人文学科、社会学科的知识。夸张一点可以说:如果一部小说或电影意义比较丰富,那么它创造的世界,可以支持任何论辩,因为它不仅牵涉解释者个人,而且卷入符号的总体社会表意潜能几乎是一个独立的意义世界。
意义问题最可能的解决途径,必须到符用维度中找。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24)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New York:Blackwell,1997,p.29;又见:Garth Hallet,Wittgenstein’s Definition of Meaning as Use,New York:Fodham Univ Press,1967.这是极其精彩的观点,简明,而且影响极大。到符号的用法中寻找意义固然复杂,但是符号的真正意义就是它的使用意义,而符号学作为意义学无法躲开意义,不然我们永远无法解开“意义”这个结。英美学界受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影响很深,约翰·奥斯丁(John Austin)与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语用理论在英语世界发展迅速,(25)此说源自M.H.艾布拉姆斯《关于维特根斯坦与文学批评的一点说明》《如何以文行事》二文,见[美]M.H.艾布拉姆斯:《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63-75、251-273页。使符用学成为当今意义理论研究最重要的方向。
意义的实现,是个不断深入的过程,每一步都牵涉到符号文本的使用者。面对符号,解释者从感知,到注意,到识别,到解释,到理解,到再述,实为一个“无级”的深入过程。为方便讨论,笔者把符号意义的接收分成感知、接收、解释三步。符号意义“被感知”为第一步,感知却不一定导向认知。解释者生活在各种各样刺激的海洋中,这些刺激都能被感知,也有相当多已经被感知,但是没有多少被识知(cognized),而被解释的就更少。例如驾车者一上街,满眼是可感知物,但是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能涌入眼睛、耳朵,成为被感知的部分,而且他必须马上从中筛选出一部分需要立即判断其意义的感知,予以接收,成为意义文本,而让其余的感知作为“噪音”排除出去。在这样一个过程之后,这位使用者才能对接收到的符号文本作出理解。这个过程说起来很复杂,却是每时每刻在刹那间自动进行的,不然马上会出现意外事故。
此种“高度选择性接收”,贯穿于任何解释过程中。感知不是接收者的意向性过程,接收才是他的意向性结果:任何解释,都是选择的结果。一旦这个过程程式化,就变得自动而高效。例如一个交通标志,说明前面道路弯道较多应降速。见到此标志,驾车者最好不去想路牌上弯曲的线如何“像似”弯道,而是该用自己对交通规则的熟悉,去程式化地理解此符号,即跳过所有的中间环节,从感知直接接入理解,迅速调整车速。如果开车者没有程式化理解的能力,涌向他的感官要过滤与解释的符号元素太多,则他几乎无法开车。
对于艺术符号文本来说,程式化地缩短识别流程,却是最失败的接收方式:见了开头就知道结果,这样的小说、电影简直乏味;文本与解释之间缺少距离,就是浅薄的诗。艺术是理解的缓刑,是让接收者从感知中艰难地寻找理解。这个过程越费力越让人满意,让人乐在其中;最后找不到理解,恐怕更好。甚至可以说,理解艺术作品,只是一个障蔽理解的借口,艺术就是让人停留在感知和识别层面的琢磨。
因此,有句奇怪的话可以说得通:学习理解,就是学习不再去理解。此悖论可以有两个意思:驾车者过斑马线的反应中,就是对感知以最快速度“不假思索”的解释,就是对符号自动化的反应;在艺术欣赏的例子中,不理解就是努力推迟理解,过程本身就是艺术欣赏,解释是第二位的。
符号学界原先也认为,符用学的地位是成问题的,有人甚至觉得符用学是符号学的“垃圾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可以说“这是符用问题,太复杂”而搁置一边。这个看法现在不对了,今天,符用学成了符号学最重要的领域,“使用中的意义”的确最为复杂,却成为符号学最广阔的天地。
有论者认为,索绪尔影响下的符号学的法国学派,依然偏重符形学与符义学,而皮尔斯理论主导下的英语学界的符号学研究,其核心一直是符用学。我们可以看到,莫里斯的符号学三分维,虽然不是皮尔斯提出的,却与皮尔斯的符号构造本身的三分法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符形学研究的是符号组合形态,是“再现体”的品质;符义学研究的是“对象”,是符号与对象的再现关系;符用学强调的是符号的解释意义,即所谓“解释项”,没有使用者的解释,就没有解释项。
这两种三维度的对应方式,并非如我们所说的这么简单,但这个对应关系看起来的确存在。意义包括了相对比较固定的再现对象,也包括了根据具体使用语境才能得出的解释。例如三个颜体字“同仁堂”,指称对象是著名的重要老字号药店。如果使用于匾额,那是指一家专营同仁堂产品的药店;如果使用于药品包装,指的是同仁堂亲制或监制的合约厂家制造;再进一步追溯解释,就是同仁堂的历史信用对药材调制质量的保证。因此,在对符号文本意义的具体分析中,符义与符用,有时可以看清,有时却很难截然划分,此即所谓的符义、符用维度。
五、三维配置与中国书法
以上简单地梳理了符号意义过程的三维,实际上,每一维度都应当有专文或专著来讲解才能说清楚。想想语言学仅仅一个句法学,就有多少专著在讨论,就明白这些问题之复杂。目前符号意义过程的分维度讨论,许多问题尚未解决。以上的介绍相当抽象,必须用一系列例子,具体说明讨论任何符号意义问题都需要分维讨论,不然很可能陷于概念不清、分解不明,越说越糊涂。
应当说,三维度意义配置,出现于任何符号意义问题中,例子无穷无尽。笔者先找一些艺术产业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例子,看看分维配置,是否能帮忙解开一些复杂问题。中国书法艺术,看起来简单,实际上极端复杂,我们从中国书法(26)说明:此文讨论不牵涉所谓的“美术字”。美术字是指字形的图案化,利用字的形态表示某种图像意义。任何文字都可以变化出很多图案化的方式,用符形变化表现某种意义。中文字形特别复杂,变化方式可能比世上任何文字更多。但是各国文字在美术字以字作图方面,方式相仿,因此暂且不论。的意义维度谈起。
书法作为中国的一门特殊艺术,非常难以分析,至今理论争议点实际上不多,因为谁也没有提出一个可供检验的分析方式。论者一般凭直觉,用诗性语言讨论诗性对象,如此解释只是增添了一层解释对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用“象”概念讨论书法艺术,这“象”可以从《周易》的“立象尽意”说起,古今中外历史上有无穷无尽关于“象”的说法,“象”的书法学只是把书法研究变得更为复杂。如果说“象”就是视觉性、书法是视觉性艺术,这就相当于什么也没说,书法不可能经由其他感官渠道被接受者感知。
另一些专心于西方哲学流派(例如现象学)的学者似乎也找不到着眼点。例如,“当我们(用胡塞尔的‘还原’)悬置起所有的知识与看法,不再关注书法作品的书写材料、纸张大小与材质等,以‘陌生化’的眼光去打量它,我们会发现,书法作品不仅仅是一个技法展示,而是一种生命、一个新世界”。(27)王静珂:《西方哲学方法论视域下的书法美学探究》,《汉字文化》2021年第24期,第178-179页。这些过于宽泛的说法,用于书法这样一种具体的艺术,或许能让人们感觉书法艺术的博大精深,却无法分析出书法的意义构成。
如果我们按照符号意义研究的三分科来讨论书法,问题就比较容易显露了。书法是文字的书写方法,任何文字都有写法问题。拼音文字字母有限,其写法也有变体,有妍媸美丑,也可能成为“艺术”,具有让观者感到脱离日常凡庸的气质。伊斯兰民族尤其重视阿拉伯文的书法,因为教义禁止为神与圣人造像,各种宗教场合,以《可兰经》中的文字代替,作为神在之证明。阿拉伯人认为他们的书法是艺术,但是显然与中文的书法非常不同。问题是:这个不同点在哪里?
书法是普遍的,但各种文字的写法多有变体,都只是“抄录法”(script)之变异。拼音字母,包括阿拉伯文,文字意义是最重要的表意维度。其符义是意义主导方式,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是唯一的意义维度。其符形的意义是次要的,从属的,服从其语义的。书写形态的变化能独立表达的意义很有限,写法(形态)本身的独立意义也有限。阿拉伯文的书法为世人瞩目,但其以硬笔与皮革为主要的书写工具,发挥余地不大。看一段清真寺的经文装饰,字的形态固然重要,所引用的经文是否合体,远远更为重要,也就是说,符用、符义大于符形。
而中文的写法非常不同。软毛笔与宣纸的接触,可以变出无穷样式,书写者经常随心挥洒,创造艺术,具体写什么文字反而成为次要维度。有学者甚至认为中文书法只需要符形,不需要符义,与拼音文字的书写情况正好相反。林语堂强调说,“在欣赏中国书法的时候,是全然不顾其字面含义的,人们仅仅欣赏它的线条和构造”。(28)林语堂:《中国人》,郝志东、沈益洪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8页。沈鹏认为,“书法和绘画是不同的,它的美是高度抽象的,不存在‘题材’问题……书写的文辞并非书法的内容”。(29)刘鹤翔:《回到现代书学的开端——二十世纪前期书学研讨会综述》,《中国书法》2017年第4期,第34页。
此种论断认为中国书法只有符形,有点夸张。我们看一幅书法,不可能完全不理会文字的意义,事实上,在不同场合,文字意义得体与否是非常重要的事。不过这些理论家的极端之论,说出了一个道理:中国书法艺术的侧重点在形态,一般情况下语义居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忽视符义与符用。这就是为什么草书有时让人看不懂字,依然被称为令人惊叹的艺术。甚至有时故意写错字(如傅山书法、徐冰《天书》),反而更为意义深长,让人们深思书法的艺术性究竟落在何处。这就是为什么美术界经常把中国书法比之以抽象艺术:形态本身的意义,超过了其指称意义。
古人写一篇书法,不宜重复用字,一旦复用,常常添笔改字形,以能猜出为准。创造出花样百出的“异体字”,反见其功力,见出书法家用心。唐代张怀瓘有云:“文则数言乃成其意,书则一字已见其心。”此言中说的字数对比,不见得如此,但就文须见其“意”与书见其“心”而言,的确说得很到位。文字具有实用价值,书写文字的目的就是让人明白其意义,而书法只要能见形,哪怕一个字、意义不全,也能见其艺术精髓。而优美文字与高妙书法的恰当结合,实为佳品。如在中国书法史上有崇高地位的颜真卿《祭侄文稿》就是形态、文意、用途三者的完美结合,书者的家国悲怆之感在三维配置中互相加强,遂成千古名作。
可见书法的意义重点在符形上。这不是说书法意义没有符义、符用维度,而是说大部分情况下,其主导维度是符形。真正用作交流的信札文件,其字依然要求能看得懂。用作建筑物悬于门屏上的匾额、重要场所的对联,字不能太草,字义也要合体。一旦只作为书法展示,跌宕变化的幅度就较大,形态可以夸张任性。可见,书法作为艺术,意义配置以符形为主导,符义与符用在绝大部分情况下起配合作用。
六、艺术无赝品?
研究艺术问题的符号学,一直被称为“符号美学”。(30)④ 陆正兰、张珂:《当代艺术产业分类及其符号美学特征》,《符号与传媒》2022年第1期,第66、60页。“艺术无赝品”这个说法是笔者在多年前提出来的,意思是艺术品固然苦于大量赝品充斥、捣乱市场,但是“赝品破坏的市场价值,是它的实用表意功能,而不是艺术表意功能。艺术性本身无法标价,因此真正的艺术,无所谓真伪,没有原作与赝品之分”(31)赵毅衡:《符号学:原理与推演》,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艺术品、收藏品市场,最头痛的就是赝品。有的赝品在感知上与原作一样,在接收者能感知到的符形品格上与原作不分轩轾,也就是说接收者对符形得到的是几乎相同的感觉,艺术性就来自这种符形感觉,因为艺术性停留在感知上。
任何物都可以是“使用物-实际意义符号-艺术符号”三联体,它的物功用、实用表意功能、艺术表意功能,三者可能共时共存;甚至,这三种意义可以同时出现在同一物身上。(32)陆正兰、赵毅衡:《艺术符号学:必要性与可能性》,《当代文坛》2021年第1期,第52-53页。我们从最普通的商品入手,看任何“物-符号-艺术品”的三层功能滑动:一是作为纯然之物的物用功能。一件家具,其使用与其物质组成有关,例如用料质量与加工精致程度。二是作为符号文本的实用表意功能。如品牌、格调、时尚、风味、价值,这是社会型的实用符义、符用价值。三是艺术性。如美观、色彩与空间的配合,这是纯感知的功能,是符形价值。任何物在这三层之间滑动。如在一件家具中,在几乎任何商品中,这三种功能在滑动之后合成一体。
举个例子:一件家具不管是真正名牌,还是假冒名牌,它们在艺术上是一样的。价格差别主要来自符义,即该家具的商标或特殊样式指称的品牌价值;家具作为符号文本的艺术性,来自于符形;而家具作为收藏品的市场价值,来自它的符用品格。艺术性是感知,无所谓真伪。可以如此总结:从符号的意义三维度来看,在符义、符用维度上,艺术品有赝品;在符形维度上,艺术无赝品。
工业社会给艺术带来的最大变化,不仅仅是机械复制,而且是大众化、世俗化以及日常生活化。(33)④ 陆正兰、张珂:《当代艺术产业分类及其符号美学特征》,《符号与传媒》2022年第1期,第66、60页。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提出:在现代这个“机械复制时代”,艺术品的“灵韵”(Aura)消失了,社会上流通的、大众能看到的,是大量的复制品。符形上一旦被认为提供了相同感知,文本是否原作就已经不重要了。实际上不少人在已经看惯了《蒙娜丽莎》的各种精致的复制品后,花了很大力气到卢浮宫作朝圣之旅,看到尺幅颇小、色彩有些灰暗的《蒙娜丽莎》原作,反而颇为失望——灵韵的确消失了。
艺术需凭借一定的媒介形式方能呈现,艺术会因媒介形态而发生深刻变革。由于现代科技的基础、传媒载体和传播渠道深度介入,如今的艺术有逐渐被高度媒介化的趋势。(34)刘俊:《理解艺术媒介:从“材料”到“传播”》,《当代文坛》2021年第6期,第124-128页。在当今虚拟时代,区块链的衍生技术NFT(Non-Fungible Token)代表非同质化通证(35)Fungible,来自中世纪拉丁语fungi,意为perform,即function(起某种功能)的原词。原意指经济活动中,商品(例如订购某种布料)可以以同质的布料替代。使艺术品充斥赝品的局面发生翻转。区块链的衍生技术NFT使得虚拟数字世界形成三个特点:首先,全程有凭证留痕(指时间戳time stamp,或称区块链指纹)保证已经存在的文件或文本的有效性;其次,公开透明,去中心化,任何人可以看到并参与原文本及其发展过程(包括转卖、拍卖等经济活动);第三,用强制的不受篡改的品格,使“真品”这个原本依靠人为判断的不可靠品格,成为有程序保证的品格,从而保证了各种符号文本的“唯一真实性”,尤其保证了原创性的版权、合同、文件等,即符义、符用上必要的“真品”品格得到了保证。购买商品时,我们只需关心类型相同的(同质量、同产地等)货品即可,而艺术品(例如拍卖行、博物馆)必须保证是“原作”这个具有特殊符义性的单符,而不仅仅是具有符形等值的艺术品。正如卢浮宫大批警卫保卫的,不是具有艺术性符形的《蒙娜丽莎》,而是具有独特符义指称的《蒙娜丽莎》。
因此,在数字时代,具有艺术性的符形文本就与艺术品要求的符义、符用维度结合起来了。在公开、透明的过程中,区块链恢复了艺术品的原创性不可篡改的“灵韵”,同时又保存了艺术性可以被复制的符形感知,而且复制率与精密度远远超过了一个世纪前的“机械复制”。我们至少可以预言,在数字媒介时代,艺术的意义方式有重大变化。一方面,艺术品可以被高保真地复制,而且大量传播,“艺术无赝品”这条关于艺术性的符号美学依然成立;另一方面,由于NFT的安全性,艺术品本身有时间戳做通证,原件的稀缺性得到保证,拍卖双方更为放心,已经被保证稀缺化(原创性得到保护),很容易在市场流动。过去的原作保存于宫殿贵宅的珍藏中,只有上层人物乃至贵族才能看到;艺术品之真,往往需要著名收藏家的签字文件(中国画往往靠名家收藏章)作不太可靠的保证。现在只要及时放进有认证的区块之中,艺术品就既可以复制,又可以拍卖。哪怕复制再如真,原作不可篡改地存留在那里,它的灵韵一直存在。
七、三维配置与现代工艺艺术中的抽象艺术
为何现代工艺艺术爱用抽象艺术风格?为何大众难以接受抽象艺术,却乐于接受日用商品与公共空间设计的抽象艺术风格?这是全国设计专业都明白的、在教学与实践中一直实施、却至今没有人从理论上探讨的重要美学问题。
首先,什么是“抽象艺术”(abstract art)?顾名思义,抽象艺术的反面是“具象艺术”(figurative art)。有人认为抽象艺术就是“非再现艺术”(non-representational art),这说法把符号的再现对象看得太狭窄:再现的对象不一定是具体物,有可能是概念、想法、虚构物,甚至艺术文本自身。(36)赵毅衡:《论艺术的“自身再现”》,《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第77-84页。一旦指称对象非具体物时,再现本身就变得抽象。此种“非实在再现”不难理解。早在19世纪,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就明确指出“所有的艺术都追求音乐的效果”。(37)Walter Pater,“The School of Giorgione,”The Renaissance:Studies in Art and Poe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p.104-105.所有艺术再现都多多少少与对象保持距离,各种体裁、各种风格流派程度不同,却都或近或远地推开对象。多少跳越指称、淡化对自然物的直接模仿,是艺术的本质,只不过音乐倾向于与具象保持距离。
抽象即非具象,这点容易理解,也极易辨认。几乎在所有的艺术中,都有抽象因素。诚然,某些现代艺术流派抽象程度比较明显,甚至有些流派标榜“纯”抽象,无对象再现痕迹可循。可以说,现代与后现代的艺术,甚至所有的艺术,都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反过来,立体主义、野兽主义、达达-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等现代艺术流派,都有部分具象,哪怕画幅上之“象”非常扭曲,哪怕能辨识对象只是一个借口。(38)孙金燕:《无法与无需抵达之象:贡布里希艺术思想核心理念讨论》,《符号与传媒》2020年第2期,第32-43页。但的确有些画派纯抽象、全不具象,只剩下点、线、面与色块,留个标题似乎说明有个再现对象,如波洛克的《秋之韵律》。但是相当多作品连借个对象作借口都不屑,例如罗斯科的作品干脆称为《红22号》。
纯抽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艺术史上回顾,抽象艺术的几位创始人,与工艺艺术和科学技术都关系密切,这不是偶然的。或许正是商品外形、现代城市景观、技术的运行方式之线条化、高速化,迫使艺术家的眼光离开大自然的繁复、离开自然物的符义性。这些艺术家认为现代工业的运动,已经把物分解为速度与力量,因此艺术作品也应当解体为形状、线条、色彩、块面。
因此,在1910年左右,抽象艺术在设计艺术中诞生,而且几乎同时出现于西欧与东欧。荷兰“风格派”(Stijl)画家彼埃·蒙德里安(Piet Mondrian)的抽象来自于他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接触及对世界进行“理性控制的结构”,他的方格色块,追求人神统一的“造型数学”。因此蒙德里安式的抽象,几乎是几何图形,往往被称为“冷抽象”。
而在另一端,苏联的呼捷玛斯设计学院,为20世纪初在俄国兴起的“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提供了温床,其核心人物瓦西里·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直接受到沃林格尔理论的影响。这一派还包括构造主义雕塑家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以及发动“至上主义”(Suprematism)的画家卡西米尔·塞文洛维奇·马列维奇(Kazimir Malevich)等。这些抽象艺术家对现代科技怀抱热情,也热烈拥抱社会革命。这一派的抽象方式,被称为“热抽象”。马列维奇的著作《无物象的世界》(1930)是对抽象概念相当精确的总结。
真正把抽象艺术与现代工艺艺术结合在一起的,是现代工艺美学史上的里程碑——德国设计学校包豪斯(Bauhaus),包豪斯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抽象艺术设计,成为现代工艺设计与艺术结合的发源地。
诚然,在包豪斯之前,美术与技术的互相靠拢,在各国已经成为趋势。只不过包豪斯以工艺设计为教学,长期坚持抽象艺术理念,对现代艺术史影响最大。包豪斯的创建者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提出“功能第一,形式第二”,反对19世纪工业商品中残留的中世纪装饰,例如钢铁制件上加花纹、建筑尖顶加金饰、女性衣帽加蕾丝花边。他们主张在设计中放弃这些花饰,转向抽象主义的纯粹块面线条。
现代工艺艺术与抽象艺术的融合显得很自然,似乎并非刻意为之,这个现象无法不令人注意。茅盾在20世纪50年代的批评著作《夜读偶记》中高度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坚决否定并且批判“资产阶级现代主义”,但他却承认现代主义风格用在建筑设计上很有特色。(39)茅盾:《夜读偶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第56页。艺术学家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 Fried)的说法更为明白:“恰恰是在设计领域,而不是与功利无关的纯艺术领域,纯粹美最鲜明地成为现代品质的基本内涵。”(40)④ [美]迈克尔·弗雷德:《艺术与物性:论文与评论集》,张晓剑、沈语冰译,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145、144页。为什么抽象是现代艺术的“纯粹美”呢?因为抽象艺术“是一种零符号的美,或者说是一种冷感的趋于意义零度的美”。④抽象艺术“意义零度”,应当理解为没有指称对象。
纵观整个现代艺术,我们不得不承认,抽象艺术是其中最小众的一端。奥尔特加就公然说,现代派艺术观者分成两类:一类懂这种艺术,一类不懂,现代艺术“不是面向一切人,而是面向有特殊天赋的少数人”。(41)Jose Ortega Y Gasset,“The Dehumanization of Art,” in W.J.Bate (ed),Criticism:The Major Texts, New York:Harcourt,1970,p.661.全面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批评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er W.Adorno),是现代艺术的辩护士,他的辩护方式却是赞美现代艺术之反大众。他提出,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现代艺术就是应当“与现实拉开距离,形成对这个应该被否定的世界之否定”,而“其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拒绝被大众接受”。(42)转引自周宪编:《20世纪西方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83-84页。
这些倾向不同的艺术理论家,观点听起来极端,说的却是客观事实。抽象主义的“纯艺术”,的确是一种精英艺术,这些艺术家毫不讳言地反大众、反市场,使现代派艺术作品只能存活于“博物馆坟场”。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大众,各国的大众,对现代抽象艺术大多敬而远之,在大众眼中,这些艺术家剑走偏锋、欺世盗名,艺术批评家故弄玄虚、捣鼓术语,收藏界则投机跟风、哄抬价格。
为了给当代艺术提供一个辩护,不少理论家提出各种观点。1966年,英国艺术学家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首先提出所谓的“环境美学”(Environmental Aesthetics)。(43)Ronald Hepburn,“Contemporary Aesthetics and the Neglect of Natural Beauty,”“Wonder”and Other Essays:Eight Studies in Aesthetics and Neighbouring Fields,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84,p.9.美学家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审美域”(aesthetic field)理论,(44)Arnold Berleant,The Aesthetic Field:A Phenomenology of Aesthetic Experience, Springfield Ill,Thomas,1970,p.49.又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艺术与介入》(45)Arnold Berleant, Aesthetics and Engagement,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91.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参与式美学”。他认为,“环境中审美参与的核心是感知的持续在场”。(46)[美]阿诺德·伯林特:《远方的城市:关于都市美学的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第5-11页。这就给工艺设计中的抽象艺术风格提供了一种辩护方式:大众不需要看懂抽象艺术,只需要“沉浸”在结合了抽象设计的“审美域”之中。在美学层面上极端“脱离大众”的抽象艺术,通过工艺艺术,深深地楔入当代生活,形成当代社会文化“泛艺术化”的基础。
抽象风格的工艺艺术,既然是符号文本,就依然有意义,只不过一旦摆脱了具象,其符形意义,就几乎全部跳过了符义的对象指称,不再能认出具体的指称对象。由于其指称方向往往是“自我指涉”,或称“自我再现”,它们的解释项由此打开,获得了意义解释的自由度。抽象艺术再现的指称对象既然已被虚化,它的再现对象主要就是艺术文本本身。工艺设计如果采用抽象风格,艺术的直接对象意义基本上被跳越。冲淡了指称意义的抽象艺术,一旦融入工艺设计,第一个明显后果就是比较容易与器物意义结合,形成符号文本定义要求的“意义合一”,即前文说过的奥格登与瑞恰慈提出的文本意义“合一原则”:商品艺术的符形跳过符义维度,而直接具有符用意义。
可以说,现代社会之前,工艺艺术与商品之间的关系,是“分列附着式”的,工艺艺术与器物的意义关系,经常可以(虽然不一定必须如此)作为两个不同文本,分别表达意义。例如今日考察瓷器历史意义时,工艺瓷画的艺术意义及其身份标识作用,可能远大于瓷器本身的意义,也即瓶与画二者分成两层,各有其意义。所以我们看到不少器皿装饰华丽、层次纷繁、精工细作,其身份意义与美学意义,可以与器皿关系不大。例如花瓶上有精工描绘的《二十四孝图》:花瓶是一件艺术品,有其单独的意义;而瓷器上所画是另外一个艺术文本,有其单独的符义(儒家的训诫),二者是意义分离的两个文本。
现代工艺艺术中,除了有意“仿古”的花瓶,大多采用了抽象艺术。当今瓷器材料与加工技术进步、时代风气演变,都是原因。例如摩天大楼之间的广场,大都有雕塑装饰,一旦其风格抽象化,就不会喧宾夺主另立意义,而是与广场的城市空间意义结合;旅馆大堂常有屏风间隔、有抽象艺术为装饰,就不会意义分裂;晚会礼服不再饰以“龙凤呈祥”图案表现社会地位,而是用抽象线条呈现身体姿态之美。这样,符形与符义、符用表意合成一体,不再是意义分离为两层的文本。
现代工艺设计,趋向于采用抽象风格,趋向于跳脱指称。这样可以退回到符形,让器物、公共空间本身呈现符义、符用功能,而不至于干扰它们的意义。相对于古代公共建筑,当代建筑的形体特征减淡自身的指称意义,以突出周围空间的符义,尽量不干扰其符用。以贝聿铭设计的卢浮宫入口为例:玻璃金字塔的抽象形体,不干扰周围宫殿式建筑已经非常饱满的符义、符用意义,反而以其符形意义上的抽离,完美地与卢浮宫厚重的历史感合成一个完美的意义文本。随着“泛艺术化”深入当代文化,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周围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