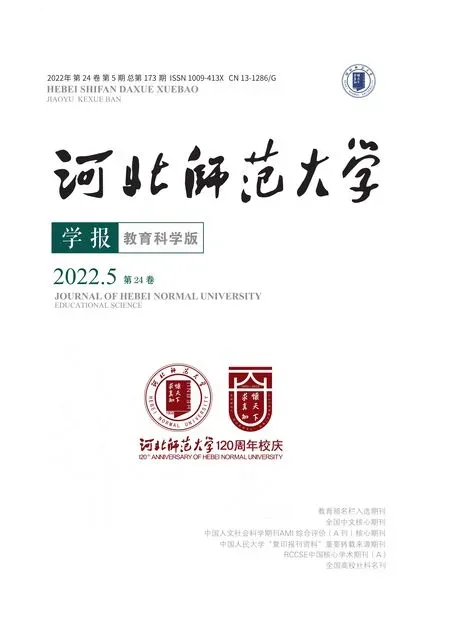“怀天下,求真知”
——由精神激励到文化传承
王俊才
(河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现代大学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欧洲由于在近代以来的迅速崛起,一度成为人类灿烂文化、辉煌文明的典型代表,自然也就成了现代大学的发源地。当然,反过来讲可能更合理:正是由于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最早在欧洲出现并得到迅速发展,使欧洲很快成为近代人类活力文化和进步文明的杰出代表。一般认为,意大利于1088年建立的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是欧洲“大学之母”,世界第一所大学。以人为本、崇尚理性、学术神圣、精神独立、思想自由,这些助推人类文明与文化快速发展的理念相汇在人类的“新圣地”,她们融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新生的大学具备了极强的生命力,获得快速发展。到了13世纪,相继诞生了包括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在内的欧洲大学群(四百年后作为剑桥大学在北美的复制品,有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一种符号,当我们讨论近代以来美洲的灿烂、辉煌时总是在她的象征意义笼罩下)。他们成为推动欧美,乃至全球人类文明进步和文化活跃的生力军。
当然,不同国家、地区的大学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各自文明、文化土壤的差异,不仅有明显的民族精神特征,而且还铸就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理念。这种民族精神和价值理念总是体现在各自尊奉的校训中。诸如剑桥大学的“启蒙之所,智慧之源”,哈佛大学的“与真理为友”,斯坦福大学的“让自由之风劲吹”,麻省理工大学的“既学会动脑,也学会动手”;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开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以及中山大学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这些经过历史积淀和理性提炼而熔铸荟萃成的校训名句,言简意赅,由一种精神激励衍生成一种文化传承。所以说,校训是校魂、是学范、是标杆、是信念,是精神支点,是价值理念。她们既体现着不同学校的精神风貌,也展示了各自民族的文化特征;她们既是人类精英的理性荟萃,也是全人类健康发展、全面进步的智慧航标。
校训是一校之魂,既有底蕴又有活力,经由师生代代传承而约定俗成,春风细雨,润物无声,通过滋润校园尔后辐射社会。校训是一把标杆,是办学原则、目标、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她一直勉励、鞭策着在校师生的言行,即使已经离校的学子总是在心灵深处留下厚重的记忆和家园的温馨。校训是一种文化,她不仅体现着一所大学的精神,而且总是激励社会的正气、承载民族的精气、引领时代的生气、校正世俗的邪气。
“怀天下,求真知”是河北师范大学历经百年沧桑、多源一脉汇总提炼而成的校训。如果由近推远,伴随20世纪90年代我国改革浪潮诞生的新河北师范大学是由1988年在原河北职业技术师范专科学校基础上升格的河北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与1980年底诞生的河北教育学院,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新学大潮中应运而生的河北师范学院与河北师范大学两所跨世纪大学共同组成。所以,新河北师范大学既有新时代的生命活力,又具备厚重的历史积淀。因此,“怀天下,求真知”是一道光阴,是一串符号,是一面旗帜,是一种信念,是一个灵魂,是精神的彰显,是文化的体现,有历史的积淀,有当今的承担。她有多源的丰富,又有一脉相承的执着。对于她过去坎坷的梳理,既能增进我们对于她当今的珍爱,还能激发我们对于她未来的信念。
一、求真创新、崇实明理,底定一种精神
历史跨入20世纪,中华民族进入了不得不变、不得不巨变的时代。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均失败的背景下,为了不被时代抛弃,清廷又使出最后一把力气作为延续统治的努力,推出了清末新政。但从时代潮流与历史大势看,清政府的腐朽已经到了不能自救、也无法自救的地步,所以“新政”注定与“洋务”“戊戌”的命运一样:既不能挽救清王朝的灭亡,也摆脱不了自身在襁褓中夭折的宿命。可是,就像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中华民族却得到了一个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这样的骄子一样,清末新政虽然失败了,可燕赵大地上诞生了从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到河北师范大学的时代领潮者,在培育民族英才、唤起全民觉醒、结束帝制统治、争取国家独立、追求男女平等、创建新式教育等方面成为时代潮流的先锋。
顺天府学堂诞生于首善之地,由中央政府钦定、直隶京师操办、顺天府尹亲手经办而成。“天子脚下”“皇恩浩荡”“王贵护佑”“权臣监理”等此类,使得顺天府学堂诞生于官贵的襁褓之中。北洋女师范学堂的诞生与之类似,虽没有生于首善之地,但也是在晚清权臣、直隶总督、清廷新派领袖的直接关照下成立于中国最开放的第一商埠天津,虽然是新潮女学,却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实权派的保护。这些对于她们的生长固然重要,但绝不是最关键的。出身高贵只能说明过去,能否活下去,甚至活的辉煌灿烂并日渐强大,尤其是处于一个不仅在器物制度层面,而且深入到价值理念领域的动荡巨变的时代,靠“娘胎”带来的营养绝对不能长久维持。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之所以能在那个时代成为领潮者,并健康地衍生下来,我们不否认先天营养的基础,但至关重要的是她们在后天的成长中脚踏实地、顺应时潮、直面社会、求真创新、崇实明理、放眼世界、坚信未来,迎着时代的暴风骤雨而上,在现实的狂风巨浪中汲取营养。她们虽然是官办,但管理者与教师主要由开明士绅、新潮名流主持和充任;生源虽然主要不是来自普通大众和寻常百姓子弟,但绝大部分是淡于科举功名、厌恶儒道玄虚之说、痛恨旧礼教束缚、热心时务、关心天下、不守旧、敢创新的有心男女少年。这两个条件就决定了生于危难中的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绝不同于传统的制科教育,百姓的艰难、社会的问题、现实的危机、国家的出路、民族的前途必然是她们生存的动力和奋斗的方向。如何顺应时代潮流,在改造社会、创新人生的道路上开辟出美好前景,是其孜孜以索、矢志不渝的追求。正因如此,求真创新、崇实明理的理念信条也就成了她们的生存方式。这种由于生存本能铸就的理念信条就是从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到河北师范大学在文脉中一直流淌着的解码基因。
20世纪第一个年头的元月底,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光绪趁着两宫流亡西安尚未“回銮”发布“新政诏”,开始了由中央政府发动和领导的新政改革。其中在“兴学诏”中强调“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要求“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1](P504)。后来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就是从此起步的。在洋务运动尤其是戊戌变法中受重挫的新式教育又开始慢慢复兴,直至1905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各类新学制的官办、私立学堂在全国普遍兴起,朝野关于教育改革的设想开始逐步得到落实,中国新的教育制度终于日渐兴起。而顺天中学堂、北洋女师学堂与稍早的北洋学堂、京师大学堂等实属中国新教育制度的先行者和开创者,所以她们早期的成长过程是我国现代教育制度诞生的最典型代表之一。
探讨河北师范大学的第一源头,我们必须得从顺天府学堂(亦称“顺天中学堂”)说起,而探讨顺天府学堂的源头必须得从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阳人)说起。他认真总结过去,看到了洋务学堂在指导思想方面摆脱不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在具体操作中又“斤斤于文字语言”“皆囿于一才一艺”,在思路方面缺乏从学科体系入手考虑培养全新人才的的整体设计,便于1896年6月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分斋教育,并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并在《请推广学校折》中详细向清廷建议不仅京师更要扩及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规定各级学堂优先入学者的条件、年龄以及学制和教学内容。时任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县人)奏复,同意李端棻的建议,并附议强调“宗旨宜先定”“学堂宜早造”“学问宜分科”“教习宜访求”“生徒宜慎选”和“出身宜推广”等六条措施,并将学问细分为天文、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和医学等10科的设想,最早勾画出了近代分科大学的蓝图。这是我国建立新式学校、构筑现代教育的真正萌芽。
到1898年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浪潮推涌,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获得批准,光绪帝任命孙家鼐为管理学堂事务大臣。此时的京师大学堂,既是以国家名义设立的全国最高学府,也是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全国的学务。成为学务大臣的孙家鼐在落实京师大学堂筹建的同时,就李端棻“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议复同意,从京师开始,先筹划建立五城中学堂,接着又会同顺天府尹胡燏棻(1840-1906,字芸楣,安徽泗县人)在向慈禧和光绪帝的奏折中详细陈述了改建顺天府中学堂(一个月前他的奏折中是筹建顺天小学堂)的计划,指出顺天为首善之区,应作为各省会表率,所以请将金台书院原拟筹建顺天小学堂改为顺天府中学堂。之后鉴于金台书院房屋有限,用来讲课的教室少而小,孙家鼐等了解到地安门外兵将局有一所屋舍宽敞而又闲置的抄产官房,便继续上奏,请求将该处拨给顺天府作为首善中学堂之用。由于内容详细,设计具体,可行性强,所以奏折很快获得批准。可惜这两项举措还未及实施,即遭遇戊戌政变失败而被搁置一边。但顺天府学堂的源头却与李端棻、孙家鼐、胡燏棻,乃至戊戌变法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戊戌变法被清廷的顽固派扼杀了,民族的精英们或被杀、或逃亡,士子集体救亡意识、尤其是通过唤起政府主动变法救亡的意识遭到了摧残;但是从社会底层燃起的大众怒火——义和团运动却使清廷失去了对局势和秩序的控制;而接踵发生的八国联军进北京,盗、抢、焚、杀种种恶行,在世纪之交给这个古老的民族留下了无法泯灭的耻辱,昔日对臣民颐指气使的清廷变成了逃亡政府。苦难的中华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告别19世纪、进入20世纪的。而顺天中学堂就是在这个多灾多难时期、动荡巨变的中心,坐胎孕育、准备诞生的。
从李端棻到胡燏棻,由于国家处于多难之际,顺天中学堂前后经历6年的孕育期,虽然属于难产,终于伴随清末新政在顺天府尹陈璧的操持下诞生了,准确的时间应该是1902年的秋天。因为这时真正确定了校址——将地安门外兵将局官房修葺完善成校舍,完成了招生任务——将西文、东文学堂整体搬入。顺天中学堂在筹办过程中,早期试办阶段称“西文东文学堂”,后来有时称作“顺天府学堂”,有时称作“首善学堂”。尔后,张百熙(1847-1907,字冶秋或埜秋,湖南长沙人)等奉旨着手酝酿拟订新学制,但顺天府学堂早已先声夺人,在天子脚下吹响了教育改革的号角,成为古老民族在新时代创建新教育的先锋。
顺天学堂(这里包括顺天中学堂与顺天高等学堂,下同)早期初创因当时风气乍开,报名考学的人并不踊跃,学生名额经过后来连续几次招考才勉强足数。但是“方今时事多艰,需材孔亟”,其面对现实、培养人才、挽救危局的办学宗旨坚定不移,要求“考试策、论各一篇。能通西文须于卷面声明在何处学堂肄业,并附作论一节,以凭录取”[2],考试虽然灵活,但宗旨却很明确。而且教学内容除了传统的修身、经史、文学外,还有地理、物理、化学、数学、英文、法文、东文等,所以说顺天学堂所开课程相对于传统教育而言,可概括为八个字:求真创新、务实具体。
甲午战败之后,李端棻对洋务学堂的得失总结以及建立各种新式学堂的建议标志着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由酝酿期转入萌芽阶段。戊戌变法留下的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新教育萌芽期孕育出来的最杰出的硕果,学务大臣孙家鼐(也是京师大学堂的首任负责人)和顺天府尹胡燏棻(顺天学堂完整设计者)关于顺天学堂的提议和设计则是新式教育由萌芽步入定型的起步。而“新政”时期将这一计划付诸实行的顺天府尹陈璧不仅是顺天学堂的真正创建者,也是我国新式教育的重要创始人。
如果从时间的先后顺序说,河北师范大学的第二个源头是北洋女师范学堂。当然,北洋女师范学堂的真正创办者是傅增湘(1872-1949,字润沅,四川江安人)、吕兰清(1883-1943,字碧城,安徽旌德人)。傅先生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而他最杰出的成就是敢为人先、独领风骚的开创了我国女子新式教育,为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受压迫、被歧视的卑贱地位和悲苦命运迈出了革命性的步伐。这种非暴力的革命——“新式女学”运动对推动全民心理观念的变化、进步,比短暂的摧枯拉朽式的暴力革命还要稳健得多、深刻得多、有效得多。就此一点,今日的河北师范大学实乃百年前振臂独起,向宗法至上、王权至贵、父权至尊、男权横行的传统社会结构、家庭统序、权力组织、意识观念发起实质性挑战,“倡女权、兴女学”,为中国女性改变数千年来被压迫、被歧视命运的华夏第一校,从推动中华文明的进步、增强炎黄文化的活力讲,功莫大焉。所以,仅就溯源缕流的角度看,河北师大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可数的跨世纪百年大学中的一所,而且是中国跨世纪百年大学中创办新式女校的第一所。这在整个华夏民族的近代化历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民族,没有女子的近代化就不会有母亲的近代化,没有母亲的近代化就不会有家庭的近代化、更不会有新一代的近代化,没有家庭的近代化和新一代的近代化就不会有整个社会的近代化和全民族的近代化。而尤其对于华夏民族言,女性的启蒙、醒悟和近代化是整个民族近代化的基础。河北师范大学在她幼小的心灵中、鲜活的血液里、稚嫩的躯体内、单薄的肩臂上就孕育和承载着启蒙女性、唤醒母亲、觉悟全民的圣神使命。而作为一个符号,使这个圣神使命变成现实、开始落实的第一个代表人,就是傅增湘先生。
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虽然潮流继续以变革为主导,而且革命的呼声越来越高,但是腐朽势力仍然很强大,旧的堡垒仍然很坚固。所以尽管由皇帝牵头搞“新政”,也摆脱不了夭折的命运。即使一批精英们奔走呼唤,兴办新学,实际是旁观者多、怀疑者多、鄙视者多,真正响应者少,参与者更少。而傅增湘主动放弃安稳的幕僚之职“而专营学事”,不仅要兴办新学,难能可贵的是兴办女子新学,要为几千年来被歧视、受压迫的华夏女性觉醒、自主、自由、独立而开山辟路。1902年他顺应政府《壬寅学制》的新政潮流,毅然就任“天津女学事物总理”这一新鲜而又艰难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创办中国新式女学的事务中,190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所新式女子公学——天津女子公学,第二年接着创办了天津高等女学堂,第三年为了迎接新式女学热潮的到来、提前储备女学师资而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公立女子师范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第四年由于在天津兴办女学业绩卓著,用傅先生自己的话讲是“粗有声绩”,被张之洞点将,“为女子师范学堂总理”,入京不久创建了京师女子师范学堂。这四所女子学堂就像是傅先生的四个亲生女儿,当然,投入心血最多,最受他宠爱的是北洋女师范学堂。后来天津女子公学和天津女子高等学堂都并入了北洋女师范学堂,可以说是这种偏爱的一个结果。所以说,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和男子一样在社会中为自由与独立奔走呼告,从教育唤醒的角度看,北洋女师范学堂功不可没。而北洋女师范学堂在近代唤醒华夏女性方面能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则傅增湘功不可没。
说起近代中国新女性,常常首屈一指女侠秋瑾。当然,秋瑾是近代中国新女性的典型代表。但事实上,如果非要“首屈”,应该至少是“二指”,那就是除了秋瑾,还应该有吕兰清。吕兰清与秋瑾有非常相似的早年经历,都出身书香之家,具有叛逆性格和独立思想,青少年时就摆脱家庭束缚,从封建堡垒中冲杀出来,独闯社会。吕兰清凭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认识到中国的迫切问题,也是根本问题,是唤醒全民的觉悟,尤其是女性的觉悟更紧迫;提高国民的素质,尤其是女性的素质更急切。因此,她以犀利的笔锋向戕害妇女的旧制度宣战,提出“欲求强种者,必讲求体育。中国女子不惟不知体育为何事,且紧缠其足,生性戕伐,气血枯衰,安望其育强健之儿!”她向全社会大声疾呼“若女学不兴,虽通国遍立学堂,如无根之木,卒显之效”。所以她认为中国当时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兴女学、倡女权、破夫纲”。“女学之兴,有协力合群之效,有强国强种之益”,能够真正收到塑造新人格、创建新人生、开辟新局面的效益。新局面出现,旧枷锁自断。“自强之道,须以开女智、兴女权为根本”[3]。所以,吕兰清的重点所在乃是倡女学、兴女权、开女智的立新一面。如果说秋瑾是武斗之侠女,那么吕兰清则是文战之巾帼。她们虽形式不同,道路有别,但在解放女性、唤起国民、振兴民族、富强国家等方面志向相同。吕兰清明确表示愿以此生“任文字之役”,为女性的觉醒、自由、独立而奔走。她的这些奔波与呼唤召唤起一批又一批的巾帼英雄,她们在争取自由与独立的同时,投入到改造社会、振兴民族的大潮中,成为20世纪叱咤风云的一股生力军。
其实在创立北洋女师范学堂之前,吕兰清早已是傅增湘的老搭档和得力助手,共同的志向与事业追求使他们走在了一起。早在1904年傅增湘创办我国第一所公立女子学校——天津女子公学时,吕兰清就被聘为总教习,主持教务工作,一直到1911年女子公学并入北洋女师学堂(不久,高等女学堂也并入北洋女师学堂)。1905年,傅增湘创办天津高等女学堂,吕兰清当然又是主挑大梁。当大家越来越觉得兴女学必须配备足够的女教师时,创办女子师范学校、储备更多的女性师资便成了他们的一致想法。为此,他们将更多的精力与心思投入到了北洋女师学堂,结合此前创办女子公学的经验,成功开创了我国官立、公立女子师范教育的先河。1916年随着时代的变化,已改名为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原北洋女师范学堂提出了“勤朴、奋勉之‘诚’”与“娴婉、爱敬之‘淑’”的校训,内中虽然有封建妇德规范与束缚女性的残余,但更多张扬的是女性走出家庭,求新知、找自由、争独立,通过勤朴、奋勉,争取自主、自立,以娴婉、爱敬的品格实现平等、获得尊重。当然,到了1933年,已经升格为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原北洋女师范学堂总结出新的校训:“崇实明理、守法合作”。这是对北洋女师范学堂以来办学宗旨、办学精神的提炼和升华。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要提到当时在任的,也是河北师范大学从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一直到今天120年的历史中一位任校长时间最长(33年)的齐国樑先生(1883-1968,号璧亭,山东宁津人),他于1916年1月至1948年8月先后连续任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的校长与院长,1922-1926年齐校长留学美国虽另派代理校长,但他的校长职位仍保留直到其回国。他在出任校长前曾两次留学日本,学习时间超过4年,获得广岛高师学士学位,怀着男女教育平等,而女子教育对于当时的中国又有特殊性和紧迫性的先进教育理念走上校长岗位。他“极力提倡实用教育”,“以为办理女子教育,必以家事为主”,“设立家事专修科以培养中等女校师资”①,从而开创了中国最早的新式家政学。创业艰难,更何况当时国家贫弱,既无独立,又无主权,又何以顾及家事、家政。所以经营惨淡可想而知,但他信念坚定,矢志不渝。为了把这件事做成,他于1922年至1926年间两次赴美国,在斯坦福大学教育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从专业理论层面进一步完善自己,并在回国后的第三年向当时的河北省政府提案设立家政学院。提案虽没能被接受,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从此在国内大学中第一个有了家政学系。这种务实理性、敢为人先的精神便是北洋女师范学堂的一贯精神。从傅增湘、吕兰清到齐国樑等,无论是北洋女师范学堂,还是河北女子师院,他们在求真创新、崇实明理的宗旨持守、精神追求方面一以贯之。
二、“怀天下,求真知”,传承一种文化
大学是汇聚精英、培育人才的场所。办好一所特色鲜明且对社会有益的学校,首先要拥有一支包括管理层在内的优秀教师精英班底。而一所被社会认可的好学校不仅要具备师资精英的强干,更主要的是能不断培养出可堪大用的人才。育人的精英与被培养的人才构成了一所大学的主体。这一以人为本、崇尚理性、学术神圣的主体,便是一所大学的本位。主体本位的确立、壮大,和不断衍生,就是一所大学生命历程的展示。当我们从顺天府学堂、北洋女师范学堂入手,紧扣主体本位之核心,梳理精英人才的成就,自然就会感受到河北师范大学师生百年血汗浇铸“怀天下,求真知”的坎坷历程和灵魂升华。
顺天中学堂自1902年秋天创办以来伴随中国社会动荡巨变的潮流、与民族命运的脉搏同步跳动、适应着不同时期生存发展的环境,先后经历了顺天高等学堂、京兆公立一中、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学和河北省立北平高级中学、河北师范专科学校、河北师范学院,直至1996年5月合并入河北师范大学,坎坷辗转,艰难前进。
草创初期由于有诸如陈璧(1852-1928,字玉苍、佩苍或雨苍,福建候官人)、王劭廉(1866-1936,字少荃,天津人)等的开明绅士、新学名流主持和任教,所以顺天府学堂起步就在一个高而坚实的平台上。作为真正创始人的陈璧是晚清政要中一位思想开放,行动果敢,办事能力极强的官员,在实业、教育方面皆有卓越业绩。他在户部侍郎任上办天津币厂、设大清银行(中国银行前身),在邮传部尚书任上规划路、电、航、邮四政大纲,并创办交通银行,电报国有,将收回京汉铁路管理权所得余利修建京张铁路等。他虽然是旧科制出身的进士,但是思想观念不保守,嗅觉敏感,视野宽阔,对新潮事物极有兴趣。早在戊戌变法以前,他联络乡贤林纾、陈宝琛等在福州将旧书院略加改造,创办了一所新型学校——苍霞精舍。这是福建省最早设立的兼习中学、西学的新式学校。苍霞精舍设在林纾旧居,招收学生50人,开设中文、西文两类课程。中学课程在经史的基础上加开实务、策论,西学设英文、日文、算学、地理等课,以新式的教育方式培养新型的实用人才,“闽中学风为之一变”,“实开风气之先”。正是这样一位对现实有切身感受,对问题有解决办法,在旧体制内有权威影响,对新事物敢大胆尝试,对新教育积极提倡的绅士,把他的维新思想、新政理念——务实、创新、求真、奉献落实到创办管理顺天学堂的过程中,渗透到师生言行的活动中。
如果说陈璧作为创建者与管理者,其形象体现的是办学的目标和方向;那么名流王劭廉作为洋文总教习,当然就是学堂新学内容的典型代表,也就是学堂办学目标和方向获得具体落实的保障。王劭廉于1886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第一期毕业,是当时学堂总办严复的得意弟子,毕业后即被派往英国格林海军士官学校深造。他在英先学造船工程,后又专研法律政治,学成归国后受到李鸿章重用,任威海水师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教习,讲授英文、数学等课程。他教学认真,教授得法,师表在先,要求严格,深受学生爱戴。1902年受北京五城御史陈璧邀请,任五城学堂(北师大附中前身)洋文总教习。不久陈璧升任顺天府尹并创办顺天府学堂,王劭廉兼顺天府学堂洋文总教习,总领“五城”“顺天”两校英文、算法、格致、体操诸学科教席,是当时北京城有名的“西学”教师。后来著名学者梁漱溟(1906年至1911年在顺天府学堂读书)先生回忆“那时每一班有一专任洋文教习,所有这一班的英文、数学、外国地理都由他以英文原本教授。这些位洋文教习,全是天津水师学堂出身,而王劭廉先生的门徒……他们秉承王先生的规矩,教课认真,做事有军人风格”[4](P24-25)。可见以王劭廉为首的新学教师在当时的影响力之大。当然,他在后来中国新教育建制方面有更大发展,如1906年奉命离开顺天府学堂,赴天津接任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总教习(不久改称教务提调)长达9年,历经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和民国成立这一动荡时期,开创了中国人管理近代完全新式大学的先河。北洋大学堂的创办人是盛宣怀,创办于1895年甲午战败之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完全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最初的名字叫北洋西学学堂,其办学思想对“中体西用”有所突破,积极倡导“西学体用”。王劭廉到任后,不仅维持了全新西式办学传统,并开创了北洋大学堂的新局面,对北洋大学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无论在顺天学堂,还是在北洋大学堂,王劭廉都以矢志于教育事业而闻名。他学兼中西,能根据中国学生的特点讲授西学,是著名的教育家,又能结合中国人文精神、民族性格严格要求教师学生,有很强的责任心,有很丰富的管理学校的经验,无论在顺天还是北洋,都促进了学校良好风气的形成,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1909年,清政府因其“兴办教育持久”特奖予进士出身。他虽然获得的是个旧式的荣誉,但承载这个荣誉的却是杰出的新功(王劭廉还先后担任直隶学务公所议长、天津县议事会副议长、直隶咨议局局长、教育部教育会议议长等职,为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提出过不少的议案)。正是有以王劭廉为首的这样一批杰出精英的具体操持、倡导和奠定基础,顺天府学堂在开基立业之初孕育出求真创新、务实奉献的精神,这就是今天河北师范大学“怀天下,求真知”的根底。
尽管在这个祖制尊严、新生难产的传统型社会里,新式学堂面临生存的艰难,但绵延几千年的华夏文明自身同时具备绝处逢生、多难兴邦、从善如流的文化基因,看似强大的腐朽永远扼杀不了新生突围的活力,多难的时代必陶铸出兴邦的干才。从世俗庸常的观点看,学堂不读圣贤之书,而学“雕虫之技”“夷狄之文”,对于大多数士绅家庭和普通民众来说,或者是不予理睬,或者是迷惑不解、猜疑质问,更甚者认为是背祖胡闹、坚决反对。所以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人对新学持观望、质疑态度,甚至持鄙视、反对立场,这并不奇怪。但是“生生之谓易”“日新之谓盛德”,崇尚“新生”也是易学以来中华文化本身具备的代传不息、历久弥坚的一个传统,而这个传统往往是被少数的民族精英所传承,从而构建起炎黄的脊梁。精英们创办了新式学堂,少数眼观远大、思想开明、敢担当、有使命的家庭、家长把子弟送入新学堂读书。这就决定了早期的学堂集中了一批好学上进、求真创新、挑战传统、淡于名利,对新事物非常敏感的少年才俊。有什么样的土壤和根基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树干。顺天学堂是一片新天地,超越时代的一批精英召唤、聚集了一群时代新秀。因此不需要“百年树人”,在顺天学堂汇聚和从顺天学堂走来的一群英才很快就成了在20世纪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其中最杰出者当数梁漱溟、张申府(崧年)、汤用彤,以及郭晓峰、甄元熙、荣高棠、康世恩、王蒙等诸君。这里我们只选梁漱溟,点数其在20世纪的几件行举,进而感受当今师大“怀天下,求真知”校训的渊源所自、基因之本。
梁家因漱溟先生曾祖考中进士而由桂林始宦游北方,到他父亲时仍然官至清廷内阁中书、候补侍读,是典型的书香官宦之家。而家庭成员中对梁先生最有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我之所以能如此者,先父之成就我极大”[4](P55),“凡事认真,讲求实效,厌弃虚文,同时又重侠义,关心大局,崇尚维新。因此不要求子女读四书五经,而送我入中西小学堂、顺天中学堂,习理化英文,受新式教育。这在我同辈人中是少见的”[4](P1)。家庭是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启蒙老师。虽然其父对他是“信任与放宽态度”,但身教胜于言教,这种和风细雨的感化与尊重选择的宽松,正好培育了他积极健康的“向上心”。而当他14岁进入顺天学堂之后,这里的建制环境、教学内容、师生举止融汇在一起,形成了在社会上难以找到的人文氛围,再加上这里得天独厚的课外读物为之了解社会、跟上潮流提供了便利条件。他利用课外时间,对《新民丛报》《新小说》《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进行了认真研读。从而“促使我自中学起即对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追求不已”[4](P2)。
顺天学堂五年多的学习生活中有两位同学对梁先生影响极大。一是郭人麟,年长他两岁却比他低一年级。当时梁漱溟以胸有救国救世、建功立业之志,重事功而轻学问,孤傲自负,冷僻自高。“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他于老、庄、易经、佛典皆有心得,而最喜欢谭嗣同的‘仁学’。其思路高于我,其精神亦足以笼罩我。……我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课暇就去请教,记录他的谈话订成一巨册,题曰‘郭师语录’。一般同学多半讥笑我们,号之曰‘梁贤人’、‘郭圣人’。”“自与郭君接近后,我一项狭隘的功利见解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在我的思想上,实为一绝大转进”[4](P31)。可以说,梁先生对于人生问题的追求与郭同学的影响有极大关系。
另一位同学甄元熙,是后来插班成为梁先生的同班同学。梁先生回忆说:“甄君是(1910年)从广州、上海来北京的,似先已与革命派有关系。我们彼此同是对时局积极的,不久成了很好的朋友。但彼此政见不大相同。甄君当然是一革命派。我只热心政治改造,而不同情排满。在政治改造上,我又以英国式政治为理想,否认君主国体、民主国体在政治改造上有什么等差不同。……后来清廷一天天失去人心,许多立宪派皆转而为革命派,我亦是这样。中学毕业期近,而武昌起义。到处人心奋动,我们在学堂里更呆不住。其时北京的和天津的、保定的学生界秘密互有联络,而头绪不一。适清廷释放汪精卫。汪一面议和,一面与李石曾、魏宸组、赵铁桥等暗中组织京津同盟会。甄君同我即参加其中,是为北方革命团体之最大者”[4](P32-33)。由此可见,梁先生在社会改造方面由宪政改革到革命改造的立场变化与甄元熙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中学时期的关注现实、用心读书和师友切磋让梁先生梳理出“两个问题”,并由此入手开始了他一生的探索。他认为,“从人生之追求,使我出入于西洋哲学、印度宗教、中国周、秦、宋、明诸学派间,而被人看作是哲学家。从社会问题之追求,使我参加了中国革命,并至今投身社会运动”[4](P26)。从追求人生真谛的角度,梁先生起手于《究元决疑论》的探索,徜徉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比较,倾心于《中国文化要义》的阐释,而最终得出《人心与人生》的结论。由历经危难现实的感受,“便体认人生唯是苦,觉得佛家出世最合我意,茹素不婚,勤求佛典,有志学佛”到投身新潮涌动的大浪,突破小我的情感痛苦,在淘沙的时代浪潮中用理性“把西洋、中国、印度不相同的三大文化体系各予以人类文化发展史上适当的位置”,“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4](P46)。“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4](扉页),这种心力宏愿最终使梁先生在人生问题上得出了人心主导人生的结论。
至于探索社会出路、民族前途的问题,虽然是在顺天学堂正式理出思绪,其实这种怀天下的胸襟此前已经深受其父熏陶。梁先生虽也是科举出身,但最看不起坐而论道、咬文嚼字的文人,而趋向维新务实、看重果断干练的事功之人,所以其启蒙教育不是传统的圣贤之书,而是略述天下规模、世界大势的《地球韵言》。实际上,他最喜欢读且受影响最大的是关心时事、揭露现实、鼓吹社会运动、介绍世界大事的《启蒙画报》。以上这些都是后来他进入顺天学堂梳理出“社会问题”的重要积累。关于民族出路问题,他在顺天学堂曾经历了由倡导保留清廷、推行宪政体制到倾向革命、参加京津同盟会的转变,进入社会之后,目睹辛亥革命后的一系列严重的、令人失望的社会问题,使自己在痛苦的摸索中超越了具体的、现实的和本民族的问题,撰成《社会主义粹言》一书。在社会问题上的艰难探索,加上在人生问题上更是无法突破,一时使他难以从极大的痛苦中摆脱出来,于是萌动了出世为僧的念头,前后长达近十年。然而割舍不断的怀天下的情结最终使他探索出了一条自认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努力为之奋斗,这就是“乡村建设”。梁先生认为,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必须是以农民问题与乡村问题的解决为前提。而农民问题与乡村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和完善“团体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经由农民的生产合作而建立起来的团体自治的合作社组织,一定是借助于将科学技术引入农村、介绍给农民、渗透到农业中的路径来实现。所以“团体组织”与“科学技术”是梁先生乡村建设运动的核心。因为他“认定北伐后,老社会已崩溃,只有理清头绪来建设新社会,没有再事暴动破坏的必要”。“从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4](P155),是他当时持守的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信念,这些集中体现于他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等论著中。用建设完成革命,靠进步达到平等,而且看到中国社会问题的重头就是农民与乡村的问题,中国社会绝不同于欧美靠侵略与扩张贸易推进社会发展,而主要是靠提高农民素质、完善乡村建设来实现国家的富强与民族的复兴。这些观点,时至今日仍很有价值,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日本侵华,抗战爆发,在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梁先生从大局出发,积极奔走于联合抗日、统一建国的事业中。1938年年初,他亲赴延安考察,1939年2月开始历时8个月的巡历华北、华东各战地,接着为了减少和避免国共联合中的对抗、冲突,维护全民族统一抗战而投身于统一建国同志会、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三方努力中,并亲赴香港创办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抗战胜利之后为避免内战、实现统一建国,他代表民盟参与国共两党和谈。总之,关于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就像他关于人生哲学问题一样,虽历经坎坷,但追求一生。可以说怀天下而求真知是对梁先生一生活动的最简约概括。
北洋女师范学堂前有傅增湘、吕兰清等筚路蓝缕、鞠躬尽瘁底定其成,后有张伯苓、齐国樑等续善其后,“崇实明理”、敢为人先的精神代代传承。从管理和教学的层面看,一批批精英为中华女性的觉醒、自主、自由、独立而奔走呼唤;从学子与人才的培养看,于是便有一大批时代的娇子、华夏的巾帼聚拢起来、成长起来,她们用北洋女师的精神点燃了中华崛起的烈火,不仅使自己成为涅槃凤凰,而且为同胞姐妹们开辟出了一条新生的光明大道,成为华夏女性挣脱几千年封建枷锁、走出家庭、步入社会、获得自由、享受独立的开路先锋。从北洋女师到河北女师,一批批的才女们用她们的生命谱写出了20世纪华夏女性辉煌的篇章。从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一直到张志新,她们为了心中的真理,为了民族的复兴,不怕牺牲,历经磨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她们的精神追求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宝藏。
这里有不尽的营养补给、生命源泉,相信在新的时代中、新的师大里,有先辈精英、娇子一个多世纪积淀、孕育出的“怀天下,求真知”,无论是精神的激励,还是文化的传承,都将结出河北师范大学的新硕果。绍续天下一家之道统,弘扬求真致用之学脉,尊师贵道,尚真创新,在21世纪中华民族强大崛起、中华文化全面繁荣的时代展示出自己的风采。
注释:
① 转引自戴建兵等:《齐国樑文选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