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堂激情澎湃的倪氏语文课
陈娟 黄先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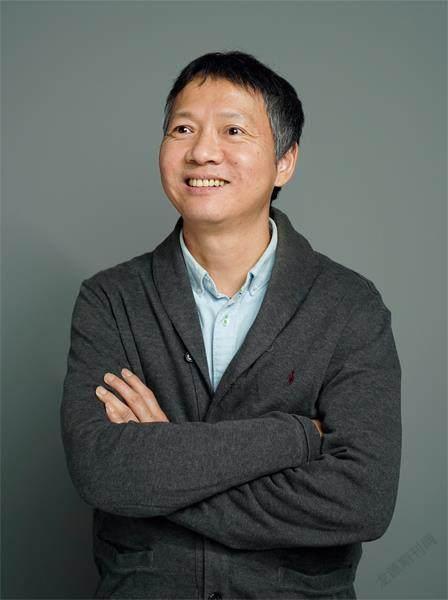
倪文尖
1967年生于江苏南通,華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编《新课标语文学本》等系列助学读物,著有《欲望的辩证法》《倪文尖语文课》。
12月5日午后,上海的天有些阴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倪文尖老师去上海曹杨二中上了一堂语文课,讲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这部发表于近百年前的小说,主人公是吕纬甫,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热血青年,后来变成了意志消沉的文人。在以往的解读中,大都认为吕纬甫是一个鲁迅投射了反思和批判目光的人物,而小说叙事者“我”,则更多地代表作者鲁迅的立场。
倪文尖却不这么讲。他努力摆脱以往的定见,带着学生进行了一场“尊重普通读者的阅读原初感觉的精读”。
他分析小说中吕纬甫讲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他千里迢迢回故乡,为3岁就死去的小弟迁坟;一个是他给当年邻居女孩顺姑送剪绒花。“吕纬甫讲得那么详细,甚至有点婆婆妈妈,在小说中占了那么大篇幅。”倪文尖说。停顿了几秒钟。
“吕纬甫和他讲的故事特别重要的话,鲁迅为什么要颇费周章地这么写:先写‘我’、写两人相遇,再由吕纬甫讲出故事来呢?”倪文尖问同学也问自己。他双目炯炯有神,声音铿锵有力。 “其实我也未必有确定答案,而我能肯定的是,吕纬甫的讲述里有一种深情,小说笼罩着怀旧的感伤。”带着学生细读文本后,他指出,“吕纬甫身上有鲁迅的影子”。
这堂课一如既往地受欢迎。课后,他被一群高中生围在中央,有的抱着《新课标语文学本》,有的拿着作业本,等待他的签名。
不仅高中生喜欢倪文尖的课,他更是B站“超火”的名师——700万人爱上了他的语文课。
倪文尖告诉记者,在B站讲课,缘于一帮年轻人的动员和“软磨硬泡”。几年前,他们找倪文尖开视频课,他的第一反应是谢绝,“一是懒,一是也有些清高”。直到前年岁末,有学生讲到自己在贵州贫困地区的见闻,然后对他说:“倪老师,你就把给我们上课讲的东西讲出来,由我们来借助互联网让更多人听到,尤其是那些偏远地区好学的年轻人。”
听完这番真诚的话,倪文尖不再推却,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踏上了网上讲课之旅。
他把视频内容主要聚焦在语文教材中的现当代文学名篇名家。如朱自清《背影》、鲁迅《祝福》、史铁生《合欢树》,等等。每次讲课他都花大量时间精力准备,“我要把论文写在B站上”。
“我是半开玩笑半当真说的这句话,我感觉找到了写作发表的另一种形态。要像写论文一样把力气用足,用做学术的态度做视频。”倪文尖说。
最先发布的视频,是给华师大二附中学生讲废名的名著《桥》中的一节《花红山》。废名“像写绝句那样写小说”,被认为是新文学作家中最难读懂的。那节课,倪文尖像往常一样,拿着保温杯走进教室,在黑板上写下“文学何以是语言的艺术”,这是他讲《花红山》的最高目标。之后,他带着大家逐句拆解,参悟文学和语言的艺术,一步步走进废名描绘的花红山中:花很多,花很艳,艳阳高照。
“这是废名虚构的花红山……是作者主观的表达……只有这么写、必须这么写,废名的花才多得像废名的花……”倪文尖越讲越激动,挥舞着手臂,说:“文学就是虚构!文学就是无中生有!文学是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在这样的“语文课”上,倪文尖陆陆续续讲了好多篇名家经典。他以文本为中心,倾力把文本读透、读通。不少人最直接的感受是“豁然开朗”“好像从未读过这部作品”。

2022年12月5日,倪文尖(左一)到上海市曹杨二中讲课。

倪文尖讲《花红山》视频截图。
他讲鲁迅的《祝福》,剖析祥林嫂之死,既真的是“穷死”的,也是死在鲁镇的社会和文化里,“对祥林嫂还要‘怒其不争’就太可怕了”,因为她做出过不少抗争;他讲《荷塘月色》,称荷塘是朱自清创造的另一世界,是他因为心里颇不宁静而转移注意力后,有关“自由”的想象与写作……
除细抠文本、视角新颖外,倪文尖讲经典自有他独特的味道。这味道源自他的语言,浅显、直白中蕴含着深刻的道理,还有种幽默,再加上他声情并茂,“像是一场表演”。他在B站开设的“语文名篇重读——现代文学系列”由此引爆网络,收割了大批粉丝。
火了之后,既是同事又是好友的罗岗一半戏谑、一半认真地给倪文尖封了个雅号“倪大红”。另一好友毛尖,则调侃说,“B站观众应该能够感觉到老倪上课的那种投入,他在上课中投入的荷尔蒙比他投在爱情里的还多”。
倪文尖讲课,非常注重与学生的互动,在B站也是如此。他经常看弹幕和留言,“核心观众一部分是语文教师,要为他们提供教学资源,开阔视野;其次是中学生,视频可作为语文课堂的补充;此外,如果有一些观众自觉没有接受过很好的语文和文学教育,也可通过这一系列视频来补课。”
倪文尖觉得“语文比天大”,语文课很重要。他至今还记得自己曾遇到过不少优秀的老师。他的父亲是文学爱好者,潜移默化之下,倪文尖打小也喜欢文学。1979年,他考进南通中学,遇到了语文老师汪根弟。有一次,他写了篇以父亲练毛笔字为题材的作文,结尾处夸张地说“父亲写的‘人’字昂首阔步”,交上去后忐忑不安,没想到汪老师给了90分,还在班上读,“一下子就对写作更有信心,甚至也从此偏科”。
1985年,倪文尖被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一路读到博士,师从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当年,钱老师家的客厅和书房,就是研究生们的教室。大家自由自在地聊天,有时有主题,有时漫无边际,“学生有时比老师话还多,相互启发讨论,热热闹闹”。
但在做学问时,钱先生又很严厉。有一次,倪文尖交的論文,老师要求推倒重来。“钱先生说,做学问,第一求真,真的是自己。你是有自己想法的,表达出了真,自然就能深,真的深了,就会新。”这些一直影响着倪文尖,他后来一直“求真”“立诚”,无论做学问,还是做人。
1996年,倪文尖博士毕业,留校任教,一边教书,一边做文学研究。他热爱课堂和学生,不那么热衷著述,“写得很少,注意环保”。他将上课当成一门艺术,一般没有讲稿,时有即兴发挥。即便是往年同样的课,依然会下功夫重新备课, “那种激情澎湃,循循善诱……乃至通过自己的表演,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创造力,为的是学生领悟出自己的答案来”,有同事旁听他的课后说。他自己也说每上一次课,精力、体力都耗费极大,“下课后回到家,什么也不想做了”。

倪文尖(右)和导师钱谷融合影。
倪文尖重视文本解读乃至后来做语文研究,开始于1997年。那年夏天,他到桂林参加一个读书会,细读研讨现代抒情小说。其间,会议组织方广西教育出版社李人凡总编说想出一套普及性的文学读物,后来确定做中学生导读本。
当时,倪文尖分到了20多篇散文,他一篇换着一篇读,怎么也读不出新意来。直到有一天,他一拍桌子,“有了!”他对《背影》有了新的理解。“一方面是压力使然,一方面是我非常崇拜的父亲老了,他做了爷爷,而我也做了父亲。”这次读,他读出《背影》的背后是一个纠葛的父子关系史,写《背影》也是朱自清与父亲和解的过程。就这样,倪文尖对《公寓生活记趣》《祝福》等文章,一一点评、批注。
四五年后,倪文尖又独力主编了《新课标语文学本》初、高中卷共17本,从此“走上了不归路”。他参与了不少国家语文教育的顶层设计工作,如参与编写初中、高中语文统编版教科书,他还与王荣生、郑桂华等合作编写《国家课程标准高中实验课本(试编本)》,参与主编《大学语文》等。不久前,他出了《倪文尖语文课》,书里既有这些年细读经典之所得“文学课堂”,又有对经典名篇“字里行间”的批注。“我努力以‘既不在门外,也不在门内’的姿态,关注并投身于文学与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
“天南地北,全中国无数的语文老师后来成了老倪教学法的信徒。”毛尖在《老倪》一文中写道。


2021年9月,倪文尖(中)参加《明暗之间:鲁迅传》新书发布活动。
我觉得学语文既要无功利心,又要有功利心。这就像是说,手是我们的工具呢,还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你要做一个中国人,说起李白、杜甫、鲁迅,你一点反应也没有,这怎么行?说得玄乎一点,语文是无用之大用。
我理解的“语文”,不是小儿科,而是大智慧,不该在“工具性”和“人文性”上一直纠缠不清,而应在“如何做一个中国人”和“如何做一个有创造性的人”相统合的高度上重新定义、重新出发。
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学习语文?我的建议是,首先上好语文课,然后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在学校里自觉学时,那还得有虔敬之心——对祖国语言文字的虔敬之心,对人文经典的虔敬之心,对人与人之间表达和交流的虔敬之心。
这实际上是一种“语义磨损”的现象。所谓“语义磨损”,指的是词语使用时的意义与词典义相比程度的弱化。语言学家吕叔湘早在1947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就提到,一些表示程度的副词如“很、怪、太”等,“一切表高度的词语,用久了就都失去锋芒”。
语文的范畴应是大于文学的。我们在生活着也就是在语文着。比如说我们如何读新闻,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媒体爆炸的时代;再比如说如何写请假条。很大程度上学语文,学的还是语言文字运用。“社会运用”在我的一贯认知里,是和文化传承、精神修养、现代思维、语文才能同等重要的“语文素养五棵树”之一。
而文学,就像我在课里说的,给我们的世界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它更新了我们原本已经被磨损了的、日常化了的、实用化了的、无趣的、无聊的、乏味的世界。
我所说的经典是宽泛的。不同的时代,经典也会有不同的意义。比如说鲁迅,不同的时代能读出不同的内容。比如说今天,我觉得甚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或者之前的一些作品,也是经典了。
好的文学或者说文学知识,不在文学理论里,而是在文学作品里。文学知识存在的方式,就像盐溶于水一样,是融在文学作品里,尤其是融在经典里。为什么要读文学、读经典?就是前面说的,文学给这个世界打开了另外一扇窗。
1967年生于江苏南通,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主编《新课标语文学本》等系列助学读物,著有《欲望的辩证法》《倪文尖语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