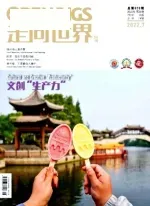《上海新报》四任主编的殖民意识和新闻倾向
王雅鹃
咸丰11年10月24日(即1861年11月26日),字林洋行创办了《上海新报》。创刊时是周报,每周一期,英文名称是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Advertisers,直译为《中文船期广告纸》。1862年5月7日起,每周逢周二、周四、周六出版3次,1872年7月2日改为日报。《上海新报》的诞生时逢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的相关新闻报道一度成为《上海新报》的热点。作为一份在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势力,迎合西方各国在华商人商业需求的报纸,它从一开始对言论的不重视,到连载长篇言论《逆寇略论》,这种转变体现了怎样的传播策略?认真解读《上海新报》有关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新闻报道,客观分析《上海新报》的立场与新闻倾向,以及它后期对维新革命、洋务运动、西方科学、国际法、民风民俗等,都发表过重要的、长篇的和连载的讨论,这些内容从目前主流的报刊史评价中,可以认为它客观上推进了中国迈向近代文明进程。但作为近代世界资本主义以及英美西方列强殖民语境下的报纸,它的报道视角与新闻倾向究竟如何?
近代新兴报纸的发展,推动了全球帝国主义和殖民化,按照近代英国报刊的描述,英国的殖民行为,是为野蛮人和荒凉之地带去文明的高尚使命,是勇于开拓涉险的动人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军事上的胜利是因为个人勇敢的行为而非先进的武器。这种论调是在炫耀大英帝国在全球的统治地位。维多利亚时代,最受欢迎的日报《每日邮报》( Daily Mail)在一篇报道中激动地写道:
我们把子弟派遣到四面八方,他们掌管着蛮荒之地,教导当地的蛮夷行军射击,让他们服从他、信仰他,愿意为他和女王而牺牲。别人说我们是平庸、愚蠢、木讷的民族,我们却一直在各个地方为各种各样的野蛮人做着这样的好事。
《上海新报》四任主编均来自近代报刊繁荣发达的英美国家,大众报刊(便士报)在他们来到中国之前,就已经在其所在国家成为一种普遍的媒介存在,在舆论影响、广告营收率、信息普及化等方面,已呈现出“第四种权力”的巨大影响效力。传教士主编新闻倾向上强烈的“舶来”性质,透露出世界资本主义和基督教观念遮蔽下的殖民意识与帝国观念,以及英美宗教与世俗社会近代观,这些深层意识构成了其报纸报道框架,并且由此报道中国事务。
《上海新報》从一开始对言论的不重视,到连载长篇言论《逆寇略论》,这种转变体现了传教士及《上海新报》的西方资本主义利益与殖民化目的。
据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b Roberts)回忆,洪秀全、洪仁玕曾先后到他处“学道”。太平天国运动以宗教的旗帜在晚清中国曾一度所向披靡。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初期,大多数基督教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抱有期望,希望能在中国大开自由传教之门。用艾约瑟(Joseph Edkins)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个革命运动是大有利于基督教的”,但当他们发现这个政权不能达到他们传教的目的时,态度随之改变。理雅各(James Legge)归结为:
当1853年占领南京后,此革命运动初露锋芒于世上之际,传教士中许多人因该运动的领袖们所颁发的书籍和文告中所表现的基督教感情而欢呼称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这些运动所许诺的花朵逐渐枯萎而死时,他们产生的悔恨一如初期的希望。
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运动态度的调整与变化,深刻还原了以基督教为旗号的英美国家在晚清中国的殖民策略与计划。包括罗孝全、林乐知也都经历了从期望到失落的过程。
1859-1860年,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到南京协助洪秀全总理太平天国政务时,香港、上海、南京、宁波各地传教士纷纷给洪仁玕写信,或亲自到南京想与他会晤。对大多数传教士来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能在中国本土自由传教,不受清政府的各种限制,而太平天国正好以基督教教义作为政权支撑的理论武器之一,他们想从这个角度打开对中国宗教的影响。正如杨格非(Griffith John)说:“我的目的是要从太平天国首领处获取一份宗教自由的诏旨,我已领到这份诏旨,完全准许传教士到起义者的地区居住和传教。”这是杨格非在南京会见干王提出的要求,他获得了幼天王以天王的名义颁发的“宗教自由诏旨”。杨格非问干王洪仁玕:“这个诏旨是否把太平天国全部开放给传教工作?”干王回答:“是的,但必须遵守太平天国的法律,不可触犯 ‘天规’。” 杨格非在给英国伦敦会的报告写道,“我坚信上帝将借太平军之力扫除中国的偶像崇拜,上帝将通过他们联合外国传教士传播基督教以替代偶像崇拜。”“我完全相信,如果他们在江苏省境内建立了秩序,那么江苏省在20年内名义上就要成为一个基督教省份。同样的看法也可以用于所有其它各省。”慕维廉在南京一个月的访问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南京周围一带传播福音。但他希望外国传教士到中国自由传教的目的与太平天国高层的要求不一致,干王洪仁玕明确告诉他:“(关于外国传教士)天王不欲依赖外援,他认为中国人可以自己做这件事。” 慕维廉承认:“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我们之为我们已令其坚决自行其道了。”
罗孝全是美国基督教南浸礼会传教士,1837年来到中国传教。他先在澳门,1842年到达香港,1844在广州开设礼拜堂传教。1853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引起了传教士的极大兴趣,多数认为从此可以在中国本土大大扩展基督教的势力了。罗孝全想利用他同洪秀全的“师生关系”与太平天国建立联系。在洪秀全的几次邀请下,罗孝全终于在1860年10月到达天京。天王封他为义爵,任命他为外务大臣,辅佐干王洪仁玕,给予优厚的待遇。从此,罗孝全出入宫廷,以天王“宗教师”自居,宣传他的教务,还多次与宫廷官员进行辩论,企图说服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跟着他的宗教思路走。他不断向美国差会寄出在天京搜集的情报,鼓动国外差会趁此时机增派传教士到太平天国边辖区内活动。在天京活动一年后,他在1861年12月31日写给差会的信中表达对太平天国政权的失望与自己宗教抱负未成的失落:
他(指洪秀全)要我到这里来,但不要我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劝化人民信奉上帝。他是要我做他的官司,宣传他的主义,劝导外国人信奉他。我宁愿劝导他们去信奉摩门主义,或别种不基于《圣經》而出的于魔鬼的什么主义。我相信在他们的心中,他们是实在反对耶稣福音的,但是为了政策的缘故,他们给予了宽容。可是我相信,至少在南京城内,他们是企图要阻止其实现的。……我也看出我的传教事业是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了,也不再期望能容许有别的传教士和我一起在这里进行主的工作。因些我决计要离开他们了。……
罗孝全在这份报告发出后于1862年1月20日,从天京不辞而别回到上海,之后就开始在《北华捷报》上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太平天国领袖,攻击太平天国“只宣传‘政治的宗教’,而不准外国传教士传教”。
包括林乐知也是曾企图从太平天国打开一个缺口,推进传教事业。1861年,林乐知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南京,拜见了洪仁玕,但太平天国忙于对付清军的围攻,并未对林乐知的传教要求产生兴趣。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欲施加的影响不局限于宗教方面,他们的行动是“政治性”的,其步调也是和他们各自所属的政府相一致。总的说来初期是“拉拢”,接着在“中立”的幌子下“观望”,洪仁玕到南京后,又变成了“拉拢”,失败之后再转而拉拢清政府,对太平天国公开抱敌视态度了。
19世纪初,当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们怀着拯救世界的精神信仰来到中国时,他们与殖民者的步伐一致,而令他们尴尬的是,传教士们还不得不委身于殖民者的保护与资助。当时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的基本信条: “只有基督能拯救中国解脱鸦片,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传教士从来没有公开谴责过英美政府和英美商人经营这项毒害人民的罪恶贸易,相反地,“基督教传教士都不反对这种贸易,他们乘坐贩运鸦片的飞剪船到中国去,他们还从贩运鸦片的公司和商人的手中接受捐款。”第一位到中国的传教士马礼逊从英国转道美国,就是乘一艘鸦片船到达广州,最后隐藏在美国的商会里,进行着他“伟大”的传教事业。对于中国知识层对传教士那种复杂的心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先生是这样分析的:“传教士只是寻求与中国民众进行东西两种文明的直接沟通。……他们浸透到中国人民生活的深处,与所有的外国侵略者一同深深卷入中国的政治舞台。其间,为了取得家乡资助机构的继续支持,他们同时又是为西方公众有的放矢地广泛报道中国的外国人,这一活动的双重性留给他们的是历史的矛盾心理:在一部分中国人心里,他们是救世主,或至少是行善积德者,而在其他的中国人心里,他们却是文化帝国主义者。”随后西方传教士纷至沓来,第一个到上海传教的基督教传教士是英国人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他于1843年抵达上海。随后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和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等美国传教士于1845、1847年先后而来。他们在中国搜集情况,研究汉学,为英美国家殖民统治中国大肆进行着各类档案信息的反馈与储备工作,而鸦片对中国的危害,却认为只要中国人接受了基督,鸦片的危害也就自然会消失,而要使中国人接受基督,唯一的办法就是战争,“只有战争能开放中国给基督”,这就是传教士鼓吹使用武力和直接投入战争的逻辑 。
林乐知认为,外国入侵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能抵御的。他在《中东战纪纪本末》中分析:
西人志在通商,不愿天下有一地方示开,一物之未出,故先从温和带地面立足,其热带下之不可居者,亦必伸其辖治之权,如水之京下,不能以人事遏之也。传教亦犹之通商也。……
欧洲各国,类皆驰情于域外,虽以非洲之酷热,北极之严寒,我且图剖分而食之,造舟黾勉而赴之,矧以地处温和带下民殷物阜之中国,有不思染指于鼎,过屠门而大嚼乎?…… 夫他国以恃强蔑理之心,专欺中国,……其于中国,则日逼日近,日压日重也。且察其舆论,验其人情,又似出于不得不然,非有所矫揉造作也。呜呼!秋木时至,百川灌河,尚有朝潮夕汐,进退盈缩之一候,若夫各国之入中国,则竟如水之就下,有进无退,有盈无缩也,其孰从而御之哉!
林乐知的这些认知与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完全一致,切实成为殖民主义的鼓吹者和辩护士,英国在华殖民势力的喉舌上海《字林西报》对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大肆吹捧:
林乐知博士这部著作从文笔到观点已是达到可以称颂的顶点。……但愿该书所提出的原则和教诲能得到应有的传播(它们一定会得到传播),它们将对中国的政治的全部任务产生丰硕的成果。
对于宗教与科学,晚清来华传教士曾有自己的说法。他们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
科学没有宗教会导致人的自私和道德败坏;而宗教没有科学也常常会导致人的心胸狭窄和迷信。真正的科学和真正的宗教是互不排斥的,他们像一对孪生子—— 从天堂来的两个天使,充满光明、生命和欢乐来祝福人类。我会就是宗教和科学这两者的代表,用我们的出版物来向中国人宣传,两者互不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
从表面上看,传教士们提出了诸多改良主张,但是传教士提出通过这些变革所要达到的目标与洋务派、维新派根本不同,两者是有原则区别的。传教士们的目标是要中国变为某一外国或数个外国的殖民地,是为了更加便利于外国对中国掠夺而进行一些必要的变革。从林乐知的《万国公报》主要内容看,尽管它提出了很多变革方案,译述了种种“西学”,但根本确是要按照传教士提出的模式把中国逐步变为某一外国或几个外国统治的掠夺的殖民地。裨治文创办的《中国丛报》,记载了鸦片战争前后20年期间有关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语言、文字、风俗等多方面的调察研究,其中包括很多中外关系和外国人在中国活动的一手资料,成为英帝国对中国殖民侵略而准备的档案和各类信息储备。需要指出的是,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们在中国介绍西学、鼓吹中国改革的过程中,至死都没有放弃让中国基督化的理想。“他们追步利玛窦、汤若望的后尘,实行所谓学术传教,但他们又不像利玛窦那样钦佩中国传统文化,相反视西方基督教为文明的极致,因而鼓吹中国必须改革,那目标便是彻底西化。”
《上海新报》的传教士主编如何看待晚清中国社会,除了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直接关系外,从传教士的角度来看,如何发挥自己的主體性来办报是很自然的选择。秦绍德教授就明确指出:外国商人及传教士在华办报是“将他们母国所办报刊的那一套,设法搬过来,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从已有的传记和其它记录来看,传教士主编总体对中国的看法较负面,并且希望中国能大力提升跟上西方的思想与文化,但在自己主编的报纸上看,报道倾向又总体偏向中立。一般讲,传教士主编要通过主编的报纸表达自己的观点、价值取向和他要通过媒介所力图表达的对中国的看法。但事实上媒介的表达和他们真实的看法是不一致的。
傅兰雅1861年来到中国,1865年从北京京师同文馆转赴上海,担任英华书馆校长。1866年11月开始,在江南制造局当翻译的傅兰雅,因出色的中文水平,被字林洋行聘为《上海新报》主编。他一边办报一边翻译西方各类科学书籍,密切注意中国社会新动向,在报纸上配发新闻和评论,以期引起中国读者的兴趣。对傅兰雅来说,他在报馆里积累的翻译写作经验,确立了最初的声名,但他始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正如他所说:
名义上我是英国国教的一名成员,但在中国期间,我的宗教视野扩展了,所以我倾向于很自由的思想....... (Dagenais [1997])
傅兰雅的著(译)书籍对中国的科学普及和近代工业的发展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了28年,一生共译书129种,涉及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军事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当时,大多数中国人迫切需要的正是科学的基础知识,而有意识地、系统地从事这项工作的,傅兰雅为第一人。从一定意义上说,他的一些译著还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部分学科的奠基之作。例如,他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等书就成为中国近代化学的奠基著作。他所翻译的化学系列、国际法系列书籍和政治学书籍,都是19世纪中国所译西书中最有学术价值的部分。他的翻译工作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敬,也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1876年4月13日,清政府授予他三品衔,又于1899年5月20日授予他“三等第一宝星”。傅兰雅在中国所做的3件大事是:创办近代中国第一份专门性的科普杂志——《格致汇编》,参与创办近代中国第一所科普学校——格致书院,创办近代中国第一家科技书店——格致书室。傅兰雅在讲到其创办缘由时说:“近来格致风行,译书日广,好学之士,争览者多。惟以局刻家刻,购求颇艰,故设格致书屋,使人采取。”他将格致书室办成了中国科技书籍的集散基地,成为中国学生学习西学的圣地。
傅兰雅在中国工作生活30多年,对中国的科学教育程度非常关心,他感到中国的进步太慢:
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经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人最大的需要是道德或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眼前的危急。
对中国改良运动的最终目的他也不无遗憾,他认为中国人办理洋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启蒙中国,而是帮助中国了解外国人的一些情况,以便能成功地与他们斗争,最后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
作为一名传教士,傅兰雅并没有忘记自己的本行,但他的传教方式有所不同,他不主张在学校里直接传教,认为要潜移默化地进行,否则,会因为书馆过分的宗教色彩而将(中国)学生吓走。他的这一主张被圣公会认为是太过世俗化而不满。对近代晚清中国来说,他译书巨擘,是科普先驱,同期的林乐知、丁韪良、徐寿、华蘅芳都不能望其项背。傅兰雅把一生大量的精力投入进教学、译书、编报的工作中,而他的编报思想我们也只能从林乐知接棒后窥其一二,因缺少他任主编时间的报刊样本,只能从《傅兰雅档案》等其它文献了解他与近代中国的深刻渊源。
《上海新报》第四任主编林乐知。在近代晚清中国,林乐知的形象似乎更像是一位传播西方文化的使者,而非庄重的传教士。之所以如此,与林乐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以及他的传教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林乐知本质上是一位虔诚的宣教士,宗教宣传成为他在中国工作的重要一环。
林乐知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很深,他对晚清社会弊病的批评,对教育兴国的呼吁,发人深思。但他的意见,也同时带有相对的西方立场和优越感,有些意见则是任何一个真正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
他对中国的批评重点落在3个方面:迷信、鸦片、科举。他从总体上以科学与迷信对比,认为科学兴则迷信灭,科学衰则迷信盛:
格致之理明,而风水之说,不待辨而自息矣。即如白昼而行墦间心无所怯,夜则疑心生鬼,寸步难行,一见灯光,而胆忽壮。格致者,即风水中之趋昼与灯光也。…… 再之天大雨时,雷电交加,敬雷者畏其击死,遂有建庙而造雷祖殿者,不知电与雷,二而一者也,先发光而后发声,如开炮然,何畏之有!且西国取其电气而传信也,非明征耶?又有不明天文地理者,见日食月食与彗屋,则以为关乎国家吉凶,或鸣锣救之,或建醮禳之矣……据此而言,又中西所关系者也,其在不明化学之小人,祀祖祀神而焚纸锭,见磷火而生俱生疑,不知焚烧纸锭,仍归本质,徒费钱文,若磷火,西人取作自来火,以为日用之物,惧何为哉,疑何为哉?此等愚味之见,举国如狂,皆君子未能详细辩明,予斯世以着实可靠之理。
林乐知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差异方面说明鸦片之害,但把鸦片与酒类同,观点虽不一定能成立,但他将中西方人们的嗜好与宗教、文化特性加以综合考虑的论述也启发了当时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东人性近于静,迷于鸦片者恒多,而静中之物,鸦片之累为最深。西人性近于动,迷于酒者恒多,而动中之特,酒为最重。
对于中国科举制度,林乐知批评的着眼点是学问与实事的关系。他认为,科举制度的最大弊端是一个空字,言大而夸,不切实际,结果导致国家败弱:
……而今中国士人,天道固不知矣,即格致亦仅存其名而已,所伪为知者,诚正修齐治平之事耳。言大而夺,问其何为诚正、何为修齐、何为治平,则茫乎莫解,与未学者等。谓之为士,其信然耶? 中国开科取士,立意甚良,而惟以文章试帖为专长,其策论则空衍了事也,无殊拘士之手足而不能运动,锢士之心思而不能灵活,蔽士之耳目而无所见闻矣。倘能于文诗策论而外,讲求尧舜禹汤之经济,文武周孔之薪传,中国不几独步流瀛寰,而为天下万不可及之国哉!
林乐知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适应中国文化,让基督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在晚清基督教新教派(Protestant Christianity)的傳教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是习惯上所称的“直接布道式”,就是涉足中国的乡村、城市,面对广大的平民百姓,宣讲教义,歌颂上帝,发布传单,广送宗教图书,选择合适地点建立教堂。也就是为传教而传教,较少触及中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也不去办报、兴学、建医院等。从1807年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后的多数传教士都是采用的这种方法,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收效并不显著。林乐知来华之后,采用的也是这种方法。70年代之后,林乐知等个别传教士提出了一种新的所谓“自由派”(liberal)的传教方式。这种方式要求传教士一要认真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针对中国的文化特点去改造中国,二要把基督教义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文化巧妙地揉合起来,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要以“触及在中国人中施展影响的源头”的策略,以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为手段,如办教育、建医院、办报纸等,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扩大基督教文化的市场,吸纳更多的华人入教。
1868年12月,林乐知给家乡教会写信,在谈及他作为《上海新报》的主编时指出这份报纸拥有众多读者,并希望能给予他们真理指导,从而来改变那些滋生迷信思想的根源,使他们和基督教徒们一样去寻求真理。可见此时林乐知已有了通过报纸宣传宗教的想法。碍于《上海新报》的商业性质,在接手《上海新报》初期,林乐知并没有大肆宣传基督教。虽在《上海新报》上经常见到“录中国教会新报”的字样,但并不直接宣教,而是对社会上新鲜事的报道。林乐知主张采取利用中国本土条件传教,这些本土化色彩的教化文章是林乐知根据中国人的脾气、兴趣刊登的,更易于华人接受。这些宗教性内容都刊登在新闻版,使《上海新报》的新闻内容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新闻版面的内容。
1871年2月2日,《上海新报》刊登了“林先生往广方言馆教书翻译”,介绍了他3年来的工作情况,并表示“(林)虽有时因中原风俗与海外不合者稍加辩论,亦不过与华友赏奇析疑,互相教益而已,纵无高着眼孔俯视一切之处”。专门强调了林乐知“中立”“平等”的办报理念与原则。他在担任《上海新报》主编的同时,于1868年9月在上海创办了《中国教会新报》,由林华书院刻发。每年出版50期。以宗教为主要内容,还有科学、新闻、广告等。1872年8月从第201期起,变更体例,分为“政事”“教务”“中外”“格致”“杂事”五栏。并改名为《教会新报》,期数续前。1874年9月自第301期起,再改名为《万国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