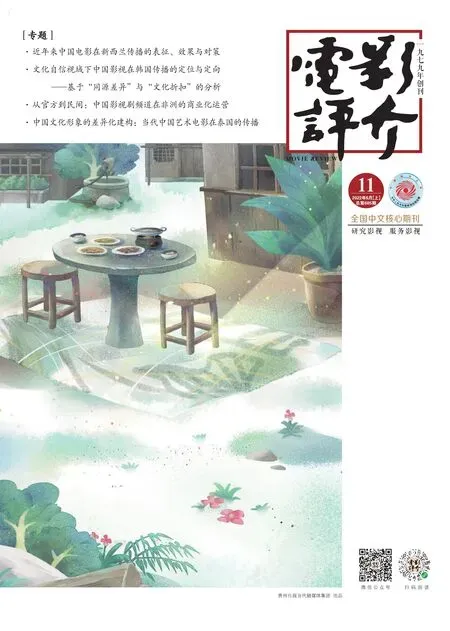从“启程”到“归途”:《心灵奇旅》的生命母题聚焦
王立霞
2020年12月,由彼特·道格特执导的动画电影《心灵奇旅》正式上映,这部斩获第93届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以及最佳配乐两项大奖的影片在国内创下了不到两个月就收获3亿元票房的好成绩。这部电影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优良的制作、娴熟的技巧,还应归功于其直击心灵的电影主题。
该片运用双场域的创作手法构建了多元叙事空间,打造了一个“生之来处”的灵魂入世前的生存场,讲述了梦想成为爵士演奏家的乔伊·高纳和灵魂22号共同寻找入世通行证的重要组成部分——“火花”的故事。影片用隐喻的意象、哲学的思辨塑造了代表两个群体缩影的人物形象,实现了跨文化的情感认同。影片的主题即是对“火花”的追寻、探究,通过主人公的错位人生的双场域转换,最终得出“火花”即“享受当下每一分钟”的反追梦哲理。这是一部动画电影,也是一部治愈系影片,这部电影通过离奇的情节设计揭示影片主题,引人深思。
一、多重叙事空间下的生死之途:启程
《心灵奇旅》讲述了将爵士乐当成人生理想的中学音乐教师乔伊·高纳意外死亡后,碰到一个厌世的灵魂22号的故事。这两个独特个体一个拼命想活,即便一无是处也对生命充满了激情和渴望,另一个却拼命不想活,待在“生之来处”上千年,气走了若干位“导师”,对生命毫无期待,无知无感、毫无意义的“活着”。两个独立的个体被随机分配在一起,却又因为各自心里的“理想”达成了共识,开启了一段灵魂互换的旅程。
在迪士尼动画影片中,采用空间叙事的手法并不鲜见,《头脑特工队》《寻梦环游记》等都采用过这种手法,在多重空间叙事角度下,能够最大限度打破空间界限,无限度开发脑洞,创编奇幻的情节以推动故事发展。《心灵奇旅》构建了一个多重叙事空间,即地球的现实空间,想象出来的灵魂空间,而在灵魂空间里又有象征出生前的“生之来处”,生命结束后的“生之彼岸”以及“忘我之境”等虚幻空间。
影片构建的虚拟世界在东西方神话体系中都存在着。《心灵奇旅》探讨的是生命的起点,提出的是寻找生而为人的意义的哲学命题。
《心灵奇旅》在两个时空中设计了两套人物形象,双重形象设计使灵魂世界更加真实,满足了人们想象空间中“另一个世界”的虚幻之感,也让两个平行时空中的不同时空流能够互不干扰,各自独立叙事。“和而不同”的人物形象设计,即区分了两个叙事时空,使其各自丰满立体,又相互融合,为人物的活动搭建了转换的舞台,使哲学命题得以深入讨论。
在视听语言中,时间流和空间流可以通过影音技术达到相对的独立。戈罗德和若斯特认为:“空间还是以某种方式先于时间……正是因为画格先于画格的连接,电影中的时间性确实必须建立在空间上,由此植入叙事之内。”[1]“灵魂”错置式互换中,乔伊的灵魂进入了猫的身体,灵魂22号则成为了乔伊,现实世界的时间流被限定为一天,而“生之来处”的时间流则是非线性的,灵魂关于哲学命题的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思考于“永恒”时间流里完成,而人物的生命体验、时间紧迫感则来自现实世界,电影故事的推进依靠时间的流变,而时间的流变又需要在空间转换中来呈现。[2]乔伊和灵魂22号得以在多个空间中穿越,在空间转换过程中完成双重时间流下的情节推动,于生与死的旅途中找到自我,实现人格的成长。
二、内聚焦视角的审视:启蒙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将灵魂描述为三个部分:理性、欲望和情感。普鲁塔克发展了柏拉图的这种说法,进一步将人的灵肉从高到低分为三层结构:心智、灵魂、身体。普鲁塔克认为“灵魂比身体优越和神圣多少,心智就比灵魂优越和神圣多少”“灵魂与心智相互塑造”。[3]作为心智与身体的纽带,灵魂独立于肉体而存在,又依附于肉体才能真正存在。
《心灵奇旅》采用了内聚焦的叙事视角。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并不罕见,由法国学者热奈特提出,这种视角通过聚焦者的视点、感受、认知来叙述事件,故事的主人公乔伊即故事的聚焦者。[4]影片通过乔伊的内聚焦式视角展现了灵魂的迷茫、迷醉、迷失的过程,这是灵魂探索生命意义的旅途,也是心智启蒙的过程。
(一)迷茫
“内聚焦的最大特点是能充分敞开人物的内心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人物激烈的内心冲突和漫无边际的思绪。”[5]影片以内聚焦的叙事手法拉近了观众和乔伊的关系,使乔伊的心绪在观众面前完全袒露。从影片开端就构建出一个无聊且无意义的生活场景:杂乱、烦闷的教室里,一群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和一个无聊的老师待在一起,烦闷、无趣充斥着乔伊的生活,即便是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教师的好消息也让他提不起兴趣。这种无聊、无意义的生活场景让乔伊习以为常,以至于自以为有着强烈梦想的乔伊完全忽略了生活本身。可是,爵士乐真的能让生活不一样吗?当乔伊如愿地参加完演奏会后,他的生活没有发生半点儿变化,等待他的依旧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乔伊的灵魂再度陷入迷茫。内聚焦的透明性让迷茫无限放大,让每一个观众都找到了生活中的类似场景,乔伊仿佛就是自己,日复一日的追求到底要的是什么?没有人能够解答。
迷茫的不只有乔伊,还有灵魂22号。内聚焦的视角使得22号的状态必须要通过主角乔伊的眼睛去观察、去感受,离开聚焦者的感受后,观众对其他角色的状态无从感知,这是由内聚焦的限定性所决定的。内聚焦从个人视角展现所见所闻,在视野上具有严格的限制,即限定性。灵魂22号由于在“生之来处”滞留时间太过于漫长,没有身体的依附使其缺失了感知能力,重复性生活让其更加感受到无聊、无意义,他迷茫地漂浮在“生之来处”,没有目标,更遑论去感悟生命。
(二)迷醉
在影片的设定中,存在一个特殊的空间,即现实世界和“生之来处”的纽带——“忘我之境”。当人们做一件事情异常投入的时候,灵魂就会出窍,来到“忘我之境”,这是一种迷醉其中的特定状态,也是灵魂从现实空间到达灵魂空间的通道。在“忘我之境”的灵魂闪闪发光,他们或是在演奏音乐,或是在理发,或是在走钢丝,或是在扣篮,总之,没有平凡和伟大之分,只要沉浸其中,就能获得超凡的精神享受,达到迷醉的程度。这个特殊空间的存在显然在为后续的哲学命题做铺垫。只要认真地对待平凡的生活,就会获得精神享受。“谁说生活就一定是要有意义的呢?”“生之来处”的管理者的话也解答了这个特殊空间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多重空间的叙事语境下,叙事层次进一步加深,为影片构建出更加立体的深度空间。
(三)迷失
当迷醉在“忘我之境”的灵魂将追求视为执念的时候,就会被包裹在密不透风的沙尘里,变得面目狰狞、可怕、癫狂,成为迷失的灵魂。如果没有人解救,灵魂会一直游荡,甚至具有攻击性,导致其本体永远不会醒来。影片中一个被包裹在沙尘里的迷失灵魂,是一个基金经理,嘴里不停地喊着“交易”。虽然极具讽刺意味,却也增强了观众的代入感。灵魂22号也成为了迷失的灵魂,当其在乔伊的身体里找到生命的价值,点亮“火花”拿到地球通行证后,又在乔伊一连串的发问以及对自己的不自信中迷失了。在内聚焦的限定性下,观众无法从22号本身去感受他的无助与失落,只能通过乔伊去观察22号的挣扎,去感受22号从无肉体的冷漠到和身体联通后的兴奋再到失去身体、失去“火花”后的迷失、彷徨,一个从厌世者转变为探索者的人物形象被刻画得栩栩如生。
三、生而为人的探索:归途
“火花”是影片里灵魂入世的通行证,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苦苦追逐“诗与远方”。影片用反追梦的手段消解了梦想,那灵魂上的远方呢?在乔伊实现梦想却产生失落感的时候,多茜亚·威廉姆斯给乔伊讲了一个故事:“一条小鱼问老鱼海洋在哪里,老鱼说我们现在就在海洋中,小鱼却说这里只有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一)隐喻
《心灵奇旅》是一部“合家欢”式的动画电影,它摆脱了传统动画的低幼化,不是单纯给小朋友看的教育意义影片,其丰富的寓意、普遍的隐喻随处可见,多重场域的相互转换使情节越发复杂,其叙事的开放程度以及对主题的深刻构建,引发了观众跨越情感、种族、时空,产生心理上的强烈共鸣。
《心灵奇旅》具有强烈的治愈性,可以说它是遭遇过挫折、痛苦以及对生活产生迷茫的成年人的一剂良药。电影给我们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天堂和地狱”的独特空间。在这里,“生之来处”和“生之彼岸”是生与死的轮回,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出生的过程太痛苦了,所以健忘也是一种幸福。”一句话把生之痛、死之悲描述得更为释然,也颇为让人感慨。“这点儿压力都扛不住,还怎么去地球。”直击观众内心,使观众联想到自己生活中的压力,既无奈又充满感叹。在“忘我之境”里,出窍的灵魂是幸福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并达到忘我之境是每一个人极度渴求却难以企及的。从忘我到执念再到迷失自己,是为生活奔波的大多数普通人所面临的噩梦。“又一个基金经理”让人感到辛酸。当执念成为枷锁裹挟着鲜活的生命时,当琐碎的工作与世俗的观念绑架个体时,焦虑、不安、麻木等情绪就会出现,《心灵奇旅》点出了现代社会中普通人的“内卷”与无奈,以致普通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对影片产生精神上的共鸣。
(二)思辨
《心灵奇旅》是动画的,更是哲学的。“一条小鱼问老鱼海洋在哪里,老鱼说我们现在就在海洋中,小鱼却说这里只有水,我想要的是海洋。”到底是水还是海?乔伊和22号的错位人生让22号体会到什么是“活着”,22号之所以能在错位人生里找到“火花”,是因为没有时间概念的“生之来处”只能让他感到无知、无感、无聊,待得越久就越会丧失感知生命的能力,就像水里的鱼失去了对水的感知。当他重新感受到“水”的时候,生命被重新唤醒,他可以“看见”世界,就算是简单的走路,也能让他兴奋。
错位人生也让乔伊有了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自己的生活,所有他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从猫的视角去观察时,有了很多不同。22号的兴奋让他不解,理发师的絮絮叨叨也让他疑惑,这些平时被他忽略掉的日常生活细节似乎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无聊。他以为的一切并非是他以为的,他正是那条生活在海里的鱼,每天都在追求海,却从不知道自己早已身在海里,甚至于忽视了海的存在。他忽视了生活中的各种美好,用对立的态度去对待一切。生活里的危险、学生的情感、理发师的友善、母亲的期盼,所有的一切都要为他所追寻的“海”让步,直到在享受到成功后,另一种失落感出现时才有所感悟。
(三)火花
《心灵奇旅》是一个神话故事,也是一个成长故事,乔伊不是拯救世界的大英雄,却是疗愈心灵的探路英雄,是一个带领平凡人寻找生命意义的英雄。
《心灵奇旅》遵循了“启程——启蒙——归来”的叙事模型,无论是“启程”还是“启蒙”,都是影片在为归途做铺垫。乔伊和22号的归途是在探索中完成的,是思辨的归途而不是空间的归途,这也是影片的侧重点所在。
影片用了大量的精力去引导乔伊和22号思考他们所要寻找的“火花”到底是什么。在“生之来处”消磨了大量时间的22号一直误以为“火花”就是目标,是生命要追寻的结果,他遇见过很多导师,甚至包括圣雄甘地、林肯总统等众多优秀人物、成功人士,或许也正是因此才误导了22号,让他对生命产生了厌烦情绪。乔伊则将理想当成了“火花”,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音乐就是他的“火花”,他还想要让音乐也成为22号的“火花”,甚至误以为在经历错位人生的情况下,22号以他的身体活过一次,就能和他一样被音乐点亮“火花”,还因此与22号大吵一架。
乔伊的误解影响了22号,严重的不自信与被点亮的“火花”让22号成了一个矛盾综合体,苦思不得解的结果是22号成为了迷失的灵魂。影片在探讨什么是“火花”,却又并没有说出什么是“火花”,而是用“生之来处”管理者杰瑞的话——“火花不是目标,我们不分配目标”、多茜亚·威廉姆斯说的海洋与水的故事,引导乔伊和观众一步步去探求“火花”的深层次内涵。
幡然醒悟的乔伊成为了自己的英雄,也成为了22号的英雄。他拯救了迷失的22号的灵魂,也坦然面对了“生之彼岸”,生即珍惜,死亦坦然。至此,乔伊懂得了生与死的意义,也懂得了生命的思辨哲理,生命没有那么复杂,“大道至简”。所谓的“火花”不过是一日三餐、两点一线,是生命中的每一天,是对每一分钟的珍视。“火花”就是生活,生活就是“火花”。
结语
《心灵奇旅》给观众呈现了一场特别的旅程,洗涤了心灵,救赎了灵魂。影片灵活运用多重空间设计,突破空间束缚,在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上达到了灵与肉的和谐统一。多元世界的空间架构,凝练的叙事场景,情节、人物形象的创新性设计,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心灵奇旅》之所以成功,在于其塑造了乔伊和22号灵魂两个人物形象,讲述了一个直击观众心灵的哲学故事。“生死之旅”中的意象隐喻了追求梦想的大众,生活的重压被影片中一句句台词轻描淡写地呈现出来,反而成为压碎心房的最后一根稻草,挣扎在生活里苦寻出路的普罗大众仿佛在影片中窥见了自己的影子,收获了心灵上的共鸣。影片采用思辨的叙事手法和哲学式对话,塑造了在平凡生活中得到一步步成长的另类英雄形象,阐释了“珍惜生命、珍爱生活”这一看似平凡实则深奥的哲学道理。在影片的探寻中,观众跟着乔伊和22号灵魂一起,得到了心灵的治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