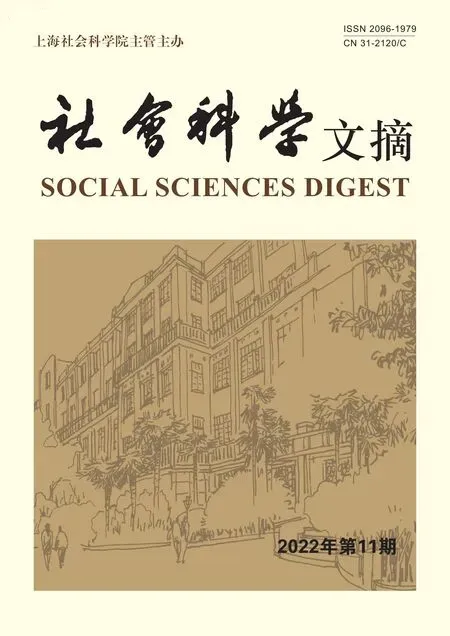现实制度主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的合成
文/张发林
国际关系理论是对国际关系现实的规律发现和系统解释,然而,国际关系是否具有跨时空客观性颇具争议,现实的变化需要理论的发展与创新。本文尝试对国际关系两大主流理性流派(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进行合成,将解释国家行为和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融合起来,构建现实制度主义的新理论,以解释国际关系现实的新变化,尤其是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变迁。
权力与制度逻辑的初步融合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了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不同逻辑,主要包括现实主义侧重解释国际冲突的权力逻辑,新自由制度主义尝试解释国际合作的制度逻辑,以及建构主义的文化逻辑。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构建主要是在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合成。尽管这两种逻辑各有侧重,但本质上并不是相互独立和完全互斥的,而是存在不同程度的交集和重合,一些理论和经验研究也尝试对其进行融合,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在权力或制度逻辑下对制度或权力加以考量,进行范式内拓展。在制度逻辑下研究权力的代表性理论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在权力逻辑下的制度研究,具体表现为不同现实主义流派的制度观。
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尝试跳脱出特定理论范式的束缚,将权力和制度两种逻辑不同程度地折中或合成。相关研究大致从理论的四个不同层级进行融合尝试。在宏观理论层面,自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论战之初,理论对话和理论融合的呼吁便不断。在具体理论层面,一些研究尝试结合权力和制度逻辑构建具有一定范围解释力的理论,这较于宏观范式层面的融合相对更容易。更多将权力和制度逻辑进行结合的尝试是在分析框架层面。在概念层面,“制度性权力”对国际制度的权力属性和权力的制度工具进行了概括和总结。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创建
在上述既有理论融合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尝试进一步对权力逻辑和制度逻辑进行融合,并初步提出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构想。
(一)概念界定与理论需求:为何是“现实制度主义”?
现实制度主义(realist institutionalism)的概念和用法早已有之,但其所指却多有不同。在较为有限的相关研究中,现实制度主义的主流用法是指将权力和制度逻辑进行融合的折中分析框架或理论,这与其概念的字面含义也是吻合的。但是,这些融合尚停留在分析框架和概念层面,缺少理论构建或理论化。沿袭了这种概念的用法和基本思路,出于以下几点主要原因,本文试图进一步将这种折中思路理论化:其一,国际关系不是跨时空的客观事实,而是具有历时性,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内涵和特征,由此国际关系理论需要与时俱进;其二,“冲突—合作复合形态”是当前国际关系形态的主要特征,片面强调冲突或合作的理论都无法全面解释这种形态;其三,解释国际秩序变革的现实需求和推动国际秩序和平演进的规范性目标迫切需要理论创新。
基于此,现实制度主义尝试回答的核心理论问题是:在表现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国际制度体系中,国际秩序将如何演进?这一核心问题包含以下背景性和支撑性问题:国际关系何以表现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换言之,在经济全球化(复合相互依赖)和国际体系制度化的背景下,为什么国家间关系的合作性并未随之增强(如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而是充满了冲突与竞争,但国际关系也并未陷入无限的冲突中(如古典和结构现实主义所认为),而是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形态?如何理解国际制度的多重权力属性?在国际制度体系中,大国国际制度竞争如何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
(二)现实制度主义的内涵与核心逻辑
现实制度主义对这一核心问题的回答是: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下,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是主权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动力,国际制度性权力成为一种基础性权力形式,国际制度具有多重权力属性,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导致冲突—合作复合形态,并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方向和方式。这一核心结论包含以下三个假定和两个核心假设:
假定一:主权国家是理性且自利的单一行为主体,有追求权力的天然倾向。
假定二:国际体系是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
假定三:国际制度是权力的对象、工具和来源,具有中性和非中性的双重属性。
基于上述三个假定,现实制度主义理论有两大核心假设。
假设一:国际制度的多重权力属性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导致了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
上述国际制度的三种权力属性共同构成了“国际制度性权力”(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ower)的内涵,而国际制度性权力是主权国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所追逐的重要权力。具体而言,国际制度性权力是指:国家在国际制度的创建、存续、变迁过程中影响国际社会其他行为体的观念及/或行为的能力,其中,国际制度是权力的结果、工具及/或来源。在高度制度化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追逐和分配,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形态。但是,相关理论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不同界定推导出了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古典现实主义和华尔兹结构现实主义聚焦的权力是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国际制度多是权力的附属品,由此,国际关系是冲突性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对无政府状态的功能性缓解作用,国际合作是可能的,在复合相互依赖下,国际关系是偏合作性的。克拉斯纳等新现实制度主义研究也一定程度承认国际制度的独立性和功能性作用,但现实主义的底色决定了其对国际关系形态偏冲突性的判断。强制度主义和理想主义都认为国际制度有高度的自主性,是权力的来源,对权力政治有很强的制约作用,甚至可以替代权力政治,因此,国际关系的形态是合作性的。现实制度主义的国际制度性权力定义融合了上述三种权力逻辑,认为在具体的国际关系实践中三种权力逻辑并存,由此得出冲突—合作复合形态的判断。
假设二: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决定国际秩序演变的方向和方式。国际制度自主性越高,国家权力自主性则相应减弱,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则越低。反之,国际制度自主性越低,国家权力自主性则相应更强,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则越高。
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是国际制度,特定国际秩序是通过国际制度界定的。国际秩序的建立或改革在根本上表现为国际制度的确立或改变,无论国家使用暴力或非暴力手段,建立或改革国际制度都是必要的过程。因此,核心国家的国际制度竞争是决定国际秩序演变方向和方式的重要变量。演变方向是指秩序更加沿着谁的认知和偏好改变。在国际制度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其认知和偏好将更大程度上决定国际秩序的演变方向。演变方式是指秩序变迁的冲突性(或合作性)程度。国际制度竞争的优势来源于国家实力和能力,这从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权力政治的逻辑上。但是,国家与国际制度存在三重权力逻辑,权力政治逻辑下将国际制度完全视为权力结果只是三重逻辑中的一种,权力政治逻辑关于国际秩序变革完全冲突性的判断有失偏颇,国际制度还可以是国家行为的外在约束,可在一定程度和特定条件下制约国家权力。
在国际秩序变迁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国际制度竞争表现为三种权力的博弈,即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通过国际制度的权力和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在这三种权力中,国际制度自主性从低到高变化,而国家权力自主性则从高到低变化,两者呈现负相关。国际制度自主性表现为国际制度身份、地位和影响力相对于主权国家的独立程度,而国家权力自主性是指国家在国际社会实施权力所受到的外在约束程度。国际制度受国家权力的影响越弱,对国家行为的约束越强,则国际制度自主性越高,而国家权力自主性越低,反之亦然。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强,国家间关系越可能陷入古典现实主义的高度冲突中,而国家权力自主性越弱,国家间关系越可能表现为理想主义的合作与和平。因此,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强弱在根本上取决于国际制度和国家权力的自主性,在具体形式上表现为国家在三种权力上的竞争,三种权力竞争同时存在,何种权力竞争的比重更大,将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冲突性强弱。
在上述核心问题、假定和假设的基础上,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逻辑逐渐清晰。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制度性成为国际体系的新特征,国际体系表现出了无政府性和制度性,国际关系呈现出冲突与合作并存的复合形态。在无政府性和制度性的国际体系中,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决定了主权国家的行为,行为的核心目标是追逐国际制度性权力和与此相关的多元收益。国际制度具有三种权力属性,即作用于国际制度的权力、通过国际制度表达的权力和来源于国际制度的权力,这三种权力属性构成了国际制度性权力的内涵,但三种权力属性会偏向于导致不同的国际关系形态,正是国际制度性权力的多重属性决定了国际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主权国家对国际制度性权力的追逐在更长时期里又将改变国际制度性权力分配和国际制度体系,并决定国际秩序变迁的方向和方式。
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属性
就理论构建方法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范式间合成的理论。本文理论构建的方法是理论综合,最核心的综合逻辑是将解释国际关系形态的权力逻辑与制度逻辑相结合,寻找解释国际关系复合形态和国际秩序演进的合成逻辑。具体而言,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创建包含了四种具体路径:折中(主要吸取华尔兹式结构现实主义和基欧汉式新自由制度主义中的有用元素)、回归(从既有相关制度理论中拟合出国际制度的三种权力逻辑)、批判(对相关理论的一些假设和逻辑进行了批判和创新)、合成(通过核心问题和假设等方面的详细界定,将权力和制度两种逻辑有机结合,尝试形成具有内核和内在逻辑的理论)。其中,合成是最重要的路径。
就理论层级而言,现实制度主义是在范式和宏观理论下的具体理论。现实制度主义是对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具体理论分支进行折中、回归、批判和合成而构成的一种具体理论。
就本体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个体主义的偏好,是一种体系理论,但也强调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影响。现实制度主义将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界定为主权国家,认为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会对主权国家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会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行为体的个体特征继承了新现实主义的天然权力欲望观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多元利益观。由此,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的体系理论。个体主义体系理论的常见特征是强调从结构到施动者的单向维度,将体系结构的特征视为外生的。现实制度主义有所不同,其通过强调国际体系的历时性和引入时间变量,加入了施动者对结构的影响维度。
就认识论而言,现实制度主义具有物质主义的偏好,是一种理性理论,遵循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制度性权力结构对主权国家行为的影响,具有明显的物质主义色彩。这种影响是通过主权国家的理性选择而实现的,遵循了一种结果性逻辑。作为这两种理论的合成理论,现实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结构对利益权衡和行动选择的决定作用(即制度结构选择)。由此,现实制度主义是一种个体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体系理论。
现实制度主义的研究议程
现实制度主义的核心理论内涵和理论属性决定了其主要研究对象和议程。
其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新变化。国际体系逐渐演化为一个国际制度网络,国际制度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支柱。二战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具体表现为安全、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国际制度。由此可见,相对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诞生时的国际体系(20世纪70—80年代),当前国际关系的制度化程度显著提高,国际体系的内涵更为直接地表现为一个国际制度体系。现实制度主义的一个核心研究议程便是对国际制度体系的形态、内涵和特征的研究,如制度化是否会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增加国际体系的等级性?
其二,对冲突—合作复合国际关系形态的系统描述和解释。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制度化导致了国际关系形态的高度复杂化,出现了冲突—合作复合形态,这种复合形态是现实制度主义理论解释的重要现象。根据本文的现实制度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和解释逻辑,对具体案例中这种复合形态进行解释,是现实制度主义研究议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尤其就中美关系而言,系统地分析其双边关系的冲突—合作复合形态,避免整体主义的单一判断,有助于更加客观地分析中美关系,更加有效地管控可能出现的冲突,积极地推动合作和发展。
其三,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和自主性的度量。在国际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演进中,国际制度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国际制度自主性的生成机制和表现形式仍需要更加深入的探究。具体而言,国际组织在何种条件下能成为在国际社会中与国家并列的行为主体?国际规则何以对国家行为产生约束或体现特定国家的利益和偏好?国际规范如何转播并引导国家行为?与自主性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制度的变迁路径,相关研究多强调外部冲击后的结构性变化和渐进变革两种方式,且这两种方式的具体机制尚不够清晰。
其四,大国制度竞争与国际秩序变革。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实力格局的变化,国际秩序显现出变革态势,大国间的国际制度竞争及其结果将决定国际秩序演进的过程和结果。现实制度主义理论将有助于分析和解释中美制度竞争和国际秩序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