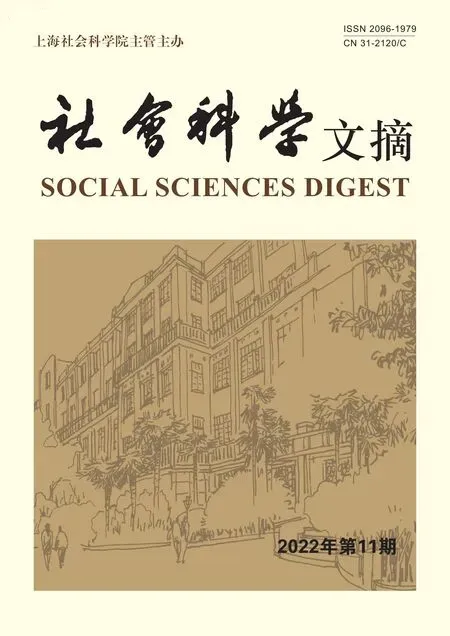中国艺术的“不作时史”问题
文/朱良志
中国传统艺术在唐宋以来出现一种思想观念:真正的艺术创造,不是追逐时尚潮流,而要与这种潮流保持一定距离。艺术家应是冷静的思考者,而不是追赶热流的弄潮儿。“不作时史”便是在这一过程中凝结的重要观点。
这里涉及对“历史”的理解。在中国艺术家心目中,存在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一是在时间流动中出现的历史事实本身,这是历史现象,是历史的第一种形态。二是被书写的历史,汉语中有“改写历史”的说法,即历史是人“写”出来的,具有知识属性,并具有鲜明的权威性特点。这是第二种历史,一般所说的“历史”即指此。三是作为“真性”的历史,它既不同于被书写的历史,又不同于具体的历史现象,而是人在体验中发现的、依生命逻辑展开的存在本身。千余年来,中国艺术家特别重视这第三种历史的呈现,它给人的生命存在带来一种底定力量。
强调“不作时史”的中国艺术,不是否定历史,而带有突出的反思性特征。就“书写的历史”来说,它要挣脱知识和权威等束缚;而就历史现象来说,它更要透过时间过程中呈现的表象,发掘人内在生命的力量。这第三种历史的根本指向,就是不要被历史叙述左右,去直面鲜活的生命感受,去发现历史现象背后人的生命价值世界。所以,“不作时史”的根本包括两方面:不作历史现象的表面记录者;不作“书写的历史”的复述者。它要通过艺术,在更深层次、更广视域中,发现历史的脉动,从而传递出艺术中本应有的历史感、人生感和宇宙感。
不入时趋
“时趋”,是一种附和世俗的创作倾向。就时代潮流而言,是时之所尚;就个人选择而言,是追逐时流。为“时趋”所左右的艺术创造,本质上是目的性追逐,其创作是从属性活动。“时趋”是与“古趣”相对应的概念。中国艺术所追求的“古趣”,是历史表相、历史书写背后流淌的永恒精神,是那种人之为人的生命趣尚(或者本质属性)。而“时趋”则是对此一精神的背离。
宋元以来的文人艺术主流重视“四时之外”的意趣,不屑与时追趋,强调表达一己真实生命感受,在“非时间”中铸造艺术的理想世界。它不是“宣谕”式的,它要在切己体验中去更好地发挥艺术作用人心的功能。文人艺术有几个特点,第一,从历史大势看,文人艺术的主体是熟稔技法、拥有丰厚学养并具有独立精神追求的群体,基本可以说是“士林”中人。第二,文人艺术乃士林中能“作隶家品”者,具有“隶气”(文人意识常被称为“隶气”)。即具有非从属性特征的创作群体,不是为了完成别人交给的“作业”,只为性灵寄托而作画。第三,文人艺术以追求“天趣”为理想,超迈于人工秩序之外,不趋于时流,在时间和历史书写外,展拓自己的理想天地。由此可见,文人艺术的关键不在于“文人”身份,而在于它是否具有关乎“人文”的思考。其根本特性是对时间、历史的超越,要将人从“从属性”的泥淖中拯救出来,让艺术变成性灵独立的创造,让艺术传递人生命深层的独立声音。媚时媚俗,难有独立创造,时趋者,为时所趋,为艺者外为种种权威、法门所限,内为种种目的牵引,必然会将艺术引入“俗”流中。
“时史”概念就是由早期“画史”发展而来的。五代北宋以来,画院制度兴起,画院画家一般被称为“画史”(又称“画工”),作为职业画家,经过集中训练,重视形式工巧是其基本倾向,后来将画院外重视技巧的画家也称为“画史”。进而“画史”泛指唯论工巧、不论情性的一类画者。明清以来,艺术论中又以“时史”去取代“画史”概念。“画史”与“时史”二者含义并无多大差别,但明清以来易“画史”为“时史”,注目的中心已从元之前的技巧斟酌转向与时代、社会、历史关系的思考。艺坛人士反“时史”的倾向,就是从“时”切入,来思考艺术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染上“时史”的习气,步履时趋,艺术成为时代风气的传声筒、应声虫,附庸世俗,逞才斗艳,急于依附在别人屋檐下,寻一席容身地,骨力全无,这是艺术的堕落。人们看到很多所谓艺坛胜流,入于时趋,乞灵权威,一己性灵在滚滚马头尘、孜孜功利事下徘徊。反时史,所反的就是这样的风气。这种观念转换,也有现实针对性。明代中期以来随着经济发展,艺术与普通人生活的密合度增强,为艺者迎合时尚、沾染流俗的气息也较浓厚。文人艺术推崇“妙合神解”,不是远离时代,远离普通人,而是在超越时代和历史中,更好地呈现人的真实生命感觉。
中国艺术的反“时史”思潮,体现出一些重要特点。第一,反“时史”,强调在时代土壤中培养“悟性”。艺术创造不能等待外在“大叙述”导引,而要深深植根于时代土壤中,氤氲在时代气息里;脱离时代,脱离人的真实生命体验,人的“悟性”便会钝化。外在“大叙述”固然重要,但是这种“大叙述”还要转换成内在“小叙述”,转换成人直接的生命感悟。第二,反“时史”,是为了寻回“真宰”。艺术家是艺术创造的主人,不能自甘奴役。第三,反“时史”,是要荡却纵横习气。强调艺术应是心灵自然而然的流露。如像战国纵横家那样,受目的支配,有纵横习气,重视“宣说”,哪怕昧着良心也在所不惜,那便是艺术的堕落。第四,反“时史”,在风格上趋于简淡高古一路。
不落时品
在艺术与时代关系的论述中,明末清初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影响很大。如今在学界,它成为艺术与时代密合关系的简洁口号。按一般理解,石涛这句话强调艺术创造要顺应时代、追随时代,但这种理解有片面性。综合石涛理论,他强调两点,一是“一代有一代之艺术”,二是“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这两句合在一起,才能见出“笔墨当随时代”的完整意思,即笔墨当追随时代中活生生的人的鲜活感受。这鲜活的感受是艺术创造力的本源,即他所说的“一画”。他强调,为艺要重视滋生于时代土壤中的个体鲜活感悟,而不是完全服务、顺从外在权威话语和现实功用。将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简单理解为艺术要顺着时代、做时代的吹鼓手、做时代潮流的推波助澜者,是对石涛的绝大误解。
石涛谈笔墨与时代的关系,认为画家笔墨情趣会受时代影响,就像诗文风格的流变,早期的笔墨简朴,唐五代至北宋时趋于繁复壮丽,而发展到元代,复归于平淡幽深,并转出新的风调。画家陶染在不同时代风气里,思想感情在具体生活中激荡,创造动能也主要来源于与时代的互动,任何一个人都无法脱离时代。切入时代,直面当下体验,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这里说的“随”是受时代风气影响,陶染于直接生活,而不是“随顺”某种外在的法度和律令,去按谱按法为之。石涛所强调的是,艺术不是要跟着时代节拍,成为某种时尚的传声筒,而是要跟上自己“性灵的节拍”——这来源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的生命节拍。
石涛认为,文章翰墨一代有一代之神理,一人有一人之体验,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古法,不能随波逐流。画由心出,由生命真性酿造而成。一代有一代之艺术,艺术家之于时代,是要发挥创造力,既不死于古人章句下,也不拘限于当代“门庭”里。石涛说,“一代一夫执掌”——“一代”只在“一夫”(自我的创造)掌握中,而不是每一个时代都要换一种法。笔墨当随时代,当“随”于时代中那创造者的自性。书画重要的是求“一夫”之“执掌”,出于自性之创造,不在为一代争名,也不在为某家立派。石涛的“笔墨当随时代”,既是“一代之事”,又是“一人之事”。就“一代”而言,艺术一代有一代之面目,艺术创造不能以古法为今法。就“一人”而言,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关键是从一心流出,不必以荆关董巨等面目为自己之面目。“一代之事”即为“一人之事”,这才是他所说的“见地欲稳”的“稳”。
石涛提出了“不入时品”的创作主张。逸神妙能四个品级,由能到逸,渐次提升,能品主要指技巧上的功夫,而神妙能三品之上的逸品,则是偭规矩,逸法度,独标孤帜。然而,石涛在四品论之外,特列“时品”一目。他认为,逸神妙能各有品第,均可论之,而“时品”是艺术的大敌,所谓“自不相类”,一落时品,即入俗流,一入俗流,笔墨成为时流的传声筒,就会丧失艺术的基本品质。
石涛“笔墨当随时代”的思想,反映了文人艺术的基本主张,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人的生命感悟来自时代气息的氤氲,人的真正创造必须超越时代藩篱。
不到人境
中国艺术推崇空山无人之境,尤其在绘画创造中,抽去人的活动场景,略去人的活动过程,如元代以来的山水面目,大都是空山、空林、空亭、无人的山村、空空的院落,透出浓浓的荒寒冷寂气味。这不是个别人的趣味,而几乎是整个文人艺术的基本趣尚。
传统艺术特别注重无人之境的创造。董其昌以“无人之境”为南宗不言之秘。龚贤的山水小幅,有千古的寂寥;八大山人晚年山水,突出的特点就是“无人间相”。这样的观念直接影响艺术的形式构成。画家刻意创造的枯木寒林,要表现的是不生不灭的静寂;造园家、盆景艺术家热衷于创造青苔历历的景象,要“苔封”时空的变化流动。唐人审美观念中其实就具有这种思想。像王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小诗表现的境界,空花自落,空林自响,所谓“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暮鼓晨钟不是为了记录时间变化,而是在强调朝朝暮暮如斯,一声清响,深山、世界乃至历史都顿入无时间的幽深中;古木参差也不是为了记载年轮,而是要在春花秋月、花开花落的表象背后寻觅世界的真实。“空山不见人”是王维诗的一个喻象,也可以说是文人艺术的典型喻象。
艺术是人的创造,为什么要刻意排斥人的活动?这在世界艺术史中都是罕见的。这是一种由思想观念推动的艺术现象。(一)不作人间语。中国艺术的空山无人之境,与突出隐居、突出环境的阒寂没有多大关系,其要义在与十丈红尘隔开。艺术家“不作人间语”,表面上看似乎对人的活动失去兴趣,其实是在超越时间、历史的情境里营构人的存在世界。在艺术中抽离人的活动,是为了更好表现人的存在境遇。(二)请从天际看。作无人之境,也是为了换一种方式看世界,从凡尘超出,作天际的俯瞰。中国古代典籍中常有“无始以来……”的叙述方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是过程性的存在。站在时间绵延的角度,会有一套叙述;而透出时间,透过历史,透过人的知识性存在,站在天地宇宙的视角,又会有另一套叙述。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家善于透出时间之网,以天际的目光飘瞥苍穹。(三)寂寞自太古。无人之境,乃寂寞之境,它超越时空,如聆太古之音。“寂寞”(或称“寂寥”)二字,为文人艺术所重。恽南田以“寂寞无可奈何之境”概括倪瓒的艺术境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有元一代艺术之追求。这与那个时代压抑的气氛有关,更重要的则是出自文人艺术的超越梦幻,他们要在寂寞的太古之境——这一绝对时空里,铸造神明清远、意态豁然的理想天国。(四)无人花自开。北宋以来,文人艺术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东坡语)为八字真髓,人们创造寂寞的境界,并非要表达老僧入定、心如枯井的感受,而是要通过它,感受世界的活泼,高扬性灵的腾踔——这是一种没有活泼表相的活泼。中国艺术追求气韵生动,追求生意,追求活泼泼的境界,这是大方向。从时间角度看,它有两种方式:一是时空界内的,即人通过感觉器可以捕捉到的,这是“看世界活”;一是“让世界活”,就是荡涤心灵的遮蔽,让世界敞亮,让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这看起来并无活泼表相的活泼,也就是世界依其自性而自在兴现的境界。历史、知识的星空布满了乌云,人们看不清世界,也发现不了这世界的活泼。
谱千年之调
文人艺术“不作时史”,又如何体现社会责任感?一种连人都不愿意触及的艺术,会对人生有什么价值?
文人艺术的“为一己陶胸次”,绝不是一种自私行为。李流芳说:“夫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性情,非有二也。人人之所欲达而达之,则必通;人人之所欲达而不能达者而达之,则必惊,亦非有二也。”文人艺术追求的“古意”,其实就是追求“人之性情”与“人人之情性”的合一。古意,作为文人艺术的审美理想,反映的是文人艺术家对艺术普遍价值的关切。恽向在一则画跋中说:“蛩在寒砌,蝉在高柳。其声虽甚细,而能使人闻之有刻骨幽思、高视青冥之意。故逸品之画,以秀骨而藏于嫩,以古心而入于幽。非其人,恐皮骨俱不似也。”古心入微,秀骨在目,苍老中的鲜嫩,高古中的清思;澄波古木,使人得意于尘埃之外,在超越古今的创造中,彰显高视阔步的人生境界——此之为“逸”。文人艺术的荒寒之旅,常为人误解,讥为一己之哀鸣。而恽向认为,以元画为代表的文人艺术所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如高柳上的寒蝉,瓦砾间的飞蛩,声虽细,意悠长,以萧瑟冷寒之音,发人深省,觉人所未觉。声在柳上,高视青冥;藏身瓦砾,饮恨沧桑。艺术家超越身己限制,横绝时空之域,唱出生命的清曲。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千余年来的中国艺术特别强调对时间、历史的超越,推崇荒寒境界的创造,艺术家的意绪常在寂寞无人世界里徘徊,这是世界艺术史中的独特现象,所体现的不是对人生存环境的疏离,恰恰蕴含着对人类真实生命的殷殷关切。对这种传统艺术观念的准确诠释和了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从而将其转化为当今文化艺术创造和精神营构的有效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