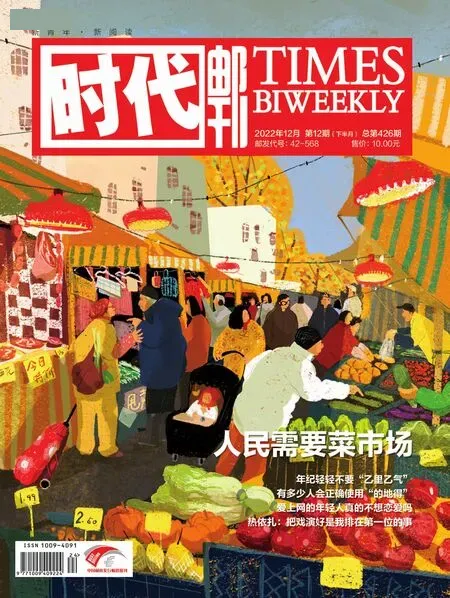17岁遇见一个男孩
文小一

17岁时,我是一个高中女孩,他是隔壁班的男孩。我们所在的两个班是同一位语文老师教的,老师在我们班念他的作文,在他们班念我的作文,于是我们就知道了彼此。
他高高的,瘦瘦的,眉目清俊,不笑的时候忧郁清冷,偶尔一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柔和。这样一个男孩,还写一手好文章,真适合让女孩情窦初开。
在小小的校园里,我们一次次擦肩而过,但不曾交谈。直到有一天,他来找我,说:“我们成立一个文学社好不好?”
文学社最初只有八九个人,大多是我们两个班的。我们还出了几期《文学报》。有一段时间,每天傍晚,我们几个无论是对文学还是对报纸都完全生涩的高中生,在教室、在操场、在草坪上,热烈地谈论着要出一份《文学报》。第一期报纸是他手写的。他的字那么隽秀。我们传阅着那张报纸,觉得新奇、骄傲,又有那么一些羞涩。
冬天的周日,文学社的人一起骑车去江边玩。一个活泼的女孩对我说:“你坐他的车吧。”我不做声。我不要坐他的车。女孩们都喜欢他,他那么适合被喜欢,我不要和他太接近,我不要让大家觉得我也喜欢他。可是,他推着车走到我身边,说:“你坐我的车吧。”
那之前,我们几乎没有单独谈过话。那一路上谈了些什么,我早已经忘了,只记得那一天风很大,江边芦荻瑟瑟,天空风起云涌,令那一次出行多了一些文学的意味。
总有同学在我面前提起他,似乎觉得我应该喜欢他才对,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孩,当然应该喜欢他啊。可是,我不要喜欢他,喜欢他的人那么多,掺和这件事不是太傻了吗?而且有时候,“喜欢”是一件很落俗套的事情。
去上自习的路上,有时遇到他骑单车经过,他脚尖踮地,停下来,叫一声我的名字。有一次经过我时,他将搭在肩上的外套递给我说:“帮我拿着吧,我要出去。”这意味着我第二天得去他们班教室将外套还给他。我想了想,将外套交给了隔壁宿舍他们班的一个女生。
有一天他来教室找我,递给我他的作文本,说:“我有事要出去,作文才刚写一段,你帮我写完吧。”将作文本还给他时,他一边看,一边笑起来,说:“我们算是一起做过坏事了啊。”是,我们仍然不熟,可是一起做过坏事了。
毕业后,我们自然而然地失散了。可是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想起他。我不想忘记他。
如果记忆有气味的话,他留给我的,是春天刚刚苏醒时新叶初萌的气味 — 不 是花的气味,是草木的气味。我喜欢这种气味。我喜欢一个男孩对我说“我们成立一个文学社好不好”,我喜欢和一个男孩谈论“文学”,我喜欢一个男孩骑单车经过我身边时停下来喊我的名字,我喜欢一个男孩说“我们一起做过坏事了”— 女孩也行,只不过我遇到的,正好是个男孩。我喜欢生命中有这样的人,不走近,亦有相惜的默契,像一幅疏淡的山水画,笔墨美,留白亦美。
我喜欢我的17岁,那青涩的,别扭的,骄傲的,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1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