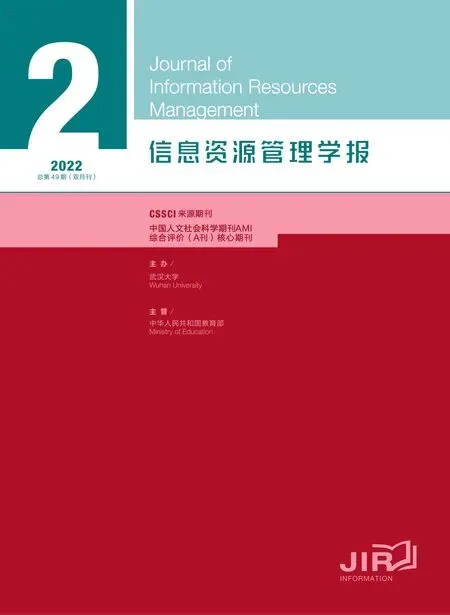美国过程性信息公开中的可预见损害标准及对我国的启示
李瑞瑞 李 斯
(1.东南大学图书馆,南京,211189; 2.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100871)
1 引言
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十六条第二款正式确立了过程性信息作为政府信息的一种存在形态,规定“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形成的讨论记录、过程稿、磋商信函、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以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可以不予公开。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上述信息应当公开的,从其规定”。根据该条,过程性信息具有过程性特点,在时间上形成于最终决定作出之前,表现为讨论记录、过程稿等形式,行政机关的最终决定和决策则不属于过程性信息;过程性信息还具有行政性特点,它与行政机关对外履行行政管理职能有关,内部人事制度、管理规范等内部信息不属于过程性信息。
十六条第二款还规定除“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信息外,其余信息“可以不予公开”,该款与第十四条对国家秘密以及“三安全一稳定”信息“不予公开”的规定不同,意味着过程性信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公开,政府机构对这类信息的公开与否具有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缺乏公开标准,实践中政府机构出于信息公开将被问责或形象受损等考虑,往往会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豁免公开规定。“可以不予公开”的表述容易让政府机构仅凭猜测或笼统的理由就可以拒绝公开信息,变成了绝对不公开。这种处理方式封闭了政府机关的决策过程,不利于透明政府建设[1]。
法规体系建设是政府信息治理或数据治理的基本保障[1]。完善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是解决当前实践困境的有效途径。美国在2016年修订的《信息自由法》等多项法律政策中纳入了可预见损害标准,为政府机构增加审查可预见损害的义务,限制了政府机构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条款的过度使用,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本文将研究美国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制定背景、确立过程、具体内容和司法案例,分析特点,结合实际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2 研究现状
政府信息公开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领域[2-3]。随着2019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修订,对过程性信息的界定以及公开标准的研究成为了热点。梁艺[4]和钟琰[5]认为目前的法律制度中存在对过程性信息的概念界定模糊、公开与否的认定标准不一等问题;影响了行政机关裁量权的适用,导致了过程性信息司法判断较为混乱、案件胜诉率低等问题[6]。鉴于此,许多研究试图界定过程性信息的范围,目前已形成较为一致的认识,即过程性信息形成于行政程序之中,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开始后、行政决策作出之前制作或获取的信息[5,7-8]。关于公开标准,主要从两种视角开展研究。①信息类型视角。如王敬波[9]认为将信息类型化是判断信息能否公开的基础。按照信息的特点可以分为事实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按照信息形成过程可分为行政决策准备阶段、行政决策进行阶段以及行政决策完成阶段等信息。其中事实性信息应当公开,工作人员的意见性信息原则上应当不公开,专家的意见性信息原则上应公开。黎业明[10]认为应最大限度公开事实性信息,意见性信息则需进一步根据利害关系决定是否公开。②信息功能视角。这类研究立足于过程性信息公开后造成的后果,要求政府机构考虑公开信息是否影响政府内部的坦诚交流,权衡保护公众知情权与保护机构决策质量之间的利益后,再决定公开与否。如杨建生[11]认为同时满足协商性、决策前、非依赖三个条件的过程性信息应免于公开;而决策过程中的事实文件、决策后文件或依赖文件应该公开。李幸祥[12]提出可以引入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来审查和确定信息能否公开,如果过程性信息公开不会对机构决策产生实质性损害,则应当公开。
国外文献对“可预见损害”标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该标准纳入法律的意义和影响,提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McDermott等指出,该标准的确立可以限制各机构广泛使用《信息自由法》豁免,特别是审议程序特权,符合推定开放的准则[13-14];Sumar[15]对标准确立后的司法案例进行梳理和分析后指出,法院在认定机构如何达到“可预见损害标准”上存在困境,并提出了对策。
已有研究指出了政府机构使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的随意性问题;强调通过明确界定豁免公开范围和完善公开标准来提升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可操作性,对推动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对于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的研究还需深入推进,采用类型划分的方式不能穷尽,且披露某类豁免信息中的特定信息与保护政府机构决策质量的目标并不冲突。基于信息功能视角提出公开标准是可行的路径,但研究相对缺乏。虽然提及了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但对于该标准的发展历程、具体内容、司法认定等问题还未明确。因此,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开展研究,结合实际提出对我国的启示,以期完善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制度。
3 美国可预见损害标准制定背景及发展历程
了解美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中可预见损害标准制定的背景和发展历程,可帮助理解这一标准制定的现实需求、价值意蕴和立法理念。
3.1 制定背景
美国《信息自由法》第五项豁免保护反映咨询意见、建议和审议的文件,这些文件反映了政府决策和政策制定过程,通常被称为“审议过程特权”(Deliberative process’privilege)[16]。豁免公开这类信息的目的在于防止损害政府机构决策的质量,确保公职人员可以对政策问题进行开放和坦率的讨论,而不必担心遭到嘲笑或问责,以及防止传播与最终决策无关的相关材料而误导公众[17]。
然而,在美国多年的信息公开实践中,审议过程特权被广泛认为是政府机构拒绝公众获取信息最常被滥用的条款之一,成为政府机构隐瞒信息的合法工具[16]。几乎所有在特定决策中产生的信息都会被政府机构划入豁免范围,并且在决策结束后很长时间内都被豁免公开。政府机构援引审议过程特权往往不是为了保护决策,而只是想隐瞒令人尴尬的、不专业的或政治上不方便披露的信息。美国参议院的一项报告指出,各机构依赖自由裁量豁免保留了大量政府信息,即使披露这些信息大多数情况下不会造成损害[15]。仅2013年,第五项豁免就被政府机构援引了81000次[16]。
3.2 发展历程
为解决政府机构过度使用审议过程特权的问题,美国司法部提出了可预见损害标准。随着信息公开进程不断推进,2016年,该标准最终被纳入《信息自由法》。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提出
1993年10月4日,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信息自由法备忘录》中,司法部部长Janet Reno建立了信息披露的新标准:只有在该机构合理预见信息披露将损害受该项豁免所保护利益的情况下,司法部才会为政府机构扣留信息的主张辩护[18]。1994年1月,司法部信息政策办公室(OIP)向各机构发布了一项指南,特别关注政府机构对《信息自由法》第五项豁免中审议过程特权使用扩大化的问题,要求官员考虑披露是否“可预见地损害作为该项豁免特权基础的机构利益”,并列举了在审查中要权衡的八个主要因素,包括所涉决策的性质、地位以及相关人员的情况等[14]。
(2)撤销
可预见损害标准在司法部2001年10月12日的《信息自由法备忘录》中被撤销。根据新标准,司法部鼓励政府机构在根据《信息自由法》作出披露决定时应仔细考虑对所有豁免信息涉及利益的保护。在对所有受保护的信息作出任何自由裁量披露决定时,应充分和慎重考虑信息披露是否会影响到机构决策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利益。在司法审查中,司法部将为政府机构扣留信息的决定辩护,除非政府机构缺乏合理的法律依据[19]。这种“合理法律依据”标准远低于“可预见损害”的标准,要求政府机构从信息不公开的理由考虑问题,而不是推定公开。与可预见损害标准要考虑的八个因素不同,在合理法律依据标准下,政府机构不必提出信息公开可能造成损害的实质性证据,只需要引用《信息自由法》中有关的条款,就可以扣留信息。
(3)再次提出
2009年1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布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信息自由法》的执行应有一个明确的假设:面对怀疑,公开占上风,要求政府机构采用推定披露原则来指导信息公开工作,并指示司法部部长在90天内发布最新的《信息自由法指南》。2009 年 3 月 19日,司法部部长Eric Holder发布了新的备忘录,声明废除司法部 2001 年《信息自由法备忘录》中的公开标准,规定只有在①机构合理预见披露会损害受其中一项法定豁免保护的利益,或②法律禁止披露时,司法部才会为政府机构拒绝披露信息的决定辩护[20]。
(4)纳入法律
司法部的备忘录和指南并不能创造可在法律上强制政府机构执行的义务。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实践的不断深入,2016年6月30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信息自由法改进法案》(FOIA Improvement Act of 2016)[21],修订了《信息自由法》。经修订,尽管有豁免条款规定,但仅允许政府机构在“合理预见披露会损害受《信息自由法》豁免保护的利益时才能向请求者隐瞒信息”,该要求不适用于“法律禁止披露”的信息。这一修订标志着可预见损害标准上升为法律,意味着在信息公开前审查可预见损害成为了强制政府机构执行的程序。2016 年《信息自由法》同时也修订了第五项豁免,规定达到25年及以上的审议过程信息不在豁免公开范围内。当然,这项要求不适用于法律禁止披露的情况,如不适用于受信息保密等相关法律保护的信息。
可预见损害标准经历了提出、撤销、再次提出,到最终确定为法律的过程,反映了公众知情权和政府行政权之间的博弈。提出该标准的现实需求在于解决政府机构在自由裁量公开中过度引用审议过程特权的问题,其目的是通过增加政府机构的负担,帮助公职人员考虑是否主动披露政府信息,限制仅以猜测或对损害的模糊认识而过度援引豁免条款的情况,确保信息能够最大限度公开。
4 美国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具体内容
美国2016年修订的《信息自由法》向政府机构的信息审查工作施加了新的义务。随着相关补充政策的完善和司法案例的出现,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具体内容不断完善。
4.1 《信息自由法》的规定
《信息自由法》第a章(8)(A)(i)规定,政府机构应仅在以下情况下不披露信息:该机构合理地预见到披露会损害受(b)款所保护的利益,或者法律禁止披露。这一条款规定了信息公开中两种豁免公开情形的标准,一种是自由裁量披露,即需要政府机构根据有关原则和标准决定是否披露的情形,适用于可预见损害标准;另一种是法律禁止披露的情形,如根据法律规定,涉及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受法律保护的信息,政府机构无权披露。根据该条,第五项豁免中的审议过程特权适用可预见损害标准[14],政府机构可以根据审议过程特权保留信息,前提是该机构可以合理预见披露会损害受豁免保护的利益,否则应公开[22]。
将可预见损害标准纳入法律也赋予了请求者诉权,如果政府机构援引第五项豁免的审议过程特权拒绝披露信息,请求者可以通过行政上诉程序或司法诉讼来捍卫知情权,要求法院审查政府机构扣留的信息是否达到了可预见损害标准。
4.2 司法部的指南
美国司法部具有鼓励政府机构遵守《信息自由法》的法定权力,司法部的信息政策办公室会定期制定和发布实施该法的指南。
1994年司法部的《信息自由法指南》列出了政府机构审查审议过程信息是否造成可预见损害时需要考虑的八个主要因素,对机构的信息审查具有指导作用,包括:①信息所涉及的决策性质,决策本身是否特别敏感或需要保密。②决策过程的性质,该过程是否需要保密。③该项决策的状态,是否已完成或者尚未完成?如果尚未完成,则披露造成损害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相反,如果决策已经作出,可能性要小得多。④有关人员的状况,披露是否可能影响同一机构的公职人员或其他参与决策的公职人员。⑤损害的可能性,披露事实上会否降低决策质量。如果相关人员确实感到被潜在的披露所抑制,那么决策质量的实际下降空间有多大。⑥损害的严重性,“寒蝉效应”有多大。例如,如果信息不被豁免,可能会影响政府机构继续获取决策信息,但在某些情况下,对机构决策过程的任何预期“寒蝉效应”可能很小,实际上可以忽略不计。⑦信息的年限,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减少了潜在的危害。⑧单个记录的敏感性,记录中的特定信息是否敏感[14]。
这八项因素要求政府机构更多地关注过程性信息公开后的影响,而不是过程性信息的类型。总结起来,包含以下要素:①决策和决策过程本身的敏感性。如果决策本身或决策过程中涉及国家秘密等敏感事项,那么信息应当保密。②信息披露对决策过程损害的后果严重性。考虑信息披露是否对参与决策人员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机构决策质量。例如,过早公开信息会导致参与决策人员暴露在公众批评的目光下,使他们不能自由沟通和协商;另外,有些信息的公开会导致“寒蝉效应”,即如果信息不被豁免,会导致以后决策中参与决策者因担心过程性信息被公开而不敢大胆提出意见,影响决策质量。③成熟原则。过程性信息披露的危害可能会因时间变化而减少,信息应在时机成熟时公开,包含两方面:一方面,考虑决策所处的阶段,如果与过程性信息相关的决策尚未作出,那么公开这些信息的危害性会比较大;如果决策已经通过并公开,那么与此关联的过程性信息应公开。另一方面,即使决策作出后因为决策敏感性不能立即公开的过程性信息也可能在多年后敏感性降低,基于这一考虑,《信息自由法》规定超过25年的审议过程性信息将不再豁免公开。④可分割性。即使一个文件满足豁免公开的条件,政府机构也要考虑其中是否存在可公开的信息,并将可公开的信息与豁免公开的信息进行分割后再公开。
4.3 司法案例
判例法的发展为政府机构的信息审查提供了更好的指导,许多申请人胜诉的司法案例实践正推动着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实施走向深化。政府机构除了遵守司法部的指南外,还应遵循法院在司法案例中发布的指导。
第一个对可预见损害标准进行解释的案例是2018年的Rosenberg诉国防部案[23]。两名记者要求访问Kelly将军在担任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时期的邮件。国防部向请求者公开了部分信息,同时援引第五项豁免扣留了部分信息。原告辩称,国防部的解释不符合可预见损害标准。双方的争议要求法院确定政府机构如何证明才能满足可预见损害标准。
在美国,有关《信息自由法》的案件要求政府机构提交一份宣誓书,其中应阐述扣留信息的理由。法院认为,要满足可预见损害标准,国防部必须解释被扣留的信息具体将如何损害该机构的决策质量。国防部可以通过分类方法,将类似的信息集中在一起,但仍需解释披露每一类信息的可预见损害。但国防部在其提交的宣誓书中笼统地说明披露所有被扣留信息将危害机构内部的自由交流,这一说法不符合可预见损害标准。法院驳回了国防部扣留信息的动议。
但是,法院审查是慎重的,并没有立即强制国防部披露信息,而是允许其再次补充声明,证明满足了可预见损害标准。在秘密审查了一些有争议的信息后,法院才最后作出裁决。
自此以后,涉及可预见损害标准的案件都普遍效仿该案。在2021年7月记者委员会诉联邦调查局一案中,法院结合Rosenberg诉国防部案阐明政府机构必须通过以下测试,才能根据审议过程特权和可预见损害标准扣留信息:可预见性要求机构必须具体解释信息披露如何“将”而不是“可能”对内部审议产生不利影响;敷衍声明披露所有被扣留的信息将危及机构内外高级领导人之间的信息自由交流是不够的;相反,需要有针对性和具体地证明为什么披露特定类型的信息会损害机构决策的质量。
应用该测试,法院认为联邦调查局的声明完全是概括性和结论性的,只提供了一般性理由,忽视了确定披露每条特定记录会损害利益的具体义务[24]。最后,法院推翻了地区法院允许联邦调查局扣留部分信息的决定。
目前,司法实践中已经产生了许多申请人胜诉的案件,表明可预见损害标准有效限制了政府机构对审议过程特权的滥用。
5 美国过程性信息公开中可预见损害标准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有效限制了政府机构对过程性信息豁免条款的过度使用,并随着相关补充政策和司法案例的推进不断完善,该标准在所体现的立法理念、操作程序和司法审查等方面具有独特性,对我国政府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的立法理念、立法内容和司法审查等方面都具有启示意义。
5.1 美国过程性信息公开中的可预见损害标准特点分析
(1)体现了推定开放的立法理念。可预见损害标准被纳入《信息自由法》,体现了美国推定开放的立法理念。美国司法部曾表示,该标准的确立是实现最大限度披露目标的基础[14]。本质上,可预见损害标准要求以开放性的假设审查记录,政府机构应首先考虑确定哪些信息可以披露,而不是哪些信息可以扣留,除非该机构能表明披露将损害受到保护的利益。只有符合可预见损害标准的信息才能豁免披露,否则不能向公众隐瞒。
(2)要求政府机构逐一审查信息,并阐述扣留信息的实质性证据。在《信息自由法》修订之前,政府机构可以在没有实质性证据的情况下援引审议过程特权条款。可预见损害标准给政府机构施加了新的义务,使得审查可预见的损害成为信息披露的强制性步骤,可预见损害的要求也逐渐明确。首先,在审查的粒度上,政府机构必须逐一审查每条信息,而不是某类信息;第二,在确定信息损害性时,要考虑所涉及决策及过程的敏感性、披露信息对决策过程的损害性、时间因素和信息的可分割性,清楚地阐明披露特定信息将造成的实质性损害,并使用事实支持;第三,可预见性要求政府机构明确损害的可能性是“将”,而不是“可能”,政府机构不能依靠猜测或对尴尬的恐惧来隐瞒信息。
(3)法院对判决信息公开与否采取慎重态度。在司法审查中,当政府机构宣誓书中的阐述没有达到可预见损害标准时,法院不会立即判决政府机构公开信息,而是要求政府机构补充可预见损害的阐述,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于信息能否公开的慎重态度。因为政府机构没有充分解释信息披露的危害,并不代表信息的披露就没有危害,法院给予政府机构补充说明的机会,帮助政府机构充分考虑信息披露的危害性,防止豁免公开的信息最终被披露。
5.2 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启示
过程性信息公开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出于各种原因,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还有待完善。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对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的建立具有一定启示意义,有助于完善我国过程性信息公开制度。
5.2.1 对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范围作狭义界定
当前,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只明确过程性信息属于相对公开的信息,但没有提供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关于公开标准的制定,本文认为应符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立法原则。事实上,我国“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与美国“推定公开”原则一致,都鼓励政府机构积极公开信息,面对审查中存在疑问的信息,除非有实质性的理由,否则应鼓励公开。目前的实践和研究主要从正向视角研究可公开的标准,即只有符合标准的信息才能公开,对公开范围作了狭义解释。要实现“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准则,应推定信息公开,从反向视角制定例外不公开的标准。
借鉴美国的立法经验,对过程性信息的豁免公开范围应作狭义的界定。本文建议我国应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或是相关的补充政策中,从反向视角规定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即除非满足何种条件,否则信息都应该公开。
5.2.2 引入可预见损害标准制定我国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
我国“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昭示政府信息公开的应然逻辑是符合公开要求的信息都应充分开放,人民群众应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受益人,任何一个主体或过程都不应该使这一目的发生偏离。然而,现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给行政机关留下自由裁量权的开口[25],政府机构往往出于机构自身的利益而拒绝公开信息,背离了信息公开的应然逻辑。如果过程性信息公开没有一个必要的限度加以控制,那么滥用裁量权的几率就会增加[26]。因此,制定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是当前要重点解决的问题。本研究认为,可引入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来制定我国的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
引入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原因在于当前一些学者所认为的事实性过程性信息应公开、而讨论性过程信息应豁免公开的做法容易导致政府机构僵化执行。对过程性信息豁免公开的认定,不应以信息的概念和类型为核心,本质上,过程性信息背后的交流过程以及其中体现的利益取舍才是豁免公开真正的保护对象[5]。因而,过程性信息公开与不公开的区分,是保护公众知情权与保障行政效率之间的利益衡量。引入可预见损害标准,可以避免行政机关过于僵化地对待过程性信息的公开申请,也可以使信息公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12]。
在立法路径上,应把可预见损害标准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为政府机构的一项法律义务,并在相关的补充政策中规定可预见损害标准的内容。如此,可以让政府机构审查可预见损害成为一项强制义务。当公众认为信息并不符合标准时,赋予公众的诉权也可以让他们采用司法审查手段寻求救济。
结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实际,借鉴美国政府机构的审查标准,我国可要求政府机构审查可预见损害时应考虑以下因素:第一,过程性信息所涉及决策或决策过程的敏感性,是否适宜公开;第二,如果公开过程性信息,是否确定会影响到决策制定的质量、决策的有效执行以及社会秩序;第三,成熟原则,主要考虑内容的成熟度,过程性信息所涉及的决策是否已经完成,或者如果信息年代久远,公开的危害性是否已经减轻;第四,可分割性,政府机构对过程性信息的审查粒度应尽可能细,考虑在被豁免的文件中是否含有可公开的信息,如果含有,可通过技术措施公开可以公开的内容。
5.2.3 法院应加强对过程性信息公开案件的实质性审查
笔者于2021年8月20日在北大法宝中检索有关过程性信息的案件发现,自2019年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来,有关过程性信息的案件记录共有562条。法院对案件的审查只进行了程序性审查,即只审查政府机关是否遵守程序对过程性信息进行认定,以及是否向申请人说明理由,如果行政机关决定不公开,法院大多从其规定判决不予公开,而不审查其具体的理由。如在2021年5月18日审结的李洪波诉沈阳市房产局一案中[27],原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为沈河区东滨河路听雨里棚户区改造《拆迁条件审批表》,法院认为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及市征收办情况说明,该表应属于请示报告等过程性信息,且并无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当公开,故被告对原告作出的答复内容亦无不当,应予维持。与此类似的案例还有2021年5月审结的张巍诉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案、2021年5月18日杨春霞诉郑州市公安局案等。我国法院只从程序合理性审查就支持不予公开过程性信息,损害了原告的知情权和诉权[7],也使得实践中政府机构对该条的滥用日益增多。
借鉴美国对过程性信息公开的司法审查经验,司法审查的重点不应在于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而在于公开是否会损害到政府机构的决策质量、行政效率或者对社会造成危害。我国法院应加强对过程性信息公开案件的实质性审查,用更多的申请人胜诉案件推动政府对过程性信息的公开。在具体操作上,法院应把信息类型认定和是否公开认定分开处理。首先依据相关法律对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进行界定,其次对政府机构豁免公开的理由进行实质性审查,以确定政府机构的陈述是否能充分说明信息的公开将危害到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如果政府机构说理不足,法院可以驳回其豁免公开的决定。当然,在司法审查中,也应采用审慎原则,在政府机构说理不足的情况下,可以要求其补充说明,防止豁免公开的信息被公开。
6 结语
由于我国缺乏过程性信息的公开标准,使得政府机构自由裁量权扩大,存在过度使用豁免条款的现象,影响了政府信息公开进程。借鉴美国的经验,我国应制定符合“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原则的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对过程性信息的公开范围作狭义界定。结合我国实际,引入美国的“可预见损害”标准制定过程性信息公开标准,并将公开标准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相关补充政策中。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应加强对过程性信息公开案件的实质性审查,不仅应审查信息是否属于过程性信息,更要进一步审查公开是否会损害到政府机构的决策质量、行政效率或者对社会造成危害,以更多胜诉的司法案例推动过程性信息的公开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