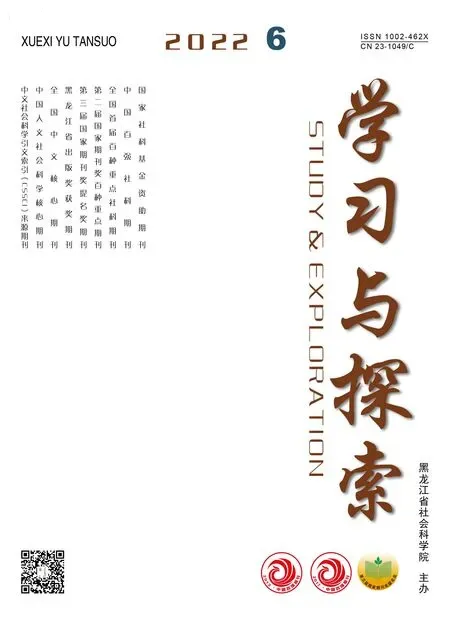“法庭之友”的多元检视
——兼论我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的构建
杨 博 超
(中国政法大学 人权研究院,北京 100088)
“法庭之友”(拉丁语amicus curiae,英文friend-of-the-court),字面意为“法院的朋友”,《布莱克法律词典》将其定义为对案件实质问题有重大利害关系的非诉讼当事人(组织),主动申请或应法院要求而向法院提交书面意见。(1)① Black’s Law Dictionary (9th edn.), West Publishing, 2009, p.98.应当说,“法庭之友”制度是民意与司法互动的较好实践。该制度肇始于罗马法,在普通法国家发挥着传统作用,而后在美国充分发展成为一种现代司法工具,形成了较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在实践中,除国家司法机构外,区域性司法机构如欧洲人权法院、中美洲人权法院,以及准司法机构如WTO争端解决机制等,也引入了该制度。
对中国而言,并没有与“法庭之友”相对应的制度,但对照“法庭之友”的定义可以发现,中国的司法鉴定制度、专家辅助人(有专门知识人、专家证人)制度、专家论证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法庭之友”所倡导的司法参与精神。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若干重要文件均将司法参与作为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手段和宏观规划,(2)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拓宽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 “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进行了宏观规划。参见《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第1版,2014年10月29日第1版。司法参与也因此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要路径。但从实践来看,专家法律意见或专家证人制度体系在我国尚未充分建立,鉴定人、专家证人、有专门知识人、专家咨询意见等在参与司法程序方面仍存藩篱,基本定义和界定也尚未完全厘清。其中,专家咨询意见的法律规范留白尤多,甚至可以说处于无序状态,例如对署名、受资助情况、内容格式、书写规范、提交程序等均缺乏具体要求。应当承认,社会关系的日益复杂必然导致法律适用的复杂化,加之职业法官制度完善尚需时日,难以期待法官对案件涉及的所有法律事实和程序均充分思量并了然于胸,而依照中国法律文化传统和实际构建符合中国司法特色的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将有助于提供充分的事实和法律论据,帮助法官作出公正判决,从而实现司法民主多元化。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学术界专门研究“法庭之友”的成果尚不多见,大多讨论其与专家辅助人和专家证人的区别、历史沿革、主题特征、制度的利弊分析等,亦有论文在论述其他法律问题时涉及这一制度。因此,本文将在厘清“法庭之友”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融合普通法系国家制度的运行模式和构成要素,分析这一制度的实践情况,深入探讨“法庭之友”意见书的价值和面临的挑战,以期对中国专家法律意见书形成实体和程序化规范作出有益探索。
一、何谓“法庭之友”:起源和特质
“法庭之友”在普通法和大陆法地区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包含准司法机构)中已成为使用频率较高的拉丁文词汇,但“法庭之友”到底为何意?其在法律诉讼中的作用又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给予厘清并作出回答的问题。
(一)“法庭之友”的基本内涵
谁可以成为“法庭之友”?学界和实务界一直在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Christina Murray曾言,判断谁不是“法庭之友”要比确定谁是更容易[1]。“法庭之友”这一概念经过长久发展,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职能广泛、作用多样的通用概念(versatile)。如果未充分梳理“法庭之友”产生的历史渊源,加之概念的模糊,就可能导致对“法庭之友”机制的滥用。在许多司法机构中,也尚未建立起针对该机制的法律规范体系,包括如何认定及其构成要素等。这种情形犹如硬币的两面:一方面为“法庭之友”发展提供了较为灵活的空间,有利于制度创新;而另一方面,则可能产生概念模糊的后果。如在英国Ex parte Lloyd破产案中,一位律师接受了双方的聘请,这使得他左右为难,而大法庭法官则认为他无权指定律师应该代表何方。同时,法官亦不想失去自己在法庭中的主导地位,于是任命自己为“法庭之友”,并以此种身份向律师提供建议。由于缺乏精确的规则,法官成为自己的“朋友”。(3)Ex parte Brockman, 134 S.W. 977, 233 Missouri Reports 135 (Sup. Ct. 1911).关于此案例评述参见:Samuel Krislov, “The Amicus Curiae Brief: From Friendship to Advocacy”,Yale Law Journal, Vol. 694, No. 72, 1963, pp. 695-696.
从法律语言表述习惯看,使用拉丁文表达的法律术语一般是简单而精确的,但“法庭之友”却正相反[2]。若将拉丁文直译为“法庭之友”,则经常会对其性质和范围造成混淆,并可能掩盖这一概念的真正内涵。由于多年来包含英国和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国际司法机构对这一古老制度的使用和发展存在诸多差异,使得各种版本的法律词典中的词义翻译也有不同侧重。因此,仅将其拉丁文表述翻译为“法院的朋友”,似乎是一种“想当然简单化”(deceptively simple)的结果。
若求助于词典,则可能对理解“法庭之友”的概念没有太多裨益,即使捻熟法律的人士在同一法律体系下也可能对此概念的构成要素产生疑惑,更遑论不同司法体系中对此概念的理解。各类词典对“法庭之友”的概述参见文末列表。
各法律词典的多种表述,进一步展示了“法庭之友”定义的模糊性。从主体资格看,“法庭之友”是人还是组织?是否必须有法律背景?是法院的独立顾问,还是具有党派背景但主要为法院提供协助的人士?是协助法律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又或两者皆有?从出庭程序看,是法院邀请参加还是主动参与?有学者用英文介词“of”和“to”来描述“朋友”(friend)和法庭的关系,即“朋友”仅是为了向法庭提供信息,以避免法庭出现错漏,而自身并未寻求或期待对最终结果的影响(“of”表明独立和中立,强调“协助”);又或是为了说服法院采纳其提供的相关意见,不论最终结果是否存在利益(“to”表明参与和施加影响,强调“说服”)。这种对“法庭之友”的目的性解构已经超出了语义学范畴,更多地表现了对其学理研究及对普通法系司法审判产生的影响。
若求助于法律史,在罗马法中,一般任命博学的法学家依照法院要求提供建议,这或许是“法庭之友”的雏形。在中世纪普通法体系中,“法庭之友”(amicus)获得了比罗马法中更广的角色[3]。由于司法程序是在城市公共广场上举行,旁听者可以随时作为“法庭之友”介入,与法官分享相关信息。由此,对“法庭之友”的起源,学界存在两种认知:一是认为虽然大陆法体系中也存在“法庭之友”制度,但这一制度发源于普通法系[4];二是认为“法庭之友”制度起源于9世纪的罗马法。(4)很多中国学者在提及“法庭之友”制度时持此主张。
持有第一种意见者,从早期法院《(判例)年鉴》(5)指一系列用诺曼法语(Norman French)记载英格兰中世纪案件辩诉情况的判例集。中梳理出“法庭之友”的渊源来佐证其观点。如1957年的加拿大Grice v. The Queen案,Kozak法官将“法庭之友”定义为:当法官对法律问题或事实产生疑问时邀请的旁观者(bystander)。在通常的实践中,该术语意味着“友好的干预”(friendly intervention),提醒法院可能产生错漏风险的某种法律问题。(6)Grice v. The Queen (1957), 11 DLR (2d) 699, p. 702.在早期的普通法实践中,任何在法庭上的人均可以作为“法庭之友”为法庭提供建议。持有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1686年英国的Horton v. Ruesby案是“法庭之友”成为一项可以应用于审判制度的最早实践。(7)Horton v. Ruesby, 90 Eng. Rep.326(1686).根据4Hen.IV(1403)规约,任何陌生人均可参与法庭活动;但根据法庭习惯,只有大律师(barrister)或代理律师(counsellor)(8)Counsellor指可在所有法院执业的律师,在英格兰法庭已不使用这种表述,但在爱尔兰和美国时有使用。才可作为第三方被确认为“法庭之友”,可以行使引导、预警、报告职责。几个世纪以来,“法庭之友”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在发挥作用,不仅是为了彰显民主参与、维护“法庭荣誉”帮助法庭作出正确判决,而且从公共利益层面,被作为防止司法专断和维护自由政府的重要手段。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法庭之友”起源于罗马法实践。但对于罗马法对“法庭之友”的描述,则缺乏直接的资料或文字的证实[5]。Frank Covey提出了相反意见,在考察了第三版《布维尔法律词典》对“法庭之友”的描述后,他认为“法庭之友”这一概念在罗马法中的表达和其应有的内涵并不一致。根据《布维尔法律词典》,在罗马法中,“法庭之友”为一位由法官任命的顾问(consilium),(9)Consilium在罗马法体系中一般有两层含义:其一为中世纪罗马法学家作为顾问给统治者提供的建议,其二为奥古斯丁设立的“君主顾问委员会”(concilium principis)。文中为避免翻译与“法庭之友”混淆,部分采用拉丁文原文表述。当法官产生疑问时为其提供建议[6]。而“amicus”和“consilium”所具有的不同内涵,则让人对“法庭之友起源于罗马法”这一论断心生疑惑:一是consilium仅能依照法庭要求提出建议,而“法庭之友”可以主动参加法庭活动;二是consilium可以依照法庭要求对抗刑事审判被告人,而“法庭之友”则几乎没有可能站在刑事被告人的对立面。但也有学者认为Covey的论述受到美国司法体系下“法庭之友”制度的影响,曲解了古罗马法体系下对“法庭之友”的规则设定[7]。
一些研究罗马法的专著或许可以揭示出“法庭之友”制度在罗马的运转过程。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奥古斯丁大帝曾颁布法令,授予杰出法学家以皇帝名义发表意见的权利(ius pubice respondendi)[8]。罗马皇帝哈德良也曾聘用知名法学家作为顾问(consilium),据说这一制度延续了四个多世纪。这样的传统一定程度上确定了“法庭之友”制度的罗马法渊源。主权国家出现后,罗马法对西欧法律体系产生影响,并通过殖民而扩展到其他国家,如法国、荷兰、西班牙、南非、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也有学者认为这种制度曾出现在中国[9]。而作为“罗马法传统最丰富的花朵”[10]的国际法,也在司法体系或准司法体系中引入了“法庭之友”制度。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在现存古罗马法律文字或学术著作中,虽然有类似于“法庭之友”的表述或者某些职位的设定,也体现了“法庭之友”的精神和职责,但和现今使用的拉丁文术语并不一致。所以有学者说,要发现罗马法规定的顾问机制的真正内涵,总是“异常艰难”[11]。
(二)“法庭之友”的特质和价值
通过对“法庭之友”概念和内涵的描述,可以总结出其具有以下特质:一是要求“法庭之友”提供协助是法庭的固有权利。这种特质主要源于普通法系对“法庭之友”制度的发展,即在特定的司法管辖区域的法院要求法律人士对特定事项提供专业意见。
二是“法庭之友”作为“旁观者”(bystander)介入。这一理论建立在普通法系早期的实践中。在一段时间之内,被指控有严重刑事犯罪的人是不被允许聘用代理人的,即被指控人必须自行回答关于犯罪行为的内容,而不得聘用律师代表其发言。Herman Cohen在对英国早期律师制度的研究中发现,被告由其“朋友”陪同出席的部分原因或许是避免“法律之外的复仇”[12]。简言之,“旁观者”的身份并非受限于律师,他们被允许协助法庭的制度是通过普通法的司法实践逐渐确立起来的。“法庭之友”的设置是为避免司法审判错漏而允许律师协助法官,从而保障刑事案件中“无辩护能力”的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
然而,这种“旁观者介入”是否能真正代表“法庭之友”的性质和目的也受到质疑。1968年英国大法官Salmon勋爵在Allen v. Sir Alfred McAlpine & Sons Ltd案判决中描述了“法庭之友”的角色:“‘法庭之友’扮演了中立的协助法院解释法律的角色,抑或在案件中的某一方未缺席的情况下代表其阐述法律主张。”(10)Allen v. Sir Alfred McAlpine & Sons Ltd (1968) 2 QB 229 at p. 266 F-G.根据《美国联邦法规》(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CFR)规定,“介入”(intervention)制度可被解释为“个人或组织认为审判程序或审判裁决可能对其权利或义务产生影响,而依愿加入审判程序”。(11)CFR 1201.34 (a). 关于介入制度权利、条件和程序之规定,参见《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Federal Rules of Civil Procedure,Fed.R.Civ.P)第24条。依据该程序而介入审判的主体可被称为“介入者”(intervenor/intervener),该主体享有法定参加权利。由此可见,“介入者”可被认为是诉讼主体(a party),法院判决对其产生拘束力;而“法庭之友”则为非诉讼主体(a nonparty),不受法院判决约束[13]。同时,《美国联邦法规》还规定:“任何人或组织不符合介入者身份参加法庭审判,均可向法院提起申请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12)CFR 1201.34 (e) (1).
三是“法庭之友”为法院提供口头案件索引(oral shepardizing),以维护法院的荣耀和声誉。在英国1656年Protector v. Geering案中,判决指出避免错漏是法院的荣耀,如果法官存在未尽注意的严重失误或犯有职务错误,将与“野蛮人”无异。(13)Protector v. Geering, Hardres 85, 86, 145 Eng. Rep. 394 (1656).See Edmund Ruffin Beckwith and Rudolf Sobernheim, “Amicus Curiae-Minister of Justice”,Fordham Law Review,Vol.17,Issue 1,1948,pp.38-62.“法庭之友”据此被允许向法院提出撤销之前错误决定的请求。同时,为避免法官对法律适用和先例判决的疏漏,“法庭之友”可提请法院注意先例判决或超出其注意范围的专业知识,发挥案件口头索引的功能。这也被认为是普通法体系中“法庭之友”一词的由来。如在1990年美国联邦最高院Maryland v. Craig案中,美国心理学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APA)利用专业知识作为“法庭之友”提交了书面材料,并被法官在最终意见中予以引用。(14)Maryland v. Craig, 497 U.S. 836(1990).Citing Brief for Amicus Curia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in Support of Neither Party, Maryland v. Craig, 110 S. Ct. 3157 (1990) (No. 89-478).
四是“法庭之友”制度有助于克服抗辩制“党派影响”或“两造抗辩”的缺点。抗辩制将司法活动局限于争端方之内并作为追求正义的本质,仅聚焦争端本身涉及的问题,过程中没有更广泛的第三方参与或公共利益的考量。而普通法下对抗式司法程序的本质迫使人们不得不接纳一个独立顾问,并代表第三方向法院提供协助。近年来,一些司法体系越来越愿意使用“公共利益”作为解释第三方参与的理由。“法庭之友”机制在普通法体系发展过程中产生分野:美国法律体系下的“法庭之友”保持着更多的对抗性,以实现其“民主增强”(democracy-enhancing)功能;在其他国家这种制度则较为柔和,“保持着罗马时期的纯洁性”。持“法庭之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制度自罗马之后融入了英国普通法,虽然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名称,但因其具有可调试性而被沿袭下来。
二、何以“法庭之友”:实践和挑战
“法庭之友”制度不断发展,产生了多种表现形式,在提升多元司法和公共利益的参与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但同时其可靠性和可信性也面临挑战。
(一)基于历史实践视角的“法庭之友”类型
根据“法庭之友”的发展进路和特质,可以大体将其分为传统意义上的“法庭之友”、作为旁观者或介入者的“法庭之友”、由法院指定的“法庭之友”、非当事人的直接利益第三方、政府官员作为“法庭之友”、社会或政治利益集团作为“法庭之友”等。
传统意义上的“法庭之友”恪守为法官提供中立意见的职能,仅当法院认为需要当前争端各方的信息时,指定具有足够专业知识的律师提供独立和中立意见。这类“法庭之友”更贴合罗马法中的描述,它并非倡导者、介入者或诉讼的一方。某些英联邦国家也有这种规定,如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公益律师可以代表无律师的被告一方,也可以申请到场进行旁观并向法院提供报告。此种类型的“法庭之友”一般具有这样的特点:其一,主体是受过法律训练的人,类似于罗马法中的“consilium”概念。同时,与罗马法规定类似,“法庭之友”一般是无偿的,律师一旦被法院任命,将视为对自身地位、专业知识和智慧的认可,代表了荣誉和声望。其二,程序上经由法院的任命,即在公共利益的需要下经过法院任命或经法院要求才能行使“法庭之友”职责,“法庭之友”的意见书也可能被法院引用。其三,“法庭之友”并非诉讼一方,而是独立的、非党派的法庭顾问。1988年澳大利亚“US Tobacco”(美国烟草)案中,法院强调“法庭之友”概念与介入者相对立,其在案件中不能代表争端当事人的个人利益,也不提供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立场的观点表述。(15)United States Tobacco Co. v. Minister for Consumer Affairs[1988]83 A.L.R.79(F.C.A.)[US Tobacco].而在2002年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案件中,英国上议院在审议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是否可以就人权法问题介入北爱尔兰法院和法庭的诉讼问题时指出,作为不具党派立场的“法庭之友”与介入者存在差异,并否决了北爱尔兰人权委员会作为“法庭之友”参与诉讼的主张,理由在于委员会“极力主张其所持有的对人权和人权保护的看法”,这与“法庭之友”协助法院的职责并不契合。(16)Judgments - In Re Northern Ireland Human Rights Commission,[2002] UKHL 25.总结而言,传统意义上的“法庭之友”不介入或干预法庭审判,只是通过法院邀请而提供公正的信息、阐述法律事实或解释法律适用,以追求判决的公正。
“法庭之友”作为旁观者或介入者是在中世纪普通法中发展出来的功能。这主要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其一,14世纪的司法审判大都在城市公共广场举行,并对旁听者开放,他们可以介入审判,但对于参与的程度和被法院接受的程度,文献中并没有清晰描述。其二,在当时的一段时间内,刑事案件中的被告无权获得律师的辩护,而被定罪的被告将受到严厉的处罚,出席审判的各方可以通过向法庭提供信息来介入审判,从而帮助被告。其三,从《(判例)年鉴》中的案例可以看出,13世纪后,少数活跃的英国大律师经常被法院要求出庭并提供咨询服务。在现今的美国法院,法官时有要求具有“法庭之友”身份的律师协助法院工作或在案件早期即介入司法程序。即使在19世纪70年代前的美国,若“法庭之友”碰巧参与法院听证会,也会自发地口头向法院提出建议[14]。
由法院指定的“法庭之友”、非当事人的直接利益第三方、政府官员作为“法庭之友”这三类,主要功能在于实现对诉讼的支持(supportive)。由法院指定的“法庭之友”主要为保证司法公平,代表未获得辩护人的诉讼一方陈述案情。非直接利益第三方作为“法庭之友”,即允许非当事方在某些情况下作为“法庭之友”参加诉讼。这种类型主要出现在介入制度出现之前,一般是与案件有直接利益的人士,并对法院查明案件具有重要作用。如1736年英国的Coxe v. Phillips案,Muilman作为第三方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诉讼,并阐明她的婚姻状况,以佐证相关合同条款的有效性。(17)Coxe v. Phillips, 95 Eng. Rep. 152 (K.B. 1786).政府官员作为“法庭之友”则是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其主要职责是向法院通报公共政策问题。在 1854年美国的Florida v. George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批准了之前被州政府拒绝的由司法部长担任“法庭之友”的动议,(18)Floriday v. George 58US (17How) 478 (1854).由此推动了“法庭之友”在美国的重要发展,并确立了政府非经当事人同意亦可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制度。迄今,美国主要的宪法诉讼几乎都有政府参与,即使他们并非司法程序的当事方。英国1967年的Rondell v. Worsley案、新加坡1988年的Times Publishing Bhd v. S.Sivadas案中都有政府官员作为“法庭之友”的身影。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政府作为“法庭之友”参与的模式与14世纪的罗马相类似,作用在于帮助法院避免错漏[15]。
政治性或社会性的“法庭之友”展现出对审判结果的强烈关注,这种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19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几乎已经不存在提供无偿法律咨询以协助法院工作的传统类型的“法庭之友”。其带来的结果是,关注社会议题或政治议程的利益集团形式的“法庭之友”数量激增,“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数量也急剧上升。到20世纪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中超过85%附有至少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而在一些社会影响大、涉及特定群体的案件中,经常会收到数十件“法庭之友”意见书。如“法庭之友”向2018年“同性婚姻蛋糕案”提交了95份意见书,向同年的“川普旅行禁令案”提供了73份意见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早期类似的案件中,如在消除种族歧视领域具有标志性的“布朗案”中,仅有6份“法庭之友”意见书。这种数量上的悬殊落差表明,“法庭之友”愈发意识到法院是推动社会法治改革的重要通道,因此更乐于在法庭上开展“游说”(advocate)活动。
(二)基于现实视角的“法庭之友”面临的挑战
自1823 年Green v. Biddle案,“法庭之友”首次出现在美国司法审判中,至21世纪其数量呈“井喷式”增长,迫使美国最高法院修订了“法庭之友”规则,以提醒各方应向法院提交法院尚未掌握的新的且与案件相关的事项。同时,法院要求“法庭之友”在意见书中要说明是否得到当事方律师的协助,并且明确列出对该意见书的资金支持者。“法庭之友”制度在美国法律体系下深入发展,并放大了其在司法体系中的作用:除增强司法民主、提供涉及案件的更广泛的信息(如立法背景和特定制度的实际运作模式等)和观点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释放案件是否具有被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紧迫性的信号(政府类“法庭之友”或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团体在此方面有重要影响)。事实上,并非所有的“法庭之友”意见书都被法院重视。Scalia大法官曾言,联邦政府作为“法庭之友”的意见书一定会被阅读,某些社会团体的法律意见书也有很大几率被阅读,又或者法官认为某个(些)“法庭之友”具有被法官信赖的品格或专业能力时,可能会关注其意见书[16]。
随着“法庭之友”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愈发重要,越来越多的案件判决开始引用“法庭之友”意见书中的观点,但这也对司法体系产生了某些消极影响。
首先,为使“法庭之友”意见书更具说服力,出现对案件争议焦点问题使用“现身说法”(voice briefs)形式提出法律意见的趋势,这种趋势导致了判决中反对意见的增多。在2016年美国Whole Woman’s Health v. Hellerstedt案中,百位以上的女性律师、教授和退休法官,在“法庭之友”意见书中通过描述自身堕胎的经历,说明最高法院判例赋予女性自主决定是否怀孕的权利对女性人生发展的重要性。 2015年美国同性恋合法化判决Obergefell v. Hodges案中,支持同性恋的非政府组织向法院提交了“法庭之友”意见书,其中涵盖八个以第一人称记述的真实案例,借以向法院传达同性恋者婚姻的幸福和稳固性,并希望通过法院判决洗清对同性恋的污名化。事实上,大量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有时会相互矛盾,进而导致了信息和数据的混乱。1945年之后,美国最高法院的不一致裁决也因此明显增加,频繁的异议裁决造成了法律不确定性的风险,这与公共利益相悖。
其次,法官引用“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比例逐步上升,忽视了当事人的陈述。美国早期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规则中只允许非当事人在诉讼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向法院提交意见书,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仍会相当频繁地批准可能未被任何一方同意而提交意见书的请求,从而导致意见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审判过程中。从联邦最高法院的实践看,“法庭之友”意见书已经为历史上若干件有影响力的案件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是在 Mapp v. Ohio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诉讼各方在论证非法搜查和扣押问题方面相当失败,因此,在起草裁决时频繁引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ACLU)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最后,“法庭之友”在司法中的体系性发展和权限拓展,致使其开始深度介入司法审判,导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并削弱了司法透明性,如帮书记员找到“好案子”(good case)和帮助法官宣布更广泛适用的法律规则。但仍有学者认为,“法庭之友机制化”(Amicus Machine)有利于司法制度创新[17],这种模式将政府类“法庭之友”所占据的优势分散到更广泛的人群中,从而增加具有声望的对案件的“感兴趣方”(interesting parties)成为“法庭之友”,进而监督法院提出的不恰当主张。但这种观点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当前具有影响力的“法庭之友”基本上被“精英俱乐部”(elite club)所垄断,“法庭之友”促进法治民主的理想面临挑战。一方面,机制化时代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主要为了迎合书记员的“口味”。因书记员在法官撰写裁决中占据事实上的重要地位,法律精英提供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会帮助书记员形成解构法律问题的思路,从而使意见书成为书记员引用和使用的工具,这也是意见书篇幅越来越长的一个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法律精英提供的法律意见书,很多时候是由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法庭前书记员执笔起草的,这些前书记员很了解阅读者的需求,这种利益交换式的交叉引用也使得“法庭之友”失去了司法公众参与和追求司法民主的本意。
三、凿渠引水: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的发展进路
从各国的司法实践可以看出,“法庭之友”制度起到了开放司法民主渠道、凝聚民意、帮助法官全面掌握事实、增强司法公信力、推动法律发展等作用,但过度自由的“法庭之友”也给司法体系造成了消极影响。对中国而言,借鉴“法庭之友”的优长之处,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家法律意见制度对完善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实现人民群众参与司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不在科学技术意见(专家鉴定结论或专家证人陈述)方面过多着墨,仅对法学专家针对法律适用、量刑标准、法律程序等阐述其看法或意见的文书进行讨论。
(一)专家法律意见与多元化司法民主
中国司法体系建构的专家论证制度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个体户戴晓忠因技术转让被杭州市检察院以“科技投机倒把罪”逮捕并起诉,其代理律师将专家意见融合至辩护词中,使得戴晓忠被无罪释放,此案被认为开创了中国专家论证的先河。在此案影响下,原国家科委制定了科技人员技术转让条例,此后,专家论证制度在中国得到快速发展,并鉴于其早期对中国司法审判的推动作用而获积极评价。然而,2002年“刘涌黑社会案”审理中提交的专家论证意见,使得法律专家对案件发表意见的公正性及合理性受到质疑。2019年“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控告魏银仓孙国华非法侵占公司财产案”又将该制度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学术界对法律专家意见的程序规范及存废展开新一轮争论。
专家法律意见是中国司法实践中产生的特殊法律现象,其存在的必要性主要涉及追求司法公正(抵制司法腐败)和提供法理支持(帮助法官理清事实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从中国司法发展历史来看,由于中国法学教育曾中断,导致中国法律专业执业人员有一个时期严重短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力推进法治建设和法学教育,司法人员整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司法中仍然存在法官对法律的理解能力和领悟水平较低的情况。由此,当事人对法院判决结果公正性存在怀疑,进而希望求助法学专家对案件就法律背景、解释和使用等提供具体咨询意见,以期凭借专家的权威性和话语权(或者是在舆论上所具有的潜在号召力)使法院支持其主张。
从法官角度来看,专家法律意见可为法官审判案件提供启发和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吴晓芳法官曾指出,好的专家法律意见将会为法官对于法律事实的全面考量提供启发,并有借鉴作用[18]。陈兴良教授也曾指出,审判活动非常专业,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而特别从事某一方面法律研究的法学专家对其研究领域有一定发言权。这类人向律师或司法机关提供参考性法律意见的作用应该给予肯定。同时,社会飞速发展,现阶段中国立法落后于新型案件产生的速度,法律体系一定存在某些漏洞。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将“法庭之友”制度引入中国司法体系,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司法模式与普通法系存在根本区别,生硬移植可能会造成“东施效颦”。有学者也曾指出,当前中国的司法土壤不适合“法庭之友”制度的原因有三点:一是诉讼模式与法律文化差异,二是专家法律意见与中国第三人及人民陪审员发挥的作用有部分重合,三是中国诉讼资源不足以应对“法庭之友”的庞大信息[19]。
(二)中国专家法律意见制度的建构
从中国立法及司法实践看来,构建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司法体制是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而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也将对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法官)形成挑战。基于此,专家法律意见可帮助法官快速了解案情,理清法律线索。但也应当注意,不论“法庭之友”意见书或专家法律意见,虽能为法官全面了解事实和深入理解法律立法背景及思路提供帮助,但也要求法官对法律具有深厚的理解能力和更高的鉴别能力。当前中国法律尚未对专家法律意见的形式及程序进行详细规定,从而导致了一定程度的适用混乱。笔者认为,可考虑借鉴美国的“法院之友”制度,制定出一套切实可行的合理措施对其进行规制,但切不可机械生搬、操之过急。
首先,专家法律意见书的递交许可应当交由当事人或法院审定。该项规定可参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则》中对于“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提交规定,即需要得到全体当事人一致同意,或在当事人不同意提交意见书的情况下,提请法院裁决,或应法院之邀时才可提交意见书。“法院之友”提交的法律意见书应在程序规定时间内送达给案件当事人,若法院认为必要,可邀请“法庭之友”出庭参与法庭辩论、质证和交叉询问。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专家意见书基于一方提供的资料得出结论,中立性难以保证;并且提交无需得到双方当事人的同意;提交法庭后不向对方当事人公开,导致对方当事人缺乏知情权,从而产生信息不对称。这些情形潜在地伤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平等诉讼权利。
其次,应对专家法律意见书的形式与内容进行规定,着重补充事实、法理和法律适用论证,避免向法庭提出结论性意见。当前,部分专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大多着重提出结论,忽略了对该结论的论证及法理展开,颇有干涉法官自主判断和绑架司法之嫌。有些专家提交的法律意见内容冗长,对案件相关事实重复论证,对司法资源造成浪费。因此,法律意见书的内容可适度参考英美法系对于“法庭之友”意见书的规定,即仅针对法院未掌握的事实进行论述,并依靠法律事实得出结论。同时,法学专家应聚焦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对如何理解某特定法条提出意见,而非对事实和证据问题进行评论,(19)以浙江省为例,该省的21份论证意见书中仅有3份属于法律问题的探讨,其余18件均涉及对事实的评判。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专家法律意见书”对审判工作的影响》,《法律适用》2003年第10期;潘剑锋、牛正浩:《构建专家法律意见书裁量采纳机制的思考——基于全国法院 1418 件裁判文书实证分析与比较法研究》,《理论学刊》2020年第5期。以避免干涉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此外,也可从“法庭之友”词源特质出发,即仅有法院认为的资深、专业、诚信的人士才能成为“法庭之友”,进而考虑设置“不可靠名单”,对存有问题的法律专家意见书执笔人设立惩戒机制,直至不再接受其向法院提交的意见书。
再次,为避免一方当事人聘用法学专家提供偏颇的法律意见,可考虑引入揭示制度。美国司法判例曾指出,“法庭之友”意见书有可能对诉讼产生阻碍,并违背既定法律原则。因此,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规则》第37条第6款规定了个人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揭示义务,要求在意见书第一页第1个脚注中指明案件当事人一方的律师是否参与全部或部分意见书的撰写,以及除“法庭之友”外有哪些组织(包括成员)、个人或律师在意见书的准备和提交过程中提供了资金支持;还要求明确并解释“法院之友”的法律意见书对法院审判有何种帮助。此种规定使“法庭之友”淡化自身利益,着重分析法院先例的形成与结果,从而起到推动司法公正的作用。当前中国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专家通常是受一方当事人委托,为一方当事人进行有偿服务,尽管专家们声称会保持客观与公正,但由于约束制度缺失,其公正性受到较大质疑。
最后,应进一步完善法官职业化体系建设,提高法官自身素质,加深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加强其职业技能,避免产生专家意见主导审判方向的情况,真正发挥专家意见对审判工作的补充和支持性功能,从而使判决更加严谨,维护司法公正。
四、结语
“法庭之友”制度起源于罗马法并经由普通法系国家司法实践逐步发展完善,亦有国际(准)司法机构在实践中引入该制度,发挥了促进公众参与、维护司法正义的作用,对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但此制度在运行中存有一定缺陷,其概念内涵也尚未完全厘清。本文在梳理“法庭之友”原述概念和内涵发展进路基础上,结合普通法系国家司法实践,剖析“法庭之友”制度的法律渊源、运作情况和缺陷,进而提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专家法律论证体系的设想。在中国司法体系下,专家法律论证制度与“法庭之友”制度在法律价值上存在一定的相通之处,因此可考虑从“何人可以提交”(同意为前提)—“如何提交”(程序与内容)—“如何使用(法官专业性)”等方面批判性地进行制度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