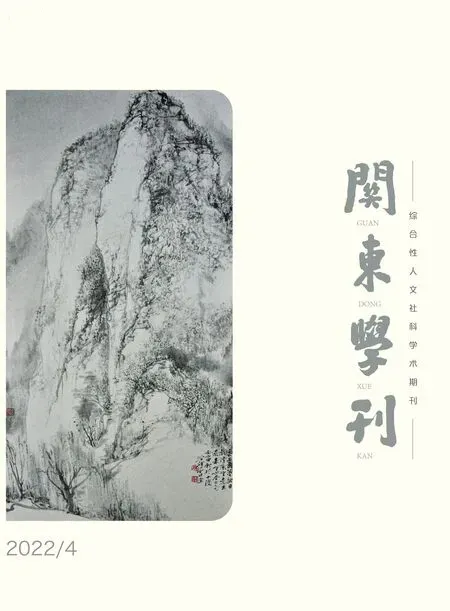“自文字至文章”:现代中国文学史著作基因性构造的隐没
——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起
王增宝
鲁迅曾计划做一部《中国文学史》,但这一愿望并未最终实现。1926年11月1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表达了对此事业的自信:“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一定也可以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1)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第502页。。那么,鲁迅已完成的文学史写作,如《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论著,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门外文谈》等文章,是否真的说出了“别人没有见到的话”呢?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例,这“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2)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4卷,第323页。,此讲义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的论述逻辑是:自语言而文字、自文字而文章,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这一撰写思路都无甚新意。鲁迅的写作意图及其实践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如何理解这一现象?本文即以文字问题为核心,从对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的分析出发,探讨现代中国文学史写作中“文字史”的消长及其原因和意义。
中国人撰写本国的文学史,学界多认为肇始于20世纪初的林传甲与黄人,二者分别撰有《中国文学史》著作。文学史作为一种现代学科,为中国传统所无。旧学者也谈论过去的文学事实,但其“所以考文学之源流、种类、正变、沿革者,惟有文学家列传(如文苑传,而稍讲考据、性理者,尚入别传),及目录(如艺文志类)、选本(如以时、地、流派选合者)、批评(如《文心雕龙》、《诗品》、诗话之类)而已。”(3)黄人著,杨旭辉点校:《中国文学史》,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页。相比之下,文学史作为新的述学文体,一方面仍要面对传统知识世界中的大量诗文史料,另一方面更要运用舶来的文学理念进行选择、编排和叙事。这些新的理念之一,即以胡适为代表的“文学的历史观念”。这一观念背后是当时流行的科学史观,某种内在价值或因果关系使文学史叙事获得内在的连贯性、有机性。
同时,文学传统的塑造也是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生产的一部分。黄人如此论述文学史的效用:“故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而文学史之能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亦无异于国史焉!”(4)黄人著,杨旭辉点校:《中国文学史》,第4页。中国文学史如同一条河流,从其起源处向着现代蜿蜒而来。这一观念的产生,正是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海外汉学界的观察更为明晰:“中国文学史的现代书写,从1920年代首次全面成熟之后,却一直持守着十九世纪对语言、种族、政体的同一性的信念。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它不断重述一个汉民族的史诗,重述从远古到现代、散布于极其广阔的地域的中国文学文化的历史与连续性。”(5)[美]孙康宜、[美]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15页。近代中国要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文学史书写也以明确的民族文学、世界文学意识为前提。因此,中国文学史的写作,首先就要确立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独特身份,其方式之一即追溯自身的起源。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往往会在开篇追溯中国的“文字史”,如此设置章节的根本动机,即对起源中所蕴藏的文明内核及国民性质的信仰和追求。
一、鲁迅:从“小学”传统到“三美”说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篇《自文字至文章》,从“文字”谈起,就有上述追寻民族身份“起源”的冲动。这份厦大讲义原名《中国文学史略》,后改为《汉文学史纲要》,从“中国”改为“汉”,部分是因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及中国境内之古外遗文研究的兴起,促动了鲁迅‘中国’意识的调整”。因此,“‘汉文学’是基于语言层面构建起来的概念”。(6)宋声泉:《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命名新解》,《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期。
鲁迅对语言文字的重视,近看是受到章太炎的影响,远观则可追溯到中国的小学传统。章太炎的革命思想主张“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而第一种国粹即“语言文字”,章太炎认为“中国文字,与地球各国绝异”,而小学知识是文学的基础,“言辞的本根,全在文字。……可惜小学日衰,言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7)章太炎:《演说录》,张枬、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448、452、453页。在章太炎心目中,小学不仅是文学的基础,也是一切学问的基本单位,更是“立足于对于文字独特的信赖,试图以正确继承古代语言创造出新语汇的方式来挽救象征着国运衰退的现代语汇不足的策略。”(8)[日]木山英雄著:《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赵京华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2页。
陈平原曾重申蔡元培的一个观点:鲁迅的治学方法受到“清儒家法”的影响,而又“不为清儒所囿”。一方面,“鲁迅治学从根本做起,注重辑佚和考据”。另一方面,鲁迅独特的“文学感觉”(包括文学修养和创作经验)使他的学术研究超越了清儒家法。(9)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28、334、336页。周作人在回忆中,也屡次提及鲁迅的小学修养,如“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10)周作人著,止庵校定:《鲁迅的青年时代》,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74页。他的《中国字体发达史》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门外文谈》(1934)虽是谈闲天,也可见出鲁迅的小学功底。
从知识储备来看,鲁迅的文学史写作从文字源流谈起,这一点也不奇怪。但鲁迅和章太炎的文学观毕竟极为不同。章太炎的《文学总略》开宗明义:“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称文。”(11)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9页。在接受了现代文学观念的鲁迅看来,这种将“文学”范围扩展到所有文字领域的做法,实在是难以接受的。鲁迅认为:“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12)许寿裳:《生存,并不是苟活:鲁迅传》,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第30页。这一定义从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分入手,以知/情/意这种人类心理机能的三重划分为哲学、美学基础,因此已经从句读、骈散等传统问题中摆脱出来,距离晚清民初文坛上的桐城、朴学、选学等问题域也已经很远了。
“文学所以增人感”,这就是鲁迅所谓的“纯文学”观:“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13)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4页。非常明显,这种“纯文学”既不同于章太炎式的宽泛学问,也不同于自摒于社会历史之外的纯粹美学。这是一种视文学为“无用之用”式的逻辑,它拒绝直接的功利性(物质、科学),而希望用文学发扬“国民精神”,进而“立人”的方式来兴起邦国。虽然对间接裨益(立国)的追求最终仍是功利性的,但第一步却是:通过文学“增人感”而“立人”。因此,鲁迅在《自文字至文章》一篇中对于文字源流的追溯最终指向了“感”的问题:感心、感耳、感目。
鲁迅将文字划分为“形音义”三部分,这明显是借鉴传统小学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的区分。其独特之处在于,鲁迅分别将此三分与人的感官相对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识”说:“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自文字至文章,遂有“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14)鲁迅:《鲁迅全集:编年版》第4卷,第324-325页。鲁迅将文字、文章之美视为对于人的“感发”作用,这正是现代文学观念与现代美学的契合——在现代美学之父鲍姆嘉通那里,美学(Aesthetica)的本义即“感性学”。
和章太炎相比,这是文学观念不同导致的致用路径区别。章太炎的学术总是较为直接地与其革命政治想象关联在一起,其学问以小学为入手功夫。宽泛的文学观念及复古观念,却使他对强调“增人感”的现代文学观没什么好感,而且“音美”“形美”的说法与“选学派”的音声美辞论又是如此相近,这正是章太炎不能同意的“文饰”文字观。在章太炎看来,浮华文饰就是对于古文古义的背离:“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苟失其原,巧伪斯甚。”(15)章太炎撰,陈平原导读:《国故论衡》,第10页。相比之下,鲁迅要通过文艺来改变国民精神,他对文艺及其重要性的看法自然不同。而且,鲁迅以文艺启蒙国民、改造国民性进而重建中国文明的路径要迂回得多。这种“文化政治”的迂回,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独特性所在。不管人们对于这种“文化主义”式的思维的历史影响如何评价,“一种通过文化与政治的区分而介入、激发政治的方式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的独特现象。”(16)汪晖:《文化与政治的变奏——战争、革命与1910年代的思想战》之《序论“觉悟”的时代》部分,《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以文化迂回的方式重建中国文明,是鲁迅不同于章太炎之处,这种“文化政治”,即鲁迅在文学史开端探讨文字源流这种写作方法的历史背景。
鲁迅所身处其中的“文化政治”和思想范式,伴随着现代学术体系的发展和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影响弥漫当时,并及于今日。这种知识型之下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写作,倾向于将文学视为艺术之一种,将文字视为现代主体表情达意的工具。较之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的文字观,这毕竟窄化了许多。如果我们能够跳出“五四”知识型的翳障,暂时悬置“现代”价值观,就会发现:无论是章太炎的“用国粹激动种性”说,还是黄人、林传甲等人对文明内核及民族性质的信仰,其观念固然仍属“前现代”,但皆令人感到一种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温情和敬意;而以小学为文学言辞之根本的观念和实践,更映照出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与语言学、文字学、书法学等学科分科而治的不足。考之现代文学史写作对于文字问题的处理,就会发现,文学史“现代化”的代价是,我们渐渐失却了曾经的那份丰富性。
二、林传甲:小学乃一切学问之基
20世纪初以来的多种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以文字史开篇的不在少数,但其著述理念各不相同。将这些文学史著作与鲁迅的写作实践作一番比较,对于历史性理解鲁迅的文学观念或不无裨益。作为国人编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是一个理想的比较范本。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开篇即探讨中国文字源流,认为书契是人类由草昧进于文明的标志。但“中国文学史”毕竟是一种现代述学文体,林传甲在传统治化/词章二元的“文学”想象中,亦有比较明确的将文学史写作与现代学术生产、进而与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结合起来的意识。林传甲也认为,“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而文学史写作之所以要特别讨论文字,是因为“考文字之变迁,亦兴亡之大鉴戒”。他特意在第一篇第三小节下加了如下按语:“辽、金、元三朝太祖皆创国书,以致勃兴。英、法、德、俄因拉丁以为国书,且以识字人数逐年比较,以征民智之开塞,科学之盛衰。吾愿黄帝神明之胄宜于文学科学加勉矣。”(17)本段引文皆见于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60、61、67页。原文仅有句读,标点为引者所加。后同。此处“国书”概念,仍然是传统的教化文学观的产物,而并未考虑到文学“表情达意”的现代意义。
作为拓荒之作,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理念和结构原则并未完全摆脱传统知识框架。这部教材的前三篇,恰与《四库全书》“经部-小学类”下的“字书”“音韵”“训诂”相对应,传统目录学知识的影响可谓深远。此外,这种章节设置有其直接来源,即1904年由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主持重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癸卯学制”)。林著《中国文学史》共十六篇,篇名与“章程”中“文学研究之要义”前十六款完全一致。
对于林著《中国文学史》目次与“章程”的对应关系,学界已经充分注意。但二者之间存在的一种错位关系,却往往被忽视了。“癸卯学制”将大学堂分为八科,其一“文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又分为九门,其一为“中国文学门”;“中国文学门科目”中设“主课”七种,其中两门课程为“文学研究法”和“历代文章流别”。对于林传甲的文学史写作而言,“章程”中“历代文章流别”下的“讲习法略解”应是最具参考意义的。但遗憾的是,“章程”恰恰在这一部分语焉未详,而仅有一句“日本有《中国文学史》,可仿其意自行编纂讲授。”(18)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奏定大学堂章程》,璩鑫圭、唐良炎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可见,就连大学堂章程的制定者,也不清楚如何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林传甲也确实说要仿照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但事实证明,他并未充分理解笹川著作中的现代文学观念,对小说一体的贬斥态度仅是其传统文学观之一例而已。
因此,林著文学史涵盖的内容十分庞杂,自谓包括籀篆等字体变迁、经史子集文体、汉魏唐宋之家法,而这些也仅仅是“章程”中“文学研究要义”的一部分内容而已。林传甲在文学史开端先讨论文字源流,是因为他视文字、音韵、训诂为经史词章之学的基础,这仍不出“小学乃经史词章之本”(19)姚永朴著,许振轩校点:《文学研究法》,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第5页。的传统观念范围。而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于文字的讨论,则是另一番全新的风景。鲁迅只谈文字的起源和构成法(六书区别及次第),并未细述籀篆隶草等字体的变迁史,“鲁迅的着眼点始终是在关注语言产生与文学发生的关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受到时代社会生活发展的影响问题,关注语言由最早作为记录人类社会生活的载体,如何逐渐转化为记录和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并产生美感的过程,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发生史的考察,而不是一部汉语产生历史的考察。”(20)刘克敌:《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撰写理念及影响》,《关东学刊》2018年第4期。如上所述,这也是鲁迅的现代文学观念看待“文字”问题时迥异于“小学”传统之处。小学以文字为一切学问之基,而鲁迅则秉持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的现代观念,视文字为记录现代人思想情感的工具。
三、“自文字至文章”:作为文学史著作的基因性构造
文学史书写必从本民族文字开始,“从字句、篇章结构再到文体,依次论列其法式”,陈广宏将此称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一种“基因性构造”。这种构造形成的机制,除了小学、文章学等传统学术影响外,还受到当时西方古典语文学中修辞、语法之学的影响。在中国“文学”知识体系经历现代“文艺学”的蜕变之前,文学史写作从文字论至文学,实在是非常自然的事情。而随着现代学科分化的发展,中国文学学科的边界经历了“民国以来经历又一波西方文学论的洗礼后,才愈益明晰而滴定,文学与语言学获得裂变,各有分工,文字、语法、修辞学皆归属于语言学。”(21)本段引文皆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48、50页。即便如此,文字问题始终以一种基因的形式存在于文学史著作中。在现代学术体系中,文学与语言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文学史中关于文字讨论的比重也逐渐变小,由显趋隐。但是,这一构件基因持续存在,并未从文学史中彻底消失。究其原因,大而言之,即文学终需以文字为符号媒介;具体而言,则由于修辞学与文学之间的紧密关系。晚清、“五四”以来,“文学”的概念逐渐收窄、纯化,专指用语言来表达人之思想、情感的具有创造性、想象性的作品。在这种现代文学观念当中,语言是现代主体表意行为的工具。正是在这一层面上,修辞学与文学产生了特殊的关联。人用语言来有效地表情达意,这种现代文学实践本身也是一种修辞行为。况且中国文字的特性,又总是与中国文学的独特美质密切相关。
随着“四库”知识体系的去魅及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传统小学渐向现代语言学科转化。各种中国文学史著述的起始章节中,传统小学知识的比重越来越少。而那些仍然坚持在文学史中探讨“文字源流”者,也不再完全是因为重视小学的学术基础意义,而多是基于和鲁迅同样的原因:一是对文字表情达意作用的认同;二是强调汉字特性(如单音节构造)对于中国文学美学特征生成(如对仗、押韵)的重要意义。在现代学科分化的过程中,文章修辞学(传统的与现代的)的考量,是诸多文学史著作坚持讨论文字源流的根本原因。这一动机,及其所生成的“自文字至文章”的基因性构造,持续地存在于现代以来的泛文学史、纯文学史及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等类型的著作当中。
(一)文章的修辞:泛文学史中的“文字”
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之前,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1918)对文字源流问题的处理,明显有新旧知识体系对接的痕迹。谢无量在讨论“文学之定义”时,还要略显笨拙地分别罗列中国古代、外国学者论文学之定义。以此为基础,他一方面认同中国传统广义文学观,另一方面则肯定戴昆西(De Quincy)的知/情文学之别,中西交融后的文学分类即:“大抵无句读文,及有句读文中之无韵文,多主于知与实用;而有句读文中之有韵文,及无韵文中之小说等,多主于情与美。”这仍是章太炎式的文学理解,只不过多了一点知/情/意划分基础上的现代学术分科精神。因此,非常自然地,谢无量文学史的第二章为《文字之起源及变迁》,并辟专节分别讨论字音、字形、字义之变迁。又辟第四章《中国文学之特质》,强调:“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诸夏所独有者也。”由中国文字音读形式世界最古,谈到中国独有之美文,仍是林传甲式的治化/词章二元文学观。确实,谢无量虽然列举了“专为述作之殊名”的现代狭义文学观,并且知道“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但具体到文字问题,他仍从“文章形式”角度着眼,文字仍是文言以行远的辅助手段:“声律,美之在外者也;道德,美之在内者也。”(22)本段未注引文皆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谢无量文集》第九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8、9、13、45页。这种视文学视为修辞、视文字为形式之末的治化文章观,和那种用文字记录人类思想情感、以文学“立人”的现代文学观相比,有着细微但根本的差别。
曾毅《中国文学史》(1915年9月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第二章《文学与文字》,在例行追溯中国文字源流及字体变迁后,特意谈到“文字与文学之关系”,“……形声转注假借之为用大矣。形声演而为声韵。古无四声,惟有清浊长短。至齐梁间,始辨平上去入,而为韵谱。文学增一美质。文字亦因以统纪。转注假借之法,则开后人文章练字之用。”(23)曾毅:《中国文学史》上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9年订正初版,第7页。曾毅虽然注意到当时“欧美文学稗贩甚盛,颇摭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但他的文学类别仍以有韵无韵、记事论理为标准。他认为,文字为文学增加了声韵的“美质”,这种看法,与谢无量“声律,美之在外者”的观点如出一辙。
关于曾毅《中国文学史》对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1912年)的编译和增删,学者多已指出。曾著第二章《文学与文字》,与儿岛第三章标题相同,细考之下,其内容虽有增删,而文字观念基本相同。儿岛认为,中国文字以象形为基础,所以诸如郭璞《江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等作品的文字形象、生动,具有“图画的形式”及“美术的模样”。(24)儿岛献吉郎:《支那文学史纲》,东京:东京富山房,1912年,第11、12页。这和曾毅以文字为文学“美质”的观点并无二异,二者之间或有影响关系,但从更大的现代学术体制视野来看,他们的观念都是上述修辞性文字观的体现。
(二)表现的工具:纯文学史中的“文字”
胡适的《国语文学史》及《白话文学史》,开篇就直接探讨“古文是何时死的”,文字史问题并未进入其讨论视域。文学史文本的空白、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症候:文字作为表情达意之工具的意义已经无须赘述了。胡适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实践,在在彰显着现代学术精神,而他对文字的看法却是简单粗暴的工具论。在他看来,“文学革命”仅仅是文字工具的新旧更替而已:“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25)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胡适的“言之有物”论曾引起陈独秀的担忧,“以文学为手段为器械,必附他物以生存”,这会不会产生“文以载道”的流弊?(26)《通信》,《新青年》第2卷第2号,1916年。实际上,陈独秀强调文学作为艺术的美学价值和独立地位,与胡适强调文学表情达意的作用,二者并不根本冲突,它们都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中国学界的“纯文学观”:“西方浪漫主义时期以来的文学观念被概括为情绪、想象、思想、形式四个要素”(27)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第238页。,这种现代文学观恰好涵盖了陈独秀、胡适所代表的两个面向: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它用文字来表达人类的思想、情感。在这种纯文学观影响下,一些文学史著作试图超越胡适文/白对立范式,在他们看来,胡适的白话语体文学史不啻为一种幻翳,必须痛下针砭。而从这些著作对于文字问题的处理来看,它们与胡适的工具文字观,并无根本区别。
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1926)第一章“太古文章”第三节标题为“文字”,在欧亚对比视野下强调汉字与中国文学特质的利弊关系:“至今吾民族犹沿用象形文字,与他国所用拼音文字为对待。……至象形文字之有大影响于文学者,亦得失互见,第一,限制语言之变化,尤最便利于形式主义拟古主义也。第二,因使用法之困难,而令文章简洁也。”顾实对中国文字起源、六书的介绍已趋简略,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这些内容的介绍并非文学史应有之义:“中国文字及音韵之研究,有成一科学之价值,若适用言语学之原理而组织一新体系,庶其可乎。”(28)顾实编纂:《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2页。很明显,一方面,顾实将“古来能特别感动人之作品”视为“纯文学”,则文字为文学传达情志之手段的意义即近乎自明;另一方面,顾实也感受到了现代学科分化的压力,文字与音韵并非文学史著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对“谢无量、曾毅……等辈”的广义文学史表示不屑,“至于音韵,训诂,以及经传诸子……中的文学,有未可以被我采入这部‘中国文学史’中者,当然是留给专门研究音韵,训诂,经传……的学者们去讲述,本书只好一律抛弃不理了。”(29)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初版,上海:北新书局,1930年,第15、20页。在学科分化意识的影响下,文字源流问题被明确抛开了。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对之前的二十多种文学史著作提出批评,其中专门提到,因为缺乏明确的现代文学观念,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史里,如谢无量、曾毅、顾实、王梦曾、张之莼、汪剑如(余)、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30)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初版,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第3页。胡云翼的纯文学史则以文体、文派的流变为中心,因此开篇亦不谈文字,而是沿诗经、楚辞、汉赋等文体线索一路讲下来。
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935)正文从先秦诗歌谈起,也没有了关于文字源流的讨论。只是在《诸论》中谈到了“中国文字与文学”,而且也完全是用一种形式化、工具性的态度来看文字,其态度十分明确:“文字是文学的工具”,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是单音的孤立语,其运用于文学,则有“便于模拟,不便于创造”等弊端;而好处有三:“一是文章简洁,二便于造对语,三音韵和谐。”(31)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北京:北平著者书店,1935年,第6-7页。刘经庵特别指出中国文字特点与中国骈文、律诗文体的关系,及押韵、双声叠韵及重言诸法所造成的文字音节之美。文字是表情达意之工具,中国象形文字又使中国文学有独特的美学特性,这是上述几种纯文学史著作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之文字观相通之处。这种观念历经沉淀,几乎成为后来文学史写作的定则。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文学是一个主体(灵魂、心灵)用语言来表情达意。语言文字与特定文学形式相对应,这种语言工具意识已经深入文学史作者的内心。
从这一线索来看,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关于文字的讨论,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工具论”。其“三美”说中的“意美以感心”,即鲁迅“文学所以增人感”观的体现——文学是一个独立自由、有创造性的灵魂的创造,而文字就是这个现代主体表情达“意”的工具。从根本上说,鲁迅关于“自文字至文章”的讨论,只是现代文学史写作理念从小学传统向现代学术转变中的一个普通节点而已。但相对于“音美”和“形美”,“意美”逐渐“前景化”而占据“三美”的主导地位,却也是后出文学史将文字窄化为工具的不祥征兆。
戴燕曾指出,中国自古文学,广义包罗万象,狭义则专讲声律形式之美,这种分裂“等于在未来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与研究中,预埋了两条路线,而由于历史的机缘,其中的一条路线,又将借着旧的文学观念被颠覆的势头,由隐而显,拓宽其途,成为今后几十年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唯一‘正途’。”(3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7页。此处,所谓“历史的机缘”,即“五四”新文学运动;所谓“正途”,即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学观——文学是人类情感的表现。沿着中国文学史内在理路的线索,鲁迅将狭义“文”的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嫁接。于是,“载道”传统由显而隐,“言志”“缘情”之说由隐而显。而《文选》派对于丽辞专美的要求,因为符合纯文学观对文字工具形式之美的要求,被“五四”人从“文以载道”的旧传统中有意无意地剔除,而被“文学革命”宽恕、放过。正如陈平原所说,五四新文化人中的“章门弟子虚晃一枪,专门对付‘桐城’去了,这就难怪‘谬种’不断挨批,而所谓的‘妖孽’则基本无恙。”而其原因之一,即刘师培、黄侃等人的“六朝的文章趣味与其时刚传入的西方文学观念比较容易会通;一是朴学家的思路与作为大学课程兼著述体例的‘文学史’比较容易契合。”(33)陈平原:《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第22、23页。选学派文学观及其实践,作为一个活的传统,是现代文学发生、现代文学史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
于是,在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关于文字源流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小学传统、《文选》传统与现代文学观念的复杂角力。这导致鲁迅所持又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工具论”:文字的物质形式(声音和形象)除表意功能外,本身就是文学意义的直接构成要素,这也是鲁迅提出“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的原因。从小学传统、《文选》传统的角度来看,鲁迅对文字之能指(音、形)的重视无甚特别之处。鲁迅对文字音、形“感人”之力的强调,亦其来有自,即本于“文学所以增人感”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在晚清“五四”以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史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声。
结论或许令人失望,从现代中国纯文学史书写的传统来看,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对文字源流的讨论,并没有说出什么“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毕竟,随着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及学科分化意识的深化,随着“五四”新文学的经典化,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纯文学史写作如此,俗文学史写作也不例外。
郑振铎的俗文学研究影响深远。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在新文学观和新资料发现的支持下,将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等草野文学拉进了文学史视野。而此书上卷“古代文学”,仍专设一章“文字的起源”,乍看稍显突兀。而细观其论述,他视文学为艺术,以情绪为文学和非文学的疆界,而“文字和语言同为传达思想和情绪的东西”,“所谓文学便是用这种特创的符号记录下或传达出的人类的情思的最伟大的、最崇高的和最美丽的成就。”(34)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17页。这仍属于视文字为表现工具的纯文学史传统。郑振铎一方面接受了纯文学史观的文体纯化行为,另一方面更为关注作者和受众的民间身份,且往往在一种对比关系中凸显自家身份。如他在后来专史《中国俗文学史》(1938)所言:“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3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版,第2页。不论雅人、俗士,都要以语言文字来传情达意,且俗文学是民众情感的流露,具有大众性、新鲜但粗鄙、想象力奔放等特质,基于此种原因,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已经无需特别处理文字问题:文字不过是大众表意的工具而已。
(三)反映的工具:马克思主义文学史中的“文字”
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941、1949年),因其文学史观念的马克思主义色彩,被认为是中国文学史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刘大杰特别注意特定时代的物质基础、政治状态、社会生活等因素对于文学的影响。刘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并未单设章节讨论文字问题,只是在第一章《殷商社会与巫术文学》有所涉及。而之所以讨论文字,是因为卜辞是中国信史的有力材料,卜辞和《周易》都是后人认识商周时代的重要依据。刘大杰一方面强调文字作为信史依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他认为较为完备的文字的出现,标志着文学从诗乐舞三位一体的原始形式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艺术。可见,在现代学术分化视野下,文学是一种语言艺术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不过,刘大杰尤其强调文学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功用:“文学正如其它的艺术一样,是社会生活的反映。”(36)本段引文皆见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正文第618页,“自序”第2页,正文第6、10页。据书末附陈尚君文章,此书为《中国文学发展史》四十年代初版重印。在这种反映论的文学观念中,被反映的思想、情感、现实世界才是最根本的一元,文字只能获得一个叨陪末座的工具性位置。另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第一版)、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1963)等著作皆是如此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文学史的话语体系中,文字对于文学的意义并非根本的——文字产生之前,口头文学的存在就是证明。
结语:重申“汉语言文字的印记”
中国文学史的书写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许多曾经热烈争论的题目被当作常识接受,并渐内化于文学史写作者心中。无论是关于音、形、义的划分,还是关于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特性的对应,已经看不出“用国粹激动种性”的抱负,看不出治化/词章二元论下的修辞性文字观,也很难再体会到“五四”人为纯文学辩护的激情。
1996年,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一时有“古破天惊”“开创文学研究的新境界”之誉(3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新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原序”第1页。。此书特色在于,试图突破“左”的思想影响下的文学史模式,而以人性解放与文学形式的互动作为描述中国文学演变的内在理路。“导论”部分用长达61页的篇幅,探讨作为文学史写作基础的“文学是什么”问题,最终定义如下:“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如果脱离新时期的历史语境来看,这个定义实在没有什么新意:文学“以感情来打动人”之与鲁迅之“三美”说,“形象”说之于纯文学观念对于感性/抽象的严格区分,“社会生活的反映”之于刘大杰的艺术社会学,更不论语言工具论与“五四”以来文学艺术观念的内在关联,上文都曾分析过。确实,这个定义浓缩了百年来中国文学观念的变迁史。章著《中国文学史》要批评的,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定义: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的、对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而其所要重申的,是文学“以情动人”的性质。而文学之所以能以情动人,是因为作品中体现出的人性。于是,著者一方面借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来完善其人性论述;另一方面,也非常自然地接续鲁迅的“三美”传统及“五四”以来的纯文学观念,并且和“五四”人有选择地激活选学传统一样,充分肯定梁代萧纲、萧绎的历史作用——二萧是文学自觉这一历程的最终完成者。无论是具体观点,还是为文学独立地位辩护的路数,都似曾相识。章著《中国文学史》通过接续“五四”传统,将感情及其人性根底、将文学形式之美的问题重新提出。人性论与形式主义,在左翼文学理论中长期是一种恶谥,新时期以来,人们开始为它们恢复名誉。因为是“恢复”,所以我们看到如下文字观时,就不会感到陌生:“从文学角度来说,文字既为书面文学提供了基本条件,也在某些方面决定了文学的特点。譬如,中国文学重骈偶的现象,就是从汉字的特点中产生的。”(38)本段以上未注引文皆见于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第59、1、55、68页。很快,章著《中国文学史》出了增订本《中国文学史新著》,并被列入“教育部重点推荐大学文科教材”。增订本第一编“上古文学”“概说”部分,在介绍民族文化特点时,专设一小节“汉语言文字的印记”,虽亦提及汉字构成方法等问题,但重心不在梳理文字源流,而是强调汉字特性在中国文学形式上留下的印记,如单音节、言文分离等特点与中国诗歌韵脚、句式及骈文文体等的对应关系。如上文所述,这是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文学史书写者分享的常识。
目前中国高校较普遍使用另一部文学史教材,就是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1999),它被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其“总绪论”特别强调“文学本位”,同时也及时指出:“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反映现实的功能,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方面的功能是怎样实现的呢?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而实现的。”此处“文学本位”的提法,明显是借鉴“新批评”内部/外部研究的区分,所针对的即政治经济、作家生平等外部研究。对文学功能的强调,说明“反映论”的压力仍然强大。其“绪论”第一节“中国文学的源头”认为:“甲骨文和金文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书面文学的萌芽。……从此,文学的各种形式在语言文字的不断成熟过程中分途发展。”文字是文明的标志,汉字特点与文学形式相对应——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关于文字问题的各种观点又出现了。袁著《中国文学史》试图唤醒“五四”时期的纯文学观资源——文学是现代主体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的艺术。“借助语言这个工具以唤起接受者的美感”,(39)本段引文皆见于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24页。这种说法与鲁迅的文字“三美”说如出一辙。“文学本位”说,是在“新批评”等西方文论的支持下,对鲁迅等人“纯文学”观的创造性转化。
经过以上对近现代以来多种文学史著作关于文字问题讨论史的追溯,可以发现,中国“文字”身上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政治想象,如作为民族身份之根本、激励种性之国粹、一切学问之基础、中国文学特性之来源、文章之修辞、主体表现之工具、反映现实之工具,如此等等。这些观念共时性地存在于各种文学史之中,而其比重则随时代氛围、著者观念而调整。随着文学史写作外部社会历史环境的变迁,随着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和现代文学观念的深化,中国文学史写作者逐渐形成共识,许多一度争论的主题层累为知识传统。因此,“自文字至文章”,这一基因性构造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变化。文学史写作中,文字问题的相关讨论比重逐渐下降,文字的工具性意义愈加趋向于不证自明。但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文字”媒介是它区分于其它艺术的本质性特征,文字的物质性与其能指形式的美学意义,亦应是文学写作、研究(如手稿研究)的重要维度,而文学史写作正是维系、更新这种文字意识的重要学术体制。上世纪初的林传甲尚且花大篇幅讨论“古文籀文小篆八分草书隶书北朝书唐以后正书”这样类似书法史的内容,鲁迅亦讲文字之“三美”,而百年来的“现代”文学史写作却对此问题渐趋沉默,文字渐被窄化为表意工具。相较于视文字为一切学问之基的小学传统,“自文字至文章”这一基因性构造的隐没,或许是“现代”学术分化体制下文学史写作范式的一种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