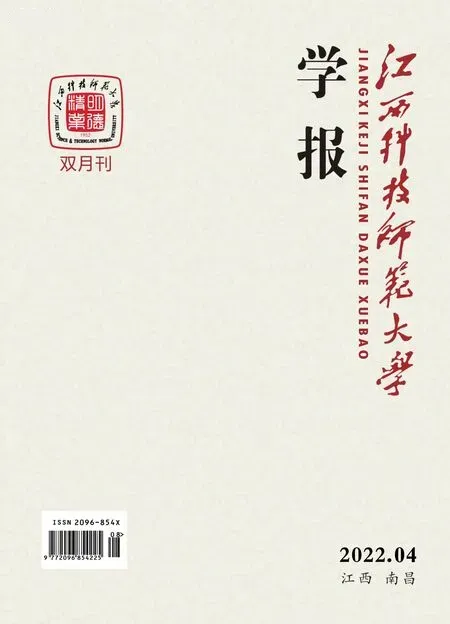认同、反抗与回归:王朔创作与精英文化形态考辩
汤凯伟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金华 321004)
引言
以往的评论家总是将王朔与精英文化对立起来,仿佛王朔只能是大众文化的执旗者,与精英文化是天然的对抗者。不可否认,王朔为了其作品能获得更多的读者市场,处处标榜自己反叛、抵抗的姿态;书商和出版社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也总是对王朔小说中最受市场欢迎的一面进行过度宣传。也就是说,王朔的叛逆、反叛其实是三方合谋的结果。在王朔淡出文坛、“王朔热”再无追捧者的今天,对王朔创作与精英文化形态的关系确乎有考辩的必要。脱掉市场经济这一神圣的外衣之后,王朔与精英文化的关系除了对立还存在另外的可能。本文通过分析王朔的创作发现,王朔的精英倾向一直潜藏在他的创作无意识之中,他的小说的核心内涵从来不是描写边缘人物的颓丧,而是精神贵族的反抗。
王朔在当代作家中是比较复杂的一个。有人将他归于先锋作家,也有人将他归于新写实小说作家,还有人认为王朔属于商业市井写作一类的作家①如丁柏铨在《新写实小说漫谈》中将王朔的《千万别把我当人》算作新潮小说;陈晓明在《“新写实”小说座谈辑录》中将王朔与刘恒、刘震云、池莉、方方、李晓等人归于一类,称他们为“新写实主义”中“面对现实的群体”;白烨在《“后新时期小说”走向刍议》中将王朔看作林斤澜、邓友梅等人的继承者,归于“新市井小说”。。这种身份的复杂性体现的是王朔创作的复杂性。而王朔的创作复杂性又源于他对精英文化既反对又支持的矛盾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于他有意识地对现存的精英意识的批评,另一方面又受他无意识的城市市民妥协讨巧的性格影响。因此,我们需要对王朔复杂的创作全貌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
在《空中小姐》中,王朔说了这样一段话:“当年,我们是作为最优秀的青年被送入部队的,如今却成了生活的迟到者,二十五岁重又像个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费力地迈向社会的大门。”[1]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王朔自身有很强烈的精英身份意识。在七十年代能够去参军的无一不是精英分子(这种精英不仅指他个人,也包括精英家庭的出身)。与同龄人相比,当其他人还在上山下乡的抉择面前苦恼时,军人身份是一份荣誉也是一种保护。但是王朔却不是以一个精英的身份轰动文坛的,从王朔被文坛集中关注的那一刻起,他的身边始终围绕着痞子、犯罪、毒害年轻人等负面评价。本来是精英群体一员的王朔,何以反过来被精英群体所排斥?其人其创作为何登不上正统文学史?他的创作谈和访谈为何总是带有反精英、反知识分子倾向?结合王朔的创作谈和他作品中表现的对精英文化的态度,可以将他的创作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一、对精英身份的认同
第一阶段是自觉的靠拢。王朔的创作开始得很早,在以《空中小姐》引起文坛注意之时,他已经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等待》(1978 年《解放军文艺》第11 期)、《海鸥的故事》(1982 年《解放军文艺》第9 期)和《长长的鱼线》(1984 年《胶东文学》第8 期)。《等待》以一个青年女孩小丽的视角感受文革的历史。小丽因为处处受到母亲的约束,感觉生活苦闷无聊,威胁父母说要离家出走。但在作者笔下,这是有意将精神上的苦闷单调通过这个小家庭表现出来。小丽向往美好事物,有一腔精力要发泄,但是没有正当的途径。小丽和她的青年朋友们的追求一味地受到压抑、束缚,因此在他们心里留下了被勒紧的“伤痕”。小说借爸爸的口说到:
是的,今天的年轻人,仅仅不愁吃、不愁穿是不能叫他们满足的。你们,年轻人的生活应该是丰富的,有趣的,充满了歌声和笑声的。你们享受不到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同样很难过。尤其是当孩子把这一切归罪于我们的时候[2]。
王朔发表这篇小说的时候正值“伤痕文学”思潮兴起。卢新华《伤痕》中的王晓华引起了很大的争论,争论之一就是王晓华的身份问题。荒煤在他的文中写道:“尤其是一些革命干部的子女,都或多或少有点荣誉感,对党、对革命、对自己有光荣历史的父母,几乎有一种极为自然的、传统的、真诚深厚的感情。”[3]王晓华出于这种复杂的感情,为了革命而毅然与自己的母亲决裂,选择了革命情而抛弃了亲情。王朔《等待》中的女主人公有同样的倾向,她将母亲对她的关心当做管教和虐待,也产生了退学、离家出走的想法。在另一篇“伤痕文学”小说《班主任》中,《牛虻》在文中起着推动情节曲折发展的作用,而在《等待》中起同样作用的则是《安娜·卡列尼娜》。如果说刘心武在《班主任》中发出的是救救孩子的呼告,那么《等待》中发出的则是救救青年的呼告。正因为和“伤痕文学”在人物身份、故事结构和主题表达上的相似(或者说这篇小说就是“伤痕文学”),它也暴露了和“伤痕文学”一样的精英意识。并且,有学者总结认为,“伤痕文学”的主人公只有三类:“知识分子”“老干部”和“知识青年”。这些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是社会的精英,因此,写作“伤痕文学”也就是写作精英文学。
《海鸥的故事》和《长长的鱼线》都是以水兵为描写对象。《海鸥的故事》讲述的是一群水兵因为贪吃所以去打海鸥,但却和守护海鸥的老人产生了矛盾,最后受到老人爱鸥精神的感化而完成了从吃鸥人向护鸥人的转变。《海鸥的故事》中的海鸥可以看作是中国水兵的象征,它们勇敢坚强,是海洋的守护神,但是这并不是《海鸥的故事》的核心思想。在《海鸥的故事》中有这样一段思考从未被重视过,它是在海鸥“杨杨”因为感染快要死去的时候发生的:
窗外,开始下小雨了。不知为啥,我觉得这夜色很熟悉,十年前的一个夜晚也是这样,但那是个星星闪烁的晴朗夏夜……
……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今晚会想起这件事。这十年,我早把那个晚上忘得一干二净。这十年,我自扪还算个好孩子,没有像有的同龄人那样变成不可救药的小坏蛋。可是,是不是人就一定越长大越失去童年的真挚呢?要没十年动乱,我能不能比现在好点呢?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叫人后悔的事太多了[4]。
这段话应该作为《海鸥的故事》的核心思想受到重视。无独有偶,《长长的鱼线》虽然表面上是写解放军小战士与钓鱼的小孩之间短暂的友情,实际上是写为了执行任务必须远离正常社会生活的苦闷。这两篇小说与《等待》虽然在题材、人物、情节方面有很大不同,但其中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以小说中人物在现实中遭遇的苦闷境遇来诉说心中的“伤痕”。
并且经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是,王朔从小生活在部队大院里,那是建国后精英扎堆的场所。他的父亲是军队的文职干部,他的母亲甚至是上过医科大学的知识女性。王朔从小就受到文学的熏陶:“家里的书很多,天羽是个爱书人,常常买书。两个儿子从小也都喜欢看书。特别是王朔更热爱阅读,国内国外的小说都看,连他爸爸的军事书也看,家里的书他几乎读遍了。”[5]所以,王朔生活在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军人的家庭里,精英文化是从他一落生就最先接受的文化类型。因此,王朔早期的三篇小说《等待》《海鸥的故事》《长长的鱼线》对精英意识的认同是顺理成章的,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这反映的是他无意识中的精英意识的留存,在面对自我的这一向度上,王朔还没有挣脱家庭、部队带给他的深刻焦虑。
除了这三篇早期的作品,这一阶段的创作还包括《空中小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浮出海面》和《橡皮人》等。由于《空中小姐》这篇小说在王朔创作中的特殊性,以往总是将《空中小姐》当做王朔最初的作品。因为从小说的人物、背景、语言来看,与他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如《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是属于同一类型的。连作家自己在《我是王朔》中也绝口不提前三篇作品。在“伤痕文学”阶段的王朔并没有得到文坛和读者的太多的青睐,但紧接着发表的《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小说为他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这几部作品中,王朔将前期对“伤痕”的执着描写骤然转向了对青年最关心的“情爱”的叙述。这种叙述看似与前期创作是断裂的,但其实质仍是“伤痕”的延续,是写作“伤痕”的精英们对新时期巨变的环境做出的自觉/不自觉的应对。其中爱情正是他们这个年龄遇到的第一个考验。“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都晚胡说八道,但总有一个时刻是真的。”所以他选择了爱情作为人物的精神立足点。“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时候更值得真实起来。你说在事业上真实?在理想上真实?这简直有些不知所云。这是本能的选择。”[6]82例如在对“性”这一爱情中敏感问题的处理上王朔就体现了他的“真”。如《空中小姐》中对“我和阿眉是分开睡的”的着意强调;《浮出海面》中“我说过,我对婚前性行为持宽容态度,很使晶晶紧张过一段”半是戏弄半是认真的调笑,后来于晶了解石岜后才安下心,因为“我是典型的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等等细节。对性的谨慎态度表示人物既承担着道德包袱,也有对真爱的追求,不会轻易言性。虽然人物在言语上经常出格,但心灵上却是很纯洁和充实的。在《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上篇中,王朔却一改对性的谨慎描写,对张明、亚红、方方等人的荒淫生活做了细致描写,其中令人发指的是对女大学生吴迪的诱奸,生生将一个花季女大学生送入了罪恶的深渊。有趣的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的下篇,剧情和上篇几乎一模一样。但张明成为了一个正人君子,不仅对胡亦主动投怀送抱无动于衷,而且希望把她引上正道。虽然结果依然是悲剧,但是张明本人却得到了救赎(其实是一种圣人式的精神胜利)。这其实也可以看做是对性的谨慎态度的一种反向言说:既然社会上的风气是性解放,那么王朔就把“乱性”毁人的一面展现给读者看。最终其本质还是劝人向善的、道德的。
陈思和这样评价王朔的《橡皮人》中的性观念:“它不是淫秽的煽动性的,而是出于道德观念的虚无和冷漠。”[7]王朔对“性”这一话题用了两种差别很大的笔墨来描写,其实也表现了王朔矛盾的心情。一方面,具有精英意识的作家身份使得王朔向往《红楼梦》《西厢记》那样的古典爱情、“才子佳人”式的纯情爱恋,而爱而不得的状态是精英意识爱情观的代表特征,因此才会出现《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下篇中的道德圣人形象。另一方面,王朔又不满足于让笔下的人物只做道德圣人,他既有精英意识又有反精英的意识,既然精英人士耻于谈性,那么就把性大方地写出来,多写性,乱写性,写乱性。这给精英文学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也招致了很多的非议,但本质上仍旧可以看做王朔在主动向精英文化群体靠近的表征。
二、嘲讽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群体
王朔小说的第二阶段是自觉对抗。如以《顽主》为代表的“顽主”系列作品,有《顽主》(1987)、《一点正经没有》(1989)、《玩的就是心跳》(1988)和《千万别把我当人》(1989);“编辑部的故事”中的几个短篇,如《痴人》(1988)、《修改后发表》(1991)、《谁比谁傻多少》(1991)、《懵然无知》(1992)是另一个系列。这一时期王朔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调侃”,这也是王朔选择向精英文化发起进攻的武器。在《我是王朔》里作者说:“第二阶段就是调侃。包括《编辑部的故事》这类东西,都是1989 年以前的。1989 年初,2 月份把《千万别把我当人》寄出去后,我就不再调侃了。”[6]31“调侃”作为王朔小说公认的艺术特色,以往的研究常常将它和反文化、反英雄、躲避崇高等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些都不能解释为什么王朔偏偏在这个时期开始调侃,以及王朔的调侃最终是要达到什么效果。
从王朔与精英文化的关系解读王朔的调侃似乎比较确切。经过上一个时期向精英文学的主动靠拢之后,王朔发现自己似乎并不能真正地被精英文学群体接纳,反而常常被精英文化当做攻击的对象,尤其是来自电影界的攻击声音。如宋崇将王朔电影称作“痞子写、痞子演”;邵牧君认为王朔电影中只有“一个类型人物……混水摸鱼的痞子型青年”[8];汪兆骞曾回忆因为自己应王朔邀请在《北京晚报》上发了一篇《侃爷王朔》的文章而遭到一位获茅盾文学奖的朋友的电话取笑:“你是堂堂大编辑家,怎么以爷称王朔?”而一位颇有成就的北京作家在某一次作协在云南的活动上对王兆骞关于王朔的发言颇感不满,拍案而起:“兆骞兄,你休谈王朔,我们耻于与王朔为伍!”[9]这些言辞激烈的发言从侧面印证了王朔在精英文学的群体中愈发艰难的生存。反而是作为普通人的读者才让王朔感到他们是自己真正的支持者。为此他有深切的感受:“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10]真正使王朔对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精英群体感到绝望是“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发生。在这场意在挽救中国社会岌岌可危的人文精神运动中,王朔在其中被迫扮演的角色并不光彩。这场运动后来演变成了文人之间的意气之争,导致王朔在文坛上没有了立身之处,于是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王朔脱离文学启事》,在文章中他将知识分子称为“灵魂的扒手”[11],宣言彻底与知识分子决裂。因此,他对精英文化产生了对抗的心理,体现在作品中,就是描写虚伪猥琐的赵尧舜、自吹自擂的赵宝康等知识分子,如:
赵尧舜诚恳地望着于观:“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上仍流动着热血,仍爱激动,这些,我一想到你、马青、杨重这些可爱的青年,我就不能自己,就睡不着觉。”[12]
赵尧舜的“诚恳”并不真实,当于观、马青这些青年不再捧他的场的时候,赵尧舜就暴露了真面目——在公共电话亭给他的熟人打电话并辱骂他们。这类人物在《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中是没有的。这种对知识分子公开的攻击不仅考验精英文化群体,也同时考验王朔。为了不至于闹得太僵,彻底堵死进入精英文化群体的可能,所以王朔用的是嘲讽这一软刀子,不捅死人,但却恶心人。
其实王朔的这种态度在他的前期创作中还是可以看见一些端倪。如《浮出海面》中追求于晶的那群高级知分子,方言去看于晶表演的舞台剧《屈原》时那个一直试图和他对话的男人;又如《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中吴迪的前男友韩劲、吴迪的好朋友陈伟玲。桂琳认为王朔的小说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有一个从隐藏到不隐藏的过程。王朔在《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中将这种在前期小说中被隐藏的态度放大了,如果前期王朔还用爱情来隐藏反抗的机锋的话,现在王朔就是将机锋直接露出来。对于王朔来说,他和精英文化的对抗感由来已久。他的父母就是精英分子中的一员。对他来说,身为精英分子的父母并没有很好地照顾他、给予他爱,反而是国家的保育院养育了他,所以“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人是爸爸妈妈生的,以为是国家生的”[13]。王朔把对父母的怨恨和不满转嫁到了精英群体的身上。他的这种态度虽然暂时解了自己的困窘、发泄了自己的不满,但他明白作为一名作家是无法长久地站在精英群体的对立面的,因此,在下一个阶段,王朔就不得不与精英文化合流了。
三、回归精英立场
王朔意识到自己的精英身份无法回避是在世纪之交的节点上。新世纪伊始王朔出版了自己的随笔集《无知者无畏》。在《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中,他这样看待自己与精英文化的关系:“不管知识分子对我多么排斥,强调我的知识结构、人品德行以至来历取向和他们的云泥之别,但是,对不起,我还是你们中的一员,至多是比较糟糕的那一种。我们的不同只是表面姿态的不同,时间久了,等咱们都老了,你会发现咱们其实一直是一伙,手心手背的区别,所谓痞子,也是文痞,古已有之,今后也不会绝种,咱们之间打的那些架,都叫窝里斗。”[14]在“我看”系列中,《我看金庸》可以被视作王朔回归精英立场的标志。金庸作为港台通俗文学的代表具有很高的声望,王朔却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定为“四大俗”,并给自己与这“四大俗”划了一条界限。在很多研究者眼里,王朔和金庸并没什么区别,王朔和金庸之争属于大众文化的内斗[15],其实是忽略了世纪之交王朔在思想立场上的转变。
因此第三个阶段是回归精英立场。庐山的某次笔会让王朔对自己“调侃”的模式产生了怀疑,他问自己:“这是文学么?我,用俗话说,真的深沉了。”[6]34这一时期王朔的作品也很多,有:《永失我爱》(1989)、《给我顶住》(1990)、《无人喝彩》(1991)、《动物凶猛》(1991)、《许爷》(1992)、《过把瘾就死》(1992)、《刘慧芳》(1992)、《我是你爸爸》(1991)、《看上去很美》(1999)、《我的千岁寒》(2007)、《致女儿书》(2007)、《和我们的女儿谈话》(2008)。这一段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原因是王朔1992 年之后,有七年的时间没有发表正式的小说。在这七年里,王朔将重心放到了电影、电视剧的剧本创作和文化公司的开设上,王朔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要多赚钱。他不再和精英文化纠缠不清,而是拥抱资本,想做文化托拉斯,将精英作家招致麾下为其工作,打算用市场生产的方式生产文学作品。这一点放在现在已经不稀奇了,但在当时还是创举。和王朔关系密切的华艺的编辑金丽红也承认:“他当时就有郭敬明这样的想法,就说我弄个公司,培养年轻作家,不断地生产电视剧。”[16]超前时代的王朔创办这些公司:一方面是为了赚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培养属于自己的文化势力,以期能够扭转当时他在精英文化群体中势单力薄的处境。
虽然王朔自己并不想丢掉“大众文化”“青年作家”等能够赢得读者好感的头衔,但随着生活经验的变化、人生心态的变化,他已经写不出《顽主》《一点正经没有》这样的小说了。在写作《顽主》等小说时,王朔正有一腔青年的热血需要泼洒,正有一些不满和当时的青年读者类似,正有一种生活走在了时代的前沿。随着名声越来越大、头衔越来越多、生活经历越来越复杂,王朔被迫重新站上精英文化的平台,就像水涨船高,旧有的平台就被淹没了。有些研究者将《看上去很美》作为王朔后期创作的起点,认为前期王朔“为读者写作”,后期“为自己写作”[17]。从“为读者”转向“为自己”,也是祛除浮躁、沉淀自我的一种表现。但其实,王朔后期创作的起点从《给我顶住》就开始了,从“为读者”到“为自己”的转变也是因为当时的读者群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等待》到《看上去很美》正好是一代人的更替,更加年轻的读者取代了上一代的读者。王朔后期创作的变化是被动的。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王朔的小说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中年危机类作品,第二类是老年回忆类作品。这一时期王朔的小说故事多与家庭有关,这也与王朔自身的经历有关。1988 年王朔的女儿出生,这对王朔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这之后王朔就把重心移到了家庭。王朔的锋芒渐渐内敛,他开始描写中年夫妻之间的爱情、离婚、出轨、再婚等,他的批判矛头不再直接指向社会、知识分子,而是指向家庭内部的矛盾。换句话说,他沉下去了。这一点和巴金的创作过程有些类似。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巴金在结婚之后的作品,是他的写作渐渐从浪漫抽象的题材转向具体的婚姻问题、家庭问题的转折点,因此巴金后期的小说《第四病室》《寒夜》等是他成就比较高的小说[18]。与之类似,进入深沉期的王朔写出的作品才真正达到了其艺术的高峰。他不再卖弄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恨离合,不再对知识分子和作家挑肥拣瘦,而是转入了自己的家庭,转入了自己的内心。早已过了而立之年的王朔,开始经营自己的家庭。王朔不再反叛自己的精英身份,他将另一只迈入底层人群中的脚收了回来。这时候他写出的是面对30-40 岁步入中年之后的读者的家庭感悟,他对爱的理解更深了一层。如果说前期王朔的文风比较尖锐和激烈,这时候王朔的文风已经渐趋沉稳,但是反讽却运用得更加老道了。《我的千岁寒》《和我们女儿谈话》和《致女儿书》是王朔时隔许久之后发表的三部作品。第一本书讨论佛法与妄想;后两本书的特殊之处在于王朔写作的对象变成了自己的女儿,用王朔自己的话说是给女儿留下“遗嘱”。而用文字的方式留下“遗嘱”是典型的精英式的方式。由此看出,王朔的创作已经从精英文化立场出发,精英式写作的意味呼之欲出。
结语
通过梳理王朔这些年来的创作路径,可以看出他与精英文化互相缠绕的关系。在一段时期内,他是精英文化的宠儿,在主流期刊上发表过多篇具有强烈精英意识的作品,同时也被精英群体所认可和接受。在另一段时期内,他又被打成了精英文化的逆子,在批评界陷入被围攻的境地。这两种情况既有王朔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有被时代大潮裹挟的因素在内。最后王朔意识到无论怎样反叛,他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他一直都是精英群体的一员。这对他来说既悲哀又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