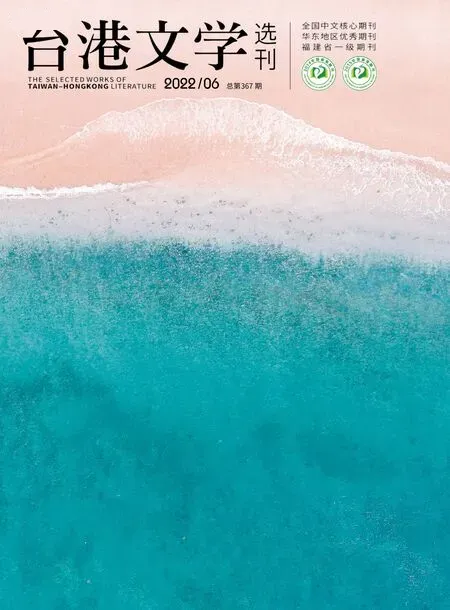看客散尽之后
■ 童元方(中国台湾)
从前陈先生在的时候,我们整天说个不停。他公认的形象是话少、沉默。我问过他,为什么我不觉得呢?真要说起来,他不遑多让,何况很多时候,我说话是在答他出的题;谁要那些题又太复杂,答起来没完。他说:“那是看我跟谁在一起呢!旁人并没说错。”现如今可好了,一般是没人跟我说话,我的双子个性有时在不知不觉间从铿锵走向幽微;在没有对话的世界,有时自然也从宽广走向深刻,从星辰大海走向芍药蔷薇。我发现自己会突然想起些诗句,便浸淫其间,又琢磨、又咀嚼的,不论是否脱离了原诗的语境,总会品出些滋味来。千载下,若仍惆怅,已无感伤。
比如陶渊明,我为什么会无端想起《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几句诗来:
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正夏长风急,林室顿烧燔。
一宅无遗宇,舫舟荫门前。
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
……
这是他归园田居之后的第四年,家宅忽遭大火,所置草屋八九间,竟无一室幸存,只能暂居门前小船。在这样窘迫的情况下,既无一瓦遮头,他亦无怨无悔。倒是身卧小舟,望着将圆的月亮,整个秋夜的天空,一览无遗的清辉,是否因此而兴新生的力量,而得遂其灌园之志?自己人过中年以后,屡遭风雨,才能如宋人一样,逐渐了解陶渊明的情怀。从文学史发展的观点看,在前路茫茫之际,或说从“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的情境中,无翅可展,无桥可渡,陶潜却对我们说,其实你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头”。所以他直抒胸臆:田园将芜胡不归?然后归园田,继而带出了“归家”的主题。这是文学史上的惊天一瞬,我每想起都如初读《归去来兮》时那样震动。在读到“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将圆”时,在火灾后无家可居的当儿望月,应是另类的惊天一瞬,我心中永远的大块文章。有此磅礴而沉稳的底气,才会有日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浑然天成。
也是在这无声的世界,最常想起王维,尤其是《辋川集》的五绝来。绝句既断在未尽之意,五言又相对字少,特别有禅意。好像我随意想想,就觉得舒服。而且轻省,而且自在;身上连最后一粒红尘的重量也飘落了。说说《辛夷坞》与《书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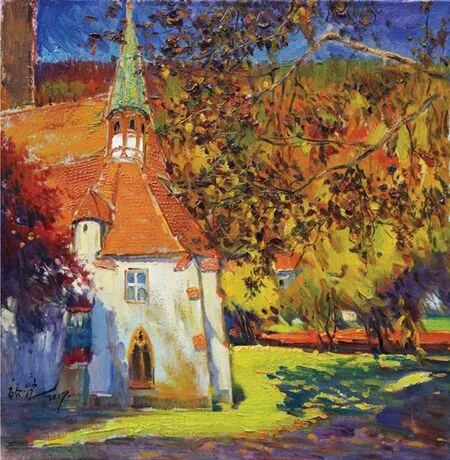
王裕亮 布劳博伊伦小教堂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辛夷坞》
是怎样的心境会让诗人留意花开的周期,继之思及枝头红颜自我完成的生命旅程,其实与外界无关,与旁人无关。开满了,落尽了,无晴亦无雨。理应如此!这样体会了一“静”字,一“闲”字。把眼光缓缓收回,从山中涧口的花朵到家中小院的青苔。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书事》
《书事》是写眼前实时所见。诗人晨早慵懒而起,步入小院,扑上眼帘的不是花树,而是雨后冒生的苍苔;不是静态的一片绿意,而是汹涌上冲的生命力。我七岁开蒙所学的第一首诗,是白居易的《凌霄花》,第一篇文章则是刘禹锡的《陋室铭》。初读“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文字在脑海里即刻转成了图画,而且是动态的,苔会上阶,草亦入帘;儿童读着真是太上口,又上心。王维的诗写得比刘诗早,我却认识得晚。对照坐看诗人的慵懒之姿,他所凝视的苍苔绿意,其势欲飞,实是寓动于静,悄悄展现了萌发的生机。
在无意间捕捉到人间胜景,即使是小院一角的微小世界,我依然心惊于时光之飞逝于无形,而恐风光之不再!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乃永远无解的千古一叹。对于明知将残的美,只能在日落后强留一会儿。下面这首《花下醉》的后两句,即是李商隐对绝情时间的回应,不论是说斜阳,还是说花朵。
寻芳不觉醉流霞,倚树沉眠日已斜。
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
余晖的光彩既尽,一片漆黑中点上红烛,仔细审视花儿最后的美丽。我在独处的光阴中,因为安静而留神流动的“将残”,也因为诗人这最后的呵护与欣赏而在“残”中看到生命的完整与圆熟。想到李商隐对花的留恋,最动人的自然是他的《落花》诗了。
高阁客竟去,小园花乱飞。参差连曲陌,迢递送斜晖。
肠断未忍扫,眼穿仍欲归。芳心向春尽,所得是沾衣。
我一般不是特别喜欢五言律诗,亦不特别钟情咏物诗,但对这首咏物的五律却是情有独钟。不谈诗人寓意,只说诗人寄情。客散之后,才注意到:啊!满天翻飞的缤纷的落花!往远处看,花儿一路飘在院外蜿蜒的小径上,弯弯曲曲伴送着夕阳的光影。好不容易盼来了春天,如今花容与日色皆残。只能因不舍而落泪,而延时,但终究是留不住的。
以诗的形式而言,从五绝到七绝,那未断的欲留的深情在枯荷听雨的审美上终究于亘古中不朽。
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
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残荷听雨声。
仍在青春洋溢的岁华已因年少丧父而遍历风雨的李商隐,对刚经失怙之痛的崔氏兄弟说,虽隔天涯,我懂以后人生的孤寂,总惦记着你们,牵挂着你们;枯荷失了颜色,仍可听雨声,不是吗?
《红楼梦》40回贾母率众游湖,宝玉说荷叶已破败,怎么不拔了去?黛玉说李商隐诗自己只喜欢一句,即:留得残荷听雨声。残荷成了枯荷的变奏,意思却改了;一语道尽了兴衰。
在无人跟我说话的家宅日常,夜色深沉中有时会进入幽独之境,自会想起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我喜欢,特别觉着宁静、纯粹、恣意、自由。少时喜欢诗的意境,也喜欢其映照出的画境,而现在,就是诗画中人。如此,我又在不知不觉间从小院中的一角青苔走向洪荒天地,在幽州台上应和起陈子昂的歌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我更喜欢了。挟着初唐的气势,归来仍是少年。时间本来只是幻象而已,无所谓过去、现在、未来。如果换成英文,前是未来,后是过去:以唐诗的语境而言,自是相反。所以见不到已成过去的古人,也见不到尚未来到的新人,在高台之上、时间之流中,与唐人的眼泪不同,必当长啸慷慨,吐纳呼吸,尽情化出沧海一声笑。
看客散尽之后,回到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选自中国台湾《文讯》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