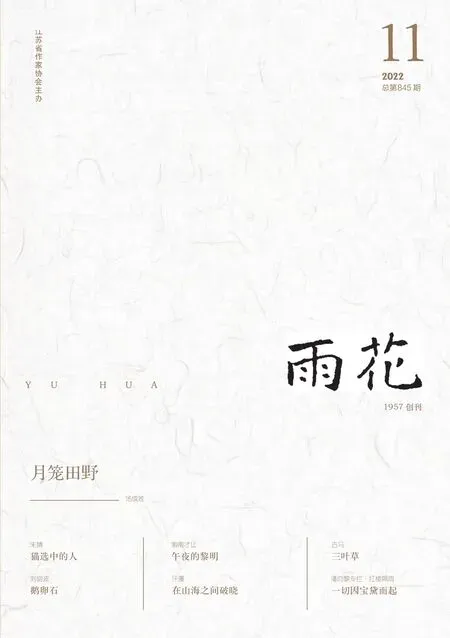下山草
徐晓华
东门医院临街的八九级台阶,原是东门渡口前往大小十街的过道,却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老城的兰市。
卖草的人撒亮口来。头天挖下山的草,蔸上还裹着泥沙,摆在身前,不用吆喝,河风传香入巷,好那一口的哪还坐得住,三三两两围过去,看花,看叶,看品相。
眼光毒的,挑中一苗两苗,并不马上下手,任生意客讨价还价。卖草的多是农人,闲时进山找草,得几个跑路钱,往往熟而不精,却会察言观色,听一坡的报价,心里有了底。叫价稳住时,真正懂草的人,装作不经意挤过去,一把掐断箭上的花,在众人惊呼中付了钱,笑呵呵地捧草而去。
这招管用。生意人要带花买草,没了花,看不准好歹,不敢轻易进手,怕成了“巴手货”。卖的人也是,少了花,寻常的草卖不起价。也有盲买的,叫赌草,时下端正,日后长成什么样子,并无十分把握,回去当奶娃娃疼着,熬过冰雪天,待春雷动土,地气上冲,春风入圃催芽,春水润根提苗,直盼到花箭破土,花苞萌到豆粒大小,方能看出一些叶态花势,看走眼就亏得血本无归。与赌石略同,看似赌运气,考的却是行内功夫。当年湘爷就因为一苗侏儒草损了元气,淡出兰市好多年。
说来识草并不难。好草出深山,行内称为“下山草”,风里抽芽日里晒叶,霜打雪冻,鸟啄虫啮,难免蒙尘染垢,茬残茎断,苗太齐整就假了。再者,人怕败相,草贵变异,叶看金边斑点,花数瓣多瓣少,形畸色变,就不是凡品。这是粗浅的入门功课,修为要精进一层,得从《金漳兰谱》读起,识阴阳寒暑之异,悟草性花形之变,熟栽培灌溉之法,再去兰市历练。
养兰观兰本为雅事闲趣,有了买卖就生出许多贪念。有人租了田土,搭起巨大遮阳棚,不论好歹五元一苗统收,找草的人涌进山,所过处兰子兰孙一扫而光,未必能淘到奇珍。也有人把大棚培植的组培草移栽山里,养得一年半载,沾些枯叶杂根,当下山草卖,让不少初涉兰市的人吃过闷头亏,头年栽下萼异瓣重,来年就还原成普草,一文不值。好比把死水塘的鱼捞到活水里养些时日,当清江鱼卖,买的人回去油煎火熬,入口满嘴泥腥味,直呼上当。还有两郎舅半辈子情同手足,误打误撞入了兰市,合伙做下几单生意,颇有进账,后买进一苗好草,姐夫卖到江浙,赚的钱均分,却被生意客无中生有挑拨,说当姐夫的吃食瞒食,搞得两家人十年不通行走。不讲理的人归罪于兰草,毁了人品,断了人脉。兰草天长地生,没惹谁赖谁,何罪之有?
老城那帮俗称“兰癫子”的玩草人,看到湘爷回来,以为沉闷的兰市会响几声炸雷。谁知众人品草,湘爷并不凑闹热,只坐在最矮的一级台阶上,从麻袋里掏一矿泉水瓶儿出来,倒出细沙,用手掌摸平,食指当笔,在沙面划字,两点秀花蕊,三横擎劲叶。认得他的人,进手一苗好草,过来恭敬地问,湘爷,嫦娥瓣,一苗一芽,一千元买得不?湘爷望也不望,说,七十不管事,八十不当家,人老眼花,哪分得清好歹贵贱,喜欢就是价。问的人讨个没趣,拉下脸说,不想枝头果,不在树下望,天天打早来,专门练字吗?写的“兰”字能抽苗发花?看别人买,心里发痒吧。还有人直戳戳地叹气,唉,不到八十不知八十,人老草枯,老的是心性,枯的是命。
这辈子听的挖苦话清江河都装不下,湘爷横竖不往心里去。指头游走于沙粒,时提时顿,米欧颜柳,肥了瘦,瘦了肥,一笔一画,兰叶舒展,蕙苞带露。心细的人,会盯住湘爷的耳朵看,听到一苗草高价成交,一对招风耳触电似的抖几抖。老家伙,心,还被兰草挽着。
太阳爬上连珠塔顶,赶兰市的人稀拉散去,湘爷才慢悠悠抓起砂粒,灌回矿泉水瓶,往台阶上扫一眼,弃草流浪儿样横七竖八躺在凉丝丝的水泥板上。下山草的命就这样,下山容易回山难。深山幽谷,云里雾里,长得自在,却被找草的当财神菩萨请下山。若有人买,总归有了主,厅堂庭院,书斋案头,养在盆里栽在钵里,一月观花,四时看叶,也不枉春风一度,雨露一场。可玩兰的人嘴刁,挑尽选绝,买走的不到十之一二。奇花不愁无主,普草是配相的,哪怕紫茎报春,素花抽雪,最终却没人要,与菜贩子撇下的烂菜叶一般,扫街的当垃圾清走。
一苗草儿一个命。湘爷看得心疼,一苗苗捡起来捋叶顺茎,放进麻袋,活动活动腰身,袋子往肩上一搭,快步往黄家茆子走去。他得赶回家,侍弄那些草儿。叶折茎断的,修叶剪茬,栽进院后的兰圃。看相好的,润土疏泥,扶根正苗,钵里栽了,过得十天半月,草儿坐了根立了叶,油光渗过叶脉爬到叶梢,搭上斗大的兰字,送给“千里读书会”的新人旧友。兰葳蕤,字精神,人慷慨,兰香透着书香,倒合了诵读的风雅。
当年买茆上的土墙屋,湘爷看中的是屋边二三分荒地。乡里人,田土就是心境,离了泥巴土块,即如被剥得赤身裸体,空荡荡悬在空中,时刻不踏实。肥田大土搬不进城,买房子时就多了心眼,只找单家独户带菜地的。不说种瓜种豆,早薅晚锄之趣,没事去园子转一圈,看辣椒续花、茄子结蒂、丝瓜秧上架,懒散的身子就跟它们一样鲜活。爱上兰草那阵儿,又感叹自己有先见之明,菜地一角,辟为苗圃,兰本土里生发,回到土里,即是回了家。屋边,原有松几棵,杂树十几根,又补栽了一蔸慈竹,长得绿荫垂户,热天还有蝉鸣。他却不甚喜欢城里的蝉,分不清昼夜,三更天叫得吵人。不怪它们乱了分寸,城里灯太多,太亮,一团团光把夜驱散了。
刚进城那会儿,湘爷是个地道的兰痴,比“兰癫子”还要着迷。但凡听闻老城现了异草,即如酒鬼闻了窖香,坐立不安,找个理由带上礼物登门,只求一观。倘若爱说恭维话,人家也是喜欢的,偏偏生性耿直,鉴花品叶,只往实处说。淘到天珍地宝的人,听他一席点评,抠到痒处,赏到妙处,高兴得烫壶蜂蜜酒,去城门洞买卤菜凉菜,摆碟儿装盘儿,对倾三杯五盏。清风拂帘,明月洗尘,叶疏影幽,醉眼相看,都是花下神仙。做瞎买卖的人,本就吃了亏,心里堵一把乱草,湘爷劈头盖脸一通嘲讽,眼睛雾了吗?不晓得看鼻头,裂口的菜花头才买得,淘苗乱草,还当个宝贝,被人耍了呢,硬是死木墩子一个。伤疤上着火烧,哪里听得下去,就黑了脸逐客,你是乡巴佬扫大街——闲得慌,不好好卖肉,东跑西跑干吗?又没谁请你来,出门不看晴雨,进门不分阴阳,亏的是我,又不找你赊肉吃。推推攘攘送出门去,湘爷人到了街上,嘴巴还收不住,大声大气嚷,鼻子短就莫装象,没点见识,玩什么兰草。话多成仇,被人反唇相讥,吃的亏少了吗?自己摔得头破血流,何必笑人栽跟头。
这样的话,石块一样硬,哽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湘爷就蹦蹦跳跳逃了。坐在肉案上细想,几十年山里闯到山外,追根溯源,源于一苗下山草。
好生生去收猪的人,肚子疼什么。那是三月天气,阳雀子闹热了村庄,田里忙着耕种的人多了,山边还有人砍刺烧火土。只好搂起裤子往密林钻,一蓬杨桃藤下,刚好有个草坝,就蹲下来畅快地拉。藤子上雀儿蹦,刺花上蜜蜂嗡,密叶筛下的光影,如顽童涂抹的铅笔画,横重竖叠,没个章法。有只蜂喷香的花不采,绕着飞几圈,歇在上头,故意看他的窘相。他便面红耳赤,想起身走,摸遍口袋没手纸,心“噗通噗通”跳得快了。胡乱扯几把青草救急,整理好衣裤,起身走时,扯开的草丛里,一箭素花挡在身前。他犹豫几秒,还是往外走。走了几步,再回头望,花儿像有话说。索性停下来细看,浅白的花瓣上,布了丝丝血痕,如痛哭后的眼。那神态,似曾相识。他忍不住回头,蹲下身子又看了一回。不错,真是一苗兰草,读书时老师讲河谷植物,对着挂图介绍过,还摇头晃脑引用了前人一段话:兰兼有竹之劲节,梅之幽雅,松之常青,餐霞饮露,清香淑质,不妍不奢,是真君子。何为真君子,那时湘爷还想不透,一缕兰香,却含在了心里。不期头次遇到兰草,是在这样尴尬的场合。扶过花箭闻,有荷叶的清香,还有新竹破开的薄薄甜味。他从刀匣里拔出剔骨刀,正要以刀撬土,见刀刃上残留的血痕,摇了摇头,又插回刀匣。干脆伸出十指,刨开覆土,连根掏出来,托在手心,裹一路香风往家里走。
认得他的人便喊,杀猪佬,有闲心采花花草草,又准备去教书吗?教什么书,怕误人子弟,还是跟猪打交道利索。提到教书,湘爷浑身不爽。举家之力供他读十八年长学,老牌师范毕业,以为跳出了深山老林,到头来还是分回本乡本土,从村小教到中学,家长学生都喜欢,却因管不住嘴,酒后狂言妄语,惹来是非,丢了饭碗。湘爷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只叹了半夜长气,下半夜鼾声就破了窗。第二天神清气朗爬起来,把父亲留下的肉案打理干净,从伙计手里分了半边猪肉,划得肘是肘、肋是肋,粽树叶搓茆子穿了上架,当街挂起来卖,生意好时,比吃粉笔灰的日子宽绰。
捧着兰草往回走,路上就想栽哪里好。栽场坝坎上,怕鸡子啄;栽田里,又怕人扯走。走进走出,相中了装糖的瓷罐,白净外壁描幅淡墨兰草。沾在罐底的糖粒抠出来冲碗水喝下,罐子去溪里洗干净,扶根正苗,培土浇水,栽好后放堂屋正中的八仙桌上,再看时,花瓣像蝉儿的翅膀,要飞起来。看得起劲,找条钢锯皮,折一截磨得锋利,在罐面刻一行小篆:蝉翼无尘。
每天去市场,不嫌麻烦,把兰罐端到肉案上摆着。架上猪肉还在滴血,浓浓血腥味中,兰香格外勾人。砍肉时血滴溅在草上,有闲空,湘爷就拿块抹布,一芽一叶揩干净。完全不搭调的两样东西,让湘爷拢在一处,在小镇人眼里,是老和尚穿花袄,别扭得很。
教书匠卖肉,在小镇上是个新鲜事,不想买肉的人,都来看几眼,以为拿粉笔的手去剁肉,会无从下手。哪晓得湘爷上两代都是杀猪佬,标准的门里师,剔骨割肉,麻利得很。一米八的块头,生得紧扎,一张油腻的羊皮兜在胸前,一把雪亮的尖刀衔在嘴里,肉案前一站,硬是比同行多了些威风。有的学生家长本想买肉的,怕扫了湘爷面子,路过摊子就故意把头扭在一边。湘爷大方得很,扯起嗓门打招呼,来来来,称点肉回去,有筋巴巴的二刀圆尾。喊声过了街,别人不想搭话,碍于情面应一声,以为认错了,您还吃得这个苦啊,锅里个把月没见荤,那就割斤把。湘爷把肉称好递过去,说供学生不简单,一斤少一毛钱。家长客套道,哪能让您吃亏,卖肉赚的是辛苦钱,就按市价八毛一斤算。湘爷认真地说,不光跟你少,学生家长买肉都优惠,天下唯有读书苦,娃儿多吃一口肉,多读几句书,那才是大赚。时间一长,“让一毛”的肉摊出了名。
摆了肉案,得走村串户收猪,去学生家里就多了。湘爷让价在前,卖猪时,家长们不好意思喂食。一头肥猪,少则吃八斤十斤草料,草口好的要吃十几二十斤,一进一出算账是十几块钱,这人情送得大了。同行们说他心机深,卖小乖得了大便宜。湘爷开玩笑似的回一句,不舍花露,哪得蜜甜。
一日午后,早前学校的同事谭老师来到摊前。湘爷老远就问,砍肉吗?喜欢哪块割哪块。谭老师摇头说,放早学了,送学生顺路来转转,看这苗草乖,卖不卖呢?湘爷愣了一愣,随口说,肉是卖的,草是看的。谭老师果真端起罐子看了一回,看得直摇头,一苗好草,你未必养得活,兰性喜幽,最怕暴晒,露天街头,茅草都会晒枯。又指着罐底说,不留气孔,渍水腐根,几天就成了烂泥巴,好比把你鼻子嘴巴捂紧,还有活路吗。草命哪有那么金贵,石头上也生根呢,再说,误一苗草事小,误人子弟才缺德。湘爷话里有话。谭老师明白,湘爷说的是气话,意思是离了教书,照样活得旺,顺便讥讽自己教书不在行。他长叹一声,一苗神仙草投错了门,可惜可惜。转身走了。湘爷也不挽留,心里说,不晓得好多娃儿被庸师误了,嘴里却故意大声吆喝,熟食喂的黑猪肉,膘厚肉嫩哦。
谭老师还没走远,湘爷急忙端起兰罐看,有好几片叶子垂了肩。想来他说的在理。一个下午,他的心思就盘在草上。人家好模好样长在山里,早听雀鸟叫,晚听流水响,花开香一朝,草长绿一岁,活得无瓜无葛,淘神费力弄下山,又养不好,糟蹋呢。思去想来,来买肉的喊几遍,还回不过神。旁边摊位的人笑他,这草前生是个美人,受了你的恩惠,转世变妖,缠你下半辈子的。
这话听得湘爷心底一震。清朗世界有聊斋之事不成?看那花确有些灵异,素颜堆雪,有泪流不出一滴,有话说不出一句。
迷糊间,他想起舅舅家的表妹。舅妈说,表妹落地,房前屋后蝉叫得叫人心慌。洗过三朝,发现眉眼间有个清晰的胎记,不红不黑,一抹浅灰,形如一对张开的蝉翼。遍野蝉声里,舅舅给表妹取了个小名,叫蝉儿。湘爷发蒙就在舅舅家寄读,最熟悉表妹的哭叫,别人的娃是夜哭郎,表妹大白天拉开嗓门哭,哭得珠眼血丝结网,胎记也变得透亮。舅舅白天教私塾,夜里去街上米行当记账先生,舅母一个人忙田里活路,湘爷放学回来要背上表妹做作业,蝉儿算是在湘爷背上哭大的。玩伴们笑他,背个小媳妇。湘爷红了脸争辩,是我表妹呢。大伙儿不依不饶,唱起歌儿起哄,表妹表,从小好,一天不好,背时老表。听得湘爷背也不是,放也不是。表妹却在背上哼起了童谣:
蝉儿飞,飞下树,
飞到哪里去?
飞到我梦里。
一梦醒来蝉儿惊,
一翅飞到池塘里。
草木落叶雪落地,
变个虫儿钻了泥。
热天还好,表妹哭声起,湘爷就爬上树捉几只蝉下来,“胡子胡子挂齐,胡子胡子挂齐,挂齐呀,挂齐啦”,蝉鸣声中表妹很快住了哭。寒冬之际,秋蝉已化蛹入泥,表妹闹脾气,湘爷哄不好时,学几声蝉鸣,表妹就安静了。别的小女孩喜欢踢毽子、跳房子,表妹却爱爬树抓蝉,还缠着湘爷问,蝉儿吃什么?喝露水。露水好喝吗?凉丝丝的润喉,要不叫声那么亮。我也要喝露水,声音会跟蝉儿一样好听吗?是吧,我也不懂。
读初中的湘爷是真不懂。上古文课,老师讲蝉饮金风,餐玉露,振翅发声。湘爷记住了,回去说给表妹听。好几次他发现表妹傻傻地站在树下,踮脚仰望伏在叶间的鸣蝉。蝉声起,表妹脸上的蝉翼活灵活现。有日午休,校园的树上飞来好多只蝉,齐声鼓噪,像嘶哑的哭。听得湘爷下午几节课走了神。挨到放学跑回去,舅舅屋里围了好多人,蝉儿在舅妈怀里,小脸上灰白的胎记褪了色。六七岁的孩子爬那么高的树,干什么呢?大人们猜不透。湘爷明白,十二岁的湘爷不敢说出来。哀恸声中,湘爷隐隐听到了熟悉的童谣:
蝉儿飞,飞下树,
飞到哪里去?
飞到我梦里。
大人们把表妹装进木匣子,送到几里外的山里,盖了一堆黄土。那片密林子,大树参天小树据地,却静悄悄听不到一声蝉鸣,热烘烘的六月风,烫得树叶儿发卷。湘爷猜想,表妹是跟蝉儿做伴飞走了。
忆起旧人旧事,一把枯泪,嘀嗒在清幽的兰叶上。由教书到当街卖肉,命运反转之际,碰到这苗兰草,是福是祸,是冥冥中的指引,还是毫无关联的巧遇?湘爷想得乱糟糟的。
他等不到散场,四点多收了肉案,搂着兰罐往家里去。路过邮局,一个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一脸苦相,跟柜台里的营业员争吵。上世纪80年代初,镇上一条独街,两排铺面,街头走街尾,卖葱头蒜脑的都认得,哪来的生面孔。湘爷便过去问。那人自称姓牛,名有旺,天门岳口的,与几个生意客来山里收老牛废牛,一车牛收好了,没办长途贩运手续,被工商局的扣了下来,说要当投机倒把处理。合伙人见事不好,一溜烟走了,剩下身上分文没有的他,来邮局拍电报,让家里寄路费。电报拍了,要一元七角的电报费,口袋翻破,毛角子都没一个。又找不到熟人借,他就把一件糊得看不到原色的外套脱了,想做抵押。营业员哪肯答应。
问明就里,湘爷掏出一元七角钱,帮他付了电报费。两人走出邮局,叙起年庚,都满三十九了,湘爷比他大个把月。牛有旺叫了声哥,说,遭罪呢,两天只喝了一碗稀饭,住宿费也没给,老板天天催。湘爷说,乱草长天涯,天南海北的出门不容易,不嫌弃跟我去吃住,等你家里消息。牛有旺道了谢,又好奇地问,这年月都在蹦生活,你还玩兰草?湘爷说,山里遇到的,花开得奇,扯回来栽个好看。牛有旺又问,罐上的字谁刻的?湘爷说,我信手刻的。哈,一手字写得不错,名字也取得好,这草就叫蝉翼梅瓣,你刻的蝉翼无尘,蒙的?他顺手接过罐子,偏起脑壳看了一会儿说,奇草哦,卖得好,比几头牛值钱。湘爷说,做牛生意的,不怕把牛皮吹破了。瞎!你是真不懂吗?我拿两头牛换你一苗草,干不干?只是你这栽法不对。说着就吩咐湘爷去生资门市买个花钵,回去换钵。
换钵之法,马虎不得,要敲碎原钵,理顺根须,而后移栽。何故?百草多为草根,兰科是肉根,皮细肉嫩,撬土移苗不仔细会伤根断须。根为固土培元之要害,根损则神亏,神亏则香残韵散。看湘爷听得入迷,牛有旺越发卖弄起来。根与壤合,气与神通,纳日月精华,山川灵气,方得自然之本。草木如人,人亦草木,若人离了生养之地,气脉变,风向移,阴阳改,序属异,轻则水土不服,重则气运两损,襁褓之土,生存之基,不可轻移也。听了半天兰经,湘爷听出些道道来。反问道,明知生养之地不可轻移,你不好好教书,偏要跑山里来做牛生意?牛有旺叹口气说,若非无奈,谁肯放下现世安稳。
夜来好天色,松风竹影,明月蛙鼓。湘爷熬一罐老树茶,坐院坝听牛有旺山南海北地侃。他早前是农学院毕业的,在农校教书,家里娃儿多,老婆是个药罐子,硬是养不走,才赶了下海潮,停薪留职,跟朋友学做牛生意,哪晓得第一趟就不顺。九头牛,本钱加路费,花去上万块,要是牛被没收,就回不去“南朝”了。问湘爷有没有办法。湘爷笑着说,牛有旺,牛——有旺,做牛生意该红火才对。一句话把牛有旺逗笑了。沉默了一会儿,湘爷说,办法有,只怕就在这蔸草身上。牛有旺问,怎么扯到兰草了?湘爷说,与我以前同事的谭老师,老婆在工商局上班,他平素喜欢花草,下午还来看了这蔸草,托他说说,事情或有转机。牛有旺说,旱田栽水草,试一下吧。
两人正聊着,院门响了。来人正是谭老师。茶没上手就绕着花钵看。湘爷问,有什么不对?对,对,谁换钵的,深得通透之理,是行家里手。湘爷介绍二人认识,煮水续茶,面兰叙话。蔫茄子一样的牛有旺,说起兰草嗓门大了,养兰品兰,仪态形神,无所不及。又论历代咏兰诗文,说最爱宋人的一句“着意闻时不肯香,香在无心处”。谭老师拍掌附和,好一个“无心”,造幽境发幽思得幽趣。一唱一和,陶醉其中,湘爷哪插得上嘴。听到后来,又觉得不对劲,这牛有旺,浮草一根,河东漂河西,哪来的闲情逸致,一花一草,好上天好下地,怎么都是个闲物,能填饱肚子?
眼看月亮翻过屋脊,湘爷就指着花钵对谭老师说,好久不来走动,今晚是为它来的吧,我也养不好,就送给你,顺便说个事,看能帮个忙不?一五一十说了牛有旺贩牛被扣之事。谭老师顿了顿才说,你也是个读书人出身,怎不知时事,如今山外时兴做生意,叫开放搞活,不偷不抢不骗,南方之物北方卖,淡季买旺季卖,赚点差价,合法生意政府鼓励做呢,不过手续要办齐。这个忙,我肯定帮了。草,你若不卖,我不白要,来年发了新苗,记得分一苗给我。说完起身走了。
夜半的月光洒下来,地上如抹了一层细腻顺滑的猪板油。湘爷深吸几口兰香,自言自语,过些日子,花儿要谢了。
几天不见谭老师的影子。牛有旺好像把牛的事忘了,吃饭睡觉前还要念半天兰经,生怕湘爷听不入耳。下乡买猪他也一路跟着,见到林子就拉着湘爷往里钻,现场教徒弟。清江河谷,土壤疏松,雾气重,树林密,最适合兰草生长。春兰、剑兰、寒兰、兔儿兰、春剑、蕙兰,哪些伴石而生,哪些抱谷而长,哪些爱山涧清幽,哪些爱山脊通畅,讲得环环相扣。湘爷从心里佩服起来,便开玩笑说,这么喜欢兰草,你该改名叫牛有兰。牛有旺说,兰草这东西有灵气,光喜欢不行,没缘分的擦肩而过,有缘呢,绕十个八个弯,还是会相逢,好比你我。
又过几天,盼来了谭老师回话,办好手续就能放行。湘爷赶紧跑村跑乡打证明,又到工商局办手续。证件办下来,编号是恩施001 号长途贩运证。办的这个证,湘爷最是得意,多年后还跟朋友吹牛,说乡里的一个杀猪佬,本事不大胆子大,是全市第一个搞长途贩运的。揣着那张盖了大印的纸,像捡了一坛银子,满面春风回了小镇。他和牛有旺商量,合伙做这单生意,花的本钱湘爷出一半。多年累积的人缘不错,湘爷去贷款、租车、装车启运,没费多大周折。
出山途中,两人盘算着市场牛价,若一切顺利,除去费用,赚三千没问题。当时上班的月薪才四五十元,上千数的钱可是不得了的一笔大钱。牛有旺说,我的病婆娘有指望了。山路颠簸雨雾大,路面湿滑,湘爷一路嘱咐司机慢些开。世事蹊跷,担心什么还真就来什么。一个下坡急弯,刹车踩急了,车忽然侧翻下坎。等湘爷抖落满身玻璃渣钻出驾驶室,司机和牛有旺也哼哼唧唧爬了起来,幸得土坎不高,下面是熟田,雨后泥地疏软,人没受大伤,但车厢里的牛却摔得断骨瘸腿,哪还卖得出去。牛有旺哭着问,怎么办?湘爷冲他吼道,大男人哭个卵!霜再大,能把草冻死?嘴里说得豪气,心里却急得冒烟,上万块的本钱,该怎么还?
当头一棒并没有打垮湘爷。他去城里找到肉联厂的熟人,把牛运去宰杀了,九头牛七千多斤肉,加牛皮一起卖掉,算账亏了三千多,还好车损有保险赔。回小镇路上,湘爷嘱咐司机和牛有旺,千万不要说翻车的事,要打起精神,说行情好,到宜昌就把牛卖了,赚了好几千块。牛有旺听得一愣一愣的。湘爷说,话还要说破吗?让人知道生意泼了,催贷款的明早就会登门,我把屋子卖了也还不齐。
回到镇上,湘爷体体面面在馆子里请了一大桌客。众人称道,说湘爷敢开生荒,以后山里的东西好卖了。席间,谭老师悄悄问,你脸上怎么有伤?湘爷说,还不是喝酒害的,赚了钱心里高兴,多喝了一口,回旅馆摔了一跤。谭老师又看了看牛有旺,意味深长地说,你俩真投缘,摔跤都一路,这个酒嘛,以后还是少喝。送走客人,湘爷才对牛有旺说,这回的损失,我认了,卖牛肉的钱,你先拿回去安顿家口,我的贷款再想办法还。牛有旺说,那不行。湘爷说,莫啰嗦,我一个人过生活,哪门都磨得过去,你家里病人急用呢。说完把装钱的布口袋塞给了牛有旺。牛有旺抓着钱袋子,望着湘爷说不出话来。
当晚回到湘爷家,两人各有心事,相对无言。放在腰墙上的那钵兰草却长得越发苍劲,新发的三苗芽箭破土,有鸭嘴大小了。
连日操劳,湘爷睡得沉,醒来发现牛有旺走了,床头抽屉桌上搁着熟悉的钱袋子。打开袋子,发现有一便条:
好兄弟,我走了,钱我拿走了一半,不是我不要脸,没办法,救急用,让你跟我受累,深表歉意。人生无常,这趟生意败了,却结识了你这位热心的朋友,还见到了珍稀的兰草,也搞明白了我只适合吃粉笔灰。另,我讲的培草识草之法,并非心血来潮逞口舌之利,好歹我也是农大毕业的高材生,你若真爱兰,日后或许有益。啰嗦一句,养兰要义,在于与兰共生,修身养性。相处月余,兄为人处事即如兰香袭人,深为钦佩。所欠之钱,绝不赖账,稍有转机,定当上门奉还。
大恩不言谢!期待再见!
牛有旺 即日晨
看到落款的名字,湘爷想笑,叫什么牛有旺哦,该叫牛有难才对。杀猪杀得好好的,神差鬼使遇到这么蔸草,遇上这么个人,生意没做成,背了几千块的贷款,后头日子怎么过。湘爷默想了一天,想不出个头绪来。眼睛,就落在了那钵兰草之上。那草像受了莫大的委屈,素叶在风里微微颤动着。窗外,牛毛雨笼罩了小镇。
湘爷到底是个通透之人。当晚就端上兰草去了谭老师家里,原原本本讲了翻车的事,求谭老师帮忙去信用社担个保,贷款分期还,拆屋卖瓦,绝不拖欠。谭老师问他日后有何打算。湘爷说,还不是杀猪卖,想去城里开个肉案。谭老师点了点头说,这个想法我支持,早就该到城里去,乡里买猪城里卖肉,差价大些。又问,这草你拿来干啥,不兴这么搞的。湘爷说,我去做事,哪里管得到,寄你家里帮我养着。谭老师也干脆,就应承了,好吧,是我劝你去做的牛生意,我也有份责任,保我担了,兰草帮你养着。
沿路雨小雾重,湘爷带了杀猪的行头,赶早班车进了恩施城。与月前相比,大街小巷忽然敞亮了,临街的铺面装了柜台,货架上摆了各色货物,街面上有个空地就摆了小摊,昔日冷清的街道上,到处是打货送货的人。湘爷租了间房管所的房子,又找居委会申请,在东门上支起了肉摊。那周围住户密,饭馆多,哪家不买肉呢?大行大市,可不敢降价卖,初来乍到,得讲行规。不过,湘爷脑壳转得快,生意做得活,价钱虽不少,有时给这个搭块寸骨,给那个送二两边角肉,需要砍剁骨头的,就帮忙砍规矩包理顺。记性好嘴巴又乖,来买肉的,这个叫大伯那个喊大嫂,亲热得很,慢慢回头客多起来,杀一头猪经常早市没散就卖光了。头个月做下来,净赚六百块。他盘算着做下去,两年就能把贷款还清。
活该走一截弯路。湘爷的肉摊开张没多久,卖兰草的人看中了东门的人气。买卖兰草的人一天天多起来。起初,湘爷只是隔街解馋,闻闻兰香,有时竖起耳朵听听热闹。后来赶兰市的人过来称肉,慢慢熟了,也聊几句兰草。回数多了,闻到兰香心里痒,不免抽空跑过去看,想长些见识学些乖,心里还一遍一遍叮嘱自己,切莫陷进去。
有天跑早暴雨,赶兰市的人呼啦走光了,来卖草的一位小哥来得迟,见兰市没人,就来湘爷的棚子里躲雨,顺便把口袋里的十几苗草拿出来,要湘爷帮忙认认。湘爷看了一眼,就说,免得你提回去,不嫌少二十元一苗,我全部要了。那小哥高兴坏了,数钱成交,欢欢喜喜回去了。湘爷买时也拿不准是不是梅瓣,看前几天有人卖过,反正进手价不高,亏不了多少。第二天,等不到肉卖完,就跑到兰市,刚把袋口打开,才露出叶片,几个兰癫子就扯住了口袋,说一百元一苗,全要了。湘爷还算机灵,说,我自己要留五苗。哪留得住,几个人扯扯拉拉把口袋拿过去,数了一千五百元钱给他,提起口袋就跑了。一进一出,湘爷赚了一千二百元,是两个月卖肉的赚头,本该高兴。可没过几天,听兰市的人说,真是梅瓣,他们拿去卖了五百一苗。湘爷感叹,兰市的水太深了,要多学点识草辨花的真本事,赚钱快呢。有一回就有二回,他又出手做了几单,小打小敲,赚多赔少,眼看贷款就要还清了,手头还攒了一笔小钱,只是卖肉的生意却寡淡下来。
湘爷心思跑偏了,肉摊每天卖多卖少,心里也不发愁,听说哪里有苗好草,倒是要去赶热闹。还是那个卖梅瓣的小哥,有天来到摊前,神神秘秘从口袋里取出一苗一芽草来,茎叶短而肥厚,看不出有什么稀奇。那小哥压低声音说,没见过吧,叫侏儒草,难得一见呢,您帮过我的,我也不去那边卖了,出个良心价,就卖给您。湘爷拿不准,又觉得头回把他的梅瓣压得太低,情面上过不去,就说,你便宜点卖,我看有没有那么多钱。那小哥说,一苗三千五,一芽送给您,一分都不能少了。湘爷也不是轻易上当的人,趁上厕所的机会跑去兰市,找好几个兰癫子问,都说那一定是侏儒草,哪里有,出五千一苗都不亏。湘爷嘴里说随便问问,心里却乐得开花,赶回租住房,把压在棉絮下的钱袋子拿出来,数了两遍,才一千九百块。想到表哥在中药材门市部当经理,赶忙跑去,说肥猪最近要涨价,想多收几头,本钱差了点,专门来借的。表哥晓得湘爷在城里卖肉,就没多问,借了一千六百元给他。他满心欢喜地回去与那小哥成交了。次日肉摊摆出来,还没开秤,就去了兰市。开始还有几个人看货,却被一个外地来的老板识破了,这哪是侏儒草,苗圃里做出来的假货,你不信养半年,看走眼我赔你一万。湘爷心里还不服气,觉得那小哥怎么都不会蒙人,是那些人有眼无珠不识货。心里七上八下,把草捧回去栽了,左想右想一定是兰癫子们看走了眼。
第二天中午回乡下收猪,湘爷就把那草带上,去找谭老师。谭老师看着看着,就摆了头,看得湘爷心里发抖。谭老师又拿出放大镜细看了一回,才冷冷地说,什么侏儒草,使了手脚的。又很正色地问湘爷,做着好好的猪生意,去玩什么兰草呢,那个热闹赶不得,泡泡一样,一吹就大,一碰就破。你的贷款还没还清哦。湘爷就怄得呼哧呼哧喘粗气。谭老师泡了杯茶给湘爷,又一字一顿地说,讲本事,你比我大,知识也多,记不记得昔日的八旗子弟,成天蹲戏园子、逛花街、斗蛐蛐、逗雀儿,把一座锦绣江山败得支离破碎。以你的处境,还去追风求雅,眼里尽是浮华,再不警醒,破落的日子只怕不远了。乡里人进城做个生意不简单,这么好的市场,自己不珍惜,指望老天处处帮你?混不下去又灰头土脸回乡下来杀猪?你若真是爱兰的人,要明白一句话,下山容易回山难。
湘爷好一番神聊!由兰草而追忆过往,讲到此处,湘爷的一张老脸窘得绯红。谁没个年轻的时候,像您现在的生活,大家都羡慕呢。我赶忙把话题扯开了。
初识湘爷,是受邀参加“千里读书会”与本土作家在社区的一次互动。记得参加的七八十人中,有鹤发童颜的老者,也有七八岁的小学生,诵读国学经典,也读本土作家的诗文,原以为只是退休的老人家做个样子,搞个场面热闹,谁知上台诵读的人一个个有板有眼,对作品的情感把握还浓淡得体。心中便惶恐起来,头几次湘爷托人请我参加,我以单位事多为由推脱了。会后听闻活动的组织、策划、资金筹措,湘爷是一把抓,在附近的社区街道轮换着举办,很多居民成了读书会的票友,便对湘爷刮目相看起来。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家,劳神费力推广读书活动,真是不简单。后来又去参加了几次,可能因为都是从乡里进城谋生的,和湘爷蛮投缘,聊着就聊到了湘爷的大半生。
走的时候,湘爷专门写了条幅送我,是明代陈汝言《兰》诗中的两句:何如在林壑,时至还自芳。本想问问那盆蝉翼梅瓣和后来的变故,湘爷笑笑说,还要送你一钵兰草的,等开春了去我的兰圃,你自己选。
选什么呢,兰遇有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