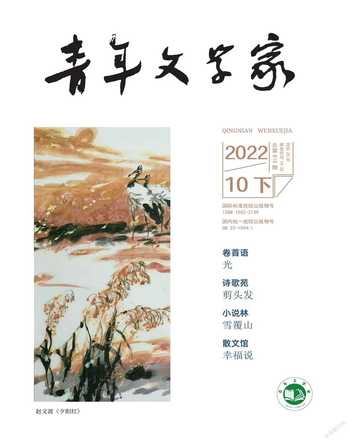文学创作中的真实与虚构
倪润梅
众所周知,《紅楼梦》是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的经典之作,想要读懂该作品,就难以绕过小说中关于真实与虚构的表达。因此,本文将以《红楼梦》为例,浅谈一下本人对文学作品中真实与虚构间关系的看法。因本人能力有限,若有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何谓真实与虚构
回顾文学史和批评史可以发现“真实”与“虚构”这一对概念在作品中互相制衡、依托,并行发展。洪子诚先生探讨过什么叫“真实性”、什么叫“真实”,以及如何判断“真实”等问题,但最终没能找出标准答案。事实上“真实”的定义本身就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有时亲眼所见都不一定为真,口耳相传抑或是史书野史上记载的内容,可信度又有多高呢?雷内·韦勒克在其《文学理论》中谈到所有虚构性的作品,不论其艺术造诣高低,都可以纳入到文学的范围内,文学的核心性质就是虚构性,而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就是因为小说中存在着虚构的成分。《美学大辞典》是这样定义“虚构”的:虚构是相对于实际生活而言的,虚指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限于描写实际发生的事,人物、事件、时间、地点都可以改变;虚构指构思、结构、重新组合。通过虚构,现实美转化为艺术美,作品获得假定性,并渗透进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评价。虚构从一个侧面体现着艺术规律。它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按可然律或必然律进行的虚构,即遵从生活本身的逻辑,对现实生活所提供的素材进行选择、分解、提炼、重组,从而创造出酷肖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象;另一类是按主观情感逻辑进行的虚构,即创作者不囿于现实生活可然律或必然律的限制,而根据自己的感受、情绪和理想,进行大胆地变形、夸张,从而创造出生活中不可能实有的艺术形象。以小说为例,小说既可以是真实的,同时也可以是虚构的,作者常常将个人经验作为小说的基础所在。艺术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事实上所有的文学作品中都存在着作者的个人经验,只是文学创作并不强求作者将其个人经验直接作为内容来书写。带有自传体以及使用个人经验的写作都是来自于真实,并在真实的基础上开始建构的,这或许可以解释红学“索隐派”和“考证派”的主要观点及相关研究。其实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很早就接触到了周汝昌、刘心武等先生的学说,如贾家的原型就是曹家,而贾宝玉指的就是曹雪芹自己,脂砚斋就是史湘云等观点。一开始,我看他们从各种细节里抽丝剥茧、旁征博引,觉得很有道理:林黛玉刚进贾府时看到的“荣禧堂”金匾就是由康熙亲笔御书的赠予曹寅织造府的“萱瑞堂”匾演化而来,而那副银联则是太子胤礽被废前钟爱的刘禹锡的作品,“黼黻”则影射的是曹家几代曾担任过江宁织造……但是了解得越多,产生的疑惑也就越多,诸如他怎么就这边拉出来两句,那边拉出来两句,然后结合史书一考证,凤姐的原型就是魏忠贤呢?慢慢地,我觉得后期这些流派的考证有些穿凿太过,或者说是先预设目标,然后再搜寻证据,非要从犄角旮旯里找到的几句话上延伸出去,再和各种历史相对照,由此得出《红楼梦》是隐写明亡史等推断,让我恍惚间仿佛成了鲁迅先生笔下在酒店里硬要被孔乙己教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小孩儿。
我认为文学即使多少有一点儿现实生活的影子,然而文学毕竟离不开虚构。正如鲁迅指出的那样,作家所写的事情大多是听过或者见过的,也并不全用事实,包括写人物也一样,不会完全照着一个人去描述,总是会想象着不同的人来成功地拼凑成作家自己理想的人物,也正是凭着这点见过或者听过的印象来组合成一个全新的角色的,所以即便是想象虚构也不会离开真实的存在。就像《红楼梦》一书,虽然不是纪实小说,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举世公认的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巨著之一。正如冯梦龙在《警世通言·序》中所说,“野史尽真乎?曰: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共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不论作品的真假与否,都有作者的一番用意在里面,或是为了“补金匮石室之遗”(冯梦龙《警世通言》),或是为了“激扬劝诱、悲歌感慨”(冯梦龙《警世通言》)罢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构建了两个叙述维度:一个是真实的叙述维度,以荣宁二府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和情恨纠葛为主;另一个是虚构的叙述维度,以与现实相对的太虚幻境、风月宝鉴、木石前缘等为主。可以说整部《红楼梦》是以兴衰为经、虚实为纬,相互交织、映衬建构而成。《红楼梦》的虚实相生是曹雪芹在小说起始就挑明了的:将“真事隐去”,以“假语村言”,而脂砚斋等人在评点时也多次提到这一点。我认为《红楼梦》的虚实相生主要体现在小说的情节结构设置和人物塑造两方面。
二、《红楼梦》中的虚实相生
就情节结构来说,小说以虚实结合起笔,直接奠定了其总基调。《红楼梦》在开卷第一回设置了一个自述性段落,作者用现实的笔调写出了作品的创作背景、成书经历、故事起因及人物原型等,接下来又用虚幻的笔调写明本书只是记录一则刻在石头上的故事,而这个顽石还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这样闻所未闻也无从考稽的地方,且无“朝代年纪、地舆邦国”可考。这块无才补天、幻形入世的顽石被那渺渺真人和茫茫大士带入红尘,在经历了一番人生之后,在自己的石面上写下了所有的经历,即后文贾府故事的前身。将这一实一虚的两段故事融合起来便是《红楼梦》整个作品的起源了,后面作者又转而写“篇中间用‘梦‘幻等字,却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似乎是在提醒读者这部作品的本旨是虚化的,不可当真。这样的结构设置就很好地体现了虚实相生的艺术手法。小说第五回,贾宝玉在梦中神游了太虚幻境(太虚玄境)。当他从凡间梦游而出,到仙界参透天机时,不仅在“薄命司”看到了《金陵十二钗》的图册,还听到了《红楼梦曲》,了解《红楼梦》一书的读者应该都知道它们暗示着书中黛玉、宝钗等一众女性的命运与结局。贾府以及府中众人在冥冥之中进入到了太虚幻境(太虚玄境)早已设置好的结局当中。太虚幻境(太虚玄境)相对于贾府中现实的大观园来说是虚幻的,但是对于贾府来说现实的大观园在读者眼中是虚幻的,也是作者创设出来的一个虚幻的世界,幻中有真,真中有幻,虚虚实实。作品中这样虚实结合的例子不胜枚举,限于篇幅原因,此处不再一一列举。此外,若是联系小说创作的时代背景,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曹雪芹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这部作品的虚构性,或许只是为了掩人耳目,避免麻烦;又或许这实为反语,是在提醒读者反其道为之,要用现实的眼光阅读小说,从而读出真实,读到作品真正的主旨所在。
就人物塑造来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了众多栩栩如生、经久不衰的人物形象,他们给人的感觉是如此的真实,好像薛宝钗、史湘云、妙玉等人就在那不同时空下经历着自己的悲欢离合。我想,小说人物塑造的成功也离不开作者在建构人物时运用了虚实结合的写作手法。《红楼梦》的主要描述地点是贾府这一点毋庸置疑,曹雪芹却把与之关联甚微的贾雨村和甄士隐放在了小说的起首,这看似有失轻重,细品之却饱含深意。贾雨村和甄士隐二人可谓是小说的引子人物,虽然篇幅较少,却在小说中起到了很好的引入与作结的作用。曹雪芹对二人的描写就是虚实结合的典例。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便清晰地告诉读者这二人名字的含义及他们在全文中的作用,“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闱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如此看来,甄士隐原是“真事隐”,贾雨村原是“假语村言”,这里的一“真”一“假”就成功奠定了全文虚实结合的基调。宋健先生在《〈红楼梦〉虚幻描写初论》中谈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假借石头之口说明了他所写的乃是他‘半世亲历亲闻的真实故事,‘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加穿凿,体现了生活的真实性。”言外之意即《红楼梦》并非杜撰,只是将“真事隐去”而已,同时也暗暗提醒了读者书中多处名称皆是取谐音而来。有一点值得读者去关注,即作者既说是“梦幻”,又何来“曾历过”“真事”一说?此中的孰真孰假恐怕只能靠读者自己去判断了。而后文中甄士隐与贾雨村之间的交往及各自的生活经历甚是俗世平常,充满着人间烟火气,让人很难不相信这世上就是有着这样两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是叫甄士隐的隐居乡宦,一个是叫贾雨村的落魄读书人。再后面甄士隐随道人飘然而去,贾雨村引出了演说荣国府的故事,这正是曹雪芹在前段铺垫的“真事隐”和“假语村言”。小说随后便顺理成章地以贾雨村为切入点,把故事重心转移到了贾府。而《红楼梦》的最后一回回目是“甄士隐详说太虚境,贾雨村归结红楼梦”,小说在完结了贾府的故事后又以这二人作结:贾雨村因罪被贬为平民,归家途中遇到了甄士隐,此时已然飘升的甄士隐再次向贾雨村详说太虚幻境(太虚玄境),二人遂一同离开尘世。后经几世几劫,空空道人偶遇顽石知晓其中曲折,便到悼红轩寻到了曹雪芹,归结了《红楼梦》,直到此处整个故事才尘埃落定。甄士隐与贾雨村二人在小说中时隐时现,不时提醒着读者《红楼梦》“真事隐”“假语村言”的创作方法。当然,除了甄士隐和贾雨村外,小说中还有许多真真假假的人物,例如“跛足道士”和“癞头和尚”即渺渺真人和茫茫大士,他们在书中的活动实际构成了《红楼梦》叙事的一条暗线。还有贾元春、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以及钟情大士等,甚至“甄”“贾”宝玉的塑造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曹雪芹综合了自身的经历,通过文学想象创作而成的,但是那与主人公有着丝丝缕缕联系的不同阶级、年龄、性别、姿容和性格的几百个人物,那发生在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冲突,那在他们身上所反映出的人间百态,却是那么真实可信。曹雪芹是在通过虚实结合的方式来用“实”批判社会、用“虚”寄托理想。
或许有读者会认为曹雪芹一方面强调他“实录其事”的创作主张,一方面又多次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方式创作的小说,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事实上并非如此,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可以理解为作者抛弃了写实的自然主义叙写,通过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再创造,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将其升华转换为艺术真实。正如宋健先生在《〈红楼梦〉虚幻描写初论》中说的那样:“所谓‘虚,即是‘不实;所谓‘幻,即是‘不真,‘虚与‘幻都是假。”这一创作理念反映到作品中,就如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审虚实》中所讨论的那样:“实者,就事敷陈,不假造作,有根有据之谓也。虚者,空中楼阁,随意构成,无影无形之谓也。”也就是曹老先生自己所说的“荒唐”二字。曹雪芹在作品中通过现实理想国大观园和幻梦理想国太虚幻境(太虚玄境)的破灭,尖锐地指出不管是现实中的还是幻梦中的理想国,都难以在当时的社会中寻得一席之地,流露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挣扎与悲哀,以及他对当时社会深沉、强烈的控诉。以大观园为界,大观园里面是清白美好的世界,而它的外面是污浊恶臭的世界,作者建造这个虚幻的乌托邦世界的目的就在于他想要逃避真实的世界。《红楼梦》中的虚构成分自然不能与作家“半世之亲见亲闻”相提并论,但这并不与其“实录其事”的主张相矛盾,因为它们都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真实。被认为是最了解曹雪芹创作理念的脂砚斋就曾提出《红楼梦》中的虚幻描写是幻中不幻,是情里生情,且情即是幻,幻即是情。这些都足以说明曹雪芹在作品中的虚构并不是毫无根基、虚无缥缈的,而是在另一种程度上展现了现实,是真实性情即脂砚斋所谓“情”的虚化。护花主人(王希廉)评《红楼梦》时说:“《石头记》一书,全部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不是‘真,‘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在《红楼梦》中,真实与虚构是交织在一起的,虚实结合写作手法的运用不仅使《红楼梦》更加丰满,还使其具有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饱含意境的灵妙境界。这种手法的运用既有作者避祸的目的存在,同时又作为一种虚实同构、相互补充的高超的叙事策略衬托着这部小说。这样的一实一虚正如太虚幻境(太虚玄境)中的那副对联所言:“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
三、“假作真时真亦假”
文学的真实是指文学作品无论采取何种虚幻的形式,它所揭示的现实意义、表现内容以及逻辑的发展总是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真实的。没有完全真实的文学,也没有完全虚构的文学,应该把文学看作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产物,它是现实中既定事物与想象事物之间相互纠缠、彼此渗透的结果。真可假,假亦可真,或许虚构是另一种真实,而真实只是另一种虚构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