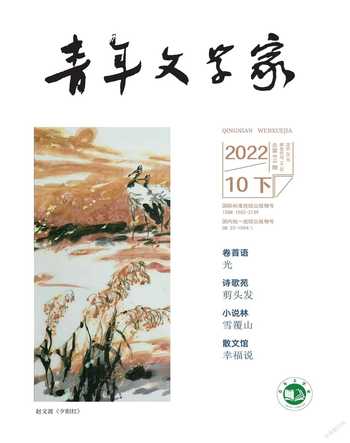沉甸甸的斧子
綦德周

手里握着这把斧子,手腕子坠得有点儿酸痛。斧子的脸面布满了皱纹和疤痕,细端详显得有些苍老,弯曲的身板折射着出过大力的影子,不再像年轻时那样魁梧挺拔,不过,让人觉得它仍是一条有血性的汉子。
斧子,说起来应该是木匠手下的爱将,可是,不承想自己拥有过人本事,倒惹得许多寻常百姓喜欢。于是,老百姓家的工具箱里就添了斧子一族。但无论身在何处,斧子都张扬着自己的个性,守正。它在木匠手里劈个橛、去个疤、削个平、钉个卯榫等都是俯首尽力;可如果让农家人把自己握在手里,仅仅是劈个柴、除个树枝、在墙壁上钉个钉子、砸个炭块什么的自是心里多少有点儿不平衡,甚至憋屈,好像主人没把它当个牌出似的。
憋屈,凭什么?斧子自信地抬起头来,这个时候的它显得很洒脱。你知道民间的顺口溜吗?“大木匠的斧,小木匠的锯”“快锯不如钝斧”,这是说斧子在木匠手里的地位。说起木匠,也是有级别的。民间给木匠划分级别权当评职称,行当里很有道道。他们把木匠分为大木匠、小木匠和圆木匠。在这里,不是说大木匠就技术好,小木匠技艺就逊色。大小木匠的分类依据仅仅是从事木工活儿的类别。把那些盖房子的粗木工叫大木匠,把那些做家具的细木工则叫小木匠,那些箍桶做盆的叫圆木匠。木匠总是与斧子有缘分不开,无论哪种木匠,都把斧子视为掌上明珠。缘分归缘分,也不是哪一个木匠就能把斧子玩得应手自如,这倒不是因为斧子沉甸甸的,而是由于那句“千日锛,百日斧,学大锯一早晨”的木工谣很有道理。也就是说,要使好斧子,不是一日之功,你得好好磨炼些时日啊!其实,生活中每个行当都有自己的密码和基因,我们要驾驭它,不费一番心血,不洒几滴汗水是不行的。
腊月日晌,北风伴雪。农家一只胖乎乎的狸花猫趴在地上瞅着刚剁完的那些冰带鱼,散发着腥味的斧子,不知它是对锈迹斑斑的斧子感兴趣还是源于腥味的诱惑?此时的斧子,无奈地摇着头,何曾想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自己可是荣耀过、高光过的。
斧子的出世是轰轰烈烈的。一块铁坯经过敲打、煅烧、锻造、高温、淬火、锉磨等工序之后,才有了自己的雏形,那时,只能叫它小名—斧头。它被主人收留之后,再为它饰上一硬木手柄,才成“立世大器”,也就有了正式名分—斧子了。
露着锋芒的斧刃,透着光亮。斧子被一只只粗糙的大手拎起,咔嚓咔嚓,一根根木头表面的枝杈去了,疤痕光了,顺溜了。新盖的房子正在上梁搭檩,由于叉木不周正,斜排的六根檩条儿就是不在一个水平上。大木匠看出了道道儿,二话不说,握起那把大斧子,照着要害“咔咔”砍了几下,转眼间,好了。那辆小推车年龄太大了,也是力气透支了,如今,主人推着它“吱吱嘎嘎”直唉哼。木匠如同老中医,但不全是望闻问切,只一听就知道小推车是什么病。于是,木匠拿起那把锋利的大斧头,随便找了一块小槐木板,一砍一劈一剁,便成了一个剪刀尖似的精致小榭子,拿着它来到小推车的大把手外侧照着卯榫处轻轻钉了进去。不用说,小推车康复了。沉甸甸的斧子不光斧刃锋利,它的四方屁股也很得力。细木匠正在给邻居家做结婚的大衣橱,将形态不一的木料摆了一地,让主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细木匠拿起毫无章法地躺在地上的几根楸木撑子,一根放在地上左脚踩着,一根左手扶着,右手攥着那把斧子,让斧子坚硬的屁股对准开好的卯榫组合“啪啪”墩砸了几下,刹那间,大衣橱的框架立现在眼前。也是一把斧子,看起来有些年份,浑身锈迹斑斑,它的木柄被勤劳的手不知握过多少次,但看木柄的颜色足以知道主人用手掌的多少油汗滋养过它。纤细娇嫩的手提着它似乎有点儿吃力,但没办法,还是踩着麦秸草墩,把手里的长榆木橛子一下一下地钉进了西屋土坯垒的墙上。这根钉进去的榆木橛子就是晾晒地瓜干儿的最佳之处,随后,风吹屋檐,串串渐渐晾干的地瓜干儿在休闲摇曳着……
斧子是有灵性的,也有自己的规矩,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动的。俗语说:“木匠的斧子瓦匠的刀,单身汉的行李大姑娘的腰。”也就是说,木匠的斧子不是轻易去碰的。个中原因,一是危险,弄不好伤着自己;二是斧子一般不能外借;三是拿起斧子有没有施展的本领和手艺。千万不要拿得起放不下,弄巧成拙。那一年,生产队里的耙和犁具坏了,有个小伙子说能修好。于是,他带着斧头和几个凿刀来修,结果,捣鼓了好几个小时,也没修好。小队长说他是“猪鼻子插大葱”,惹得围观的几个老人笑声不歇。
为温饱忙碌的那个年代,村里谁家出了个木匠那可是一件幸事。除了温饱无忧,家里人气也旺。木匠是凭手艺吃饭的,既可为四邻八舍的人家盖房、做家具等,又可以在村里干些木工活儿挣工分,吃香得很。尤其是对木匠家的男孩儿,从小就有人断言,人家谁谁谁找个媳妇不愁了,真摊了个木匠爹有福气。当然,这些话是不可全信的。还有不可全信的话就是“木匠的孩儿会砍寨(取音,橛的意思)”,砍寨,就是用斧子砍出个合适的橛子。我父亲就是一名老木匠,当年,他也有意思让我学这行手艺,偏偏我没有这个天赋。放学回家走到外门,一听屋里面有割锯刨木的声音,我就把书包扔进过道,一溜烟儿出去玩了。后来,父亲看我对木匠活儿没兴趣,干脆就不再勉强我了。我知道,这是父亲对我背叛他的手艺给予了宽恕,心里顿觉暖呼呼的。为此事,我终生不会忘记。假如当时我学了木匠,现在会是个啥样子?结果想象不到。如今,我家里也有把斧子,但对于它的使用我还是很生疏的,几乎成了家中工具箱里的摆设。
一把斧子不知施展了怎样的法力让人们挖空心思地去记忆它,理解它,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上初中时,我就在教科书中读到有关斧子的记载,“人有窃斧也,疑其邻之子”。这是怀疑邻居儿子偷自己斧子的古文。再后来,学了些关于斧子的成语:班门弄斧、鬼斧神工、大刀阔斧、刀锯斧钺等。还不止于此,那些有“斧”字的歇后语也是朗朗上口:“斧砍三江水—不断流”“鲁班的斧子—准得很”……再有,“斧大好砍树,针小能穿布”。读着这些,你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一些感悟和联系:大刀阔斧的人,让你敬佩;班门弄斧的人,让你讨厌;鬼斧神工的艺术品,令你倾慕。“斧砍三江水—不断流”“斧大好砍树,针小能穿布”,让你对抽象的哲学原理的理解有了莫大的帮助。沉甸甸的一把斧子,把匠人、文人和常人玩于股掌之间,你不能说它没有魅力,不能说它没有智慧。
走过火红的年代,经历了风花雪月,斧子也渐渐失去了华丽的青春。侍奉主人,久经沙场,这把斧子的锋刃也是伤痕累累。好在主人早就给它找好了“保健师”—在南屋墙角躺着的磨刀石。来吧!斧子毫不懼怕,先是在印有“福”字的旧铁瓷盆里用水洗了个澡,然后,干净利落地躺在了磨刀石上。“唰唰唰”,几十个来回的压磨,斧子的锋刃又焕发出了光的青春,但,锋刃明显比以前窄小了,锋利程度也逊色了不少,体重也在下降。说起来,这次打磨虽然让它锋利了起来,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但实际是折损了它的生命长度。主人这次左手握着它,右手中指轻轻擦去斧子锋刃上的水珠,这淡水珠其实是斧子的泪水,那浑水珠是斧子的心脏滴的血。这时,忽然看到它主人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也湿润了。
沉甸甸的斧子让主人想起了自己肩上曾经沉甸甸的生活重担。瞬间,他明白了,一切美好的生活都是需要付出沉甸甸的汗水和心血才能换来。任何事物有因才有果!有果必有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