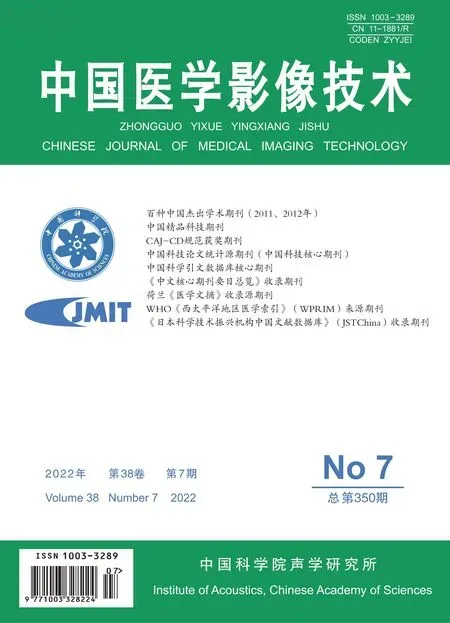心脏MRI观察法布里病累及心脏研究进展
徐杨飞,杨 凯,赵世华*
(1.池州市人民医院医学影像科,安徽 池州 247100;2.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磁共振影像科,北京 100037)
法布里(Fabry)病即Anderson-Fabry病(Anderson-Fabry disease, AFD),为临床罕见X染色体连锁隐性遗传性溶酶体贮积病,与染色体Xq22 a-糖苷酶A(a-Gal A)基因突变导致细胞溶酶体中a-Gal A功能部分或全部缺失有关,最终造成a-Gal A代谢底物三己糖酰基鞘脂醇(globotriaosylceramide, Gb3)正常降解途径受阻并贮积于全身多种组织细胞的溶酶体中而引发器官功能障碍;AFD累及心脏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2]。本文对近年心脏MRI(cardiac MRI, CMRI)所见AFD表现及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AFD概述
全世界范围内AFD患病率约1/100 000,导致男性患者寿命较预期减少15~20年,女性患者减少6~10年[3]。AFD临床分型包括经典型和非经典型,前者临床症状最为严重,主要发生于男性,患者几无功能性a-Gal A酶活性,临床症状出现较早,多始于儿童期或青春期,可累及全身多系统,如合并外周神经痛、皮肤血管角化瘤、肾功能不全和眼部病变等;后者又称迟发型、晚发型,主要发生于女性,患者体内a-Gal A残留一定活性,临床症状常出现较晚且不典型,又可分为心脏亚型和肾脏亚型,单独累及心脏或肾脏可为其唯一表现[4]。约75% AFD累及心脏,40%的男性和28%的女性AFD患者仅见心脏受累[2]。AFD累及心脏时,蓄积的Gb3通过释放促炎性细胞因子、促生长因子和诱导氧化应激引起心肌细胞外基质重构、左心室肥厚(left ventricular hypertrophy, LVH)、血管功能障碍及间质纤维化[5],常表现为心肌肥厚、左心房增大、传导阻滞、快速性心律失常、微循环心绞痛及心脏瓣膜病变等,严重时可出现心力衰竭、心肌梗死及心源性猝死[2],且AFD累及心脏是导致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故早期准确诊断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2 CMRI观察AFD累及心脏
凭借优越的空间分辨率及软组织分辨率、大视野和多层面成像等优势,CMRI现已成为评估心脏结构与功能的金标准。钆对比剂延迟强化(late gadolinium enhancement, LGE)成像可用于定性及定量评估心肌纤维化等异常病理学改变,对于诊断AFD累及心脏、判断预后及危险分层等具有重要意义;利用新技术如T1/T2 mapping、特征追踪(feature tracking, FT)技术等可进一步评估心肌微观组织特征及早期心脏功能改变,有助于诊断AFD累及心脏及判断预后。
2.1 心脏电影 心脏电影图像中,AFD多表现为对称性LVH(或称为同心圆样肥厚);但越来越多研究[6-7]发现,AFD还可表现为不对称性及局限性LVH。DEVA等[6]根据有无LVH及LVH累及部位将AFD分为无肥厚(43.6%)、同心圆样肥厚(43.6%)、室间隔非对称性肥厚(7.8%)及心尖部肥厚(5.0%)。另外,不同性别可有不同LVH表现,如NORDIN等[8]发现不同性别AFD患者LVH患病率均与年龄呈正相关,但男性AFD患者更易出现LVH(男性:66%,女性:27%),且出现年龄较早(男性:40~49岁,女性:60~69岁)、病情更为严重,男性AFD患者左心室心肌质量指数(left ventricular mass index, LVMI)甚至高达健康人的2.6倍,女性则为健康人的1.7倍,男性最大室壁厚度为30 mm,女性最大室壁厚度为26 mm。AFD患者易出现左心室质量增加,尤以左心室乳头肌质量增加更为明显。KOZOR等[9-10]发现,对于48%患者可通过LVMI和LGE成像明确诊断AFD累及心脏,测量乳头肌质量有助于鉴别AFD累及心脏、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 HCM)、心脏淀粉样变、高血压或主动脉狭窄所致LVH。此外,LVH对于预测AFD患者预后也有重要价值,LVMI升高者室性心律失常发生率更高[6],故LVH是预测AFD患者发生心脏不良事件的重要因子。CMRI可准确、重复评估AFD患者是否有心脏受累,并评估疗效及预后[11]。
2.2 LGE 已有大量研究[6-7]显示,AFD累及心脏患者典型LGE位置为左心室基底段下侧壁肌壁间,具体原因尚不清楚,可能与Gb3沉积、心肌应力增加、血管分布、心肌相对缺氧环境、炎症浸润、心肌重构及心肌肥厚等复合因素有关[5-6,12]。AFD患者心脏其他部位也可出现LGE,如肌壁间、心内膜下或心外膜下,范围或局限或广泛[5-6],且即使未出现LVH,也可出现LGE[8]。另外,不同性别之间LGE也可表现不一,男性AFD患者心脏LGE出现较早但晚于LVH,女性患者则无论是否出现LVH均可见LGE[8]。LGE是AFD患者发生不良心脏事件的重要预测因子[11,13],出现LGE可能提示酶替代疗法治疗效果不佳[14]。
2.3 T1 mapping/细胞外容积分数(extracellular volume, ECV) 心肌T1 mapping极具潜力的定量技术,可量化图像中每个像素的T1弛豫时间,特别是可通过非对比剂增强检查获得Native T1值;Native T1值降低主要见于铁沉积、AFD及脂肪瘤化生,其升高则见于心肌纤维化和水肿[15]。心肌ECV可反映细胞外间质(包括血管和间质)在整个心肌中的占比,多数心血管疾病引发水肿、重塑或纤维化致间质成分增加,将造成ECV增高[15]。
AFD患者Gb3堆积于细胞内,使心肌T1弛豫时间缩短,即Native T1值减低,此为AFD的特征性参数改变[8,16-19]。DEBORDE等[17]的观察结果显示,AFD组室间隔及左心室整体Native T1值均低于HCM组及健康对照组;以室间隔Native T1值940 ms区分AFD与HCM,其敏感度为88%、特异度为92%,区分AFD与健康人的敏感度为88%、特异度为86%。KARUR等[18]发现AFD组室间隔、整体左心室Native T1值和右心室局部T1值均显著低于HCM组;以室间隔Native T1值1 220 ms为阈值,区分AFD与HCM的敏感度为97%、特异度为93%。AFD的 Native T1值可随病理发展而分为4个阶段,依次为Native T1值正常期、低Native T1值期、LVH伴低Native T1值期及Native T1值假性正常值期[8];在同时存在Gb3沉积和纤维化的区域,Native T1值可能正常。Native T1值不仅可用于监测疾病发生、发展,还可早期诊断AFD累及心脏[19]。
不同年龄、不同性别AFD患者心脏Native T1值不完全相同。儿童期Native T1值无明显降低,但呈下降趋势,处于进行性亚临床积累过程。男性Native T1值随年龄增长而下降的幅度更大,表明其Gb3储存速度更快;女性患者Native T1值亦下降,于出现LVH后Native T1值趋于稳定,而男性患者Native T1值随LVH程度加重而升高,但部分可出现Native T1值假性正常[8]。此外,出现LGE前,AFD患者的ECV与正常人无显著差异,主要因Gb3贮积于细胞内,细胞外间质增加不明显,故ECV无明显增高;但出现LGE代表发生明显间质纤维化,导致ECV增高[8]。此外,AFD还可累及右心室[18,20],引发右心室壁肥厚、LGE及Native T1值降低。
2.4 T2 mapping 以T2W为基础,可定量精确测量横向弛豫时间,显示水肿效果更佳、诊断准确率更高[21]。心肌T2值增高的主要病理基础为水肿或炎症,而T2值降低主要与铁的超顺磁性有关[22]。越来越多的研究[12]发现,炎症参与AFD发生、发展,AFD患者左心室基底段下侧壁的T2值明显增高,提示部分AFD心脏病变为慢性炎性心肌病。
2.5 CMRI-FT 为基于常规MR电影序列的新兴心肌应变技术,操作简单,图像空间分辨率高,且无须对比剂,广泛用于测量心肌应变;所测应变参数与超声斑点追踪技术和MR Tagging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好[23-25]。
研究[26]发现,AFD累及心脏伴LVH患者心肌应变异常,表现为整体纵向应变(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 GLS)和整体周向应变(global circumferential strain, GCS)均受损;不合并LVH者心肌应变状态不一,无LVH的AFD患者GLS或GCS可与健康人无显著差异[27-28],也可出现GLS受损[29-30]。ZHAO等[26]根据心力衰竭程度及CMRI表现将AFD患者分为3组,与健康人相比,无LVH及LGE者GCS无显著差异而GLS存在差异,LVH患者(无论存在LGE与否)、合并LGE、左心室壁变薄及心力衰竭患者的GLS、GCS与健康人均存在差异,提示GLS可敏感提示早期心肌收缩异常。CMRI-FT有助于早期诊断AFD累及心脏,未来可能成为影像学随访AFD的方法之一。
2.6 心肌灌注 心肌灌注也已用于AFD研究。KNOTT等[20]评估AFD患者心肌血流,发现心肌灌注受损甚至发生于LVH之前,AFD灌注损害以心内膜下更为明显;左心室心内膜下为纵向纤维,心内膜下灌注异常可部分解释疾病早期GLS改变[26]。
3 小结与展望
AFD累及心脏的CMRI表现具有一定特征性,LGE成像可反映其宏观变化,T1/T2 mapping及FT技术能够反映其微观或早期病变。随着技术的发展,CMRI可能成为模拟病理的替代工具,即“病理化成像”[31],在诊断AFD累及心脏、危险分层、评估治疗、判断预后,以及探索疾病病理特点、发病机制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目前AFD累及心脏研究大多针对左心室,对右心室及左、右心房的研究甚少,与右心室及双房壁较薄、部分形态不规则有关,导致相关测量结果的可重复性较差,而后者可能成为未来的研究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