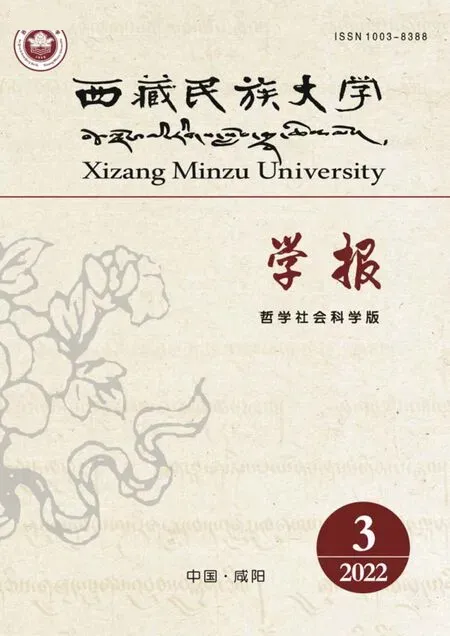现实主义地呈现,理想主义之照耀
——评周伟团的长篇小说《东山顶上》
徐 琴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2021年7月,周伟团的长篇小说《东山顶上》出版,这是作者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献礼之作。作品围绕农奴出身的格桑梅朵、格桑德吉两姐妹的成长经历以及她们与解放军战士怡高远和贵族少爷巴鲁云丹的爱恨情仇,通过中国共产党在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校——西藏民族大学60余年的办学历程,刻画了三代人的学习、工作与成长之路,展现了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到新时代全面脱贫的伟大历程,并呈现出藏汉一家亲、秦藏山海情,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崇高情怀。作品因对西藏革命历史书写的开拓,立意的开阔和从中传达的高远情怀,以及在艺术手法上的多元探求,实现了对西藏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新突破。
一、独具匠心的革命历史书写
《东山顶上》属于革命历史题材的写作。何建明在《让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鲜活起来》一文中写道:“革命历史题材创作重现惊心动魄的风云岁月,毫无疑问是当代民族精神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一次次纪念波澜壮阔的历史,一批批文学创作者‘前仆后继’地辛勤创作,写出了一部部革命历史题材的精品力作。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岁月的流逝,那些拥有精彩故事的历史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参与到历史‘故事’的当事人,基本上很难直接与我们对话了。在这种情形下,如何写好革命历史,宣扬好革命历史,成为我们文学工作当前与今后的一大艰巨任务。”[1]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代驻藏部队官兵和援藏干部同西藏各族群众一道,在和平解放西藏、建设西藏的伟大历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孕育了优秀的精神资源,如何在新时代把弘扬优秀的精神传统与坚持不懈的美学追求、艺术创新结合起来,创作出有时代内涵和审美价值的作品是对新时代创作者的重大考验。
西藏当代革命历史题材的书写,以20世纪80年代降边嘉措和益西单增的创作最具代表性。他们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创作了《格桑梅朵》《迷茫的大地》《幸存的人》等作品,书写西藏和平解放的历程和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翻身做主人的转变,以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昭示了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西藏和平解放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点,从此西藏地方的历史画卷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西藏还进行了民主改革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脱贫攻坚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绩。在降边嘉措、益西单增之后,虽有创作者从不同角度展现西藏的现代化之路,但涉及近70年西藏社会发展进程、展现社会主义新西藏征程之路的文学作品,周伟团的《东山顶上》还是第一部,从这一点来看,周伟团对历史的书写和现实的关注是有大抱负的,也是有担当意识的。
周伟团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将关注的视点落到历史的一些重大节点上,力求呈现西藏的革命历程和社会发展的脉络。作品以西藏和平解放为背景,写了备受欺压的农奴格桑梅朵两姐妹为了摆脱被农奴主残害的命运,踏上了前往当雄机场寻找解放军的道路。在解放军的引领和帮助下,她们积极寻求进步。在修建机场任务完成后,两姐妹进入西藏干部学校进行培训。1957年7月,中央批准西藏在内地筹办西藏公学,格桑梅朵姐妹和其他三千多名农牧民被送往内地学习。在学校,她们不仅学得了专业知识,而且思想觉悟也得到了很大提高。1959年拉萨武装叛乱发生,一批优秀的学员回到西藏参加平叛斗争和民主改革,格桑梅朵回到家乡山南,担任工作队队长,组织农民协会,积极发挥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在平叛和民主改革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格桑梅朵和怡高远也收获了心心相印的爱情,结成幸福的家庭。格桑梅朵在长期的革命历程中不断成长,成为优秀的藏族女干部,担任自治区副主席,怡高远担任副厅长。他们的儿子怡西平再次到西藏民族大学上学,毕业分配到山南工作,在母亲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历练自己,孙子怡清风大学毕业后毫不犹豫地回到西藏,在山南琼结县担任驻村扶贫点党支部第一书记,为村子的脱贫做了不俗的成绩。作品将一家三代人的成长经历融入到西藏的发展历程之中,以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呈现出社会主义新西藏曲折而又坚定的发展路径,并将个体的发展与民族的解放、繁荣结合起来,指出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发展符合西藏各族群众对于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作者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将西藏的解放和发展放在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去展现,体现出浓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结构上,《东山顶上》颇具匠心。作品以格桑梅朵姐妹的成长之路和西藏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脉络,并巧妙地将西藏民族大学的发展与之相贯穿,绘就了一幅藏汉人民共建新西藏的恢宏图画。作者在高校工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校径人踪》是西藏当代文学史上最早的高校题材长篇小说。《东山顶上》这部作品继续延续了写自己熟悉题材的优势,巧妙地将西藏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与西藏现代化进程相联系,展现藏族青年在党的关心和教育下思想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的逐渐提高,指出教育改造在西藏解放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作用,具有开创性意义。西藏民族大学是西藏和平解放后党中央在祖国内地为西藏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学校,其前身是1958年创建的西藏公学,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学院,2015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西藏民族大学。西藏民族大学在西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作者详尽地展现了西藏民族大学艰难的创建过程,通过以怡高远、格桑梅朵为代表的一家三代人的经历展现了西藏民族大学不同阶段的发展及其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重要作用。作者熟悉校史,资料相当翔实,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将资料堆积在书中,而是渗透在西藏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去展现,独辟蹊径地指出在西藏人民翻身做主人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作用,并以个体人物的成长经历展现出西藏高等教育在西藏现代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在西藏民族大学,不仅农奴出身的学员如格桑梅朵、巴桑次仁,农奴主出身的贵族子弟如巴鲁云丹、桑果嘉美,以及出身僧侣阶层的伦珠,都在党的教育下思想觉悟和专技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时代的大熔炉中得到了锻炼,成为建设西藏的中坚力量。作者的思路宏阔,构思巧妙,因为西藏民族大学是在陕西建校,所以借此又呈现出陕西和西藏,黄土塬与青藏高原之间的历史勾连和现实情愫,描绘出汉藏一家亲、秦藏山海情,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美好篇章。
二、历史中的人物建构与精神传承
如何使文字中的历史显得饱满有温度,很大程度上在于能否写好历史进程中的人物。这就要求革命历史叙事不能仅仅满足于历史事件的呈现,还需在日常的生活图景上建构鲜活的人物及其灵魂,才可能实现革命历史叙事的审美图景。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提到过:“历史的编纂只写社会的历史,而不写人的历史。”[2](P36)历史学家往往会从宏观的角度关注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但作为文学家,他的目的却是展现历史进程中的人,通过史学家们所忽视的细节与真实,展示历史材料中所缺失的有血有肉的灵魂的个体。谢有顺亦道:“小说家笔下的真实,可以为历史补上许多细节和肌理。如果没有这些血肉,所谓的历史,可能就只剩下干巴巴的结论,只剩下时间、地点、事情,以及那些没有内心生活的人物。历史是人事,小说却是人生;只有人事没有人生的历史,就太单调了。”[3]如何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文学性创新,如何创作出更加贴近人民的革命历史作品,周伟团进行了多方面的开掘。
要做到忠于历史进程,难度并不大,但要建构丰富饱满的灵魂,并非易事。作者以脉络梳理的方式,清晰呈现了西藏70年的发展历程,依据自己对历史的想象搭建时代的脉络,塑造了一系列鲜活可感的人物,涉及到西藏社会的各行各业,“众多的人物,涉及到西藏革命和教育的各个层面,既有贵族,也有农牧奴,既有僧官,也有俗人,既有革命军人,也有叛匪游徒,既有迷途知返者,也有丧心病狂者,既有藏二代,也有回归藏胞,林林种种,编织起一幅西藏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作者的笔触从都市到乡村,从藏地到三秦大地,在广阔的时空中塑造了格桑梅朵、格桑德吉、怡高远、巴鲁云丹、李玉玲、巴桑次仁、洛丹、米玛曲吉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着力塑造的人物是怡高远和格桑梅朵,他们是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是作品中性格最为鲜明的人物。怡高远是进军西藏的解放军战士,积极参与西藏的社会进程,他有着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一生都献给了西藏人民,代表了西藏老一代革命工作者。格桑梅朵出身于农奴家庭,从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备受欺压,在解放军的引领下摆脱了苦难的命运,在党的教育下开始成长,成为西藏的高级干部,为西藏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作者将两个人的形象放在西藏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去展现,并在革命叙事中融入爱情叙事,于时代的巨大变革中写出了一种相知相惜、心心相印的深沉的情感,从而多角度地展现了人物的性格。在《东山顶上》周伟团不仅塑造了格桑梅朵、怡高远这样高洁的人物形象,还通过对人性幽深之境的描写,呈现出了丰富多元的人物。如巴鲁云丹这个人物形象,他出身贵族家庭,最初是个欺压农奴、荒淫放荡的公子哥,整天喝酒赌博,不务正业,在解放军创办的干部学校里迫于工作队的威力不敢为非作歹,后来在西藏公学学习,思想上开始有了很大的触动,积极追求进步,不断提高觉悟,最后还收获了爱情,作品在动态的变化中刻画了巴鲁云丹的性格。此外,洛丹这个人物形象的刻画也很成功,洛丹原来是有着悲惨身世的农奴,他憨厚朴实,勇敢坚毅,在西藏解放过程中积极追求进步,在民主改革后,当了八廓街街道管委会副主任。但当他获得了一定权力后,洛丹被物欲和色欲蒙蔽了心智,沦为行尸走肉,在“文化大革命”中为非作歹,走上歧途。但最后在批评和教育下,幡然醒悟,并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流下了痛彻心扉的泪水。作品于时代的变化中展现人物的性格,十分真实可信。宏大历史的书写需承载日常的建构,日常的建构积淀起了历史的书写。因对历史进程中个体人物的细致刻画,使得《东山顶上》在对历史的钩沉中呈现出鲜活的人物群像,在质朴真实的历史书写中始终包裹着作者对人的心灵的关注,呈现出高远厚重之美。
《东山顶上》十分可贵的地方是,通过人物的命运变迁展现历史的进程,并在对历史进程的描绘中让一种深厚的精神流淌在字里行间,不仅呈现出宽阔的历史视野,而且对当下的精神建构具有重要的作用。谢有顺曾说“中国人普遍有两个情结,一是土地情结,一是历史情结。”[3]虽然现在很少有作家像巴尔扎克那样将自己当成历史学家,将小说的历史承载看得格外重要,但中国作家往往十分注重文学作品背后的历史容量,这里面有着深远而厚重的文学传统,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有关,也与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思想文化资源的历史重构有着很大的关系。周伟团多年在西藏民族大学工作,并多次去西藏实地调研考察,自然对西藏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状况有着深刻探查,他的创作高扬着一种理想主义精神,从西藏的和平解放写到脱贫攻坚,既有大的时代变化,又有温馨感人的细节描绘,既有革命历史书写的阔达豪迈,又融入了人物丝丝入扣的心路发展历程,以主旋律的格调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艰难历程,并凝炼出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气质。他以三代人无私奉献西藏经历的描写,再现了老西藏精神的脉络传承,使得作品中始终流淌着一种昂奋而坚韧的情感。
在人类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一代人的经历转瞬即逝,随着他们的老去逝去终将消失在时间之流中,那时,只剩下没有温度的历史记忆。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对于弘扬时代的主旋律,展现民族团结、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核,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雅克·德里达说:“唤起记忆即唤起责任。”[4](P1)《东山顶上》有一种高阔的情怀,这就是对理想的追求和无私奉献精神的颂扬。怡高远、格桑梅朵一家三代人是很多扎根西藏、奉献西藏的人的缩影,在他们的经历中隐藏着历史的细节与真实,由此,历史不再是那抽象的激昂铿锵的过去,它仿佛变得触手可及,让人们对历史有了最真切的感受,更加珍惜当下的来之不易。
三、格物精神与多元艺术表现
小说写作既是对俗世生活的还原,也是对生命和精神的落实。“在写作中无法建构起坚不可摧的物质外壳,那作家所写的灵魂,无论再高大,读者也不会相信的。”[5]只有通过物质的写实才能达到精神的真实,这就要求写作者要有对格物的追求。周伟团的《东山顶上》在物质写实方面是很有功力的,对西藏地方风俗、民俗民情、历史典故,包括地貌的描写都是经得起推敲的。如作品对拉萨巴鲁府邸的描写:“巴鲁府高大坚固,主人一家人住在院子中央朝阳的碉楼里。碉楼盖在高高的石台上,分上下两层,一层是佛堂和领主的会客厅与卧室,二层是小姐和少爷的住房。碉楼的后边有两排厢房和几个偏院,一排是管家和贴身仆人住的,一排是客房、厨房和酒窖。偏院主要安顿那些不定期来府上做客的贵族亲戚住宿生活。每个偏院都有门路和主院相通连。碉楼里有铺床的、擦地的、哄孩子的、伺候佛堂的,外边有喂马的、背水的、磨青稞的、做糌粑的、干各种杂役的各等级奴隶。后院里的最北边的简易两层木板房,上边用于管家家人和护院们住宿,下边是领主的牲口圈。”再如对山南庄园房屋的描绘:“巴鲁庄园的主宅是一个传统的藏式庄园建筑。石砌的口字形三层大楼,大平顶上有一个高高的瞭望台,主要用于看家护院的家奴值守和休息。经过溪流上一座宽大的石桥,走进庄园大门进入到院落,宅子大门口是一个一底到顶的照壁,照壁上浮雕着释迦牟尼成佛图案和藏传佛教六字箴言。从左右两侧进入天井,沿着两个不同方向可以进入到一层房屋,另外衔接的两个大木梯旋转通向二楼。楼梯板已经被奴隶的赤脚磨出一个一个明亮的窝窝,彰示着这个庄园超过200年的历史。一楼主要是客堂、贵客和管家们住用。二楼朝阳的西厅是经堂,东厅是主人一家的住房。每个窗口悬挂着巨大的紫色牛毛幕帘,显得整个楼屋肃穆森然。从天井周边向下通有两条小路,直接可以到达溪水边,溪水边建有马棚和仓库。”如果没有对过往民俗、本土建筑进行过细致的考察研究,在细节方面做不到如此的扎实,这样一种脚踏实地的写作精神值得肯定。
此外,作者对景致的描写是充满地域特色并带有情感化的有意味的描写,如在格桑梅朵准备带庄园的农牧民进行民主选举时的景致描写,充满着憧憬和喜悦:“当日,强烈的阳光毫不吝惜地打在树叶、草地和庄稼上。因为周边溪水和渠水流淌,加之夏夜几乎都会下雨,树叶闪着金光,愈发显得油亮茂盛,草地湿漉漉的像绿色的绒毯,青稞正在抽穗,油菜正在结荚,豌豆花开成紫色的小蝴蝶,几只毛驴晃荡着脖子上的铃铛在渠边吃草,布谷鸟在树叶深处跳跃鸣叫,是谁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富庶美丽的地方。这里应该住着神仙一样幸福的人儿。”而对陕西地貌的描写也独具意味,如写怡西平回老家一路上的景致:“10月的咸阳原上,上千亩谷子和苞谷地一眼望不到头,大路边有着一条水渠,沿着水渠是两行白杨树,高高的树干好像拥挤着要钻进天空。树下渠岸上野草丛生、苜蓿连营。”作品对景物的描写是带有情感的有意味的描写,同时因为作品主要在西藏和陕西两地展开,不同地域自然呈现出不同的地域风貌和人文景观,在对三秦大地咸阳原的描写和对西藏的描写都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作者精心锤炼,使得小说语言丰富多彩,生动形象,富有浓郁的民俗风味,呈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如写怡西平回到老家怡魏村时,乡邻们说:“这娃娃不错,虽然说着普通话,还像咱怡魏村后人一样懂礼数,看来高远在外边教子有方呢!”“娃娃”“后人”“礼数”这些词语是带有秦地色彩的语言,有着鲜明的地域民间风味。而在藏族人的语言中经常会出现很多谚语:“从雪山上下来的人最知道太阳的温暖,从黑暗中走过来的人最知道光明的可贵”“马儿走对路,不是马儿聪明,是骑着马的人指引了它”“达赖的太阳照在贵族身上,毛主席的太阳照在我们穷人身上。现在达赖的太阳下山了,毛主席的太阳升起来了”“和尚没有不高古的,酒鬼没有不丧德的”“盐巴水不解渴,漂亮话不顶用”。在语言运用上的细致把握和浓郁的民俗特色使得《东山顶上》有种独特的韵味。
作品在整体意象的营造方面也显现出了独具一格的魅力。广为流传的诗歌《东山顶上》是仓央嘉措的代表诗歌,这首诗歌本来有着丰富而朦胧的意象。作品以《东山顶上》为题,除楔子外,诗歌《东山顶上》以歌唱的形式在作品中共出现四次。最初当格桑梅朵逃出巴鲁庄园,连夜奔逃来到当雄机场,在怡高远的怀抱里清醒过来时,少女的心就被这个年轻的解放军连长俘获。而在怡高远的心中也留下了这个美丽大方、多才多艺的姑娘的倩影。格桑梅朵在《东山顶上》的歌声中表达了对怡高远的深情之爱,“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月亮。年轻姑娘面容,渐渐浮现心上。拉伊呀拉索啊……”。此后,每当两人的情感进一步深厚时,这首音乐的旋律便响起。回环的音乐旋律在文本中流荡,使得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荡漾着诗情画意,也使得一个优雅多义的意象在文本中贯穿始终。
“革命历史和战争小说,是20世纪‘红色话语’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需要清理识别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6]在发展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就应该对既往的革命历史和其中所蕴含的精神资源给予大力书写和弘扬,《东山顶上》是西藏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全面展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70年发展历程的文学作品,既有对历史的追忆,又有对当下的审视和观照,更有对革命英雄精神的传承和弘扬。阎连科认为,现实主义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和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了不同层面的真实,包括:“社会控构真实”“世相经验真实”“生命经验真实”和“灵魂深度真实”[7](P7),虽然在某些方面尚需开掘,但周伟团的创作在历史题材重构、革命精神的弘扬、典型人物的塑造、语言内蕴丰富化、意象的营造等方面,都显现了他的努力和探求,是对西藏革命历史题材书写的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