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小心收藏的喜欢
Seven凉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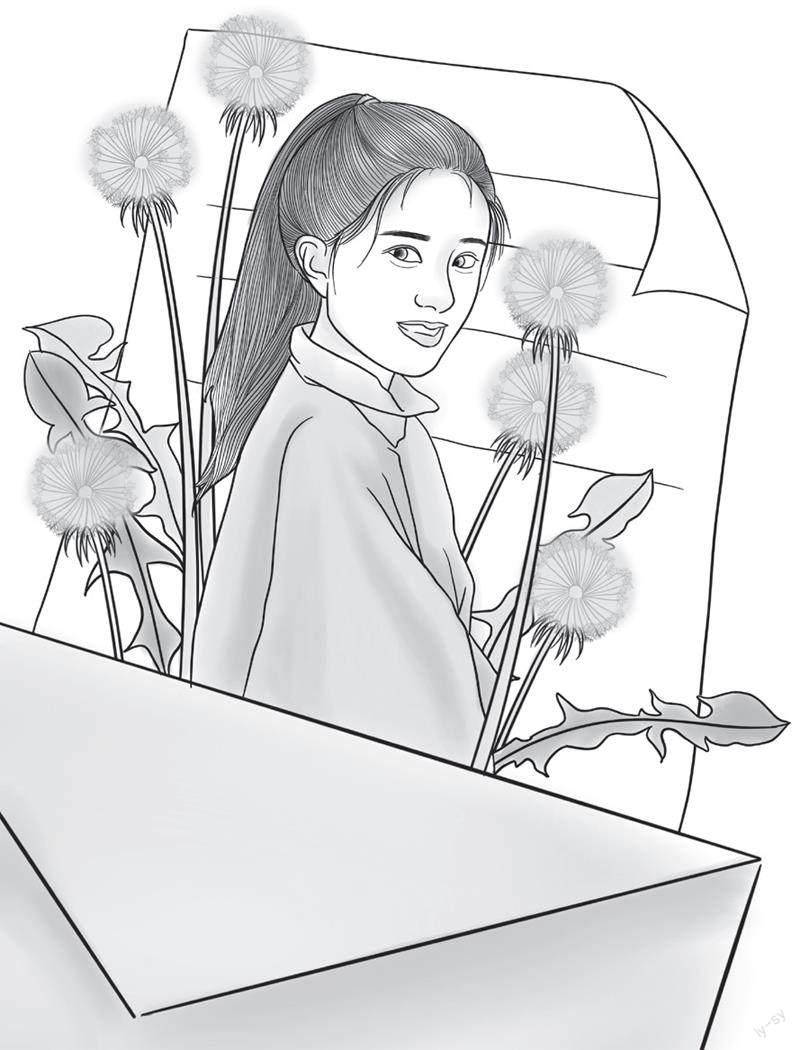
预备铃声响起的时候,我刚吃完早饭,正从食堂往办公室走,经过操场旁的一个垃圾桶时,我看到深绿色的草地上有一抹淡淡的粉色,走近了才发现,那是一封信。阳光明媚温暖,照在粉色的信封上就像少女脸庞上的淡淡红晕,闪耀着青春特有的光芒。信封上面写着:王思钰(收)。写信的人大概太想把字写好,所以小心翼翼的笔触下,带着几处颤抖。
这封信应该刚被扔掉不久,并没有沾上清晨的露水,依旧整洁干净,我将它从地上捡起来,夹在教案里继续往办公室走去。
中午1点30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准备下午公开课所需要的东西,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女生。她穿着白色球鞋、蓝色牛仔裤,牛仔外套里是一件白色的T恤衫;马尾辫扎得高高的,随着她的动作在脑袋后面轻轻摇摆;三三两两扎不住的碎发垂到额前,长长的睫毛在阳光的照射下,投下温柔的剪影。
“同学,有什么事吗?”我向女生招招手,示意她进来。看到我主动打招呼,她像是终于下定决心,一步步挪到我的面前。
“老师,我听说……”她头垂得很低,自始至终都不敢看我一眼。她的马尾垂到胸前,露出带着细微绒毛的耳朵,红透了,像是要滴出血来。我从旁边拉来一张凳子,示意她坐下,这时我才看到她的表情,她的眼睛湿漉漉的,透着慌乱,嘴唇被牙齿咬得发白,嘴里的话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说出口。
“你叫王思钰?”听到我的问题,她整个人都僵硬了,耳朵上的红色蔓延到了整张脸,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我上午路过操场的时候,捡到了一封你的信,本来想等下午老师们都上班了问问你是哪个班的。”
“老师,我知道错了。”她截断了我的话,声音里带着浓重的哭腔。
“你没有错啊!别怕,我是想问问你在哪个班,然后悄悄把信还给你。”我轻轻拍着她的背,语气不自觉变得温柔,像是安慰她,更像是安慰遥远的岁月里另一个痛哭的女生。
10年前,我17岁的时候,也是在办公室里,坐在我面前的班主任手里拿着一封信,粉色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就算我不想承认也不行。不一样的是,信封已经被拆开了,写满字的信纸就那样大剌剌地放在桌子上,远远就能看到第一句话写着:我喜欢你。
“我不知道这是谁放在我书里的,我没有早恋。”因为觉得委屈,所以我几乎要哭出来。
“你不知道?不知道人家会写这样的信给你?小小年纪就早恋,马上就要高考了,你还想不想上大学?”班主任越说越气愤,手拍在桌子上发出震耳的声响,那张信纸轻飘飘地被震起,又重重地落下。“通知你的父母明天到学校一趟,只有学校约束不行,还得父母在家里多注意,不然你们这些孩子都会往弯路上走。”
我的泪水不受控制地流,我依旧记得回到班里后,同学们好奇的眼神和轻声的议论,在我的脑子里嗡嗡作响。
第二天放学回家的日子才是最难熬的,父母的指责让我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我被要求在高考结束之前放了学必须立刻回家,周末也不准外出。
然而,自始至终,我17 岁那年收到的唯一一封情书,我只在它从书本里掉到地上的时候见过它一眼,时至今日,信里的内容、写信的人,我全都一无所知。遗憾不是因为不知道,而是未能亲手打开一段关于自己的青春。此刻,我看到眼前这个害怕到颤抖的女孩,满满的都是心疼。
将信递给她的时候,她看着完好如初的信满眼惊讶。我本以为她会立即离开,毕竟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关于情书,我只敢反锁了房门一个人悄悄地打开,像是在进行着一个天大的、不可告人的秘密。
“老师,我能在这里打开吗?”王思钰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噙了泪,似乎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可以的。”我拍了拍她的背,不禁想到曾經年幼而敏感的自己。
信里只有三行字:我偷偷地碰了你一下/不料你像蒲公英一样散开/此后到处都是你的模样。
眼前的女生原本倔强且故作镇定的表情,在读完信的一瞬间土崩瓦解,通红的眼眶暴露了她所有的真心。“如果是一年之后,我想我无论如何都不会那么残忍地当着他的面把信扔向垃圾桶。老师你知道吗?他的眼睛一瞬间就红了,可还是笑着对我说:‘王思钰你一定要幸福啊!”
这封信这么美好,可是在这样一个高三却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王思钰将信重新整齐地叠好,放回信封,然后郑重地递给了我。她的脸上扬起粲然的笑,说:“老师,我可以把这个寄存在你这里,等明年我高考结束再来拿吗?”
我笑笑说:“当然可以。”
那些存在于青春里的喜欢,就像是没有学会如何表达浪漫的树,甚至都不敢落叶,只敢在微风习习里,将内心深处的爱意长成一些不作声的枝丫。
所以,青春里任何选择都不算错,所有举动都值得被原谅,而那些被小心收藏的喜欢都有着无法预期的未来,连带着遗憾都在回忆时透着美好。
(水云间摘自《哲思2.0》2022 年第1 期,陈卓今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