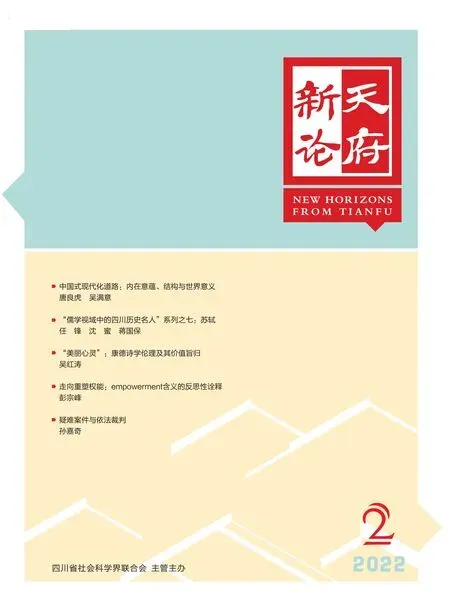论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生成的内在逻辑
杨宇鲲
一、问题的提出
尽管福柯在其著作《词与物》的“前言”部分提到“本书诞生于博尔赫斯(Borges)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引用了‘某部中国百科全书’”,(1)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1页,第11页。但这并不代表福柯或博尔赫斯的写作和思想源头全然来自中国古代的某种观念。事实上,这里的“中国百科全书”在博尔赫斯的思想体系中更像是一种象征符号,是否存在《天朝仁学广览》一书并不重要,(2)董树宝:《福柯的异托邦:绕道“中国”返回西方的“未思”》,《求是学刊》2019年第2期。重要的是福柯借此乌托邦似的符号而开展“揭示西方文化的这种最深层的参差不齐”(3)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第1页,第11页。的工作。中国古代传统的“博物”观念与近现代西方话语体系下的博物学因存在诸多本质上的不同,并不能等量齐观。科学史学家吴国盛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博物’是一个与‘博学’ ‘通识’相近的教育理念,而不是一种知识类别,更不存在‘博物学’这门学科。”(4)吴国盛:《自然史还是博物学?》,《读书》2016年第1期。诚是如此。“博物”作为中国古代不可忽视的重要观念,在思想史演变进程中无疑是重要一环。
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在许多典籍中有相当具象化的体现。晋人张华编著《博物志》,系首部直接以“博物”二字命名的博物类书籍。葛兆光曾提到“儒者‘一物不知则以为耻’的博物传统恰恰是他们超越儒家知识边界的动力”(5)葛兆光:《山海经、职贡图和旅行记中的异域记忆——利玛窦来华前后中国人关于异域的知识资源及其变化》,《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第80页。, “博物”观念与古代知识阶层(尤以儒家为代表)追求博学、崇尚多识的文化传统关联密切,这种传统自有其初承与流变。 “博物”观念始盛于春秋,战国秦汉时期更是一个“博物”知识被大量生产和传播的时代,方技、房中、术数、地理、神仙等多种知识在此间完成了自身谱系的初步构建,《方言》《尔雅》《释名》等经典亦随之涌现。张华《博物志》显然不是天才般的创造或重建,“博物”观念当是古代知识阶层重要的精神底色,正如《博物志》开篇所言:“余视《山海经》及《禹贡》、《尔雅》、《说文》、地志,虽曰悉备,各有所不载者,作略说……博物之士,览而鉴焉。”(6)范宁:《博物志校证》,中华书局,1980年,第7页。
有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缺乏对自然和外物的关照,“儒家对于自然界缺乏主动的关怀与兴趣”。(7)郑灿山:《从万物说起——〈道德经〉的宗教性精神》,《道教学刊》2019年第4期。但这种说法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儒家典籍中众多有关“辨名识物”与“博物君子”的记载,儒者颇具人文色彩的现实主义关切与对自然万物的求索并不冲突,“博物”观念也绝非老庄之学所独有。英国学者胡司德概言道:“作为智慧的化身、圣人的典型,孔子的形象经常与认识自然、教化鸟兽联系在一起。”(8)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76页。儒者多识博学的形象历来较为突出,孔子及儒者“辨名”与“博物”的相关事迹屡见于文献, 《春秋经》止于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左传》:“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哀公十四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878页。刘向《说苑》专有《辨物》一篇,(10)向宗鲁:《说苑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第442-476页。《孔子家语》亦有《辨物》篇,(11)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13年,第192-206页。清人孙星衍辑《孔子集语》,成《博物》篇,(12)郭沂:《孔子集语校注(附补录)》,中华书局,2017年,第419-431页。基本将孔子及诸生“博物多识”的相关记载网罗殆尽,这种“方位+异物”的叙事模式也多为后世沿用。学人常引《庄子·天下》“道术将为天下裂”(13)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第1065页。一句来论证东周各家学术旨趣的殊途,其实这里“裂”的前提,恰恰是庄子认识到上古学术“皆原于一”(14)郭庆藩:《庄子集释·天下》,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第1069页,第1065页。。诸子之学虽各有侧重,但毕竟同根同源,又面临相同的社会现实,故而在认识论层面上往往颇有相通之处,可见“某说为某家独有”的说法过于强调学术之“裂”,极易造成诸子“各说各话”的假象。儒家固然重视现世秩序与道德伦理,但这并不意味着儒家“对于自然界缺乏主动的关怀与兴趣”,若仅从字面意义上认识《论语·阳货》“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15)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5《阳货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1560页。一句,恐有对儒学认识论的主观割裂之嫌。
目前学界对中国古代“博物”观念的探索已有一定的基础,学者们除主要着力梳理古代“博物”观念与知识谱系的生成外(16)彭兆荣:《“词与物”:博物学的知识谱系》,《贵州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徐公持:《汉代文学的知识化特征——以汉赋“博物”取向为中心的考察》,《文学遗产》2014年第1期;郗文倩:《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及其知识分化》,《天津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东南学术》2021年第4期。,还对个别怪异现象和想象中的异物展开名物考证、知识考古和思想阐释(17)胡司德:《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蓝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青木正儿:《中华名物考》,中华书局,2005年;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陈明:《中古医疗与外来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周金泰:《孔子辨名怪兽——试筑一个儒家博物学传统》,《史林》2021年第1期;周金泰:《人参考——本草与中古宗教、政治的互动》,《文史》2019年第1期;王昕:《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以“土中之怪”为线索》,《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于沁可、刘宗迪:《蜮生南越:传统博物学的南方想象》,《文化遗产》2019年第4期。,以及在西学东渐视野下回顾并比对中西方早期“博物”观念的不同意涵(18)江晓原、刘兵主编:《好的归博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吴国盛:《博物学:传统中国的科学》,《学术月刊》2016年第4期;周远方:《中国传统博物学的变迁及其特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1年第5期。。从研究时段来看,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中古时期。这既得益于中古时期数量可观的博物类文献和敦煌文书的接连整理,为探讨该时期的“博物”观念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又得益于余欣、游自勇等学者的悉力探研,为中古时期(或称“写本时代”)“博物”观念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余欣:《中国博物学传统的重建》,《中国图书评论》2013年第10期。但正如前文所述,“博物”观念显然不是汉晋时人的“天才创造”,任何观念的产生都必然经历一个从缘起到演进的过程,而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眼光大多汇聚在“博物”观念臻至成熟的中古时期,而对形成这一思维模式的源头却鲜有论及。有感于此,笔者不揣谫陋,试图在前贤时彦的基础上,聚焦于儒家视野,回溯中国古代“博物”观念生成的思想基础,揭示其背后支撑性的文化要素。
二、“物”与“事”:先秦儒家的认知“客体”
在西方人类学家眼中,中国文化拥有古老且别具一格的事物分类体系。涂尔干说:“这个体系所依托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最为久远的过去;它肯定比中国现存最早的可信的断代文献还要源远流长。”(20)涂尔干、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78页。李宪堂曾撰文论述战国时期知识阶层盛行的类分思维,即“通过对事物进行归类、编排来模拟和再现天道运行的结构与机制,成为这个时代秩序建构的基本模式”,而“‘类比’ ‘类分’与‘类推’本是朴素而极具‘普适性’的认知方法。古老的阴阳八卦思维就是通过将事物分为两类八部并无限比附串联‘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的”(21)李宪堂:《论类分思维与战国精神——兼论五行八卦模式的专制主义本质》,《文史哲》2014年第1期。。事实上,儒家经典中“阴阳”“五行”“八卦”等抽象概念,不仅是“极具‘普适性’的认知方法”,更深层次反映出先秦儒家思维世界中“物”这一具有形上意义的复杂概念怎样被定义和把握的,进一步说,在这种朴素的、万物联动的世界图景里,其核心问题便是捕捉“物”“我”关联之发轫与前提。
《说文》释“物”为:“万物也。牛为大物。天地之数起于牵牛,故从牛,勿声。”段玉裁注:“牛为物之大者,故物从牛。”(2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3页。物即万物这一说法,习见于典籍,如《荀子·正名》:“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23)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6《正名》,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495页。同时,“事”“物”常常对举并列,亦可通用。《易·睽卦·彖传》:“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24)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卷5,潘雨廷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356-357页。《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郑玄释《大学》“致知在格物”曰:“格,来也。物,犹事也。”(25)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66《大学》,吕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6-2237页。朱熹亦言:“格,至也。物,犹事也。”(26)朱熹:《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由是观之,先秦文法中的“事”“物”之间并无清晰界限,后世注家也多循此解法。沿此思路,我们进一步将“博物”观念具体到先秦知识阶层的语境中进行揣摩。以子产为例,鲁昭公元年(前541)晋平公问疾于子产,子产引允格、台骀等上古神人事迹应答,并连用“侨闻之”“侨又闻之”的句式,平公赞其为“博物君子也”(2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346-1350页。。竹添光鸿《左氏会笺》曰:“此所谓儒者之博,非世俗集类书搜野乘之博也。”(28)竹添光鸿:《左氏会笺》(影印本),巴蜀书社,2008年,第1638页。杨伯峻注曰:“博物谓事物知识渊博。”(2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元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350页。可见在先秦儒家话语体系中,“事”“物”基本等义,以致在战国子书的表述中,“事物”一词已成固定搭配,《荀子·君道》:“如是国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应,乱之端也。”(30)王先谦:《荀子集解》卷8《君道》,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288页。综上,我们可以确定儒家认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即带有经验属性的“事”和带有物理属性的“物”在思维世界中都能成为知识来源,两者或略有区分,但在为主体提供知识甚至道德的方面,并无本质不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凡见者之谓物”,(31)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4页。所引文字皆采宽式释文。可谓深中肯綮。
以往学界在处理中国古代“博物”观念中的“他者”问题时,或倾向于人为地划分“现实存在”的“物”和“思想概念”的“事”;或者依据“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做所博之物的“狭义”“广义”之分;(32)所谓“狭义”,指客观存在(或想象中)的“鸟兽草木”与“物妖”一类;“广义”则泛指事件、经验、寓言等。或直接以西哲概念为准,做“唯心”“唯物”之分。不同分法虽各有立场,但都各有不足之处。前两者稍有望文生义之嫌,且忽略了各学派对“物”的定义不尽相同,后者则划分范围过大,以至概括性不够。中国古代的“博物”观念,本就是知识阶层面对外部客观世界纷杂的知识和危险时自我选择的一种认识方式或处理经验,很难以现代标准进行划分,遑论先秦已然出现用法成熟的“事物”一词。因此,强行区分“事”“物”,只会徒增与古代思想家之间的距离。张立文将“物”细分为“各种不同体积、性质、形相、状态的多样性物体的概念”“事”“称谓”“自虚即空”“道”“理”等概念,(33)张立文:《元亨利贞——中国哲学元理之一》,《中州学刊》2020年第1期。其划分依据虽稍显宽泛,但总体思路却与笔者暗合。我们认为,先秦儒家所言的“物”,乃至“百物”“万物”等概念,不应仅被视作“鸟兽草木”,其基本意涵还应包括历史、记忆、 智慧、 感受等 “事” 的要素。其中,历史要素居统摄地位,故博物者常以“通达古今”(34)《汉书》曰:“自孔子后,缀多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恰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见《汉书》卷36《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1972页。之姿态出现。明乎此,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先秦儒家视野下的 “物” “我” 关系, 也就是认知的主体和客体间的关系。
三、“万物皆备于我”:先秦儒家语境中的“物”与“我”
欲探求“物”“我”关系这一命题,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先秦儒家如何认识“我”之概念。换言之,即如何定义认知的主体。这里认知的主体,实质上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横向的社会性主体,亦即身体;二是纵向的历史性主体。关于儒家的身体观,目前学界已取得阶段性共识。杨儒宾在《儒家身体观》中指出:
儒家身体观的特征是四种体的综摄体,它综摄了意识的主体、形气的主体、自然的主体与文化的主体,这四体绵密地编织于身体主体之上。儒家理解的身体主体只要一展现,它即含有意识的、形气的、自然的与文化的向度。(35)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第9页,第44页。
在此基础上,杨先生将“改造威仪观及血气观,使它们由共同体的德目一变而为具有主体的道德意识之德行者”的节点归至孟子及其后学处。(36)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9年,第9页,第44页。赵法生则将儒家身体观成熟化的节点推至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处,(37)见赵法生:《威仪、身体与性命——儒家身心一体的威仪观及其中道超越》,《齐鲁学刊》2018年第2期;赵法生:《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齐鲁学刊》2019年第6期。认为《性自命出》的理论前提是“通天下一气的宇宙观,身心一本,因一本而一体,身与心如阴阳两面,交感互通,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实体”(38)赵法生:《论〈性自命出〉性情化的身体观》,《齐鲁学刊》2019年第6期。。可以看到,先秦儒家身体观所强调的重点虽然在于身外“有物”,但“物”并不是一切意义上的“他者”,它固然有超脱的一面,但人自身和万物毕竟在本质上同根同源,即汉儒所云“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39)陈立:《白虎通疏证》卷7《圣人》,吴则虞点校,中华书局,1994年,第341页。。
在此基础上,理解儒家在历史维度中的自我定位以及为其认识论提供理论依据的历史观就成为关键所在。在先秦思想家的表述中,常见的一种模式是托古言事,不唯儒家,道、墨、法、农诸家言必取上古圣王神人或近世伯主贤臣之事迹以图造势,遂成文献屡见的“吾闻”“吾闻之”“臣闻之”一类句式。此类言论大多出于政治诉求,真伪自然难辨,或者说,它们提供的主要参考价值不在考证上古史迹,而在窥察其言论背后纵向的历史观。《论语》所载孔子言行虽以伦理教化为主,但仍保留了不少能够反映孔子历史观的材料。《论语·雍也》:“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40)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2《雍也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551页。《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41)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6《泰伯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705页。孔子对上古圣王述其事、赞其行,又言:“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42)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7《子罕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746页。可见孔子的历史观虽非线性,后世儒家万古一系的“道统”说也未成形,但孔子有意拉近与上古圣王间的距离,却是不争的事实。钱穆即谓:
孔子博学深思,好古敏求,据所见闻,以会通之于历史演变之全进程。上溯尧、舜,下穷周代。举一反三,推一合十,验之于当前之人事,证之以心理之同然。从变得通,从通知变。此乃孔子所独有的一套历史文化哲学,固非无据而来。(43)钱穆:《论语新解》,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55-56页。
至孟子生活的时代,“以力假仁者霸”的局面已然变成“杀人盈野”“杀人盈城”,又有杨、墨之学为当世显学,孟子必然从历史中汲取辩论资源,提炼成一家之言。《孟子·滕文公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44)焦循:《孟子正义》卷13《滕文公下》,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459-461页。《孟子》虽仍未明确提出“道统”二字,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的历史观可谓振聋发聩,又曰:“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45)焦循:《孟子正义》卷9《公孙丑下》,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309-311页。如此一经《孟子》整合,后世儒家所谓“道统”便“由史入经”,刘家和总结道:“这一点的确定,正是儒家经学源头的确定。”(46)刘家和:《孟子和儒家经传》,《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笔者深以为然。这种儒者与三代圣王一系的历史观经汉儒排定而最终成型,《汉书·艺文志》论儒家曰:“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47)班固: 《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728页。一言以蔽之,先秦儒家的历史观在时间维度上是流动的,一如孔子之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48)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8《子罕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788页。与其强行指责先秦儒家的历史思维进程单一且缺乏对三代以前社会的记载,不似老、庄动辄言及“小国寡民”一类的理想,毋宁说这恰是理性主义在儒家历史观中的具体体现。对此,刘家和曾展开详论,现略摘如下:
所以,如果说历史理性的运行方向是向前(由古而今或化朴为智)的,那么,在老子看来,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正好背道而驰;不然,历史理性自身就必须转向其反面(由今而古或去智归朴),从而使其自身形成矛盾……不过,他的使人“复归于朴”的设想实际上也只不过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幻影而已。类似的思想在《庄子》里还有更充分的展开论述。(49)刘家和:《论历史理性在古代中国的发生》,《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2期。收入刘家和: 《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页。
至此,先秦儒家思想中“物”与“我”之间的关系也就不难理解。如前所述,先秦儒家语境中的“物”即“事物”,其概念可涵盖现实维度和时间维度意义上的“他者”。这里的思维前提当然是老生常谈的“可知论”“历史客观”云云,但要强调的是,先秦儒家在经验世界或知识世界中企图扮演的角色并不执着于发明“物”的内部,类似西哲“本体”的概念,而极力以“仁”“义”“诚”等道德伦理意味突出的概念来调节中和,这在孔、孟笔下体现甚多。无论是“鸟兽草木”还是“唐尧虞舜”,先秦儒家对于未知和过去知识的态度总是崇博尚通,很少表露竭力“一通百通”之态,个中姿态明显,与寻求“道”“一”“原子”“以太”“arche”“being”等概念的哲学旨趣颇为不同。马一浮、熊十力、张岱年、李泽厚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就儒学“本体论”进行阐发。陈来综括众说,在其《仁学本体论》一书中描绘了儒家以“关联”为存在基底的“仁”,“事物与关系共同构成一体共生共存便是仁”,陈来进而强调道:
这种注重他人存在,反对一味以自我优先的精神气质与近代西方哲学大相径庭。萨特以他人为自我的地狱,或视他人为虚无,而不是自己存在的要素,其哲学必然归结为个体自我,不可能建立与他人的积极关系。海德格尔的此在也是个体的自我,与群体力求疏离,摆脱共在的束缚。(50)陈来:《仁学本体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31页。
蒋重跃在解析《大学》中蕴藏着的本体思想时同样指出:
“格物致知”是在“明明德”的范畴内“止于至善”的第一步;而“絜矩之道”则是在“亲民/新民”的范畴里“止于至善”的根本一着。这三者由“止于至善”紧紧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整体,这就是《大学》的体系——一个没有终极存在作为宇宙本体,只以否定性的相互原则为底线道德的政治理想,表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质。(51)蒋重跃:《〈大学〉思想体系的中国特质——基于元典和古代诠释传统的本体论透视》,《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收入蒋重跃: 《道的生成与本体化:论古代中国的本体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09页。
可见在先秦儒家的学术体系中,对个体内在精神修养最大程度的关注以及对个体之外一切事物的共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取“本体”而代之的。
《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赵岐注曰:“物,事也。我,身也。普谓人为成人已往,皆备知天下万物,常有所行矣。”(52)焦循:《孟子正义》卷26《尽心上》,沈文倬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882-883页。朱熹注曰:“大则君臣父子,小则事物细微,其当然之理,无一不具于性分之内也。”(53)朱熹:《孟子集注》卷13《尽心上》,《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第357页。这与《庄子·齐物论》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54)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1961年,第79页。的说法对比鲜明。两者对“物”的态度分别是“备于我”和“与我为一”,前者“万物”与“我”之间明显存在一定空间和距离,后者则将“我”高度抽象化,很大程度上也正贴合道家“历史理性与道德理性正好背道而驰”的历史观。《中庸》即谓“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55)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60《中庸》,吕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13页。,欲“知人”,那么“知天”也就必不可少。由是观之,先秦儒家即便多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6)程树德:《论语集释》卷9《公冶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411页。的大体思路展开话题,但在思想领域游弋的学问必然会有涉及超越性范畴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先秦儒家所持的方法与道、法、名诸家的根本不同便在于是否主动建构一套带有“本体”定义的生成体系,诸如“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57)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2000年,第203页。“虚无无形谓之道”(58)黎翔凤:《管子校注》卷13《心术上》,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第759页。等言。先秦儒家显然没有用某一先验性的“本体”概念统摄整个形上世界的打算,于“从何而来”这一哲学核心问题既不回避也不贸然一头扎进,而是借取旧有的“仁”“礼”“德”“恕”等伦理性观念,赋予其“本体”功能,儒家思想中的世界图景遂成为伦理与思维、客体与主体、现世与“宇宙”的有机统一。我们之所以在文献中屡见先秦儒家好谈“博物”、夸耀“博物君子”的言论,当是其“万物皆备于我”的哲学意识在现世伦理中的具体体现——基于这种哲学意识的指导,博物通识自然成为深入理解“我”,进而理解社会、理解历史与自然的最基本前提。
四、重检先秦儒家的“格物致知”
《大学》一篇自宋代被列入《四书》,后世儒生无不汲汲于斯,或解字疏证,或贯通义理,其中尤以对“格物致知”一条的诠释最为繁杂,据明儒考证,当时就有“七十二家”之多,晚近学者则更是灼见迭出。究其原因,恐怕与宋儒流派门户之见和对“本心”的发挥角度有关。 “今天大多数学者都不再认为《大学》的成书时间是在秦汉时期那么晚”(59)陈来:《〈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东岳论丛》2020年第9期。,今人梳理旧说,结合郭店楚简等出土文献来看,基本赞成《大学》成书于战国初期,先于《孟子》,系曾子或其弟子所作。(60)参见梁涛:《〈大学〉早出新证》,《中国哲学史》2000年第3期;又见刘光胜:《〈大学〉成书问题新探——兼谈朱熹怀疑〈曾子〉十篇真实性的内在思想根源》,《文史哲》2012年第3期。既成书于先秦,那么回到先秦儒家视角审视《大学》与“格物致知”,进而理解彼时“博物”观念的内在思维进路,就成为我们应当直面的一个问题。
《大学》“致知在格物”一句,汉唐注疏思路基本一致。(61)宋代之前,学人似乎也并未对《大学》投入过多精力。陈来说:“在唐代以前大家不是很关注这篇文献,没人研究它,但是从北宋开始,关注《大学》的人就比较多了。”见陈来: 《〈大学〉的作者、文本争论与思想诠释》,《东岳论丛》2020年第9期。郑注:“其知于善深则来善物,其知于恶深则来恶物,言事缘人所好来也。”孔疏:“言善事随人行善而来应之,恶事随人行恶亦来应之。”(62)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66《大学》,吕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237-2241页。我们注意到,郑、孔皆言物有善恶,且主体自身的道德善恶能够决定“所致之物”的善恶,这种说法并非创见,在文献中有他例为证。《国语·周语中》:“叔父其懋昭明德,物将自至,余何敢以私劳变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与百姓何?”(63)徐元诰:《国语集解·周语中》,王树民、沈长云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第53页。《礼记·乐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64)郑玄注,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卷47《乐记》,吕友仁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59页。郭店楚简《性自命出》:“好恶,性也。所好所恶,物也。”(65)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页,第92页。先秦儒家将“物”与人性道德视作紧密的结合概念,人的“喜怒哀悲之气”不单是主观情绪, “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66)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93页,第92页。这样一来,“物”“我”间显然建立起某种联动关系,促成联动发生的条件就是“德”“义”“礼”等要素。此即美国学者安乐哲、郝大维所说:“一个人通过消解部分和整体,通过在存在事物的场中造就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之聚结,来同世界融为一体,以达到这种‘通联’。”(67)安乐哲等:《孔子哲学思微》,蒋弋为、李志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70页。
深入理解先秦儒家所说“格物”与“致知”,也就是作为客体的“经验”与作为主体的“认知”之间的关系,则不得不对先秦文献所反映出的“知识来源”问题做一整体性考量。裘锡圭在广考文献的基础上指出:“在战国时代,出现了强调外在事物是知识源泉的思潮。”(68)裘锡圭:《说“格物”——以先秦认识论的发展过程为背景》,《文史丛稿: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年,第13页。裘文所引《易》《礼记》《墨子》等典籍之成书年代历来聚讼纷纭,各篇的编订时间不一,其文本内容所反映出的精神内核原应早于战国时代,但不少证据表明,在这种思潮形成之前,典籍中更多的表述则指向“知识天授”,即认知主体获取知识的途径不在人事,而在天道。《诗·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郑笺:“天之生众民,其性有物象,谓五行仁义礼智信也;其情有所法,谓喜怒哀乐好恶也。”(6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23《烝民》,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967页。《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7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三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731-732页,第733页。不论这里铸鼎之人是禹还是启,(71)杨伯峻注:“古代于夏铸鼎之人有两说,一说为禹,则‘方有德’之时指禹之时;一说为启,则‘方有德’之时指启之时。” 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三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731-732页。两者在此语境中都是具有神秘色彩的“圣人”,故他们所铸之鼎“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72)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三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731-732页,第733页。《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杜注“五材”为“金、木、水、火、土也”(7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七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254页。。同样表明在春秋时期知识阶层的认知中,“天生”是知识或具备知识属性的要素产生的重要途径。
以上几例,从“烝民”到“圣人”,皆为“知识天授”,可见至少在“外在事物是知识源泉的思潮”于战国时期全面展开之前,先秦知识阶层在面对“知识来源”问题时往往借助“天”这一概念完成自身的阐释。前辈学人也曾注意到相关问题,以对“铸鼎象物”的研究为例,考古学、艺术学、思想史等领域的学者在过去的研究中多借助文化人类学建构的理论模型作为分析进路,以此解释先秦“博物”观念的发生,其结论指向集中在上古圣王所掌握的“命名巫术”“图像禁忌”等攫取并保持权力的手段上。(74)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47-88页;赵世超:《铸鼎象物说》,《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4期;王晖:《夏禹为巫祝宗主之谜与名字巫术论》,《人文杂志》2007年第4期;王静、郗文倩:《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东南学术》2021年第 4期。曹峰曾总结道: “‘名’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如此高的地位,显然与‘名’能把握‘物’的本质,或者说事物只有被命名之后才具有意义,这样一种神秘观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75)曹峰:《中国古代“名”的政治思想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55页。此类研究路径揭示了人类学语境下“象物”与“权力”间以巫术等神秘力量为纽带的关联,颇具启发性。但同时我们应当继续追问的是,既然难以言说的“天”被认为拥有授人知识的能力,并且被现世政治秩序赋予一定的“权威”色彩,那么为何到了诸子笔下,尤其是儒家笔下,唯有“格物”才能“致知”,而非“格天”或“格上帝”?获取知识时,从求诸“天”,到求诸“物”,这种思想史上的转变机制与思维逻辑是怎样形成的?
以后见之明来看,也许“格物致知”这一说法只能出现在战国时代,也只能出现在儒家笔下。《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76)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5《阳货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 ,第1580页。孔子发出这样的感叹,可视作先秦思想史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此处“四时”“百物”所对应的“行”和“生”的状态更具自在的性质,故“天”与两者间不存在必然和直接的催生关系,但在孔子时代之前,周人对“天”的概念不似传统观点中“高悬在头上的铁板一块”,实际上有着非线性、非一蹴而就的流变进程。郭沫若对周人的天命观有过这样的判断:“(周人)自己尽管知道那是不可信的东西,但拿来统治素来信仰它的民族,却是很大的一个方便。”(77)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青铜时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美国学者史华兹也基于思想史角度,将发现“宗教—伦理的超验存在的明确证据”的时间节点安置在周初。(78)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0页。该说在学界一度颇有影响,但随着研究逐层深入,更多学者认识到,周代“精英阶层确曾在某一关键的思想点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他们的观念领域中,非理性因素消失殆尽”(79)罗新慧:《周代天命观的发展与嬗变》,《历史研究》2012年第5期。。与此同时,“春秋智者对于西周晚期之后的乱局是出于天灾还是出于人祸的辨析,从观念意识方面廓清了上天并非乱政之源,维护了天的崇高性”(80)罗新慧:《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可以看到,两周之际政治上的巨大变动在思想层面引发同样规模的革故鼎新,“天”的象征意义恰恰在周室动荡中被春秋时期的知识阶层重新拾起。从《诗经》中一些对“天”的责难可以看出,西周晚期存在一种“怨天”的思想动向。《诗·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臻。”(81)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23《云汉》,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952-953页。《大雅·召旻》:“旻天疾威,天笃降丧。”(82)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23《召旻》,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995页。而《小雅·雨无正》则更为直接:“浩浩昊天,不骏其德。”(83)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17《雨无正》,吴格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683页。这固然与厉、幽之时民生苦怨,用比兴手法怨天以刺统治集团之昏聩有关,但昔时“皇皇上天”在这时成为承载社会苦痛情绪之处,亦是不争的事实。再将时间前推至周初,“天”的形象较之后世更显崇高伟岸,同时在“殷鉴”观念的影响下,“天命靡常”成为周初的一大命题。成王时期《何尊》铭文载“肆文王受兹大命”,又载“视于公氏,有勋于天,彻命,敬享哉”。(8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06014,中华书局,2007年,第3703页。以下简称《集成》。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载“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 (《集成》02837AB)。 《尚书·大诰》:“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卜用,克绥受兹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85)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卷14《大诰》,陈抗、盛冬铃点校,中华书局,2003年,第348页。除“受大命”的形式外,周人从“天”又引申出“德”的概念,亦为典型的“知识天授”类型的叙事模式,如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天多降德,滂滂在下,攸自求悦,诸尔多子,逐思忱之。”(86)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三)》,中西书局,2012年,第133页。通过以上“倒推”式论证,我们能够认识到西周时期有关“天”的概念大致经历了一个从“被树立”到“被质疑”的过程,人们对于“天”的态度,实际上与对现世政治的态度保持一致。概言之,经厉、幽乱世,周室奔迁,“天”的崇高性几乎不再,转而成为“不骏其德”的形象。既然如此,为何我们在春秋时期的文献中又屡见“天授”“天命”一类的语句呢?笔者认为,随着语境的转换,这里“天”的意涵已然褪去最后一丝权威和神秘,郭沫若所说“只是把天来利用着当成了一种工具”的情况,在西周尚不十分明显,但在春秋时期,“天”的“工具属性”就展现得相当清晰了。
春秋时期,知识不再为某一阶层所垄断,“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87)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十七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1541页。,有关这一现象,学界早已给出多条理解途径,无须赘述。我们关心的是,“知识天授”这种理念本应随着“天子失官”和西周晚期“疑天”“怨天”之思潮而消散。可事实相反,文献中大量的证据表明,春秋时人几乎言必及“天”。罗新慧对此现象曾有很好的解释:“在政治领域内,天与天命的力量不可低估。诸侯心目中的天命,并非改朝换代的象征,它更多的是表示上天的庇护、佑助。”(88)罗新慧:《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笔者想进一步补充的是,春秋时期“天”的确重新被树立起象征政权合法性的形象,但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未尝不可视为“天”的权威几近落地。从《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来看,时人对“天”的反复引证基本不出两种模式:一是“天”降灾祸于某国或某地,二是“天”将嘉祐某国或某人。从表面上看,这与西周时期“天降丧乱”与“受命于天”的表述并无不同,但通过分析比对,可发现两者间实有本质上的区别。以下几条材料就很能说明问题。《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犯曰: ‘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89)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僖公二十八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502页。《左传·宣公十五年》:“天方授楚,未可与争。”(9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宣公十五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829页。《左传·成公二年》:“齐、晋亦唯天所授,岂必晋?”(9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成公二年》,中华书局,2016年,第873页。此类例证不绝如缕。但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综观《左传》,“天授”“得天”等表述基本都出现在齐桓公霸政建成之后,尚为霸政潜伏期的鲁庄公时期,则不见这类话题。这或许是解读春秋时期“天”的意涵与西周不同的关键。囿于史料,我们已很难判断在此类话语背后有着怎样的政治企图,但可以确定的是,虽然说出“天授”“得天”之语的主体立场和具体时政背景不尽相同,可“天”不再是周王室专属之命题,其“使用权”已降至诸侯甚至卿大夫一级。据罗新慧的考察,不唯周室“宗亲甥舅”的齐、晋,或是实力超然的秦、楚,就连曾、蔡、随这种霸政体系下的“边缘小国”,都有自称“得天命”的权利。(92)罗新慧:《春秋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天”的权威下降,由此可见一斑。尽管在春秋霸主道义、力量双管齐下的抟聚与号召下,齐、晋、秦、楚间并未爆发战国时期动辄投入数十万军队的大型会战,但在大国以战争为主要手段的争霸过程中,“由战争而引发的冲突/竞争就刺激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首先在战争行动,继而在其他社会领域中的兴起”(93)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第74页。。也正如葛兆光所言: “在普遍追求实利和实力的时代,价值的理性依据和意义的历史背景对他们来说可有可无,但是,有时候人们包括政治权力拥有者又需要这种价值和意义对自己的行为给予证明或支撑。”(9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三卷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77页。同样,“天”既已变成“可有可无”之“支撑性”理论,它的工具属性也自然不言而喻。
有以上分析为基础,就不难解释为何战国时期出现“外在事物是知识源泉的思潮”这一现象,也便于理解《大学》“格物致知”的深层含义,进而“历史地”关照先秦儒家“博物”观念在文化层面的发生与源流。考诸文献,《论语·述而》虽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95)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4《述而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619页,第624页,第632-633页。,表明孔子并不认为自己属于“生而知之者”,但《季氏》又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96)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3《季氏》,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1492页,第1492页。在孔子看来,“生而知之者”在观念上是可以存在的,皇侃《论语义疏》即云:“若生而自有知识者,此明是上智圣人,故云上也。”(97)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3《季氏》,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1492页,第1492页。孔子一方面否认自己“生而知之”,另一方面却说“天生德于予”(98)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4《述而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619页,第624页,第632-633页。,表面上看似乎有些矛盾,但细细琢磨,实则代表了孔子对传统思维方式的一次精细化处理和超越性突破。“生而知之”和“天生德于予”若得以并存,就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即“生而知之”的“圣人”不是“天生德”的唯一对应选项,“学而知之”者同样能够体味并践行“德”。而孔子言论中,恰恰将“德”等种种“神圣要素”的修习人群进一步拓宽,有志者皆可以通过勤学博思来提升生命境界,故《述而》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99)程树德:《论语集释》卷14《述而下》,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619页,第624页,第632-633页。子夏曾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100)程树德:《论语集释》卷38《子张》,程俊英、蒋见元点校,中华书局,2017年,第1687页。是说对孔子“学”和“仁”的理念体悟甚深。徐复观指出:
由孔子所开辟的内在的人格世界,是从血肉、欲望中沉浸下去,发现生命的根源,本是无限深、无限广的一片道德理性,这在孔子,即是仁;由此而将客观世界乃至在客观世界中的各种成就,涵融于此一仁的内在世界之中,而赋予以意味、价值;此时人不要求对客观世界的主宰性、自由性,而自有其主宰性与自由性。这种主观与客观的融和,同时即是客观世界的融和。(101)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九州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近年来,余英时综“新儒家”、汉学家之说,结合雅思贝尔斯“轴心突破”的概念,将中国思想史上的轴心突破以“内向超越”说涵盖,他强调:
孔子创建“仁礼一体”的新说是内向超越在中国思想史上破天荒之举,他将价值之源的超越世界第一次从外在的“天”移入人的内心并取得高度的成功。(102)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中华书局,2014年,第205-206页。
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孔子在对前代知识传统的尊重与调和下,注入富于创造力的思辨性因素,使先秦儒家在不与传统割裂的基础上,对“物”的关切显示出更加道德化的取向。如果说“敬天保民”尚为周室在“殷鉴”思维余绪中所酝酿出的政治观念,经周室东迁、春秋霸政之社会激荡,思想也随之呈现出愈发复杂、深刻的样貌,又于孔子“述而不作”的过程中实现所谓“内向”的哲学突破,终在战国时期以儒家为主的诸子手中形成以“仁”为本、以“物”求“仁”的“博物”观念。《荀子·天论》的一段话便极具代表性: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103)王先谦:《荀子集解》卷11《天论篇》,沈啸寰、王星贤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第374-375页。
荀子认为“天”应当与“物”同属,并清楚地谈到他对“天”的态度是“制天命而用之”。故而从这条线索出发,《大学》“致知在格物”一句,郑、孔皆从人性善恶解之,无疑是符合战国时代思想史背景的准确解法。人性道德与“物”之善恶高度融摄,在这个意义上,先秦儒家之“博物”就不仅仅是向外的博学,亦是向内的工夫,两者以“博物”为通道,实现某种智识上的双向互动,以成己、成身、成君子,最终追求“仁”的境界。
五、余 论
当我们从思想史角度重新审视发端于战国、初成于秦汉、喷薄于魏晋的众多“博物”故事之时,厘清它们共同叙事模式的发生源流就成为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显然,从“圣人辨名识物”到《博物志》《白泽精怪图》等文献,再到后世形形色色的“博物志怪”类小说文体的形成,(104)王昕:《论志怪与古代博物之学——以“土中之怪”为线索》,《文学遗产》2018年第2期。其叙事模式均难以脱离《山海经》《穆天子传》等“方位+异物”的传统结构类型。常金仓指出:
《山海经》中绝大多数的志怪神话并非史前文化的“遗存”,而是在战国时代根据特定社会需求对前赋文化做出的新综合。记录在儒家经传上的传说故事也不是神话的历史化,倒正是《山海经》神话的原始素材。(105)常金仓:《〈山海经〉与战国时期的造神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研究表明,在《山海经》文本编定之前,其内在思维模式就已经进入较为稳定典型的阶段。事实上,战国时期“轰轰烈烈”的也不仅是阴阳、方士之流主推的造神运动,在思想史层面迸发出同样激烈且迅猛的声音。“天”的姿态已影影绰绰,取之而代的“天下”观念却深入人心,内化为诸子共同的学术旨归和政治追求。而孔子关于“天”的阐说和“物”的辨析,对孔门后学以至于整个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一思维方式或可看作朱熹理学思想的学术源头之一:“目前事事物物,皆有至理。如一草一木,一禽一兽,皆有理。草木春生秋杀,好生恶死。‘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皆是顺阴阳道理。”(106)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朱子语类》卷1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7页。赵汀阳基于中国传统哲学立场,从方法论角度出发,认为“‘天下’是个已经完成了从chaos到kosmos的转变的世界,是个兼备了人文和物理含义的世界”,进而提出:“这个能够作为任何生活事物的解释条件的最大情景就是‘天下’。”(107)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8-29页。赵汀阳对“天下”的一系列申说应是帮助我们理解先秦儒家“博物”观念的可行范式。总之,过去研究多将中国传统哲理中的“物”“我”联动按照列维-布留尔经典的“互渗律”来进行解读,这固然是一条解决思路,但在研究思想史上的某种现象时,忽视某文明自身的思想史发展脉络和社会背景而言其他,终究不是探讨思想问题的最佳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