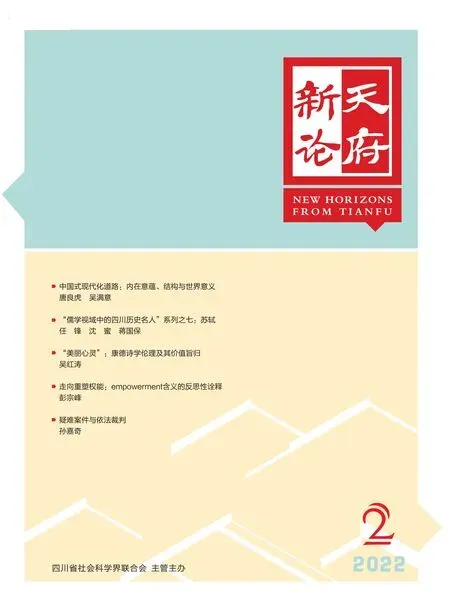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资本与资本逻辑
林彦虎
在人们通常的直观印象中,资本是一种“生产要素”。然而,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会发现“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只是资本复杂属性中的一种表象,若要对资本有更为深层和全面的理解,必须立足于马克思所强调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层面。同时,资本的运动过程生成了资本逻辑,资本复杂的多维属性决定了要准确而全面地理解资本逻辑并非易事。那么,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实质各自是什么?资本与资本逻辑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科学解答这些问题,必须要深入马克思的论述中。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资本及其实质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资本”(capital)这一概念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每天都或多或少要受到资本的影响,因此,“在日常用语中,‘资本’一词通常用于表述个人所拥有的作为财富的资产。”(1)汤姆·博托莫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陈叔平等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2页。说陌生,则是因为要对资本作出一个准确而全面的定义难度很大。显然,熟知不等于真知。查看普通词典,对“资本”的界定主要围绕三个层面:一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生产资料和用来雇佣工人的货币”,二是“经营工商业的本钱”,三是“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41页。显然,这三种解释都侧重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生产要素,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实质上指的是长寿的,因而需要折旧的生产资料(不包括耗材),由此延伸又将资本理解为各种投资品(包括货币、股票等等)。”(3)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资本”界定为两个层面:一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资本(Capital as a Factor of Production)”,二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资本(Capital as a Social Relation)”。(4)约翰·伊特韦尔,默里·米尔盖特:《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 (第二版)第一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56、362页。这种解释不仅包含了对资本是“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理解,而且将资本上升到了一种“社会关系”层面,的确要深刻得多,但仍失全面。那么,资本究竟为何物呢?对这一问题的科学解答,必须要深入马克思的语境中。
第一,资本是一种在持续运动中不断获取剩余价值的价值。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第714页。也就是说,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将劳动力变为商品,进而通过预付的方式购买劳动力。在大规模生产中,劳动者创造出巨大的价值,但资本家仅给了劳动者得以维持自身和家庭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以及支付给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最低费用,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资本的本性就是通过不断追求剩余价值来实现自身增殖。资本的这种本性构成了资本扩张的内在动力,造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第714页。。资本要最大化实现自身增殖,就要始终处于运动中,即资本“是一种运动”,或者说,“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122页。。资本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即在持续运动中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并将其不断资本化,才成其为资本。而要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资本就要不断地将自己获取的剩余价值资本化,从而在不断的自我循环中完成自身增殖,进而表现为一种持续的运动。一旦停止了运动,就意味着资本的死亡。
第二,资本是一种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社会关系。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指出:“构成资本的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难道不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内生产出来和积累起来的吗?……难道不正是这种一定的社会性质把那些用来进行新生产的产品变为资本的吗?”(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在这里,马克思用反问的方式明确指出了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同时也指出各种生产要素不仅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和积累起来的,而且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用于新的生产并变为资本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土地、劳动”并列为生产要素,并认为三者分别生产出“资本—利息(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3页,第922页。。马克思批判这是一种“三位一体的公式”,指出:“资本,土地,劳动!但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资本不是物质的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总和。资本是已经转化为资本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本身不是资本。”(1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33页,第922页。从马克思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看作一种“物”、看作一种客观化的“生产要素”。这种“见物不见人”、更不见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决定了庸俗经济学家不可能对资本有深入、准确且全面的理解,更不可能从深层次揭示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真正秘密。对此,马克思指出:“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4页。庸俗经济学家将资本理解为物、生产要素,而马克思看到的是物与物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页,第 877-878页。那么,何为“生产关系”呢?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第724页,第130页。这段话不仅指出了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是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且说明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是由一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社会又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构成的。因此,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主要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方面,其中,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也就是说,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这启示我们:“当马克思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关系的时候,也就等于把资本理解为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存在的社会现象,并把其实质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4)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 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总体来说,马克思不是停留在静态的“物”的层面来理解资本,而是深入动态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理解资本。同时,对于这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形式,马克思在肯定韦克菲尔德对资本的理解时有过明确论述:韦克菲尔德“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8页,第 877-878页。显然,韦克菲尔德对资本的理解同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也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第724页,第130页。是一致的。而且在这里,马克思也进一步强调了资本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以物为媒介的”,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以物(生产要素)为载体的社会关系。
第三,资本是一种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生成的社会权力。亚当·斯密在引证了霍布斯的“财富就是权力”的观点后,进一步指出:财产对财富所有者“直接提供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当时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各种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必然恰等于这物品对其所有者所提供的劳动支配权”。(17)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7页。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这一思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引用了亚当·斯密类似于上述的思想,而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4页,第724页,第130页。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之所以拥有“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二是劳动者除了拥有劳动力之外一无所有。也就是说,“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第31-32页。这样一来,劳动者是一个失去了生产资料而只有劳动力的自由无产者,劳动者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要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换取物质资料。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形成一种对无产阶级的支配权,劳动力在资本家眼中只不过是商品而已,只是这种商品能够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资本不仅是“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而且,“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页,第31-32页。资本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力,是因为作为人格化的资本,资本家通过占有各种生产资料,以一种看似“你情我愿”的方式绝对地控制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依赖必然会转变为对资本家的人身依附,只能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发展。对于资本权力带来的这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尖锐地批判道:“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2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2页。资本积累过程就是资本权力的不断扩张过程,而且这种权力已经超越经济权力,渗透到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因而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全部权力都是在作为‘经济权力’的资本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22)俞吾金:《资本诠释学——马克思考察、 批判现代社会的独特路径》,《哲学研究》2007年第1期。
总结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深层揭示,可以将“资本”界定为投入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殖,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剩余劳动力价值,其实质是一种作为物化劳动的物质化生产关系。(23)参见鲁品越、王珊:《论资本逻辑的基本内涵》,《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的“资本”指产业资本,是实体经济中的资本,是一切其他形式资本的根源。货币资本、商品资本、金融资本等都由产业资本衍生而来,脱离产业资本而谈论其他资本,将是无根的。因此,该论文中的“资本”若无特别说明,均指产业资本。因而,资本同时呈现出两种性质:一方面,资本是投入生产过程中追求自身增殖的剩余劳动力价值,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在生产领域表现为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在流通领域则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必须以生产要素为载体,进而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并以物质生产活动的生产要素的方式呈现,通常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说,资本是一种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生产要素只有被纳入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因此,“真正意义上的‘资本’既不是脱离社会关系的物质生产资料,也不是脱离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关系,而是物化了的生产关系——是用物质形态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通过这种物质形态而成为支配社会的物质力量,成为支配人的权力。”(24)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20页。正如马克思所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2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23页。由此可见,“黑人”通常情况下只是客观存在的“人”,只有在奴隶制社会关系中,才与奴隶主形成了剥削与被剥削的社会关系。而“纺纱机”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生产工具,虽然它本身是“中性”的,一旦被纳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中,就会成为一种负载着社会关系的物质,被资本家掌握后,就成了剥削工人的工具。资本必须要物质化才能成为社会关系,且这种社会关系负载于物上,并通过对物的占有而生成了一种支配人的权力。因此,脱离了物质载体,资本就不是“资本”了,只会是一般的抽象劳动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资本逻辑及实质
根据词意,“逻辑”一词主要有三层含义,即“思维的规律”“客观的规律性”“逻辑学,研究思维的形式和规律的科学”。(2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小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62页。有学者从狭义和广义层面来理解资本逻辑,认为狭义的资本逻辑是指“资本自身的逻辑,即从商品逻辑到货币逻辑到资本逻辑的递进发展过程以及‘利用资本消灭资本’的整个资本逻辑的形成、发展过程”,广义的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作用的逻辑,即资本逻辑以‘普照光’的形式影响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27)王巍:《马克思视域下的资本逻辑批判》,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4页。实际上,上述对狭义资本逻辑和广义资本逻辑的理解是统一的,毕竟资本逻辑不仅是一个资本自身运动的逻辑,而且它在资本自身运动过程中不可能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领域割裂开来。也就是说,资本运动过程生成了资本逻辑,并遵循着自身发展的逻辑,也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说的“逻辑”来自黑格尔,是辩证法。但从“资本”的角度而言,马克思语境中的“资本逻辑”来自资本的逻各斯,即资本运动在历史上所遵循的道或规律。(28)马拥军:《超越对“资本逻辑”的模糊理解》,《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8期。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讲的“逻辑”是指“客观的规律性”,而规律是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是事物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就此而言,可以将“资本逻辑”的字面意思理解为“资本运动的客观规律”,即资本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一种必然性发展趋势。当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于字面意思层面。
实质上,资本内在两方面性质的统一,将原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化劳动的物质化生产关系,以物化了的社会关系的方式不断追求自身增殖,这种增殖本性成为资本支配一切的内驱力,在不断将剩余价值资本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将全社会的一切生产要素都纳入自己的增殖范围,从而在对人的劳动的支配中不断将客观世界“资本化”,“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客观物质力量及其遵循的矛盾发展规律。这是物化了的‘人的本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及其遵循的规律强制地推动着社会经济运行”,并成为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运行规律,即“资本逻辑乃是作为物化的生产关系的资本的自身运动的矛盾规律”(29)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43页。。有学者将资本逻辑的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持续运动中的增值性逻辑”“资本在特定生产关系条件下的主体性逻辑”“资本全面控制社会生活的总体性逻辑”“资本自我发展与自我限制的矛盾性逻辑”。(30)韩昌跃:《资本逻辑支配下当代资本主义的运行和发展规律》,《甘肃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不难看出,这种概括是比较中肯的。立足这一基础,我们进一步对资本逻辑的理解做几点深化和拓展:
第一,资本逻辑是一种资本不断扩张的规律。资本扩张规律的实质是剩余价值不断资本化,是资本千方百计地将世间一切生产要素尽可能多地纳入自己的扩张范围,进而实现不断增殖。驱动这种规律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内在扩张动力,主要是由资本本性决定的。即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其本性在于不断扩张。资本的扩张本性决定了资本家会千方百计地将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在通常情况下,资本家仅会将剩余价值的很少部分用于自身消费,而普遍会将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不断资本化,即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从而在不断推动资本扩张的过程中寻求更多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是外在竞争压力。马克思指出:“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3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3页。因此,资本家要想在竞争中不被淘汰,就要千方百计地扩大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不断资本化过程。以产业资本为例,其循环过程的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但必须要在流通领域通过交换最终才能完成。因此,资本积累过程不仅要在生产领域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资本化,而且要千方百计地将生产出的大量商品销售出去。低廉的价格、广阔的市场、巨大的利润,必然是资本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对于价格竞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有过明确阐述:资产阶级“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3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5页。。同样,为了赢得更多市场,资本家之间每时每刻都展开着激烈的竞争,无论是生产工具的及时更新、管理技术的有效改进、生产效率的极大提升,还是以野蛮方式疯狂压低劳动力价格和无情延长工作时间,不仅是资本攫取更多剩余价值的手段,也是资本家为了更好地应对外在竞争压力的手段。在外在竞争压力的驱使下,资本家会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资本化,进而形成一种资本的扩张逻辑。
第二,资本逻辑是一种资本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呈正比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性是将剩余价值不断资本化,不断实现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过程主要通过开发和利用三种自然力来实现:资本不断吸收和利用“人的自然力”以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使劳动者不断陷入经济上的“贫困积累”;资本不断吸收和利用“自然界的自然力”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载体,使自然界不断陷入生态环境的“贫困积累”;资本不断吸收和利用“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以提高剩余价值率,使劳动者不断陷入人的发展空间上的“贫困积累”。(33)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资本论〉到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83-332页。也就是说,资本积累越膨胀,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规模越大,经济危机、生态危机和人的发展危机等问题也会越严重。当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之间的这种正比关系,在某个企业内部或者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定时间段内或许表现得不是很明显,但从资本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角度而言,当资本扩张到一定界限时,资本积累带来的“贫困积累”将会十分明显,且会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第三,资本逻辑是一种资本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讲的“矛盾”是指不同事物之间或者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资本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是一种资本自我发展(统一)和自我限制(对立)的规律,是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走向扩张悖论的规律,也是资本自我否定的规律。资本扩张在不断推进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又与资本增殖的本性发生冲突,必然限制生产力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8页。。具体而言,资本为最大化获取剩余价值必然会不断扩张和积累,从而极大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但另一方面,在永无止境的剩余价值资本化过程中,资本必然要吮吸各种“自然力”作为自身扩张的工具,进而导致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的发展危机等,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断显现和升级。因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1页。。这是资本运动的必然结果,是资本逻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显现。资本逻辑存在的这种内在矛盾是资本自我否定的必然结果。资本运动过程是一个资本不断集中的过程,当资本推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3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74页。这实质上就是资本逻辑展现的资本发展的矛盾运动规律,是资本运动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资本逻辑蕴含的资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趋势是,资本要经历一个从产生到成长、成熟,再到逐步完成自身历史使命后走向自行消亡的内在否定过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的资本与资本逻辑的关系
那么,“资本”与“资本逻辑”有着怎样的关系呢?总体来说,资本与资本逻辑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密不可分。资本是一种运动过程,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过程的一种规律性呈现。然而,在现实生活的具体理解中,两者又有着显著的差异。
资本是资本逻辑的“根”,资本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固有前提和基础是资本的存在,但有资本并非就有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资本运动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资本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原始社会末期资本就已经以“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出现,但这时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资本生成过程的萌芽状态,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在奴隶制社会中,商品交换不断发展,为资本的生成提供了一定机会。在封建社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较大发展,尤其在封建社会末期,开始出现少量自由工人在市场上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也随之开始形成。但受强大的自然经济的影响,这一时期的资本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有限的力量。简言之,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条件下,资本经历了一个从缺场到萌发的过程,但始终未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资本逻辑也尚未显现。而在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劳动力成为商品已非常普遍,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进入常态化,货币不再仅仅充当一般等价物,而且成了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货币,即资本,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已经形成。从这一时期起,资本开始成为“凌驾于世界之上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某种力量”(3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并形成了强大的资本逻辑影响着整个世界。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不断战胜封建社会,并成为代表人类社会更高文明的一种社会形态。
资本逻辑生成于资本的运动过程,但又反作用于资本,进而加剧和强化着资本的力量。虽然资本逻辑的生成是资本运动过程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资本运动过程中的规律呈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并不代表资本逻辑完全受制于资本的作用。相反,资本逻辑对资本发挥着强大的反作用,即资本逻辑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力度越强、影响范围越广,资本对现实社会各个领域的支配力度就会越大、影响范围也会越广。也就是说,资本与资本逻辑是紧密联系的,两者是在相互作用中呈现的。在具体运行过程中,资本逻辑对现实社会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力,既有效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又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资本逻辑在现实运行中对社会的影响力度越大,资本对现实社会的支配力度也就越大。反之亦然,资本对现实社会的作用力越强,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也就越强大,其自身的系列特征就越明显。
资本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暂时的“过渡点”,必然会伴随其历史使命的完成而自行“消亡”,而资本的“消亡”则意味着资本逻辑随之消失。资本的最终宿命是实现自我否定,即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自行“消亡”,但这一过程只能伴随人类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的到来而到来。当资本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第32页,第32页。这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资本创造的强大生产力在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同时,无形中为未来社会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资本积累造成的经济危机、生态危机、人的发展危机等不可避免的严重问题无形中成为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定时炸弹”;三是资本生产出了它自身的掘墓人,“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第32页,第32页。,而且“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4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第32页,第32页。这种直接明了的阶级矛盾一旦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必然会引发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冲突乃至阶级革命,最终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宣告终结。因此,资本完成其历史使命的过程形成了一个将人类社会从“人的依赖社会”推向“物的依赖社会”、再推向“个人全面发展的社会”的漫长历程,无形中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走向了自行“消亡”。资本是资本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固有前提和基础,资本的自行“消亡”意味着资本逻辑的“根”将不复存在,进而宣告了资本逻辑将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