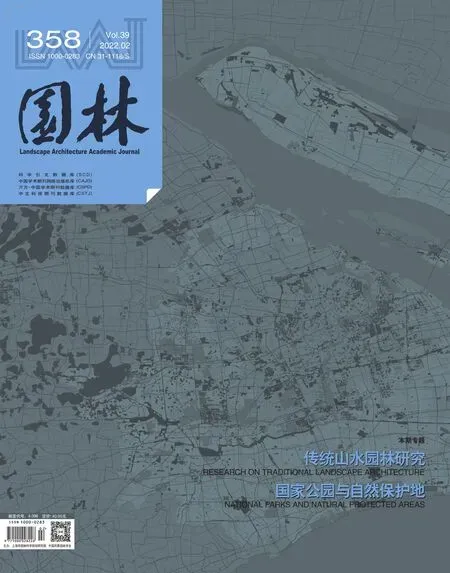中国园林的点题原则与经典母题
胡运宏 陈咏奕
(南京林业大学风景园林学院,江苏南京 210037)
中国园林“文心”的呈现方式大体有三种:(1)借鉴诗文创作中意在笔先、精心结构等手法来造园筑圃。意在笔先之“意”,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作品主题,一是指创作构思,前者是作品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即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抑或对理想的表现;后者是说造园者要胸有丘壑,能从大处着眼因地造景,从小处着手精心设计,用作诗文的起承转合、虚实结合、先抑后扬等方法来精心营构园林。(2)通过述古与编新、着迹与妙套、应景与应情等基本原则,直接为园名景名点题。述古就是用典,要跟园林的具体景致和游园情形结合起来,在切中造园旨趣和景象意境的基础上,巧妙地套用和编新,方能产生含蓄婉转且诗意盎然的效果,反之生搬硬套,随意乃至滥用旧人旧事旧语,不仅让人不知所云,更有害于园林意境的表达。(3)将原来只存在于诗文中的虚景变成现实的可游可居的实景,化“诗意”为“园境”,像“桃花源”“濠濮间”“沧浪水”“芭蕉雨”“疏影梅”等经常成为中国园林的造景母题。
文人园林;点题;《红楼梦》;造景母题
“园林应以文化为魂”[1],中国园林是士人“文心”的呈现,士人或借鉴书画诗文创作中意在笔先、精心结构等手法造园筑圃,人在游园时,能够获得如阅读美文一样愉悦感;或通过匾额、楹联、石刻等形式直接为园名、景名点题,文字往往采撷诗文,用诗一般的语言写景状物,传达士人的精微情感;或将诗文中的场景、意境在园林中予以实景呈现,并由此形成了一些常见的造景母题。
1 意在笔先与精心结构:从书画诗文创作到造园筑圃
中国园林不是造园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皇家园林规模宏大,气势雄伟,以壮阔华丽取胜,非大手笔不能为;私家园林(寺观、衙署、书院等园林可归为私家)布局精巧,风格雅致,以亲切宜人取胜,亦非精心营构而不能成。无论哪一种造园,凡相地选址、立基构屋、叠山置石、凿池理水、植花种草等等,都要求造园者以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艺术眼光统摄之。
1.1 意在笔先
“意在笔先”本是中国书画创作的一个基本原则。东晋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有云:“意在笔先,然后作字。”[2]唐代王维在《山水论》也说:“凡画山水,意在笔先。”[3]后来,这一关于书画的理论被广泛推用于各种文艺创作,成为中国文艺理论的重要命题。唐代王昌龄《诗格》有云“先立意则文脉畅通”[4],清代刘熙载总结道:“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于手忙脚乱。”[5]中国园林作为一种与书法、绘画、文学相通的艺术门类,自然也受到这一文艺创作理论的影响。
“意在笔先”之“意”,主要有两种涵义:一是指作品主题,一是指创作构思。所谓“作品主题”,是指作品所表现的中心思想,即作者对现实的思考,抑或对理想的表现。以中国园林为例,清皇家园林避暑山庄,湖泊区的江南绮丽、平原区的塞外风光、山岳区的崇山峻岭,以及蜿蜒如万里长城的宫墙、若众星拱月般的外八庙,表达的正是清帝“移天缩地在君怀”的大一统思想。苏州的拙政园,是明代御史王献臣在官场失意后还乡所建,取晋代潘岳《闲居赋》中“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文意而命名,表达的是王献臣欲求归隐的造园旨趣。所谓“创作构思”,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提到“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2],意思是说先将所写之字的大小、笔画、结构、章法在头脑中预演一番,然后再落笔成型。这是说的书法创作构思。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描述画竹过程:“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6]这是说的绘画创作构思,推衍至造园创作构思,是指造园者要胸有丘壑,能从大处着眼因地造景,“因高就深,傍山依水,相度地宜,构结亭榭”[7];能从小处着手精心设计,用隔景、分景、障景划分空间与景区,用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实借、虚借增加景深与层次,用或通幽或便捷的园路组织游览,用动静对比、虚实相济、以曲带直、小中见大、聚散开合等对比协调法统一全园。就叠山理水而言,要明确园中山石脉络走向,山林地可按照自然脉理来构山,平地则可考虑因高就低;还要疏通园中的水源,尽量与自然水系相连,形成活水。此外更要精心处理好山水之间关系,使山因水活、水随山转,以形成山环水抱之局。就植物栽植而言,无论成林还是孤植,古虬还是繁茂,成林于山巅还是横卧于水畔,都要与山石、水体、建筑互为凭藉,相得益彰,又要自然天成,富有野趣。就园林建筑而言,要以先确定主体建筑,“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8];其他亭、台、楼、阁等建筑,则随山水脉理、地势高低和观景需要,因地制宜合理布置,并以廊、桥、路相连,门、窗、墙分隔,形成园中园、景中景的园林格局。
当然,“意在笔先”并非指在造园之前要把所有过程和环节都思虑周全,在实践中往往还存在一个“意随笔生”过程。清代郑板桥曾将自己与文同画竹作比较:“文与可画竹胸有成竹,郑板桥画竹胸无成竹,浓淡疏密,短长肥瘦,随手写去,自尔成局,其神理具足也。”[9]文同胸有成竹,能意在笔先;郑板桥胸无成竹,而意随笔生,随手写去,自成格局。造园也是如此,有时确立主题和明确构思并非能一步到位,而是在营造时不断修正和推进;甚至有时先前立的“意”,后来改得面目全非,乃至完全推翻。袁枚造随园,在确立“随”的主题后,经“一造三改”4次修造,格局才基本定型。康熙初营建避暑山庄,本意只是模仿江南湖景,在湖中如意洲上修建无暑清凉等殿,后来却不断增修,成为一座寓意大清江山一统、囊括四海的大型皇家园林。可见,笔先之“意”很多时候只是一个朦胧的主题,胸中之“丘壑”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思,更多内蕴深刻的主题和设计精巧的构思,是在造园过程中被不断发掘和形成的。这是一个感性到理性的多次反馈过程,要靠造园者长期揣摩和反复构思。
要之,意在笔先是说造园之前需要构思一个基本主题和大致构思,然后在造园过程中不囿于框架,根据园林环境、造园素材等需要作必要修正和深化。
1.2 精心结构
造园还有一个如作文般“精心结构”的过程[10]。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有云:“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11]这里,“曲折有法,前后呼应”其实就是古诗文所讲究的起、承、转、合的内在结构。以古律诗为例,“起”即诗的首句,往往交代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内容,起烘托背景的作用;“承”是“起”内容的佐证、延续与深化,起承上启下的作用;“转”是在之前铺垫蓄势基础上,内容与结构的转换,往往体现为由物及人、由景及情、由事及理的转折,要尽量使文意荡开,形成波澜,既让文意鲜活生动,又使主旨得以揭示;“合”即在感情迸发高潮后,或点明主旨,收束全诗,或以景结情,余意绵绵。以宋代陆游《登赏心亭》为例,首联“蜀栈秦关岁月遒,今年乘兴却东游”为“起”,诗人在蜀栈秦关一段峥嵘岁月后,终于要东归了,兴奋心情溢于言表,由此铺垫了一个乘兴东游的基调;颔联“全家稳下黄牛峡,半醉来寻白鹭洲”为“承”,是对诗人从长江上游到下游一路东归历程的高度概括,“稳”“醉”二字表达出诗人历险如夷、平安归来的心境;颈联“黯黯江云瓜步雨,萧萧木叶石城秋”为“转”,乘兴东归、酒酣气张的诗人登上赏心亭,却只看到一派肃杀凄凉的秋景,瓜步之黯黯与石城之萧萧,让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尾联“孤臣老抱忧时意,欲请迁都涕已流”为“合”,在前句基础上诗人情感再次抒发,念及迁都之事不禁涕泪纵横不能自已。全诗起于喜,终于悲,欢情着笔,悲意落句,结构上呼应开篇,圆合首尾。
中国园林如同诗文一样,也要尽量避免平铺直叙、简单堆砌,而追求通过山石、水体、植物、建筑等要素的艺术化处理与安排,形成起承转合、前后呼应的空间序列。以颐和园前山中央建筑群为例,在南北中轴线上,昆明湖岸的云辉玉宇牌楼为“起”,牌楼三间四柱七楼,顶覆黄色琉璃瓦,气度非凡,定下整座园林皇家气派的基调。排云门、排云殿为“承”,“排云”典出晋代郭璞“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诗句,与云辉玉宇牌楼上的“云辉玉宇”“星拱瑶枢”金字相互呼应,均寓意高高在上的神仙境界。排云殿为全园最富丽的建筑,重檐歇山屋顶,覆黄色琉璃瓦,屋身梁柱施和玺彩画,是慈禧寿辰时接受拜贺的主殿。德辉殿、佛香阁为“转”,德辉殿为通往佛香阁的歇脚更衣之处,佛香阁为全园的中心建筑,气势宏伟,巍然耸立,是颐和园的标志。人间的君主虽然高高在上,但是跟佛祖相比,则是信仰者与被信仰者的关系,从排云殿到佛香阁,体现了君王居所向佛祖圣地的转换。众香界、智慧海为“合”,众香界亦是一座牌坊,与起点的云辉玉宇牌楼前后呼应,智慧海寓意佛的智慧像海一样旷阔无边,既重申了景点的主题,又以海之辽阔喻佛法广大,令人余意绵绵。
除了起承转合的章法结构,中国园林在虚实结合、先抑后扬等表达技巧方面也与诗文有融通之处。(1)虚实结合。人所见之景为实,想象之景为虚,景物为实,感情为虚,虚实结合相生,能增添诗文的趣味和意境。如唐代王之涣《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中太阳、黄河、高山为实,但鹳雀楼上不可能看到海,故大海为虚,眼前太阳下山是实景,想象的黄河入海为虚景,两者完美融合。中国园林亦处处体现着实虚之间的高度融合,如沈复《浮生六记》所总结的:“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于墙头,如上有月台而实虚也。”[12]又如,太湖石的石质本体是“实”,瘦、漏、皱、透的体型与纹理是“虚”,虚因实而显现,实因虚而古雅,实与虚相得益彰。再如,亭子有顶无墙、四面开敞,特征在于空虚,但空虚之亭能收聚万千实景,人登亭而望,能突破有限的空间,通向无限的宇宙。(2)欲扬先抑。这也是诗文常见的表达技巧,往往先从反面着手,欲擒故纵,先隐后显,最后才表达作者真实意图。这种手法在中国园林中颇为常见,一般通过曲直、大小、藏露、开合等手法丰富园林的结构层次,形成景愈藏而意愈深的效果。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留园入口,采用多重的转折形成曲折蜿蜒的路径,一再收藏园林主景,反复压抑观者欲望,走到尽头,漏窗下隐约可见园中山水,最后绕过门窗,一切豁然开朗,方进入真正的主景区,正是对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山有小口,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文字的生动呈现。
2 循景点题:从《红楼梦》第十七回谈起
中国园林山石、水体、植物、建筑等要素所形成的园林景象,虽然能被人通过感官直接感知,但是景象背后抽象的园林意象或意境往往不易为人觉察,而这有赖于匾额、楹联、石刻等形式的点题,方能画龙点睛地得以呈现与深化。“造园亭之难,难于结构,更难于命名”[13],中国园林必须用文学点题作精加工,这是中国园林有别于西方园林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是中国园林史上少有的理论华章[14],其意义不亚于计成《园冶》。这一回讲大观园初成,贾政领着贾宝玉及一帮清客在园中循景点题的经过。在小说中,曹雪芹借贾政之口指出:“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也觉寥落无趣,任有花柳山水,也断不能生色。”[15]仔细品读这一回,可以总结中国园林点题的一些基本原则。
2.1 述古与编新
大观园入口处有一座作为障景的假山,白石崚嶒,或如鬼怪,或如猛兽,纵横拱立,上面苔藓成斑,藤萝掩映,其中微露羊肠小径。贾政身边的一众清客为这座大假山所题点的“锦嶂”“赛香炉”“小终南”等,皆是俗套。曹雪芹借贾宝玉提出了“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的点题原则。这里的“述旧”“刻古”,其实就是常说的用典。用典是中国传统诗文创作的一种重要手法,一则涉及古人古语,可以使作品更显典雅隽永,二则典中往往饱含作者情感,给读者以无穷遐想的阐释空间。中国园林中这样的用典可谓俯拾即是,例如:北宋司马光独乐园之“独乐”,典出《礼记》“独乐其志,不厌其道”;清代圆明园四十景之“坦坦荡荡”出自《论语》“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上下天光”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苏州沧浪亭出自《楚辞》“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无锡寄畅园“知鱼槛”出自《庄子》“安知我不知鱼之乐”;苏州留园之“闻木樨香轩”、狮子林之“指柏轩”出自禅宗公案。
大观园门口的这座假山,本身作障景之用,藤萝之间的羊肠小道又吸引和暗示着游人的路径,因此贾宝玉干脆直接点题为“曲径通幽处”,既用了唐代常建《题破册寺后禅院》“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诗的典,又与这座假山的景致和功能契合,可谓妥帖之极。可见,用典要跟园景结合起来,典故切中了造园旨趣和景象意境,方能产生含蓄婉转且诗意盎然的效果。反之,用典过度,随意乃至滥用旧人旧事旧语,跟所造之园景不符,不仅让人不知所云,更有害于园林意境的表达。小说中,下文为“沁芳亭”命名时,就谈到了这个道理。“沁芳亭”建于一座三孔石桥之上,是大观园假山背后的第一景,且在中轴线上跟主殿遥遥相对;亭桥之下的那条溪水贯通全园,园内所有的院馆几乎是沿此溪曲折布置的,可谓大观园命脉。因此,此亭之点题非同小可。一开始,众清客用了欧阳修《醉翁亭记》“有亭翼然临于泉上”的典,题点为“翼然亭”,但此亭压水而建,“翼然”二字就亭言亭,与亭的景象不切合,属于胶柱鼓瑟式用典,遭到贾政否定。贾政依然用《醉翁亭记》中“有泉泻出于两峰之间者”之句,题点为“泄玉”,将意象凝聚在溪水之上,可谓抓住了重点。只是,大观园乃为元春省亲而建,带有皇家园林的意味,“泄玉亭”放在郊野或其他园林或许可以,但放在大观园则略显粗陋不雅,是以贾宝玉变“泄”为“沁”,改“玉”为“芳”,题名“沁芳”。这里,“沁芳”二字没有述古用典,完全是用“泄玉”之意用对仗方法新编而来,但这一编新却极为成功:“泻玉”专注于水,“沁芳”则将周围植物容纳进来,没有点名“水”字,但处处含有水意。贾宝玉又为“沁芳亭”题了一副楹联:“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这里,“绕堤”“隔岸”暗指此处花柳乃依水而植的;“绿”之颜色,“香”之气味,均无质无形,却用“三篙”“一脉”量词修饰,更显生动灵巧,花柳的翠绿芬芳仿佛随着溪水沁人心脾。——“沁芳”二字可谓韵味无穷。
2.2 着迹与妙套
大观园中蘅芜苑的景致颇有独到之处:入院门,迎面一座高大玲珑山石,四面群绕着各式石块,将里面的房屋都遮隐住;院内不栽一株乔灌花木,却植满了藤萝、薜荔、杜若、蘅芜、茝兰、清葛、金䔲草、玉蕗藤、紫芸、青芷等奇花异草。这些花草牵藤引蔓,苍翠欲滴,味芬气馥,因此众清客为其题点“兰风蕙露”,用兰、蕙指代奇花异草,兰风与蕙露还喻有高洁之义,有一定可取之处。只是后面的两副对联,与这里景致不契合,因为“麝兰芳霭斜阳院,杜若香飘明月洲”是说兰麝的芬芳笼罩在夕阳下的院落里,杜若的香气飘散在明月中的洲岛上;“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是指小路上微风吹来玉蕙的阵阵香气,庭院里明月照着金兰的亭亭玉姿,虽然都将焦点落在麝兰、杜若、玉蕙、金兰等植物上,似乎也应对了这里遍布奇花异草的景致,但是文中所谓麝兰、明月、斜阳、洲渚、三径等,与这里“四面群绕各式石块,竟把里面所有房屋悉皆遮住”的环境大相径庭,用贾宝玉的话说,这叫“着迹”,斧凿之迹明显,显得生硬不自然,没有达到出神入化、浑然一体的境地。
与“着迹”相对的,是“妙套”。所谓“妙套”,是对前人诗文的巧妙仿套。例如熟知的初唐王勃的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是套用南朝庾信《马射赋》中的“落花雨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因为仿套巧妙,不留痕迹,以致人们只知前者而不知后者。这里,清客所拟联中“麝兰芳霭斜阳院”一句,套用了唐代鱼玄机《闺怨》中“靡芜盈手泣斜晖”诗句;“三径香风飘玉蕙,一庭明月照金兰”,似乎还是对贾宝玉“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的套用,但是诗句所描写的内容,与所题的景致毫不相干,也属于生搬硬套。这样的随意编造,用贾宝玉的话评价就是“题两百联也不能完”。可见,仿套不是不可以,关键是仿要仿得精致,套要套得巧妙。李白在江夏黄鹤楼看到崔颢《黄鹤楼》诗,掷笔长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后来到金陵仿套崔诗写了《登金陵风凰台》,但因为“套得妙”,所以两诗相似,格律气势不相上下。
“妙套”之“妙”,在能袭故而弥新,套出新意。贾宝玉题点“蘅芷清芬”后,拟联“吟成豆蔻才犹艳,睡足酴醿梦也香”,便是套用时人所熟知的一副对联“书成蕉叶文犹绿,吟到梅花句亦香”。两联结构相同,用词相近,“书成”变“吟成”,“才犹艳”仿“文犹绿”,“梦也香”套“句亦香”,因此贾宝玉的对联一出,贾政立即指出仿套来源。但是,仔细品读,原作不免质实呆板,而贾宝玉套作中,“豆蔻”为多年生草本,花开芬芳,荼蘼亦有香味,与此处藤蔓攀援、花草芬芳的景致高度契合,而且将豆蔻之“艳”移来说诗之“艳”,将荼蘼之“香”移来说梦之“香”,使“艳”“香”二字,既实又虚,兼顾两面,摇曳生姿,更显幽娴活泼,简直“视‘书成’之句竟似套此而来”。可见,别出心裁的妙套往往能超越原作,甚至让人以为原作袭自套作,正如李渔所论:“妙在信手拈来,无心巧合,竟似古人寻我,并非我觅古人。”[16]
需指出的是,小说中曹雪芹接贾宝玉之口似乎在肯定“妙套”而否定“着迹”,但是在中国园林实际点题实践之中,“着迹”的现象还是挺多的,不妨将“妙套”作为求乎其上的高标准,而将“着迹”视为一般的要求,只要不过于生搬硬套、文不对题,还是可以接受的。
2.3 应景与应情
怡红院内一边种数丛芭蕉,另一边种一棵西府海棠。众清客先题“蕉鹤”,后题“崇光泛彩”。前者“蕉鹤”中的芭蕉、仙鹤乃文人诗画中常见主题,芭蕉关照了院中那“数本芭蕉”,仙鹤喻长寿、闲适,但院中没有养鹤,用在这里略显硬套;后者“崇光泛彩”关照那“一棵西府海棠”,典出苏轼《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之句,意谓海棠流溢出红艳之光。这两个题名,一个对应绿的芭蕉,一个对应红的海棠,单用哪一个都不能概括院中的实景,所谓“有蕉无棠不可,有棠无蕉更不可”,是以贾宝玉题为“红香绿玉”,这就叫应景,即对所题园景的恰道关照。后因“红香绿玉”显得女儿气,被元春改为“怡红快绿”,意思一样,仍是两不偏爱地照应实景。
点题除了应景,还要应情。这里的情,不是感情,而是事情与情形。林黛玉居住的潇湘馆,最大特点就是竹子多。众清客为之点题为“淇水遗风”和“睢园雅迹”,这里,“淇水”典出《诗经·淇奥》中的“绿竹猗猗”“绿竹青青”“绿竹如箦”等句,“睢园”为汉梁孝王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的菟园,枚乘《梁王菟园赋》中有“修竹檀栾”之句。可见,这两个题名都贴合这里竹林茂密的特点,按说还是比较应景的,但是均被贾政批评为“俗”,究其原因,在于这两个典用得陈旧无新意。贾宝玉认为,这里将会是元春省亲时第一个游幸的地方,“必须颂圣方可”,因此点题为“有凤来仪”。这一题名,典出自《尚书·益稷》中“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一则凤凰以竹为食,暗合此处的竹景;二则凤凰又是后妃象征,符合元春的身份;三则“来仪”意为“来归”,切合元春省亲回娘家的本事,正可谓不落俗套,既应景又应情。
3 以意造景:中国园林的经典母题
除了循景点题之外,中国园林还有以意造景的情况。以意造景,简单理解就是按照诗文或绘画来造园,将纸上二维虚景转换为立体三维实景。以大观园为例,20世纪80年代,上海和北京等地便运用中国传统造园手法,将曹雪芹的纸上园林变成了实景园林。又如,承德避暑山庄山岳区“有真意轩”,取意陶渊明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之意,“食蔗居”用了顾恺之食甘蔗,从梢端往尾端越吃越甜“渐入佳境”的典。苏州拙政园“兰雪堂”,取李白“独立天地间,清风洒兰雪”诗意,“与谁同坐轩”取苏轼“与谁同坐,清风明月我”诗意。这些园林或园景,将原来只存在于诗文中的虚景变成现实的可游可居的实景,化“诗意”为“园境”,园境与诗境合二为一。以意造景,正是中国园林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园林被誉“凝固的诗”的根源所在。在以意造景实践中,中国园林形成了一些常见的经典母题。
3.1 桃花源
东晋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述了一个既有良田、美池、桑竹,又远离政治、没有纷扰、人际和谐的理想空间,人可在无意之间误入,却在有意前往时不得路径,从而激发人的无限向往,成为历代文人不断追寻的地方[17]。在陶渊明笔下,桃花源本是一处由溪流、桃花林、山中小口等具有隐喻性特征的隔绝之境,在后世不断追寻中,这片绝域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简单来说,南朝和隋唐时期,人们所追寻的是桃花源的隐域仙境,宋元时期桃花源回归人间,成为文人批判现实的一面镜子和补偿心灵的一弯港湾,明清时期因世俗生活的高度发达,文人将桃花源实体化,成为世俗生活的一部分。隐域仙境之桃花源是想象的虚幻之地,镜子与港湾之桃花源是现实世界的投影与反射,实体化之桃花源则是尘世汪洋之中的一座安乐岛。但无论如何,桃花源始终与普通的现实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也正是这种距离感,成为古往今来人们不断追寻的动力源泉。
实体化的桃花源,其实就是园林。苏州留园西部景区有一座黄石假山,极富山林自然之趣,山上设有“至乐”“舒啸”二亭;山南布置蜿蜒小溪,两岸植桃柳,溪尽头在廊壁上题点“缘溪行”三字;山北又有“小桃坞”,阴翳成林,与小溪遥相呼应。这里,除了“至乐亭”外,其余点题皆出自陶渊明诗文:“舒啸”出自《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之句;“缘溪行”是将《桃花源记》中的“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的文字实景化;“小桃坞”为一座外观小巧轻盈的小屋,旁植桃李,更是直接点题。无独有偶,苏州另有一处更为著名的桃花坞,明代唐寅在此筑桃花庵,写有著名的《桃花庵歌》。清代圆明园中亦有桃花坞,是雍正时期的初名,乾隆时期改名为“武陵春色”,便是著名圆明园四十景之一。
3.2 濠濮间
《庄子·秋水》记载了庄子与惠子的濠梁之辩,体现了二人完全不同的认知方式,庄子以审美观察事物,将人的主观感受投射到鱼身上,故有移情之同感,惠子则以逻辑分析对象,从认识活动上作推理判断,故对庄子表示怀疑。在庄子那里,人在濠梁自乐,鱼在水中自乐,两者同为“一片天机”,因此可以相通相感,这种通过直觉领悟,从鱼的悠游姿态之中感受到鱼的快乐,成为中国传统审美的基本模式[18]。《秋水》另有一则记载庄子钓于濮水的典故,说的是楚王派人请庄子做官,庄子表示宁愿做“曳尾涂中”的活龟,而不愿做贡在庙堂的死龟。这两则故事,在《世说新语》中被糅合为“濠濮间想”,道:“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19]晋简文帝对山水的“会心”,实际是体悟到了庄子在濠上与濮水的快乐自由,表达了人与自然亲近通体的状态。
濠濮间想与濠梁观鱼为中国园林常见主题。承德避暑山庄康熙三十六景之中便有“濠濮间想”,在澄湖北岸,为一座八角亭,东邻莺啭乔木,西接水流云在,人置身其间,颇能感受自得其乐的自然意趣。北京西苑三海之北海亦有“濠濮间”,在北海东岸小土山的北端,为一间临河石柱敞厅。苏州留园中有“濠濮亭”,位于中部水池,为一座四角方亭,三面临水,下部叠石而空悬,正是观鱼佳处。此外,以观鱼知鱼为主题的造景更多,如避暑山庄有石矶观鱼、知鱼矶,颐和园有知鱼桥,西苑三海之南海有鱼乐亭,圆明园有知鱼亭,香山静宜园有知乐濠,无锡寄畅园有知鱼槛,苏州沧浪亭有观鱼亭,等等。
3.3 沧浪水
《孟子·离娄上》记载了一段孔子听到的孺子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20]《楚辞·渔父》亦记载了渔父对屈原唱的同样的歌词。歌词大意是说水清可以洗冠缨,水浊只可以洗脚,引申为水之所以受到人的不同对待,是因水自身的清浊所自取的,后被用来形容人对不同对象(清君与昏君、清世与浊世)的不同态度。中国园林作为中唐以后文人的主要隐逸场所,常常以此造景,隐喻文人对朝政的看法,时局清明时出仕,时局混浊时归隐。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苏州沧浪亭,园主苏舜钦本是进奏院监官,因卖掉积存的旧文书充作费用宴请宾客而被削职为民。按理说,苏舜钦卖旧文书固然有错,但罪不至除名,但由于他是改革派范仲淹的亲信,反对派便把他视为打击目标[21]。苏舜钦的“奏邸之狱”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时期,是当时朝政的一个侧影。胸怀大志又才华横溢的苏舜钦流寓苏州时,一直愤懑不平,沧浪亭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营建的,正是苏舜钦对时局与朝政看法的一种表达。
需要指出的是,沧浪水作为主题造景,多出现在私家园林,除了沧浪亭外,其他如拙政园和留园均有“小沧浪”,网师园还有“濯缨水阁”,其用意基本相同。但是“沧浪水”在皇家园林中基本没有用过,大概没有哪位帝王愿意承认自己的统治乃“浊政”吧?
3.4 芭蕉雨
芭蕉是中国园林中常见的造景植物。唐代岑参有“雨滴芭蕉赤,霜催橘子黄”诗句,大约是最早的“雨打芭蕉”吟咏。中唐两宋时期,韩愈、白居易、杜牧、皮日休、李煜、苏辙、杨万里等名家都描写过雨打芭蕉。这些诗人笔下的芭蕉雨,多为离别相思愁苦的象征,如唐代杜牧《芭蕉》诗:“芭蕉为雨移,故向窗前种。怜渠点滴声,留得归乡梦。梦远莫归乡,觉来一翻动。”这里的芭蕉雨,“似杂鲛人之泣泪”(计成),与梧桐雨、残荷雨一样,雨中带愁,正是中唐之后士人心灵内敛与精致化后的产物。雨打芭蕉又能产生清新愉悦之感,如南宋方岳《过李季子丈》诗:“春晚有诗供杖展,日长无事乐锄耕。家风终与常人别,只听芭蕉滴雨声。”呈现出诗人的优雅闲适之趣。无论是离别相思,还是优雅闲适,“雨打芭蕉”以其丰富的文化意象[22],成为中国园林的常见母题。
在窗前檐下,与山石配合,栽植三五株芭蕉,是最为常见的蕉雨造景模式。此外,在园林中构建专门的“听雨轩”“蕉雨轩”“蕉雨亭”,以观蕉听雨,也是芭蕉雨的一种造景模式。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苏州拙政园中的“听雨轩”:轩前一泓清水,池边有芭蕉、翠竹,轩后也种植一丛芭蕉,前后相映。
3.5 疏影梅
中国的梅文化源远流长。先秦诗歌总集《诗经》中有多首提及梅,汉武帝建上林苑时有从各地进献的7种梅。魏晋南北朝时期,梅花的先春而发、花香色白的形象受到关注,乐府横吹曲“梅花落”颇为流行,表达了一种韶华易逝的忧伤心绪。唐代之后,梅花的形象从单纯的惊时伤情,提升为更为广阔的社会与人生之思,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杜牧、李商隐等都有咏梅之作。宋元时期,梅花突破姿色之自然形态,成为闲静高雅、坚贞不屈的人格象征[23],乃至被尊为花中极品,咏梅、画梅的诗人与画家不胜枚举,像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千古名句,仲仁开创禅意十足的墨梅文人画,元代王冕的《墨梅图》题诗“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直接以梅花比喻气节。明清时期,梅花成为文人生活的必不可少的雅物,“书窗梅影”“梅屋弹琴”“踏雪寻梅”“月下种梅”“梅边读易”“梅花泛酒”等等,为诗词常见主题。
中国园林中以梅造景的例子颇多。宋徽宗艮岳中有在山岭植梅万本的“梅岭”,有在池边栽梅的“梅池”,还有在水中陆地植梅的“梅渚”。杭州西湖孤山为林逋隐居之地,林逋在此写有著名的“孤山八梅”,林逋死后,“孤山梅花”成为西湖一景。今苏州狮子林有“问梅阁”和“暗香疏影楼”,亦均是以梅为母题的造景佳例:问梅阁背靠狮子林西墙,地势较高,阁外植梅数株,阁中有“绮窗春汛”额,典出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暗香疏影楼在狮子林西北,楼前有山石、梅花和池水,正是林逋诗句的实景呈现。
4 余论
一般而言,中国园林所表达的内容大体有三层:第一层是景象,即人能直观感受到的山石、水体、植物、建筑等实体要素,属于感官感知;第二层是意象,是实体要素以一定手法所形成,需要一定审美眼光才能感受的诗情画意,属于审美感知;第三层是意境,是诗情画意背后的文心,也即人对人生、社会、宇宙的诗意表述与深度思考,属于哲学感知。这里,第二、三层审美与哲思背后的诗情、画意、文心,正是中国园林的灵魂所在。诗情、画意与文心的主体,是中国传统的士人。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希望处在庙堂之上实现济天下的理想,又不愿丧失独立精神和道德旨趣,而处在江湖之远保持人格空间。于是,在庙堂与江湖之间,他们选择了园林作为最后归处。所谓“此心安处是吾乡”,园林成为士人越来越倚重的心灵家园,他们将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外化为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花木鸟鱼等现实景象。这一“外化”的过程其实就是造园的过程,中国园林的立意结构、循景点题和以意造景正是围绕着上述目的而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