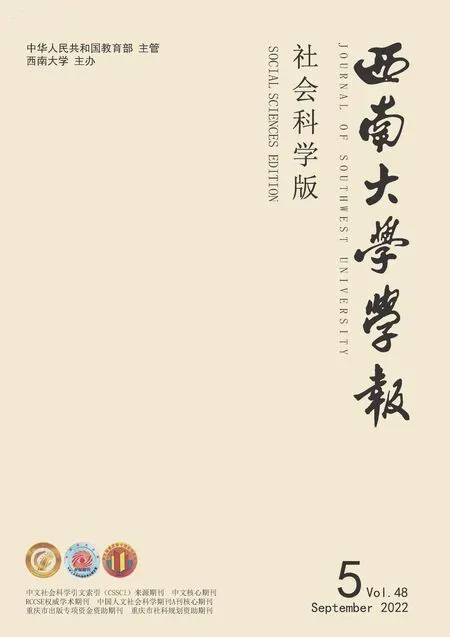明代中枢政体的演进与反思
——以“权臣论”为视角
李 佳
(吉林大学 文学院中国史系,吉林 长春,130012)
翻阅明代的史料,可以看到许多关涉权臣问题的讨论。这些权臣论以批评权臣乱政祸国为主要话语形态,也包括权臣与逆臣、重臣之辨析等内容,集中表达出明人对本朝中枢政治体制变化的关注。在明人语境中,权臣的指称对象主要为阁臣与宦官,尤其是明中期以降,那些关于阁臣的批评与阁臣的辩白之词纷纭而出,逐渐演化为一种含义深刻的政治舆论。本文澄清明代中枢政体的样貌,以内阁政治的演进为主要线索,故将讨论对象集中于阁臣,以期对明代中枢政体的变迁轨迹及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1-2]
一、明人权臣论溯源:洪武废相的理论依据
明人关于权臣的论说发端于元末明初。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发布《北伐檄文》,云:“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3]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在立国之初,就承认元朝统治者的正统地位,由此引申出的问题是:应该如何阐释元政权的败亡缘由?在这篇《北伐檄文》中,朱元璋提及元朝“宰相专权”[3]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的问题,但是并没有展开讨论。此后,朱元璋又谈及权臣对元末政局的负面影响,如朱元璋云:“元政不纲,权臣窃命于内,守将擅兵于外,是致干戈鼎沸,国势日危。”[3]卷32,洪武元年五月戊辰
洪武三年(1370)十二月,儒士严礼上疏建议朱元璋重视中书省的作用。朱元璋阅览严礼的奏疏后,就元朝得天下与失天下问题与侍臣展开如下对话:
或言:“世祖君贤臣忠以得之,后世君暗臣谀以失之”;或言:“世祖能用贤而得之,后世不能用贤而失之”;或言:“世祖好节俭而得之,后世尚奢侈而失之”。上曰:“汝等所言皆未得其要,夫元氏之有天下,固由世祖之雄武,而其亡也,由委任权臣,上下蒙蔽故也。今礼所言不得隔越中书奏事,此正元之大弊,人君不能躬览庶政,故大臣得以专权自恣。今创业之初,正当使下情通达于上,而犹欲效之,可乎?”[3]卷59,洪武三年十二月己巳
在上述引文中,朱元璋其实并未清晰说明臣下掌权到何种程度方为“权臣”,但是显然对拥有检视百官奏疏权力的中书省官员充满戒防心理。朱元璋批评秦朝设相之事,云:“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君国者。”[4]卷10,《敕问文学之士》
朱元璋在洪武初年采取各种制度措施,弱化丞相在国家中枢政体中的影响力,努力实现如下君臣关系格局,“上下相维,小大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3]卷110,洪武九年十月戊寅。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诛杀中书省仅存的一位主官胡惟庸,随后颁诏废除延续千余年之久的宰相制度,诏曰:
朕尝发号施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废兴。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紊烦。[3]卷129,洪武十三年正月癸卯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将罢相不设的思想写入《皇明祖训》首章,要求后世子孙不得恢复宰相制度。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5]卷2,《皇明祖训》。
洪武时期,朱元璋驭下严苛,百官人人自危,爬梳洪武时期的朝野士人文集,几乎看不到针对朱元璋权臣祸国论的批评意见。建文帝继位后,此时朱元璋已经去世,在一些士论中隐晦地出现反思洪武权臣祸国论的声音。如方孝孺云:“宰相之职,上有以格君,下有以足民,使贤才列乎位,教化行乎时,风俗美于天下,伦理正而礼乐兴,中国尊而夷狄服,有生之伦各遂其性,而无乖戾斗争,则可为尽职矣。”[6]卷5,《丙吉》又云:“宰相之功业视人主,人主善任相,虽中才亦足以为治,不能任相,虽俊杰不能以成功。”[6]卷5,《黄霸》在方孝孺的观念中,宰相的存在对国家有重要的意义,这种思路明显与朱元璋之权臣祸国论存在差异。方孝孺深得建文帝信任,士大夫政治的声势渐起,然建文帝旋即被朱棣推翻,方孝孺不降新主,杀身成仁。
总体来看,朱元璋认定具有检视奏疏权的中书省官员乱政祸国,这构成一种解说元末政局何以趋乱的意见。以权臣祸国论为主要理论依据,朱元璋诛杀丞相胡惟庸,并废除宰相制度,明代中枢政体由是出现了重大变革。此后经由《皇明祖训》的倡导,朱元璋所阐释的权臣祸国论成为一种官方推崇的政治理念,影响深远。还需要注意的是,以方孝孺为代表的一些士大夫从正面论述宰相,或者百官领袖人物之于国家的积极意义。方孝孺宁死不降新主的做法,不仅挫抑了朱棣的权威,也构成针对朱元璋权臣祸国论的挑战,并又与之纠缠浸润,逐渐稳定为一种内涵复杂的王朝早期历史记忆,成为随后二百余年间影响中枢政体演进的重要因素。
二、明中期以降权臣论:针对阁臣的批评
在废除宰相制度之后,朱元璋先后尝试了多种辅政制度,如设立殿阁大学士。这一制度在建文与永乐时期得以沿袭,尤其是成祖选任亲信之官入值殿阁,迅速形成了一个辅政群体,仁宗与宣宗时期,殿阁大学士辅政这一体制趋向稳定,并在英宗时期,创立阁臣“票拟”理政方式。“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阁老杨荣等虑圣体易倦,因创权制:每一早朝,止许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封诣阁下,豫以各事处分陈上。遇奏,止依所陈传旨而已。”[7]卷1,《早朝奏事》至此可以看到,从明初朱元璋废除有权检视百官奏疏的中书省,再到英宗初年,阁臣具有票拟百官奏疏的权力,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英宗“止依所陈传旨而已”,明代中枢政体已经出现重要变化。
照应内阁在中枢政体中地位上升这一趋势,明人关于权臣的议论越来越多地集中于阁臣群体,其中,尤以嘉靖以降内阁首辅受到批评最多,下文以严嵩、高拱、张居正三人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
嘉靖三十二年(1553),兵部主事杨继盛批评内阁首辅严嵩类相,云:“高皇帝罢丞相,设立殿阁之臣,备顾问视制草而已,嵩乃俨然以丞相自居。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无丞相名,而有丞相权。”[8]卷209,《杨继盛传》
隆庆六年,户科给事中曹大埜批评高拱权重,云:“昔日严嵩止是总理阁事,未尝兼吏部之权。今拱久掌吏部不肯辞退,故用舍予夺皆在其掌握中,升黜去留惟其所欲。在外抚按之举刺不计,在朝之清议不恤,故其权之重过于嵩,而其引用匪人,排斥善类甚于嵩。”[9]卷68,隆庆六年三月己酉神宗继位后,两宫太后听取了张居正、冯保等人的意见,贬黜高拱,皇太后懿旨云:
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着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幼主?姑且不究,今后都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10]卷44,《病榻遗言》
万历四年(1576),御史刘台批评张居正类相,云:
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8]卷229,《刘台传》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此后不久神宗转而支持了那些“权臣”的批评,亲自下旨给张居正定罪,罪名为“诬蔑亲藩,侵夺王坟、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聪,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11]卷152,万历十二年八月丙辰。
翻检明人文献,可见大量将阁臣指斥为权臣的论说,如上文言及严嵩、高拱与张居正事例。这些言论其实蕴含着明人对本朝相制之废,乃至内阁政治演进的认识。于此引申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明中期以降,何以“类相”成为阁臣的一种罪名。相对明初殿阁大学士而言,明中期以降的阁臣是否具有了此前没有的某种权力,在何种意义上影响了中枢政体的变化?兹从以下三方面回答上述问题:
第一,“废相”历史记忆与首辅“类相”之间的冲突。权臣之名古已有之,此中值得关注的是,在明中期以降的士人语境中,权臣与权相二语往往并出,换而言之,类相成为近于权臣的罪名。这种判定实际上延续了朱元璋权臣祸国论的思路,每当内阁首辅势起势大之时,往往就会招致舆论责难。严嵩、高拱与张居正三人是否存有贪腐之事暂且勿论,毋庸置疑地是,三人确有一些近于“宰相”的迹象,如张居正为首辅期间,“太后以帝冲年,尊礼居正甚,至同列吕调阳莫敢异同。及吏部左侍郎张四维入,恂恂若属吏,不敢以僚自处”[8]卷213,《张居正传》。在一些士人的语境中,“相”成为了一个近似于“权臣”的代名词,这是明代中后期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
第二,皇帝决策权与阁臣票拟议政权的部分重叠。相对前代而言,朱元璋主导设计的中枢政治体制尤为推重皇权,诸般政务皆由皇帝乾纲独断。自仁宣以降,内阁的政治地位获得极大提升,至英宗时,三杨内阁以票拟形式处理日常政务,再至严嵩、高拱、张居正任内阁首辅时期,诸人于官员任免、迁转等方面的意见多被皇帝直接采纳,渐渐显现出如下态势:首辅所拥有之票拟议政权与皇帝之决策权经常性地重合。
杨继盛批评严嵩云:
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报曰:“我票本荐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此人不亲附于我,故票本罢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报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罚一人,嵩又扬言于众曰:“此人得罪于我,故票本报之”;凡少有得罪于嵩者,虽小心躲避,嵩亦寻别本带出旨意,报复陷害。是嵩窃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罚以彰己之威,所以群臣感嵩之惠甚于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于畏皇上之罚也。[12]卷293,《早诛奸险巧倿贼臣疏》
刘台批评张居正云:
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8]卷229,《刘台传》
在杨继盛与刘台的权臣论中,可见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恰恰反映出阁臣票拟权的实际影响力。且严嵩、张居正诸人又有抑制言路监督的诸般举动,个人操守方面亦不免有疵,这些内容汇聚一处,引发了一些士大夫的反感,于是,将他们指斥为权臣的论说纷纭而出。就中枢政体变迁的视角来看,明中期以降的权臣论其实照应了内阁票拟议政权效能扩大的现象,其背后是一种关于皇帝决策权被部分侵夺的担忧。
第三,内阁对府、部、院的影响渐成“统辖”之势。朱元璋废相后,设五府、六部、都察院分理政务。杨继盛批评严嵩为首辅时,“凡府、部题覆,先面白而后草奏。百官请命,奔走直房如市”;曹大埜批评高拱以阁臣身份“兼吏部之权”;刘台批评张居正改变了太祖时期所定“事归部院,势不相摄”的体制。上述这些权臣论其实理路相通,采用近乎一致的话语形态勾勒出不同时期的“权臣”形象,此中实质问题指向阁部权力分属问题。更为确切地说,杨继盛、曹大埜与刘台皆认为内阁已经具备了对其他行政部门的统辖性影响力,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对太祖时期中枢政体的一种逆反。
综上所述,明中期以降针对阁臣而起的权臣论活跃,在一些士人语境中,类“相”则类“权臣”,这是明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现象。此中或不免于人事之争,不免于意气用事,亦可能参杂许多名利纷扰。但是却反映出,相对于明太祖时期的中枢政体而言,一些时段的内阁以票拟方式深度介入国家政治运作,对六部等行政机构的影响力形成统辖之势。由此言之,权臣论虽然围绕阁臣而起,却也是明中期以降中枢政体发生微妙变化的一种舆论投射。
三、阁臣的自叙:“臣本无权”
明中期以降,阁臣往往受到“权臣”的指责,那么,他们又是如何应对此类批评的呢?换而言之,处身本朝法定“无相”的中枢政治框架中,阁臣如何定位自身的政治角色呢?
正德时,武宗宠信宦官,屡屡逾越礼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外瞩目内阁,杨廷和表达了阁臣无宰相之权的困境。“昔吕端之锁王继恩,李迪之制八大王,韩琦之叱允弼,皆事权专而委任重,所以能办。我朝内阁无宰相之权,予辈任此亦难矣。”[13]卷4,《视草余录》
万历六年(1578),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权,张居正上疏辩解,云:
唐贞观时,有劝太宗揽权,不宜委政房玄龄等者。太宗曰:“此欲离间我君臣也”,立命徙之。今用汲之意实类于此,然此可以惑庸暗之君,不可以欺明哲之主也。夫自古惟明王圣主乃能择贤而属任之,非庸君暗主之所能也。三五之隆,不可殚举。成汤圣君也,其于伊尹乃学焉,而后臣之。高宗长主也,拔傅说于胥靡,一旦命总百官,而属之曰:“汝为舟楫,汝为霖雨”,其倚任之重如此然。成汤、高宗不以其故贬王,而功业之隆,照耀史册,垂宪千古……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得人,故信任贤臣者,正所谓揽权也。岂必若秦始皇之衡石程书,刚愎自用,隋文帝之猜忌任察,谗害忠良,而后谓之有权耶?若夫庸君暗主,则明不足以知贤,而信不足以使下,虽奉之以太阿之柄,彼亦不能持也。[14]卷43,《乞鉴别忠邪以定国是疏》
在与友人的信札中,张居正云:“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专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阴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宸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14]卷28,《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万历中期以后,朝野对阁臣的指责愈发频繁,阁臣举步维艰,这种政治角色的困境在万历、天启朝阁臣叶向高身上最清晰。叶向高云:
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则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败名辱,旦夕去国,无所复言,尚望后来者有所斡旋匡济,以为此官生色。尤望皇上用其人必听从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复如臣之虚拘,则天下之幸也。[11]卷511,万历四十一年八月庚寅
于此,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权臣”之名既构成中、下级官员批评阁臣的话语形态,也成为阁臣自解时的一种推托之词,在叶向高看来,阁臣的原罪其实在于身居“无权之官”,却被冀望做“有权之事”。换而言之,阁臣往往难逃“权臣”所指,主要原因在于内阁在中枢政体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明代阁臣之“无权”自叙可分为两类来看:一类以杨廷和、张居正为代表,他们言说的“无权”,虽亦有戒惧“权臣”之名情绪的流露,但其实暗含着对权力的诉求之意。如杨廷和强调阁臣缺乏足够的法定权力制约宦官,显然认为这是一种不合理的权力关系格局。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有过如下记载:“江陵以天下为己任,客有谀其相业者,辄曰:‘我非相,乃摄也’。”[15]卷9,《三诏亭》于此,可以看出张居正对自身掌控较大权力是有充分认知的,那些“无权”的自叙,是一种需要公之于众的姿态而已;一类以叶向高为代表,万历中期以降阁臣对政局的影响力与杨廷和、张居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叶向高云:“今之阁臣非复往日之阁臣也,事权、气力大较可知,譬如荒祠土偶像,设虽存久,已不能为人祸福。”[16]卷17,《请补阁臣第五十一疏》此类“无权”的自叙,其实是阁臣一种本来无权,当然无责的自解之词。明人云:“万历初年,权相勾珰擅政,天下股栗,盛满不戒,卒受诛灭之祸。嗣是宵人观望,于是一切变为侧媚。”[12]卷469,《朝政因循可虑辅臣单匮难支疏》
那么,在自叙无权的阁臣群体中,有若张居正者位近于“摄”,亦有若叶向高者,自嘲为“荒堂土偶像”。此中虽不无言语夸张之处,但亦可由此体察晚明阁臣位势变化情状。何以同为阁臣,却有此种区别?明末士人曾大奇言:“殿阁之臣名预机务,造膝陈谟,备畴咨而不闻张目吐胆,能进一贤拔一才者,何耶?上之不信耶,殿阁之自无权耶!”[17]卷上,《辅臣议》缘何君不信臣?曾大奇言:“呜呼!人主之心,不过忌臣下之得权耳。”[17]卷上,《辅臣议》从某种意义而言,明初以降诸帝未必笃信太祖权臣祸国论,但是在阁臣权力增大时,却一再用“权臣”之名打压了内阁的上升势头,此为张居正身后阁权骤然滑落主要致因。总体来看,明代内阁政治虽然在中枢政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引发了前文引述之刘台等人的批评,但是阁臣票拟权产生何种效能,能否形成内阁之于其他行政部门统辖局面,始终不免于权臣祸国论的影响。
四、明代中枢政体的演进与反思
明人的权臣论,起于元明之交,构成太祖废相的重要原因,亦构成随后内阁政治演进的重要舆论环境。进而言之,权臣论视野下的明代中枢政体展现出特有的律动模式。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明人权臣论不尽是批评阁臣之词,亦有一些讨论涉及权臣与逆臣、重臣之辨,乃至士人群体内部分权任事之说,这些内容构成明人反思本朝中枢政体的重要意见。
(一)明代政治中枢制度的演进
第一阶段,明初权臣论与无相政治框架的构建。元明之际,朱元璋认为元朝败亡的原因是权臣祸国,这种论说成为其阐释新生政权合法性的一种话语工具,又构成其调整本朝中枢政体的理论基础。为解决废相后行政中枢乏人辅理政事的问题,殿阁大学士制度应时而生,这构成明代内阁政治的源头。此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士大夫虽然质疑“无相”之事,但是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太祖时期确定的中枢政体基本框架。
第二阶段,明中期权臣论视野下内阁政治的浮沉。在建文帝至仁宣时期,权臣论其实隐而不显,阁臣在中枢政治运转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明中期以降,将阁臣比附为宰相的论说纷纭而出。“内阁密勿之地,寄以机务……百余年来政治枢要实在于此,旧制虽不设丞相,而世以宰相称之。”[18]卷9,《机务》这些言论的出现,其实从侧面反映出明代内阁政治获得了超越此前的发展。至张居正时,阁臣权力发展至顶峰。但是神宗在张居正死后的做法,确切地说,张居正所得“权臣”之名重挫了明代内阁政治的上升势头。
第三阶段,明晚期权臣论与内阁政治的末路。至明末,国事江河日下,将阁臣指责为权臣的话语愈发活跃,清人论及晚明群臣好攻讦之事,云:“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8]卷229,《赵用贤传》从某种意义上言之,后张居正时代的君臣权力关系格局显然失序,从神宗有意纵容中下级官员批评张居正,坐成其“权臣”之名,推演至万历中期以降,随着中下级官员与阁臣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内阁政治亦趋于失能。
(二)对明代中枢政体的反思
晚明国事不济,朝野上下呼吁大臣救国的声音渐起,在这种舆论背景中,权臣祸国的论说,乃至本朝中枢政体成为被反思的对象。
第一,权臣与逆臣之辨。对于张居正的“权臣”罪名,其实士大夫群体内部亦有不同声音。赵锦云:“居正诚擅权,非有异志。”[8]卷210,《赵锦传》“公(陆光祖)毅然曰:‘江陵权臣也,非逆臣也,且使端揆之地而汙此名,何以示后’?当是时,公卿之有远识者皆心服公。”[19]卷36,《太宰五台陆公七十叙》赵、陆二人所论,其实都在述说张居正虽有较大的权势,但是绝没有走到意欲颠覆皇权的地步。事实上,明后期任事阁臣如徐阶、张居正,皆强调加强皇帝的权威,徐阶题词壁上云:“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20]卷5,《徐阶》《明史》云:“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8]卷213,《张居正》崇祯时,甚至出现选任阁臣以张居正为参考的声音:“神庙初年,江陵柄政,凡民生、国计、吏治、边防综理精明。虽事嫌刻核,元气微伤,而廊庙、边疆皆有精明强固之象,则以江陵不徇情面,惟责成功。故至今谈相才者,不能不追思之也。”[21]卷9,崇祯元年五月甲子总体来看,阁臣有权未必为乱的这一类论说,是对太祖权臣祸国论的一种反思意见。
第二,权臣与重臣之辨。在明人的权臣论中,有一些涉及重臣的讨论,核心问题为权臣与重臣关系如何?陈懿典,万历二十年进士,云:“大臣可以行重臣之事,而不必避权臣之名。”[22]卷20,《拟正人心定国是疏》倪应春,万历三十五年进士,言:“(苏辙)语曰:‘权臣不可有,重臣不可无’。噫,非权而何以称重乎?愿皇上予之以权,丝纶无从中降,阁臣善用其权,意念绝无旁落,明良久而德业成,岂不猗欤休哉!”[23]卷2,《九日癸未》上述士论的要旨在于:大臣得权方能任事,因此而论,构建一个可能赋予大臣权力的政治制度体系,其实构成培育重臣的必要条件。这种观念显然与太祖权臣祸国论存在抵牾。
第三,阁、部与科道分权分责说。在上述权臣与重臣之辨中,其实已经涉及重视阁权的问题。至晚明,针对君臣权力分配,乃至百官职权问题,张纳陛与刘宗周的讨论颇有代表性。张纳陛,万历十七年进士,曾任礼部主事等官,言:“国之大权有三:曰内阁,曰铨曹,曰台谏。内阁者,无专任有独权,预制是非予夺而与天下公者也;铨臣者,采天下是非以予夺天下者;台谏者,持天下公是公非而赞予夺于铨曹者也。”[24]卷6,《邪官巧迎当路阴中受事铨臣疏》在张纳陛勾画的中枢政体蓝图中,内阁、吏部与科道三者各有权责,尤其强调内阁的“独权”,事之是非应取决于天下公论。天启时,蕺山先生刘宗周言:“以票拟归阁臣,以庶政归部、院,以献可替否予言官。”[8]卷255《刘宗周传》刘宗周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中枢政体的安排当实现诸部门分责任事的思路,与张纳陛有相通之处。总体来看,张、刘二人之论显然突破了明太祖时期设计的中枢制度体系,他们承认,并以列在首位的方式强调了内阁权力存在的合理性,冀望构建一个阁权、部权与科道权并重的中枢政体模式。
综上所述,明太祖朱元璋秉持权臣祸国理念,以此作为阐释元朝何以败亡的原因,亦以此作为废除宰相制度的理论依据。明中期以后,将阁臣指斥为“权臣”的批评与阁臣“无权”的自叙纷纭而出,内阁政治的发展始终受制于权臣祸国论。总体来看,权臣论视野下的明代中枢政体经历了如下律动诸阶段:其一,明初废相;其二,明中期内阁权力浮沉;其三,明后期内阁权力萎缩,趋于失能。晚明国事艰难,部分士大夫主张重视阁权,培育有权之重臣,追求实现内阁、六部与科道分权分责的政治局面,此类呼吁构成权臣论视野下士大夫群体对本朝中枢政体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