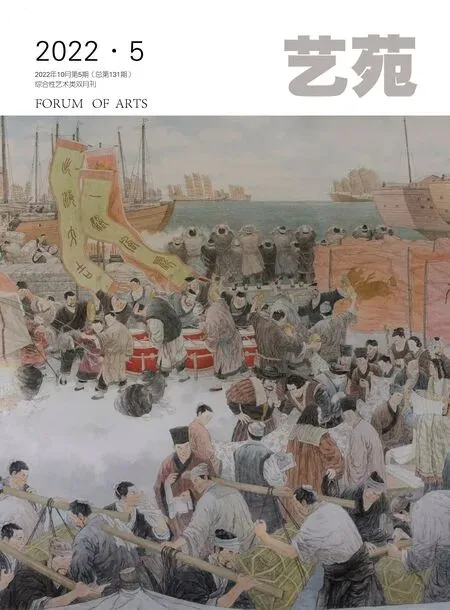基于电子界面的想象
——论数码屏幕影像的观看机制
廖晓宇 潘可武
按照法国电影学者安德烈·戈德罗(André Gaudreault)与菲利普·马里恩(Philippe Marion)的说法,数字媒介的出现带来了电影的第八次死亡。[1]16在数字转折的背景下,电影的死亡预言更多的是指电影失去了它的银幕地位、媒介特性或是文化优势,而不是媒介和产品本身的消亡。由于失去了其本身的独特性,如它的固定装置(胶片、放映机、银幕、黑暗影院等),又获得了其他图像媒介的标准,电影逐渐走向自身边界的不确定性。一方面,面对笼统而混杂的“后电影状态”,电影重新回到自己的传统领域之中。经典电影定义的空间-技术-叙事边界被重新把握,强调电影场域的纯洁性以及“电影状态”在非日常状态下的主体效果。[2]85-92另一方面,比起反复重申的特性,电影转向基于对变化和差异的接受,不再将自身设定为一个封闭的存在。在这场冲破其工业、媒介、叙事和体验边界的运动中,电影没有走向削弱,而是超越和重生。放在一种同时代的特殊经验中来看,我们所遭遇的并非是滞后话语给行为设定的基本范围,即“这样做了才能称之为看电影”。更多的是,“看电影,无论在哪”的这种现象已经来到我们身边并且实实在在影响了我们。
数字时代的影像呈现出一种移动和分散的状态,不断扩展到其传统的装置和环境之外,因此变得随处可见。影像在电影院内、电视机上、平板电脑里,还有随身携带的手机中。这些设备不仅能收看各种丰富精彩的影像类型,并且都支持播放同一个影像。弗朗西斯科·卡塞蒂用“移置”(relocation)一次来概括电影向其他设备和其他环境移动的过程。他认为,电影在“移置”中保证了电影经验的延续,“由于一种新的支持或新的设备——一种经验在其他地方重生,而以前的媒介的生命,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完整性继续存在”[3]28,从而把电影从它的死亡魔咒中解救出来。在观众一边选择观看哪部电影,一边选择在何处、以何种设备观看的过程中,电影体验的“是什么”和“如何”之间的深刻裂痕被标记出来。正如卡塞蒂所言,电影不再是完整、固定和预设的一种东西,“电影变成了电影对象和观看电影的方式两种东西”[3]54。
在此前提下,电影影像的一组“不变与变”浮现出来:不变的是不触碰任何媒介的影像作品本身以及纯粹的“观看”行为,而变动的是所谓的观看界面以及环境空间。如今,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有四种媒体/界面:电视、电脑/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LED媒体幕墙。屏幕化的影像集中在可移动性强的便携式设备上:各种电脑与智能手机。因此,此种影像结构性地具备计算机和互联网的内在特性,它与眼睛的交叉点就是不可或缺的“界面”——一块自发光的屏幕。屏幕影像的观看并不是直接的、自然的“看”,而是基于电子界面的观看。人类在日常生活中首先面对的是以电子屏幕为中介的“界面”,然后再是艺术作品或者世界。影像通过界面呈现,或者说只有透过界面,我们才能观看影像。这样一种脱离直观感受的“界面-开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观看模式?本文以数字时代的“电子界面”切入点,从界面生成、界面缝合、观看主体三个角度探讨移动影像的观看机制。
一、界面之域:从自然生成到技术生成
我们通过所见的东西来理解世界:无阻隔地直观或者透过某些东西去看。对于自然而言,人类的习惯是一种直接观看。无论是可触碰的树木还是难以触碰的云朵,人与物之间并没有另一个人造物的阻隔(眼镜颇为例外,可以看做是维持视线的透明性工具),人眼看到的就是事物呈现出的样子。在艺术领域,人类从来就无法做到直接观看,无论是绘画、雕塑,还是电影、电视、手持设备,如果没有另外一个人造物作为中介,艺术品则无法呈现给我们。因此,这个“人造物”就是界面。界面大多数时候呈现为屏幕,而屏幕“是一扇‘虚拟之窗’,改变了既有空间的物质性,加入新的视孔,大大改变了我们有关空间乃至时间的观念”[4]192。最早的界面或许是“窗”,它框定了一个空间,使其在人脑中转化为一个二维平面的想象,由此改变了人对于窗外世界的感知。如同波德莱尔所言:“在日光下所能看到的东西,总是不如一面玻璃之后发生的事情,令人产生兴趣。”然后,是绘画的界面。文艺复兴典范画家莱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在1435年有关绘画和透视的论文《论绘画》当中提出了这个著名理论,即把绘画的方形边框“看成”一扇窗,画框就是通往世界的窗口。电影的银幕是一个经典界面,一方面继承了西方绘画中画框的特点,另一方面带来了可移动性,银幕中的图像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窗、画框、银幕,这些作为屏幕的界面通常被看作是通往更大空间的窗口,“屏幕空间通常被习惯性地理解为更广阔的图景空间(scenographic space)的一部分”[5]157。虽然屏幕空间是唯一可见的部分,但更广阔的图景实际存在于屏幕之外,外面的区域与我们身处的世界息息相关。屏幕界面中图景的生成方式或是自然、或是主观自然,或是客观现实的机械复制,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保留着客观“现实”或者自然的痕迹。
与自然生成的界面不同的是,电子屏幕的界面生成建立在深刻的技术条件上。窗、画框、银幕的界面依赖的是改造自然材料的技术,一旦这些界面生成,它们就足够生硬与确定,规定着最终的艺术呈现。当画家在画布上描下最后一笔,那么他就可以宣称这是作品的“最终定稿”。但电子界面,或曰“人机交互界面”包含着技术的先验逻辑。计算机技术使“所有媒体都被转化为可供计算机使用的数值数据”[5]88。马列维奇指出,界面的数值化呈现带来的重要结果是其中呈现的一切都变得可以被编程(programmable)了。于是,“草稿”和“定稿”之间的区别被悬置了:不再有一个“确定的文本”,因为其每一步都可以被无限地再加工。这一点很好地体现在影像的草根实践中。2009年,一位名叫凯西·普格(Casey Pugh)的美国导演要求数千名网民按照自己的创意拍摄《星球大战IV:曙光乍现》中的场景。网友们在提供的15秒短片中翻拍、模仿、恶搞原作。这一场对电影的“亵渎”实践在短短几个月内赢得了巨大的关注度,并在2010年获得了艾美奖的互动媒体杰出创意成就奖。最后,这些小片段经过剪辑,组合成了一部长达124分钟的电影,命名为《星球大战未删减版》(Star Wars Uncut: Director's Cut)。这是一部不需要正式拍摄,没有正式剧本也没有导演的电影。在赛博空间中呈现的文艺作品,不论是经典原文本,还是互联网上形形色色的衍生作品,都获得了技术生成的属性。依赖计算机技术和算法的修改与二次创作,影像的创作通常会呈现出两种版本:官方版本和衍生出的民间版本,后者包括电影解说、同人剪辑、幕后花絮等多种类型。技术赋予了每个人将现有的原材料进行二次创作的权力,通过剪辑、配音、抠像、调色等手段,大量的民间“超文本”不仅有趣,而且还有着洞察力,揭示了官方版本潜在的“被压抑”的内容,有时候甚至比官方版本更受欢迎,更加深入人心。
不存在“确定的文本”暗示了在数码屏幕影像的观看中,观看者深受算法的控制。自然或者客观现实退居其次,代数算法的力量篡改着电子界面的属性。界面不再像经典屏幕(窗、画框、银幕)所反射的那样,不可逆转也不可侵蚀。界面变得具有任意性,被赛博空间的技术“代理人”(程序、预设等)与主体(创作者、传播者、观看者)共同统治。从日常经验的释义视线出发,我们遭遇了电子交互界面所带来的第一条边界的破坏,即“‘真实生活’及其机械模拟之间:技术破坏着‘自然的’生命-现实和‘人造的’现实之间的区别”[6]163。
二、界面缝合:从客观现实到主观幻象
何谓缝合?“缝合”一词最早由拉康提出,用来说明主体生成语言意义的过程。随后,法国理论家让-皮埃尔·欧达尔(Jean Pierre Oudart)将“缝合”的概念引入电影研究当中,缝合理论逐渐在电影领域内重获生机。缝合代表着缺失感被满足的过程,一般想象的模式是将外部刻写入内部,从而抹去自身生产的踪迹,使整个领域“缝合”,生产出无需外部的自我封闭效果:生产过程的踪迹、它所包含的裂缝、它的运行机理都被抹除了,产品表现为一个自然化的有机整体。[7]74齐泽克认为,在上述观点中,缝合的功能等同于“封闭性”:“缝合表示结构的裂缝、开口被消除了,使结构能够(误)认自身为自我封闭的再现性总体。”[7]41标准缝合理论包括两个假象:一是有机整体的假象,缝合将具有差异性的外部元素刻写入内部,抹除了差异性;二是自然化的假象,缝合通过正反打镜头、连续性剪辑、180度原则、灯光等一系列标准工艺,抹去了缺席者(摄影机)的痕迹。
在影像中,当主观与客观镜头的交替无法令主体感受成一个“自然的有机整体”而指向更怪异的效果,此时一般的缝合不再起作用。这开启的是“界面”(interface)的功能。在这一层面上,界面指向呈现影像的方式,即正镜头与反打镜头在同一个镜头中凝聚。界面开启了观众在普通场面中察觉到纯然幻想的维度。界面的元缝合功能包含了幻想的反身逻辑,呈现为“A-BC(AB)”结构的镜头。首先是一个正镜头(A),观众在此刻误认为镜头内的人物是动作发出的主体。然后是一个反打镜头(B),标记动作作用对象,可以是人或物。最后正反打镜头被结合进同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既是正镜头也是反打镜头(AB),却不是他们的双重在场,而是“幻想之幻想”(C)的展现。界面缝合的理论一样可以引入数码屏幕的研究中。它同时包含着元界面与界面缝合的维度,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正反打”镜头,屏幕所呈现的内容越来越深刻地标记为一种能够感知的主观幻象,而不是虚构他者的幻象。
以界面的元缝合功能出发,我们如何推导出电子界面的“镜头结构”?无论在电子屏幕上观看何种数字化的影像,标准的正反打镜头比比皆是。比如在短视频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创作者先用自拍对准自己,讲述一番经历,这是一个正镜头(A)。然后他会将镜头翻转,朝向自己的视线对象,用来解释说明他到底看到了什么,这是反打镜头(B)。但接下来不会出现一个由创作者发出正反打镜头(C),能看到这一镜头的只能是观众。“有鉴于传统的观看情境,系假定在黑暗的戏院中,所有眼睛都注视着银幕。新媒体却是经常意味着光线充足情况下的小银幕。”[5]203观看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更为彻底的界面:在移动终端的屏幕上,会映射出“我”的脸。特别是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观看者的脸会清晰地倒映在屏幕上,屏幕原本的内容变得更像是一种不稳定的投射,躲在人脸背后的阴影中。只有在观看者主体的眼中,C(AB)镜头才得以成立。在这一镜头内,不确定的正反打镜头和观看者的镜像倒映重叠在一起,与威特·哈尔兰的《牺牲》(Opfergang,1944)中那个标准的界面缝合镜头有着构图上的相似性(图1)。观看者的镜像缩减为电子屏幕上暗边的昏暗中幻觉般的孤岛,占据了观者自身的视野,有时我们会突然注意到自己的表情,看到我们自己对于屏幕内容的反应。这种方式将缝合撕开一个裂缝,外部的不一致性刻入内部,被识别、标记出来,不再能够维持一个连续性的观看状态。由于正面镜头与反打镜头的重合(它们由“我”发出,也在表现“我”),镜头视点没有分配给任何一个影片人物,反而分裂了在场空间与屏幕内空间。因此,观看的空间无法由想象进入到象征和符号,数码屏幕影像的观看由此开启了界面的效应。

图1 《牺牲》中的界面缝合镜头
三、观看之主体:从去中心化的身体到主体化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将技术提升到关乎“人类生成”的本体论的高度,提出“后种系生成”的奇特概念:在生物种系进化完成之后,促进“人类生成”的最重要因素,不再来自生物性的遗传,而是来自非遗传性的积淀,亦即,对过去的文化记忆。[8]31这些非个体性的文化记忆如今由数字媒介和信息技术共同制造与保存,塑造着人类社会的此在与未来。本质上,向电子机械驱动的赛博空间“窗口”是对现实的削弱与改造。当屏幕内的影像需要再现现实的表现形式时,往往将现实置于一个物质性界面之后。而那些可以依靠算法生成的表现形式,则更加凸显出界面的本质性力量,如同眼帘,打开就是整个世界,关上世界就会消失。观看者主体在多用户领域中逐渐去中心化,在肉身与赛博空间的多重身份中,主体身份变得越来越暧昧、含糊、不确定。
技术生成与界面缝合让观看者主体面临的是区分外部与内部的界面的缺失。这个缺失危害到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的最本质的领悟,即认为它与环境息息相关。外部与内部的界面不再被区分,而被电子屏幕整合。因此,环境不再发挥其本来的作用,而是作为界面的奴隶,被成像、被拍摄,而不是直接感受。环境因界面而存在,否则它无法被把握。更进一步来看,界面的缺失削弱了我们对于另一个人的标准现象学态度。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认为:“他人是这样一个身体:是一个为各种各样的意向所积获得身体,是一个作为许多行动和话语之主体的身体,这些话语和行动回荡在我的记忆里,正是这些话语和行动向我勾勒出他的精神风貌。”[9]59我们只能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视角去看一个他人,他人本身的存在与他的表情、姿势、言语及身体是不可分割的。如今,随着外部的内部化,我们越来越少地依赖自身身体去把握人与物,在一种无环境、无触碰、无身体的真空环境中抽象地认知当下世界。于是,在这种态度中,我们悬置了对于皮肤下真正存在何物的知识(腺体、肌肉……),认为表面(比如脸)直接反映了 “灵魂”。人类逐渐失去其在具体生命-世界中的基础,而转向在赛博空间内的注册性生存。
电子界面的观看迫使主体“分裂”出单一身体之外的许多角色。一个多用户主体潜在地会在不同的观看领域下意识地做出不同的反馈。在互动性观影网站,主体倾向于及时抒发观影感受;在直播影像中,主体倾向于释放自己的消费冲动;在游戏影像中,主体致力于培养一个强大的赛博空间分身;在短视频平台,主体放任自身的欲望驱力,延长内时间,消磨外时间。观看用户的主体性是一种戴上面具的“自我-形象”,不断地在真实肉身与想象身份之间滑动。一般性的看法是赛博空间的多重面具背后有一个真实的主体,这些虚拟的角色是主体的伪装。但齐泽克指出,赛博空间想象身份的符号面具可以它之后真实的脸更真实,“外在于屏幕上‘多重自我’是‘我想要成为的人’,是我的理想自我的表现”[6]174。想象身份补充了只能有虚构或虚假形象来描绘真实生活的隐私时刻的禁令。主体为自己创造的观看者形象可以比主体的“真实-生命”形象(“官方”的自我-形象)更像自我。就此而言,对于某部文艺作品的反馈会依据场合而发生改变。在现实生活中 (比如线下观影会),受到社会身份与大他者的限制,我们的评价判断总会偏离我们的真正想法。面对面时,我们带上“面具”,做出一些符合社会常识和主体身份的评价。而在赛博空间中,真正的自我展示隐匿,符号用户登场。在无身体的空间内,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展示真实的自我,说出真实的想法。主体在这些身份之间的滑动“预示了一种空洞的联合,它使得一个身份向另一个的跳跃成为可能,这个空洞的联合就是主体本身”[6]175。因此,“去中心化的主体”并不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自我与更多的虚拟自我的多元集合,而意味着是对分裂主体的内容的去中心化。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去中心化的身体”,我们应当参考赛博空间的“代理人”。“代理人是一个作为我的替代物完成一系列特殊功能的程序。”[6]175一方面,它作为主体的延伸,帮助主体完成赛博空间中的身份注册。比如在视频平台中注册账户,我们只需要填充信息,“代理人”就可以自动生成一个个性化的观影库,记录主体的观影历史,并做出个性化推荐。另一方面,代理人也对主体行动、控制着主体。比如听力保护措施或个性化定制服务。当观看者戴上耳机将音量调高时,界面会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提醒观看者如果继续调高音量,可能会损伤听力。代理人也会自动为观看者筛选一些信息,送到电子界面上。由于赛博空间的代理人是一个技术性的外部程序,决定着观看者的观看行为或者内容,代理人“使主体成为中介”。我们可能会想象:“另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计算机程序控制着、指导者我的代理人——假如这个情况发生的话,我事实上就是从内部被统治:我自己的自我不再是我的。”[6]176中心化的主体拥有的一个确定自我在形式上分裂成多种观看角色,从而去中心化。屏幕角色(想象身份)与主体之间并不对立分裂,而主体与空洞之间存在分裂。“空洞”指向的就是不可见的代理人背后的最高统治者,主体无法填补与其之间的沟壑,无处可逃。最终,今天主体性的一般状况就是一种斯蒂芬·霍金式的身体:一个保留着人类属性的头脑加上被中介的身体。主体通过点击去寻找,通过界面去观看,通过变声器说话,通过虚假的数字角色去评价乃至再创造。
四、结语
本文探讨了数码屏幕影像的观看机制,认为它是一种基于电子界面的想象。从界面生成的角度来看,电子界面不同于窗、画框、银幕等经典屏幕,它可以脱离自然属性而完全由技术支撑。观看的对象有一个确定的文本变为难以加以定义与阐释的超文本;从界面缝合的角度来看,光线充足的观看空间使得观看者的身份被标记出来,无法维系一个连续性的观看活动,阻碍了由想象进入到象征和符号的过程,开启了界面效应;从观看者主体的角度来看,肉身身体与数字身份的分裂是浅层的,更为深层的是主体身份与空洞之间的分裂,空洞指向一种赛博空间代理人背后的不确定性。与实体化的传统影像相比,数码屏幕影像的观看发生了巨变。其观看机制不仅深刻地影响到数字影像的话语体系与创作方向,更深刻地贯穿于当今人类的认知与记忆中,塑造着人类的未来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