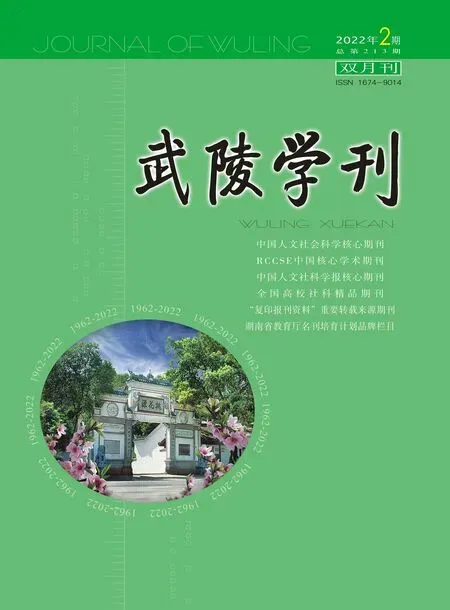重论闻一多后期杂文写作中的思想资源
杨一多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一、“三分法”与“斗士说”
1947年,朱自清在为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作序时,提出了闻一多的一生分为诗人、学者和斗士三个时期。这一“三分法”被学界沿用至今,鲜有人提出质疑。有关闻一多的研究,也依照“三分法”建立起了三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新月派时期的诗歌研究、进入象牙塔之后的学术研究以及后期“斗士”闻一多的杂文研究。
然而,对“三分法”的认同也间接导致了闻一多研究的割裂和闻一多形象的扁平化。除了年谱之外,我们几乎见不到试图“跨越”时期的研究。至于讨论闻一多“诗人转向学者”“学者转向斗士”这两次转变的论文,则显然也是基于“三分法”划定的分期之上的,而越是强调闻一多两次转变之巨大,也就更强化了三个时期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性,削弱了阶段间的关系。因此,我们很难通过现有的研究认识到一个整体且立体的闻一多,每当需要对闻一多的一生做出评定时,研究者们往往只能搬出“爱国主义”或者“五四精神”这样的“万灵药水”来,把它们作为贯穿闻氏思想的核心脉络。实际上这也没有超出朱序的“允许范围”,因为朱自清也强调了闻一多在诗人和学者的时期,“也始终不失为一个斗士”[1]442。
如果对比郭沫若所写序言,就会发现郭序也不约而同地强调了闻一多身为“斗士”的一面。朱、郭两人此时给出相同的评价,看似足以成为定论,但是仔细想来,这一点却是最为可疑的。因为朱、郭二人和闻一多的关系全然不同,朱自清是闻一多朝夕相处十几年的同事和好友,可以说是最了解闻一多为人以及学术贡献的人了。为了开明版的《闻一多全集》,朱自清可谓费尽心力,在全集出版后,他还一直坚持搜集闻一多的佚文。反观郭沫若与闻一多除了早年间因诗集而发生关联外,两人就再无交集了。然而吊诡的是,对比两篇序言,我们会发现朱自清对于闻一多学术的评价在深入和详细程度上,均不如郭沫若,反而在谈及闻一多的战斗性时,比郭序写得更热烈。
但是,朱自清何尝是一位以激进著称的文人呢?翻阅朱自清当时的日记,就能发现闻一多开始参与政治后,朱自清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闻一多有一段时间曾考虑加入国民党,也邀请朱自清和他一起入党,对此,朱自清以“未受到邀请为理由拒绝之”[2]240。而随着后来闻一多越来越接近青年学生,整个教授群体都与他产生了嫌隙。“一二·一”惨案后,闻一多积极支持学生们罢课,在教授会上他与傅斯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争执,闻一多认为应满足学生的要求,而傅斯年以为其中掺杂政治问题,不能受人利用,两人为此互骂。朱自清在日记里记录“下午起至晚九时开教授会,会上傅与闻发生口角”[2]381。游国恩谈到此事时承认自己因闻一多的转变而与他的友谊在“暗中有了很大的损伤”,行迹上也“逐渐疏远了”,当傅斯年指责闻一多是“布尔什维克”时,游国恩虽没有发言,但也“鼓掌赞成”[3]。闻一多和教授群体的疏离,却让他在青年学生心中地位不断提高,朱自清记录在劝说学生复课时,“听众反映愤怒,他们要继续罢课,我们失败了”,而后是“一多上了讲台”[2]377,才把局面安定下来。1946年5月3日,朱自清参加同文学会,发现学生们发表的“各种批评言论”,“均为一多所提议者”[2]402。透过朱自清日记中的文字,我们不难看出朱自清虽然不曾明确反对闻一多,却也意识到闻一多选择了和他不同的道路,已经不属于“我们”中的一位了,他开始有意地与闻一多保持一定距离,确保自己决不会卷入到后者的政治活动中去。
这样看来,朱自清在序言中对闻一多“斗士性”的高度评价,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迎合舆论环境的叙述策略。1946年,李公朴、闻一多被刺身亡事件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但起初学界悼念闻一多,主要还是从无辜学者被暗杀、学术损失的角度展开的。查看朱自清1946年写的《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一文,就能清楚地看到,朱自清最初悼念闻一多时是把学术贡献作为绝对重心的,同时顺带提及了闻一多早期诗歌成就,而对于其“斗士”一面,全文只有开篇一句话——“这是民主运动的大损失”,此后就再无下文了[4]。
但是,随着舆论发酵,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牵涉其中,通过对李闻事件的不同解读来抢夺宣传阵地。闻一多与闻一多之死,也就不得不负载起更多的意义。此时,如果朱自清一味强调闻一多脱离政治的一面,反而有损于闻一多已被树立起来的烈士形象。
朱自清显然也能感受到风向的变化,而且对于他来说,虽然自己并不赞同闻一多的激进,但如果“战斗”是老友的遗愿,那么他也尊重闻一多做出的选择。因此在写序时,朱自清与郭沫若一样,都反复强调了闻一多的战斗精神,并且以此为视角重新阐释了闻一多此前的诗歌创作与学术研究,来保证闻一多作为“斗士”的形象被后人铭记。
但闻一多真的始终是一位“斗士”吗?这个结论显然是可疑的。且不论闻一多早年间相当坚定的“文化守成主义”,在他进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之后,闻一多也一向是非常保守的,对于政治,他则尽可能地远离。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记录了他和老同学罗隆基1937年初去探望闻一多时的经历,闻一多此时“潜心典籍,绝不旁骛,对于当时政局不稍措意,而且对于实际政治深为厌恶”,因此对于罗隆基毫不同情,甚至认为他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5]103-104,导致气氛很不愉快。在各种政治事件中,闻一多始终是全力反对学生运动的一派。1931年到1932年间,他与青岛大学学生间的冲突就因此而起。“九一八”后,众多学生南下要求国民政府抗日,而闻一多对此持反对意见,并且在校务会议上主张开除为首的几名学生。随后青岛大学学生以“断送三十余青年学业”“提请开除是执委会十余人……压抑爱国运动”[6]379等为由,要求驱逐闻一多。“一二九”运动时期,闻一多也对学生采取示威游行的方式进行爱国运动表示了反对[7]。“西安事变”爆发之后,闻一多更是在清华的课上质问学生:“你们这种捣乱,不是害了中国吗?”[8]朱自清日记中还记录了闻一多与罗常培争吵,而让学生们“以为是骂他们而发怒”[2]212的事情。对于学生从军抗日的问题,闻一多也曾同战国策派的雷海宗一样,认为学生的主业应当是学习,“一个学生的价值远高于一个士兵的价值,学生报国应该从事更艰深的工作才对”[9]。
当然,以上的文字并非是为了抹黑或指责闻一多和朱自清两位先生,而是要指出“三分法”以及“斗士说”的不足之处。因为我们在讨论闻一多的40年代的杂文与演讲时,必须先弄清楚闻一多是以何种姿态与心态写下这些文字的,这关系着他写作时采用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更关系着我们能否真正地理解闻一多。
闻一多一生有两次杂文写作的高峰时期,一次在他就读于清华学校时,这时他的思想和文笔都还稚嫩,关注的问题也多和校园生活相关,不具有讨论价值。另一次则是在40年代,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斗士”时期,如果把1943年的唐诗课事件算作闻一多“斗士”生涯的起点的话,那么闻一多真正写作杂文的时间,只有短短三年。在此之前,闻一多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学者生涯,无论是从时间长度还是所获成就的角度来说,学术都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且联系上文提到的闻一多尚未转向“斗士”前的表现来看,闻一多对于自己“清高的教授”这一身份有着很强的认同感。因此研究闻一多杂文,必须立足于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此时的闻一多并不是一名重新拿起武器的“斗士”,而只是一名刚走出象牙塔的学者。承认了这一点,那么再面对闻一多的杂文时,就会不免产生疑虑——闻一多治学,一向以客观严谨著称,他是如何从冷静的论文写作转向激烈的杂文写作?他的论文与杂文之间是否又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关联?
二、作为“前文本”的学术论文
在以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试图解决闻一多杂文与论文之间关系的问题,但基本都意在论证闻一多的“斗士性”如何在他的论文与杂文间一脉相承,甚至认为闻一多的“杂文、论文都从现实斗争的深处汲取灵感”,是从现实里“汲取”观点来“照亮历史”[10]。
显然,这类观点也受到了“斗士说”的误导,混淆了论文与杂文的区别,也就遮蔽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就连闻一多自己也承认过他的工作“长期脱离了现实”[11]287,这位“何妨一下楼主人”,在从事学术研究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身处象牙塔而绝缘于现实斗争,且作为一名成熟的古文字学学者,即便关注现实问题,闻一多也不会让现实干扰到他的学术研究,否则论文就成了“创作”。至于杂文,虽然可以从现实中“汲取灵感”,但更需要作者调用他自身的经验与见解,来对现实问题提出另辟蹊径的解答,杂文不存在程式与技巧可言,因此它也是最能暴露出作者本人思想的文体,换言之,当闻一多提笔写作杂文时,学者身份势必为他带来与众不同的视角。这就造就了闻一多杂文与论文的独特关系,即论文以一种“前文本”的方式,与杂文展开互动,甚至是出现于杂文的写作之中。
此处的“前文本”,指的是一种先于主要文本而存在的前提或基本观点。作者因为认为此前已经说过,或因为默认读者都已理解,所以不愿在主文本中进行重复论述。“前文本”其实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在研究一些作家时,就需要以其早年的创作为钥匙,来解读此后的作品。大多数情况下,不了解“前文本”,并不影响主文本的阅读。不过,闻一多杂文的特殊性在于,作为其“前文本”的论文中,包含了许多闻一多独到的观点,而如果忽略了这部分“前文本”的存在,则会对主文本产生严重的理解偏差。
例如,1943年写成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中,闻一多明确提出文化要勇于“受”,因为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必然要“互相吸收,融合”,最终成为“一个世界的文化”,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谁都不能改变”[12]。这种近乎“武断”的文字从何而来?如果只看单独一篇文本,或只考察闻一多的杂文,那么一定无法对其给出合理的解释,也正因如此,学界至今仍把这篇文章看作闻一多转向“斗士”的重要标志,试图把它推给激进的“斗士”闻一多来负责;再如1944年《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一文,也一般被看作是闻一多为批判现实所写的杂文而未受重视,除了因为文章后半部分有不少宣泄式的文字外,主要原因还是闻一多以宗教的有无来作为衡量国民性的标准难以令人信服,比起严谨的学者,文章更像是出自一个抗争现实的“斗士”之手。但是,正如前文所言,与其把闻一多的杂文单纯地推向“现实”的一端,不妨假设闻一多的杂文写作实际上是拥有一定学术理论支撑的。带着这样的疑虑回看闻一多后期杂文中对历史和文化的批判,则会发现这确与他的学术进展有一定的“同步性”。
闻一多的治学道路,曾经历过一个从“诗”或“文”而到“史”的变化,从唐诗研究到《诗经》《楚辞》的考证,再到古代神话研究,随着闻一多研究对象越来越古,提出新观点所需的历史材料就显得愈发缺乏,而为了填补中国上古史的大量空白,闻一多研究中“史”的比重逐渐开始上升。最早表现在1934年他于《学文》上发表的《匡斋尺牍》一文,其中第五节“薏苡与芣苡,夏民族与周南”中,闻一多就以《诗经》训诂为据,展开对古史的推测[13]210。到抗战爆发后,书籍的缺乏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加重,更是促使他结束了古文字的研究,彻底走向了古史的领域。1939年,闻一多给梅贻琦去信请求休假一段时间来进行学术研究,并提出因书籍缺乏的关系,原定编纂《诗经字典》的研究工作“不易进行”,将题目改成了“中国上古文学史”,次年呈给梅贻琦的《中国上古文学史研究报告》,也证实了闻一多为探求古史所付出的心血[1]359,367-369。这意味着,在闻一多彻底转入民主斗争之前,他的研究重心是古代神话与历史。
当然,闻一多的学术研究情况并不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但需要借此提出的是,闻一多后期对于古史的研究,给他带来了一场深刻的历史观更新,而正是这种对历史的全新认识,让他即使在杂文中也显现出十足的异质性。下文将有关的几篇论文纳入考量的范围,尝试分别对前文提及的《文学的历史动向》与《从宗教论中西》加以新的解读。
1942年11月,闻一多完成了他著名的《伏羲考》,通过对洪水故事与人首蛇身象记载的考证,闻一多注意到亚洲多个民族共源的可能性,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从人首蛇神像谈到龙与图腾”,闻一多进而将蛇图腾与龙图腾联系起来,推测是蛇图腾的团族(klan)在兼并了众多其它团族后,形成了现在的龙图腾[13]58-131。之后的《龙凤》一文,闻一多还指出龙与凤是中国“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13]159,凤是殷民族的图腾,而龙图腾则代表着夏民族。
以上的论文,虽只属于古代文化史和民族史领域的研究成果,但古代民族从独立走向融合的过程,却促使闻一多对他所研究的“中华民族文化”产生更深的思索。他意识到了纯正的“中华民族”是不存在的,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只是一种“想象的混合体”。正如他在《复古的空气》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你站在东方,以夷为本位,那便是夷吸收了夏;如果站在西方,以夏为本位,那便是夏吸收了夷”,至于楚与夷夏的关系,在战国时,楚“还是被视为外国人的”,而到了汉朝,则“南北又成了一家,分不出主客来”,中华文化“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成不变的文化”[14],因此文化复古者们的追求也必然只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性的依据。
将以上的论文作为闻一多1943写作《文学的历史动向》时的“前文本”看待的话,就会理解文中所谓“一个世界文化”的判断并非闻一多信手拈来,也和鲁迅的“拿来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差别。闻一多之所以判断今后各民族文化会融为一体,是依据了他对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状况的研究成果,并在这一历史延长线上进一步推导而做出的判断,这也是为什么他十分肯定地称之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路线”。可以说,闻一多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出的激情,并非来自于“斗士”的一面,而恰恰相反,他是作为一个学者对学术观点的自信。只不过在写作《文学的历史动向》一文时,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以及他对“文化融合”趋势的坚信,闻一多不愿在文中为他的判断做出过多的解释。这种省略加之“斗士”身份的强大,使得作为理论根基和“前文本”的几篇论文一直未能得到重视,也未能与《文学的历史动向》相勾连而达成有效的解读。
同样,1944年创作的《从宗教论中西风格》固然是一篇辞气浮露的“战斗檄文”,尤其文中闻一多认为西方的“爱国思想和恋爱哲学”,甚至“科学精神”,都是“宗教的产物”,中国则正因为缺乏“宗教精神”而变得“渺小,平庸,怯懦,虚伪”,这种推论颇有夸大宗教力量的嫌疑,也很难从中找寻出严谨的论证逻辑。即便如此,《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也有与之对应的“前文本”——《神仙考》。相比于杂文中大刀阔斧的批判,作为学术论文的《神仙考》则小心严谨得多,首先以春秋时齐国人独特的“难老”的要求入手,试图探寻古代齐人不死观念的来源,在经过对古代中国各民族死亡观的考察,闻一多发现东方土著只有肉体不死的观念,因此“只求缓死……不做任何非分之想”,而灵魂不死,甚至借“毁尽”肉体来达成“灵魂永生”的概念,均由齐人从西方传入。在此基础上,闻一多提出之所以西方人追求灵魂不死,是因“浪漫的人性不甘屈服于现实”[13]132-158。回看《从宗教论中西风格》中对西方文明一味地褒扬与对中华文明的贬损的依据,显然是将《神仙考》中的结论进行夸大之后得到的,虽存有许多欠妥之处,可也并非是为了批判而进行的牵强附会。
上述的例子证明了将闻一多的学术论文作为“前文本”引入杂文分析的必要性,这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闻一多选择的“转变”方式。依此来看,闻一多后期杂文写作中看似“武断”之语,绝大多数都建立在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新历史观之上,并且有严谨的“前文本”为依托。闻一多并非是用现实“照亮历史”,而是以他在学术研究中所获得的历史意识来观照现实。而且,闻一多在面对走出象牙塔后众多的现实问题时,只选取自己有卓见的部分提出新论并加以阐述的做法,比起不顾一切的“斗士”来说,倒也更贴近他小心翼翼的学者形象。
三、被政治话语掩盖的跨学科的视野
明确了闻一多的杂文有着论文作为“前文本”这一要点之后,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闻一多杂文写作的思想资源。因为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一句“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致使很长一段时间里,闻一多研究都有一定程度的政治色彩。尤其闻一多后期思想的转变问题,经过了几位在昆明的地下党员回忆与渲染后,闻一多——马克思主义战士的形象越发清晰。而更是由于闻一多杂文体现史观的独特性,让持此观点的学者,轻易能够从其杂文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部分。如刘烜的《闻一多评传》就直接把闻一多后期史观的转变与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联系,并以此来解读《什么是儒家》《龙凤》等文,认为其中的观点来源于列宁的《论国家》与马克思的《资本论》[15];又如吴宏聪的《认同与融合:闻一多的文化观》与孙党伯的《论闻一多的文化思想》两文,均认为《文学的历史动向》中世界文化合流的观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述过的,这“并不是闻一多的首创”[16],而是闻一多“受到《共产党宣言》的启发而提出上述看法的”[17]。
持类似观点的文章不胜枚举。但关于《文学的历史动向》的“前文本”,上文已经进行了说明,它同闻一多对古代民族的研究息息相关,饱含了作为学者的闻一多的创见,同《共产党宣言》等文的关系并不紧密。
而既然明确了闻一多的思想不同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那进一步的问题是,此时闻一多开展研究采用的理论资源是什么,为何其最终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
在解决这一问题前,首先要提及的是抗战后的文化环境对闻一多研究的影响。1938年,闻一多参加了临大湘黔滇旅行团,这段被誉为“小长征”的旅途让闻一多得以接触到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原始的文化、质朴的情感、鲜活的生命力,让“文明久了的”闻一多受了不小的触动,他由此开始对先民文化的起源产生兴趣。当然,西南地区复杂的民族问题正如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不仅仅吸引了闻一多,更是让许多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教授纷纷投入研究,闻一多的《伏羲考》一文的产生,就是受了人类学者芮逸夫的《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的传说》与考古学家常任侠《沙坪坝出土之石棺》两文的启发。
而在此前,闻一多也已经在论文中显示出对于先民文化浓厚的兴趣。如1939年写作的《歌与诗》一文,即从先民的心理入手,来论证“兮”字在“原始时期的重要职责 ”以及“歌”与“诗”的起源[18]5-15。次年的《姜嫄履大人迹考》[13]50-57在对比上古时期各民族传说后,得出后稷与伏羲,分别是周人与犬戎的祖先这一结论。两月后写成的《释》[18]533-544则通过对“”字的训诂,发掘出先民有狩猎大象的文化。
但先民的生活习俗,文化思想,很多没有文字记载,闻一多之前以训诂、考据为主的研究方法,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他急切地需要新的研究方法帮助他突破瓶颈。此时,人类学进入了他的视野。苏永前的《二十世纪前期中国文学人类学实践研究》一书,在论及闻一多时指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在国内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抗战时的昆明,“正是20世纪前期中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不仅此前的几次重要田野调查多在云南境内进行,此时更有来自全国的许多社会人类学家聚集于此”[19]。人类学带来了大量的古代社会样本作为参照,填补了古史研究中许多的空白之处。因此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感叹:“人类学可供给我们的材料,似乎是无限度的。”
实际上,闻一多在昆明与人类学是一次重逢而非初遇,下文对闻一多与人类学的关系略作勾连,作为参考。
早年闻一多就读于清华学堂时,即与日后的两位社会学家吴泽霖、潘光旦结为好友,几人还共同组成了读书会性质的小社团“丄社”,以清华周刊上刊登的丄社常会记录来看,主要讨论集中在各种社会学问题上。1926年8月,闻一多在吴淞国立政治大学担任教授兼训导长时,就住在潘光旦家中,针对社会学问题,他与潘光旦有过争论[11]117,也为潘光旦的著作《小青之分析》绘制扉页插图。同时,闻一多创作并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诗经的性欲观》,这是一篇社会人类学色彩极浓重的作品,有关西方性心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被闻一多直接运用在《诗经的性欲观》一文中,在讨论《溱洧》时,闻一多写道:“‘谑’字,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解作性交。但是我疑心这个字和sadism,masochism有点关系。性的心理中,有一种以虐待对方,同受虐待为愉快之倾向。”[13]173
在闻一多正式踏入文学研究后,虽然着力于训诂、考据等方法,却也并未完全放弃跨学科的视野,他曾感叹,“中国文学虽然内容丰美,但是研究方法实在是落后了”。1934年创作《匡斋尺牍》,就被梁实秋认为“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因为闻一多在文章中“于音韵训诂之外再运用西洋近代社会科学的方法”[5]85。如在论《芣苡》一诗时,闻一多利用生物学的知识,辅助证明芣苡是一种生育的象征,并且结合社会学的判断以纠正现代人的视角,“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13]205。
闻一多真正重视人类学,还是在抗战爆发后,原因前文已经提及,此处不再赘述。1938年8月,闻一多在贵阳时,就和老同学吴泽霖谈起了他想研究图腾的计划。吴泽霖曾回忆道:“他(闻一多)告诉我,他对图腾很想研究,并愿意同我继续讨论……他劝我回清华,在联大教书,他说他回去后同光旦谈,再由光旦同我联系。”[6]4871941年,当何善周开始选编先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时,闻一多给何善周所开列的参考书单中就有大量的人类学、社会学专著。何善周在《千古英烈万世师表》回忆道:“当时他还给我开列了一个书目,那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陈望道译的《社会意识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甲骨文研究》,还有一些社会学、人类学和《舆地丛钞》一类的书。”[20]
同时,人类学与社会学的运用,在闻一多的论文中愈发频繁起来,之前已经提及的《姜嫄履大人迹考》《伏羲考》《神仙考》《龙凤》等文中都能见到源自人类学的观点。此外,现存手稿里《道家的精神》一文的写作提纲中还对此有更直接的体现,如“灵气遍在主义Animatism Manaism”(即泛灵主义)“摩那”(即mana)等就被闻一多加入到对道家思想的分析中[21]。
这种跨学科的视野,给予了闻一多的学术研究以全新的活力,帮助他从更宏观的角度面对中国文化问题,闻一多独特历史观的形成,也得益于此。此后闻一多展开对儒学的批判时,人类学自然也就成了他手中的利器。1943年6月30日,闻一多参加了云南大学的中国文化讲谈会,吴宓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闻一多自诩用anthropology治中国古籍,觉中国古圣贤之文化实甚primitive。而如《大学》中之格、致、心、物等字,皆原出初民之风俗及习惯,均是日常卑俗之实物近事。故《四书》《五经》实极浅俚,不过初民之风俗与迷信。即周秦诸子如老庄亦同。此中本无些须哲学,后儒神而化之,强解释出一番深奥高尚之义理,乃有所谓中国圣贤之文化。又曰,予治中国古学,然深信其毫无价值。中国今日实际措施,只有纯采西洋之物质科学与机械工程耳。”[22]
由此可见,闻一多后期的学术研究正是利用人类学作为他新的思想资源,从而对古代文化产生了许多独到的解读,因其论文以“前文本”形式与杂文产生的关联,一些来自人类学的判断也得以显现在他的杂文之中。而之所以能在他的杂文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相类似的表达,是因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也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的影响。闻一多的杂文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两者只因同源相近,因此不能单纯以某些论调的相似来判断两者直接相关。
结 论
闻一多40年代的转变,是一种迫于环境而产生的被动反应,这点从他悲愤的抗议中就可以看出——“另一些像我这样的人,说起来,是搞了这么多年的学术研究,自然多少算是做了一点事情,可是没有民主的国家,怎么能保障和奖励学术的研究呢?而且这些研究究竟有什么用呢?”[11]187对于他这个“何妨一下楼主人”而言,放弃自己视为终身事业的学术,想必是痛苦万分而又无可奈何的,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恐怕没有任何主义或思想可以让他主动放弃学术。因此,将他的杂文写作和论文完全割裂,或者以“斗士”逆推其学术生涯的行为,都有违闻一多的真实心境。
作为一名老学者和年轻的民主战士,闻一多的杂文写作与他的学术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其后期杂文中的一些言论虽看似激进,但背后也有着相应的学术发现作为支撑。因此与其说是某种政治自觉促成了闻一多的转变,倒不如说是“学者”闻一多终于找到了连通学术与现实的路径。最后,勾连“学者”与“斗士”闻一多之间的联系,不仅仅可用于解读其杂文,更大的意义在于打破一直以来政治话语造成的桎梏,重新拾回“斗士”闻一多身上更重要的“学者”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