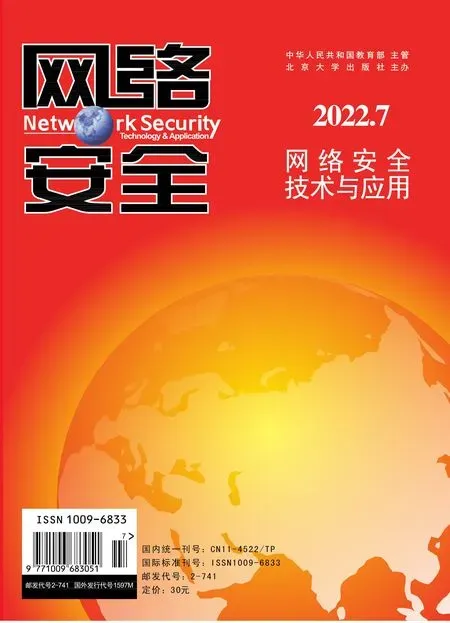自媒体时代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探析
◆付晓楠
自媒体时代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探析
◆付晓楠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北京 100038)
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日趋增多,并呈现严重化的趋势。在公安部严打网络犯罪的背景下,我国也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但由于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现有的法律规定仍存在网络证据收集难度大、自诉救济困难、量刑过轻等问题,要对网络诽谤犯罪进行更好的刑法规制,必须在贯彻宽严相济的基础上,完善网络舆论调查取证的程序和实体规定,增加救济手段,促进严重网络诽谤犯罪自诉向公诉转变,同时区分网络诽谤犯罪情节轻微与严重的量刑标准,从而更好净化网络空间,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网络诽谤;网络侦查;刑事司法政策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和自媒体平台成为人们在网络中获取信息和表达情感的主要工具,但当网络、自媒体平台给人们带来交流和维权便利的同时,也可能成为网络舆论暴力及犯罪的酿生地。近年来,一些网络参与者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在微博、微信公众号、抖音等平台对他人名誉及一些社会热点事件进行虚构事实、颠倒是非的信息传播,严重干扰了互联网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甚至危害国家安全。如2020年12月,杭州吴女士“少妇出轨快递小哥”的网络诽谤案件在全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该案对被害人造成的影响和对社会造成的恐慌是传统诽谤案件所不及的,其中凸显出的被害人取证难、自诉难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针对网络诽谤等自媒体违法犯罪活动突出的情况,公安部于2018年组织各地公安机关对包括网络诽谤在内的一系列自媒体犯罪重拳出击,对此类违法犯罪活动形成了一定的威慑。然而,由于网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以及网络证据的收集和调查难度已不是传统诽谤所能达到的,目前我国对于网络诽谤犯罪的治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近年来已陆续出台了相关法律,但在实践中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处理常常不了了之,现有刑罚规定的诽谤罪采用自诉处理的方式是否能够适用于面向社会大众的网络,如何明确诽谤罪公诉与自诉的界限以及公安机关如何获取有效证据以确定犯罪人都是司法实践中面临的难题,因此,在出台了相应的立法规定之后,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进行进一步的探究,促进立法和司法实践相互协调贯通,从而有效打击网络诽谤犯罪就成为了更加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网络诽谤行为指利用信息网络捏造诽谤事实,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是借助信息网络而实施的诽谤行为,是传统诽谤行为的变形。它包括两方面的行为要素,一是行为人借助了信息网络;二是散布了损害他人名誉的信息[1]。从本质上来说,网络诽谤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上都和传统诽谤一样,属于一对多的多线传播,成立标准都是针对特定的人或事对多个人进行捏造事实的虚假传播。但与传统诽谤不同,网络诽谤具有传播速度快、受众范围广和主体多元化的特点。网络诽谤将犯罪地由线下转移到了线上,扩大了受众范围,加快了传播速度,相较于传统诽谤造成的后果更恶劣,甚至会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造成影响。由于网络诽谤犯罪相比于传统诽谤有一些新特点,若仍采用传统诽谤法的规定在实践中会出现无所适从的困境和局限性,出现罚不当其罪的后果,因此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处理不应完全比照传统诽谤,而应针对其特殊性进一步细化其规定,确保罪责刑相适应。
1 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及存在的问题
1.1 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刑法规制,是指采用刑事处罚的方式,对某一行为认定为犯罪,并定罪处罚。从立法角度看,针对网络舆论诽谤的犯罪行为的刑法规制,我国《刑法》主要以侮辱罪或诽谤罪定罪,能够起到一定的打击效果。现行刑法规定的诽谤罪为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诽谤罪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见,我国目前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的针对网络诽谤行为的立法,仅在法律和司法解释中有关于网络犯罪的零散规定。网络诽谤犯罪相较于传统诽谤罪而言,危害程度更大,若仍和传统诽谤犯罪一样适用刑法中相同的定罪标准和法定刑会导致网络诽谤犯罪的惩罚过于宽缓,降低了网络诽谤的犯罪成本,难以形成威慑作用。2013年两高出台了《网络诽谤司法解释》,对利用网络进行诽谤、辱骂、编造或散布虚假信息等行为进行了规制。《解释》规定了网络诽谤罪的“情节严重”的标准,一是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五百次以上的;二是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三是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四是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为网络诽谤行为设定了较为明确的定罪标准。但解释对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确定和犯罪对象的区分尚未有明确的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从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全文搜索网络诽谤案件,共检索到74个案件,其中民事案件63个,行政审判11个,未检索到刑事案件,可见在实践中,此类网络诽谤案件多以民事案件进行处罚,这是由于尽管在立法中陆续出台了一些规范网络行为的法律法规,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网络诽谤行为的入罪和处罚仍然存在认定标准模糊和电子取证困难等问题。因此,还需要进一步明确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使立法规定能够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切实落实。
1.2 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互联网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新型犯罪,尽管我国陆续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进行规制,但由于其犯罪类型较新,手段形式多样,现有的规定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具体来说,在刑事司法领域存在如下问题需要解决:
(1)侦查阶段证据收集难度大
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高科技性,给取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且诽谤罪作为自诉案件,取证通常由受害人进行,普通的受害人难以掌握专业的网络取证和定位技能,给受害人取证带来了挑战,最终可能由于获取不到有利的证据,难以确定被告而导致问责落空,受害人权利得不到救济。入罪取证困难、行为人身份难以认定,使得网络暴力行为受惩罚的确定性大大降低,无法受到有效规制。
(2)起诉阶段自诉救济困难,公诉标准不明确
诽谤罪在刑法的规定中属于自诉犯罪,这主要是由于传统诽谤多发生于熟人社会中,社会影响范围小,且被害人的受侵害程度受其主观判断较大,不便于司法权力侵入,由被害人在必要时提起自诉即可。但网络诽谤信息传播的范围不再仅限于熟人之间,而是面向所有社会公众,一旦虚假信息在网络空间中进行散布就会迅速传播,给被害人造成不可磨灭的严重损害后果,甚至还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影响社会秩序,由于网络诽谤犯罪侵害的法益不仅限于某些特定的个人,而且可能威胁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传统诽谤单纯的自诉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网络诽谤犯罪的严重性,现行刑法规定对于诽谤罪,告诉才处理,但是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除外,可见对于诽谤罪以公诉方式处理是有相应的法律依据的,但由于立法者在立法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立法的漏洞会在实践中逐渐凸显,因此司法实践中在适用法条时需要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在必要的时候,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介入可以对立法漏洞进行有效弥补。刑罚中对诽谤罪的“但书”规定就是以抽象的方式对诽谤罪中的漏洞进行弥补。但是这一简单的“但书”条款在具体适用时是不明晰的,虽然司法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但司法解释也是法律的一种,仍然不能时刻应对变化发展的现实问题。因此,公权力机关对于弥补现实出现的法律漏洞就能起到十分必要的作用。然而,对于网络诽谤而言,实践中如何确定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标准,何种情况下应当提起公诉仍然不明确,常常出现被害人提起自诉,但由于证据收集不足而不能得到救济的情况,公权力在弥补法律漏洞的过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困难。
(3)审判阶段定罪标准难确定,量刑标准过轻
首先,刑法中虽然规定了诽谤罪为故意犯罪,但在网络环境中,如何认定行为人的转发行为是故意还是过失,相关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的规定。《网络诽谤司法解释》中的规定仅涉及定罪标准和“情节严重”行为的认定,而对于故意和过失行为的区分标准和不同的处罚标准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区分标准不明确,在审判过程中容易错将网络过失传播虚假事实的行为与故意进行诽谤传播的行为同等看待而判处相同的刑罚。
其次,由于诽谤行为的犯罪对象可分为社会一般成员和政府及公众人物两类,对这两类群体的信息公开程度和范围的保护应有所不同,政府及公众人物由于其特殊的工作性质,对于应当公开的信息以及合理的监督评论不能加以限制,否则就会侵犯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和言论自由,但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也应受到同等的保护,对于涉及公开其私人信息和虚假言论的行为也应受到法律的规制。现有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中对网络诽谤的犯罪对象未进行区分规定,不利于在定罪量刑时进行区分。
最后,由于线下诽谤的范围较小,且多发生于亲友之间,因此刑法对诽谤罪的量刑较轻,仅规定了最高刑为三年的有期徒刑,且将其规定为亲告罪,只有被害人向法院起诉,才能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然而对于网络诽谤来说,网络传播的快速性和受众的广泛性,一旦在网络空间中广泛传播,则会对被害人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具有更强的破坏性和社会危害性,因此,若行为人在网络发布虚假信息,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异常,甚至造成破坏社会秩序的严重后果,依据刑法仅能判处的最高刑期只有三年,犯罪成本过低,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难以进行有效的规制。
2 我国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对策
费尔巴哈认为,刑事政策是国家据以与犯罪作斗争的惩罚措施的总和,是立法国家的智慧。刑事政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刑事政策即刑事惩罚政策,也就是刑事法律政策[2],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等具体的刑事政策。本文主要讨论在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的刑事司法政策,但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是有机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刑事立法实现了追究犯罪、科处刑罚的法制化,是刑事司法的依据;同时,刑事立法的目的只有在现实的司法实践活动中才能得以实现[3]。因此探究网络诽谤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必然涉及相关立法的研究,对刑事司法政策的完善也能更好地使立法得到贯彻落实。网络作为公众发表自己声音的载体,是公民行使言论自由,对国家和政府行使监督权的便捷有效的途径之一,但若过度的自由,没有法律的限制则会导致权利过度滥用,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对于网络舆论空间,既要营造宽松自由的言论自由环境,又要加强打击和刑法规制,限制权力的滥用,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领域都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对于网络诽谤犯罪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困境及问题,可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完善:
2.1 刑事侦查阶段:完善证据调取程序,加强网络监管
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和专业性,网络诽谤行为在调查过程中常常存在取证难的问题,在传统犯罪案件中,可通过实体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取证,实体犯罪现场调查是发现和提取证据的重要手段。但是网络诽谤行为发生于虚拟的网络空间,不能够在现场进行调查取证,且由于网络并非实名制,给犯罪人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犯罪证据也容易被删除和修改,证据信息内容的完整性和真实性难以保证。虽然法律明确规定电子数据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但是网络证据的获取往往会成为案件的难点。网络诽谤行为的电子数据取证困难,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不法行为人肆意散布谣言逃避法律规制的行为。因此,要进一步明确网络取证的手段和界限的规定,为自诉案件被害人提供向公安机关或专业技术公司寻求帮助的救济途径,对网络取证的授权机关、侦查手段和适用范围等进行规范化、程序化的规定。
其次,执法部门要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力度,提高网络平台的准入门槛,增强网络平台的专业性。贯彻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刑事对策,加强源头预防,对网络舆论空间进行实时监督,及时发现危害严重的网络诽谤犯罪行为,并进行精准打击,增加打击的确定性。
2.2 刑事起诉阶段:促进严重网络诽谤犯罪自诉向公诉转变
由于网络诽谤作为传统诽谤的升级行为,其受众的广泛性和传播的快速性,相比于传统诽谤更容易造成严重后果,因此,要完善网络诽谤犯罪的审查起诉制度,促进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诽谤犯罪的自诉向公诉转变。目前我国《刑法》针对网络诽谤犯罪的公诉条件是要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程度。因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实质性条件。
《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规定的应当认定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主要有:引发群体性事件;引发公共秩序混乱;引发民族、宗教冲突;诽谤多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造成恶劣国际影响;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4]。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是诽谤罪中自讼与公诉的划分标准。而对于网络诽谤犯罪而言,在网络空间进行诽谤容易达到危害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因此,检察机关应及时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诽谤犯罪提起公诉,促进网络诽谤犯罪的自诉向公诉转变。对于提起公诉的条件,可针对网络空间的特点,根据有效转发量、播放量、评论数、被害人精神鉴定等标准进行综合评估,将造成被害人自杀或精神失常,受人排挤,找不到工作,引起社会大范围公众的恐慌,甚至危害国家利益或国家形象的行为认定为网络诽谤犯罪提起公诉的条件,这些后果已不仅局限于小范围的熟人之间,而是危害到国家和公众利益,或是给被害人造成人身和心理上的威胁,因此需要国家公权力介入进行保护。
但在诽谤罪自诉向诽谤罪公诉的过渡上,国家的公权力的参与需要适度且适时,要严格把握公诉的条件,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只针对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的网络诽谤行为提起公诉,而对于情节轻微的仍可通过自诉或刑事和解和恢复性司法的方式处理。
2.3 刑事审判阶段:严格界定犯罪严重程度,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网络诽谤虽然构成要件与传统的诽谤罪相近,但因网络空间的特殊性,其破坏力与危害性与传统诽谤罪不可等量齐观。因此,既要实现与传统定罪的对接,将符合诽谤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也要根据网络的特殊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罪轻罪重进行严格的区分界定,严格审查证据,对于转发量和阅读量应统计有效的传播次数,排除虚假数据。区分恶意的虚假诽谤评论和批评性的正当评论,防止以刑法错误打击正当言论自由的局面出现。
在网络诽谤犯罪中同样也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适用宽严相济的定罪标准,对造成严重后果的网络诽谤行为在法定刑的范围内加重处罚,同时又要进一步细化对网络诽谤犯罪主观意图以及犯罪对象的区分和认定,网络诽谤犯罪的严惩应只针对主观恶性大,造成了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对于过失、情节较轻以及针对公众人物的言论应适当放宽,避免惩罚范围过宽而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在严厉打击和保障言论自由上找到平衡点。
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网络舆论暴力犯罪往往缺乏与之相匹配的法律条文,只能依据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以及法官的自由裁量定罪量刑,因此,法官的自由裁量对于网络诽谤犯罪的治理效果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弥补立法、侦查和起诉漏洞的最后一环,因此在审判过程中要灵活合理地适用法律,严格根据犯罪情节、犯罪后果、犯罪对象和主观意识对网络诽谤犯罪行为情节的严重性进行区分,在宽严相济的理念指导下,做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合理审判。
3 结束语
在网络、自媒体日益发展和信息化爆炸的时代,各式各样的信息充斥于网络空间,给人们带来信息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不法分子进行网络诽谤行为的容身之处。网络的隐蔽性、受众广泛性和传播迅速性的特点,加重了诽谤行为的严重性,因此对于网络诽谤犯罪若仍依照传统诽谤犯罪的定罪和量刑标准,则会导致网络诽谤行为量刑过轻,不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虽然现已出台了相关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但都较为零散,在实践过程中仍出现侦查阶段证据搜集难度大、起诉阶段自诉救济困难,公诉条件不明确、审判阶段定罪标准难确定,量刑标准过轻的问题。因此要更好地治理网络诽谤犯罪,除了完善立法,更重要的是促进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的衔接,让司法实践在现有的立法规定的指导下,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处理,以弥补立法的漏洞。针对目前刑事司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指导下,通过在侦查中完善证据调取程序,加强网络监管;在起诉中促进严重网络诽谤案件由自诉向公诉转变;在定罪过程中严格界定网络诽谤犯罪的严重性等刑事司法政策,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分别进行完善,促使刑事司法既能在刑法规制的框架下进行,又能根据具体案件实际进行灵活变通,确保网络诽谤犯罪的处理能够有罪有罚,罚当其罪。
[1]张佩.网络诽谤行为入罪的司法认定标准研究[D].山东科技大学,2020.
[2]王牧.犯罪学[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
[3]王宏玉.刑事政策学[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
[4]周毅晶.网络暴力的刑法规制研究[J].行业研究,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