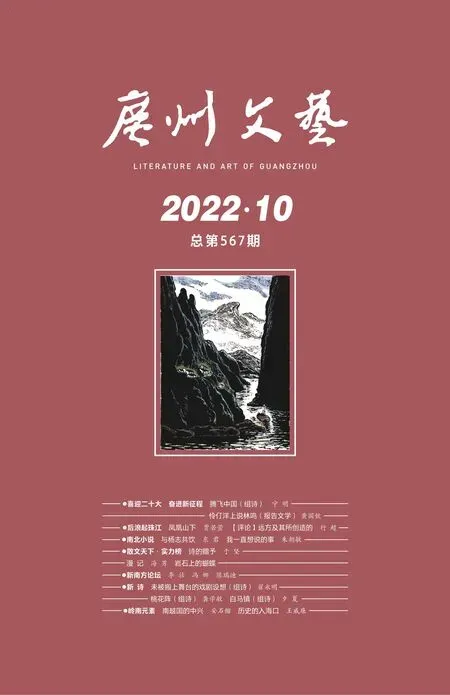诗的赠予
于 坚
以文为生
在写作四十年后,我愈加坚定地认为,写作应当回到文章。汉字一开始就是文,文,错画也。章,彰显。以文去敝,解放敞开动物性生命。文明,以文明之,以文为黑暗的动物性生命去敝、照亮。人通过语言的道说,道可道,非常道而超越,成为仁者之人。“系辞焉,以辩吉凶。”这是一种开天辟地式的超越。这种语言超越在西方,只是晚近才觉悟,比如海德格尔、德里达。
在云南许多古老民族的祭祀中,说唱史诗总是现在向过去追溯,直到开天辟地之时。他们不敢忘记自己是谁,从哪里来,由此知道自己要去何处。孔子称为温故知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即是在场的,也是对出生的知。
文章乃是中国文明的持久传统。只是在“五四”后才被遗忘。今天我们不写文章,写作是分类的。传统中国的作者叫作文人,诗人一词与文人同义。其实,只有诗人,没有小说、诗、散文……之类的划分。
是语言令我们成为作者而不是小说、剧本、散文或者分行排列的白话诗。
语言是一种镜子,某种“他者”,令我们发现自己是谁。没有语言,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而他人也在镜子中。语言令我们记起自己,这是一种可疑的记忆,形同虚构。我不喜欢虚构这个词,这令人以为写作就是凭空捏造。语言不是虚构,人作为人只在语言中才存在。没有语言,人与兽无异。语言记录的是对发生过的可疑记忆,而非事实,事实没有语言。就像结绳记事,一种最原始的形而上的仅仅关于要点的、点到为止的记录。人一旦在语言中存在,他就没有事实了。文章的高明就在于它知道那不是事实,那是敞开。
写作是写意思还是写语言?我认为是后者。
人、社会、时代、历史……没有语言,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系辞焉,以辩吉凶。”(《易传》)人通过语言而在。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早就确立了语言的本体论地位。
言,言说;说,释也,解释说明。(《说文》)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毛诗序》)
文是言的载体、物化。“文,错画也。象交文。凡文之属皆从文。”(《说文解字》)“其旨远,其辞文。”(《易·系辞下》)“经纬天地曰文。”(《左传》)“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合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
我们用文写作,而不是别的什么。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艺,种植。”(《说文》)“艺术就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因此,艺术就是真理的生成和发生。”(海德格尔)
文,中国独有。文明,就是以文照亮。
文意味着对无、对不可知者的象征性转移,表象化,知白守黑、有无相生。以期获得某种冥冥中的“灵晕”(本雅明的词),与诸神对话,持存一种“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dos者”。(陈寅恪)
文的诞生是惊天动地的事件,所以,天雨粟,鬼夜哭。巴别塔再也建不成了。
文天人合一,能指和所指在文中无法分开。其品质在度的掌控,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就是存在的敞开、此在。文不仅仅是展示个人聪明才智的修辞造句活动,修辞立其诚,这是汉语写作的本具,在世界写作中独一无二。
汉语这种古老的写作(种植)被遗忘了——“写,置物也。”(《说文》)
在以神照亮的世界中,语言只是通神的天梯、工具。世界是作者们写的对象。能指和所指的分裂,令这种写作总是在两极之间摇摆。或者意缔牢结,或者追求所谓纯粹写作,以摆脱意义的困扰、阻滞,是西方写作的根本焦虑。
19世纪以降,繁文缛节意缔牢结,文垂死。山崩地裂,对文的怀疑开始,之前汉语从未怀疑过“文明”,导致了写作的革命。受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影响的“拿来”式写作,成为汉语写作的主流。一向道法自然、师法造化的,混沌、“篇终接混茫”“曲径通幽”的文在直线式修辞面前开始自卑,自惭形秽,文声名狼藉。文人成为一个贬义词。“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刘挚)
文体必须界限分明,已经成为一种德性。文不再是一种“种植”“置物”,而是各种壁垒森严的专业修辞技术。
与未来主义不同,道法自然、温故知新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真理。
写作就是文,就像“文”这个字既是名词也是动词一样。在名词,它的意思是,写一切。文人就是写一切,司马迁、李白、苏轼都是伟大的例子。文人一词其实统括了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评论家、记者、画家的身份。在动词,它的含义起源更早,文,错画也。文就是为世界文身。山水诗、山水画都是在为大地文身。诗、文章、绘画、舞蹈、音乐无不源自文身。文是古代萨满教祭祀向书面的一种转移。文就是祭。随物赋形,这个形是不确定的。在一篇文中,即将出现的是随笔、分行的诗、小说、评论或者图像……这是不确定的。
中国古代那些伟大的经典无不是文。《尤利西斯》的风格极似《左传》。严肃的作者应当已经注意到,西方19世纪末以降的写作都在努力脱离传统的线性写作,写得更自由,更随心所欲,更没有文体界限。乔伊斯、普鲁斯特、罗兰·巴特似乎都在将他们的写作“随笔化”。
拿来主义到今天,已经越过模仿学习的阶段,拿来就像一种药,开始发生某种始料未及的效果。这种药不再是指向虚无的千禧年,而是开始复苏已经被遗忘的记忆,文转世的时代到来了。就像西方现代主义通过塔希提岛、黑森林之类的地方重新想起希腊。我最近与一位印度作家也谈到此,英国就像一种醒药,提醒了印度自己到底是谁。
汉语是一种大地语言,上善若水,随物赋形。这意味着写作是文的流动,而不是形的凝固。
“给平庸的东西以威严,给日常的现实以神秘。”(诺瓦利斯)
“将过去被抹杀的意义、陈腐的意义、当下的意义、新奇的意义、最古老的意义和最现代的意义熔为一炉。”(艾略特)
“写作:是世界和语言之间的某种路径,而不是语言产品的结构形式。”“反对一切‘凝固’的事物。世界不再以对象的方式呈现在我面前,而是出现为写作的形式。”“有多少篇片段便有多少文章起头,也便有多少的乐趣。”“利用短的片段提炼出永远新鲜的话语、强烈、动态,不固着于特定位置……盲目似的、不向任何普遍意义、宿命意念、精神超越开放:总之,是纯粹的漫游、无目的性的流变……而一切,会尽可能地、突然且无限地重新开始。”(罗兰·巴特)
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苏轼文集》)
就像汉字书写中各个笔画、构件之间的关系,个人化的手书,笔画(字典)是一套,但永远没有两个字的结构、气韵、场域是一样的。各种断句、碎片、细节、故事、分行、记录、叙述、表达、引文……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条直抵主题、意义的直线,而是迂回、协调、商量、讨论、停顿、尊重……随笔而至,最后抵达一种恍兮惚兮、大象无形之境,一个语词的场,一场语词祭祀。“艺术是历史性的,历史性的艺术是对作品中的真理的创作性保存。艺术发生为诗。诗乃赠予、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海德格尔)“写,置物也。”(《说文》)
“《奥德赛》之所以新颖,是因为它使一个像奥德修斯这样的史诗英雄与‘女巫和巨人、怪物和食人族’斗争,这些处境,属于更古老的传奇类型,其根源是‘古代寓言的世界,甚至原始魔术和萨满教的世界’。按照霍伊贝克的说法,《奥德赛》的作者正是通过这手法向我们展示他的真正现代性,使得作者似乎更接近我们。”(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写作其实不过是一种对语言的回忆。语言的一次次转世。
用过去的“可引用性”取代过去的“可传承性”。
“我不需要说任何东西,仅仅需要展示。”(本雅明)
随笔,随着笔。
我以为现代写作其实是一种文的复活。它以复古的假象呈现着真正有效的现代性。
我最近十年完工的诗集《时代谈话》和“坚记”系列——随笔与图像的文集,可谓实践。
得砚记
2020年1月13日,余在淘宝网闲鱼购砚台一块。出售者为网名“天外石头者”。“现居河南驻马店,80后处女座男生。喜欢美食、电影、旅游、高科技、数码、善良、感性。”2600元。砚长19.5厘米,宽13.5厘米,厚3厘米,灰绿,近橄榄色,很素。墨池为桃形,蓄墨坑为月牙形。桃池边围着两根鹤头枝,缠绕着叶片,简洁不繁。
砚台左侧行书刻字:“试此砚乃出于粤东山溪之下,石乃是绿色端石也。考用其性,细润而坚洁,品之极贵也矣。太宗十三年九月 中浣 旭清氏心赏。”末端为两个方印,篆书“金永”。
太宗十三年。爱新觉罗·皇太极,庙号:清太宗,年号:天聪与崇德,1626—1636年在位,1643年(农历癸未年)逝世,立庙号太宗。(皇太极逝世后立庙号太宗之后的第十三年就是1656年,丙申年。)
中浣——浣乃唐制,官吏十天一次休息、沐浴,每月分为上浣、中浣、下浣,后来借作上旬、中旬、下旬的别称。
右侧行书刻字:既端其方如珪如璋,清而且洁寿命永昌 旭明氏 题 逸园子心赏。
背面刻放鹤图,图上有穿长袍的老翁(头系东坡巾?)和童子、云、凉亭、水、树、沙洲、四鹤。皴法。行书刻字:悬峰古道论前修,不染红尘一点尘,只谓频年风流气,深荫云里唤鹤游。云谷子 甲午年秋八月 中浣 凫山濒风老人藏(凫山在山东)。
甲午或许是1714年。所以,侧面在先,背面后刻。
文字是文字,文字古老。石头是石头,难以断代。注水于池,研墨,立刻洇出黑来,是块砚台。
“他端详手中的物品,而目光像是能见它遥远的过去,仿佛心驰神往。”(本雅明《打开我的藏书》)这块石头确实唤起了这种感受。
就在我桌子上。继续用。
一块端砚
奧东山溪的一块石头 开端于1655年秋十月
旭清氏理解了它 那是清太宗驾崩后第十三年
理解了它的细润 它的方 它的坚洁它的形而上
品质 如珪 如璋 真谛在握的一生知白守黑
旭明氏追随 逸园子心赏 1744年传到凫山
濒风老人手中 因此“不染红尘一点尘”(铭文)
之后出入于时间与空间 阴递给阳阳转给阴
一次次从死亡(粉身碎骨)那儿脱手春秋代序
文章升起 文章沉沦 转动宇宙之轮2019年
冬天传于我 再次上手 注入清水食指放在
墨锭顶端 拇指和中指 夹在两侧腕子用力
混沌初开 一团黑暗洇出如乌鸦诞生道可道
端午有感:关于故乡
公元前278年,伟大的中国巫师、文人——屈原殁于江。
屈原殁前唱道,“去终古之所居”,这令他痛不欲生。
“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对于屈原来说这是最根本的悲剧。政治上的失意倒在其次,甚至无足挂齿。刻骨铭心的是“去故乡而就远兮”。
贺知章回到故乡:“乡音无改鬓毛衰。”
故乡曾经令杜甫:“漫卷诗书喜欲狂,青春作伴好还乡。”
卡夫卡说:“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名副其实的,比如现在,人的根早已从土地里拔了出去,人们却在谈论故乡。”虽然根已经被拔去,但人们还在谈论故乡。无论屈原还是卡夫卡,失去故乡都是心痛之事。“月是故乡明。”(杜甫)
故乡意味着母语、记忆。
意味着人与世界的那种最本真、最干净的、开始的、原初的关系。
卡夫卡的现代性正在于某种对“工业化”导致的异化、遗忘的怀疑和迷惘,他的教育是支持启蒙的。卡夫卡失去的东西,马克思早有预见:“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讲的就是故乡。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个道不仅是政治之道,更是生命之道,它重要到这种程度,不行,生命就像漂浮于大海上,失去根基,危机四伏。孔子之道来自故乡,而非别处,这一点往往被释者忽略。“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
故乡赋予人们最根本的存在感。“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言是母语之言。人类精神世界因此敞开、植根、开化、升华、深邃,记忆之源自此打开,文章出世,温故知新成为可能,涌出那种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
只有故乡知道你是谁。当尤利西斯九死一生回到故乡。“牧猪人紧紧抱住神样的俄底修斯(尤利西斯),热切亲吻,似乎他正逃脱死的逼难。他放声号哭,开口说道,用长了翅膀的话语:‘你回来了,尤利西斯,像一缕明媚的光线。’”
在荷马这里,在路上意味着朝着死亡,归乡则是回到生命。“牧猪人端出盆盘,放在他们面前,装着烧烤的猪肉,上回不曾吃完,剩留的食餐,迅速拿出面包,满堆在篮里,调出美酒,蜜一样醇甜,在一只象牙的缸碗,下坐在神一样的俄底修斯对面。”
没有故乡,人类不会发生文明。只有动物世界才永远在路上,哪儿有吃的上哪儿去,居无定所。
每个人都难逃“去终古之所居”的命运,因为去终古之所居乃为人类的欲望驱使。借助现代技术,这种趋势已呈摧枯拉朽之势。甚至,手机都在摧毁手这个劳动者的亘古故乡。
《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亲,至也,近也。
失去了故乡,就失去乡亲。现代人其实是一种举目无亲之人。
当马尔库塞所谓的“陌生人社会”到来,人们会发现这不过是故乡的失去,人和人再也无法实现基于空间的亲近、关怀、仁爱。“他人就是陷阱。”(萨特)好听点,不过是合同、契约。作为孤独的个人,当灾难到来只有孤军奋战,好自为之。
曾经在我的老家听到一个故事:我的一位叔叔,突殁之际还很年轻,没有备寿材。祖母将自己备的柚木板先给他,将他的青春激昂之躯放进那古老的安静小房间,挨着曾祖父。
故乡意味着存在的确认。衣锦还乡,如果没有乡,衣锦只是虚无。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我在威尔士班戈镇的Kyffin咖啡馆念诗,结束的时候有个中年男子递给我一个字条,上面写着:
POETS
Thomas Moore
Dyian Thomas
W.B Yeats
James Joyce
(诗人托马斯·摩尔迪伦·托马斯W.B.叶芝詹姆斯·乔伊斯)
递给我条子的人显然很骄傲,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胞。
我不知道托马斯·摩尔,回来查了一下,原来他就是《夏日最后一朵玫瑰》的作者。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是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原来的叫作《年轻人的梦》,后来米利金将它重新填词,改名为《布拉尼的小树林》。到19世纪,诗人托马斯再次为这曲子填词,用他自己写的一首诗《夏日最后一朵玫瑰》,于是传遍世界。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夏日最后一朵玫瑰,
独自开放着;
她那可爱的同伴们
都已飘然消逝;
没有一朵同族的花,
没有一颗同族的苞蕾,
来映衬她的如霞红晕,
来回应她的嗟惋叹息。
我不会离开你,孤独的你!
让你独自憔悴消残,
既然你可爱的同伴都已入睡,
那去吧,与他们一同去睡吧。
我把叶片温柔地
撒落到你的床上,
你园中的侣伴
在这里红消香断。
若友谊消散,
我会紧随其后,
而珍宝也在恋人的光环中
黯淡了它的颜色。
当真心全部凋零,
当多情全都飘散,
噢!谁还会独自苦守
在这凄凉荒寒的宇宙!
(考拉 译)
通行的译文为了便于合曲,译得太油腻了。
考拉译得好,有了一点涩。诗要涩,像橄榄那样。我有一次说,诗是粗糙的砾石,在以色列荒野上将基督的脚磨得鲜血淋淋的那种东西,伤害陈词滥调的自我感觉良好,而不是鱼缸里的鹅卵石。
记忆汹涌,多年前的夏天,我在一家电影院里听到这歌声,德国电影《英俊少年》。在20世纪80年代,人很容易被外面的世界感动,已经封闭了那么长的时间。我已经不知道忧伤为何物,浪漫为何物。感动至极,《夏日最后一朵玫瑰》就会唱了。唱着在黑暗里漫游,唱着去谈恋爱。有些歌直达灵魂,永远难忘。是的,直达心灵的往往是那些鸡汤,而真正高深莫测者总是被束之高阁。
英国民歌传到中国,我又在它的原籍找到作者。
那一天,班戈镇的Kyffin咖啡馆的小房间里挤满了诗人,里面没有叫托马斯的。
一直以为《夏日最后一朵玫瑰》是匿名者的作品。
匿名乃作品的生之路。
美教
“五四”以来,新青年知识分子一直在散布中国无信仰之论。吾人甚不以为然,且不说这个词乃西来,汉语不这么说。没有这个词并不意味着中国不追求终极价值,没有宗教式的感受。
“信就是所望之实底(实质、凭据、实在),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经》)
中国没有信仰这种意思,但是有诚信。
汉字有“信”这个字,这个“信”不是对虚构者的“信”,不是向上的、仰视的,更某某的。(“信仰”一词乃佛教传入。)
信,诚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周敦颐)“诚者,真实无妄之谓。”(朱熹)“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
这种信是对常的信。“常,质也。”(《广雅》)“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
常就是诚实不欺。这就是终极价值。
常不是一成不变,不易。“生生之谓易”,这就是常。
人生是对常不断认识的过程。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道德仁是常的因地制宜的不同表现)这正是一种宗教式的生活。
“系辞焉,以辩吉凶。”(《易传》)这个终极价值是通过“修辞”(文)表现出来,“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易传》)
信仰,神唯一。中国是信万物有灵,中国的神是诸神,众神。一片云是一位神,一块石头是一位神,一辆单车是一位神,一只鸥是一位神,一个婴儿是一位神,一件古董是一位神,一列火车是一位神,一个汉字是一位神,一碗米饭是一位神……都是神。
这种万物有灵是对“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生的尊重、敬畏、感激、诚惶诚恐、战战兢兢。
《论语》:“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奥者,形而上也。灶者,形而下也。天者,存在也,有也。失去天(灶),祷即无也。”天就是“天地之大德曰生‘这个天’。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人之位来自天,得罪了天这个大德,就没有灶(位),无所祷也,奥就是虚无。
如何才能不“获罪于天”,媚于灶!
“媚,说(悦)也。”(《说文》)“媚,美也。”(《尔雅》)“媚,好也。”(《广雅》)
中国“信仰”是在形而下与形而上“天人合一”的美中。
美不是一个定义、概念。美是一个动词。
媚于灶!
庄子说:“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是以感恩神灵的口吻说到大地。
“善吾生”,善,吉祥。(《说文》)“善,德之建也。”(《国语·晋语》)大地不是科学可以解剖研究的死物、尸体式的东西。大地是有德行的,天地之大德曰生。“德,升也。境界因善行而升华。”(《说文》)
“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尚书》)
德是不可见的,形而上的。人生于大地,又在大地上获得形而上的超越性。大地、万事万物本具德这种超越性。
有无相生,知白守黑。德在万物的表现是美。“充实之谓美。”(孟子)
美是黑暗的、形而上的、先验的、无时间的、变易的。
“天地之美生。”(《管子·五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美乃大地(大块)本具,美就是天地之大德。
“美哉轮焉,美哉奂焉。”(《礼记·檀弓》)
美是超越时间的,轮回不已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康德)时间是朴素的。时间不会做作。
诚实必美。关于美,汉语的说法都与诚实(本)有关:天真、朴素、大巧若拙、大音希声、“贲象穷白,贵乎返本”。“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
“君子务本。”(《论语·学而》)
若论终极价值,则中国之终极价值就是美。
雅驯,就是美的宗教。“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毛诗序》)“雅之为言正也。”(《风俗通·声音》)“雅者,古正也。”(《白虎通·礼乐》)
美不是今天甚嚣尘上的小资美学的所谓“还有诗和远方”,这个不是美,只是一点意思、“漂亮”。
美不是意义。意义非此即彼,此是彼非。
美是对意义的超越。“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
意义总是陈词滥调。
屈原指出过“美政”。“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
美是人之为人的大事。“仁(德的另一个说法)者人也”,美是人与动物性生命的根本界限。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不学诗,无以言。”(孔子)人通过文章(语言)彰显美,为美去敝。李白所谓“大块假我以文章”,就是万物有灵,万物都是可以成为文章,世间一切皆诗。文章就是终极价值的转喻式载体。文章是对终极价值的尊重,敬畏、去敝、敞开。所以中国产生了文教(美教)而不是宗教。文教就是中国的宗教,文庙就是中国的教堂。
根本上,可以说,人就是文人、诗人,而不限于作者。
美乃是中国之终极追求,因此创造了诗国、艺术之国。自古以来都是世界上诗、艺术最发达之社会。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孔子、庄子、老子、阮籍、王维、李白、杜甫、苏轼、白居易、朱熹、王阳明、钱穆……都是中国的圣徒。注意,这些圣人都是文人而不是教宗、牧师。但是其执着、诚信、牺牲:“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又何曾亚于耶教、佛教的圣徒。
西方,19世纪尼采主张以“艺术形而上”取代上帝。艺术形而上就是“美政”。在1972年的一次讨论会上,当有人冲着博伊斯吼道“您谈论上帝啊,世界啊,就是不谈艺术”时,博伊斯冷静地回答道:“可上帝和世界就是艺术啊!”博伊斯认为,艺术具有革命潜力,艺术创新是促进社会复兴的无害的乌托邦。
不美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那是动物之生。
味道、美味,不美的味就是动物之味,无道。
今日生之郁闷盖在于:一切都是“有点意思”,追求个意思,但不美。
不美,必无信仰,无终极价值。
“尽美矣,又尽善矣。”(孔子)美在第一,善第二。善是意思,此善非彼善。陆游说“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行不远,因为不美,只是有点短平快的意思。
论大地性
各民族真理的可信都来自一种大地性。
《圣经》说光是好的。树木花草是好的。日月星辰是好的。昼夜,分别明暗是好的。飞鸟与鱼类是好的。地上的活物是好的……
这就是大地性,没有大地,神就无法指出什么是好的。
《论语》则不说什么好、什么不好,什么有用、什么无用。第一句是“子曰,学而时习之”。这个子是一个人,这个人开天辟地张口就说:学而时习之!
学吧,不断地学吧。
没说学什么。这个学是不言自明的。
学什么?“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天地就是庄子所谓的大块:“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也就是老子所谓“道法自然”。
先验的一切都是好的。
自然而然,学就是了。
“未知生,焉知死。”学就是知生。学那个“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大德,学那个“生生之谓易”者。
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是啊,子如不言,小子何由述焉?“系辞焉,以辩吉凶。”(《易传》)
言,辞,就是语言。学就是学语言。人超越动物群,说出万物有灵,只能通过语言。语言即存在。语言意味着人终于与大地发生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道法自然”。
语言是大地的转喻。语言记录、转述大地。人因此获得真理性、超越性,“物物而不物于物”,这就是大地性的语言转喻。
《论语》之学与《圣经》之学不同,《论语》学一切,学的是存在。
《圣经》学的是“好的”。“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语言是“向好”(例如天堂。更好的是天堂而不是大地)的工具、阶梯。
“大块假我以文章。会桃李之芳园,序天伦之乐事。”(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黄金时代的中国文章,是写一切,一切都好。
好,“表示男女亲密相处”。(《象形字典》)“好,美也。”(《说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种好。“充实之谓美”(孟子),美是好的充实。
古代中国的诗歌都是大地之歌。感激与敬畏乃是两个永恒的主题。
山水画也是,大地赞美。人相对小,面目模糊如树叶。
学好的,是一种有用性。学一切(大地),不问是非,导致了不同的文明。更好的,是对好的虚构,导致大地本具之好最终被抛弃。
更好的是水泥,因此泥巴不再信了。更好的是水管,于是水井不再信了。更好的是飞机,于是鸟不再信了。更好的是味精,于是盐巴不再信了。
不信的结果是,人失去了大地。
人自己将自己囚禁起来,因为不信,或者只信自己,其他一切都可疑,人洁身自好。所以今天,这个世界无可救药地患着洁癖。抑郁症乃洁癖所致。
手机也是洁癖,失去了大地性,人自己将自己囚禁在这个小机器中,时时刻刻在“更好着”。
古典中国的形而上世界,须臾不能脱离大地。
美不是洁癖,美就是大地。大地是先验的好,而不会更好。
不美(不生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就是中国的真理,形而上学。
咏而归。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这是一种大地上的生活,美的生活。
叫魂
在云南,有时会遇到女巫(师娘)。这些古老的灵魂王国从业者站在高山边上为亡灵和生者叫魂。
宰杀牺牲,洒酒于地,吟唱只有神知道含义的歌曲。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就是这一套,在中原地区失传已久,在云南的高山峡谷中还在继续。
叫魂是一个祭祀之场。正如孔子描述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迩远、多识。
一些邻人围着她,“白象似的群山”,巨大的天空。云烟苍苍兮万物有灵,诸神不语兮溪流喧响。
我们在公路边停下来,抛锚,魂被叫住。
叫魂这种事是无法实证的。它只是带来一场祭祀、一个玩场、一种表演、一种催眠……以缓释某种紧张、恐惧、害怕,或者抑郁。
弗洛伊德是现代的叫魂者,弗洛伊德更像一个技术时代的巫师。他与师娘不同,他试图将灵魂这种东西分析成一种知识、一套体系:潜意识、力比多、自我、本我、超我……其实就是灵魂一词的异名同谓。弗洛伊德被一些教授视为骗子。
弗洛伊德的实验室太冷酷,太做作了。因为他的精神分析学是一种对生病的灵魂的治疗。灵魂不是疾病,也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完美的作品就应当一挥而就——我们欣赏完美的作品时,往往忽略掉其创作问题,而只是愉悦于眼前的作品,仿佛它是魔棍一挥,便从地下跳出来似的。在这里,我们仿佛还处在一种古老神话感觉所遗留的影响之下。我们还有这样的心情,好像某个早晨有一位神灵,游戏似的用这些巨材盖了他的住宅,或者好像有一个灵物,突然被魔法镇入一块巨石,现在想借此诉说。艺术家知道,他的作品唯有在使人相信是即兴而作、是奇迹般地一挥而就之时,才生出圆满效果。所以,他巧妙地助长这种幻觉,把创作开始时那热烈的不安、盲目抓取的纷乱、留神倾听的梦幻等因素引入艺术,以当作欺骗手段,使观者或听者陷入某种心境,相信这完美的作品是一下子蹦出来的。不言而喻,艺术科学断然反对这种幻觉,指出悟性的误解和积习,也正是由于这些误解和积习,悟性中了艺术家的圈套。”尼采这一段讲的就像是叫魂。
杜甫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字典对魂这个字的解释历来语焉不详,说不清楚,很难定义。
就字形来看,这个字由云和鬼组成。
云,指给你看就是。鬼则指不出来。
《说文解字》: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鬼阴气贼害,从厶。
汉字中有许多与魂组合的词,恐怕是世界上最多的:魂胆、魂舆、魂质、魂洲、魂子、魂报、魂常、魂车、魂出、魂床、魂意、魂衣、魂旦、魂想、魂守、魂爽、魂髓、魂台、魂亭、魂庭、魂消、魂销、魂神、魂鉴、魂交、魂轿、魂精、魂景、魂痕、魂骸、魂蝶、魂断、魂幡、魂旛、魂构、魂府、魂干、魂识、魂帕、魂露、魂灵、魂楼、魂梦、魂牌、魂瓶、魂魄、魂气、魂人、魂色、魂舍、魂兮、魂牵梦绕、魂萦旧梦、魂耗神丧、魂归故里、魂飞湮灭、魂傍要离、魂慴色沮、魂亡胆落、魂亡魄失、魂消胆丧、魂消魄夺、魂消魄散、魂消魄丧、魂销肠断、魂销目断、魂压怒涛、魂摇魄乱、魂依姜被、魂不附体、魂丧神夺、魂不赴体、魂不守舍、魂不守宅、魂不着体、魂惭色褫、魂驰梦想、魂颠梦倒、魂飞胆颤、魂飞胆裂、魂飞胆落、魂飞胆破、魂飞胆丧、魂慑色沮、魂牵梦萦、魂祈梦请、魂劳梦断、魂梦为劳、魂飘魄散、魂飘神荡、魂飞目断、魂飞魄荡、魂飞魄散、魂飞魄扬、魂飞魄飏、魂飞魄越……
这是一个可以加在任何一个汉字上而不会不通的字。万物有魂。
魂兮归来!
东方不可以托些。
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
彼皆习之,魂往必释些。
归来兮!不可以托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
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往来倏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屈原《招魂》)
屈原就是一位巫师。
“噫吁嚱,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李白的《蜀道难》也是一场叫魂,大地之魂。
他们的叫魂都成了文字。“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陆游)
在云南高原,叫魂还没有成为文字。
那日,在元阳县的大峡谷边走,惊心动魄。司机是内陆来的,开惯的路是一马平川。越开越怕,淌着稀汗,脖子潮湿。不再信任他的开车技术了,紧紧抓着扶手。忽然看见公路边有人在跳舞,就停下来。是一位师娘正在招魂,几位乡亲跟着她。他们在公路边坐着,吃肉、喝酒。师娘坐一阵又站起来对着天空、峡谷跳舞,唱起来,一只鹰在她的声音中飞。她已经是老人,慈眉善目、精神矍铄,脸上放着光彩。一位乡亲走来,管我们要点钱给师娘,说是让她为我们唱一段。给了一点钱,师娘就对着我们唱了,她穿着一身绣片(丝、银子、翡翠)连缀成的长裙,打扮得像一只锦鸡。不知道她唱了什么,那人说,她的意思就是祝你们一路平安,幸福吉祥。
风景好,声音好,人好,听罢心里高兴,心落地了。后来司机开车也稳当了,平安到达。那个地方叫阿者科,我写了一首诗:
阿者科
时间之旋涡 大地的几何学呈现为
梯形 只有信神者知道并实施
他们崇拜泉水 大树 石头和老鹰
劳动与时日 生殖与死亡 日复一日
测量出每一块坡的深度 每一条岭
的光 一锄头一锄头修改着通天的梯子
就像康德的笔在修改 《证明上帝
存在的唯一可能的证据》 无数次
抵达伟大与光荣 被朝阳选举为
带路的人 在落日的欢呼中回到黑夜
一个秋日 我在前往阿者科的路上
遇到这些古铜色的哈尼族农人
他们的红米如此饱满 爱情如此诚实
语言如此吝啬 沉默是金 脚掌一次次
陷入土地 脚踝上全是褐色的泥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