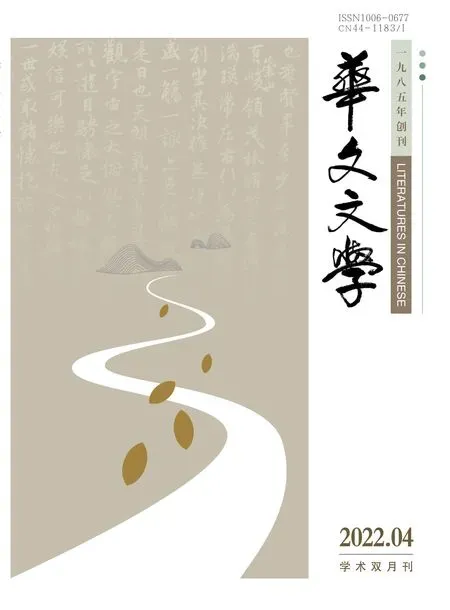伍慧明传记小说的幽灵批评
汪顺来
伍慧明(Fae Myenne Ng, 1956-)出生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的第一代华人移民家庭,是继黄玉雪、汤亭亭、谭恩美等之后活跃于当代美国文坛的华裔女作家,也是位敢于直面华人移民历史的传记小说家。她的传记小说《骨》(Bone, 1993)和《望岩》(Steer Toward the Rock,2008 或译为《向我来》)基于自己的家庭经历和华人移民群体的历史记忆,将传记的真实和小说的虚构糅合到一起,编织“一部由个人、家庭、民族的历史和政治问题构建的民族寓言”①,重写被美国官方历史掩藏或抹杀的真实故事。两部小说具有典型的自传体叙事特征,都是以唐人街华裔“契纸家庭”的日常生活为题材,揭示移民法案给华裔家庭造成的精神创伤,从而批判美国移民政策的种族主义本质。在美国种族主义政治制度下,“契纸儿子”、“契纸父亲”、“契纸家庭”、“坦白计划”等已经成为早期华人移民心中难以言说的痛和不可告人的秘密,这些秘密如幽灵般地萦绕在他们心头,挥之不去却又无法忘怀,逐渐沉淀为他们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创伤记忆。本文基于幽灵批评的思想和观点,以伍慧明传记小说《骨》和《望岩》中的幽灵人物为切入点,剖析他们“怪异”的心理空间,揭示美国主流文化霸权下华人移民的幽灵身份。
一、幽灵批评之“幽灵意象”和“幽灵性质”
幽灵批评并不成理论体系或流派,仅是一种具有幽灵性质的批评,具有神秘性和不确定性。何谓幽灵性质?就像海德格尔笔下“在删除下书写”那样,是一种包含存在与不在、有形且无形、删除与痕迹的矛盾体。德里达说:“一部名著如同一个鬼魂,时刻都在运动之中。”②根据德里达的观点,文学文本具有幽灵性质,变化无常且捉摸不定。英国学者沃尔弗雷斯认为:“当代许多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显性的或隐性的文学‘幽灵’之上,即形成于文学的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神秘纠结中。”③可见幽灵批评是以剖析文学文本中的幽灵意象为出发点,进而探索文本潜藏的隐秘因素。
(一)形形色色的幽灵意象
谈到幽灵意象,我们自然会想到“鬼”、“灵魂”或“魂灵”、“精神”或“精灵”等令人恐惧的东西,它们是人死后脱离肉体遁入另一个世界的变形。荷马史诗《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都有幽灵意象的出现,体现了文学处理和揭示秘密的怪异手法。这种手法的怪异或高明之处在于幽灵意象的选择,恰当的幽灵意象能更好地揭示秘密和推动情节的发展。
《奥德赛》中,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在返乡途中遭遇危险之时,首先得到预言师特瑞西阿斯的灵魂的指点:“你不用担心你的船只没有人引领……北风会抚送船只航行。”④接着又受到好友埃尔佩诺尔魂灵的恳求和母亲安提克勒娅魂灵的指引,母亲告诉他家中的变故和自己的死因:“须知我就是这样亡故,命运降临……是因为思念你和渴望,你的智慧和爱抚夺走了甜蜜的生命。”⑤荷马选择特瑞西阿斯的幽灵意象为奥德修斯回乡指明方向,尽管路途凶险,但终会平安到家;又以其好友和母亲的幽灵意象昭示奥德修斯的艰难处境,战争夺走了好友,命运带走了母亲,他得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孤独前行。但丁在《神曲》中选择诗人维吉尔和情人贝雅特丽齐的幽灵意象,表达自己对理性和爱情的信仰。前者指引幻游者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看尽了教会统治的罪恶;后者指引但丁步入天堂,看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曙光。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将幽灵意象搬上了舞台,开辟了幽灵戏剧的先河。剧中亡父的灵魂出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对王子哈姆雷特透露了一个谋杀的秘密,并赋予王子复仇和扭转时局的使命。可以断言,“没有哈姆雷特父亲的幽灵出现,哈姆雷特的性格和行动便均失去了依据和基础。”⑥从此,欧洲文坛徘徊着形形色色的幽灵意象,尤其是18 世纪的哥特小说大肆描写鬼魂、恶魔、幽灵等,揭示人性中的非理性一面,营造神秘恐怖的气氛。到了20 世纪的现代和后现代文学,幽灵意象从后殖民历史话语开始,蔓延到弗洛伊德主义的“怪异”心理和德里达的解构视域。
(二)历史的幽灵性质
幽灵意象是隐约存在于文本内的幻象,在诉说的同时又保留着不可告人的秘密。德里达说:“一切都从幽灵的幻象开始,确切地说从等待幻象的出现开始。这样的等待在刹那间是急躁不安、焦虑重重,又是令人恍惚的……幽灵将会出现。”⑦幽灵是在焦虑的等待中忽现,这种等待是痛苦的煎熬,是对过去事件和历史记忆的再回首。
对于这种感受,伍慧明的传记小说《骨》将“契纸儿子”的复杂心情表现得尤其到位,再现了华人移民那段难以言说的历史。“契纸儿子”利昂一直生活在焦虑中,他为自己没能兑现将“契纸父亲”的遗骨带回中国而悔责不已:“利昂一直担心那些遗骨,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比如失业、失去外卖店的竞标、失去翁梁两家合开的洗衣店。利昂甚至怨恨那些遗骨,但最终它们还是留在了这里。”⑧利昂的担心源自内心痛苦的等待,等待“契纸父亲”幽灵的出现,等待它报复自己的不守诺言;同时他怨恨自己的无能,不能让“父亲”魂归故土。小说中的遗骨象征着华人移民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幽灵,它隐含“契纸父亲”和“契纸儿子”间承下的诺言。这种诺言好比诅咒,对失信者的报复,对美国种族主义制度的控诉。因此,遗骨里藏着历史,那段早期华人移民在美国遭受的屈辱历史。
根据幽灵批评的观点,文本中的历史并非按时间顺序线性发展,而是已逝的过去对现在的不断侵扰。因此,历史就是那幽灵,或者说是幽灵出没的场所。沃尔弗雷斯说:“文本中的幽灵既不能令人感到保存了历史,也不能让人觉得摆脱了往昔。”⑨基于此观点,小说叙述历史时,离不开幽灵的参与,因为幽灵复活了过去,从而方便了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使得历史被生动地呈现给读者,同时叙述者对于幽灵充满着疑虑和困惑,留下许多不确定性。
二、华人移民的幽灵意象
传记小说属于传记文学,融忠于事实和历史的传记与基于虚构和想象的小说为一体,体现了传记的文学性。王成军认为,纪实传真是自传(传记)文学作家追求的最高叙事伦理⑩。但是传记小说显然逾越了这一界限,更加注重人物个性的塑造,从而偏离了“真实”。为了展现早期华人移民的创伤历程,伍慧明的传记小说,确切地说是自传体小说,以华裔家庭为单位,将自我叙述和叙述他者相结合,再现华人移民的悲怆历史。在历史叙述中,伍慧明跳出了传记小说的传统修辞模式,将传记虚构成传奇,书写人物的幽灵意象,彰显特殊语境下人性的扭曲。
(一)“父亲”的幽灵意象
伍慧明出生于“契纸家庭”,其父曾花4000 美元购买“纸生子”的名额移民到美国。《骨》是伍慧明的处女作,一部典型的华裔自传体小说,围绕生活在旧金山的移民家庭梁家的生活经历,突出表现了第一代华人移民与其后代间的恩怨,以及他们在同化和排斥之间的痛苦挣扎。小说的名称与内容中“骨”的意象相呼应,暗示中国文化传统对早期华人移民的影响,即使尸体腐烂了,但是遗骨尚存,会永远铭记历史。伍慧明借家庭传记的外壳,充分展现了美国华裔作家的想象力,将历史记忆的“碎片”粘合起来,形成融“家族故事、历史事实与文学想象交结在一起,展现出一幅幅现实与梦幻相交叠的、充满神秘主义气息的图景。”[11]美国华裔作家擅长鬼神、魂灵等意象的书写,将传记小说塑造成传奇故事,如汤亭亭在《女勇士》《中国佬》,谭恩美在《接骨师之女》中编织了一个个虚无缥缈的鬼魂世界和异域色彩的中国。但是伍慧明并不囿于鬼故事的讲述,而是以“遗骨”为证,重述那段被美国主流社会有意忽略的历史。
伍慧明对美国华人移民史上“契纸儿子”或“纸生子”(paper son)现象非常关注,揭示“纸生子”概念的悖论性和荒谬性。“纸生子”是移民潮、“黄祸论”、旧金山大地震等共同作用的结果,是19世纪后期美国移民政策变化造成的历史现象,它是“客体的‘纸’和家庭伦理身份的‘子’之间的结合,是虚假性和真实性的叠加。”[12]为了映衬“契纸儿子”的尴尬身份,作者挖出了被“纸”埋藏的“契纸父亲”,尽管“父亲”早已死去,但他的幽灵片刻不离“契纸儿子”,成为无法摆脱的痛苦记忆。《骨》中利昂是个“契纸儿子”,以5000 美元买下进入美国的“通行证”,并承诺将梁爷爷(梁海昆或阿福·梁)的遗骨带回中国,从此梁阿福就成了利昂的“契纸父亲”。由于美国《排华法案》的实施,梁爷爷的遗骨未能如愿地返回祖国,无法实现叶落归根。因此,利昂一想到“遗骨”的存在,就有负罪感,担心“父亲”的幽灵会报复自己的不诚信,会给全家带来坏运气。利昂时常把自己的失业、生意的失败和女儿安娜的自杀与“父亲”的幽灵联系到一起,把所有的不幸归结为幽灵的报应。幽灵就像影子一样,并不占据实际的空间,但是它早已填满了生者的心理空间,成了无法言说的秘密。
(二)母亲的幽灵意象
《望岩》是伍慧明创作的另一部自传体小说,讲述“契纸儿子”杰克的身份转换历程,“为沉默的第一代华裔男性赋予语言的力量。”[13]杰克与利昂一样,游走在“伦理身份的错位、缺失与找寻”[14]中,体现了美国早期华人移民的悲惨遭遇,夫妻不和、代际紧张、身份混乱使得他们成为主流社会的隐身人和失语者。为此,利昂选择了说谎,杰克挣扎于“坦白”。面对《排华法案》的最后阶段——“坦白计划”,杰克陷入了进退两难之中。要么供出他人,良心上受谴责,还可能招致报复;要么被他人供出,从而失去在美国的公民身份和居留权,可能被遣返回国。“坦白计划”是美国政府在1956-1965年期间针对华人群体实施的种族歧视政策,是破坏华裔家庭、摧残华人身心的恶毒计划。其最终目的是剥离华人移民与祖国的联系,以公民身份为诱饵,加快华人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和被美国文化同化的进程。杰克是伍慧明根据自己父亲的经历和文学想象而塑造出来的鲜活的“契纸儿子”形象,“展示了一个华人从此岸到彼岸的人生历程。”[15]对一个“契纸儿子”来说,从痛苦的此岸到幸福的彼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旅程,跋涉者需要勇气和力量。
小说名《望岩》(Steer Toward the Rock)很有诗意,形象地展现了华人移民杰克的“可望不可即”的人生目标。当杰克遭遇险境而迷失自我时,母亲的幽灵意象显现,指引他勇敢地战胜恐惧:“你要相信这块岩石,妈妈告诉他。要腾空你的心,把恐惧在岩石上摔碎。就像河神一样,你要向自然低头,要面对恐惧,相信恐惧,向那块岩石驶去(向我来)。”[16]岩石就是生活的目标,是心中坚强的不可动摇的信念。得到母亲幽灵的指引,杰克终于放下心理包袱,勇敢地走出生活的阴影,找到了做人的尊严。
三、华人移民的“怪异”心理
伍慧明的传记小说,非常注重人物心理刻画,生动地再现了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对华人个人和社区造成的精神创伤。赵白生认为:“传记再现的对象不是纯粹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17]传记小说应忠于传记的真实,但是小说的虚构往往突破了史实的条框限制,突显其艺术性,也透露出传记小说家的创作才能。为了彰显美国种族主义法案对华人的伤害,伍慧明将现实与想象并置,展现高压政策下华人移民扭曲的心理,塑造了一个个活着的“幽灵”。
(一)行为异常的利昂
《骨》的叙述者是大女儿莱拉,她对继父利昂的描述非常仔细,勾勒出一个“纸生子”的怪异形象,一个简直如幽灵般的怪物。“怪异”(Uncanny)与幽灵性质有相似之处,表现为异质个体,不同于正常人。如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所指出的那样,“怪异”是人特定情境下的心理状态,存在着“陌生和生疏感不断侵扰人对周围熟知和安全的心境,或者叫压抑复现。”[18]这种体验是潜在的无意识的感受,是某特定时空范围内创伤如幽灵般的再现。
利昂的行为非常怪异,其怪癖之一是喜欢与废物打交道,他制造出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还收藏废物,如一摞摞快餐盒、锡纸盒、装满番茄酱和糖袋的塑料袋、写着红色字母的白色罐头盒,还有政府发放的蔬菜:切成片的甜菜、表面光滑的绿豆和南瓜[19]。利昂的怪癖行为与第一代华人移民在美国的遭遇密切相关,面对饥饿和种族歧视的双重打击,他们不得不忍受和压抑内心的苦闷。在美国,一切可能成为证据,一切证据可能成为废纸。因此利昂得出结论:“在这个国家,纸张比血液还贵。”[20]因为那些纸张和废物证明了利昂在美国的时间,也证实了他对生活的忍耐。由于求职时曾被无数次拒绝,利昂养成了拼命干活的怪癖。他害怕失业,一直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来证明自己是一个有用的苦力。面对丧女的苦痛和生活的压力,他选择了不停地劳作,试图以劳累忘却创伤记忆。他不是在时间中度日,而是在汗水中奔命。他认为生命就是工作,而死亡却是一场梦[21]。残酷的社会现实扭曲了利昂的心理,将他变成了工作机器和人性麻木的另类。
(二)性格怪癖的杰克
心理分析学说中的怪异理论得到德里达、拉康、克里斯蒂娃等的发展,被广泛用于后殖民文学、族裔文学、离散文学等,旨为阐释内外交困的情境下人物所遭受的精神创伤。这种创伤“是对一个或多个重要事件的反应,时间上往往滞后,表现为重复、幻想、梦幻或事件促成的思想和行为等形式。”[22]精神创伤是一系列不平常的生活经历对一个人心理的长期摧残,结果造成思想混乱、性格怪异的他者形象。他者的人性由于受到侵扰和否定,成为似人非人的幽灵,因为“幽灵是人又非人,它既衍生于生前的人,却又不是那个人,而是那个人的‘他者’;它活着却又死了,是一个活着的死人。”[23]
《望岩》中杰克就是一个怪异的他者形象,或者说是一个活着的“幽灵”。小说以杰克·满·司徒的坦白开始,讲述了一个“纸生子”在美国经受的孤独、恐怖的生活经历。杰克是司徒一通花410 美元购买的“儿子”,取中文名“有信”,意为“言而有信”,作为对父子关系的一种承诺,然而实质上的金钱交易甚于父子情感。杰克为进入美国欠下了司徒一通4000 美元的债务,从此他成了司徒的债务奴隶。为了偿还债务、赎回自由,杰克只有拼命地干活,却怎么也还不完日积月累的利息。杰克看不到希望,孤独的人生让他觉得“自己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一只蝙蝠”[24],一直在盲目地突围,最终还是四处碰壁、惨不忍睹的结局。更尴尬的是情感孤独的困扰,他无权选择感情,无法组织家庭。小说的一开始就将杰克抛入了情感的漩涡中:“我爱的女人不爱我,我娶的女人不是我的女人。张伊琳在法律上是我的妻子,但事实上她是司徒一通的女人。”[25]杰克与司徒订立的契约内容非常荒诞,杰克与司徒的小妾张伊琳名义上的夫妻关系成为他合法入境的幌子,而他与乔伊斯·关之间只能止步于爱情,无法通过结婚组建家庭,以致于杰克与乔伊斯的情感日渐疏远,都变成了孤独的幽灵。
伍慧明不仅对像杰克一样的“纸生子”的遭遇充满了同情,而且非常关注华裔女性的不幸。小说中乔伊斯不敢结婚,女儿维达不愿生育,表明华裔女性遭受家庭创伤后的痛苦抉择。作者以华裔女性的消极选择控诉了美国移民政策对华人群体的精神伤害,尤其是对女性的迫害。杰克的怪异性格与“坦白计划”营造的恐怖氛围密切相关。“坦白计划”是美国移民局对华人非法移民的一次身份大清洗,将华人移民拖入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华人间相互猜忌、彼此不信任扭曲了美好的人性,导致华人社区的全面恐慌。杰克成了另一个哈姆雷特,徘徊在“坦白还是不坦白”的困境中。因为渴望爱情和公民身份,杰克坦白过自己的历史,却并未得到移民局的原谅,也没赢得想要的爱情,而被司徒的手下砍去一只手臂。从此,他活在自己幽闭的世界里。沉默寡言成了杰克的标记,女儿维达善解人意地说:“沉默的父亲是安全的父亲。”[26]在麦卡锡主义笼罩美国的时期,华人移民不得不将记忆封存,将思想禁闭,以免惹祸。种族主义移民法案正在将唐人街一步步变成可怕的“单身汉社会”和灭绝人伦的地狱,到处游荡着孤独的幽灵。
四、华人移民的幽灵身份
族裔文学离不开对身份问题的探讨,身份和身份认同充斥于族裔文学创作和研究的整个过程。华裔美国文学始于传记文学,最早的华裔作品多是自传或自传体小说,如容闳的《西学东渐》(1910)、黄玉雪的《华女阿五》(1950)、汤亭亭的《女勇士》(1975)、谭恩美的《喜福会》(1989)、伍慧明的《骨》和《望岩》等。尽管华裔传记文学的真实性引发争议,但是它对身份塑造的艺术性是不容置疑的。赵白生认为,自传作家往往从特定的身份出发再现自我,因此自传是“作者身份的寓言。”[27]自传体小说融合小说与自传的特点,展现经过修辞处理的自我,旨在艺术般地表现身份的特殊性。华裔美国传记文学“混合了美国官方的权威记忆(历史)和华裔个人的历史(自传、回忆录、日记等)”[28],近乎理想地呈现了美国华裔的动态自我,一个难以判定的幽灵身份。
(一)作为“他者”的幽灵身份
“他者”是与“自我、主体、同者”相对立的概念,可追溯到柏拉图哲学关于同者与他者的定义,指一切从属的、边缘的、次要的低级事物。“他者”泛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和事物,也即是“凡外在于自我的存在,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出现,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都是他者。”[29]尽管自我意识的构建离不开他者,但是二者的对立关系决定了他者的地位。杜波依斯从美国黑人身上找到了“他者”的属性:“一种通过别人的目光看待自己,以周围充满轻蔑和同情的人群来衡量自己灵魂的感觉。每个黑人都具有二重性(twoness)——既是美国人,又是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无法调和的斗争;一个黑色躯体中的两个敌对思想。”[30]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眼中,黑人就是“他者”,一种灵魂被刺痛的感觉。黑人的双重身份是其矛盾思想的根源,因为美国的种族主义政策决定了黑人无权决定自己的身份。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1914-1994)的名作《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1952)形象地再现了美国黑人的身份选择。为了逃避种族迫害,主人公不得不隐藏到地下,成为白人眼中“看不见的人”,或者一个行迹不定的幽灵。
同为美国少数族裔,美国华裔的身份诉求与非裔美国黑人相同。自19 世纪中期开始,迫于饥荒和战争,大批华人移民美国做苦工。第一代华人移民参与了修建贯穿美国大陆的铁路、开发加利福尼亚矿产、开垦夏威夷农场等,足迹遍布美国各地,事实证明他们是真正的美国建设者,应该享有公民身份。但是这些工程一结束,美国就开始挥舞种族主义的大棒,让华人移民失业,遭受被驱赶、被迫害的厄运。作为第二代移民的“纸生子”是《排华法案》(1882)催生的产物,由于不是“土生子”,他们的身份很尴尬,既不是美国公民,又不是华人移民的真正后代。他们举债购买的假身份随时有被揭穿的风险,因此他们设法隐藏自己,成为美国社会里“看不见的他者”。
《骨》中的利昂一直生活在焦虑和谎言中。他担忧自己会失业,担忧“纸生子”的身份被曝光;他不得不说谎,自天使岛入境开始,就以谎言来坐实自己的身份,后来他收集了一堆旧文件,包括求职时“我们不需要你”的拒绝信,用这些废纸来证明自己在美国时间和为美国的付出。但是美国社会残酷的现实总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不停地工作,不断地失业,一直在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同时,婚姻遇挫、女儿自杀、生意破产让他不堪重负,最后他签约到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货轮上工作,以漂泊大海作为总结。
利昂的人生经历是作者伍慧明对以父亲为代表的第二代移民经历的重写,是对“纸生子”身份的重新定义。“纸生子”为美国奉献了大半生,却始终被质疑身份的合法性,是美国社会的“他者”。他们一直在寻求身份认同,却找不到答案,陷入痛苦的身份悖论中:我是美国人吗?可是我没有入籍证明。我是中国人吗?可是我不能回到中国。我两者都不是或两者都是。利昂有同样的身份困惑,为了在美国生存,他只有通过自我否定和编造谎言来消极地回应美国社会,但是他始终“摆脱不了身份悖论的困境,成为飘在美国的幽灵。”[31]
(二)作为“面具”的幽灵身份
“面具”(mask)原指戏剧表演时的演员或狂欢节上的民众遮面的伪装物,后转义为“欺骗、伪装”。英国戏剧家王尔德说:“一个人讲话时,他最不像自己;给他一副面具,他就告诉你真相。”[32]王尔德指出了人的两面性,每个人都披着伪装,在不同的情境下表现不同的自我。爱尔兰诗人、戏剧家叶芝认为:“面具是在行动和艺术领域实现自我超越的一种手段……是无尽的游戏。”[33]叶芝指明了面具的艺术性,它是行动和自我的能指。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格面具”(persona)理论,认为人格面具是人为了适应环境或获取个人利益而具有的功能性情结,“它是人与社会之间关于人应该如何行事所达成的一种妥协……人格面具是一种伪装。”[34]荣格的人格面具理论表明,人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受到人格面具的挤压而被迫妥协,人格因此被扭曲。简言之,“面具”不仅遮掩了身体,而且隐藏了自我,成为不利的社会环境下表达身份的伪装。从舞台道具、人物面具到人格面具,“面具”不仅体现了一种文化,而且成为“一种艺术符号,具有隐喻或象征功能。”[35]“面具”的符号性和艺术性是其在文学中的最好表现,它起到隐喻或象征变异身份的作用。
《望岩》中名字成了符号化的面具,隐喻人物身份的变异。主人公小时候因贫穷和饥饿被卖到司徒一通家,成为传宗接代的养子“梁有信”。后来他购买了“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后改名为“杰克·满·司徒”,用作自己谋生的工具。从此“杰克”成了他脸上摘不掉的“面具”,牢牢地控制着他,成为一个无法言说的秘密。这是所有华裔美国人“假身份”的秘密,是贴在身上的标签和刻在脸上的烙印。种族歧视的高压政策下,老一代华人移民生活在恐惧中,试图借此掩盖自己黄种人的面孔。正如杰克的女儿维达说,“老唐人街的恐惧:不跟生人说话,不回答问题,不要告诉别人爸爸的名字。”[36]爸爸的名字里包含了自己、他的父亲和孩子的身份信息,一旦说破,将会殃及三代人在美国的生存权。小说的结尾处,杰克在入籍仪式上踌躇不决,女儿帮助他选择了“杰克·满·司徒”作为他公民身份的假名字。德里达认为:“选择就是幽灵,即不确定性或幽灵性。”[37]“坦白计划”制造了信任危机,将华人移民逼近心理崩溃的边缘,在忠诚和背叛间艰难抉择,造成了华人群体的精神创伤。杰克选择代表面具的假名字作为自己的真身份,以宣示对美国的忠诚,并暗示对祖国的背叛和黄面孔的否定,但是“忠诚和背叛之间的幽灵性的伦理选择加剧了杰克幽灵身份的矛盾性和悖论性。”[38]
尽管杰克最终成功入籍,但是面具与面孔、忠诚与背叛之间的矛盾选择将伴随其一生,“坦白计划”的创伤记忆如幽灵般不时地显现,再现其对幽灵身份的焦虑。
时至今日,美国种族主义制度仍未消除,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势力不时地抬头,对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实行限制和打压政策,种族暴力事件时有发生。随着新中国的崛起,当代美国华裔感受到祖国的强大力量,但受美国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影响,少数华裔的“中国心”已经发生位移,出现了余茂春之流的民族败类,再次印证了美国华裔的幽灵身份。
五、结语
《骨》和《望岩》堪称讲述唐人街华人移民生活经历的姊妹篇,是伍慧明基于自己家庭的移民经历,凭想象和记忆塑造鲜活的“纸生子”人物形象,并重新发现百年来关于美国华裔的历史文本。“纸生子”是美国华人移民史上独特的重要的一章,与《排华法案》、“坦白计划”和麦卡锡主义密切关联,反映了美国种族主义移民政策对华人的迫害,给华人群体留下了难以弥合的创伤记忆。
伍慧明的传记小说打破了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的界限,重写那段被美国官方话语忽略的华人移民史,编织了一部具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寓言。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此恶劣,华人移民整日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如同游荡在唐人街的幽灵。通过剖析幽灵人物的“怪异”心理和再现华人移民的幽灵身份,伍慧明揭示了美国种族主义政治的实质,即对人权的侵犯和人性的践踏,从而撕下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面具,暴露其丑恶的真面目。
①陆薇:《直面华裔美国历史的华裔女作家伍慧明》,载吴冰、王立礼主编:《华裔美国作家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347 页。
②[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第19 页。
③⑨Wolfreys,Julian.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th Centu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Press,2002,p.259,p.265.
④⑤[希腊]荷马:《奥德赛》,王焕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212-213 页,第225 页。
⑥曾艳兵:《关于“幽灵批评”的批评》,《文艺理论研究》2015 年第1 期。
⑦Derrida, Jaque. Specters of Marx: The State of the Dabt, the Work of Mourning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trans.Peggy Kamuf,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1994,p.4.
⑧[19][20][21][美]伍慧明:《骨》,陆薇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46 页,第3 页,第7 页,第170 页。
⑩王成军:《“事实正义论”:自传(传记)文学的叙事伦理》,《外国文学研究》2005 年第3 期。
[11]詹乔:《美国华裔英语叙事文本中的中国形象》,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版,第182 页。
[12][13]王娜:《“纸生子”概念的旅行及其文学史意义》,《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3 期。
[14]苏晖:《华裔美国文学中华人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嬗变——以〈望岩〉和〈莫娜在希望之乡〉为例》,《外国文学研究》2016 年第6 期。
[15]王小涛:《“纸生子”现象的历史现实与文学想象——以伍慧明〈望岩〉为例的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 年第3 期。
[16][24][25][26][36][美]伍慧明:《望岩》,陆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 年版,第118 页,第11 页,第3 页,第240 页,第238 页。
[17][27]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44 页,第99 页。
[18]Buse,Peter and Stott,Andrew.Ghosts: Deconstruction, Psychoanalysis, History,NewYork:Macmillian Press,1999,p.55.
[22]Herman,Judith L. Trauma and Recovery,New York:Basic Books,1992,p.32.
[23]Bennett, Andrew and Royle,Nicholas.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Criticism and Theory, Harlow, England: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1999,p.241.
[28]Grice, Helena.Negotiating Identities——An Introduction to Asian American Women’s Writing,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2,p.94.
[29]张剑:《西方文论关键词:他者》,《外国文学》2011 年第1 期。
[30]Du Bois,W.E.B.The Souls of Black Folk,New York:Bantam Books,2005,p.3.
[31]王娜:《悖论与解悖——小说〈骨〉中人物的生存境遇及策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1 期。
[32]Ellman,Richard. Oscar Wilde,New York:Vintage Books,1987,p.26.
[33]Brown,Terrence. The Life of W. B. Yeats: A Critical Biography,Dublin:Gill&Macmillan Ltd.,2001,p.177.
[34][英]安东尼·史蒂文斯:《简析荣格》,杨韶刚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 年版,第157-158 页。
[35]赵晓彬:《西方文学中面具理论的产生和发展管窥》,《外国文学研究》2019 年第1 期。
[37]岳梁:《从幽灵到宽恕》,苏州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43 页。
[38]王绍平、闫桂姝:《面具与面孔——解读〈望岩〉中杰克的‘幽灵’身份》,《语言教育》2017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