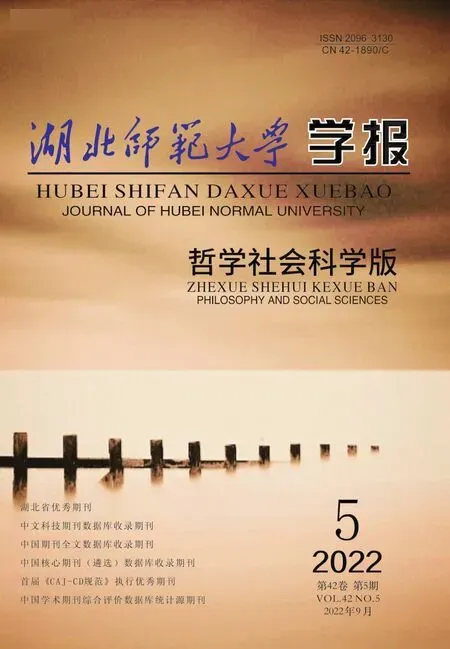从周代音乐考古看《诗经》乐器组合艺术
刘桂华
(湖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2)
《诗经》作品音乐特性,古今无异议。《诗经》涉及乐器的作品有30首:《国风》有《周南·关雎》《邶风·击鼓》《邶风·简兮》《鄘风·定之方中》《卫风·考槃》《王风·君子阳阳》《郑风·女曰鸡鸣》《唐风·山有枢》《秦风·车邻》《陈风·宛丘》等10篇;《雅》有《鹿鸣》《常棣》《伐木》《彤弓》《采芑》《何人斯》《巧言》《鼓钟》《楚茨》《甫田》《车舝》《宾之初筵》《白华》《绵》《灵台》《板》等16篇;《颂》有《周颂·执竞》《有瞽》《鲁颂·有駜》《商颂·那》等4 篇。这些歌诗涵盖周代所谓“八音”之乐。现代乐人根据乐器的演奏方式与声学原理,将“八音”之乐归并为击奏乐器、吹奏乐器、弹弦乐器三大类。而最能体现《诗经》音乐艺术成就的,是大量乐器组合艺术及其演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艺术效果。本文将结合周代音乐考古成果,以印证还原《诗经》音乐的乐器组合艺术。
一、“瑟琴”乐器组合
“瑟琴”或“琴瑟”常并称,它们是周代最流行的乐器组合之一。瑟是一种板箱体弹奏弦鸣乐器,琴是一种带长尾、半箱体弹奏弦鸣乐。[1]两者材质相同,乐音相近,以演奏旋律为主,所以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诗经》言及“瑟琴”的作品有《关雎》《定之方中》《女曰鸡鸣》《鹿鸣》《常棣》《鼓钟》《甫田》等。或连言“瑟琴”,或并提“鼓瑟鼓琴”。《定之方中》写卫文公率领卫人定都楚丘,“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冀用椅、桐、梓、漆木等来制作“琴瑟”,以重建国家礼乐制度。《常棣》“如鼓瑟琴”乃比兴“妻子好合”,亲密无间。《鼓钟》乃配合其他乐器一起演奏。《关雎》是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婚恋之歌。君子“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但锲而不舍,转而“琴瑟友之”,用美妙抒情的旋律终于俘获了淑女的芳心,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曰鸡鸣》写恩爱夫妻或同弋射,或同饮酒,或“琴瑟在御,莫不静好”,“与子偕老”,夫妻生活如琴瑟和鸣,岁月静好。《鹿鸣》写“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宴会主人极尽地主之谊,不仅用美酒佳肴来娱悦嘉宾的味觉,而且还“鼓瑟鼓琴”——用最美妙动听的音乐来娱悦客人的听觉,从而达到交流感情、示好嘉宾的绵绵盛情。
琴、瑟作为相同材质的弦乐器,音色清脆柔美,旋律婉转悠扬,抒情细腻婉约甜美,因而成为周代社会各阶层喜闻乐见的乐器。“瑟与琴是中国最古老的两种拨弦乐器,自西周以来就广为流行。……东周时期,琴瑟已在中原地区的礼乐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琴瑟”材质不易保存,西周早中期实物虽未见,但西周晚期实物却有发现。湖北随州郭家庙曾国墓地M86竟同出琴、瑟,该琴形制完整,可确定为“半箱琴”,这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实物琴。“琴瑟”并出,也是迄今最早的“琴瑟”实物组合。[3]《诗经》作品常以“瑟琴”作譬喻,说明两类乐器流行广泛,所以诗人才能够信手拈来使用。而“琴瑟在御”“琴瑟和鸣”,充分体现了《诗经》时代人们婚姻生活的美满和谐状态。
二、丝弦与击奏乐器组合
这种乐器组合在《诗经》诗作描述中仅有一例,就是《小雅·甫田》。这是一首报祭祈福的祭祀诗,祭祀的是土神、四方神与农神。周代是农业社会,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土神与农神是周人的农业保护神自不待言,而四方神也是农神。商代就有对四方风、四方神的隆重祭祀,因为四方神掌管四时风雨,而风雨与农事的丰歉密切相关。所以,这几位神灵都与周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周人祭祀神灵,多用“钟鼓”乐器组合或钟磬乐器组合,但这首诗却用“琴瑟击鼓,以御田祖。”其原因恐怕是这几位神灵与人们的关系更亲近、更具亲和力,所以节奏型的鼓与旋律型的琴瑟合奏,鼓乐喧阗,琴瑟和鸣,强烈的节奏与流畅的旋律相结合,既热烈隆重又轻松活泼,人神交流也就自然达成高度契合了。
三、埙篪乐器组合
埙是一种罐体气鸣乐器,历史悠久。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黄河流域就发现了大量陶埙。甘肃玉门火烧沟三音孔陶埙,可以吹出五声音阶,殷人的五音孔陶埙已能吹出七声音阶。[4]作为一种非常普及的旋律性吹奏乐器,周埙同样具有很强表现力。篪是一种横吹孔管乐器,双手掌心向里横持吹奏。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竹制有底横笛——篪“平吹发音圆润柔美,超吹音色明亮而有光彩”,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1]《何人斯》与《板》诗都写到埙、篪合奏,但两者都是比喻用法。《何人斯》讽刺反复无常之小人,昔曾与己如“伯氏吹埙,仲氏吹篪”般亲如兄弟,而今却“不愧于人,不愧于天”,“为鬼为蜮”,居心叵测,恶意构陷。《板》诗诗人忧国忧民,眼见政败民困危局,敢言直谏;又用“天之牖民,如埙如篪”——上帝教导人民把土烧制成埙,把竹制成篪,埙唱篪和,犹如瑟琴和鸣一般动听;又苦口婆心讽谏周王“敬天之怒”,爱恤百姓,必将政通人和。可惜的是,两诗所用埙、篪均为比喻,而非对埙、篪合奏美妙音乐的描写。证之考古发现与比喻用法,埙篪组合演奏应为常见。
四、“钟鼓”乐器组合
“钟鼓”是周代最重要的乐器组合之一,常用于上层贵族婚礼、宴飨、祭祀等重要场合。《诗经》“鼓钟”连言12次。
《诗经》叙述中的“钟鼓”既可独自编组演奏,也可“钟鼓”组合或与其他乐器编组演奏。钟声洪亮浑厚、音域宽广,音色极具穿透力,故编钟成为周代礼乐制度下“金奏”乐队中的主导乐器,处于整个乐队核心位置。周钟多成列编组,编钟数量由周初的三件组合、四件组合发展到中期的五件组合,直至晚期的八件组合甚至十六件组合,因此编钟的音程与音色越来越丰富,一套编钟就可构成完整的五声、六声甚至七声音阶,并实现由节奏型向旋律型乐器的转变。虽然《诗经》编钟的数量不详,但出土编钟实物提供了有力证明。陕西宝鸡竹园沟M7出土西周早期编钟三件一组,这是中原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陕西宝鸡茹家庄M1也出土西周相同编钟组合。[5]而湖北随州叶家山M111出土一组编钟5件,含镈钟1件,甬钟4件,保存完好,做工精良,纹饰精美。“全组编钟音高稳定,音调明确,音色醇美。”不仅是已发现西周早期数量最多成套编钟,同时还是最早双音钟。[6]一钟双音是编钟发展史上的重要进步,既拓宽了编钟的表现音域,又改变了编钟的音列结构。[7]叶家山墓曾国编钟的发现,说明西周早期编钟不仅有三件组合、四件组合,可能还有五件组合。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倗国墓地M1和M2各出土钟五件,属西周穆王时期或略晚,恰好证明西周中期前段编钟的五件组合形式。[8]
西周中晚期,编钟以八件组合最为常见。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2001号、2009号墓分别出土的虢季、虢仲编钟,就是8件一组。据测定其“音质优美,变音合理,音律准确,是迄今发现的西周时期音律最为准确的成套编钟。”[9]出土于晋穆侯墓的楚公逆钟,是西周晚期楚公室青铜器,可能是晋人将两套楚公逆钟及一套晋国编钟按音律配比拼合而成为8件套编钟。[10]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西周晚期中义钟也是八件一组,保存完好,测音效果较好,正鼓可调音。[11]由西周早期三件成编、四件成编、五件成编、到中晚期的八件成编现象,说明西周编钟功能已由节奏型向旋律型发展,已确立“节奏十旋律”的声部观念。[12]另外,八件组成编不仅规模更大、更壮观气派,而且音域在四件组的基础上拓展了两个八度至五个八度,因而极大提高了编甬钟的艺术表现力。当然,到了春秋早、中期,在八件加八件的十六件编组已相当普遍,但“8+8”组合对提高编钟的音乐性能关系不大,而只是出于“礼”的宏大才去追求形式上的“美”与“壮观”罢了。[13]
“鼓”:是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它是一种击奏膜鸣乐器。《诗经》共出现22次之多,高居众乐器之首。鼓既可单独击奏,也可与其他乐器配合演奏。《诗经》中“鼓”类繁多,有鼛鼓、贲鼓、鼍鼓、县鼓、鞉鼓等不同种类。鼓声浑厚沉雄,激越奔放,节奏感鲜明,变化多端。《陈风·宛丘》云:“简兮简兮,方将万舞”,舞师未舞先鼓,制造出浓烈的表演气氛。《邶风·击鼓》云:“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战士们在轩昂的鼓乐声中慷慨出征。《小雅·伐木》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这是伐木工人闲暇时的劳动舞乐表演。
当“钟鼓”两种不同材质的击奏乐器强强联合,就形成“两种极不相同的音色的配置,在乐队实践中有利于不同线条的旋律结合在一起 ,增强音乐线条的清晰性和层次感,反映了当时人们已经开始建立音色对置的声部观念。”[12]《周南·关雎》云:“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唐风·山有枢》云:“子有钟鼓,弗鼓弗考?”证诸周代各地诸侯墓葬出土的钟鼓乐器组合,可谓琳琅满目。
周代朝廷各种典礼场合,“钟鼓”组合必不可少。《小雅·彤弓》写周天子赐有功诸侯彤弓大礼,又“钟鼓既设,一朝飨之”,钟鸣鼎食是何等荣耀!《大雅·灵台》写周王游于灵台辟雍,钟鼓齐鸣:
虡业维枞,贲鼓维镛。于论鼓钟,于乐辟雍。于论鼓钟,于乐辟雍。鼍鼓逢逢,矇瞍奏公。
先言“贲鼓维镛”,后言“鼍鼓逢逢”。所谓“鼍鼓”是以鳄鱼皮蒙面的鼓,是从材料说;所谓“贲鼓”是从鼓的大小来说,故二者为一,分说皆可。[1]“镛”通“庸”,是殷周时代一种铜制合瓦形击奏体鸣乐器。无枚者为铙或大铙,有枚者为钟或甬钟。[1]诗中之“镛”应指周钟。周王莅临辟雍,尽情观赏钟鼓乐器组合演奏。《小雅·楚茨》描写的是周王祭祀先祖的鼓钟之乐:祭礼已备,钟鼓响起。孝孙即位,太祝告成。神祖醉酒,神尸起身。钟鼓再次响起,欢送神祖踏上归途。钟鼓组合演奏热烈隆重,表现出强劲的旋律与鲜明的节奏,音乐效果极为震撼。
五、金石乐器组合
主要是指钟、鼓、磬等击奏乐器组合。磬是一种石制板体击奏体鸣乐器,历史悠久。龙山文化时期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就发现4件特磬。商代后期出现了编磬,周代编磬数量从5件编组发展到10件甚至13件,说明西周编磬已从节奏型乐器,逐渐发展成旋律型乐器。《周颂·执竞》写后代周王合祭先祖武王、成王与康王,“钟鼓喤喤,磬筦将将”,钟鼓齐鸣,乐音激烈洪亮,磬筦(管)合奏,乐音清脆悠扬。这是以钟、鼓、磬等击奏乐器为主的祭祀音乐大合奏。证之考古发现,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M93出土编钟与编磬两种,编磬一组10件,编钟两组16件。专家推断,墓主当为春秋初年的晋文侯。[14]这是一种较早而且典型的金石乐器组合。《周颂·执竞》钟、鼓、磬的雅乐组合,应是“钟鼓”乐器组合的发展。而陕西韩城梁带村芮国墓地M27年代略早于晋文侯墓,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编钟、编磬与鼓的乐器组合。该墓计有由8编钟、10编磬、1钲、1淳于、1建鼓、1小鼓等所构成的以击奏乐器为主的组合。编钟仍为四声音阶,而编磬则出现了包括“商”声在内的五声音阶,证明西周末礼乐“商”声的存在。不难想见,这样的金石乐队组合一定能营造出钟鼓齐鸣、金声玉振、乐音飞扬的音响效果。[15]可以说,钟、鼓、磬是周代宫廷雅乐的骨干乐器,处于乐队中的核心位置。钟声清越响亮,鼓声浑厚绵长,磬声清脆悦耳,三者常组合使用于祭祀时合乐演奏。
六、击奏与吹奏乐器组合
这类乐器组合多用于宴飨、祭祀等重要场合。《小雅·宾之初筵》写周代贵族饮宴:
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礼。
宴会开始,钟鼓齐鸣,杯筹交错。宴中祭祖,笙声悠扬,鼓点锵锵,籥舞翩翩,祭礼繁复,但繁而不乱。忽而钟声清脆响亮,忽而鼓声激越高亢,忽而笙声婉转悠扬,既热烈欢快又庄严肃穆。《商颂·那》是宋人祭祀先祖的乐歌。这是鞉鼓、磬、庸、管四种不同材质乐器的大合奏。鼓乐简简,管声嘒嘒,磬声和平,钟声清越,配以“穆穆厥声”与奕奕万舞,载乐载歌载舞,气氛热烈而隆重。宋人用歌乐舞相结合的方式,表达对先祖成汤的崇敬与追思。
周人的宗庙祭祀音乐,比之殷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周颂·有瞽》“是周王大合乐于宗庙所唱的乐歌。大合乐于宗庙是把各种乐器会合一起奏给祖先听,为祖先开个盛大的音乐会。周王和群臣也来观摩聆听。”[16]这是一次包含应、田、县鼓、鞉、柷、圉、磬、箫、管等九种击奏乐器与吹奏乐器的宗庙祭祀音乐大合奏。乐队规模庞大,乐器种类齐全,击柷引乐,一会鼓声大作,一会箫声悠扬,“喤喤厥声,肃雍和鸣”,周人先祖乐享盛大辉煌的祭祀乐歌。最后乐人击圉止乐,音乐演奏获得巨大成功。如此大型的乐器组合演奏,恐怕只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曾国郭家庙墓地M1出土的乐器组合艺术差可比拟。该墓乐器种类丰富,有钟、磬、鼓、瑟等乐器组合,演奏阵容非常壮观。[17]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它体现出击奏与弹弦乐器的组合特色。
七、“六音”乐器组合
是含括击奏、吹奏与弹弦三大乐器种类的音乐大合奏。《尚书·尧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合。”“八音”,是指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八类乐器。所谓“八音克谐”,是指八种不同材质的乐器组合演奏,各种不同乐器发出的乐音配合流畅,融为一体,由此神人之间也就和谐合一了,这是原始宗教艺术的至高境界。而《诗经》最能体现这种大型交响乐器组合艺术的是《小雅·鼓钟》。其乐队规模庞大、乐器种类齐全,攘括古“八音”除土、木二音外,融击奏、弹弦与吹奏乐器于一体的“六音”乐器大组合。《鼓钟》诗的作者身份不明,创作时间难考,音乐表现的场合与目的也难知。但仔细揣摩诗意,似写一位诗人或乐官在王室衰微之际,流落淮上,重听钟鼓之乐,因而兴起了对周代发明音乐的“淑人君子”的无尽思念。不由想起了那次场面宏大、情景极为震撼的音乐大合奏:
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龠不僭。
钟、鼓、磬、瑟、琴、笙、雅、南、龠等三大类乐器来了一个激情澎湃、辉煌壮观的大融合大演出,堪称周代礼乐文化繁荣的一次全景展示。诗人的回忆恰好复现了王朝繁盛时期礼乐文明的盛况,充分体现出《诗经》大型交响乐器组合的最高水平,堪称《诗经》乐器组合艺术的巅峰。这样豪华壮观的大型交响乐器组合,可惜迄今西周、春秋音乐考古未有发现。战国初年的周代诸侯曾侯乙墓出土含编钟、编磐、鼓、瑟、琴、笙、排箫、横吹竹笛等多达八种共一百二十四件的大型乐器组合,可说是后来居上。[18]
通过上面的分析归纳可知,《诗经》音乐乐器组合形成了七种常见组合形式。其中又以瑟琴乐器组合、钟鼓乐器组合、金石乐器组合最具有代表性,而融击奏、弹弦与吹奏三大种类于一体的“六音”乐器组合则代表了《诗经》大型交响乐器组合的最高水平。另外,从《诗经》风、雅、颂音乐来看,也是各具特色。《国风》俗乐,乐器数量仅为8种,乐器组合较简单,其中瑟琴并用3次,瑟独用2次,说明琴瑟是深受民间喜爱的乐器,或合奏或独奏,其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雅》乐乐器种类多达16种,尤其鼓钟与瑟琴两类乐器使用频繁,“鼓钟”连言12次,“瑟琴”连言或并提5次。两类乐器经常组合演奏,多在宴飨、婚礼、祭祀等场合配合使用,再加上其他乐器的协奏,所以《雅》乐乐器组合登峰造极,音乐旋律复杂多变,音乐与歌诗的抒情性与仪式性兼备,体现出《诗经》音乐的最高水平。《颂》乐虽仅四首作品,但使用的乐器却达15种之多。尤其是钟、鼓、磬等金石之乐与箫、管等吹奏乐器的组合,形成周代祭祀音乐热烈隆重、庄严肃穆的音乐氛围,其典礼性、仪式性特点更突出。约言之,《国风》音乐抒情性更强烈,《雅》乐抒情性与仪式性兼备,《颂》乐的典礼性特点更出类拔萃。